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一)
去年下半年辞了职。在那之前我焦虑了很久。不满于现状,又不知道如何改变,觉得自己被困在原地,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看不到出路。慢慢地,一个决定在我脑海里萌芽:或许我该换个环境。
最后我决定试试去日本找工作。这当然有风险,但在上海几年我已经吃了不少苦,如果都是吃苦,换个环境说不定还会有点转机。于是我提了辞职,做完交接,享受了一段来之不易的自由生活。
即使辞了职,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也不想好好回顾我这几年的生活。有什么好回顾呢?其实就那点事,孤独和迷茫——我已经重复说过太多,说到自己也厌倦了。我怕这样下去我会变成一个无趣迂腐的人,实际上我已经有这种倾向:眼里只看得见自己身边二三事,脑子里只容得下自己那点碎碎念,除此之外皆是虚妄,狭隘冷漠,面目可憎。可我也不愿太苛责自己。我也不是因为想才变成这样的。
这当然是收获颇丰的三年。初入社会,爱情、友情、工作、疫情,我经历了许多。如果我装出一副受害者的模样说这几年只有痛苦,那毫无疑问是虚伪做作。苏州河边漫无目的的散步,周末夜晚隔着酒杯的谈天,深夜无人又安心的放映厅,还有那么多公园、那么多不曾知晓的街道马路,每一次出行,都像一场小小的冒险。我也认识了许多不错的人,他们身上或多或少都有让我钦佩的地方。他们中当然有人蛮不讲理、虚伪浮夸,但更多人友善温和,帮助了我很多。
但这仍然和我期望的生活差别甚远。小时候看电视,那些八十年代日本、香港的影视和歌曲塑造了我对城市生活的最初印象。那是忙碌的,却也充满活力,就连空气中仿佛也氤氲着悸动的情绪。如今我当然明白文艺作品是浪漫和虚构的,但我还是为我生活的死气沉沉感到遗憾。而那些快乐的时刻,就像在水下长久潜伏的间隙,偶尔有机会浮出水面稍稍喘息。可那些时刻太过短暂,转瞬即逝,实在无法抵抗大部分时间的痛苦。
(二)
我趁着辞职后的空闲去拜访了几个老朋友,顺便旅游。工作三年来,我还一次没有旅游过。我去了南京、杭州、北京,都是故地重游,可过去来这些地方,我只是单纯的观光客,如今它们成了我朋友们居住生活的城市,我和它们有了不同的联结。
和朋友散步聊天,聊起我们过去的生活。为何那些日子那样快乐?我说,那时我们就像在河边散步,一直没有踏进河流。我们只是在岸边远远望着河面,仿佛我们哪里都可以去,哪里都对我们敞开,我们可以过任何一种生活。那是一种尚未出发的余裕,是自由的幻觉,我们看待世间就像是暴雨天躺在被窝里看电影,安心又快活。可如今我们踏进河流,并且深陷其中。我们似乎再也看不见四周,眼前又漆黑一片。我们被困在这里。
朋友说,觉得我很多时候可以不必想这么多。我总是爱回顾过去、反思自己,并且带着同样的眼光看待周围的一切。的确,我似乎一直过着一种英文小说式的生活。那是一般过去式的,现在这一秒钟,在我落下这个句子时已经成了过去。我总是这样看待时间和生活。我从没试过过一种现在进行时的生活。
去北京的那几天过得很开心。上次去已经是许多年前,印象模糊。这次漫步其中,那些二环内的古旧破屋,那些唱片店,那些胡同老树,那些在后海边散步锻炼的老人们,惬意悠闲,和上海就像两个世界。但当我踏上早晚班地铁,当我被挤得喘不过气时,我知道其实哪里都没什么不同。
住在北京的是我一个多年的好友。我知道她过去的许多烦恼,可过去了许多年,却又像一转眼,如今我坐在她崭新的家里,虽然是租的房子,却也打理得井井有条,充满生活气息。她的小狗趴在我脚边眼巴巴看着我,想要点吃的,她男朋友坐在我对面,隔着热气腾腾的火锅和我说笑。我一时觉得欣慰又恍惚。那些烦恼和痛苦连同记忆一起,都已经成了遥远的过去,而我的朋友已经有了不错的生活。
(三)
回家后,我过上了很规律的生活。平时学日语,周二四六下午去健身,一三五晚上去医院接做完透析的爷爷。在那里我又认识了不少人,都是病人或病人的家人。医院是悲伤的地方,行走其中总让我慨叹生命的脆弱。这里每个人背后都有许多沉重的故事——丈夫早逝、儿子年纪轻轻就身患重病的单身女人;丈夫患病做透析,儿子三十多岁了却不幸从高处摔下、脑子摔出问题无法再正常工作的女人,每天白天要打工,晚上还要来接丈夫;自己身体不好,却必须每天接送岳母的男人,妻子在外地打工,女儿正为找不到工作发愁;还有更多住在下面乡镇的人们,每晚做完透析,无论刮风下雨,他们都要骑摩托或三轮走很远很远的路回家。幸福的家庭彼此相似,不幸的家庭各有不同,而那些不同的家庭,最后总是在医院相遇。
可当去医院变成我日常的一部分,我才发现这里并不只剩悲伤。当这一个个人们从不幸的故事里走出,和我打招呼、说话,我才明白他们并不需要同情。他们的确不幸,但还是努力活着,过着自己的人生。那个丈夫早逝、儿子患病的女人,从来都是一副温柔的笑脸,见谁都爱聊上几句。有一次我看见她趴在桌上,对着手机在笔记本上抄写圣经。那个丈夫患病、儿子脑袋摔出问题的女人,却也最是话痨,让等待的大厅里变得吵闹。那个每天来接送岳母的男人,临近过年时喜笑颜开,说女儿回来了,也找到一份工作,虽然挣得不多,但好歹安定了下来。他能把接送老人的任务暂时放下,回乡下钓鱼了。而更多的、许许多多我熟悉或不熟的人,没有人整天哭丧着脸,这里笑脸总是比哭脸多。
这并不是某种先抑后扬的叙事。现实的生活往往没有顺序,只有并行的状态。其中一方面是不幸的、悲伤的,可同时,人们还是寻找慰藉,尽力生活。这种姿态让我动容。
我推爷爷坐轮椅回家,路上奶奶总是跟在我身后,和我说话。直到我上初中之前,我一半的童年时光都是在爷爷奶奶家度过的,但如今我已经有太多年没好好和他们说过话。现在终于有了机会,奶奶每天都说个不停。爷爷身体衰弱,不咋吭声,只是偶尔搭腔。他们的话题,大部分时间是在回忆过去。我无法想象这是怎样的体验:当你每天都被困在医院,死亡已经并不遥远,你能做的,只有不停回忆,仿佛在你前方的不是未来,而是往昔。
有一天推爷爷出医院时,遇到了一个中年女人。女人看着我,惊讶地说毛毛都长这么大了。告别后,奶奶和我说,我小时候这个女人就住在我们家斜对面。我刚出生的时候,她们许多人就都第一时间过来看我。那时她对奶奶说,等你孙子以后上大学,一定要叫我喝喜酒。奶奶说她当时想,天妈妈嘞,上大学,那是多么遥远的事啊。我说的确遥远啊,十八年,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实在太久了。是啊,奶奶说,但又这么快,转眼我跟你爷爷都这么老了。
(四)
拖了很久才写了这篇东西。本来是想惯例地在年底写一篇年终总结,但头一回心生强烈的抗拒与疲乏,不想再总结什么东西。结果到了今天,才随性写了些碎碎念,记下这小半年的一些事情。
总结和记录,我过去习惯做这些事情。语言影响大脑,也让我更关注过去。但或许该做些改变了。我们不是只有现在吗?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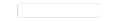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3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