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引言:前一阵子参加了大学毕业十周年的同学会,惊闻兄弟班中已有同学因病故去。想起在2005年秋的那个下午,和他两人在学校边的破旧台球厅打台球,不胜唏嘘。
寒假一过,白茹看顾生明显比过年前瘦了,人也老是心不在焉的,她问他怎么了,顾生只说是忙、累、压力大。
“工作找的不顺心?”晚饭的时候白茹小心翼翼地问,他们俩打算毕业之后就留在南京——南京虽然不比北上广深,但也是个机会相对比较多的城市。
“嗯。”顾生不太想说话,他把铝盘推在一边假装看手机,但是白茹知道他在想别的事情。自去年九月他开始找工作以来,顾生已经参加过五次笔试四次面试,但每次都被公司刷下来。这次他给南京西门子投的简历有了回应,今天他去参加了笔试,不过从他现在的反应看起来,估计还是不成。
“要不,你和我一起去考公务员吧。”白茹觉得考试也是条路子,毕竟作了十几年学生,考了十几年的试,这也算是一门本事。
“再说吧。”顾生喝了一口茶,“晚上我还得去参加一个校招,你别陪着我了,安心复习。”
白茹点点头,考期临近,她也的确没什么时间和顾生约会。不过每天两个人抽个空出来坐一坐,谈两句,她就觉得很好。虽然早几个月顾生还有抱怨,但是他也是分得起轻重的,毕竟关乎到两个人的未来。
回到租住屋里,白茹立刻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一只手机,一个复习题库软件,一沓从文印室里顺回来的草稿纸,一杯水就是她今天晚上的全部内容了。
再抬头时已经九点,顾生还没有回来,不知道今天的校招会怎么样,希望能好。她出了一会神,决定再做一套模拟卷,做到十点半的时候手机忽然震了一下,白茹不想切换出题库界面,就一直坚持到十一点把卷子全部做完。原来是顾生的消息:今天有饭局,晚一点回来,早点睡。
白茹回:知道,别喝太多。
然而改改卷子,看看错题再背一篇申论就已经是十二点半了,门外哗啦啦钥匙响,“是顾生吗?”白茹问。
“是我,茹茹。”顾生在外面闷声闷气地答,他打开门,黑着个脸,“你怎么还没睡?”
白茹笑道:“我在等你。没有酒味,今天怎么这么乖?”
顾生“嗯”了一声,然后钻进卫生间:“我洗澡了,你快睡吧。”
白茹想想是该睡觉了,整理好床铺躺进去,扭开床头灯看起了书。等到顾生钻进被窝,白茹立刻靠上去:“今天怎么样?都好吗?”
顾生摸着白茹的头发什么话也没说,白茹开始亲吻顾生的胸口,顾生稍稍用力把她推开:“快睡吧,很累了,很累了。”
入春的时候,白茹有点咳嗽,反反复复不见好。顾生说要带她去医院看病,但是她怕花钱,只是买了咳嗽糖浆、罗汉果回来自己治,为了这个事情两个人还吵过一架。最后白茹答应等考完试就去医院,顾生想想考期已近,这个时候再和她较真也不太好,就顺了她的意思。
在鼓楼医院排了一上午队,白茹说:“在我老家医院里都不怎么用排队。”顾生感慨说:“大家都往大城市跑,你老家都快成空城了。”白茹说他讲得太夸张,但想想过年回家看到的景象,似乎又没什么不对的。
“老家还是发展的太慢。”白茹说,并想起了申论的考题,然后又想到这次考得不错,应该能发挥出平时复习时的水平,甚至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了——只要同一个岗位的竞争者里不要出现太过厉害的人,面试总是能进的。不自觉地笑了起来。
“傻笑什么。”顾生从包里拿出个菠萝包,“饿不饿?”
白茹最近都没什么胃口:“渴。”
系统喊了白茹的号,顾生收拾好东西陪她一道往诊室走,看外面挤满了人,大家都想插队的样子,顾生喊了起来:“我是一百二十六号!”然后站在前面挤进人群,好不容易抢到板凳让白茹坐下。
医生问了白茹的情况,又听过肺音,然后开了胸透单子让白茹去做检查。
“等了半天,问了十秒钟。”白茹苦笑一声,这也是她不爱来医院的原因。顾生什么也没说,赶着去交了钱,领了做胸透的号,带着白茹排队。等做好胸透、领到片子再回到医生这里,已经是下午三点,那个菠萝包也叫两个人分着吃了。“晚上带你去吃好的。”顾生对白茹说。
医生看了胸透结果,又问了一遍情况:胸片上没有什么异常,大概是支气管炎,但是咳嗽的时间有点长了——先按支气管炎治吧,下周来复查。
医生是很负责的医生,从他的经验出发,这个事可大可小,说白了全看运气。他想了想还是谨慎一点的好:“没有咳血的症状吧?”
“没有。”白茹回答。
“记得下周来复查。”
两个人晚上去吃了牛肉锅贴。
月底的时候成绩出来了,白茹果然进了面试,两个人很开心。顾生问白茹要不要报个面试培训班,白茹也觉得有这个必要,但是询问价格下来,便宜的也要两三千:“一万多的那种虽然不过包退,但是过了就得把钱全给他们。”白茹是个节俭的人,小时候穷怕了,“一万多,够咱们一年半的房租了。”
顾生想了想:“两三千咱们还是出得起的,报吧,为了你的将来。”
白茹又考虑了下:“我还是先找找有没有自助学习的团体好了。”学生还是比较喜欢吃免费的午餐。
一起公考的同学里果然有张罗这个事的人,后面还有热心的老师作支持,白茹就加入了他们。顾生说白茹这么上进,自己不能干看着,也要努力找工作,于是两个人又是一整天一整天的碰不到面了。
时间飞快过去,白茹面试那天顾生一直在考点外面等着,等最后一个人垂头丧气地出来,两个人终于等到了白茹通过面试的消息。他们高兴极了,破天荒地去吃了一次金钱豹。晚上白茹一边哭着一边搂住顾生狂吻,顾生也很激动,但体力很快耗尽,他觉得自己这样有点扫了白茹的兴,但白茹依旧很开心。
然而命运总爱捉弄人。
月底白茹的入职体检报告出来了,肺上有阴影。
拿着再检不通过的报告,白茹只觉得耳边“轰”一声响,随后天旋地转、一切不知。
醒来的时候白茹已经躺在病床上,顾生坐在床边握着自己的手,他的脸上全是泪痕。“我怎么了?”白茹问。
“你,贫血晕过去了。”顾生的下巴一直在抖。
白茹心想,哦,贫血,还好,自己是有点贫血。
但她很快知道自己患的是边缘性肺癌。她本以为癌症离自己很远,没想到22岁抽中了这根坏签。她先开始拒绝治疗、吵着要出院,顾生好歹把她劝住,白茹又要求顾生一定不要通知自己的家人,顾生答应了她,但是这个时候他们两个人的存款已经见底。
“你告诉我家里也没有用啊,”白茹哭着,“我弟弟妹妹们还要上学,家里没有钱的。”她说还是让她出院吧。
顾生说他有钱,叫白茹别急:“医生也说看切片结果还是好的,只要尽快手术就会痊愈。”白茹觉得这个话就像在黑暗中的一束光。但是顾生没有告诉她的是,医生也说了手术费用大概在三十万。
三十万啊。顾生咬咬牙,虽然三十万在这个城市只是浦口乡下一间小房子的首付钱,但他们也是出不起的。不光他们两个,两家人把全部家底凑起来大概也凑不出这个数。
怎么办?
在黑漆漆的楼道里,只有顾生唇边一点火星在一闪一闪,他忽然想到:抽完身上最后这两根,他必须得戒烟了。
第二天顾生打电话把情况告诉了白茹的父母,白茹一边哭着一边无力地抬起胳膊打顾生,并用家乡话骂道:“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顾生扶着白茹怕她从病床上翻下来。
“你需要人照顾。”顾生一边抖着一边说,“我得去筹钱,你需要人照顾。”
三天后,白茹妈妈从宜宾赶过来,那个瘦小的中年女人穿着大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才能见到的衣服。她背对着顾生从自己内衣夹层里掏啊掏的掏出一沓现金塞到他手里:“家里的娃儿还要人,家里的地还要人,家里只能凑出这么多了。”顾生接过钱,大概一万不到,有整钞有零票,他带着白茹妈妈去缴费处把钱交了:“阿姨,钱我会想办法,但是茹茹离不开人照顾啊。”
白茹妈妈一脸痛苦,她当然知道大女儿需要自己。可是她明天就得回去,因为家里还有四个人要继续活着,而背在身上的债还不知道要还到什么时候。
“阿姨,你不去看看茹茹吗?”顾生握着白茹妈妈的手,他已经是在哀求她了。
白茹妈妈站在病房外面,她不敢走进去也不敢往里看——她可以进去,但是进去以后说什么呢?说我明天就要走吗?她觉得如果自己对大女儿这么说了,她就会立刻死在那儿。
“茹娃儿就托付给你了,你可别抛下她不管啊。”她哭着。
顾生什么话也说不出来。
顾生打电话向家里求救,家里的意见很大,顾生火了:“我想救她!对!就是我死我也想救她!”
顾生是家里的独子,他的父母都来了,住在顾生和白茹之前租的小屋子里。他们带来了两口子卖鸡蛋饼攒下来的七万块。
“妈,帮我照顾好茹茹。”顾生妈在医院一直陪着白茹,可她的眼神冷冰冰的从来不和白茹多说一句话,白茹看到她经常在哭,但她不敢问顾生妈妈到底为了什么在哭。
顾生找到自己的朋友,他想借钱,朋友们都是仗义的,可是学生的力量是有限的。有人提出来可以去募捐,他们从学生会的仓库里找来了招贴板,顾生一字一泪的把情况写上去,之后班长召开班会,大概募到两三千块。一群人又说去校园里募捐效果会好些,班长就带着他们一起去了。来往的学生多有停下来看他们的,可掏钱的是少数,等他们收到第二张一百块的时候,校保卫处来赶人了。
保卫处长问谁是领头的,顾生说是自己,又问有没有备案过,顾生说没有。他要把顾生带去保卫处处理,其他的学生不干了,都护着顾生。几个保安来拉顾生走,十几个男同学就挡在顾生的前面,两边越吵越大声,聚集起来的人也越来越多,等班主任赶来的时候现场已经停了两辆警车。
班主任老张把人领回去,劈头盖脸把班长一顿骂:“你们怎么想的,出了这种事不先问我?”他从兜里掏出一千块钱,“拿去先用!”
等火气消了,老张把顾生几个人又叫到一起:“学校里搞募捐得走流程,材料我已经给送教务处了,不过那帮爷爷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批下来,所以这事咱们还得想点别的办法。”几个人商量着应该向社会寻求更多帮助,有人提议找媒体,老张说正好自己有个侄女在十八频道做采编,可以找她看看。他当即约了侄女过来,那姑娘风风火火地赶到——大学生得绝症的事情虽然时常有,可这种青年情侣不离不弃的却是很少见。
小张姑娘是个情感丰富的人,顾生才把事情说了个一二,她就已经哭得稀里哗啦。小张又打电话给自己师兄,说手上有个新闻可太感人了,又把他师兄招来,他师兄是在生活频道九点档情感节目组里干副导演的。顾生又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遍,副导演再请示导演,导演让他连夜赶个策划出来,第二天就开始录制。
眼看着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老张心里也舒服了很多,他问清楚了白茹住的医院,后面又陆陆续续送了点钱去。钱都是顾生妈妈收的,不过也只是过过手就被立刻拿去付了医药费,收据都夹在小账本里,这是她多年卖早点的习惯。
录完节目顾生感觉浑浑噩噩,心里直犯恶心。他开始慌神,坐在一边充当观众的顾生爸爸立刻冲上去扶住顾生,他问过导演下面已经没有顾生的镜头,搀着顾生往外面走。顾生稍缓过来点才发觉自己正趴在父亲的背上,他一路把自己背到了医院:“你觉得这样值得吗?”
顾生咬了咬牙,可始终没有说话。
节目的宣传效果比预期的好:给节目做冠名的那家企业正是两个年轻人母校里同院教授的三产。公司找到老张及节目方,愿意出资一百万帮助白茹,但是要求电视台再做一期以采访这位教授为主题的特别节目。电视台也想顺水推舟把这件事的影响做到最大,两方一拍即合。过了一周,顾生在媒体中心接过那张象征捐款的巨大支票,并第一次在那么近的距离看到自己的副院长、院长、副校长、校长、教育副局长、教育局长、副市长、市长、省教育厅主任等等等等一些他以前没见过或者只远远见过的大人物。
“很成功,很成功!”导演用力握住顾生的手上下摇着,“事体能有这样的结果实在太好了!这也算行善积德了吧?啊?哈哈哈。”周围的人也跟着笑起来,“但是顾同学,还有一件事体要跟你讲啊,这个钱,就是这个一百万啊,虽然是已经打给你了。但是‘瑞源制药’只承诺承担白茹同学的医药费用。也就是说啊,一切为救治白茹同学的钱都可以从这一百万里支出,但是啊,顾同学,治病剩下的钱,你到时候是要还给公司的,你懂毋啦?”
顾生点点头。
“明白就好!明白就好!做善事很好嘛!但企业也要生存的嘛!”他把顾生还有顾生父亲带进一间办公室,桌上放着两份协议,“就是刚才那个事体,你看看没什么问题就签一下吧。”
顾生看也没看就要签字,顾生父亲拦住他,自己仔细看过一遍才让他签。
“你们票据什么的,一定要保留好,保留好。”导演再三叮嘱。
顾生爸爸想叫一辆出租车,被顾生阻止了。两个人往地铁站走去,顾生爸爸几次想说什么,可都没有开口,走出地铁站的时候,顾生说道:“爸,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顾生爸爸停下来看着他:“咱们也需要钱。”
顾生黑着脸:“我可以再等。”
顾生爸爸浑身颤抖着:“医院那边说已经有合适的骨髓了!”
“这钱是用来救茹茹的。”
“阿生!”昏暗的路灯下面,顾生爸爸大吼着,“你不要命了吗!”
晚上顾生给白茹打电话:“茹茹,钱筹到了,很快就能动手术。”
电话那头白茹喜极而泣。
“不要哭,茹茹,不要哭嘛。”
“我给你唱首歌吧?”
“你爱听的那首,好不好,茹茹?”
“月亮船呀,月亮船,弯弯的船在银河里面,如今就像童年的梦一样,就像,就像。。。”顾生泣不成声。
当夜顾生爸爸买了两张回铜陵的车票,临走前顾生打了三十万给妈妈,让她尽快帮白茹联系手术。
“她要问起你,我怎么说?”虽然她不愿意和白茹多说一句话,可她还是害怕白茹会问自己,顾生妈妈对她的感情十分复杂。
顾生沉默了一会:“就说家里出事了,过几天就回来。”午夜的南京站,安静极了。
“她要问出什么事呢?”
“就说,”顾生沉默了一会,“说什么也别告诉她我的事。”
“阿生,出了事有爸爸妈妈担,但是你不告诉她她会恨你一辈子的。”
“妈,字是我签的,事是我做的,我已经害了茹茹,我不能再牵连她。恨我就恨我吧,妈,我也想活下去。”他挂断了电话,火车来了。
电话那头的顾生妈妈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只是一瞬间她心如刀割。她不动声色地把三十万划进医院的账户,医生表示下周就能安排手术。她把这个消息告诉给白茹,白茹非常激动:“可是阿生什么时候能回来?我想他陪着我。”
顾生妈妈说阿生的舅舅准备给他安排一份工作,机会难得,大概得再过一阵子才能回来:“你放心,我问了医生,你这不算特别大的手术,不会有什么问题。等你养好了阿生也就回来了,他一定会回来的。”她这么说着,心中却在算顾生的手术日期,大概会是在白茹前面吧。
因为舆论宣传的继续发酵,医院减免了白茹部分的后续治疗费用,这时顾生妈妈账户里还剩三千多,这让她心里面一块石头落了地。“瑞源制药”的人在白茹手术后来过两次,名义上是探病实际上就是来查账的,顾生妈妈把存下来的缴费收据拿给他们看,算下来一共是三十五万六千多:“现在孩子还住在医院里,等她出院了一道结,估计不超过三十六万。”话虽这么说,她心里也是害怕极了,她也想过一逃了之,可逃去哪呢?顾生还在合肥医院里躺着,逃到哪也没有用。
走一步,看一步吧。
白茹出院之后住回到了学生宿舍,顾生妈妈要照顾她也住了过去,“瑞源制药”的人跟了过来——这时顾生妈妈才说钱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哪去了?”那个代表的脸一下子黑了。
“给我儿子带走了。”这是顾生和妈妈商量好的话,不能说拿来给自己看病,不然顾生妈妈就有隐瞒、诈骗的嫌疑,而白茹也会有嫌疑。
“带走了?”那人追问,“带去了哪?”
“好像是回老家了。”顾生妈妈说,“字是他签的,钱是他管的,也是要用的时候才划给我,你们可以去找他。”
代表大怒,说了很多难听的话,可他也只是职员做不了主,立刻联系了公司。公司老总也就是那个教授联系了老张和当时促成这事的节目导演,几个人风风火火地赶到学校,顾生妈妈还是这套话。
如今她倒坦然了。
老张来做顾生妈妈的工作,他动之以理晓之以情明之以法,可顾生妈妈还是不松口。眼看老张气得都快要哭出来了,那教授倒很冷静:“说到底就是为了钱,哼,这种事儿我看得也很多了。不谈了,先报警。”他气哼哼地走了,留下自己的助手处理这事。
警察一来,白茹那边也瞒不住了。女警官给卧床的白茹做笔录,白茹又惊又怕,回答前言不对后语,忽然歇斯底里起来,愤而抓起床头的东西向警察砸过去,可床头除了个手机和几本书以外也没什么可抓的。外面的顾生妈妈听到里面动静不对,立刻冲进来:“你们别冲着孩子!冲着我!冲着我来!”
白茹看到顾生妈妈忽然愣住,一口气喘不上来昏了过去,站在外面的医生赶紧过来实施急救。顾生妈妈和警察都被赶到走廊上:“你们去找顾生,去找他。”
等白茹醒过来,宿舍里又只剩下顾生妈妈和她两个人。白茹痴愣愣地看着她:“你们是不是一直瞒着我。”
顾生妈妈咬咬牙,眼泪刷地流下来:“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
警察找到顾生的时候,他正躺在病床上挨排异反应。
顾生爸爸一直在医院里陪着他,他承认事情都是自己的主意,过年的时候顾生被查出得了白血病:“我们没本事,没钱给他治。”他捂着脸呜呜的哭。
“瑞源制药”的捐款全扔进去了还不够,顾生爸爸把巢湖的房子卖了、四处借债总算又筹到一笔钱,现在他一边照顾着顾生,一边在病房里偷偷卖鸡蛋饼勉强活着。
“钱是我拿的。”骨瘦如柴的顾生挣扎着,“字是我签的。你们抓我。”
警察为难了,抓谁?抓他?怎么抓?
情况传回南京,一片哗然。
白茹不愿意再见到顾生妈妈,她把自己的母亲从宜宾又叫了过来。不过事情因白茹而起,所以白茹妈妈也被喊到了公安局。
两位母亲的第一次见面,竟然是在公安局的会议室里。顾生妈妈看到白茹妈妈感觉有点恍惚:如果没这事的话,两个人的初会应该会是在自己儿子的婚礼上,命运啊。
白茹妈妈却突然跪了下来:“我的娃儿全靠你家阿生,我家娃儿对不起你。”顾生妈妈不知所措,她搀了两下没能把眼前的这个女人搀起来,只好也跪下去:“我家阿生全靠茹茹才能活下去,是我们对不起茹茹。”两个中年女人哭在一起,心里的委屈全倒了出来。
局长、副局长、负责警官、瑞源制药老总、老张、导演都觉得于心不忍,那导演先嘟嘟囔囔说道:“假设那小伙子一开始就说清楚,也许两个人的问题都解决了,唉,不巧不巧。”
老张也觉得惋惜,虽然四年来和他们打交道不多,可他觉得两个孩子都是好孩子,就是顾生的脾气实在太倔了:“怎么能这样处理问题呢,唉。”
教授咂咂嘴,他知道这一百万是收不回来了,他心疼钱,可心里面又盘算自己能从这一百万上面捞回多少其他利益。
负责警官忙来拉地上的两个人:“不要这样嘛,我们是为了解决问题才坐到这里的,你们这样怎么解决问题嘛,快起来嘛,起来嘛。”两个女人才止住悲声。局长一看气氛刚好,于是出声来做调解,最后“瑞源制药”决定不再追究捐款,只是要求电视台免掉企业两年的节目冠名费,两方面再扯皮却和两个孩子及两个家庭都没有什么关系了。
白茹在南京休养了一阵,后来随母亲回到四川。
顾生熬过了排异阶段,熬过了恢复阶段,身体一点点好起来,当然他一时还是离不开人照顾,于是一家人决定在合肥重新开始。
顾生的毕业证是妈妈代他去领的。顾生问白茹现在好不好,顾生妈妈说没见到白茹,打听说毕业证什么的都是学校给邮去的,人已经回四川了。顾生其实知道会是这样,他曾给白茹打过几次电话,开始的时候没人接,后来是“正在通话中”,最后一次接电话的是一个讲南京话的女人——白茹已经把号给退了。
十周年同学会的时候,白茹从四川赶回南京。所有人都刻意避开顾生的话题,似乎已经没有人还记得他,他们笑着、闹着、喝着酒、唱着歌,只有白茹一人静静地、静静地凝望着窗外金陵的深秋。
(文中配图是之前答应机核某同学的水果蔬菜核磁共振扫描图,图文无关)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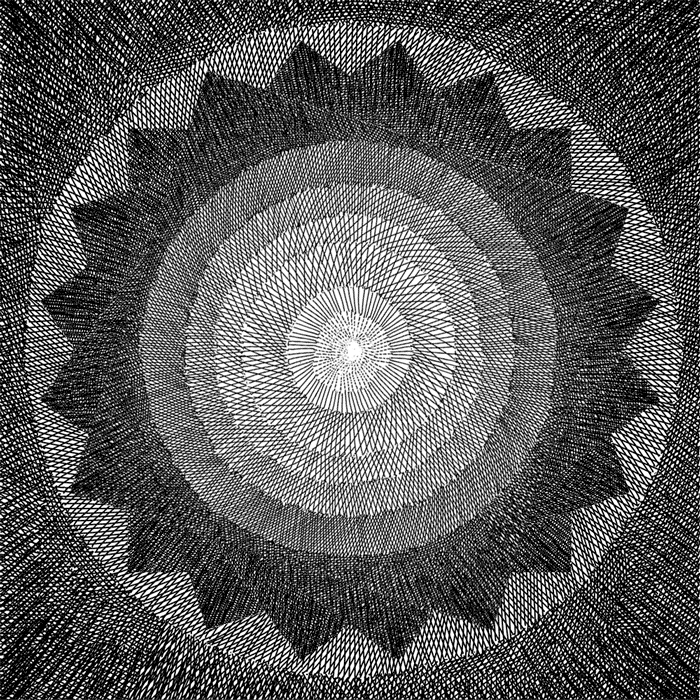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9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