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一个让我痛苦的游戏
一个让我痛苦的游戏
想写这篇文章的缘起是最近玩了一款叫做《星礼研究所》的游戏。
这款游戏是制作者的处女作,刚上架 Steam 就被称为“写论文模拟器”而喜提微博热搜。在游戏中玩家化身为一个刚考上心理学的研究生,游戏的通关要求就是发表论文。为此,整个游戏流程按照“查找文献—阅读文献—招录被试—进行试验—跑数据—写论文—投稿”进行。
游戏中不乏一些戏谑元素,比如此作中用“发量”替换了常规的生命值,跑数据消耗发量,写论文消耗发量,甚至可以用发量向好盆友购买数据和论文;心情抑郁的时候,到厕所去“哭一哭”,不仅可以排遣抑郁心情,甚至常常有意外惊喜,获得文献、被试、数据等资源。
除了某些让人会心一笑的设置,整个游戏只能用“过分真实”来形容。比如有时候在游戏中花时间读文献,会有一些读了等于白读的垃圾文献;招募被试的时候需要苦口婆心展现自己的积极一面,但还是被质疑研究有什么意义;通宵跑数据结果计算结果不显著只能就地重来;投稿给前沿杂志,结果论文被拒需要一切从原点开始。
这种真实,让游戏体验只能用痛苦来形容,因为这个游戏有着大量耗人心力的重复。如果前期 15min 还是一种新奇诱导我探寻这个游戏,之后我则只能用一种近乎苦行的心态来支撑自己完成接下来 1h 左右的游戏内容。
无他,这个游戏在某种程度上和真实的科研生活太接近,那种漫漫长路、无尽轮回的痛感,我想每一个人都或多或少感受过。
《星礼》截止目前在 Steam 上收获了“特别好评”,我也同意这款游戏本身值得被更多人看到。大部分玩家赞美它的真实,但是于我而言,在游戏过程中,我不断想起前段时间机核的那期播客《圆桌辩论:好玩,是不是一款好游戏的必须条件》。如果要站一个立场的话,我觉得游戏还是必须要好玩,一种在抽离题材、美术、音效等外在表象后有趣的内核,一个经得起考验的玩法。
我欣赏《星礼》这种强烈的现实关怀,它以一种黑色幽默的形式反省了学术生活,但题材和立意上的优秀并不能掩盖其玩法苍白的现实。
“真实“固然优秀,可我们又该如何看待这种”真实“所带来的糟糕的游戏体验呢?如果我们在游戏中的体验与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别无二致的话,我们为什么又要在游戏中再体验一遍呢?
这就是我想在这篇文章中探讨的主题:我们为什么想要在游戏中复刻现实,并尝试探讨一个模拟现实、反映现实或反思现实的游戏,是否需要平衡现实的疼痛与游戏性乐趣本身。
乐趣或新奇
乐趣或新奇
游戏的目的以及现实与游戏的关系,可以用一个称为“Magic Circle”的概念来进行探讨。此概念最早由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提出。
赫伊津哈将游戏视为一个与现实抽离的“魔术圆圈”。在圆圈内有独立的规则,人们在其中活动,只为了获得与庸俗的日常生活完全不同的快乐与投入,即柏拉图意义上的审美体验。恰如柏拉图认为,人们玩游戏,是为了在游戏中进入一种与当下心境不同的状态。
如果要总结游戏的形式特征,我们不妨称之为一种自由的活动,有意识脱离平常生活并使之“不严肃”的活动,同时又使游戏人全身心投入,忘乎所以的活动。——赫伊津哈
“心流体验”,是人们在游戏中最常寻求的乐趣,这通常表现在一些竞技类游戏中。从传统的棋牌、赌博、体育竞技,到电子游戏 MOBA、CCG,注意力的高度集中与全情投入,是将人们从现实中抽离出来的方法。但这种抽离也并非完全隔绝现实,陪领导打球和与兄弟打球显然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心态,而友谊赛和正式赛也会让比赛者选择不同的竞争策略。
游戏所处的社会生活背景依然深刻影响着游戏世界。
想要逃离庸俗日常的渴望以及对他人人生的好奇,则是游戏但另一重吸引力。这可以解释 RPG 游戏的魅力。我们可以在游戏这个“魔力圆圈”里成为了他者,而无论在现实中你是男是女,年龄几何,育碧都能让玩家参与伯罗奔尼撒战争,目睹古希腊的辉煌与瓦解,而在法国大革命期间则可与拿破仑谈笑风生;任天堂给玩家一个“一辆摩托车,驰骋海拉鲁”的机会;小岛则让玩家成为拯救全人类的最帅快递小哥。
但在一些情境中,游戏也并不完全与现实分离。比如 Nordic Game Jam的组织者 Jesper Juul 就认为,游戏空间并非是一个圆圈,而是动态“拼图”。游戏空间的边界会依据现实而发生变化,以期能够与现实规则拼接在一起。我们在游戏中依然无可避免的受到自己在真实世界中的社会、经济、文化背景影响。这在角色可塑性极强的 MMORPG 中最为明显,尽管利用网络的匿名化玩家可以在游戏中塑造一个完全与现实中不同的自己,一个替身(Avatar),但是游戏中的抉择,诸如做一个“输出”、“T”或“辅助”依然反映着玩家本身的性格特征。对于这类游戏来说,人们只是在寻求一个“假如人生能够重来”、“探寻另一种可能的自己”的尝试。
所以总结来说,游戏总是不可避免地与现实交织在一起,但好游戏必须为玩家提供超出现实的纯粹游戏性乐趣或一种新奇的游戏体验,能够让玩家能够全情投入,或满足过另一种人生的好奇心。
以游戏反观现实
以游戏反观现实
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韦伯
复刻现实或者模拟现实的游戏当然有意义。一个可能的解释来自于阐释人类学。以克利福德·格尔茨为代表的阐释人类学者认为文化来自于解释,我们以高出现实生活的姿态对生活本身进行反思,才能获得意义。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阅读诗歌和小说,观看戏剧和电影。《李尔王》与《罪与罚》是“死亡、男性气概、激情、自尊、失败、善行和机遇”的隐喻,《权力的游戏》和《指环王》是“权力、欲望、战争、挞伐、尊严和人性”的再现,我们需要在艺术中看见生活。
再回到《星礼》本身,游戏对现实反观,像是一种“无趣的抽象”。游戏所采用的一系列 QTE 玩法常常让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异化了的富士康流水线工人,机械而索然无味地看着屏幕又点击鼠标。除了玩法的枯燥,还有对现实刻画的片面。我臆想作者想在游戏中表达的也许是工匠精神或持之以恒,是“我们不能因为早高峰的地铁似乎每一趟都很满而拒绝上车”,是不能因为畏惧而放弃事业,毕竟没有哪件事是尽善尽美的。这在一些玩家评论中也被指出。但毕竟科研活动并不是如作品所表示的那样枯燥,学术所带来的“智识上的些许清明”、灵光一闪时的“惊喜”都被去掉了,这让我感到遗憾。
游戏当然也是一种用来反观的媒介。游戏性与表达之间如何平衡,并没有普适的客观标准。但媒介的表达方式有差异与高低,但最重要的是,表达本身不能够以完全牺牲游戏性为代价。这也许就是 2019 游戏届年度之争“某步行模拟器好不好玩”的核心所在。
I

The Ordinary
50 人关注

有感而发
4975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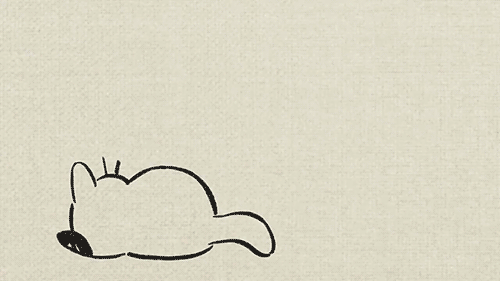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36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