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什么是哲学?
什么是哲学?
广义上的哲学是思想史,而本文所说的哲学是由维特根斯坦定义的:哲学不是一种学说,而是一种活动,其目的是对思想做出逻辑上的澄清。维特根斯坦认为,很多哲学问题之所以存在,究其原因是人们对语言的误用。不应构筑理论去处理这些问题,而是要澄清语言。只要我们搞清楚我们究竟在说些什么,哲学问题将被消解。
因此,面对“游戏是艺术吗”这个问题,澄清何谓游戏以及何谓艺术,是至关重要的。相信在这两个词的意义在我们面前清晰显露之后,这个问题将会迎刃而解。
什么是游戏?
什么是游戏?
在阐释什么是游戏之前,我们不妨先引入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概念:
看一看……我们叫作游戏的那些活动。我是指下棋、玩牌、球赛、奥林匹克竞技等等。它们共有的东西是什么?——不要说:一定有某种它们共有的东西,否则它们就不会都叫作“游戏”,而是要观察并确认一下是否有某种它们都共有的东西——因为如果你观察它们,你不会看到某种它们共有的东西,而只看到一些相似、一些关系以及整个一系列相似和关系。……这种考察的结果是:我们看到一个由部分重合和交叉的相似性组成的复杂网络……我想不到有比“家族类似”更能刻画这类相似性的表达式了;对于一个家族成员之间的各种不同的类似性来说:体格、面貌、眼睛颜色、步态、脾气等等等等都以同样方式部分重合和交叉着。——我要说,“游戏”构成了一个家族。(《哲学研究》,66——67)
维特根斯坦发明“语言游戏”来解释语言:语言并不具有一个单一的本质,并不能用一句简洁清晰的话来定义(维以《哲学研究》的论述中反驳其前期《逻辑哲学论》对语言单一本质的论述)。语言是对语言游戏们群体的称呼——“语言游戏A”、“语言游戏B”、“语言游戏C“等等——以各种不同的方式相互关联着,体现着一种家族相似性。我们用语言来陈述、告知、命令、威胁、诅咒、欺骗、抒情……等等,遵循着许多相互关联的规则,每一套规则就是一种语言游戏。
这样阐释语言,维氏的用意在于反驳他自己早期著作的意义观:《逻辑哲学论》中,词的意义就是它所指示的客体;而《哲学研究》中,他主张表达式的意义乃是它在构成语言的许多不同的语言游戏中所能派上的用场——词意即用场。维氏选择以“游戏”命名“语言游戏”这一概念,原因之一是游戏皆有规则,而语言的种种用法也皆有规则。无巧不成书,本文所要阐释的词语之一也是“游戏”。
首先,我们从用场的角度阐释“游戏”。西蒙说,“玩游戏的都是朋友”。网友们说,“在机核,你甚至可以聊游戏”。我们都知道,这里的“游戏”是指电子游戏,或称视频游戏,也就是Video Game,而不是别的什么。像桌游、卡牌、橄榄球、飞蝇钓这些机核的主营项目显然不是我们正在争论的“游戏”;下棋、玩牌、球赛、奥林匹克竞技等等更广义的游戏,显然不是此时此地我们给“游戏”这个词所派的用场。相信到这里,我们在说的“游戏”的意义,已经部分清晰了。
接下来我们从家族相似性的角度阐释“游戏”。“游戏”(可以是广义的游戏,也可以是电子游戏)到底是什么,众说纷纭。有人说是消遣,有人说是具有目的性的行为,有人说游戏必须要有乐趣,有人说游戏是ticker加上有限状态机。人们在不断地争论,不断地补充,其原因就在于,游戏是对于一系列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活动或作品的总称,当某一作品因与之前被称为“游戏”的诸作品有一定程度上的相似时,它便被划入“游戏”。从《Space Invaders》到《赛博朋克2077》,游戏是异质多元却又相互关联的。是与不是之间的limbo自然也存在——对于视频游戏来说,早期靠蒙版进行游戏的《奥德赛》,之后出现的交互式电影等等,存在于视频游戏家族的边缘。并非先有“视频游戏”的本质才有林林总总的视频游戏,而是不断被创作出来的、被人们当作“视频游戏”的视频游戏构成了“视频游戏”这一家族。
相信到这里,我们已经阐明了何谓(我们现在所聊的)“游戏”。
什么是艺术?
什么是艺术?
词语的意义在于其用法,“艺术”这个词的用法是什么?我们先考察几种不同的用法。
一位朋友第一次来到圣家堂前,惊呼“天呐,艺术”。这位朋友并不通晓建筑史,并不懂什么“新哥特”和“加泰罗尼亚现代主义”。在这个情境下,这位朋友被教堂的高耸雄伟、装饰之繁复所震撼,不由得发出惊叹。此时,“艺术”的用法等同于叹词。单纯的叹词是贫瘠的,不能表达具体的价值判断——我无法得知这位朋友惊叹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另一位朋友来了,惊呼“这就是建筑艺术啊!”显然,第二位朋友口中的“艺术”除去惊叹的意味之外,还有基于知识和见识的对眼前这幢作品的赞许——这是教堂建筑中的杰出者。此时“艺术”的意义展现于个别作品,也关联于该门类的总体。这位朋友随后讲述了该建筑建造的曲折历程,设计的巧夺天工,其完工登上了诸多新闻媒体。此时我们所谈的艺术,是作品背后具体的历史、技术和社会影响。
艺术史老师说,“梵·高是后印象派的代表艺术家之一”。在这个情境下,”艺术“显然是在说艺术史。林林总总的艺术史著作和艺术史学家写出了作为整体的艺术史,包括了艺术史学家们认为值得载入史册的艺术品和艺术家。被载入史册的缘由,可能是其在当时不凡的影响力,可能是其技法或理念的创新性,也可能是严肃的哗众取宠。一方面,艺术史是已经写就的, 另一方面,随着艺术史工作的不断进行,未被纳入艺术史的杰出人和物有被发现或重新发现的可能。如今我们面对艺术史时,要思考我们究竟在看“艺术的历史”还是“历史中的艺术”。前者假定“艺术”有某种定义或本质,达标者才能被选中。而后者则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艺术史是被称为“艺术品”的作品和被称为“艺术家”的人不断写就的。
某书法家披头散发、看似疯癫地用毛笔写下一些潇洒的符号,观众们并不理解其意义,便说:“呵呵,艺术啊”。“艺术”在这里显然被用作讽刺。观众既没有理解书法家创作的用意,书法家创作的结果也不“美”(这个没有实在意思的词也常与‘艺术’一起出现)。有一些素养的观众发现这种创作很难在现今的艺术史中找到对应。
这暴露了一个问题:有些艺术不面向大众,而是面向小圈子。这种情况下,艺术家和艺术评论家称作“艺术”之物才是艺术,艺术有了免受大众批判的特权。杜尚以《泉》这种戏谑的作品,企图打破艺术与生活的界线。然而《泉》被展出于美术馆,这场所将“艺术”与外面的“生活”相分隔。尽管这人为的界线没有被取消(入馆需要门票),但是你在欣赏《泉》时,总不得不暗暗告诉自己:“这是艺术(而不是随便哪个小便池)”。杜尚对艺术与生活界线的挑衅得以完成。
贡布里希在《艺术的故事》开篇就讲,“没有艺术这回事,只有艺术家”。只有作曲的、舞蹈的、盖房子的、画画的(或许还有做游戏的)人们,这些人中的杰出者们,被我们称为“艺术家”,他们杰出的作品,被称为“艺术”。贡布里希有意模糊艺术与生活的界线,但未完全将其取消,因为艺术史已经写就,不能视而不见。但是艺术史如今是尴尬的存在:其因充满偏见而难称为史学;而若用史学的观点要求艺术史,艺术史就溶于史学。如果要求全面展现一个时代,不应只关注梵·高,更要关注其时代绘画者的平均水平。但是,平庸的艺术不是艺术,人们可以分辨低俗小说与文学巨著。所以,当我们谈”艺术“时,是在对历史上某些杰出者进行褒奖,却又很难脱离趣味和偏见。为了解决这种尴尬,我们其实可以绕开“艺术”这个词,直接面向作品与作者本身,谈具体的语境、具体的价值。“艺术”这个词并非不可用,只是这个词包含太多事物,用起来难免粗犷。
哲学是澄清语言的活动,维特根斯坦把这种活动比作向下挖掘。当挖掘到最深处时所遇到的基岩,是赋予语言确定性的“生活形式”。生活形式是一个具有基本共识的人群所表现出来的语言或非语言行为上的一致。通俗来讲,生活形式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语言和我们的日常。如何判断我这篇文章不是胡言乱语?请考察我们的语言和我们的生活。
“艺术”这个词的用法(意义)基于某一生活形式,而在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村的人们很大程度上共享了一个生活形式。我们谈论艺术的意义时,是在谈论世界上人们对这个词在生活中用法的共识。因此无论如何,谈艺术难以脱离生活,艺术馆内的圣殿避难已被澄清为谎言,“艺术”可以被消解于具体的生活形式。与此同时,人们仍然热衷于使用“艺术”这个大词。在笔者看来,保留这个词有悖哲学家的本心。但是,众多画画的、写歌的、拍电影的、照相的、盖房子的、讲故事的、做雕塑的、跳舞的(或许还有做游戏的)人们会因这个词的褒奖而欢欣鼓舞,那就让它留下吧。
游戏是艺术吗?
游戏是艺术吗?
相信读到这里,读者应该已经认识到,“游戏是艺术吗”是一个范畴错位的病句,好比“鲨鱼是潜水艇吗”,其意义是模糊的。如果把话说清楚,那么它可能是如下问题:
- 问题1:视频游戏这一形式的诸多作品之中,是否有作品值得“艺术”这一词的褒奖?视频游戏这一行业中,是否有创作者值得“艺术家”的头衔?
- 问题2:如今视频游戏这一形式的诸作品,是否与艺术史中的众多形式的作品有某种家族相似性?
- 问题3:如今视频游戏这一创作形式,会被写入艺术史、成为“第X大艺术”吗?
当然,还可能是其他具体的问题,笔者基于我们正在谈的问题,暂选以上三个进行回答。
对于问题1,答案显然是肯定的。
在众多视频游戏作品中,游戏性、叙事、美术、音乐杰出者比比皆是。而这些要素被统合成视频游戏这一个整体之后的作品中,更是有许多堪称卓越的。视频游戏这一形式的精妙之处就在于这种统合。这种统合或可以提供我们世界的摹本,或可以提供完全不同的天马行空,让欣赏者身处其中。一些视频游戏本身就是技术和美术上的杰作,如画作一般给人图形美感上的享受,让人感慨其天工巧夺(这是一种技艺崇拜,照相术出现前人们对油画“逼真”的欣赏很大程度上也是技艺崇拜)。
对于顶尖的游戏开发者而言,他们自然也配得上“艺术家”这一称赞。他们是软件工程师、概念艺术家、三维美术师、数值策划、编剧……他们选择进入游戏行业,为一部游戏作品而付出心血。有人会质疑,软件工程师被称为艺术家未免牵强。这里我们要说的不是“编程艺术”这种修辞,而是回到作为游戏开发者的软件工程师的生活形式:他知道每一行代码都是未来游戏作品的基石,一个lerp()函数会让一个镜头运动颇具真实感,开发游戏的软件工程师知道自己在做的事与开发数据库的同行不同。
制作人很大程度上赋予游戏作者性,直观上更可以被称为“艺术家”。优秀的制作人把控全局,做出决断,与指导“这个镜头如何拍”的导演无异,与安排“这一笔应该画在哪”的画家无异。更重要的是,优秀的制作人将热情与心血投入到作品中,严肃地抛出问题,严肃地给出回答。
体验过并折服于这些优秀的游戏作品,被这些优秀的从业者感动,是玩家共同的生活形式。
对于问题2,答案也是肯定的。
首先需要澄清一个问题:这种家族相似性并不是因为游戏聚集了绘画、音乐、叙事、摄影等诸多要素,更不是通过把艺术史中的一些作品搬到游戏中而获得的。
要具体展示这种家族相似性,我们不妨先考察《蒙娜丽莎》与《超级马里奥兄弟》两部作品。
观看《蒙娜丽莎》,我们看到的是一副神态宁静祥和、给人以亲切感的妇人肖像,似笑非笑,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场。相比于之前的中世纪呆板的画作,《蒙娜丽莎》的人物更加生动、真实,画面的前景与背景更加融洽,画面达到了整体上的和谐。将该做放到历史中,我们认识到它突破了中世纪的桎梏展现人性的光辉,具有人文主义精神,在技法上运用多层颜料和渐隐法。画家深谙解剖学知识,所以对人物神态的拿捏十分到位。因此,该作品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艺术史价值。
游玩《超级马里奥兄弟》,我们化身马里奥,在像素块构成的简单世界中以跑和跳的形式克服障碍、击倒敌人,最后救出碧琪公主,其过程颇有乐趣。相比于雅达利大崩溃之前的游戏,该做设计精巧,横板滚轴的形式颇具创新性,画面与音乐一起营造了轻松愉悦的游玩氛围。作为硬件基础的红白机相比之前的竞品有很大提升。该作品因游戏性、美术、音乐俱佳而取得成功,成为了享誉全球的划时代作品。
我们可以用相同的逻辑去考察《蒙娜丽莎》和《超级马里奥兄弟》,尽管二者直觉上似乎有着本质的不同。观看《蒙娜丽莎》,观者直接获得视觉上的愉悦。而游玩《超级马里奥兄弟》的过程中玩家需要不停的操作手柄、完成一定动作,不断尝试,收获愉悦。保有成见的人会认为前者更高级,因为这是在“欣赏艺术”。但是事情真的是这样吗?有人把游戏的快乐解释成一套“多巴胺回路”,似乎这种感受是“生物性”的,因而给人“低级”的感觉。然而如果我们考察视觉图像带来“审美体验”的过程,必然也可以从物理-生物学意义上说出“光经颜料反射射入人眼,刺激视觉细胞,经神经传导到大脑皮层最后产生一些列电-化学反应”。这种阐述与“多巴胺回路”同样“生物性”,没有原则上的区别。如果说一种愉悦比另一种愉悦更“高级”,则其后必有进行价值判断的具体理由,是道德哲学的问题。
如果说《蒙娜丽莎》画得“像”、“生动”,渐隐法带来了更和谐的画面,这是对莱昂纳多技法的赞扬。然而这是一种技艺崇拜,是将莱昂纳多放到时代背景中说“他比别人画的好”。宫本茂为“跳”单独设置按键,也是“如何将游戏设计的好玩”这种技艺上的出类拔萃。至于颜料、画布的选用,无数层的油彩,则可以对应到红白机里的集成电路和程序语言上去了——这是作品的技术基础。
通过这样的分析,我们似乎找到了某种“相似性”。但是我们发现,两种分析看似比较到位,但是总会让人觉得“干巴巴”的,说了很多又没有说到点子上。而且,如果我们认为音乐、诗也是“艺术”的话,这种分析似乎很难成立。然而“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艺术”间的相通之处到底在哪里?
答案是诗性。海德格尔极力推崇诗。诗人中的诗人荷尔德林指出,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人借(诗性的)语言见证其(世界)本质”。当我们读诗时,其中的诗性(诗意)来自于何处呢?来自于韵律美吗?显然不是,没人把顺口溜称为诗。“本质”和“真理”不可言说,只可展示。诗的语言既是对被遮蔽的本真的生活形式的展示,这一过程既是诗性的显现。
我们以《登幽州台》为例来说明: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没有古人与来者,只有“我”于此刻孑然独立,古人和来着的缺席使得“此刻”得以展现。人忙于琐事忽视存在,时间如沙从指尖划过,人认识到意识内时间的奥秘却依然无法将时间留住。“此刻”是人习以为常、日用而不知的生活形式。天地无始无终而悠悠,“我”这有死的、时间性的存在,因“此刻”而怆然。
语文课讲解修辞行文,讲解音律对仗,讲解历史背景,却很难讲解诗性,因为诗性不可言说(也就不可考试)。但是诗性的根基是人共同的生活形式,是主体间性的根基(维特根斯坦所谓确定性),因此笔者才得以不称“诗人”怆然而说“我”怆然。(音乐有情绪而无语义,因此可以超越性地唤醒存在于世界的人。)
让我们回到《蒙娜丽莎》。回顾最开始我们的分析,读者应该可以意识到究竟少了些什么了——不可言说而只可展示的某种东西。《蒙娜丽莎》通过画面整体,展现了人性的光辉。“光辉”这一隐喻正是在说,人性是这种朦胧不真切而无法描述的东西,但我们在日复一日的与人交往中,常常因各种各样的原因视之不见。此刻,天才的莱昂纳多将其焕发了,是那么的耀眼。
那么,《超级马里奥兄弟》也有类似的展示吗?是的,也有,就是“玩”本身。我们隐约知道“玩”是什么,或许是消遣,寻求片刻的欢愉,却又说不真切——难道只是无聊生活中的另一种无聊?人不能为了玩而玩。我们或许都有这样的经历:我不想写作业,妈妈发火了,把玩具丢到地上,恶狠狠地说:“你玩啊,你使劲玩,你玩个够!” 如果把“玩”解释成“多巴胺回路”,则是对人地误解:人是会反思地动物,“玩”并不止于当时的体验——玩没玩取决于玩过之后,是收获一段美好地回忆,还是懊悔地说“我这干啥呢”。我们无法言说“玩”。“玩”正是这样一种人类共有的生活形式,无论是荒野中艰难求生的祖先还是钢筋水泥丛林中的我们,总要忙里偷闲,去寻找快乐(请注意,不是“快感”)。
“玩物丧志”。自古“玩”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远古的时代,或许偷闲“玩”一下,就可能面对野兽的袭击或物资的短缺进而丧命。当人步入文明,人又发明一些宗教、形而上学、意识形态来控制另一些人。“玩”这一无关物质生产却关乎人幸福的生活形式总是惨遭毒手。如今“玩”作为关注人和人的心灵的服务业的一部分发展壮大,却依然承受着旧时代遗留的偏见。此时此刻笔者所做的不是在为“玩”(或许还有游戏)正名,而仅仅是澄清,“玩”是人类共同的生活形式。
当然,这并不是说视频游戏的诗性只能通过对“玩”的展示来体现。视频游戏是一个庞杂无比、内容丰富的总体,诗性的表达自然也各异。我们不妨考察《赛博朋克2077》中的“太阳”结局:
V踏出太空舱,只身飞向荒坂水晶宫。背景是轨道视角下的地球,而更多的,是漆黑的宇宙背景和浩渺星光。在宇航时代,“天”和“地”的隐喻已经消逝,但是宇宙的真空和星辰取代了陈子昂诗中的悠悠天地,让此刻的V更加孑然。然而此刻宇航头盔中的V并没有“怆然而涕下”,而是目光坚毅,义无反顾。现代人不再对宗教许诺的来世(afterlife)天堂信以为真,荒坂却在大气层之上建立水晶宫意欲取而代之。V知道来生(afterlife)不在这里,在夜之城,而V是夜之城的王,手里握着枪。
对于问题3,这个问题无关事实,而是话语权之争。2011,美国联邦政府下属的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正式宣布“电子游戏是一种艺术形式”,同年,大法官安东尼·斯卡里亚在判决中宣称电子游戏是艺术,它应像书籍、漫画、戏剧和其它艺术形式一样受到美国《第一修正案》的保护。
然而美国立法不代表社会整体的认知,反而说明目前社会的整体认知需要法律来修正。法律的作用只是限定人行为的预期,是调节社会的一种权宜之计,并不能直接改变人的心智:玩家为某人不承认游戏是艺术而群情激愤;一些媒体和家长将游戏斥为“电子海洛因”;一些“社会精英”(使用这个词的目的在于区分群情激愤的一般网友)严词禁止游戏加入艺术的行列。
本文已经论述过,感谢杜尚们、贡布里希们和哲学家们的努力,“艺术”这个大词已经被澄清为对一些作品和作者的家族相似性的描述,没有清晰的、原则性的界定。艺术与生活并无界线,那么艺术理应向一切杰出的作品敞开大门。在保留“艺术”这个词的前提下,我们反思艺术史,在诸多作品中瞥见“诗性”这跟脉络,那么显示诗性的游戏理应得到“艺术”的称号。
当艺术与生活的界线消散后,又有人发明(或者重新发明)崇高艺术、伟大艺术、纯艺术或者说区别于art的Art,来重新划定一种艺术,以这个新词来取代“艺术”之前的位置。既然“艺术”没有边界,那么“崇高艺术”有没有切实的边界,就很可疑。
没有“崇高艺术”。“崇高艺术”在诸作品中甄选,必然遵循某种标准。然而对生活形式的展示是异质多元的,展示的巧妙程度(既诗意的浓淡)可以做程度上的区分,展示的内容却无法原则区分。为了程度区分而新造一个词,并无必要。如果给被展示的具体的诸生活形式排序,则是道德哲学的问题了。
所以,区别于艺术的“崇高艺术”的标准,是规则制定者的趣味(taste),趣味皆偏见。人当然可以拥有趣味,但把偏见当作标准是错误的。这里将通过对Brian Moriarty演讲中“崇高艺术”相关的话语进行评论,来展示这些偏见。
Moriarty寻求叔本华的帮助,捍卫“崇高艺术”。叔本华?十九世纪青黄不接时代的二流形而上学家?生存意志又是在说繁殖欲吗?钟摆理论又是什么心理学小册子上的东西?Moriarty你还是闭嘴吧,我来教你什么叫哲学。
请欣赏《赛博朋克2077》恶魔结局,“梦安魂于九霄”任务最后选择回到地球。在通往回程穿梭机的走廊上,V看向窗外的那颗蓝色星球,无数的人们在上面度过一生的地方,宇宙中渺小苍白的点。要放弃永生回到那里吗?
1881年,尼采在山林中散步时,听到了不知是天使还是恶魔的低语:你将永远重复这一生,永恒轮回。那么,这是一种祝福,还是诅咒?人终于可以克服死亡,然而要面对的是另一种永恒。永恒轮回这一思想无关科学,是超越虚无主义的智慧。人在这一问题下审视自己的人生,要面对的不只是必将来临的死亡,更是“此刻即永恒”。这个问题也无关自由意志的存在与否,而是另一个问题:即使明知未来是那样,我还要选择那样的未来吗?某一选择既是永恒的重复,这种假设让选择严肃。
要放弃永生回到那里吗?V做了决定,为了帕南,为了朱迪,为了老维……为了杰克·威尔斯,V做了不后悔的决定。这决定不单单是关于情感的,该结局通过永生选择的对立面明确地展示了人(mortal)的本质——神并不需要做决断,神有无尽的将来,而V在最虚无的末世重估了价值,超越了人。
这才是真正的崇高艺术!尼采(世纪末的超人)比叔本华(厌女二流悲观形而上学家)强出了一百个弗洛伊德(纯大忽悠)。
上述评论中,笔者有七成认真,语气效果之外对《赛博朋克2077》这一结局的讨论是严肃的。
偏见多见于泛泛而谈,Roger Ebert说:“电子游戏意味着大量失去了的接受更有文化、有教养、有共情能力的熏陶的宝贵时间。” 我们不妨把话说细致一些:是被定义为shared information的文化还是某一特定地域的文化?如何选择?传统清教徒家庭的教养?还是说要学习日本人使用敬语?时间花在哪里?如果说不同作品形式给人共情能力熏陶的效率不同,那么为什么不干脆只保留效率最高者而取消其他?简短的话语可能真的简短,也可能是在故意隐瞒些什么。Ebert这番话显然是首先划定某些形式“更有文化、有教养、有共情能力”、再用这些形式将游戏除外的循环论证。
让我们回到话语权之争。连与生活无界线的“艺术”都不是意义明确的概念,“第X大艺术”这种说法只会更无聊。我们应该认识到,这种说法和“四大发明”、“四大名著”、“八大奇迹”、“五大连池”、“B站百大阿婆主”一样,是为了方便传播而被发明的短语,而非基于某种规则的严格甄选(或许百大阿婆主的评选更严格)。
话语权问题的答案,在于整个社会的心智。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并不在于其委员会,而在于奖的得主。如果笔者明年拿下诺贝尔文学奖,那么诺贝尔文学奖的权威性将瞬间崩塌。然而整个社会的心智很难由某种理论、某项法律的横空出世而改变,更多的是随着老一代人的死去而改变。从这种意义上讲,我们欣然发现Roger Ebert已经死了,正如欣然看到雷峰塔的倒掉。
结语
结语
笔者于开篇阐明“哲学是澄清语言的活动”,并以这种态度澄清“游戏是艺术吗”这一问题。通过考察“游戏”这一词语,引出了“语言游戏”和“家族相似性”。接着提出“意义既用场”,明确我们正在谈的是“视频游戏(Video Game)”。随后考察“艺术”的几种用场并澄清“艺术”并非具体的原则,与生活没有明确界线。出于情感需要,保留这一词汇对杰出者进行嘉奖的用法。之后具体回答“游戏是艺术吗”可能表示的三个问题,并在回答中展示游戏作为小写的art、游戏的诗性显现以及这个问题背后的话语权之争。
本文的目的在于澄清问题,让读者免受“游戏是艺术吗”这一虚幻问题的困扰,直接面向游戏作品本身。回想这个问题的起因,也就是Ebert的言论,其实颇为诡异:一个完全不玩游戏影评人单单看了一部不怎么入流的电影中致敬游戏画面的片段,说出了对游戏这一创作形式的整体评价。显然,无论Ebert做出什么样的评价,都是毫无根据的。在这件事情上,Ebert有的只是偏见和影响力而已,体验过游戏的人只可能会拍拍他的肩膀,摇摇头,然后笑笑了之。 然而大家还是吵了起来,原因在于网络交流(其实很难)的特性和玩家对游戏的热爱。关于Ebert的讨论应该在他承认他在谈论他自己根本不了解的事物之后就戛然而止。
然而Brian Moriarty站出来为Ebert(没什么道理的论断)进行辩护。辩护的形式是公开演讲,演讲很成功,Moriarty是很好的演讲者,以画作《下棋者》作为线索,引经据典,语言抑扬顿挫;时不时讲一些俏皮话,引得观众一片哄笑,有效得调动了观众的情绪。似乎是一场很成功的辩护。然而当笔者去阅读文字版演讲稿时,观感直线下降。字里行间尽是偷换概念(聊聊足球和棋)、树稻草人(浮木经典示范)和不得要领的顾左右而言它(游戏是不是艺术和激流派到底有什么关系?),想要对其进行反驳,会觉得无从下手——因为哪里都没什么道理。究其原因,是因为演讲这种形式的要旨在于煽动听众于一时一地,收获掌声,而非严肃的讨论些什么。
在《通识:东方》那期电台节目中,麦教授介绍了黑格尔对东方的轻视:“……所以不存在真正的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西蒙对此直言:“放他妈的屁。” 将西方的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命名为“真正的”,那么东方的诗歌、艺术、哲学和科学不同于西方,自然也就不是“真正的”。眼明的人都能看出,这是一种循环论证。
维特根斯坦目无尊长,恃才傲物,规定哲学是澄清语言的活动,将此前的“哲学”巨构们划归为形而上学,平等地封存在思想史当中。这种无偏见性来自于他对确定性的挖掘——意义的基岩是人的生活形式。
因此笔者决定另起炉灶,从我们的语言和生活形式出发,以这种确定性聊聊游戏。在一期聊《死亡搁浅》的电台节目中,平时“牛逼疯了”、“一般”、“放他妈的屁”的西蒙动情地说:“生命的赞歌”。原因就在于《死亡搁浅》展示了“为人父母”这一人类普遍的生活形式,显示了诗性,戳中了初为人父的西蒙。到这里,相信各位读者和玩家应该已经明白了——不要纠结于语言错乱制造的幻觉问题,应当对“游戏不是艺术”的言论处之泰然。这种泰然不是玩家圈子的“我不听我不听”、“好玩就够了”,而是回到语言确定性——生活。
毕竟,只有生活(Reality),才是唯一真实的东西。
还请阅读:
- 《大地上的尺规》,作者巫怀宇。全书分为四个部分,分析了历史、艺术、科技和现代智慧形态,界限清晰又相互映衬地描绘了何谓现代人。该书是本文思想的直接来源,但是该书作者更为激进——主张取消“艺术”这一空泛的大词。
- 《牛津通识读本:维特根斯坦与哲学》,A.C.格雷林著,张金言译。该书结合生平与背景,简明扼要地带你认识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哲学。
- 《艺术的故事》,贡布里希著,开篇就展现“历史中的艺术”视角的艺术史著作。
- 《游戏是艺术吗?是高尚艺术吗?这是个重要问题》 小李老师以点带面,以几个否定和几个要点严肃地谈这个问题,也让笔者决意要系统的谈这个问题。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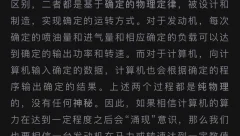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8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