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先前在听技术哲学家许煜老师分享时听说了这篇文章与格雷戈里·贝特森这位学者,我认为他大大被忽略了,甚至他《迈向心智生态学之路》这本经典之作至今都还没有中文译本。而他又是如此地鲜活与深刻,甚至有大量以自己和小女儿的对话体写成的「元对话 metalogue」,非常有趣,而他自身的研究和思考领域也极为广泛。
从他《心灵与自然》一书的序言中可见一斑:
正规教育几乎从来没有教授学生任何有关发生在海岸、红杉林、沙漠及平原上事物的本质。面对自己的孩子时,即便是成年人也无法合理解释如下的概念,诸如熵、圣礼、句法、数字、数量、模式、线性关系、名称、类、相关性、能源、冗余、力量、概率、部分、整体、信息、重言说、同源、质量(牛顿理论或者基督教义)、解释、描述、维度规则、逻辑类型、隐喻、拓扑学,等。蝴蝶是什么?海星是什么?美与丑又是什么?
他实际上是横亘学术研究-嬉皮士运动-控制论-互联网之间的一位特别的学者,甚至我怀疑这种难以归类正是难以为人所知的原因。他是在60、70年代的旧金山反主流文化的标志人物,是《全球概览》的主编斯图亚特·布兰德所崇敬的思想家,布兰德说他三年来一直在寻找将控制论的整体系统思想与宗教的整体系统思想明确结合的可能,是贝特森填补了这一空白。
这篇文章来自他对于酗酒者问题的考察,考察酗酒者匿名协会(A.A)这个组织是如何应对和挽救这些酗酒者的,但本文却不仅仅只是停留在此,实际上,文中大部分的论述展开了对西方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的批判,并详细叙述了他所提出的控制论/系统论的认识论。通过潜入酗酒者心智的最深处,他试图将其作为一种涉及宇宙的根本的理论,而这甚至关系到人类这一物种的存续,在文末,他这样写道:
我认为非酗酒的世界可以从系统论的认识论和 A.A. 的方式中学习到很多。如果我们继续以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来运作,我们可能也会继续以上帝与人、精英与人民、被选中的种族与其他种族、国家与国家、人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一个既拥有先进技术又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看待世界的物种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这是存疑的。
那为什么我做了这篇翻译,和游戏的关系是什么?
首先这篇能够体现贝特森基本哲学的文章是重要的,而他值得介绍;而对我来说,这也是我思索游戏本体论的重要资源,你可以借此思索系统论背后的哲学意义,他对系统、计算机在五十年前的思索依旧适用;而在对于心理治疗-游戏的研究中,若是将玩游戏的过程看作一个控制论系统,那么我们也需要一个以控制论与系统的视角看待自我与心理的一个典型范例。此外,如果你有过精神上的跌入谷底,或许这篇文章也能让你的「无我」和放下自我的感受会有所共鸣。
不过在思考游戏与此的关联上,我也不是唯一这样想的人:
对布兰德而言,存在着两个“控制论前沿”,而且它们是紧密相连的。第一个是贝特森的整体主义哲学论;第二个是发布于1962年的《太空大战》(Spacewar),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 —— 《机器崛起:遗失的控制论历史》
Gregory Bateson
Gregory Bateson
格雷戈里·贝特森 (Gregory Bateson,1904—1980)受过人类学的训练,曾在新几内亚和巴里岛研究模式与沟通,而后又从事精神医学、精神分裂,以及海豚的研究。是一位英国人类学家、社会科学家、语言学家、视觉人类学家、符号学家、控制论学者,他的著作还贯穿了许多其他学科,被誉为「20世纪重要的社会学家之一」。1942年他参加了著名首届梅西会议,1940年代他帮助将系统论/控制论扩散至社会/行为科学领域,晚年致力于发展一种认识论的「元科学」,统一系统论的各种早期形式。他的主要言论包含在《迈向心智生态学》《心灵与自然》等中。
The Cybernetics of “Self”: A Theory of Alcoholism
「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的理论
The Cybernetics of “Self”: A Theory of Alcoholism
「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的理论
本文发表为 Bateson G. The cybernetics of “self”: A theory of alcoholism. Psychiatry, 1971, 34(1): 1-18. 后编入其著作《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下载链接
- THE PROBLEM 问题
- SOBRIETY 清醒
-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认识论和本体论
- THE EPISTEMOLOGY OF CYBERNETICS 控制论的认识论
- ALCOHOLIC “PRIDE" 酗酒者的「骄傲」
- PRIDE AND SYMMETRY 骄傲与对称性
- PRIDE OR INVERTED PROOF? 骄傲,亦或颠倒的证明?
- THE DRUNKEN STATE 醉酒状态
- HITTING BOTTOM 跌入谷底
- THE THEOLOGY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酗酒者匿名协会的神学
- THE EPISTEMOLOGICAL STATUS OP COMPLEMENTARY AND SYMMETRICAL PREMISES 互补性和对称性前提的认识论地位
- LIMITATIONS OF THE HYPOTHESIS 假设的局限性
酗酒成瘾的 「逻辑」 与酗酒者匿名协会(Alcoholics Anonymous,文中简称 A.A)这个组织能够抵制酒瘾的艰苦精神制度的 「逻辑」一样,都让精神病学家困惑不已。在这篇文章中,我认为:
- 一种全新的认识论必须从控制论和系统论中产生,包括对心智、自我、人类关系和权力的新理解;
- 成瘾的酗酒者在清醒时是按照西方文化中传统的认识论运作的,但这是系统论无法接受的。
- 对醉酒的屈服提供了一条通往更正确心智状态的一部分的、主观的捷径;
- 匿名酗酒者协会的神学与控制论的认识论密切吻合。
这篇文章以一些想法为基础,这些想法或许都是和酗酒者打过交道的精神科医师,或是思考过控制论和系统理论的哲学家们所熟悉的。这里的论点中唯一的新意,就是把这些思想作为论证的前提来认真对待,并把两个过于独立的思想领域陈词滥调的观点结合起来。
在最初的构思中,这篇文章计划成为一个关于酒精成瘾的系统理论研究,其中我将使用来自匿名酗酒者协会出版物的数据,该协会在处理酗酒者方面有唯一突出的成功记录。然而,很快就可以看出,A.A.的宗教观点和组织结构与系统理论十分相关,我的研究的正确的范围应不仅包括酒精成瘾的,也应包括 A.A. 治疗系统的以及 A.A. 组织的前提。
我对 A.A. 的致意将贯穿始终:同时,对该组织,特别是对其共同创始人Bill W.和Bob博士的非凡智慧表示尊重。
此外,我还必须感谢一小部分的酗酒病人,在1949-52年期间,我曾与他们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的退伍军人管理医院进行了大约两年的密切合作。应提到的是,这些人除了酗酒的痛苦外,还带有其他病症——主要是「精神分裂症 schizophrenia」。有几个人是 A.A. 的成员,恐怕我根本没帮到他们。
THE PROBLEM
问题
THE PROBLEM
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酗酒的“原因”或“理由”应在酗酒者的清醒生活(sober life)中寻找。酗酒者,他们的表现,通常被称作“不成熟”、“母性固着”、“口唇”、“同性恋”、“被动攻击性”、“害怕成功”、“过度敏感”、“骄傲”、“和蔼可亲”,或只是“软弱”,但这种信念的逻辑隐含通常没有被检验。
- 如果酗酒者的清醒生活以某种方式促使他喝酒或成为走向醉酒的第一步,那么就不能指望任何加强他的特定清醒风格的程序会减少或控制他的酗酒。
- 如果他的清醒时的生活方式促使他喝酒,那么这种方式中一定包含错误或病理;而醉酒必须对这种错误提供某种——至少是主观性的纠正。换句话说,他的清醒在某种程度上是“错误的”,与此相比,他的醉酒在某种程度上则是“正确的”。 古老的短语“In vino veritas 酒后吐真言”可能包含着比通常我们赋予它的更深刻的真理。
- 另一个假设是,当清醒时,酒鬼在某种程度上比他周围的人更神志清楚,而这种情况不可容忍。我曾听到酗酒者主张这种可能性,但在这篇文章中我将忽略它。我认为A.A.的非酗酒者法务代表 Bernard Smith 说得很到位,他说:“A.A.成员从未被酒精奴役过。酒精只是作为逃避个人对物质主义社会虚假理想的奴役 ”。这不是对周遭疯狂观念的反抗,而是逃离自己疯狂的前提,而这些前提不断地被周遭社会所强化。然而,有可能的是,酗酒者在某种程度上比正常人更脆弱与敏感,更容易因为其疯狂(但也是普通平凡的)的前提而导致不幸后果。
- 因此,当前的醉酒理论在清醒和醉酒之间提供一个相反的匹配,这样,后者可以被看作是对前者的一个适当的主观修正。
- 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人们求助于酒精,甚至是极端的醉酒,作为一种麻醉剂,以释放日常的悲痛、怨恨或身体痛苦。也许有人会说,酒精的麻醉作用为我们的理论目的提供了充分的反面匹配。然而,我将把这些情况排除在外,因为它们与成瘾性或重复性酗酒的问题无关;尽管“悲伤”、“怨恨”和“沮丧”被成瘾的酗酒者通常用来作为饮酒的借口是毋庸置疑的。
接下来,我将提出在清醒(sobriety)和醉酒(intoxication)之间有一个相反的匹配(converse matching),比单纯的麻醉所提供的更具体。
SOBRIETY
清醒
SOBRIETY
清醒
酗酒者的亲戚朋友通常敦促他“坚强”和“抵制诱惑”。他们这样说的意思并不是很清楚,但重要的是,酗酒者自己清醒时通常会同意他们对他的“醉酒问题”的看法。他相信自己可以,或者至少应该成为“自己灵魂的船长”。【注:这句话被A.A.用来嘲笑那些试图用意志力对抗酒的酒鬼。这句话以及“我的头是血淋淋的,但没有受伤”这句话来自 William Ernest Henley 的诗《Invictus》,不过他是个瘸子而不是酒鬼。使用意志力来战胜痛苦和身体的无能,可能并不能与使用意志力控制酗酒相比较。】
但是,这是酗酒的陈词滥调,在“第一杯酒”后,戒酒的动力变为零。通常情况下,整个问题被表述为“自我”和“John Barleycorn”之间的战斗。酗酒者可能在隐蔽地计划,甚至秘密地为下一次酗酒准备用品,但几乎不可能(在医院环境中)让清醒的酗酒者以公开的方式计划他的下一次酗酒。他似乎不能成为自己灵魂的“船长”,公开表示愿意或授权他自己酗酒。“船长”只能命令他保持清醒,然后不被服从。【译注:John Barleycorn是一首英国民谣,歌中John Barleycorn是制酒的麦芽或啤酒等含酒精饮料的拟人化形象。】
Bill W.,匿名酗酒协会的创始人之一,他本人也是一名酗酒者,在A.A.著名的“十二步”(Twelve Steps)中的第一步就突破了所有这些冲突的神话。第一步要求酗酒者同意他对酒精没有抵抗力。这一步通常被视为“投降 surrender”,许多酗酒者要么无法承认它,要么只是在酗酒后的悔恨期短暂地承认它。A.A.不认为这些情况是有希望的:他们还没有“跌到谷底 hit bottom”;他们的绝望是不充分的,在或多或少的短暂清醒后,他们会再次试图使用“自我控制”来对抗“诱惑”。他们不会或不能接受这样一个前提,即无论醉酒还是清醒,酗酒者的全部人格都是酗酒的人格,其无法与酗酒作斗争。正如A.A.手册所言,“试图使用意志力来控制就像试图用你的鞋带把自己举起”。
A.A. 的前两步是这样的:
- 我们承认我们对酒精无能为力,我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难以控制。
- 开始相信,有一种比我们自己更强大的力量(Power)可以使我们恢复明智。[A.A.,1939]
在这两个步骤的组合中,隐含着一个我认为是正确的、非同寻常的想法:战败的经历不仅能使酗酒者信服改变是必要的,而且这正是改变的第一步。被酒瓶打败并确信这一事实,是第一步的“心灵体验”。自我力量的神话(myth of self-power)才能因此被更强大的力量所打破。
总体来说,我将论证,酗酒者的“清醒”是笛卡尔二元论(Cartesian dualism)的一个异常糟糕的变体,即心与物(Mind and Matter)间的分裂,或者,在这种情况下,是有意识的意志(conscious will)或所谓的“自我”(self)与人格其余部分间的分裂。 Bill W. 的天才之举是用第一“步”打破了这种二元论结构。
从哲学上看,这第一步不是投降;它只是认识论的转变,是如何认识「在世界中的人格」personality-in-the-world 的改变。而且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变化来自于从一个不正确的认识论到一个更正确的认识论。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认识论和本体论
EPISTEMOLOGY AND ONTOLOGY
认识论和本体论
哲学家们已经认识到并区分了两种问题。首先是事物如何存在 (how things are) ,什么是人,以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这些是本体论的问题。其次,是我们如何知道任何事情的问题,或者更具体地说,我们如何知道这是一个怎样的世界,以及我们是什么样的生物,可以知道一些(或可能什么也不知道)的问题。这都是认识论的问题。无论是本体论的还是认识论的这些问题,哲学家们都试图找到真正的答案。
但观察人类行为的自然主义者会提出相当不同的问题。如果他是一个文化相对主义者,他可能会同意那些认为“真实的”本体论是可构想的哲学家,但他不会追问他所观察的人群的本体论是否“真实”。他会认为他们的认识论是由文化决定,甚至是特异性的(idiosyncratic),并认为整体文化才使得他们特定的认识论和本体论有意义。
另一方面,如果这种地方性的认识论显然是错误的,那么自然主义者就应警惕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整个文化永远不会真正有“意义”,或者只有在限制环境下才有意义,而与其他文化和新技术的接触可能会破坏这种环境。
在人类活动的自然历史中,本体论和认识论是不能分开的。他(通常是无意识的)对世界是什么样的信念将决定他如何看待它并在其中行动,而他感知和行动的方式将决定他对世界的本质(nature)的信念。因此,一个活着的人被束缚在认识论和本体论前提的网中,无论最终真假,这些前提对他来说形成了部分的自我验证(self-validating)。
不断提及认识论和本体论是尴尬的,而认为它们在人类自然史中是可分开的也是不对的。似乎没有一个合适的词语来涵盖这两个概念的结合。最接近的是“认知结构(cognitive structure)”或“性格结构(character structure)”,但这些术语未能说明:重要的是,人与环境间的关系中,隐含着大量的习惯性假设或前提,而且这些前提可能是真的或假的。因此,在这篇文章中,我将使用单一的术语“认识论(epistemology)”来涵盖支配对人类和物理环境的适应(或适应不良)的前提网的两个方面。在 George Kelly 的词汇中,这些是个人“解释 construes”其经验的规则。
我特别关注的是“自我 self”的西式概念所依据的那组前提假定,反过来说,也关注那些纠正与此概念相关的更严重的西式错误的前提假定。
THE EPISTEMOLOGY OF CYBERNETICS
控制论的认识论
THE EPISTEMOLOGY OF CYBERNETICS
控制论的认识论
新的,且令人惊讶的是,我们现在对其中一些问题有了部分答案。在过去的25年里,我们对环境是什么样的、有机体(organism)是什么样的,特别是心智(mind)是什么样,这些问题的认识取得了非凡进展。这些进展来自于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和相关的学科。
我们现在相当肯定地知道,心灵是内在的(immanent)还是超越性的(超验的 transcendent )的这个古老的问题可以得到有利于内在性的答案,而且这个答案比任何超越的答案更节省解释资源:它至少有 "奥卡姆剃刀" 的消极支持。
在积极方面,我们可以断言,任何正在进行的事件和物体的集合体(on-going ensemble),如果具有恰当的因果循环的复杂性和恰当的能量关系,那一定会显示出心智特征(mental characteristics)。它将会比较(compare),即,对差异做出反应(除了受普通物理 "原因"的影响,如冲击或力)。它将“处理信息 process information”,并将不可避免地进行自我修正,要么朝向稳态平衡(homeostatic)的最佳状态,要么朝向某些变量的最大化。【译注:这里说的是负反馈与正反馈循环】
一个信息的“位 bit”可以定义为一个产生差别的差异(a difference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这种差异是一个基本的概念,它在回路(circuit)中传播并经历连续的变换。
但是,与目前情况最相关的是,我们知道,这样一个内部互动系统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对其余或任何其他部分进行单方面的控制。心智特征是作为集合整体而固有或内在的。
即使在非常简单的自纠正系统中,这种整体性(holistic)的特征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带有“调速器”的蒸汽机中,把“调速器 governor”这个词理解为系统具有单方面的控制权的一部分,这是错误的说法。调速器本质上是一个感知器官或传感器(transducer),它接收发动机的实际运行速度和理想/预期速度间的差异。这个感觉器官将这些差异变换为某些传出信息的差异,例如,对燃料供应或刹车的差异。换句话说,调速器的行为是由系统中其他部分的行为决定的,并且间接地由它自身先前的行为决定。
这个系统的整体性和心智特征通过这最后一个事实得到了最清楚的证明,即调速器的行为(事实上,也是因果回路中每部分的行为)部分地由它自己先前的行为决定。信息材料(Message material)(即差异的连续变换)必须在整个回路中传递,以及而后返回到它开始的地方所需要的时间,这是整个系统的一个基本特征。因此,调速器(或回路任何其他部分)的行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仅由它的直接过去决定,而且也由它在信息完成回路所需要的必要时间间隔之前所做的事情决定。因此,即使是最简单的控制论回路,也有一种决定式的记忆(determinative memory)。
系统的稳定性(它是否会自我纠正或振荡或走向失控)取决于回路周围所有差值的变换的操作性结果(operational product)和这个特征时间之间的关系。“调速器”(操控者)无法控制这些因素。即使是社会系统中的人类管理者也受到同样限制。他受控于来自系统的信息,并且他必须使自己的行动适应系统的时间特征和他自己过去行动所造成的影响。【译注:调速器的英文为governor,字面上带有操控,管理者的意涵】
因此,在任何显示出心智特征的系统中,任何部分都不能对整体进行单方面的控制。换句话说,系统的心智特征是内在的(immanent),不是在某些部分中,而是在作为整体的系统中。
当我们问:“计算机能思考吗?”或“心智(mind)在大脑中吗?”时这一结论的意义就会显现出来。这两个问题的回答都是否定的,除非这个问题是关注于计算机内或大脑中包含的少量的心智特征。计算机某些内部变量方面可以自我纠正的。例如,它可能包括温度计或其他感知器官,它们受到其工作温度差异的影响,而感知器官对这些差异的反应可能会影响风扇的作用,而因此又调节了温度。因此,我们可以说,该系统在其内部温度方面显示出心智特征。
但是,如果说计算机的主要事务,即将输入差异变换为输出差异是“一个心智过程”,那就错了。计算机只是一个更大回路的一段弧,这个回路总是包括一个人和一个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信息被接收,计算机所传出的信息产生作用。而这个总的系统,或者说集合体,可以合理地被说其显示出某种心智特征。它通过试错运转,具有创造性。
同样,我们可以说,“心智“、”内在于那些在完整在大脑内的回路之中。或者,心智内在于大脑加身体这个系统中的完整回路中。或者,最后,心智是存在于更大的人-系统(system-man)与环境中。
原则上,如果我们想解释或理解任何生命过程(biological event)的心智方面,我们必须考虑到系统——即闭合回路的网络,在这个网络中,生命过程被决定。而当我们试图解释一个人或任何其他生物的行为时, “系统”通常不像“自我”这个术语通常被(并且多种方式)理解的方式那样,有相同的限制。
让我们想象一个人用斧头砍树。斧头的每一次挥动都会根据前一次的砍击留下的树的切面形状进行调整或纠正。这种自我修正(即心智)过程是由一个整体系统带来的,即树-眼睛-大脑-肌肉-斧头-斧印-树:而正是这个整体系统具有内在心智特征。
更正确地说,我们应该把这回事写作:(树的差异)-(视网膜的差异)-(大脑的差异)-(肌肉的差异)-(斧头运动的差异)- (树的差异),诸如此类。在回路中传输的是差异的变换。而且,如上所述,一个产生差别的差异(difference which makes a difference)是一个信息的单位或意图(idea)。
但一般西方人并不是这样看待砍树的事件序列的。他说,“我砍了树”,他甚至相信有一个划定界限的能动者,即“自我”,对一个划定界限的物,进行了一次划定界限的“有目的”的行动。
“台球A打到了台球B,并把它送进了球袋”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的;而且,如果我们能做到对包含人和树的回路周遭所有事件给出一个完整的硬科学说明的话,也许是正确的。但是,通常地说法(译注:我 砍 树)在其话语中使用人称代词把心智囊括其中,而通过把心智限制在人之中、并把树给实物化(reifying),实现了心灵主义(mentalism)和物理主义(physicalism)的混合。最终,心智本身也被这样的概念重塑:既然“自我”作用于斧头,而斧头作用于树,那么“自我”也必须是一个“东西”。但“我打了台球”和“球打了另一个球”之间的平行句法是完全误导的。
【译注:reify 意思是 to consider or represent as a material or concrete thing,将抽象概念具体化,将某物当做物质和实体物。】
如果你问任何人关于自我的定位和边界,这些困惑就会立即显现出来。例如想象一个拿着棍子的盲人。盲人的自我从哪里开始?在棍子的顶端?在棍子的柄上?还是在棍子间的某个点上?这些问题都毫无意义,因为棍子是一条让差异在变化中传递的通路(pathway),因此,在这条通路上画一条分界线就等于是切掉了形成了盲人运动的系统回路的一部分。
同样,他的感知器官是信息的传感器或通路,包括他的轴突(axons)等等。从系统论的角度来看,说在轴突中传递的是“脉冲 impulse”是一个误导性的比喻。更正确的说法是,传递的是一种差异,或一种差异的变换(transform of a difference)。
“脉冲”的隐喻暗示了一种硬科学的思路,它很容易就会演变成有关“超自然能量”的无稽之谈,而那些说这种无稽之谈的人们无视静止状态(quiescence)的信息内容。轴突从活跃到静止,和它从静止到活跃间有同等的差异。因此,静止和活跃具有同等的信息意义(informational relevance)。只有在静止状态的信息可靠的情况下,活跃的信息才能被接受为有效。
谈论“活跃的信息”和“静止的信息”甚至是不正确的。应该永远记住信息是差异的变化(transform of difference)这一事实,我们最好把一个信息称为“活跃-而非静止”,另一个称为“静止-而非活跃”。
类似的考虑也适用于忏悔的酗酒者。他不能简单地选择“清醒”。他最多只能选择“清醒-不醉”,他的世界仍是两极化的,总是带着两种可能(alternatives)。
处理信息的总体自我修正单元,或者,正如我所说的,“思考”、“行动”和“决定”是一个系统,其边界与身体边界或流行的所谓“自我”或“意识”边界完全不同;需要注意的是,以系统思考和普遍认为的“自我”之间存在着多种差异:
- 系统不是一个超越的实体,而“自我”通常被认为是。
- 意图(ideas)是存在于因果通路的网络中,差异的变化沿着这个网络进行。系统的“意图”在所有情况下至少是二元结构的,并没有所谓的“脉冲”,而是“信息”。
- 这个通路网络不以意识为界,而是延伸包括所有无意识心理活动的通路,同时包括自主的和被压抑的,神经的与荷尔蒙的。
- 该网络不以皮肤为界,而是包括所有信息可传播的外部通路。它还包括那些内在于这些信息“对象”的有效差异。它包括声音和光的通路,沿着这些路径传播的差异原本内在于事物和其他人身上,特别是在我们自己的行动中。
重要的是要注意到,通常的认识论教条(我认为是错误的),其基础是相互强化的(mutually reinforcing)。例如,如果流行的超越性的假设被抛弃,那么直接的替代就是身体中的内在性的假设前提。但这个替代方案是不可接受的,因为思考的网络很大一部分都在身体之外。所谓的“身-心”问题被错误地提出,迫使论证走向悖论:如果心智被认为是在身体中,那么它必须是超越性的。如果是超越的,它就必须是内在的,等等(见科林伍德)。
同样,如果我们把无意识的过程从“自我”中排除,并称它们为“自我-异己(ego-alien)”,那么这些过程就具有了“冲动”和“力量”的主观色彩:而这种假的动态性质(dynamic quality)随后被扩展为有意识的“自我”,它试图“抵制”无意识的“力量”。“自我”于是就成为它自己看似“有力”的“组织”(organization)。将“自我”等同于意识的流行观念因此导向了意图(ideas)是“有力的”的观点;而这一谬误又得到了轴突携带“脉冲/冲力”说法的支持。要找到摆脱这一混乱困境的方法绝非易事。
我们将首先检视酗酒者的极化结构。在一个认识论谬误的解释中,“我将与酒抗争”,到底什么在对抗什么?
ALCOHOLIC "PRIDE"
酗酒者的「骄傲」
ALCOHOLIC "PRIDE"
酗酒者的「骄傲」
如同所有人类(和所有哺乳动物)都被高度抽象的原则所指导,酗酒者是普遍意义上的哲学家,他们要么完全无意识,要么就是还未意识到支配他们感知和行动的原则是哲学性的(philosophic)。这些原则的常被误称作“感觉 feelings”(Bateson, 1963)。
这个错误的名称自然产生于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认识论倾向,即把所有与意识相联系的心智现象(mental phenomena)实物化,或归于身体。毫无疑问,这个错误得到了以下事实的支持:这些原则的行使和/或挫折往往伴随着出于本能的和其他的身体感觉。然而,我相信帕斯卡尔是正确的,他说:“心有心的理由,而理性对此一无所知。”
但读者绝不能指望酗酒者呈现出一致的图景。当基本的认识论充满错误时,从它推导出来的结果不可避免地要么自相矛盾,要么范围极其有限。一致性的定理无法从不一致的公理中推出。在这种情况下,试图保持一致的做法要么导向精神分析理论和基督教神学所特有的复杂性的极大扩散,要么导向当代行为主义所特有的极其狭窄的观点。
因此,我将着手研究酗酒者的特点:“骄傲 pride”,以表明他们行为的这一原则来自西方文明特有的怪异的二元认识论。
描述“骄傲”、“依赖”、“宿命论”等原则的一个方便之法,便是把这一原则当作是再学习的结果(deutero-learning,Bateson, 1942)来研究,并探寻什么样的学习背景使得这一原则可理解地被灌输。
【注:这种将背景的形式结构作为描述手段的方法并不一定假设所讨论的原则是完全或部分地是在当前适当的形式结构背景中实际习得的。这些原则可能是由基因决定的,而且仍可能通过形式划定所体现的背景来进行很好的描述。正是这种行为与背景(context)的密不可分,使得我们很难或根本不可能确定一个行为原则是由基因决定的还是在该背景下习得的。】
- 很明显,A.A.称之为“骄傲”的酗酒者生活原则,并不是围绕着过去的成就构建的。他们使用这个词并不是指对所完成的事情感到骄傲。他们强调的不是“我成功了”,而是“我能......”这是一种对挑战的迷恋式的接受,是对“我不能”这一命题的否定。
- 在酗酒者开始忍受或被指责酗酒后,这种“骄傲”原则在“我能保持清醒”的主张背后开始启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一启动达成带来的成功破坏了“挑战”。正如 A.A. 所说的,酗酒者变得“过分自信 cocksure”了。他放松了他的决心,来了一杯,并发现自己开始了滥饮。我们可以说,清醒的背景性结构随之改变,清醒,在这一点上,不再是“骄傲”的合适背景设置。现在具有挑战性的是饮酒的风险,呼唤着致命的“我能....”
- A.A. 尽力持续推动这种背景结构的改变永远不会发生。他们通过一遍又一遍地断言“一朝是酗酒者,永远是酗酒者”来重组整个背景,他们试图让酗酒者将酗酒置于自我之内,就像荣格学派分析者试图让病人发现他的“心理类型”,并学习与这种类型的优缺点相处。相比之下,酗酒者“骄傲”的背景结构将酗酒置于自我之外:“我能抵制饮酒”。
- 酗酒者的“骄傲”的挑战构成与冒险(risk-tak-ing)相关。这个原理可以用文字表述:“我能做一些不可能成功,且会带来灾难性的失败的事。”显然,这个原则永远不会有助于保持持续的清醒。当成功开始出现可能性时,酗酒者必须挑战喝酒的风险。失败的“坏运气”或“概率”要素使得失败被置于自我的界限之外。“如果失败发生了,那也不是我的。”酗酒者的“骄傲”逐渐窄化了“自我”的概念,将发生的事情置于其范围之外。
- 冒险中的骄傲(pride-in-risk)原则最终几乎是自杀性的。检验一次世界是否站在你这边是可行的,但一次又一次地这样做,且证据越来越严密,这就等同于开始了一个只能证明世界讨厌你的项目。但 A.A.的叙述仍然反复表明,在绝望的谷底,骄傲有时会阻止自杀。最后的安宁不能由“自我”来给予(参见 Bill's Story,A.A.,1939年)。
PRIDE AND SYMMETRY
骄傲与对称性
PRIDE AND SYMMETRY
骄傲与对称性
所谓酗酒者的骄傲总是假定有个真实的或虚构的“他者(other)”,因此它完整的语境定义要求我们描述与这个“他者”真实或想象的关系。这项任务的第一步是将这种关系分类为“对称”或“互补的”(Bateson, 1936)。当“他者”是一种无意识的创造时,达成这点并不简单,但我们将看到,这种分类的迹象是很清晰的。
不过,解释性的离题是必要的。主要的标准很简单:
在一个二元关系中,如果A和B的行为被(A和B)认为是相似的,并且相联系,而A更多的特定行为会刺激B的更多行为,反之亦然,那么就这些行为而言,这种关系是“对称的 symmetrical”。反之,如果A和B的行为不同,但又是相匹配(例如,观者的臀部匹配露阴癖),而且这些行为相联系,使A的更多行为刺激B的更多匹配的行为,那么,就这些行为而言,这种关系是“互补的 complementary”。
简单对称关系的常见例子是:军备竞赛、与他人攀比、模仿行动、拳击比赛等等。常见互补关系的例子有:支配-服从、虐待狂-受虐狂、养育-依赖、观看-展示,等等。
当更高的逻辑类型存在时,就会出现更复杂的考量。比如:A和B可能在赠礼方面竞争,从而在主要是互补的行为上叠加一个更大的对称框架。或者,反过来说,治疗师可能在某种游戏治疗中与病人进行交流,环绕主要是对称的游戏交流放置一个互补的教育框架。当A和B以不同的方式感知他们关系的前提时,就会产生各种的“双重约束 (double binds)”,当B认为自己在帮助A时,A可能会把B的行为视为竞争。
我们在此不关心这些复杂问题,因为酗酒者“骄傲”中想象的“他者”或对应物,并不是精神分裂患者所具有的“多重声音(voices)”的复杂游戏。
互补性和对称性的关系都有可能发生渐进变化,我称之为分裂发生(schismogenesis , Bateson, 1936)。对称的斗争和军备竞赛,用现在的话说,可能会“升级(escalate)”;父母和孩子之间正常的帮助-依赖模式可能会变得畸形。这些潜在的病态发展是由于系统中未被抑制或修正的正反馈 (uncorrected positive feedback) 而可能发生在上述的互补或对称系统中。两个国家之间的军备竞赛将通过接受它们之间的互补性主题 (complementary themes)(如主导性、依赖性、钦佩等)而减慢。而通过对这些主题的否定而加速。
毫无疑问,互补性和对称性主题之间的这种对立关系由于每一主题都是另一主题的逻辑反面。在一个几乎对称性的军备竞赛中,国家A被它对B的实力的估计所激励而做出更大努力,当它估计B较弱时,国家A将放松努力。但如果A将这个关系结构构想为互补时,则会完全相反。观察到B比它弱时,A将带着征服的希望而继续向前(参见 Bateson, 1946, and Richardson)。
这种互补和对称模式间的对立面不只是简单的逻辑问题。值得注意,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参见Erikson, 1937),被称为“力比多的(libidinal)”模式和性敏感区(erogenous zones)的形式都是互补的。侵入、包容、排斥、接受、保留,以及类似的东西,所有这些都被归作“力比多的(libidinal)”。而对抗、竞争,以及类似的则属于“自我 ego”和“防御”范畴。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两种对立的编码:对称和互补的,在生理上可能由中枢神经系统的对比状态所代表。“分裂发生”的渐进变化可能会达至高潮间断和突然逆转。对称性的愤怒可能突然转为悲伤;夹着尾巴撤退的动物可能突然开始“困兽之斗(turn at bay)”,在一场绝望的对称性战斗中直至死亡;恶霸在受到挑战时可能突然变成懦夫,而在对称性冲突中被击败的狼可能突然发出 "投降" 信号,阻止进一步攻击。
最后一个例子具有特殊意义。如果狼群之间的斗争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如果狼A被B的攻击性行为刺激得更有攻击性,那么,如果B突然表现出我们可以称之为的“消极进攻性”,那A将无法继续战斗,除非他能迅速切换到互补的心理状态,而在互补心态下,B的示弱将成为它攻击性的刺激。在对称模式和互补模式的假说中,没有必要为投降信号假定一个特殊的“抑制 inhibitory”作用。
拥有语言的人类可以将“攻击”这一标签应用于所有损害他人的企图,无论这种企图是由对方的强大或是还是孱弱引起的;但在前语言的哺乳动物层面,这两种“攻击”肯定看起来完全不同。我们被告知,从狮子的角度来看,对斑马的“攻击”与对另一只狮子的“攻击”是完全不同的(Lorenz)。
现在已经说得足够而提出问题了:酗酒者的骄傲感是以对称或互补的形式在背景中形成的吗?
首先,在西方文化的正常饮酒习惯中,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称性倾向。除了成瘾酗酒外,两个人在一起喝酒时,会被惯例所驱使,互相配合,以酒养酒。在这个阶段,“他者”仍然是真实的,而这种对称性或竞争是友好的。
当酗酒者成瘾并试图抵制饮酒时,他开始发现很难抵制这种应该与朋友饮酒相匹配的社会环境。A.A说:“天知道,我们为了像其他人一样喝酒已经努力了多久!”
随着情况恶化,酗酒者很可能成为一个孤独的饮酒者,并对挑战表现出各种各样的反应。他的妻子和朋友开始建议他喝酒是一个缺点,他可能会作出对称性的反应,既怨恨他们,而又坚持自己的力量来抵制饮酒。但是,就像对称反应的特点一样,短期的成功斗争削弱了他的动力,他就会掉进摇篮里。对称性的努力需要来自对手的持续反击。
渐渐地,战斗的重点改变了,酗酒者发现自己致力于一种新的、更致命的对称性冲突。他现在必须证明,瓶子不能杀死他。他的“满头鲜血,却头颅昂起”。无论如何,他仍然是“他的灵魂的船长”。
同时,他与妻子、老板和朋友的关系也在不断恶化。他从来没有喜欢过他作为权威互补地位的老板;现在随着他的恶化,他的妻子越来越多地被迫承担起互补性的作用。她可能试图施加权威,或变得保护,或表现出忍耐,但所有这些都会激起愤怒或羞愧。他对称性的 "骄傲" 不能容忍任何补充性的角色。
总而言之,酗酒者与他的真实或虚构的“他者”间的关系明显是对称性的,也是明显“分裂发生”的。它不断升级。我们将看到,当被A.A.拯救时,酗酒者的宗教性转换可以被描述为从这种对称性的习惯或认识论,而到一个他与他者和宇宙或上帝的几乎纯然互补性关系看法的戏剧性转变。
PRIDE OR INVERTED PROOF?
骄傲,亦或颠倒的证明?
PRIDE OR INVERTED PROOF?
骄傲,亦或颠倒的证明?
酗酒者可能看起来很固执,但他们并不愚蠢。决定他们策略的那部分心智是很深层的,以至于 “愚蠢”这个词并不适用。心智的这些层次是前语言学的,在那的计算是在初级过程中编码的。
【译注:初级过程,原初过程,主要过程来自弗洛伊德理论,涉及到塑造一个欲望对象的心理图像来满足对于对象的欲望 the primary process involves forming a mental image of the desired object in order to satisfy the desire for that object.】
无论是在梦中还是在哺乳动物的互动中,实现一个包含自我否定的命题(“我不会咬你”或“我不怕他”)的唯一途径是通过对要否定的命题进行精心的想象或表演,从而导向归谬法(reductio ad absurdum)。“我不会咬你”通过两个哺乳动物之间的试探性战斗来实现的,这是一种“非战斗”,有时被称为“游戏”。正是由于这个原因,“好斗的 agonistic”行为通常演变为友好的问候(Bateson, 1969)。
在这个意义上,所谓酗酒者的骄傲感在某种程度上是讽刺性的。它是一种坚定的努力,以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以证明“自我控制”是无效和荒谬的。“这根本行不通”,这个最终的命题,因为它包含一个简单的否定,所以不能用初级过程来表达。它的最终表达是在一个行动中 —— 饮酒。与酒的英勇战斗,那个虚构的“他者”最终以“亲吻和交个朋友”结束。
支持这一假设的是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试图考验自控会导致人们重新饮酒。而且,正如我在上面所论证的,他的朋友们对酗酒者要求的整个自我控制的认识论是畸形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酗酒者反驳它是明智的。他已实现了对传统认识论的归谬。
但是,这种关于实现归谬法的描述已接近于目的论。如果在初级过程的编码中不能接受“这根本行不通”的命题,那么初级过程的计算又如何能引导生物去尝试那些能证明“行不通”的行动方案呢?这种一般类型的问题在精神病学中常出现,也许只能通过一个模型来解决,在这个模型中,某些情况下,生物的不适感会激活一个正反馈循环,以增加不适感之前的行为。这样的正反馈将提供一个验证,即确实是那个特定的行为带来了不适,并可能将不适增加到某种阈值水平,在这个水平上,改变将成为可能。
在心理治疗中,这种正反馈循环通常是由治疗师提供的,治疗师将病人推向他的症状方向:这种技术被称为“治疗性双重约束(therapeutic double bind)”。这篇文章后面引用了这种技术的一个例子,A.A.成员挑战酗酒者去做一些“有控制的饮酒”,以便让他自己发现他没有控制力,精神分裂症患者的症状和幻觉(如梦)也通常构成了一种纠正的经验,因此整个精神分裂症发作具有自我启动(self-initiation)的特征。Barbara O'Brien 对她自己精神病的描述可能是这种现象最突出的例子,这种现象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Bateson, 1961. Introduction)。
人们会注意到,这种将导致在某个阈值(可能是在死亡的另一边)之前的不适感增加的方向上的失控的正反馈循环并没有包括在传统学习理论中。但是,通过寻求对不愉快的重复体验来验证它的倾向是人类的一个共同特征。这也许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死本能(death instinct)”。
THE DRUNKEN STATE
醉酒状态
THE DRUNKEN STATE
醉酒状态
上面所说的关于对称性的骄傲感的枯燥工作只是图景的一半。它是酗酒者与饮酒搏斗的心理状态的画面。显然,这种状态是非常令人不快的,而且显然也是不符合现实的。他的“他者”要么是完全想象出来的,要么是他所依赖的、他可能爱的人的严重歪曲。他有一个替代这种不舒服状态的方法,他可以喝醉。或者“至少”,喝上一杯。
随着这种互补性的投降,酗酒者往往把它看作一种恼怒行为(an act of spite) ——在他的整个认识论发生了变化的对称性斗争中的帕提亚飞镖。他的焦虑、怨恨和恐慌就像变魔术般消失了,他的自我控制降低了,而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的需要甚至进一步减少。他在血管中切身感受到了酒精的温暖,在许多情况下,对他人也有相应的心理的温暖。他可能是悲哀的,或愤怒的,但他至少已经再次成为人类场景的一部分。
关于从清醒到醉酒,也是从对称性的挑战到互补性的步骤这一论点的直接数据很少,而且总是被回忆的歪曲和酒精的复杂毒性所迷惑。但从歌曲和故事中可以看出,这一步是这样的。在仪式中,饮酒一直代表着人们在宗教“共融 communion”或世俗的舒适感(Gemütlichkeit)。从字面意义上来说,酒精被认为能使个人把自己看作是群体的一部分,并以此行事。即,它能使他周围的关系形成互补。
HITTING BOTTOM
跌入谷底
HITTING BOTTOM
跌入谷底
A.A. 非常重视这一现象,认为没有触底的酗酒者是没有希望得到他们的帮助的。而相对的,他们倾向于说那些回归酗酒的个人的失败是因为他还没有“跌入谷底”。
当然,许多类灾难可能导致酗酒者跌入谷底。各种事故,震颤性谵妄的发作,失去记忆的一段醉酒时间,被妻子抛弃,失去工作,无望的诊断等等,这些都可能产生所需的效果。A.A.说,“谷底”对不同的人来说是不同的,有些人可能在到达底部前就已经死了(来自一位成员的个人通信)。
然而,这是可能的,“谷底”由任何给定的个人达到多次;“底部”是一个惊恐的咒语,提供了一个对改变有利,但却并不一定能带来改变的时刻。朋友和亲戚,甚至治疗师可能会把酗酒者从他的惊恐中拉出,无论是用药物还是安抚,使他“恢复”,回复他的“骄傲感”和酗酒,只是在之后的某个时间达到一个更灾难性的“底部”,在那时他又将足够达成改变。试图在这种惊恐时刻之间的阶段去改变酗酒者是不可能成功的。
以下对“测试”的描述清楚地说明了惊恐的性质。
我们不喜欢宣称任何个人是酗酒者,但你可以迅速诊断自己。走到最近的酒吧间,尝试一些有控制的饮酒。试着喝酒并突然停止。多试一次。如果你对自己诚实的话,不需要很长时间就能做出判断。为了你对自己的状况有了充分了解,这值得一次糟糕的紧张不安。[A.A.,1939,p.43]
我们可以把上面引用的测试比作命令一个司机在湿滑的道路上行驶时突然刹车:他将很快发现他的控制力是有限的。(用“湿滑的道路 slippery road / skid row(译注:应该是一个发音的双关,skid row 为贫民窟)”来比喻城里的酗酒区并不恰当)。
跌入谷底的酗酒者的惊恐就像是一个人以为自己可以控制一辆车,却突然发现这辆车和他一同失控。突然间,按压他所知道的刹车似乎让车辆变得更快。这是一种发现它(系统,即他自我+车辆)远比比他自身更巨大的恐慌。
就这里展示的理论而言,我们可以说,“跌入谷底”在三个层面上体现了系统理论。
- 酗酒者在清醒的不适上的努力,到了一个临界点,他的“自我控制”的认识论已破产。然后他喝醉了,因为“系统”比他自己还庞大,他可能会向它投降。
- 他反复地醉酒,直到他证明了有一个大得多的系统。然后他遇到了“跌入谷底”的恐慌。
- 如果朋友和治疗师安抚他,他可能会进一步实现不稳定的调整,对他们的帮助上瘾,直到他证明这个系统不起作用,并再次“触底”,并到一个更低的水平上。在这点上,就像在所有控制论系统中一样,任何侵入对系统影响的效果(正负)都取决于时机。
- 最后,“触底”现象与双重约束的经验有着复杂的联系(Bateson等,1956)。Bill w.叙述了他在1939年被William D. Silkworth医生诊断为无药可救的酗酒者时触底,这一事件被认为是A.A.历史开端(A.A., 1957, p. vii)。D. Silkworth 还“向我们提供了工具,用来刺穿最强硬的酗酒者的自我,他用这些令人震惊的短语来描述我们的疾病:强迫我们喝酒的心魔(obsession of mind)和迫使我们发疯或死亡的身体过敏”(Bill w. in A.A., 1957, p. 13; 斜体)
这种基于酗酒者的身心二分法认识论的双重约束(double bind)被正确找到了。他被这些话逼到了一个地步,在这个地步,只有深层无意识的认识论的非自愿改变:一种灵性的体验,才能使致命的描述变得无关紧要。
THE THEOLOGY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酗酒者匿名协会的神学
THE THEOLOGY OF ALCOHOLICS ANONYMOUS
酗酒者匿名协会的神学
A.A. 神学的一些突出要点是:
(1) 有一种比自我更强大的力量(Power)。控制论将进一步认识到,通常理解的 "自我" 只是一个更大的负责思考、行动和决定的试错系统(trial-and-error system)的一小部分。这个系统包括了在任何特定时刻任何特定决定相关的所有信息通路。"自我" 是对这互锁过程所属于的更大领域中的一个不恰当限定了的部分的错误 "实物化 reification"。控制论还认为,两个或更多的人(任何一群人)可以共同形成一个这样的思考和行动系统。
(2)这种力量被认为是个人化的,与每个人密切相关。它是 "你所理解的上帝"。
从控制论的角度上讲,"我"与我周围任何更大的系统(包括其他事物和人)的关系将不同于 "你"与你周围一些类似系统的关系。从逻辑上讲,"一部分"关系必须是互补性的,但 "一部分" 这个短语的含义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这种融合风格的多样性可以解释为什么有些人成为酗酒者,而其他人则不会。) 这种差异在包含一个以上的人的系统中尤其重要。系统或 "力量" 与每个人所处的位置不同。此外,可预见的是,当这些系统遇到对方时,会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对方为系统。我走过的森林的 "美" 是我对个别树木和森林整体作为系统的生态的认可。当我与另一个人交谈时,类似的审美认可会更加印象深刻。
(3) 通过 "触底" 和 "投降",发现了与这种力量的良好关系。
(4) 通过抵制这种力量,人,特别是酗酒者给自己带来了灾难。因为科技人员越来越有能力对抗最大的系统,将 "人"与环境对立起来的物质主义哲学正在迅速瓦解。他所赢得的每场战斗都会带来灾难的威胁。无论是在伦理学还是在进化论中,生存的单位不是生物或物种,而是生物所处的最大系统或 "力量"。如果生物摧毁了它的环境,那么它也就摧毁了自己。
(5) 但很重要的是,力量没有奖惩。它不具备这种意义上的 "能力"。用圣经的话说,"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反之,对那些不爱的人也是如此。单方面控制意义上的力量的概念对A.A.来说是异质的。他们的组织是严格的 "民主"(他们的说法),甚至他们的神也仍然受到我们称之为系统决定论的约束。同样的限制也适用于A.A.赞助人和他希望帮助的酗酒者之间的关系,以及A.A.中央办公室和每个地方团体之间的关系。
(6)匿名酗酒者协会的前两 "步" 共同确定了成瘾是这种力量的一种表现。
(7) 每个人与这种力量之间的健康关系是互补性的。这与酗酒者的 "骄傲" 形成了鲜明对比,后者的前提是与想象中的 "他者" 保持对称性的关系。分裂-发生的变化总是比它之中的参与者更强大。
(8) 每个人与这种力量的关系的质量和内容在 A.A. 的社交结构中得到指示或反映。这个系统的世俗方面,即它的管理,在 "十二项传统"(A.A.,1957年)中有所阐述,它是对 "十二步" 的补充,后者发展了人与力量的关系。这两份文件在第十二步中有所重叠,其中规定:对其他酗酒者的援助是一项必要的精神锻炼,否则成员很可能会复发。整个系统是一种涂尔干式的宗教,即人与社区的关系与人与上帝的关系相似。"总之,每个人与力量的关系最好用 "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句话来定义"。
(9) 匿名性。须明白,在A.A.的思想和神学中,匿名的意义远超过保护成员不被暴露和羞辱。随着整个组织的名气越来越大,成功越来越多,成员在公共关系、政治、教育和其他许多领域利用他们的成员身份作为一种积极的资产,已经成为了一种诱惑。本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Bill w. 本人在早期就意识到了这种诱惑,并在一篇发表的文章中讨论了这个问题(A.A.,1957,第86-294页)。他首先看到,任何抢夺焦点的行为都会对成员造成个人和精神上的危险,他们无法承受这种追逐私利(self-seeking)的行为;除此之外,参与政治、宗教争论和社会改革对整个组织来说是致命的。他明确指出,酗酒者的过错与 "今天把世界四分五裂的力量" 是一样的,但拯救世界不是 A.A. 的事。他们的唯一目的是 "将A.A.的讯息传递给需要它的生病的酗酒者"。他总结说,匿名是 "我们所知的自我牺牲的最大象征"。在其他地方,"十二条传统 "中的第十二条指出,"匿名是我们传统的精神基础。不断提醒我们将原则置于个人之上。"
对此,我们可以补充说,匿名性也是对系统性关系(systemic relation)的深刻表述,即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一些系统理论家甚至会走得更远,因为系统理论的一个主要诱惑在于理论概念的实物化(reification)。Anatol Holt 说他想要一个保险杠贴纸,上面会(自相矛盾地)写着:"消灭名词"(Wenner-Gren 基金会)。
(10) 祈祷。A.A.对祈祷的使用也同样肯定了部分与整体关系的互补性,其方法非常简单,就是寻求这种关系。他们寻求那些个人的特质,如谦逊,实际上正是在祈祷的行为中练习的。如果祈祷的行为是真诚的(这并不那么容易),上帝就不能不答应请求。这对于 "你所理解的上帝" 来说尤其正确。这个自我确认(self-affirming)的同义词,包含了它自己的美,正是在跌入谷底的双重约束痛苦后需要的安慰。
更为复杂的是著名的“平静祷文(Sernity Prayer)”:
"上帝请赐予我们宁静,接受我们无法改变的事;请赐予我们勇气,改变我们能改变的事情;请赐予我们智慧,使我们能分辨其中的区别。" (这不是A.A.的原始文件,作者不详。我引用了我个人喜欢的形式(A.A., 1957, p.196)。
如果双重约束导致痛苦和绝望,并深层地上破坏了个人的认识论前提,那么反过来说,对于这些伤口的愈合和新认识论的成长,对双重约束的颠倒将是适当的。双重约束导致了绝望的结论,"没有其他选择"。而宁静祷文明确地将礼拜者从这些令人疯狂的约束中解放出来。
在这方面,值得一提的是,伟大的精神分裂症患者 John Perceval 观察到了他的 "声音" 的变化。在他的精神病开始时,他们用 "矛盾的命令"(或我说的双重约束)欺负他,但后来当他们向他提供明确定义的选择时,他就开始恢复了(Bateson,1961)。
(11)在一个特点上,A.A. 与家庭或红杉林这样的自然心智系统有很大不同。它有一个单一的、组织致力于最大限度地实现的目的,“A.A.的信息传递给需要它的酗酒病人”。在这一点上,A.A.并不比通用汽车公司或西方航空更先进。但生物系统,不同于那些西方思想(尤其是金钱)的那些前提,都具有多目的性(multipurposed)。在红杉林中没有一个单一的变量,使得我们能说整个系统是以最大化该变量为导向,且所有其他的变量都是附属于它的;而且,事实上,红杉林的运作方向是最小值(ptima),而不是最大值。它的需求可以被满足的,任何东西过多都是不好的。
然而,有一点:A.A. 的唯一目的是向外的,旨在与更大的世界建立非竞争的关系。要最大化的变量是一种互补性的,具有 "服务" 的性质,而非主导。
THE EPITSTEMOLOGICAL STATUS OP COMPLEMENTARY AND SYMMETRICAL PREMISES
互补性和对称性前提的认识论地位
THE EPITSTEMOLOGICAL STATUS OP COMPLEMENTARY AND SYMMETRICAL PREMISES
互补性和对称性前提的认识论地位
上文指出,在人类的互动中,对称性和互补性可能被复杂地结合。因此,我们有理由问,在文化和人际关系前提的自然史研究中,怎么可能把这些主题看成是如此基本的,以至于能被称为 "认识论"。
答案似乎取决于在对人类自然历史的研究中 "基本" 的含义;这个词似乎有两种含义。
首先,我把那些更深地植根于头脑中的前提称为更基本的,它们是更 "硬编码" 的,不易被改变。在这个意义上,对称性的骄傲与酗酒者的傲慢是基本的。
其次,我将把那些指的是更大的而不是更小的宇宙系统或构架(gestalten)的思想前提称为更基本的。"草是绿的"这一命题不如 "颜色差异带来差别 "这一命题来得基本。
但是,如果我们问一下,当前提发生变化时会发生什么,很明显,"基本" 的这两个定义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如果一个人实现或经受了深植于他头脑中的前提的改变,他肯定会发现,这种改变的结果会影响到他的整个世界。这样的变化我们完全可以称之为 "认识论的"(epistemological)。
那么问题来了,什么是认识论上的正确,什么是认识论上的 "错误"。从酗酒对称性的 "骄傲" 到互补性的 A.A.的变化是对他的认识论的修正吗?互补性是否比对称性更好?
对A.A.成员来说,互补性永远比对称性好,即使是网球或国际象棋微不足道的竞争也可能是危险的。这一肤浅的小插曲可能会触动深藏的对称性前提,但这并不意味着网球和国际象棋为每个人提出了认识论上的错误。
伦理和哲学问题实际上只涉及最广泛的宇宙和最深的心理层面。如果我们深入甚至无意识地相信,我们与我们相关的最大系统:"大于自我的力量(Power)" 的关系是对称的和竞争性的,那么我们就错了。
LIMITATIONS OF THE HYPOTHESIS
假设的局限性
LIMITATIONS OF THE HYPOTHESIS
假设的局限性
最后,上述分析受制于以下限制和含义。
(1)并不是说所有的酗酒者都是按照这里概述的逻辑来操作的。很可能存在其他类型的酗酒者,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在其他文化中,酗酒者的成瘾性将遵循其他路线。
(2) 并不是说匿名酗酒者协会的方式是唯一正确的生活方式,也不是说他们的神学是唯一正确地从控制论和系统论的认识论中衍生出来的。
(3)我们没有断言人与人之间的所有联系都应该是互补的,尽管很明显,个人与他所处的大系统之间的关系必须是这样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将(我希望)永远是复杂的。
(4) 然而,我认为非酗酒的世界可以从系统论的认识论和 A.A. 的方式中学习到很多。如果我们继续以笛卡尔式的心物二元论来运作,我们可能也会继续以上帝与人、精英与人民、被选中的种族与其他种族、国家与国家、人与环境的角度来看待这个世界。一个既拥有先进技术又以这种奇怪的方式看待世界的物种是否能够持续下去,这是存疑的。
Oceanic Institiute Hawaii 夏威夷海洋研究所
落日间是一座有关「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迷宫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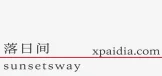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