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第一章 受表扬
第一章 受表扬
2014年度过了长达一年的恢复期,出院带8种(不是8片)口服药,吃完激素吃降压,吃完降压吃护肝。医生教我,激素会导致血压升高,所以要让降压药“迎着激素来”。每两周回肾内科复查,抽血、验尿,根据化验结果逐渐减少激素。从一天12片阿赛松减到停药,看病成了我的主业。每次复查,都因为恢复得好受表扬,油然而生一种在后进班当学习委员的感觉。嘈杂的诊室里,医生指着我对别的病人宣讲:“不要盲目排斥透析啊,身体不好该透就透啊,你看她,之前都不行啦,现在也恢复得挺好呀。”别的病人也不知道我之前怎么“不行啦”,没头没尾听了一句,就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我。
2016年底,通过核磁共振,确诊早期双股骨头坏死。股骨头坏死的病因有三种:激素、外伤和饮酒。我是激素造成的。即使早期几乎没有症状,即使是我这么想得开的人,也蔫了几天。当时不知道,这才哪到哪。
第二章 你来做个核磁,我们就有故事
第二章 你来做个核磁,我们就有故事
2017年5月5号,一个普通的周末。我去看电影,下车时可能步子迈大了,忽然觉得左边腰侧面一阵刺痛,就像有人拿改锥扎了一下,还挺深。每走一步都疼得抬不起腿来,别说上台阶,就连上电扶梯都成问题。忍着疼、蹭着地、拖着左腿走进电影院,坚持看完了《记忆大师》,黄渤不错。电影结束时,疼痛也消失了,像一场幻觉。但多次生病的经验告诉我,这个疼有问题。
5月7号,某综合性三甲医院骨科诊室,医生举着X光片,眯起眼睛看了又看,仿佛要破译出疾病的密码。他常规问,最近有没有扭到、抻到?指着X光上左边腰侧,说这儿看不太清楚,像一团雾。我赶紧接话,当时特别疼,您给开个核磁吧。医生似乎没见过这么没病找病的患者,但也尊重我的意愿,给开了核磁,自费800元。事后证明,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5月10号,请了半天假去放射科做核磁。作为一个专业病人,我提前换上了没有钢圈和金属扣的运动内衣,没有金属扣的运动裤,方便穿脱的鞋,不戴手表手机配饰眼镜。躺在核磁共振的检查床上,头戴耳机,双手抱肩,表情庄重,幻想自己是木乃伊,马上就要进金字塔了。这次核磁时间比平时长,滴滴铛铛一顿响。下床穿鞋时,放射科医生说:“给你多做了一截儿啊”。我迷迷糊糊地说谢谢,没意识到那意味着什么。
5月12号,担心请假扣钱,请父母帮我拿结果。正在上班,我妈打电话来,略带惊慌地说哎呀你长东西了,大夫让你继续看病,下午请假吧。我的腰后来再也没疼过,但我妈坚持,我只好同意,下午又做了CT。医生说,拿到结果咱们再谈吧。
5月15号,“你这个,有个囊肿啊,你看。”主任指给我看,肉眼可见的一个白球嵌在左髂骨上,和股骨头差不多大。我抬头:“那我在您这儿切了呗,能做微创吗?”骨科主任斟酌着说:“切是可以切啊,但是切出来万一不好,后续治疗我这儿也做不了啊,比如,嗯,化疗什么的。”
我一脸不明白,“为什么要做化疗?”
主任终于说:“你这不就是肿瘤嘛!还不小,拿手能不能摸到啊?”后来遇到的每个医生,都表示想抠一下髂骨,因为肿瘤特别靠边,想试试能不能摸到。
主任委婉地表示不收住院,建议我去肿瘤医院。他原话说:“你这个髂骨切掉了,以后穿裤子没法系皮带,挂不住”。去放射科取报告的时候,实验室的医生再次叮嘱我,要做穿刺活检啊,你要重视啊。走出医院大门,我俨然拥有了肿瘤病人的新身份。蔫头耷脑地跟老板请了长假,我长肿瘤了,要去看病,多长时间说不好。此时,距离确诊双股骨头坏死,仅隔了四个月。
第三章 “医生最怕不疼不痒的病了”
第三章 “医生最怕不疼不痒的病了”
5月17号,带着不甘心和全部的检查报告,我跑去骨科医院找熟悉的医生看。这几个月来,因为股骨头坏死,骨科医院跑得很熟,也有了固定复查的医生。我信任医生,医生也有一说一。他看了片子,说是啊,就是肿瘤,5厘米,还不小,这么靠外,能不能摸到啊。我就站起来给他按一按。他又翻出之前的X光片对比,“其实之前就有了,但没有核磁真看不出来啊”。
然后,医生用了很长时间引导劝慰我,说了很多苦口婆心的话。他说:“你不要怕麻烦啊尽快去看,别耽误,别觉得不疼就没事。我们大夫啊,最怕不疼不痒的病了。你去了挂骨软肿瘤门诊,做检查别怕麻烦,要全身扫描一下的。”他打了个绕圈的手势,“我只看髋关节,我院也有骨软肿瘤门诊,你要在这看我介绍你去某主任那。但还是肿瘤医院见得多点,效果可能好一些。别耽误啊尽快去。”
最后他说:这病不归我看,你去把号退了吧。
就这样,5月18号我去了肿瘤医院,距离第一次腰疼,只隔了13天。
第四章 肿瘤医院,从挂号到挂床
第四章 肿瘤医院,从挂号到挂床
看病比相亲更讲缘分。从门诊坐下说第一句话开始,病人与医生,都在互相判断。用最短的时间建立基本的信任,诊疗才能事半功倍。医生也是人,人都有个性,有人激进点,有人保守点。我看病的一点体会,越是大病,医生的个性对治疗的影响越大。所以治病要找合得来的医生,信任医生,按时交费,住院期间保证余额充足,一家人商量好由一个人负责谈话、签字、主事儿。这些细节,能让医患双方更舒服,让诊疗更有效率。
5月18号,办理住院。由于我是本地人,路途方便,所以先挂床,提前做好术前检查,安顿好孩子,紧锣密鼓准备开刀切瘤子。
肿瘤医院的气质和综合性医院不一样,病人比较焦虑,比较犯愁。挂床半个月,我做了各种术前检查,第一次体验全身骨扫描。
PET-CT(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俗称“全身骨扫描”,是将放射性药剂注入血液中,再用仪器扫描出骨破坏的部位和数量。全身骨扫描有辐射,因此坐落在门诊楼外的平房。注射放射性药剂之后,病人就变成了小小的辐射源,建议1-2天少去人多的地方,不接触孕妇、儿童,在家多喝水多休息。药剂8000元,注射当天不能安排胸透。经过短暂的排队,我把胳膊伸进窗口,全身防护服的医生为我注射,虽然是很厉害的药,但并没有什么特殊感觉。再次排队躺在机器上,大夫让躺平,双手贴紧腿两侧,用绑带把人固定在机器上。机器一开,眼前的“天花板”离我越来越近,明知不会有伤害,但还是害怕,握紧了拳头。几天后取结果,显影出整个一幅骨架,股骨头的地方有点黑,肿瘤的地方有点黑。后来在网上浏览对比,恶性骨肿瘤扩散后的骨扫描胶片,就像在一副骨架上,撒了一把椒盐,密密麻麻一片黑点。
结果拿给医生看,他看的时间越长我越慌张。医生:“哎?你这股骨头也挺厉害的啊?”“你先别管那个,看瘤子,瘤子。”
第五章 世界上最动听的话
第五章 世界上最动听的话
2013年子痫,身在其中其实也不知道什么,给治就治,给药就吃。五年后,孩子大了,父母老了,这次是真的怕,怕结果不如所愿,怕手术横生枝节。世界上最动听的话不是“我爱你”,而是“你的肿瘤是良性的”。办理入院填写既往病史,我一犹豫,主管医生说“填齐了啊,来看病可不许骗大夫啊”。我嬉皮笑脸:“没有,哪能呢,是格儿太小,写不开”。肿瘤医院的医生通常更委婉,会刻意避免提“肿瘤”二字。做各种术前检查时医生都问“你这个是怎么发现的呀?”医患共同的默契是,只问怎么发现的,不问怎么得的,也不提它的名字。
在门诊做了活检,很便捷。侧躺在狭窄的床上,医生用一个订书器一样的仪器贴在髂骨位置,咔哒一声,快得感觉不到疼。取一点点肿瘤组织做病理检查。有了活检结果做基础,感觉医生更放心了。骨肿瘤介于良性与恶性之间,所以要切掉,不切可能会病变。直径5厘米多点,比乒乓球大一圈。人的骨盆左右对称,各分三个区,肿瘤贴近髂骨外侧,几乎要切掉一个区。幸运的是髂骨不承重,切掉没什么影响。医生说会努力保留一部分髂骨,不然以后穿牛仔裤没法系皮带,挂不住。
医生说,我们对手术不担心,但是担心肝肾功能,毕竟受过损伤。说起之前在ICU做过骨髓穿刺,医生不无遗憾地说,你要是当时在左髂骨做穿刺,就能查到这个肿瘤了,这么大,不是一两年长成的。2017年孩子已经五岁了,而肿瘤可能是她姐姐。
第六章 “您等着,我给您摘个寿桃”
第六章 “您等着,我给您摘个寿桃”
6月5日,我被安置在监护室,监护室收集了骨软肿瘤科即将手术和刚做完手术的病人,不同的年龄和背景,共同点是都有肿瘤。老人身边是沉默不语的中年儿女,年轻女孩身边是焦虑聒噪的母亲。
下午插了尿管,做了灌肠,给我手术的主任风风火火走来,拿出马克笔,在我身上画线标记。我痒得嘻嘻嘻,他就装凶说你还笑,我都要愁死了。主任刚走,护士过来备皮,三下五除二,把我整个侧身刮成半扇光猪。然后用超大棉球淋着碘酒洗刷我,我一边不敢动,一边担心刚画的线擦掉了。
监护室不允许探视,晚上护士发了某某西泮的助眠药,我问,自己能睡着,还吃吗?护士说那别吃了。夜里有病人痛苦呻吟,我也没耽误觉,我有耳机,还有郭德纲。
6月6日,麻醉医生来接人,他问你能自己走吗?我应声而动、一窜下床,摘掉眼镜,揣着尿袋,趿拉着拖鞋擦擦擦地跟着。早已等在门口的我爸我妈,我妹妹,姑姑姑父,舅舅舅妈,跃跃欲试又不敢一拥而上。我狐假虎威地跟着医生上了“手术专用梯”,舅舅一直在旁边小声说:走慢点,疼;走慢点,疼。
手术当天是我爸生日,我说:“您等着,我给您摘个寿桃”。
到了手术室门口,护士接手说:家属,给病人换上拖鞋。我妈明显已经慌了,拎起拖鞋就往自己脚上套。我说了两遍“给我”,才抢回来。她的手微微发抖,可能天下的妈妈都是一样的。
前一位病人还没离开,医生给我一个圆形不锈钢皮革面马扎,说你坐门口等会,喊你再进去。我点点头。他又说,你离门远点,那是电动推拉门,别撞着你。我眯着眼目测了相邻两扇门的走向,在它俩都碰不着我的地方坐下来,满脸高度近视的呆滞。
进手术室,脱掉上衣,小跳一下蹿上手术台躺平。右胳膊架在一个窄台面上,还挺舒服。医生在我胳膊肘弯扎了留置针,说一句“我推药了啊”,再睁眼,已经推回监护室。
回到监护室,我意识清醒,想跟爸妈说“我没事,都挺好”。但是嗓子哑,又头晕,大胯戴了C形的护具,挣扎几下还是躺下了。找护士要了一口水喝,晚上吐了三次。我在那嗷嗷吐,吓得第二天手术回来的五个病人谁都没敢再提喝水的事。护士帮我卡住了止疼泵,说这是麻醉药代谢的身体反应,会好的。提前买了产后束腹带,帮助保护伤口,生孩子都没用过,这次体验到了。又焐又紧,护具又硌,就像躺在一本精装书上。就这么过了术后第一晚。转入普通病房又躺了两三天,才终于不晕了。有了这次麻醉经验,两年后股骨头置换,和麻醉医生探讨后,选择不用镇痛泵,舒服多了。
第七章 IPad那么长的封贴,一次用一根半
第七章 IPad那么长的封贴,一次用一根半
经过病理诊断,确诊为骨巨细胞瘤。听说它好可爱,像骨头上吹出了一个个圆泡泡。手术切口比较大,缝了22针。术后插了几天引流管,从负压引流过渡到自然引流,又复杂又科学。我有些害怕引流管,总觉得它与血肉相连,医用橡皮膏封住管子与封贴的交界处,像一扇通向体内的、神秘的门。
有一次我正在输液,就觉得嗓子眼痒。难受的感觉一点点浮出来,有点喘气,有点疲倦。忍了一会,又忍了一会,不舒服,又更不舒服。喊我妈,“给我拿个盆儿我要吐!你去叫大夫!”主管医生跑过来,看看我说,你吸点氧,然后叫护士换药。我治病其实很少觉得难受觉得疼,这是一件印象比较深的小事。生病不难受,未知才难受。
每次换药,医生把伤口露出来,涂一遍碘酒,观察之后换上新的封贴。刀口前起于髂骨的尖尖,绕着髂骨划了一个半圆,向后几乎到尾椎,一道圆润美丽的弧线。Ipad那么长的封贴,拐着弯一次用一根半。出院前夕,我问能不能在社区医院请医生出诊换药,能不能在家自己换药。主管医生说,最好还是回病房,谁手术谁负责;病人没有专业医学知识,自己在家换药可能伤口感染了也看不出来。每一个细节,都关系到病人预后的生存质量。
刚出院时大腿不能弯,只能平躺,打120去医院换药,劳师动众。后来买了折叠轻便轮椅,父母推我出行。我一个夏天没晒太阳,白得发光,仿佛再世为人。
第八章 生活没有剧本,人生仍在继续
第八章 生活没有剧本,人生仍在继续
拆线回家第一次站着照镜子,放松下来有点自怜自艾,伤口又大又深,像鳄鱼的嘴角。皮肤神经切断了,左大腿外侧没有触感,木木的。医生讲神经要“慢慢爬”,也许就恢复不到原样了(坏消息是截至2022年底仍未完全恢复,好消息是习惯了)。直到现在逛商场看到巨幅内衣广告,模特露出美丽的髂骨,都会有点羡慕。但医生说话算话,留了一个尖尖的髂骨尖,我现在穿牛仔裤,还能系皮带。
因为肿瘤有可能复发,所以术后两年定期复查。每三个月做一次B超和X光,输一次唑来磷酸,国产药几百块,进口药两千块。因为坚持用进口药,躲过了发烧的副作用。但药劲儿大,输完跟抽了骨头似的,能在家躺一天。两年复查即将结束时,2019年5月又做了右侧股骨头置换手术。当我再次带着全新的股骨头去肿瘤医院复查,医生也很高兴。我说谢谢您给我切得这么好,医生说哎,别这么说,是你的肿瘤自己长得好。
感谢现代医学,感谢车轮战、流水席一样治疗我、照料我的医护人员。我就像墙上摔下来的蛋头人,你们又一次拼好了我。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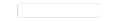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7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