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这是之前一篇文章【神曲·沉淹】的节选。
因为那篇真的没什么人看,所以想着把自己觉得【很有画面感、很让我自己对这个感觉着迷】的片段节选出来,再给大家看一下!
其实这篇文章没有什么故事性,只是一个【落下第二巴别塔后向下沉去,来到灰白村落之前】的一段描写【塔下世界,即耶路撒冷下巨大深渊的环境和氛围】的序章。
关于【主线的地点推进】的话,是:
【落塔】→【慢长的沉淹】→(骨沼)→【灰白村落】→大断崖→神垂之林(花女之地)
那我们就开始吧!最后有一段碎碎念哦!
神曲·沉淹(节选),ON!
【片段1】
【片段1】
我深入临时的水底,听那腐烂的奏鸣。莲花开出泡沫向上飘去,纷纷攘攘聚合在一起倒成了肉瘤,于是忽然重了,沉着,落着,不知觉间又噎回那花的嘴里,涨得茎与叶通红。红得发烫,灼了脚下的土生疼,一粒粒土与沙疼得尖叫起来,奏起一股烟去熏那海,海水呛得连连咳嗽,一用力竟然咳出了血红——每一滴水都开出火红的花来,包裹着花与土的海水迅速弥散了半透明的血色,而那红触及了含在花里的肉瘤,竟发出噼啪声来,那瘤上的疙瘩爆出脓白的浆来,顺着气泡向上浮去,忽然又凝固住——长成了惨败的鹿角如尸首,岔成了枯木的老枝张牙舞爪。
就算是死了也再逃不出这里——正如瘤死了的脓被水囚住,又如枯木被风在冬日钉死住。
第二次的死从不柔和,灼烧与冻伤的若只有肉体,那也是此处容不下的仁慈。
“来,于是无处可去。”
那声音是死寂里唯一的回声。没人知道从哪里发出,又远远不知要飘去何处。非男非女,时高时低。若说上帝的嗓音是无可形容的至高,那这声音便在地下坐于同等深度之不可形容。——但它是死寂里唯一的活的意志,如是空寂的教堂里短促却不停反复的尖声嘶鸣,却是孤寂空虚灵魂们日夜渴望的唯一刺激——即使它的恶意从无时无地滋生,又向着每时每地扩张蔓延,病菌的黑色与极乐的红粉,没入骨的隙里于是繁殖,直到那余音飘远消散,带来死亡的声音却携着希望,一通融散了。
【片段2】
【片段2】
在肉盖下的湖面,暗红的光照出夕阳的氛围,恰逢我的魂灵同那残照一同下沉。死亡铺满这小世界的穹顶,压着我的头顶坠向永夜;巨骨的白同敲碎的云。升腾的沸泡裹着湖的喃喃,我多么渴望听到他人的声音啊,于是抓去一把来听,然抬起手时那言语里的信息与活的意识却同我烫烂的皮肤一同碎成细沙,顺着无所不知的缝隙滑落,沉回深渊的思想里。
散落的沙与血滴进我的倒影里。我看见了自己,湿透的长发竟然还未脱落头顶,失去皮肤而通红的肌体已经看不出我的脸庞。但我想起了曾经自己的脸,于是那脸上皮肤突然又顺着耳下生了出来,如苔藓般迅速蔓延铺满了我的头颅。我惊诧地摸着自己复原的脸。那肉盖突然剧烈震动起来,穹庐上猛然伸出一道道臂膀,以我的头作了中心。他们尖利地笑着,嘲讽的意味涨满了狭隘的空间。
“他们会……认出你,会,认出你……咕……会的……”
【片段3】
【片段3】
那些花是从一具具亡魂身上长出来的,那花瓣根底包围外的一圈是血肉的沟,坑坑洼洼的沟啊,漫嵌着被曾经的火球烧焦的肉碳。那些肉碳一跳一跳的,从不知哪里长出的发育不完全的嘴里,替着他看来早已失去生命反应的亡魂肉体发出尖锐而闷沉的号哭悲鸣——世上最哀的,也莫过于如它这般未有思想却真切地在悲伤。花瓣向着肉碳躺卧的血沟卷曲,仿佛是母亲伸手想要安抚襁褓中的孩子,有几个触达它黑色孩子的,就被烫焊在了血沟里,呈了环,也似拱门,也同肉碳一般作了漆黑的颜色,而失去了其作为原来体内地肌骨内脏那材质的惨白与橙红。
它们的主人被剜空的不止是腹部,还有口与眼。
那树上还回荡着哈尔比的咒骂,即使骂声的主人早已沉没到更深处——这原惩罚者的陨落或许预示着原有秩序的崩塌,于是未知的恐惧从身下的黑里伸出冰凉的五指,摸住了我的后颈。而随着枝体的沸腾弯软,我只是不得不继续下沉。
其间我见大的分枝处有着一个个幽魂,极尽扭曲而动弹不得,它们且长在了一起,有的脖子长出别人的手臂,有点口中戳出他人的脚掌,他们互相责备咒骂,愈发滚烫的水也幸灾乐祸,助燃着他们的愤怒与自相撕咬。彼此斗着,始终没有停歇。
【片段4】
【片段4】
米诺斯的巨型头颅在水中浮起,星点臃肿的乳白掏空了其中的营养,于是从一个个孔洞中探出头来向我张望,饥饿在他们肥满无脸的肢体上用一翕一忽的唯一孔洞表达着迫切的渴望。
脸上的肉已然粉碎成泡沫般淅淅粒粒,随着白蛆的探出被带出,噗吱噗吱地卡在孔洞边缘,如毛绒的垫托住了那群外来住客的肥肚。
顿时所有的蠕动一同静止了,耷拉在了孔洞边缘——那巨大的头颅开口了,露出里面一圈圈被白虫缠绕排布的舌头,发出来巨大震动——说出了话来。
“……新的……主……身体,……我,快乐……但是我……变成了谁……?”
我不知道是蛆的思想还是米诺斯的余念,让那声音传递出其背后灵魂的意志。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甚至不清楚自己是不是在被问一个问题。
“你是谁?”我问道。
“……快乐的……虫子……?”那颗头不确定道。
我知道问下去也不会有结果,于是从它身上拉出一管虫子作了口粮储备,任凭上浮的头颅在失去如今自己的一部分后发出哀嚎,拱着面部肌肉向我扑来。但它失了一条虫子就更轻了,于是只是上浮得更快了。
我咬掉那虫的屁股上连着头颅的脐带,顺带扯出了内脏。
它很快就不动了。哀嚎愈发凄厉,愈发远去。我越沉越深。
【结束语&碎碎念】
【结束语&碎碎念】
当时写完【神曲·沉淹】,真的感觉自己有种san值掉光的轻松感。(?)
一切思想中混沌淤积的东西因为自卑而一直出不来,直到终于用文字外化了其中的一部分。于是思想的业障也稍稍轻了一些。
渴望无数的死亡,却依旧要活着。
眼中有悲观的病,于是流出的泪里掺了脓,脓里的卵孵出了未来的模样。
我也想如我那世界里的【虫树】般,成为最悲惨的希望,却不用再思考。
我只需要默默生长,让一切悲欢离合都与我无关。
在安定里半死不活,却成为希望。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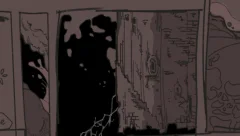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