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抵达乞力
抵达乞力
从非洲传出来的消息全都是坏消息。正因为如此,我才想去那儿,只不过我不是为了那儿的惨状、纷争,也不是因为报纸上屠杀与地震的报道,我只是想要重温身在非洲的愉悦。
——保罗‧索鲁
过去三年,如果有人问起我,可以出门的时候你最想去到哪里?我的答案一直是非洲。这着实有一些奇怪。因为作为一个深中蓝毒10年的潜水员,我最想念的理应是大海,时不时抓心挠肺让人不得安宁的也是大海,最想第一时间回去的,却是那仿佛没有生命,又充溢着生命的土地,想去再次感知那些风尘仆仆的道路和过去。
我很想再去一次,解释这个中缘由。于是我们再次出发,这次我们乘坐的是埃塞俄比亚航空,经刚刚摆脱战火和内乱不久的埃塞首都亚的斯亚贝巴中转,前往坦桑尼亚。在出发之前我对这个地方一无所知,保罗称埃塞人民是“身无分文的贵族民族”,既高傲又贫乏,因为埃塞在黑人非洲中非常独特,他们有自己的文字,因此有属于自己的书写历史及对过去的强烈认知。
亚的斯亚贝巴机场结构简单,大平层一般的建筑物中充斥着在此中转的欧美背包客,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匆忙的生意人面孔,人们大多聚集在几家餐厅里打发转机时间,品尝着称不上好吃的食物。
抵达乞力马扎罗机场是午后,我们顶着非洲正午的太阳,吹着当时还因兴奋感觉不到的热带暖风,跟着背包客的人流来到航站楼前,工作人员在此核对护照与登机牌信息,长长的队伍移动缓慢,但也许因为大家都兴奋不已,也没有人表现出疲惫。
在海关窗口,我们开始逐渐感受到这个国家的办事效率,并在后续的行程中不断验证并无奈的接受。保罗在自己的非洲大陆旅行书中曾经写道,非洲人对时间的态度如此满不在乎的原因是:在非洲,没有人的生命能长到足够成就任何实质的目标,或亲眼看到任何重要工作的完成。这次旅行的伴读,我选的是保罗鲁索的非洲游记:暗星萨伐旅,从开罗到开普敦 ,一本横跨非洲大陆的旅行文学作品。保罗在书中不仅倾诉了对非洲的喜爱,同时也大力的批判了城市的腐败。
塔兰吉雷的猴面包树、象群与巨大彩虹
塔兰吉雷的猴面包树、象群与巨大彩虹
早上吃过早饭,我们准备正式出发safari行程。首先需要与未来几天和我们深度绑定的向导见面,大厅的safari车辆来来去去,我始终没有找到自己的名字,于是只得请求酒店工作人员的协助。很快,一个体态丰满,带着宽边眼镜,与其他非洲人身材格格不入的人张着双臂向我走来:“我一直在大堂等你,你在哪里?你留的名字是Piero,我还以为我来接的是一个意大利人!”
Francise出生在Arusha郊外的一个小镇,现在定居Arusha,并且已经做了15年的safari向导,从他的父亲手中接过衣钵,未来还有可能继续教他儿子成为一名优秀的向导。
继续在A104公路上行驶,约莫一个半小时之后,我们抵达了第一个国家公园,塔兰吉雷国家公园。因为几年前在肯尼亚地狱之门的自行车和徒步之旅,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所以我也在行程中安排了一次徒步之旅,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场徒步会发生在非洲草原的正午12点,这个时间,即便是动物,也不愿意在艳阳下多做逗留。
Francise从此刻,开始展现出了他最优异和始终如一的品质,交际。从我们踏入国家公园的时刻,一直到行程结束将我们送至机场飞往桑给巴尔岛 ,Francise没有漏下在路上遇到的每一个safari向导、同事、朋友,甚至是路边岗亭的警卫、闸机旁的工作人员,他与每一位与他擦身而过的司机欢谈,击掌,甚至与新碰面的同行进行自我介绍。他是这草原上唯一一个始终保持活跃的生物,不论是正午还是清晨。
旱季的草原可以毫无生机,但这里的每种生命都懂得如何发挥自身的毅力和创造力,特别是猴面包树。塔兰吉雷公园里有许多非洲猴面包树,有时候又被叫做倒立的树,因为与粗大的树干相比,它的枝条纤细,看起来更像一个复杂的根系。这种树木被誉为非洲的生命之树,因为它不仅可以给自己也可以给其他动物与人类提供水、食物、住所,甚至治疗疾病。
在林中徒步让我们有机会走近观看这种树木,避开一丛丛低矮的灌木,朋友甚至爬了上去,确实可以居住,甚至比胶囊旅店还要宽敞些。与其他树不同,猴面包树的树干没有年轮,其实这棵树本质上是一棵巨大的多肉植物,在其巨大的树干中储存水,人们用放射性碳测法推断它的寿命可以高达 3000 年。
我们的路线大概是从公园管理处出发,横穿一片林地,抵达汇合点。这片林地四周不远处,有明显的人类活动痕迹,所以在正午时分发现动物身影的机率更加渺茫。随着我们的深入,灌木丛逐渐变得又密又高,还出现了带刺的一丛丛低矮灌木。我开始在林地里满头大汗的做起了高抬腿动作。向导时不时指给我们常见的果子,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开着玩笑。偶尔我们也会听到动物的声响,看到野猪一晃而过的身影,我们还发现了大象的粪便,新鲜的与陈旧的,想来在气温比较低的清晨和傍晚,象群应该会经过此处。站在土地上,才会发现,大象的脚印竟然可以有一个人的拥抱那么宽。
我知道在这样的路线上遇到野生动物的机率不会太大,但我还是走近了草原,得以细细观察它的一草一木,就好像一个简单的道理,想要养好一株植物,种好一种庄稼,惟一需要的就是将双手插进土里。双脚踏在坚实的土地上,一路捕获那些附着在你衣物上,拼命想散播生命的种子与花草,尝试体会擅长行走的非洲部落人们的日常,在烈日下用力的大口呼吸,在干旱的风中再次意识到自己的渺小。
成功与Francise会合后,我们驱车前往午饭地点,半路经过一片沼泽地带,遇到了此次safari的第一队象群,他们镇定的穿过游猎的车队,与探出头的人们擦肩而过。人群安静异常,都在屏息等待他们缓缓的经过,虽然大象看起来温和,但仍然有可能被喧噪的声音惊到,而受惊的大象是非常危险的。我们都很喜欢观察大象,尤其是巨大而美丽的象牙,大象永远沉静、自若,在皮肤褶皱间的双眼蕴含着智慧的光辉,人们会不自觉的屏息,并安静下来。
我们在一处休息区的树荫下,享用了午餐。今天的午餐相比后面几天,可以称得上是豪华。蒸薯角和米饭,彩椒和白菜,鸡肉和牛肉,面包和玉米豆子汤。Francise还给我们准备了当地啤酒,结束了近两小时的烈日徒步,能啜饮一口清爽的啤酒,此前的炎热与疲惫都一扫而空了。
今晚的住处位于国家公园北部地区的一座小山上,一个一个的小帐篷沿着山脊而建,坐在帐篷门口就可以远眺山下的塔兰吉雷河和美丽的河谷风景,个头娇小的柯氏犬羚穿梭在帐篷之间啃食青草,酒店里大概有四五只柯氏犬羚,平时就安静的卧在前台外边的花园里,我注意到有非常多年纪较大的欧美游客,老年夫妇,结伴来到这辛苦又遥远的非洲大陆,对周遭报以礼貌而善意的微笑,安静而沉默的用餐。酒店白天断电,只在公共休息区有网络信号,天黑后不能独自出行,终于又过上了这种简单清净的时光。
在非洲,清晨和落日前是游猎的黄金时间,气温舒适,野生动物活跃。草原上有区域落了雨,当我们行驶到一片空旷地带,一条巨大的彩虹突然映入眼帘,它完整而清晰,横跨了眼前的整个塔兰吉雷草原,在此时稀薄的云层下展露无遗,而一队大象,正慢悠悠的走入林地,走向那道彩虹的末端,所有人丢失了语言。对我来说,那是最特别的时刻,完全敬畏地凝视着这些美丽的动物。我站起身注视,惊叹于彩虹可以如此宽阔,七种颜色竟可以如此泾渭分明与清晰可辨。
彩虹过后,临近黄昏时分,气温已经下降,一切都变得凉爽宜人与可爱。天空中开始布满了棉花糖一般的蓬松云朵,随着太阳落下,云朵逐渐变得稀薄,化成烟尘的形状。Francise带我们来到草原上最标致的面包树旁,静静等着落日的余晖从猴面包树倒转的根系中穿过,将枝桠映衬得更加美丽。
返回酒店的途中,我拍到了此次坦桑之行最喜欢的照片之一。任何一位野生动物摄影师或爱好者,他们心中都有一个最想拍摄的“那一刻”,这可能是一张可以定义摄影师职业生涯的照片,是爱好者多年来梦想的一张照片。再次回到非洲,我更希望能拍摄到一些美丽的自然、和谐的生态和有故事的照片,或者可以用时下最流行的“氛围感”来形容的时刻。一只雄性水羚,听到车子的声响,从灌木丛中抬起头来,静静凝视着我们,而它身后的落日余晖将灌木与它都镶上了金边。水羚长得俊美异常,它的腹部、喉部、嘴部及眼睛外圈为白色,这让它的嘴角似乎带着一丝笑意。
出乎意料的,坦桑尼亚的傍晚竟异常潮湿,而且几乎夜夜落雨。入夜后床铺开始返潮,第一晚我们都睡得有些不安。全程的帐篷都是双层防护,帐篷内鲜有蚊虫,帐篷外却热闹许多。在这里的每个晚上,都伴随着虫叫和鸟鸣,因为种类繁多,竟形成了和谐的协奏,让人不会觉得单一和吵闹。
Ndutu的猎豹三兄弟与花豹母子
Ndutu的猎豹三兄弟与花豹母子
坦桑尼亚的几大国家公园风光各有特色,让人丝毫不会审美疲劳。塔兰吉雷国家公园的风景和植被非常多元化,与广阔寂寥的塞伦盖地和自成体系一派恬静的恩戈罗火山口不同,大片的猴面包树、茂密的灌木和高长的野草,与沼泽河流在塔兰吉雷完美地融合在一起,妆点了一座座小丘。虽然没有湖泊,但塔兰吉雷河由南向北贯穿整个公园,作为一条永久性河流,为那些旅居的野生动物提供了水源。
今天我们前往的Ndutu地区实际上属于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的一部分,但同时也延伸到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的南部未围栏区域。因此,Ndutu既与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相关联,也与塞伦盖蒂国家公园相连,是这两个保护区之间的一个过渡区域。这里拥有起伏的草原和碱性湖泊,以及沿岸茂盛的金合欢林地,这些湖泊与林地吸引了成群的火烈鸟与非洲秃鹳、椋鸟等鸟类,整个林地热闹非常,是极佳的观鸟地。
坦桑尼亚大部分北部环线探险活动都会经过这里。十二月到三月是角马产仔的时间,又被称作calving season,通常被认为是角马大迁徙的开始,尽管大迁徙其实是一个持续的旅程,永无休止。12月开始,新生牛犊陆续出生,也为这个区域的常驻捕食者们提供了食物,大量大型猫科动物与大量新生有蹄类动物混在一起,非洲大草原每天都在上演戏剧性的捕猎画面。在大多数国家公园,车辆不允许驶出小径,或者开进林地,因此很难追踪狩猎中的掠食者,或者更近距离的观察野生动物。但是在Ndutu,游猎车辆可以开到任何地方,甚至可以近到仿佛要从狮子脸上开过去,Francise就是这样秀他的视力和车技的。
而一月下旬开始,这里的天气也是一年中最令人惊叹的时节。风暴单元可以在几分钟内滚入滚出,当与坦桑尼亚强烈的阳光混合时,天空的景色令人惊叹。
我们深入林地,在绿油油的灌木叶子中发现了猎豹三兄弟的小脑袋,而在它们前方不远处,是一小群角马。Francise告诉我们,这些猎豹应该已经非常饥饿了,如果我们幸运的话,也许能看到捕猎的场景。人群开始兴奋,游猎的车辆逐渐聚集起来,三兄弟处乱不惊,时不时站起身跟随着角马群走几步,始终保持着一个安全距离,角马吃草的时候,这三兄弟就在草地上打滚,洗脸,和家里的大猫毫无二致。
Francise一点没闲着,一边帮我们找最合适的机位,让我们永远在豹子的脸前,一边和遇到的每一个人交谈,我们已经逐渐习惯了他的这种背景音。我们拍着照、交流着相机的参数、观察着这些大猫,回想起在肯尼亚遇到的猎豹,通常是比较隐蔽的躲在草丛中,看不太清楚,哪里像眼前的三兄弟这般,毫无顾忌。
安静的等待了大约40分钟,我们发现猎豹仍然没有发动进攻,Francise果断的发动汽车准备离开,因为他觉察到此时的风向并不利于猎豹狩猎,气味会随着风传给角马,并不适宜发动攻势,怪不得三兄弟只是跟着角马,也并没有捕猎的意图。
行驶了没多久,我们又发现了另一种难以观察到的生物:花豹。花豹通常会藏在树上,他们的斑纹是非常完美的掩饰,Francise带领我们来到一片林地,这里灌木丛生,高大的合欢树是非常完美和隐蔽的栖息地,而树上就趴着一大一小两只花豹。我们在此等待了一会儿,竟然等到了花豹下树,得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他的身影,这并不常见,因为花豹相比猎豹和狮子更加谨慎,通常在夜间活动,对人类和车辆也没有那么熟悉。花豹的体型较猎豹更粗壮,身上的斑点近看起来很精细,霸气异常,和猎豹完全不同,大爪子看起来很有力,非常适合爬树。
而我更喜欢的,是眼前这片林地,层层叠叠生长茂盛的灌木像极了电影侏罗纪公园。很难想象竟然在非洲大草原可以看到如此丰富的自然植被景观。
Ndutu这片林地有非常多的鸟类,紫胸佛法僧是肯尼亚的国鸟,但是几年前在肯尼亚我们却没有看到很多,如今在Ndutu几乎每一株灌木的枝桠上都停靠着这种鸟,这种鸟仅分布在非洲,上体是淡棕栗色,下体淡蓝色,背上辅以黄绿色和褐色的羽毛,翅膀间还有亮蓝色的羽毛点缀,整只鸟五彩斑斓,异常美丽。
结束游猎后,我们返回营地。在Ndutu,我们选择住在移动营地,这也是这片区域的一大特色。相对于设施较为齐全而传统的营地,移动营地的陈设朴素简单,对周遭环境的破坏与影响相对较小。一小片空地足以,帐篷使用简易的木制底座直接放置于林地之上,方便拆卸迁移,因电力有限,白天大家在外面safari的时候没有电,傍晚所有的电子设备可以在公共区域充电,网络信号也是只覆盖在公共区域。
每日的水是限量的,洗澡使用的是简易的装置,将收集的干净雨水过滤后人工升起至帐篷顶端,每次可以使用30L,快速洗完是足够的。
所有资源突然受限,人们被迫减少活动。减少使用网络、减少不必要的行动、减少某些洁净自身的需求、减少在草原上完全无用的化妆、卸妆和娱乐活动。信息、忙碌与焦虑随之减少。每天返回营地吃完晚饭几乎已经接近21点,星空已经显现,这里不是什么黯夜星空保护区,但由于光污染较少,星空的模样低垂清晰可辨。
奔腾的大迁徙与动人的非洲画卷
奔腾的大迁徙与动人的非洲画卷
早晨很早就醒了。虽然清脆的鸟鸣声不断,但夜晚睡得很踏实,朋友说听到大型动物的喘息声,我一点也没察觉,Francise推测应该是角马。我走出帐篷,太阳还没升起,繁星都还挂在天空,隔壁帐篷的一对美国老人已经并排在帐篷外坐好赏雨,向我问好了。这对老年夫妇,看起来已经年近80,尤其是老爷爷,感觉走起路来都是颤颤巍巍。
营地还没有完全苏醒。昨晚的雨水丰足,地表湿润,我穿着冲锋衣,甚至还有点冷。今天的游猎是最舒服的节奏,在凉快的清晨出发,中午最热的时候返回营地午餐,傍晚再出发寻找动物。吃完早餐准备出发的时候,太阳终于升起,阳光穿透合欢树梢,洒在整片营地上。
我们直奔河谷高地处,这里可以远观清晨升起的热气球,却意外的发现了正在进食的两只母 狮子与一只公狮子,一时眼睛竟有些不够用,不知道该看向远方还是眼前。
我们抵达的时候公狮子已经差不多吃饱,两只母狮开始凑过来大快朵颐。这是一只角马,牛角形状清晰可辨。围观的车辆丝毫没有打扰狮子的兴致,姊妹两个吃的懒懒洋洋,除了牙齿费力的撕咬,其他地方哪也不想动,有一只竟吃着吃着倚靠着尸体睡着了。从动物的体型和状态不难看出,大迁徙时节的草原食物充沛,遍地都是圆滚滚的肚子,不是吃的饱饱的,就是怀孕待产的母亲。还记得同样在2月,我在肯尼亚的马赛马拉看到的公狮子饿的皮包骨头,毫无威严可言。
远处,薄雾尚未散去,层层叠叠覆盖在河谷、合欢树梢、飞起的热气球下。高大的蛇鹫立于树梢,与热气球交相辉映。这种鸟可以高达1.2米,有一个官方认定的别称“秘书鸟”,因为脖子顶部有长长的羽毛,让人想起古代抄写员在工作休息时懒洋洋地塞在耳朵上的那些鹅毛笔,朋友笑说蛇鹫的发型就好像每天早上匆匆起床打工的她。
紧接着我们发现一头怀孕的母狮,肚子已经很大,看起来即将生产。Francise说她会像所有猫科动物一样,找一个安静隐蔽的地方生产,确保不被人发现,而不多久她应该就会上树,因为孕晚期让她坐立难安,这点和人类的情况一样。Francise的判断再次应验,虽然有孕在身,但母狮上树的动作还是非常轻盈,她给自己找了个舒服的枝桠,正对着我们坐了下来,大大的肚子横亘在树干上,显得悬垂的爪子更加肉乎可爱了。
但她没有维持太久,脸上的苍蝇让她烦躁不已,沉重的腹部也让她坐立难安,时不时站起身走动,最后又下了树,躲到了树丛中。我觉得很有趣,这一次我不仅像集邮一样看到了更多的动物,也观察到了更多的动物行为。几年前我去到肯尼亚的时候,就惊讶于动物行为的多样性,相比我们从小在动物园中目睹的大型哺乳动物,大多数时候都是睡觉、发呆或乞食,这其实是动物园的丰容不够,动物表现非常不健康的一种行为。在肯尼亚的时候,我已经目睹了灵动的动物行为,象群的迁徙,野猪的放哨,长颈鹿的奔跑与聚集等等,这在野生动物园也是难以目睹的。在坦桑尼亚,我解锁了更多有趣的过去只在纪录片中目睹的场景,母狮哺育新生儿、猎豹的跟踪捕食、象群在水中的嬉戏玩耍、角马和斑马的长途奔袭、草原上的杀戮盛宴。
现在我不再去任何的动物园了,我仍然认可动物园的教育意义,但却再也无法忘却真正自由的场景。我们也没有选择乘坐热气球俯瞰草原,因为我和朋友都觉得应尽可能减少一些人类的痕迹和影响,人类喜欢观看的充满戏剧冲突的大迁徙过程,充满血腥和杀戮,极其残忍,而我们却以等到、看到、拍到为一种达成,这似乎并不是应该从大自然中获得的感受。
气温逐渐升高,我们从林里驶出,来到lake elemeti附近的河谷地带。眼前突然出现一片空旷的低矮草地,一小群长颈鹿立于期间,三三两两保持着一定的距离。Francise解释说长颈鹿既可以群居也可以独居,而它身上的花纹颜色越深,代表着年纪越大。我突然羡慕起来,它们可以自由选择是做一个i人还是e人。我们花了一些时间确定长颈鹿的种类,非洲有三种长颈鹿: 马赛长颈鹿、罗氏长颈鹿和网纹长颈鹿,最终通过他们身上边缘参差不齐的斑纹确定我们看到的是马赛长颈鹿。
我们突然又集体陷入一片沉默无言。这通常出现在那些不需要言语就让我们深觉震撼的时刻。例如巨大的划破天空的彩虹,例如象群簇拥保护着小象缓步前行,例如现在,数只长颈鹿在河谷间伫立,远近交错,合欢树作为背景,仿佛一幅宽阔画卷舒展于眼前。
“如果有人问我,我会说这就是非洲”,Francise放下望远镜,不由说道,想必他也理解了我们的感受。
突然我们看到在更远一点的河谷处,两只长颈鹿长长的脖颈交错在一起,他们摆动着长长的脖颈,先是缓慢的后仰,然后再碰撞交叉在一起,看起来在跳舞,Francise说他们是在打架,争夺配偶。我们观望了一阵,实在想不出这样如何分出胜负,需要多久才能分出胜负。
我们继续沿着河滩搜寻,Francise不时通过对讲机与其他人交谈,突然他好像透过望远镜发现了什么,只见他放下望远镜,加大油门,飞奔向前方,突然一个急刹车,我们发现一只公狮子 就仰卧在我们的车下,而Francise差一点就从狮子的脸上开过去了!距离之近,让它看起来像我家的辛巴玩具一样,也让我佩服狮子和我们的镇静。
Francise显然是第一个发现的人,“你们见过在河边睡觉的狮子吗?”,很快他便在对讲机里呼朋唤友,而我们在车辆聚集之前就已经收获了各式各样各种角度狮子的照片。
离开河谷后,我们来到林地的另一侧,这里的合欢树逐渐减少,灌木丛也开始变成低矮的草地,草地的状况看起来非常健康,充满雨水滋润,土地湿润,很多动物藏在草丛中,不时能看到各式各样探出头来忽闪的小耳朵。
我们远离河谷,来到一片开阔的草原之上,这里有大群的斑马和角马。实际上只有两种动物会大迁徙,斑马和角马,偶尔还会有一些瞪羚混迹期间。角马没有脑子但是它们可以闻到食物和雨水,斑马可以GPS导航路线还能缓存去年的线路。角马的牙只能吃到高处的草,而斑马可以吃到低处的草,真是一对完美的排挡。
我们注意到,斑马通常两两和三三一起贴贴,样子有些滑稽,这种行为的意思是I watch your back and you watch mine.他们彼此还可以用尾巴为对方赶走苍蝇。
我们在这里等了一小会,队伍开始迁徙,因为远方高地逐渐聚集起了云,角马一定是嗅到了雨水的味道,队伍在“hero”的带领下向着雨水开始奔袭,不知疲倦,掀起阵阵沙尘。角马的幼崽一出生就能走路,并且当它们只有几天大时就能和群体一起奔跑。Francise说这只小角马应该刚刚出生两三天,因为他的颜色还是淡淡的褐色。
角马和斑马逐雨而去,我们也紧随其后。Francise告诉我们,这个季节傍晚的草原气象也很壮观,于是我们离开游猎的人群,加速驾驶在草原上,追逐远方正在形成的一场暴雨。乌云在几分钟之内聚集在眼前,四周平坦毫无遮挡,天空巨大异常,我突然理解了海明威在非洲的青山里说过的话:这里的天空也许不是最好,但这里无与伦比。
一场弱肉强食的饕餮盛宴
一场弱肉强食的饕餮盛宴
我们向Ndutu西北前行,准备离开Ndutu区域,往塞伦盖地国家公园的中部前进。刚刚离开营地,我们在一棵树上竟然发现了四只母狮,而这里距离我们的营地也只不过10分钟的车程,她们看起来个个吃的心满意足,正在惬意的休息。
起先我们只是发现了两只鬣狗的身影,有一只嘴巴里面还叼着某类动物的残骸。之后就看到一只前几天也看到过的黑背胡狼,在草丛间跑来跑去,伺机而动。此时天空已经开始聚集秃鹫,我们跟随着秃鹫的脚步找到了角马的尸体。鬣狗是草原上地位仅次于狮子的肉食动物,此时两只鬣狗已经吃的差不多了,围观的动物也开始越聚越多,鹰、秃鹫、胡狼,大家排着队,在不远处焦急的等着,都想来分一口。而此时体型较小的胡狼选择和鬣狗合作,帮它们驱赶虎视眈眈的秃鹫,同时希望能够趁鬣狗不备偷得一些残羹冷炙。
鬣狗终于离开,围观群众们蜂拥而上,瞬间淹没了尸体,场面一度非常混乱,食腐动物们争先恐后,互不相让,我们甚至可以听到清晰的咀嚼声,却又觉得兀鹫探头探脑跳进跳出的样子十足滑稽,大个子的非洲秃鹳此时也降落在旁,但是却插不进去。
离开Ndutu区域后,我们向塞伦盖地中部前进。
随着我们深入到塞伦盖地腹地,大草原的景致也开始变换,青绿的林地逐渐变化为黄色的草丛,草丛很高,这意味着没有食草动物在这片草地出没。车辆从进入塞伦盖地国家公园开始,便不能驶进草原了,只能沿着大路行进。
新生的狮子王与庞大的大象家族
新生的狮子王与庞大的大象家族
塞伦盖蒂草原有一种特殊的香肠树,因为它的果实是长长的圆柱形,像香肠一样悬挂着,这种树的树冠巨大,树姿也很优美,同时也是花豹很喜爱的藏身之地,遗憾的是,我们这两天并没有发现任何花豹的身影。
Francise告诉我们关于河马的故事:据说河马一开始只能在陆地上生活,但是它们无法忍受非洲的酷热,所以恳求上帝,如果能够让它们在水中生存,它们就一辈子吃素。上帝答应了,所以河马得以在炎热的白天在水中乘凉,夜晚上岸吃草,在水中休息的时候它们会时不时的张开大嘴,这是为了向上帝证明它们信守诺言,嘴里空空如也。
我们意外的看到了珍贵的画面,一只母狮,嘴中叼着一头目测刚刚出生2天的幼狮,试图寻找一处僻静的隐匿藏身之地。小狮子非常可爱,像小猫一般大小,还没有睁眼,圆鼓鼓的肚子很醒目,身上有淡淡的花纹,小尾巴无助的翘着,在母亲嘴里乖乖的毫无抵抗之力。游猎的车辆安静的跟在母狮两旁,并保持着一定距离,人群也不约而同的相继噤声,生怕惊扰了母狮。我们和其他车辆跟随了它们一小段路程,便不约而同的掉头离开了,大家都不希望过多的叨扰。
离开母狮后,我们又收集到一副有趣的画面。草原上出现两个池塘,一只河马和一群大象正在彼此商量着池塘的归属,它们先是交换了一次场地,最终一方占据一个,互不打扰。这个象群是个大家庭,大概有20多只大象,其中有三头关系亲密的小象,最小的一只看起来也是出生不久,走路还有些不稳,没有断奶,正是集万千宠爱于一身的年纪。所有的家人都在保护着它,大象时刻簇拥着它,将它护在身下,挡在身后,或包围在中间。年纪稍长的哥哥姐姐,陪它在池塘中玩耍,用鼻子淋湿它,帮它清洗身体。
下午的草原吹着微风,这里没有惊心动魄的厮杀与捕猎,没有斗转变换的天空,只有一派宁静祥和。
终于得以相见的黑犀牛
终于得以相见的黑犀牛
结束塞伦盖地中部的游猎之旅,我们驱车前往恩戈罗恩戈罗保护区,这个名字来源于它的所在地: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世界上最大的未破裂且未填充的火山口,形态非常完美,火山口在约245万至200万年前大型火山爆发后坍塌形成,原始火山的高度估计为4,500-5,800米,现在大概600米高的墙壁在四周陡然升起,火山口的直径达到了20KM。在火山口底部驱车进行游猎,就好像在一个巨大的野生动物园中,这里生活着25,000多只大型动物和超过400多种鸟类,拥有一些沼泽和一个大咸水湖,完备的生态系统让它成为新的世界奇迹之一,也被誉为“ 非洲伊甸园”。而我们来到这里,主要是为了了解和寻找两次非洲之行都未能看到的非洲五霸之一:游走在灭绝边缘,濒危的黑犀牛。
恩戈罗恩戈罗火山口的中央谷底部分星罗棋布着很多不大的水塘、沼泽,使得这里水草肥美,郁郁葱葱。因为这里很少有极度干旱缺乏水源的情况,再加上特有的地形地貌,这里的野生动物们常年比较固定地生活在这个完善稳定的生态环境中,不必参加东非大草原上浩浩荡荡的动物大迁徙。
据估计,今天非洲大陆上的白犀牛和黑犀牛的总数量大约为21,000只。犀牛曾经在非洲大陆上大量漫游,数量可能多达几十万只。然而,在维多利亚时代,大型狩猎的流行导致欧洲定居者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各种野生动物。在1960年代,因为犀牛角的需求激增,导致在20年的时间里,犀牛数量从70,000只下降到仅有10,000只。今天,犀牛被严格地监控,甚至生活在武装警卫的保护下。
虽然火山口内的犀牛数量并不多,据Francise说可能有1500头,它们经常在清晨时分被发现藏在金合欢树中,但通常只能远远的观望,因为犀牛对车辆和人类都不太熟悉,并且非常胆小,一有声响就会躲进灌木丛中,不再露面。
在漫无目的的搜索犀牛身影的途中,Francise遇到了一位女司机,擦肩而过后他喃喃自语:女司机!然后竟把车倒了回去攀谈起来。我们在两人互相介绍的只字片语中发现他们彼此并不认识,于是再一次惊叹于Francise的e人属性。
搜索了大半天后,黑犀牛终于现身了。Francise放下望远镜,告诉我们那远处的黑点就是一直寻找的犀牛。由于距离较远,我甚至需要使用长焦拍下照片后再进行放大,当看到它那独特的犀牛角时,才最终确认这确实是一只遥远的,孤单的,黑犀牛。
我觉得这种生物非常美丽。它们实际上是灰白色,体型是犀牛中比较小的,小眼睛充满无辜,显得人畜无害,短小的四肢透露着一丝憨厚和可爱,大多数时候都是独自生活。这种可怜的动物,一个世纪以来一直活在人类捕猎和偷猎的阴影之下,人们几次将它们从灭绝边缘拉回,又几次将它们推至濒危。
尾声
尾声
这是我第二次来到非洲了。
我没有去非洲以前,非洲在我的想象中与帕卡姆在夜航西飞中的书写类似,粗旷而野蛮,充满机遇、冒险与生命力,她漫不经心的写作,读来却让人屏息。那一个个名字,那么遥远又熟悉,内罗毕 、恩乔罗、莫洛、蒙巴萨、纳库鲁、纳瓦沙…而去了非洲之后,又与凯伦克里克森在走出非洲中的书写更加相似,浪漫而温柔,饱含热爱和情感。
2019年,在肯尼亚Safari的途中,我在阅读海明威的《非洲的青山》,海明威痴迷狩猎,追捕大捻,在非洲得过几次疟疾,差点丧命,但他也痴迷于这种男子气概的最大化体现,他诉说对 非洲的思念,说他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想念,他说风总会把人的气味先送上来,他讲如何跨越山丘和土路,到达视野开阔的狩猎平台...
我自己的非洲是什么样子呢?你不记得每天几点睡几点醒,只记得在清晨第一缕阳光照射在金色的合欢树梢时,出发去看看大自然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礼物。穿梭在侏罗纪公园一般的林间,合欢树与灌木丛此起彼伏,每一株灌木枝桠都落满了点翠蓝色的丽椋鸟,随时随地惊起一群群,鹰在头顶飞翔,非洲秃鹳在湖边恣意的晾晒翅膀,你从未觉得鸟儿如此自由。
大象的脚印像一个人的怀抱那么大,每天都有新出生的角马,它们在“hero”的带领下向着雨水长途奔袭不知疲倦,掀起阵阵沙尘,喂饱了一群群的狮子和猎豹。黄昏时分,阳光穿透猴面包树,水羚沐浴在其间,偶尔抬头张望,乌云聚集在眼前平坦的草地与广阔的天空,雨水落在每一寸草丛里,青草飘香,露珠闪烁,原来大自然有属于自己的调香。
就像海明威说的,这里的天空也许不是最好,但这里无与伦比。
从非洲回来以后,我去了马尔代夫潜水,也是在这两次旅行之后,我开始觉得过去的旅行已经没有意义。我想现在,我可以试着回答,为何我一再想回到非洲。那是因为我越来越被开阔的大自然所吸引。在那里,一切都变得清晰,世界也最有意义。当我置身其中,我总是带着新的东西回来,一如我刚开始旅行时一样。
而就像有关Patagonia的纪录片【180°以南】中所讲,被困在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建不出来更具生态意识的世界,你不想呼吸脏空气,不想听到噪音,你闭眼不看,因为周遭很丑陋,这导致我们不理解,不爱,也不关心自然。接下来的旅行,我想除了让自己最大限度的一次次的置身于荒野之中,也希望能有余力保护我所爱的东西。
最好的旅行回答了那些在开始时你甚至没有想到要问的问题
祝旅行愉快!
I

juliepiero
413 人关注

出去走走
1328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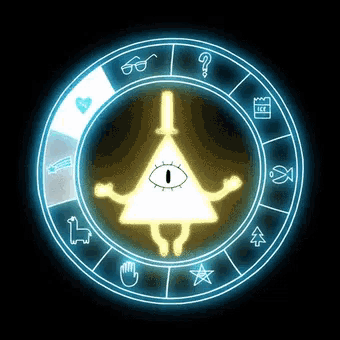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6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