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题记:这个短篇小说算是一种实验性文章,因为故事简单荒谬而且我想给读者营造一种异乡的不和谐感和在场感,会有一些照片穿插非本人拍摄的都会标注来源,也会直接的出现英文,但绝不是为了炫耀或卖弄文采,希望读者键盘下留情。有任何不足和缺点欢迎指正批评,首次创作,未来希望能写重庆轻赛博朋克小短篇,希望你能喜欢。
柯布西耶理想中那共产主义理想般的房屋是四通八达,整整齐齐,宛如一个终其一生都不需要步入泥土的空中之城,他如果能看到纽约这旅馆改造的公寓应该会很满意地将其列入包豪斯学院的教材中,但我在这里,却是感受到《闪灵》里一般的惊悚不安,时常需要隐匿自己将这后现代主义建筑炸毁的冲动欲望。这栋楼里住着各个种族,各个年龄段的人,活像某个人类学家的收藏。我不喜欢抬头看门牌,也讨厌钥匙无法捅入的急躁,于是我特地将从中国带来的门神贴纸粘好,这才能不假思索地找到我在偌大纷繁中的容身之所。
正值一月初,黄昏的风雪像扑面扫射的子弹打在人们疲惫的脸上,从学校抱着厚厚的《当代艺术》,《简约至上》以及《尼各马可伦理学》,风尘仆仆的我冲进房门,只想用泡一杯花茶提神暖胃。手忙脚乱的我还不知道,这个晚上我将遇见李于期,开启中国春节前最奇妙故事。
大约下午六点的时候,我听见房门被轻轻敲了几下。
“Who’s there?”我一边问一边放下手中的书,拿起防狼喷雾。
“Sorry to bother you, did you draw the paintings on the door?”门外的声音礼貌却急促。“The landlord said the student lives here want to sublet her suit during the spring break, so I come here to see the apartment type.”
我将喷雾藏在背后缓缓打开了门,眼前是一个高大修长的黑人,他的眼睛发着疲惫的胶片黄调,穿着剪裁工整的羊毛大衣,斜纹格子围巾敞开着透出里面笔挺的衬衫和低调的香水味。
“I didn’t draw this, actually I’m not good at it. If you want to check the apartment type you should call me or send an email first.”我有些不满,身后电视上放的《一代宗师》的对白徐徐飘来。
“你是个没有被美国改变的中国人,或者一个理解中国文化的美国人”他喃喃自语道“这里的华裔只会在家里摆佛像和景泰蓝,点左宗棠鸡外卖。”
我噗地笑出声,他不好意思地跟着笑起来,深处摘掉皮手套的右手“我是Leo,不过我有个中文名字—李于期,我是一位人类基因学家学家,会一些中文。”
我回握住他温暖的大手。
还记得那天我邀请他来进来看看房间,虽然相谈甚欢,甚至还一起去WHOLE FOOD买了便餐吃,但他并没有租下房子。
李于期曾在中国外派过五年,最近刚入职纽约的研究所。他有个在新泽西上小学的身体孱弱的孩子,此次租房既是为了找个地方下班休息又是为了让孩子能来纽约参观各大博物馆时方便休息。我那可怜的“suit”着实不适合任何成长期的青少年,不过他倒是爽快的租下了隔壁的大套房。
在异乡听到异乡人说起中国话,便会不知不觉让人把心房里的栏杆悄然放下。当时的我内心止不住的激动和兴奋着:一个了解并将东方文化平等看待的西方高级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多么可贵且体面的朋友啊!以至于后来我常常唏嘘,那种我不具备的纽约人的冷漠大概只是过分冷静的表象,如果问我直接和房东打电话求证他的身份,如果我没有邀请他进来看看,如果我们没有一起去WHOLE FOOD买熟食,是不是就不会发生后面的一切。
第二次见面时,我在二楼的无人洗衣店里读着《设计史》,李于期抱着一篮衣服进来。
“HI,你好”
“你好”
“你在读什么书呢?”
“世界设计史”
“历史?你能从中知道什么有趣的事情吗”
“比如,能知道纽约的街头建筑曾被样式主义影响过。”
“Cool,那中国的设计呢?”
“大概是被包豪斯一直影响着,像核武器辐射一样,深远持久。”
“我对中国设计不了解,不过我对包豪斯略有耳闻,纽约的那些摩天大楼都是它们的遗作。”李于期的中文流畅极了,像是滚筒洗衣机里顺滑的泡沫水在不同的语言之桶中游走。洗衣机突然一个二个开始轰鸣,我们不得不提高音量。地面上橘红色的桶里,蓝绿白三色的洗衣凝胶球轻轻的晃动起来。
“作为一个基因学家,你对设计的了解算多的。”我对非业内人士对包豪斯和摩天大楼的认知从不抱希望,但这是世界上受教育程度和普及度最高的地方,万事皆有可能。
“我了解包豪斯,是因为我想要了解德国,了解赫尔曼黑塞。”他放大了声音继续说道。“他是我最喜欢的作家,他写的那种教育,太沉重了。那是我绝对不想这么对孩子做的。”
“是学校、父亲以及两三个教师残酷的名誉心,把这个容易受到伤害的少年践踏到这步田地的。”我重述着这些黑塞写的句子,抿了抿嘴“让你的孩子成为有主见且不取悦他人的人是一个很好的想法,但把教育榜样换成Rita Pierson会更积极吧。”
我以为李于期会像以往一样微笑着点头,但他却忽然弯腰弓起之前挺拔的脊背,用修长的手捂住短圆的鼻头,仿佛再往上去,线条狭长却柔和的眼睛黯然下陷,不断地深凹,饱满的额头则不断前凸,向另一个没有方向的地方扭曲拉长。
“我的孩子不是那种喊着“every kids need a champion”的人可以教好的,他需要的是图像,竞技游戏和各行业优秀人才的指导,但我希望他成为一个优秀的技工的同时也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我一时接不上话来,难道李于期的孩子是个动手能力超强的早熟神童?而且是那种智商和情商为反比的厉害角色?虽然在中国,这样的孩子我见过太多,但此时我反而不知如何接这沉重的话茬,所幸我洗衣服的机器发出哔哔的美妙声音。
“Google《伤仲永》或者揠苗助长,或许你可以得到启发,那我就先走了。Have a nice day,Leo.”我匆匆逃走前,担忧地瞥见了李于期痛苦矛盾的背影。
后来再次见到李于期时他还是以前那样温和有礼,但我逐渐感觉李于期仿佛越来越痛苦,滑入了一个名为抉择或者其它什么致人撕扯的沙漏,他总是拿着从中国城和古着店里淘来的陶瓷或者刺绣小物件,似乎觉得那解药可以从中国和东方哲学中找到。
一月走向尾声的同时,学业繁忙和异国语言的频繁输入输出霸占得我没有多余的思绪去牵扯李于期的痛苦。导师下令要我们选出自己最喜欢的博物馆做reputation,我便开始在地铁里穿梭,后来干脆直接把NYC SUBWAY地图当手机屏保桌面,日日忍受着时不时投来的观察亚洲人的目光以及腐烂酸菜般的大麻味。
如何在纽约躲避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呢?我叹了口气,走进弗兰克盖里的经典手笔——古根海姆博物馆。
Hilma af Klint这位抽象主义先驱的画作首次在古根海姆展出,吸引了大马哈鱼群般的男女老少堆堵住了入口,我直接坐电梯到顶楼准备开始我的逆向洄游,但一位身着黑底红色龙纹方领盘扣唐装的男子吸引了我的视线。
“李于期?!”
“Nice to see you here!好久不见。”
我和李于期并肩而行,他消瘦的面孔看上去比以前更有精神了些,放着一种奇异的生命力。
“Hilma竟然要求20年以后才能将自己的抽象画作公之于众,真是不可思议。”李于期看着墙面上的文书和小字感叹道。
“作为一个女性,这些精子卵子一般的图案在当时公布只会遭到评论家的非难吧。”
“Hilma受过东方文化影响吗?”
“没有,怎么了?”
“你看,这些nautilus(鹦鹉螺)一样的图案不是和太极图中的阴阳很相似吗?”
“对她来说,阴阳是她自动书写的高级精神世界里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仔细地观察起面前的画作。“毕竟阴阳孕育生命,组成世界。”
“上帝也可以孕育生命,但他只是一道光,一股气流。不是只有男人女人才可以。”李于期淡淡地说道,语气轻轻的,仿佛再重一些就会唤醒神明和恶魔。
“Hilma的画展现的是本能的心理符号和二元性线条,可能我们说的这些她没考虑过”我试图将话题引走“不如去看看那些巨幅绘画?”
正当我们往著名的“十大幅”走去时,一个年轻的父亲抱着一个约莫7岁的金发女孩走近了一副黑色倒金字塔上有一个棕色圆圈的作品。
“Emmmm, this is like....a brown eye, right?”年轻的父亲极力向女儿解释着抽象画作。
“But I think it’s like an ice cream, a chocolate ice cream.”金发女孩咯咯笑起来,年轻的父亲一副放弃挣扎的表情,无力的抓住正想往一旁想溜走的妻子,发出求救的眼神。
李于期留恋且羡慕的看着他们,这时,我们的视线里闯入一个棕色卷发的小男孩,他跌跌撞撞地在古根海姆的螺旋过道上开心地快速爬行。
“Slow down, you drunk!”他的哥哥,一个同样是棕色卷发的高中生,戴着湖人队的鸭舌帽,笑着冲过来把他抱着肩上。
我实在忍不住了,便捂着嘴靠在黄铜栏杆旁边偷笑,但李于期却继续沉默地向前走着。
大概是想念自己的孩子了吧,我心想。
我们在“十大幅”的《青春》前坐下,李于期突然开口讲了句没头没脑的话:“有时我觉得我就是上帝。”
“为人父母的通病?”我无奈的看着他。“你可能已经没有心情赏画了吧。”
“Hlima的日记里说,只有做好舍弃世俗生活方式的时候,生活才会脱下她的外壳,向你展示她无比美丽的内核。但我没有办法准备好,我虽然创造了我的孩子,但我没办法忍受他被训练成一个塑料或钢铁一样的机器,一个模型,一个可有可无,谁都可以替代的助手,更不能接受做出这一切的人是我!我一直都知道自己缺了什么,从一开始就缺了,只是我怎么也找不到丢了的那部分,也根本不知道丢失的是什么,我只能任由这个缺口在我心里扩大。”
“李于期,Leo,你知道魔鬼的金头发的故事吗?你现在就像里面的那口井一样。”我想我没办法理解这位成年美国黑人男性的世界,只能尽我所能开导他了。
“格林童话?”李于期疑惑的看着我。
“对,有个镇里有一口涌出美酒的井,突然有一天井枯了,再次涌出来的是臭烘烘的脏水。魔鬼的金头发说,有一只死老鼠把井底的泉眼堵住了。于是村民按照头发的吩咐把老鼠的尸体打捞上来,果不其然,美酒再次喷涌而出。村民高兴得不得了,给了男主角好多金币,最后男主角高高兴兴的回去和公主结婚了。”我顿了顿,看着认真注视我的李于期,“堵住你的心底的死老鼠在哪里我不知道,但再这么下去,你会干涸的。你不是普罗米修斯一样的神,迟早会被日日啄食你的老鹰彻底榨干,沦为一副人皮空壳。你可以战胜这些困难的,不多时,你又能品味到美酒的芳香了。”
“听着有点吓人,不过,谢谢你。”李于期仿佛下定了什么决心,捏了捏空的矿泉水瓶,使它难受地低声哀怨起来。
“下次你孩子过来的时候,一起去时代广场的迪士尼专卖店逛逛吧,我们可以买Joe’s tea,然后开开心心地看《驯龙高手2》。”我说道,一面低头看向手表。
如果那时我转过头,向左大概三十度左右,就能看见李于期轻轻的摇头,又抑或他什么表情都没有,只是有些讥讽的看着自己面前的《青春》。
春节悄然来临,记得还在中国时,我每年都搞不清楚除夕的具体日期,直到笋子烧鸡和冷吃兔的香味从鼻腔钻入胃底刺激着唾液,红包油亮亮闪着眼睛才恍然大悟。然而异乡的孩子却牢牢记着日子。
黄昏,我仔细地将枸杞洒在鸡汤里,想象着其他中国同学期待的眼神和赞美,盘算着晚上十点左右和家人视频通话,脑海里的画面过于温馨,就在我准备擦眼泪时,一阵急促有力的敲门声响起。
看着门外的警察和调查人员,我心里一紧:还能选一个更合适的时间吗,世界警察们。
“这位女士,您不用紧张。”没想到一旁的调查人员会说中文。我下意识地闻了闻房间,很好,隔壁的大麻味没有涌过来。
“请问你认识Earn Glover吗?”他一边说着一边递过来一张照片。
“我不认识Earn......”我接过照片疑惑地说,但当我看到照片时,李于期的脸清楚的印在纸上,自从古根海姆一别,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听说他搬走了,没有和任何人告别。
“真的不认识吗?”他观察着我的脸。
“不好意思,我真的不认识,我才来这里没多久,没有当地的朋友。”
“也罢了,中国人基本上都不会和黑人做朋友的。”他耸了耸肩。
“请问你们在查什么吗?”
“您可以打开新闻台看,我们还要进行调查。抱歉打扰了,新春快乐。”调查人员和警察点点头,关上了房门。
几乎是同一瞬间,我颤抖着抓起遥控板打开电视,快速地在不同的新闻频道切来切去。
“昨天凌晨,纽约科技电子公司正在研发的超级人工智能初级机器被盗,盗窃者为该项目的总负责人,人工智能培训师Earn Glover,一位单身的黑人男性,目前下落不明。据悉,这台人工智能初级机器的算法能力将超越目前已知的任何机器,且具备基础能力的伦理计算和道德计算。有关专家推测,纽约科技电子公司或损失........”
我把遥控板丢在沙发上,摁开手机上的图标,推特,雅虎,CNN甚至BBC的头条新闻里都推送着相似的消息,舆论都怀疑他是俄罗斯的间谍,是谋财的强盗,组织科技时代发展的罪人,但我几乎能用肉眼看到李于期带着他的人工智能孩子在一个险象环生的VR游戏里步步为营,过关斩将,用满腔的父爱抵挡整个世界的投石。
“芯片宝宝待机的时候会梦见人类父亲吗?”我出神地望着Earn Glover的头像照片里温和的微笑。李于期,你以自由为代价,填补了那口深不见底的井。
手机突然抖动了一下,同学们开始询问起聚餐的具体地址了,开始互相发讨要红包的带着鞭炮和春联的表情包。
我头脑一片空白,把鸡汤倒在保温壶里,行尸走肉般往地铁站走去。路过的Bryant park里全是橡皮糖般黏在一起搂抱的情侣,在溜冰场里和Karen Souza和Michael Bublé的爵士歌曲一起转圈圈,纽约的节日气氛是属于十四日的情人节的。
迎面走来的朋友笑着向我招手,脸上的红唇像点亮夜空的红色彗星。
春节这样热闹的日子还是擦红唇吧,即使很快就要擦拭去,但没关系,毕竟像这时楼厦天界线间橙紫的天空,再扭头看时就黑尽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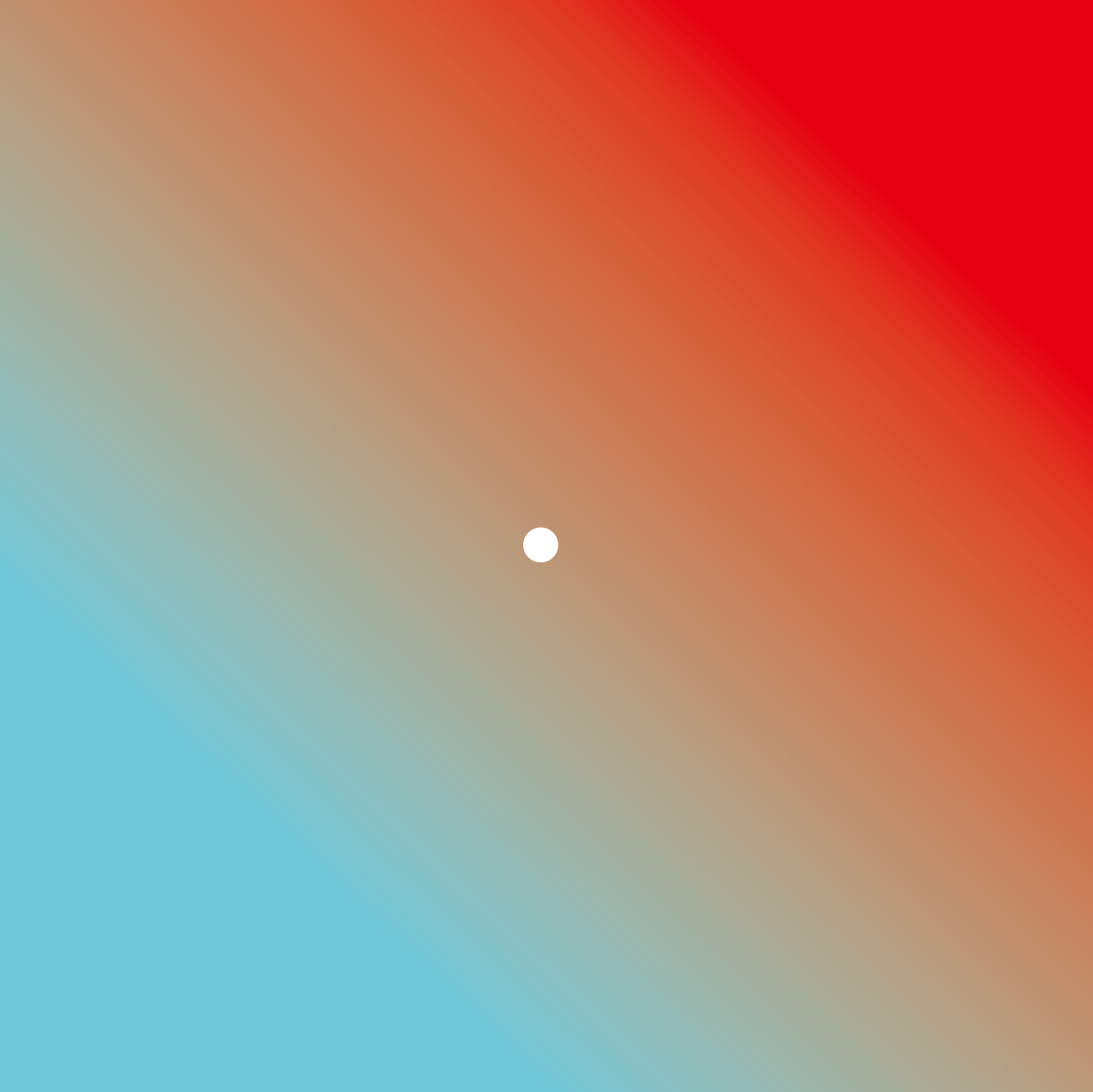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