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1995年2月8日,66岁的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仍然站在伦敦建筑联盟学校(AA School)的讲台上。他拄着手杖,扒着讲桌,缓慢地挪动到幻灯机前,用钢笔在透明幻灯片上画出解释人类意识的图示。他的图解本就以晦涩而闻名,此刻由于他颤巍巍的手而变得更难以理解。帕斯克的讲话节奏不像年轻时那么跳跃且充满戏剧性,声音却仍旧洪亮。另一点没有改变的是他个人标签式的着装:白衬衫紧系蝴蝶结,外套双排扣西装。几乎在所有能公开找到的照片中,帕斯克永远是这套行头,从17岁在北威尔士卫理公会公立学校开始,几十年如一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他愈加蓬乱的半长卷发,比平时更加疏于打理。此时的帕斯克已经被疾病缠身多年,据他离开这个“控制论世界”只有一年零一个月的时间。
次年,1996年3月28日,帕斯克卒于伦敦,享年67岁。这当然算不得长寿,除了年少起就体弱多病以外,我想这或许和他疯狂的作息习惯有关:帕斯克的一天有64小时,他通常在48个小时的连续工作之后,一口气睡上16小时。他因为糟糕的身体状况而长期服用各种药物,装在大公文包中随身携带,其中一些是安非他命。有人认为这与他精力旺盛、难以相处且令人印象深刻的天才形象密切相关。
帕斯克最为大众所知的,无疑是在欢乐宫(Fun Palace)项目中的工作。他在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与戏剧家琼·林特伍德的邀请下,担任控制论委员会的顾问(关于欢乐宫请阅读《欢乐宫:一个未竟的赛博建筑,一个关于改善低生活的社会装置》)。帕斯克被视为英国控制论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在控制论和教育心理学方面颇有建树,而且对艺术、娱乐和戏剧都有着浓厚的兴趣,这明显体现在帕斯克的实践之中。
无论如何,在多数人看来戈登·帕斯克都是一个古怪的人:爱德华时期的着装风格、极具攻击性的交流方式和难以理解的思想……他的学生和合作伙伴之一保罗·潘加罗(Paul Pangaro)在讣告中称他为:控制论的华丽公子(Dandy of cybernetics)。但是帕斯克更喜欢称自己为:机械哲学家(mechanical philosopher)。这也难怪,因为另一个关于戈登·帕斯克的常见印象是:身着双排扣西装和领结的绅士,永远在摆弄一些“无用”的机器。
不同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从更抽象更宏观的层面思考控制论,帕斯克显然是实践派,总是在具体情境中考虑电子设备能和人类产生怎样的关系。他的理论总是和他发明的机器相伴产生,这些机器并不是完成某个任务的工具,而是用来当作媒介,通过与人的互动激发自我认知。期待个体在“对话”中达成共识,产生知识,促进彼此更好的认识自我,是帕斯克一生致力的目标。
怪学生戈登
怪学生戈登
在展示戈登·帕斯克的控制论实践之前,有必要简略的回顾一下他的学生时代,以便了解其进入控制论领域前的人生,同时也能更立体的呈现其极具浪漫感的性格。其中的诸多片段都颇为“精彩”。
戈登·帕斯克的妻子伊丽莎白·普尔(Elizabeth Poole)回忆他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戈登经常否认他是被生出来的,他坚持认为自己是在一个香槟瓶里从天而降,身躯完整且穿着晚礼服。德比市长和年长者们带着铜管乐队,与整座城市一起迎接他的降生。”而另一个更真实也更无趣的版本是,戈登1928年6月28日出生于英格兰德比市(Derby),是一位富有的水果进出口商帕西·帕斯克(Percy Pask)最小的儿子,家中排行老三。
戈登对自己出生的浪漫化叙述,可视为对其一生的隐喻。他总能以最具戏剧冲突感的方式处理自己与这个世界的关系,这一个性从他在寄宿学校起就展露无疑。从那时开始,他就穿起了那套标志性的行头,显得比同龄的孩子成熟不少。戈登在校园里是著名的捣乱分子,而贯穿他一生实践的两条重要线索:舞台艺术和机械设计也分别以两次出格的事件体现出来。
第一件事发生于校长的一次风纪整顿。戈登因夜不归宿参加戏剧活动而被点名,以杀鸡儆猴。但是面对校长的公开斥责,戈登不仅没有认错,反而当场回怼“我要和我的律师谈谈”。最后这成功帮他躲过了一次体罚。第二件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戈登曾给英国陆军部寄去了一份武器设计图。几个月后他收到了回复:“我们看了你的图纸,武器很有效,但效果过于可怕,不适用于人类敌人。”
1945年,戈登毕业后应召入伍,却在训练营做俯卧撑训练时晕倒被救护车送回家,结束了他为时一个星期的短暂准皇家空军生涯。之后他进入利物浦技术学院学习,主修地质学和采矿,并取得了采矿工程师的资格。
1949年,戈登受到大哥埃德加·帕斯克(Edgar Pask)影响,进入剑桥大学唐宁学院学医。埃德加是一名皇家空军的麻醉师,在二战中做出了卓越贡献,1975年英国麻醉协会因此设立了帕斯克奖。但是戈登在医学系并不顺利,这从他解剖学考试时堪称灾难的表现就可见一斑:考场上的戈登面对一条手臂,他没有像其他学生那样拿起手术刀,而是抡起一把消防斧劈了上去,结果当然是成绩和解剖台一同报销。他随后转修生理学。然而糟糕的学医经历几乎没有给戈登造成困扰,因为学业对他来说只是次要的。戈登首要的关心的是如何将自己的两个兴趣互相整合:关于人的舞台艺术和关于物的电子机械。只是在遇见维纳之前,他还不知道自己正在尝试的事情可以被称为“控制论”。
1950年代,维纳的控制论在英国的影响正值巅峰(关于维纳请阅读《控制论之父诺伯特·维纳:信息时代的破晓骑士、持矛者与铸盾人》)。戈登有幸在维纳访问剑桥时担任他的学生助理。他惊讶的发现,维纳描述的学科与他一直研究的事物非常相符。当时戈登正在将自己的兴趣置于一个更大的主题之下:研究人类与客体互动中的认知行为。诺伯特·维纳和《控制论》给了他关键的启发,改变了他今后余生的道路。戈登1952年从剑桥毕业,取得了生理学自然科学硕士学位(MA in Natural Sciences)。毕业后,帕斯克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伊丽莎白,以及同学麦金农·伍德(McKinnon-Wood)合伙创办了系统研究公司(System Rsearch Ltd.)。一段控制论的历史从此开始。
我们曾经将会怎样交互?
我们曾经将会怎样交互?
早期控制论学家们的专业经历都跨度极大,帕斯克的经历从上文可见一斑。此外他们还有另一个共性,即最主要的研究几乎都与主流学术机构关联甚少。例如,诺伯特·维纳曾在多所著名大学担任教职,但其最重要的成果产生于梅西基金会会议这种临时学术机构之上。帕斯克也类似,其主要研究都脱胎于系统研究公司的商业项目。下文我将简单介绍最有代表性的两个项目,尝试解析帕斯克切入控制论领域的角度,展示一种完全不同的交互方式。
- Musicolour
Musicolour完成于1953年,是系统研究公司的第一个项目。简单来说,这是一个声音驱动的交互灯光装置,灯光没有预设模式,显示效果完全取决于表演者钢琴演奏的节奏和旋律的变化。帕斯克从在剑桥起就开始构思雏形,其最初目的是通过研究机器能否“习得”声音和视觉模式之间的联结,进而研究人的认知模式。可是公司初创并没有什么预算,所以这台机器是用邮局废弃的电话交换机零件,在帕斯克的卧室攒出来的。帕斯克在没有任何先例参考的情况下独立设计了所有的电路。
Musicolour的机制并不复杂。电源接通后,它会邀请演奏者共同玩儿一个声音游戏:当演奏者弹奏钢琴时,声音通过麦克风和放大器传到机器的8个滤波器中,每个滤波器以极短的时间间隔计算信号频率的平均值。接着,经过修正的信号被分别传输到8个阈值通道,当信号超过某个阈值时才能通过,输入到灯光控制部件,激活相应的灯光。但阈值并非恒定,而是会随着电容上电荷的积聚而变化,因此阈值与输入的声音模式有关。当声音以相同的节奏和频率维持一段时间后,机器会感到“厌倦”,阈值升高,灯光不再响应。这鼓励演奏者不时变换节奏与旋律,形成某种演奏模式,以激发机器的“积极响应”。一旦双方建立了相对稳定的动态交互模式,Musicolour的灯光也会相对稳定,并且具有一定程度的鲁棒性,能够抵抗其他声源的干扰。
我们可以看出,表演过程中机器与演奏者需要相互适应,以合作“创造”一种相对稳态的声光表演风格。据帕斯克描述,一位演奏者甚至过于沉浸而忘记了时间,从晚上10点弹奏到凌晨5点,一直在试验不同的演奏方式可能带来什么样的灯光效果。演奏者无法总结归纳自己的演奏模式,但能明确的感受到某种模式可能会激发相应的灯光。Musicolour和演奏者被耦合进一个反馈系统中,用帕斯克的话说“演奏者将机器当成了自己的延伸”。这比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的“媒介是人的延伸”早了十年,《维纳传》一书的作者弗洛·康韦和吉姆·西格尔曼认为维纳的控制论对麦克卢汉的媒介理论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Musicolour的电路图和工作原理虽然易懂,但演奏者无法只通过阅读图纸和文字了解它,因为这部机器没有明确的功能或者预设的目标。因此演奏者了解它的唯一方式就是用行为互动。这某种程度上模拟了人类在面对未知事物,通过直接互动的方式积累经验的学习过程。
自这部机器完成起,帕斯克和合伙人就像马戏团长一样,让其在不同场合亮相,试图将其当成一种新型舞台设备推销出去。1953年,Musicolour的第一次演出在剑桥的石榴俱乐部(Pomegranate Club)。一段时间后小有名气,便在英格兰北部的大型场馆巡回演出。Musicolour体积庞大,要用两辆面包车运输,每次安装需要五个人。1955年在波顿剧院(Boltons Theatre)出演了一部木偶剧,最终以连续一星期的技术故障结束。之后该机器还曾尝试与舞者共同演出,帕斯克为其创造了一部舞剧《Noctrune》。可是当时系统研究公司的财务状况连维护设备都捉襟见肘,更别提租用剧院排练了。其间Musicolour曾一度被改造为点唱机,但这也没能带来稳定的现金流。最终因为找不到合适的长期“演出”场所,Musicolour被搁置。这个“喜欢”和演奏者互动的机器最后一次演出,是在1957年的一场舞会之上。
在当时,Musicolour是个无法分类的物体/商品,它作为一个舞台设备表现不够稳定,作为一个艺术品又不具备上造型上的形式感。假若晚出现十年,那些摇滚乐队或许会青睐这些古怪的即兴机器吧。
- SAKI:自适应键盘教学机
Musicolour项目后期,公司开始开发另一台机器:SAKI,自适应键盘教员(Self-Adaptive Keyboard Instructor)。这是一个具有明确使用功能的商业委托:用来培训人员使用霍尔瑞斯打孔键盘(Hollerith key punch),以便能熟练录入数据。该键盘是一种只有12个按键(0到9,X和一个换挡键)的输入设备,以打孔的方式输入26个英文字母,两个孔表示一个字母:“换挡键+1到9”可打出字母A到I;“X键+1到9”可打出字母J到R;“0+1到9”可打出字母S到Z。
SAKI的原理很简单,机器通过眼与手的协同训练产生条件反射,短时间内提高学习者操作键盘的熟练度。具体使用方法是:当机器的四行指示灯显示出字数字、字母或单词时,模拟键盘上会亮起相应按键,这时学习者只需在规定的响应时间内正确按键,就算成功完成了一次操作。
不同于Musicolour的娱乐性,SAKI是一个字面意义上的学习机,但在最重要的特征上仍和Musicolour相同。SAKI也能和使用者达成一种稳定的动态交互:机器能随着学习者的正确率随时调整字符显示的复杂程度和响应时间长短。也就是说,学习者无需在SAKI上预先选择难度等级,它会根据自己熟练度自动调整难度。
帕斯克预估,如果一个键盘新手每个工作日完成两个45分钟的训练,就能在4到6周的时间内达到专家水平,即一小时7000到10000次有效按键。系统论和控制论学家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试用过SAKI后,认为这是第一个脱离“玩具”范畴的控制论装置,可以作为一种有用的机器进入市场。比尔曾经为智利的阿连德政府做顾问,设计了Cybersyn系统,这里挖个小坑有空单开一篇详谈。
SAKI可能是系统研究公司最成功的商业项目。1961年,SAKI的销售权被美国的控制论发展公司(Cybernetic Developments Inc.)买下。但之后购买加租售的数量总共只有50台,人们更倾向于将这个新潮的机器当作炫耀的收藏品,而非真的用它来“学习”。SAKI相比于帕斯克的其他项目已经算很好了,但仍不算是一个成功的商业项目。
- 对话理论和自适应机器
Musicolour和SAKI都是失败的商业项目,然而两者为帕斯克关于认知和学习的研究奠定了基础,直接帮助他在1964年取得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心理学方向的博士学位。1974年,他在伦敦开放大学开发传播具体知识的教学机器,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了最重要的对话理论(Conversation Theory),同年凭此拿到了控制论科学博士。
帕斯克的理论以晦涩难懂而著称,由于我能力所限没法精确的解释对话理论是什么,只能试着描述它关于什么。对话理论的研究主题是解释互动如何导向学习和认知,可以看做是关于“学习如何学习”的元理论。他将社会视为由象征和语言构成的系统,并解释了几个子系统(有机体或机器)在基于情境的互动过程中如何形成稳定的参照点,并产生可复现的结果——可以简单理解为系统在交流中怎样达成共识,并沉淀固定的知识或智慧。帕斯克还设想这些可复现的结果会积累成“继承网络”(entailment mesh),一个经过组织的可公开访问的知识集合,即一个动态的知识库。帕斯克不认为知识或智能是某种本质,可以通过单方的学习来获取,而是只能存在于交互之中。
在对话理论中,帕斯克用适应性行为来解释不同的系统(有机体或机器)的交互行为,并没有对“人”和“机器”做明显的区分。人和动物毫无疑问都具备适应性行为,在帕斯克看来,Musicolour和SAKI也是“自适应机器”。
这里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它们不是“计算机”而是“模拟机”,其架构都带有某种模糊性,用来模拟有机体的行为过程。因为帕斯克设计的目的不是解决某个与数学有关的问题,而是用来研究人的认知行为。对它们的预期不是导出一个非常明确的结果,而是意料之外的互动过程。其次,在非常具体的层面,我们能很直观的感觉到人创造了机器,机器又反过来影响人。人和机器互动的理想状态是达到一种动态平衡,反馈过程中双方都需要不断改变自己既有的行为方式。两者处于同一个反馈循环中,“虽然学生和机器的物理界限是明确的,但是系统中分别代表学习者和自适应机器的控制区域之间的边界却在不断变化。”
二阶控制论与人
二阶控制论与人
帕斯克在实践和理论中,将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引入机器,从而无意间将控制论带入了二阶控制论(Second - order cybernetics,由海因茨·冯·福斯特在1970年代提出)。二阶控制论和一阶控制论的区别在于:后者认为观察者独立于被观察的客观系统;前者将观察者也纳入被观察的系统一同研究,将控制论研究世界的方法应用于研究控制论自己,被福斯特称为“控制论的控制论”,出现了“大脑被要求写出关于大脑的理论”的递归状态。所以二阶控制论认为不存在绝对的客观对象,观察者和被观察系统相互影响,并且引入了“具身经验”的概念。帕斯克将人纳入到反馈回路之中,认为智能产生在互动的适应性行为之中,而非像一阶控制论学家一样,仅仅制造一个能模仿人类行为(智能?)的机器,例如格雷·沃尔特(Grey Walter)的Tortoise机器人。
如今看来,帕斯克的机器远不够精巧,但其理念中对不同系统间差异的有意模糊,潜藏了“人≈机器”的视角。这后来被当做控制论世界观/本体论的重要特征,并且很容易招来诘问:“这难道不是将人和机器等同视之,贬低为一个反馈机器?”
控制论对人的定义与生物学很接近,不同的是控制论关心的不只是肌肉记忆或神经反射,还有大脑如何认知世界。相信很多人都对青蛙的反射实验并不陌生,这揭示了生物电和神经反射的存在,其实有关青蛙的实验在控制论中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1947年,梅西基金会会议主席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计算神经科学开创者)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篇关键的论文《青蛙的眼睛向青蛙的大脑显示什么?》(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他和团队研究了青蛙的视觉神经系统,证明青蛙视网膜向大脑输出的信息经过了系统构造的再组织,导致青蛙对具备某类视觉特征的物体(例如飞行的昆虫)更为敏感:
- 局部的清晰边缘和反差;
- 黑暗物体的边缘曲率;
- 边缘的移动;
- 由移动或快速的整体变暗产生的局部变暗。
因此青蛙的视觉系统不是在反映世界,而是在构建现实。有趣的是,该论文在1959年刊登在 《无线电工程师学会期刊》(Proc. Inst. Radio Engr. 1959)上,而非生物学期刊。随后他和沃尔特·皮茨(WalterPitts)和提出了三维神经网络(Nervous Net)模型,用来识别视觉输入,可以看做是现在卷积神经网络的雏形。麦卡洛克、皮茨和维纳并称为控制论的黄金三角。三人各自的研究与控制论的关系是另一个庞大的话题,在此不多展开。
对于将论文结论类推到人类身上,麦卡洛克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不过后面几次梅西会议上,其他学者逐渐将其发展为后续研究重要前提:我们所知道的现实并非完全客观,而是被我们的生理结构塑造过的。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和智能都由此决定。反之,那些与人类不同的其他物种不是没有“智能”,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没有哪一种存在仅仅是一种纯粹的“反馈机器”,它们都是在适应被自己的生理结构所认知的环境/世界。某种程度上,人类无法只通过数据和实验等“科学方法”完全认知另一种存在,因为这些方法很难帮助人类切身感受另一种看待世界的角度。
让我们回到之前的诘问。帕斯克为了探索人类的适应性行为(adaptive behavior)确实放宽了人的定义,他认为“人本质上是适应性的”。从字面意义上看,从“适应性”角度看待人确实有那么点虚无的色彩,似乎人和其他生物没有什么不同,人的意义被消解。但帕斯克用一种非常存在主义的态度更进一步。在他的眼中,人不是什么先验的概念,不被神学和权力结构定义,而是能通过自己与他者、与世界的互动定义自身的自由个体。他曾这样说道:“人必须对某些事做出决定,才能成为人。”(Man must make decisions about something in order to be man.)这背后潜藏的观点不是“人被当做了机器,所以人可以被支配。”而是恰恰相反:“机器可以被视作人,所以机器和人同样高贵。”前者将人置入权力关系,所以人可以被贬损,就像人类制造出的为自己服务的事物一样。而后者将人视为需要平等交流的个体,所以人值得被尊重,每一次关系中的互动不可轻慢。
这种对人的重视体现在帕斯克的教育理论之中。他认为即便是培训技术工人,也应该使其从多样性中收益。工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会让他们将会成为“更好的公民”。他相信个体的潜力,并且认为这种潜力只能通过与其他个体或系统的对话(交互)来激发。
从这点来说,控制论(至少帕斯克的控制论)不是关于控制(control),而是关于几个系统之间的交流和适应,本质上是一种非等级制的互动。人不是一个握有绝对掌控权的管理员,而是一个倾听者,一个对话者。但帕斯克概念中的对话绝不仅仅是一团和气的相互赞同,“冲突”才是达成共识的首要方法,可以将其理解为一种非恶意的观点碰撞。帕斯克的学生潘加洛回忆“和帕斯克的对话经常会让自己达到意想不到的理解水平,但也会很快耗尽精力。”这种方式与帕斯克的极具戏剧化冲突的性格密不可分,这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帕斯克的研究方式和世界观,也可以解释他对戏剧艺术的兴趣。
帕斯克为什么着迷于戏剧?我认为他在艺术中首先关注的是人与人的直接接触和即时互动。他在1968年的“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展览上展出的装置“运动的对话”(The Colloquy of Mobiles)和提出审美有效环境概念就体现了这一倾向(相关内容可以移步《控制论的意外发现:艺术与电子游戏》)。在剧场中上演的戏剧中,观众不只是观看,而是能在面对面中被带入到戏剧演员的肢体动作和情绪之中。为了将这种艺术形式推向互动的极致,帕斯克曾有过一个堪称疯狂的想法:控制论剧院。通过阐述这个狂想方案,我们或许可以进一步去除关于控制论的误解。
控制论剧院
控制论剧院
控制论剧院(cybernetic theater)在1964年提出,是欢乐宫建筑项目的一部分。帕斯克设想了一种新型的戏剧和由此衍生的剧院,“观赏”方式很像戏剧和互动电影游戏的结合。戏剧保留了许多不同走向的剧情片段结构,它们包含在一个网状的结构之中。在特定的剧情分支点,观众可以基于对剧情和角色的理解,使用座位边的手柄向他选择的角色发出信号,让演员做出不同的行动选择。信号有几种预设,分别对应的排练好的表演,从座位传输到口译员,再由口译员通过声音信号和手势传达给演员。观众的总体选择经过综合后,会改变戏剧的剧情走向。帕斯克在此探索一种互动形式的戏剧,他将观众和演员通过反馈回路耦合在一起,演员和观众在不断互动中改变剧情的走向。
不得不说,控制论剧院乍看上去是相当疯狂的想法,虽然一切都发生在剧情的框架中,但这就是对演员的工具化,是赤裸裸的专制操纵。不过欢乐宫的发起人琼·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的看法却非常积极,她认为真实事件的产生的化学反应和互动会让观众和演员都更积极的参与,帕斯克对此显然也非常赞同。在当时的语境中,这或许是一种可被理解的立场。因为二战后的英国雇佣率下降,人均工作时长缩短,欢乐宫项目本身就致力于让工人能在休闲时投入更有意义的活动,充分发挥自己的主体性,而非只在酒精/牌桌-工厂流水线间来回切换的“工具”。
即便如此,我最初仍然认为他们的态度只是一种没有充分认识到技术两面性、非常天真的浪漫主义,但之后我发现自己只是在不顾具体语境的自作聪明。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剧院这种语境与电影院和智能设备非常不同,观众和演员在这里面对面交流,不论是认同还是冲突都是具体而真实的,这几乎天然的规避了匿名的恶意。控制论剧院中互动操控机制的目的在于将观众和演员拉得更近,让人有更多的参与感,同时也被设计避免发生某些极端情况。可不论是帕斯克还是林特伍德,那时都无法想象未来有一天,人与人之间将横亘着无数的智能设备和自动化机制。我们可以说这是时代的局限,但绝不是浪漫天真或想象力的匮乏。毕竟就连“先知”维纳,在晚年呼吁的也只是关注被自动化流水线冲击的工人权利,而没有提醒人们“中间媒介”的暴增极其隐患。
这些智能设备和自动机制确实加速了社会运转的效率,连接起更远的两端,让世界变“小”了。但同时这也鼓励一种虚拟且间接的接触,我们隔着屏幕,通过不可计数的中间媒介去“操控”那个我们没有具体感知的抽象个体。
被利润和商业驱动的“交互”更像是一种数字版的权力关系,人类制造的机器更像是“自动的仆人”。机器为我们提供选项,我们只是回答“是”或“否”,我们既不会说谢谢,也不会像面对一位朋友那样询问“为什么”。我们推崇的“数字化”不见得更好,但一定是“更容易的”。没有真实的互动,也就没有“真实”的烦恼。然而代价没有消失,而是转嫁给被庞大中间环节遮蔽的某处,并且最终会换一种方式回到我们身边。庞大的数字系统带来的种种荒诞之事每天都发生在我们身边;那些被“控制”的人,被排除在外的被遗忘者……
回到控制论,回到人
回到控制论,回到人
就像前面关于人与机器的诘问一样,许多人认为即便如此,技术带来的“控制和支配”的锅也应该甩给控制论。事实上,这更多是现代科学这种“官方科学”的态度:通过知识把握世界的内在机制,使其任由我们支配和处置。美国技术史学家安德鲁· 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认为“海德格尔将(现代)科学理解为关于‘座架(enframing)’和征服的计划。……而控制论的全部任务就在于如何弄明白一个无法被座架的世界。”控制论对于世界的想象是动态且即时的,这样的世界无法被人类的设计征服,“刻舟求剑”终会失败。控制论是反范式的,它不树樊篱,不结阵地。它为许多其他学科提供了最初的养分,其学科边界却在之后迅速消融。斯塔福德·比尔曾无奈的说道:“工程师们不知怎地夺走了控制系统的发明。”
近年来关于控制论的文字中多少都带着些为其正名的意味,我的这篇文字似乎也是如此。然而,如今再去呼唤对控制论“学科”的关注,无疑是不合时宜的,因为控制论在技术层面的先锋面向早已被更先进的知识和技术手段所替代。
控制论的宝石被分割成一块块闪亮的碎片,每块碎片都已被重新打磨,折射出自己的光芒。如今追溯控制论的历史,并不是要细数哪些宝石曾经来自控制论,然后将它们重新拼合,这不切实际也毫无必要。在专业知识量暴增的21世纪,用整体性的大一统学科统合如此多且深的专业领域,和征服宇宙是同一种妄想。那么我们如今为什么还要重提控制论呢?原因很简单,过程却困难重重——只是为了提醒人们不要忘记曾经那块完整的控制论宝石,曾经折射出怎样的光辉,那不是某个学术概念或技术核心,而恰恰相反:那是对人的价值既不傲慢也不贬损的肯定。这是维纳口中的“人有人的用处”,也是帕斯克所一直坚持的。
帕斯克这位“爱德华时期”的华丽公子,张扬而难以相处,内心却怀着最朴素也是最奢侈的愿望。他在《对话理论》一书中写道:
我们不能保证教育会让人成为杰出的发明家、艺术家或政治家。但我们确实隐隐约约的知道如何实现一个不那么宏大,但同样值得称赞的目标:帮助人学会理解并品味他的智识和周遭环境,体会它们的过去和未来;他将学会爱他的邻人,并不受限制地追求自己的抱负。
参考
1.An Approach to Cybernetics, Gordon Pask, 1961
2.Conversation Theory: Application in Education and Epistemology, Gordon Pask, 1976
3. Proposals for a Cybernetic Theatre, Gordon Pask, 1964
4.Gordon Pask and His Maverick Machines, Jon Bird & Ezequiel Di Paolo, 2008
5.The Cybernatic Brain, Andrew Pickering, 2010
6.The Fun Palace: Cedric Price’s experiment in architecture and Technology, Stanley Mathews
7.What the Frog‘s Eye Tells The Frog's Brain? J. Y. Lettvin, H. R. Maturana, W. S. Mcculloch, W. H. Pitts,Reprinted from: “The Mind: Biological Approaches to its Functions” , 1968 , P233-258
8.https://www.pangaro.com/pask-pdfs.html
9.《维纳传》 张国庆译 弗洛·康韦和吉姆·西格尔曼 2021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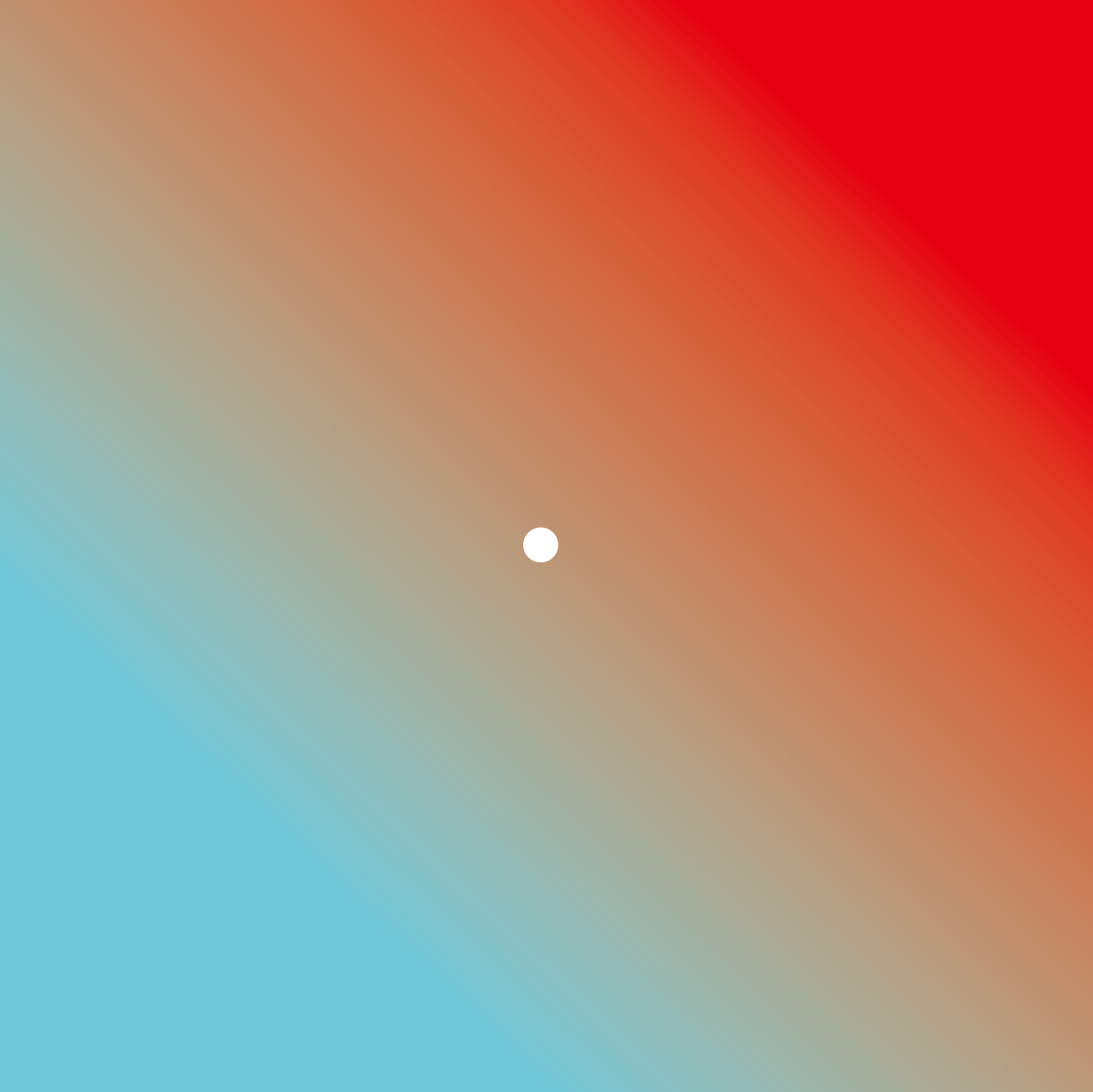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