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本文发表于1969年,那时的戈登·帕斯克还在普莱斯和林特伍德的欢乐宫项目之中。帕斯克将建筑空间视为一种「适应性结构」,并由此提出计算机系统控制的可动式建筑。以帕斯克为代表的一部分控制论学者,致力于广义的「自适应动态系统」的研究——这大抵是认知科学、神经生理学、计算机科学和机械控制的奇妙混合体,它与当时刚刚出现的人工智能共享一部分知识,甚至有人认为控制论就是人工智能的混沌雏形。
54后的今天,我们的认知刚好处于被人工智能应用的冲击之中。从2022年的Stable Disfusscion、Midjourney,再到今年初的chatGPT3。这些生成式AI展现了一种智能式定制化调用整合视觉和文本数据资源的方式。关于AI技术给创意产业带来变革的讨论贯穿始终。目前已经被判定为「即将消失」的职业包括但不限于「插画师」「美术设定」「文案」等等。但是按照AI现阶段的水平来看,它生成的内容很难直接作为成熟的商业成果应用,仍需要有经验的从业者的深化,并且完成与产业内其他环节的合作与连接。
如此看来,建筑设计作为一个高整合度的复杂分工,似乎很难被替代。但如果考虑到建筑设计中经常以大量图像作为阶段性成果,那么这些AI应用可以、甚至已经嵌入生产环节之中。这注定会淘汰建筑设计中一部分以图纸产出为主的细分工种。不只如此,在完全以经济效益为导向的建筑活动中(例如房地产业),当建筑设计只能作为夹在成本-利润中间、分类和组合建筑风格片段的细分工种时,建筑师就被缩减为他所掌握的建筑素材库,以及按照资本逻辑和成本标准对其进行排列组合的高级技工。这样的「建筑师」们被更稳定便宜的「智能风格手册」所替代也只是迟早。
这是面对新问题时,建筑设计的元语言(meta-language,指建筑学)被其他更有效用的目的和逻辑所挤占的案例之一。站在历史的角度上,或许可以像批评19世纪欧洲的学院派一样,批评这部分建筑师为「空间风格拼贴师」,但这对于每个处于产业生态和经济链条中的个体从业者都是不公的。系统性的问题也无法依靠局部的内卷来解决
作为一名控制论学者,帕斯克站在了计算机技术革命与建筑设计交叉的最前沿,试图为后者构建新的元语言。他提出的系统化的二阶设计思维,如今已经部分融入到了当今的设计教育之中,却在实践建筑师的愿景中依旧模糊。
这不奇怪,因为绝大多数建筑师注定只能实现但无法决定建筑「系统」的目的,即他只能控制设计的目标(一阶),却无权置喙设计目标的目的(二阶)。除非,他掌控了全部的生产资料与生产环节。而这,就是关于另外几个系统的问题了。
大目妖
2023年2月21日
戈登·帕斯克 Gordon Pask
戈登·帕斯克 Gordon Pask
1928年6月28日~1996年3月28日,英国控制论学者,教育家,互动艺术先驱,诺伯特·维纳之后最重要的控制论学家之一。1960年代后一直活跃在科技、教育和艺术等领域。详情可点击跳转「控制论的华丽公子、激进的对话者:戈登·帕斯克」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8000字
控制论的建筑学关联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控制论的建筑学关联
The Architectural Relevance of Cybernetics
戈登·帕斯克
1969年发表于Architectural Design, September issue No 7/6, John Wiley & Sons Ltd (London)
很容易认为控制论与建筑学有关,正如它与其他许多专业的关系一样——医学、工程或法律。例如,PERT编程语言无疑是一种「控制论」技术,它通常被用于施工进度计划。计算机辅助设计也是一种「控制论」方法,而且已经有几个应用于建筑的例子(例如,WSCC的规划提案中,设计师使用图形显示来表示结构模块在网格上的位置,并用计算机汇总了提案布局的成本结果)。在这些案例中,第一个案例(PERT编程语言)是控制论的一个有价值但相当浅显的应用;第二个案例可能会对建筑设计产生深远的影响。但它们都没有显示出控制论和建筑学之间更深层的联系。
如果让问题停留在这个层面上,那么建筑师就会将手伸入控制论的魔术袋中,取出那些似乎合适的把戏。当然,这非常合理。但是控制论和建筑学其实拥有一种更紧密的关联;两者共享一种相同的建筑哲学,在这个意义上,斯塔福德·比尔已经证明它是运筹学的哲学。
该论点基于这样的想法:建筑师首先是系统设计师,在过去的100多年里,他们迫不得已地对发展、交流和控制的组织性(即非物质的)系统属性生发兴趣。随机应变处理突如其来的设计问题,但一段时间以来,显然需要一个基础且统一的理论。控制论的抽象概念可以被解译为建筑学的术语(并在合适的时候等同于真实的建筑系统),从而形成一种理论(建筑控制论architectural cybernetics,或建筑的控制论理论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architecture),就此而言,控制论是一门填补了这个空白的学科。[1]
历史根源
Historical Roots [2]
历史根源
Historical Roots [2]
在19世纪初或之前,「纯」建筑学(pure architecture)是作为一种来自建筑艺术(the art of building)的抽象概念而存在的。它的准则基本上是观察以下方面后得到的凝练表述:工地上劳作的建筑工人,以及在不同时期和地点建造的建筑。建筑师在他们的学科中加入了些许工程实践和历史或审美感觉,并创造了具有稳固性和风格的新结构(译注:此处的结构并非是指工程技术意义上建筑结构,而是指由不同层面的要素构成的抽象整体)。总的来说,在「纯」建筑学中是依据上述准则来判断这些结构的。
当然,即使在那时,建筑师也被要求解决人的调节和容纳的相关问题;并因此而设计系统。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任务相当有限。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正确应用纯建筑学的准则来解决。人造物(房屋、学院或剧院)的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相当严格的建筑规范(例如指定可接受的整体-部分关系)以及社群或个人从业者的惯例决定的。从技术上讲,有公认的沟通介质来传达指示、指令和理念(风格手册等)。此外,还有一种元语言,用于谈论这些指示、指令和理念,并对它们进行比较、批评与评价(如稳固性或风格的陈述)。事实上,当做出阐释时,元语言陈述的主体便形成了纯建筑学的理论。因此,即便建筑师确实设计了系统,他们也不需要将自己视为系统设计师,而且证据也表明他们并未如此。[3]相反,建筑师的专业形象是一位成熟的房屋、学院或剧院建造者。
在维多利亚时代,新技术的发展过于迅速,以至于无法被纯建筑学所吸收,由此提出的新问题,不再能通过应用纯建筑学的准则来解决,例如设计一个「火车站」或一个「大展厅」。要解决这些(在当时)离奇的问题,显然需要将建筑需求视为人类社会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而且为此整合了新技术(布里斯托火车站、皇家植物园热带馆、水晶宫)。就我个人而言,这些解决方案非常漂亮。[4] 然而,它们是个别且独特的解决方案,因为在新的语境中无法进行普遍性与批判性的讨论。
让我们弄清这点。显然,有大量关于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Isambard Kingdom Brunel,1806-1859,主持设计布里斯托火车站)、德西莫斯·伯顿(Decimus Burton,1800-1881,主持设计英国皇家植物园热带馆)和约瑟夫·帕克斯顿(Joseph Paxton,1803-1865,首届世博会水晶宫设计者)对玻璃和铁艺的使用,以及技术和美学的讨论。但似乎没有人意识到这些「结构」在那个时代的建筑潜力方面的全部意义,即作为系统设计的范例。原因相当明显:虽然19世纪初的纯建筑学有一种元语言,然而这是一种阻碍创新的限制性语言,新的(增强的)建筑学尚未发展出它的语言。另一种说法是,新建筑学没有理论。[5]
建筑学的子理论
Architectural Sub-Theories
建筑学的子理论
Architectural Sub-Theories
取代了统一理论的是处理该领域个别方面的子理论;例如,材料理论、对称性理论、关于人类承诺和责任的理论、工艺理论等等。但(不妨说)这些子理论在19世纪后期都或多或少地独立发展。
很自然地,每种子理论都促进了某类建筑物或某种关于社会-建筑的信条;例如未来主义。然而,最有趣的一点是,许多子理论都是以「系统」为导向的;尽管它们预见到了这个词的发明,但从雏形的意义上说,它们是「控制论」理论,而且它们背后的思想对控制论作为一门形式科学的发展做出了宝贵的贡献。
建筑功能主义和共生主义
Archite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Mutualism
建筑功能主义和共生主义
Architectural Functionalism and Mutualism
一个结构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执行某些功能,例如为其居住者提供住所或服务。在这个层面上,「功能性」建筑与「装饰性」建筑形成对比;前者是一种朴素的结构,没有任何多余的东西。不过,功能主义的概念可以在人文主义的方向上得到有益的完善。毕竟,这些功能是为人类或人类社会而运行的。因此不能简单孤立地看待一座建筑,它只有作为一个人类环境才有意义。它不断地与其居民互动,一方面为他们服务,另一方面控制他们的行为。换句话说,结构作为包含人类组成部分的更大系统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建筑师则主要关注这些更大的系统;它们(不仅是砖和灰泥部分)是建筑师设计的内容。我将这个概念称为建筑的「共生主义」(mutualism),意思是结构与人或社会之间的共生主义。
功能主义和共生主义的一个结果是将重点转移到结构的形式(而非材料构成)上;材料和方法在设计过程后期才会突显。另一个结果是,建筑师被要求设计动态的而非静态的实体。很显然,系统中人的部分是动态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尽管不那么明显),结构部分必须被想象为可以不断地调节其人类居住者。
建筑整体主义
Architectural Holism
建筑整体主义
Architectural Holism
一旦接受了功能/共生关系假设的最初版本,那么任何单一系统的完整性都值得怀疑。大多数人类的/结构的系统都依赖于其他系统,它们通过人类的组成部分相互联系。根据假设,一些组织的整体不能被有意义地分解成几部分。整体主义有几种类型:
a.一座从功能上被解释的建筑只能在一座城市的语境中被有效考量(要注意的是,城市也是从功能上解释的,因此,它是一个动态的实体)。
b.一个(从功能上被解释的)结构,无论是建筑还是整座城市,只有在其时间上的延伸,即它的生长和发展的情况下才能被有意义地构想出来。
c.一个(从功能上被解释的)结构作为一个意图的一部分而存在,即作为一个规划的一个产物。
d.如果人应该意识到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假设的信条),那么建筑应该与这些环境结合或产生于其中(赖特的有机论)。
这是a、b和c的一个推论,即城市的结构不仅仅是社会的外壳。相反,它的结构作为一个符号控制程序,等同于那些已知的调节不同部落行为的仪式约束,它使行为保持稳定而非产生分歧。因此,建筑师对建立习俗并形塑传统的发展负有责任(这一观点只是将建筑控制其居住者的想法提升到了更高的组织水平)。
建筑中的演化思想
Evolutionary Ideas in Architecture
建筑中的演化思想
Evolutionary Ideas in Architecture
系统,尤其是城市的生长和发展以及通常说的演化。这个概念显然取决于功能主义/共生主义的假设(如果没有这个假设,就很难看出系统本身在什么意义上生长),尽管这种关联性常常未被说明。演化观点的一个直接的实际后果就是,如果建筑设计的生长是健康的而非癌变的,那么它们就应该有演化的规则。换言之,一个负责的建筑师必须关注演化属性;他不能只是站在一旁,将演化视作发生在他的结构上的事物来观察。演化论与c型的整体主义密切相关,但它是c型的一个谨慎的特殊版本,体现在日本建筑师的工作之中。(译注:此处指新陈代谢派Metabolism,是1960年左右由桢文彦、菊竹清训、黑川纪章等日本建筑师形成的建筑创作团体。主张采用新的建筑技术,并从有机体生命周期的角度看待建筑和城市,认为其是动态的,具有生长、变化和衰亡的阶段)
建筑中的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s in Architecture
建筑中的符号环境
Symbolic Environments in Architecture
人类的许多活动都具有符号性。人类使用视觉、语言或触觉的符号与他周围的环境「对话」。这些符号包括其他人、信息系统(如图书馆、计算机或艺术作品),当然还有他们周围的结构。
建筑一直被归类为艺术作品。而最新的子理论是,结构可以被设计(也可以凭直觉了解),以促进有效且令人愉悦的对话。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艺术形式中表现得最为明显,特别是超现实主义,它取决于一个主题矩阵中释放器(releasers)和超常刺激(supernormal stimuli,唤起内在的情感反应)的多样性(新颖性)的并置。在建筑层面,这种类型的设计出现在一些新艺术运动的植物超现实主义中。它在高迪的作品中成熟,特别是古埃尔公园(Parque Guell),在符号性的层面上,它是现存的最具控制论性的结构之一。当你探索这里时,声明(statement)是以释放器的方式做出的,你的探索被特别设计的反馈所引导,并在适当的地方引入了多样性(惊喜值)以促使你探索。
有趣的是,高迪的作品经常与功能主义形成对比。不过从系统的角度来看,它是纯粹而简单的功能主义,它的目的只是为了满足人类的符号和信息需求。[6]
建筑生产的机制
The Machinery of Architectural Production
建筑生产的机制
The Machinery of Architectural Production
正如一座从功能上被解释的建筑构成了一个系统一样,该建筑的建造也是一个系统。19世纪发展出的新技术和生产设施的普遍机械化,导致了与形式实现有关的子理论(最重要的围绕着包豪斯产生),这些反过来限制了能够产生的形式。
扩展的任务
The Widening Brief
扩展的任务
The Widening Brief
以上这些的结果本质上是控制论的子理论发展,许多建筑师想要设计系统,但总的来说,他们被期望设计建筑物。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事实(非常合理)。尽管如此,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建筑师的任务却在不断扩展。
这是由于一系列没有传统解决方案的问题(与航空航天发展、工业、研究、娱乐、海洋利用等有关的结构)。在这里,建筑师的处境与他们维多利亚时代的前辈被要求建造一个火车站时的处境基本相同。不过在某种程度上,由于客户和公共赞助者更普遍地采用系统导向的思维方式,约束已然放松了。如今,即使对传统项目而言,更早地介入设计过程也是合理的。例如,将城市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或至少是规划),并为其演化做准备,是很常见的。一所大学不需要被构想为一组围绕着中庭的建筑物,配有宿舍和讲堂。在某些情况下,教育系统可以在空间上散布,而不是局限在某一区域。
不论如何,建筑师都要被积极地鼓励预测趋势,如预见教育技术的发展,并为其对任何结构的影响做好准备。因此,建筑师经常参与到一个高等教育系统的筹划之中,不论它是否被称为大学。琼·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和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的「欢乐宫」(Fun Palace)项目是娱乐领域中该类型的早期项目,而且从展陈设计到工厂建筑等领域都不难找到例子。(了解欢乐宫项目可点击「欢乐宫 Fun Palace:未竟的赛博建筑,一个关于改善低生活的社会装置」)
我想明确的一点是,如今有一种对系统导向思维的需求,而在过去,人们对它只是多少有点深奥难懂的渴望。正因为这种需求,所以值得将孤立的子理论集合起来,从它们的共有构成部分之中形成一种普遍原理。正如我们已经论证过的,这些共有部分是控制、交流和系统的概念。因此,这个普遍原理不外乎是将抽象的控制论阐释为一种整体的建筑理论。
如果说必要的解释和整合已经完成,那还为时过早。但许多人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这里仅列举那些与我有个人联系的人:克里斯托弗·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1936~2022,建筑师,致力于从逻辑结合并系统化建筑的各个方面)、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1943年,计算机科学家,1968年创立建筑机器小组,1980年更名为麻省理工大学媒体实验室)、许多来自伦敦AA建筑学院和纽卡斯尔大学的学生和毕业生。
新理论的现状
Status of the New Theory
新理论的现状
Status of the New Theory
与19世纪的纯建筑学一样,控制论为批判性讨论提供了一种元语言。但控制论不仅仅是「纯」建筑学的延伸。正如我们之前所指出的,纯建筑学是描述性的(建筑物和方法的分类)和规定性的(如计划的准备),但它很少预测或解释。相比之下,控制论具有可观的预测能力。[7] 例如,城市发展可以被模拟成一个自组织系统(「建筑中的演化思想」的正式表述),在这些层面,有可能预测一座城市的发展在多大程度上是混乱的或有序分化的。即使预测的必要数据难以获得,但我们至少可以提出并测试一个合理的假设。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那些不是主要关于时间的预测;例如,预测空间和规范的约束对一个(从功能上被解释的)结构稳定性的影响。
控制论也具有一定的解释能力,因为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序有可能模仿建筑设计的某些方面[8](顺便一提,倘若程序能够了解建筑师并向其学习,而且以建筑师的语言实验的话——即通过考察计划、材料规格、提炼客户意见等)。这类程序显然是有价值的。它们是设计的潜在辅助工具;作为开篇提到的工具类程序的智能扩展。此外,它们提供了一种将建造系统(机械生产)与持续进行的设计过程相结合的方法,因为很容易在模拟中的一个特殊部分上体现当前技术的限制。然而,我认为这些程序在证明何为我们的建筑理论知识方面具有更重要的意义。只要程序能被写出来,控制论理论就具有解释力。
一些推测
Speculations
一些推测
Speculations
在建筑控制论的指导下,似乎至少有五个领域可能会取得快速进展:
- 各种计算机辅助的(甚至是计算机控制的)设计程序将被开发成有用的工具。
- 不同的学科(特别是社会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和经济学)中的概念将与建筑学的概念统一起来,以获得对「文明」、「城市」或「教育系统」等实体的足够开阔的视野。
- 在建筑作为一种社会控制的层面上,将有一种适当的和系统的构想(即在「整体主义」下提到的一个想法的萌芽将被详细阐述)。
- 功能主义的高潮是将房子作为「居住的机器」的概念。但是这倾向于一种作为服务居住者的工具的机器。我相信,这一概念将被提炼为一种环境的观念,在其中的居住者将与之协作,并且能外化他的心理过程。也就是说,相比于单纯的功能主义,共生主义将被强调。例如,居住的机器会降低居住者在记忆中储存信息和演算的必要,以及帮助处理较显见的家务,如垃圾处理和洗碗。此外,它将引起居住者的兴趣,并简单回答他的询问。
- 高迪(有意或无意地)实现了他的环境和居住者之间的对话。他仅凭物理静态结构做到了这一点(动态过程取决于人们的运动或注意力的转移)。这种对话可以在现代技术的帮助下完善和扩展,使我们能够在反应性环境(reactive environment)中编织出同样的模式。此外,如果环境具有延展性和适应性,可能会产生非常有效的结果。
我自己也沿着这些路线做过实验[9],但布罗迪(Brodey)和他的小组在环境生态学实验室的工作是一个规模更大的项目。计算机控制环境材料(environmental materials)的视觉和触觉特性(这些材料有足够的多样性,可用于大多数建筑用途),是对正在进行的事情的宽泛陈述。这些材料包括传感器,至于是触觉还是视觉则视情况而定,它们在几个通用层次上向计算机返回信息。在无人居住的情况下,反馈会导向与特定预编程不变量相关的稳定状态(例如,一个材料主体应保持机械稳定并占用一个规定值);而关于搜索过程,材料会主动寻找与它接触的人的迹象。如果环境中存在一个人类,计算机、材料和其他所有,就会与人类进行对话,并能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学习和适应他的行为模式。因此,在一种意义上,反应性环境是一个控制器,而在另一种意义上,它又被其居住者所控制。
一个简单的控制论设计范式
A Simple Cybernetic Design Paradigm
一个简单的控制论设计范式
A Simple Cybernetic Design Paradigm
在一个反应性和适应性的环境中,建筑设计是在几个相互依存的阶段中进行的:
- 明确系统的目的或目标(关于人类居住者)。应该强调的是,目标或许几乎总是不明确的。也就是说,建筑师对系统目的的了解不会比他对传统房屋目的的了解多。他的目标是提供一套约束条件,允许特定的、可能是理想的演化模式。
- 基本环境材料的选择。
- 选择要编入系统的不变量。一部分在这个阶段,一部分是在上个阶段,建筑师决定哪些属性将与人-环境的对话有关。
- 明确环境将学习什么,以及如何适应。
- 选择适应和发展的计划。如果系统的目标不明确,像(1)中那样,那么该计划中将主要包括一些演化原则。
当然,这种模式适用于在相当短的时间间隔内(几分钟或几小时)进行调整的系统。相比之下,像「欢乐宫」系统这样的项目,其适应时间间隔要长得多(例如,提案中提到的每8小时或每星期一个周期)。根据时间的限制和所需的灵活程度,使用计算机或多或少是方便的(例如,星期的周期通过灵活的办公程序编程会更经济)。但涉及的原则完全相同。
城市规划通常延续数年或数十年的时间段,按照目前的构想,规划是相当不灵活的。然而,上面提出的论点表明,它也可以是灵活的,城市发展也许可以有效地由一个类似于反应性环境对话的过程来管理(与居住者的物理接触让位于对他们的偏好和倾向的认知;一种对环境计算机器的不灵活计划)。倘若如此,那么相同的设计范式也是适用的,因为在目前为止考量的所有案例中,主要的决定都是系统性的,也就是说,它们实际上是对控制程序的描述与修改。这种普遍性是控制论方法的典型特征。
最后一个动作将会显示出控制论的意味。让我们把设计范式转向其自身;将其应用于设计师和他所设计的系统之间的互动之上,而非系统与其居住者之间的互动。设计者将计算机当作自己的助手,在这种的情况下这幅手套几乎是完美的。换句话说,当「控制器/被控制的实体」(controller / controlled entity)这对混合词被「设计者/被设计的系统」或「系统环境/居住者」或「城市规划/城市」所取代时,其中的关系将被保留。但是请注意其中的引起错觉之处:设计者控制着控制系统的建造,因此设计是对控制的控制,也就是说,设计者的工作与他设计的系统基本相同,不过他在组织层级中的更高层次上运转。
此外,设计目标几乎总是不明确的,而「控制器」也不再是这个纯技术名词通常使人联想到的独裁装置。相反,控制器是一种催化剂、支柱、储存器和仲裁器的奇怪混合物。我相信,这些都是设计师应该在他的工作中发挥的作用(当他在专业上扮演控制器的角色时),同时他也应该将这些品质置入他所设计的系统之中(控制系统)。[10]
注释
注释
[1] 相似的观点也适用于工程学,因为工程师像建筑师一样,建造了人工制品。当然,有些工程师会使用控制论。但这种要求在工程中并不普遍;控制论的影响也没那么大,因为在控制论作为大胆的创新概念出现之前,已经存在一套值得信赖的、预测性和解释性的工程理论了。此外,虽然所有建筑师设计的系统都与人类和社会密切互动,但大多数工程师(有明显的例外)并未强制如此。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是主要难点,这只有通过控制论思维才能克服。
[2] 对历史起源的选择多少有些武断,这取决于作者想要强调的重点。例如,专注于形式逻辑的亚历山大把控制论的概念基本上追溯到洛多里和劳吉尔(Marc-Antoine Laugier和Carlo Lodoli,18世纪新古典主义的首批理论家)。在本文中,我急于追索控制论思想的实用性发展,并乐见它们在现代建筑史上的出现。
[3] 有两类重要的例外情况:(i)天才建筑师,他们具有广阔的视野,促使他们以系统和跨学科的方式看待事物。他们一直都层出不穷。例如克里斯托弗·伦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英国建筑师,1632-1723曾主持设计伦敦圣保罗大教堂)和约翰·索恩爵士(Sir John Soane,英国建筑师,1753-1837,曾主持设计英格兰银行)。(ii)像约翰·纳什(John Nash,1752-1835,英国建筑师,摄政时期伦敦的主要规划者)这样的人,他的才能在于将城市发展构想为一个功能和审美的整体。但是,在19世纪初的信条中,这些人可能是「有远见的组织者」,而非「建筑师」。
[4] 我选择这些例子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它们在教科书中广为人知,但主要是因为它们的系统性和向居住者传达设计者目的的方式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两座建筑仍然存在(除水晶宫之外)。我刚好想起了水晶宫。即使是在其庸俗化身中,它也是一个了不起的结构。由于它是最早的预制建筑之一,因此也算得上是工程层面上的系统设计作品。
[5] 缺少适当的元语言并不是唯一的因素。正如尼古拉斯·佩夫斯纳(Nikolaus Pevsner,德裔英国美术史家,1951-1974年间曾编纂46卷本《英国建筑》)所指出的,工程师和艺术家们追求不同的发展路线,两者或多或少地相互冲突,这多少说明了建筑的一些特异性。然而,如果存在一种元语言,那么本世纪的综合建筑就能更早实现。
[6] 显然,从其他方面来看,居住在其中是令人不适的。
[7] 控制论对建筑学的影响相当大,单纯因为该理论确实比纯建筑学有更强的预测力。例如,控制论对改变生物化学形态的作用相对较小,因为尽管这些概念与从酶组织到分子生物学的一切都有联系,但生物化学学科已经有了自己的预测和解释理论。我在注释1中就工程学提出了同样的观点。
[8] 尽管还有其他案例,但这里我主要指的是尼葛洛庞帝小组的工作。
[9] 例如,「运动的对话」装置讨论会和Musicolour系统,A Comment, A Case History and a Plan in Computer Art,Jasia Reichardt编
[10] 本文中提出的控制论概念在以下出版物中讨论过:《An Approach to Cybernetics》,Hutchinson(伦敦)出版,1961年(1968年平装本);《Prospect》的 「My Predictions for 1984」,《The Schweppes Book of the New Generation》,Hutchinson(伦敦),1962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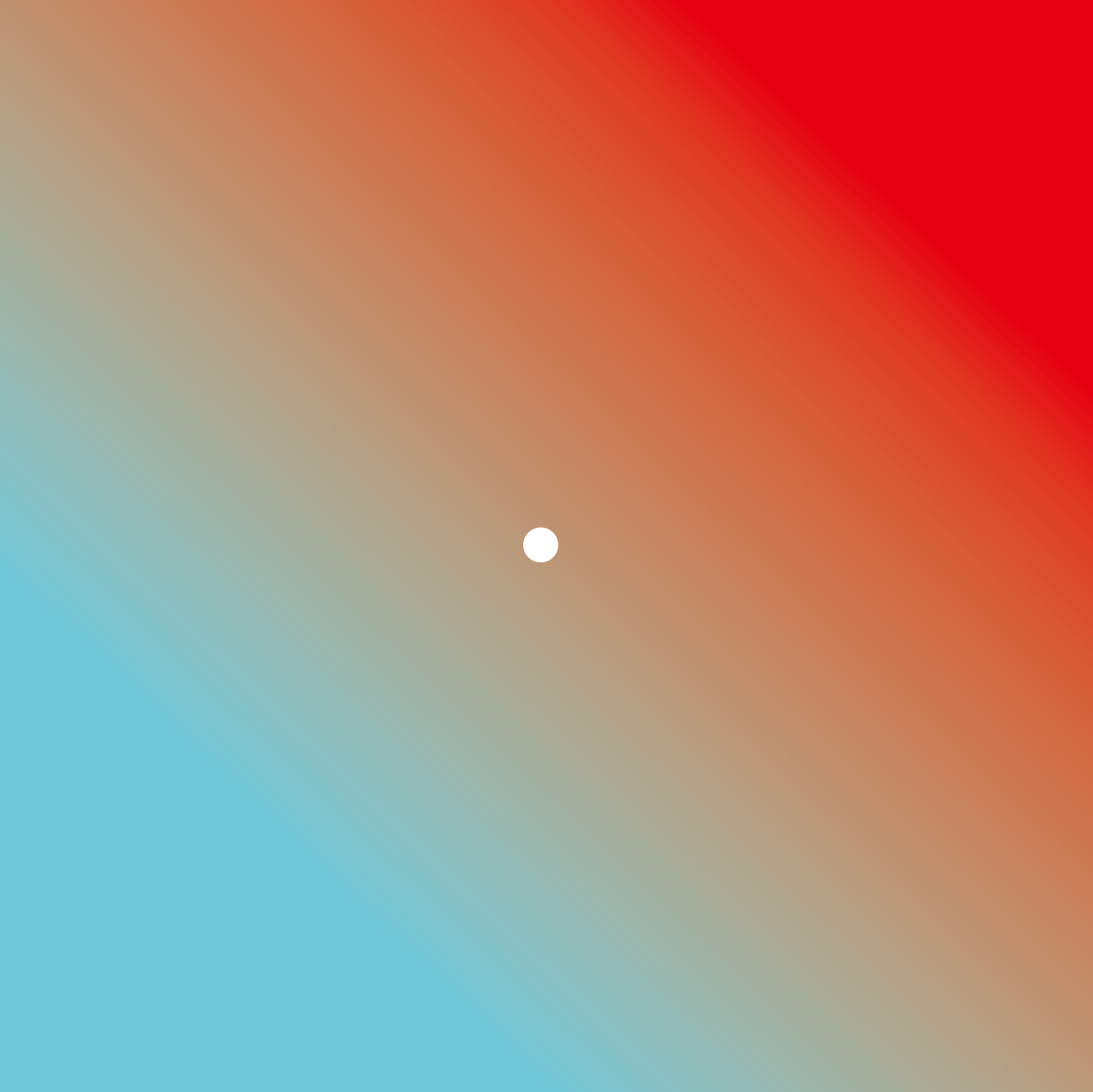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