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黑箱,black box,这个词是如此直观而具有画面感:一个黑色的盒子——很容易唤起诸多感觉:神秘、模糊、未知……这些情感清晰地指向某种亟待探索的未知事物。我想也正是这一特点,让这个源于电气工程专业的术语最终在大众语言中占有一席之地。
如今,“黑箱”一词已经成为一个相当常见的隐喻符号,用来描述我们无法完全了解内部机制的某件事物,而且似乎经常带着些许贬义。被贴上黑箱标签的东西,好像大多都决定了我们的某部分生活,可我们却无法了解或掌控。伊藤纱织就用“黑箱”来比喻性侵事件映射出的日本社会的一系列潜在规则。当然也有黑箱的含义更偏中性,仅仅代指某一块尚未被拆解的整体知识,等待好奇的人们去学习。
当人们在日常中使用“黑箱”一词时,其中包含了一种我们需要将其打开的愿望,似乎“黑箱”代表一种“非正常”的状态。如果追求“正常”的状态,那么办法就是打开它,让它变得透明,换言之就是让“黑箱”消失。这似乎是面对“黑箱”时唯一能被接受的立场,它的背后是一种科学主义式的信仰,是一种征服自然的雄心,认为万物都可以用科学的方式条理化。
现代科学的确打开了自然世界的一个又一个“黑箱”,而且每一次都将人类对世界和自我的认识提升到新的水平。但是假若某一天人类遇到了无法打开的“黑箱”,抑或是发现我们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打开过任何“黑箱”时。人类该如何认识“黑箱”并与其相处?这是一个科学的问题,更是一个哲学问题:如何认识并存在于这样的世界。
下文我将介绍一下“黑箱”与控制论(Cybernetics)的故事,以及英国控制论学家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理论,顺便聊聊控制论中的黑箱认识论。
关于「黑箱」
关于「黑箱」
据考证“黑箱”最早出现是在1943年兰德公司名为《从一个黑箱中建造出轰炸机防御系统》(Bomber Defense from a Little Black Box)的报告之中。军方出于保密和技术复杂性的考量将磁控管部件称为一个“黑箱”。在此后的一段时间内“黑箱”便成为当时许多军事机密技术的代称。但这一说法我仅见于中文互联网,未找到相应的原文。在我查阅的更多的资料中也没有明确指出“黑箱”一词的明确来源,但普遍认为该词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出现在电气工程领域,特指无法打开具有输出输入端口的密封设备。当工程师在调试或使用时,只能通过输入电压或其他干扰,观察输出端的结果来判断设备状态。但无论是哪一种,都和控制论这门学科颇有渊源。
同样在40年代,控制论的创始人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和学生朱利安·毕格罗(Julian Biglow)正在为军方开发对空火炮自动控制系统。虽然军方最终没有采用维纳的方案,但是他们在1942年提交的一份报告《外推法、内推法和平稳时间序列平滑法》却对军方的后续研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报告阐述了维纳发明的一种基于概率理论的非线性统计方法,用来预测导弹位置并自动控制火炮系统。
维纳以此为基础设计的的电路系统能够将10秒到20秒内观测到的目标飞机的位置信息转换成一系列电子信号,并计算出未来某一特定时刻飞机在空中的位置。但维纳过于追求位置的精确性,加之当时的技术水平限制,导致系统最终没有投入使用。最成功的一次他们的样机提前半秒预测了飞机的位置,但这在实际应用中远远不足够让火炮响应。但在之后,这篇报告和系统方案却产生了超出军事领域的影响,甚至可以说重新定义了通信技术科学。
而且维纳发现,在这套系统中除了电路与机械之外,飞行员的动机、目的、感官运动能力以及火炮操作员犯错后过度补偿的条件反射都会对系统的准确度产生影响。因此他邀请哈佛医学院的阿图罗·罗森布鲁斯(Arturo Rosenblueth)来解决防空火炮系统中“纠缠不清的物理、神经生理学问题”。最终,维纳通过反馈串联起了机械和生理,建立了完整的电信号回路。由此伴随的一系列通信过程中的具体问题的回应,构成了后来控制论的基础。维纳在1948年出版的《控制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
我们可以稍加简化的说,控制论最初关注的是各个系统之间的关系,它们(他们)如何互动,如何反馈。维纳基于概率理论的统计方法,就是为了对系统反馈过程中产生的海量的、非线性的数据进行有效建模。从而通过这种方式了解极其复杂事物的状态。
艾什比的大脑研究与黑箱
艾什比的大脑研究与黑箱
第一个将“黑箱”带入严肃讨论的人,是英国控制论学家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如果说维纳是从机器一端切入并总结出控制论的话,那么艾什比的路径则完全相反,他的起点在生理和病理的领域。这是因为艾什比在控制论学家之外,首先是一名长期工作于精神病院的病理学家。
罗斯·艾什比1903年生于伦敦,在32岁之前,都在尽力走一条符合父亲期望的道路—成为一名外科医生。虽然他少年时期接受的教育算不上良好,而且第一个大学学位是剑桥西德尼苏塞克斯学院(Sidney Sussex College)颁发的动物学学士,但他之后还是坚持继续在圣巴塞罗缪医学院(St Bartholomew)进修医学。尽管如此,艾什比在毕业之后,也没能成为一名外科医生。从1930年起,他先后在几所精神病院担任精神科医生和病理学家。艾什比属于弗雷德里克·戈拉(Frederick Golla)领导的一个非常唯物主义的精神病学流派。他们相信所有的心理现象都在大脑中有对应的物理基础。
从1928年起,艾什比开始在日记中持续记录他对人类大脑的持续思考。但他明确表示这些内容和日常工作无关,仅仅是纯粹的爱好,是为了“编织令人愉快的纯思想模式,不受社会、财务和其他干扰。”我们可以说他对大脑的兴趣或许和工作不存在功利上的联系,但是这显然与精神病临床工作关系密切,因为正常的大脑和病理性的大脑是一体两面的。艾什比从这里开始无意间走入了控制论的世界。
大脑作为人类身体上最复杂神秘的器官,是一种经典的“黑箱”。著名学者金观涛和华国凡先生在《控制论与科学方法论》一书中总结了三类“黑箱”:
- 某些内部结构非常复杂的系统。这类系统被人们称为特大系统(largness)或特大黑箱。
- 至今为止人们所拥有的手段尚不能打开的黑箱。例如地球内部构造。
- 人类的某一阶段打开黑箱会严重干扰其本身结构的系统。例如生物体。
作为一名精神病医生,艾什比面对的大脑就属于极端复杂(1类),打开又会严重干扰其自身结构(3类)的“黑箱”。因此他的关注点不是大脑的结构和功能,而是大脑和神经系统的适应性行为。在他看来,“适应”意味着能发现并保持与周遭世界的动态平衡关系。他断言,精神病学中“适应能力是核心,病人正是因为丧失了适应能力才会被送到精神病院。”而正常大脑(系统)所具有的最重要的特征,就是稳态机制(homeostatic mechanism)。
艾什比的控制论理论的要点在于系统(大脑或者其他复杂黑箱)和外界交互时如何适应外界,保持内部稳态。他在《控制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ybernetics)开篇写到“全书的目的在于说明:当我们打算使一个非常复杂的有病机体,例如病人,恢复他的正常机能时,我们应该遵循什么原则去做。”艾什比围绕此提出了一系列描述系统状态的概念和术语:变异度、稳定性、调节、反馈……他使用抽象的数学和统计学语言定义和说明这些词语,这使他的理论看上去完全与当时的医学无关。我想这也是艾什比早期发表于期刊《精神病学杂志》上的论文反响平平的原因,它们对临床实践几乎没有指导意义。
不过我们可以从中发现艾什比将自己的理论普遍化的愿望。他意识到“所有的事物实际上就是黑箱,并且我们从小到大一辈子都在跟黑箱打交道。”而控制论关于输入、输出和反馈调节的一般性原理就是在默认“黑箱”存在的前提下与其打交道的绝佳方法。因此艾什比有意识的将自己的概念和方法应用在科学和社会等领域,扩展控制论理论的边界。
黑箱认识论
黑箱认识论
对于接受了现代科学将一切透明化、清晰化的信念的我们来说,艾什比围绕“黑箱”发展出的这套理论有些难以理解。尤其是如今的“黑箱”在作为大众语言中隐喻符号时,显露出的“亟待打开”的潜意识倾向。我们似乎认为打开了“黑箱”才能算是认识黑箱,而在外部通过输入和输出的统计进行建模来了解“黑箱”只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艾什比的理论建构可能与他的职业经历和他不可知论者的标签有关,但起决定作用的是一种对人与世界关系的认知方式,既“主体认识与客体之间归根结底是通过输入输出相互联系的。”
从普通人的角度来看,他们在使用某个物件(系统)时,并不需要了解其构造和原理,例如电脑。从工程师的角度来看,他们只需要合理地耦合各种“黑箱”,就能得到一个可使用的稳定系统。而从科学工作者的角度来看,在认知水平有限的阶段,科学家们要暂时收起掌控整个系统的野心,在承认“黑箱”的前提下工作。即便“打开”了某个“黑箱”,又总是有更多的“黑箱”等着他。从微观到宏观、不同尺度、有型到无型的“黑箱”一层套着一层,不可能穷尽理解。甚至在打开某个“黑箱”时所用的工具也是另一个“黑箱”。
因而艾什比认为科学家面对“黑箱”(复杂系统)时最重要的不是将其“拆开”,以将绝对的客观规律摆在面前(这不可能)。关键是要提出真正准确的问题,这样才能得到真正想要的答案,而非自以为要知道的答案(He must ask for what he really wants to know, and not for what he thinks he wants.)。艾什比举了天文学家的例子:
当天文学家想要知道星团的性质时。如果他提出的问题是知道各个星球的运动轨道,那么他只会得到成山的数字和表格。而如果他问“星团会不会缩成一个球,或者散成一个盘。”他才能得到有意义的答案,得到有指导价值的理论模型。
在艾什比看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就是对各种“黑箱”的相互耦合,在此过程中产生的各种技术都可以被视为“调节器”(regulator),用来不断校正人类和世界这个“黑箱”的反馈回路。他的控制论就是研究反馈过程中系统自身如何通过“自适应”保持自身“稳态”,以及当多个系统耦合时怎样保持更大范围的“稳态”。
可以看到,艾什比对于人对世界的参与和改造方面,是持着非常积极的态度的。黑箱认识论也并不是对世界持不可知论的神秘主义,它仅仅是承认人的存在与其局限性。毕竟人类终究只能以人类的方式认知世界,我们的生理构造决定了所有知识的建构都只能以人的尺度为基准。人类无法按照世界本来的面目去理解它,打开“客观世界的黑箱”可能只是一个伪命题。人类最先进的科学理论或许能无限逼近“客观世界”,但归根结底也都是带有人的目的、对部分客观世界的同构。因此黑箱认识论不将规律看做事物间的本质联系,而是输入输出的变量之间的约束。
或许在艾什比看来,我们从来就没有“打开”过任何“黑箱”,也不需要打开任何“黑箱”。因此当我们碰到了无论如何也打不开的“终极黑箱”时。也不必那么绝望,我们其实早就学会了在这样的世界中乐得其所。
被「黑箱」改变的罗斯·艾什比
被「黑箱」改变的罗斯·艾什比
一般来说写到这里,我总想矫情地升华些什么。但是在艾什比这里却有点困难,因为他的人和理论都带着严谨的“学究气”,既缺乏维纳的那种人文主义关怀,也没有戈登·帕斯克式的浪漫主义理想(关于帕斯克请阅读《控制论的华丽公子、激进的对话者:戈登·帕斯克》)。若要说艾什比与他的理论中最具戏剧性的部分,也仅仅在后者对艾什比人生轨迹的影响之上。
艾什比的前半生基本上是竭力活在他人的期望中,但尽管如此,不论是成为外科医生的学业之路,还是精神病医生的职业生涯,他都算不得成功。艾什比对于“大脑”的业余爱好,最初只是他寄托真实自我的一种逃避方式。
1946年,他在自己家中制作的控制论大脑模型“内稳态机”(the Homeostat)被媒体争先报道,甚至在英国先驱报上比查尔斯王子受洗占据更大的版面。可艾什比却对将自己的“业余爱好”公之于众非常恐惧。他害怕探索未知的纯粹乐趣会被功利所取代。世界对他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黑箱,由于之前一直没有问出属于自己的“真正”问题,他也就缺少将自己的小世界融入这个大世界的勇气。
1952年,艾什比的第一本书控制论《大脑设计》(Design for a brain)获得了很大的成功。该书出版不久后,他在日记里这样写到“四十年来,我讨厌各种变化,只想留在原地。我不想长大,不想离开母亲,不想从学校去剑桥,不想去医院……我每走一步都不愿意。现在我似乎变成了相反的人:我唯一的目标就是继续前进。”
同年,艾什比受沃伦·麦卡洛克邀请赴美参加第九次梅西会议,他也随之被引荐到控制论的核心圈子中,他的人生轨迹因此彻底发生了改变。1959年到1970年间,他先后在美国博登神经研究所(The Burden Neurological Institute)和伊利诺伊大学生物计算实验室(Biological Computing Laboratory)担任教职。
从艾什比之后的经历来看,他无疑是一名出色的教师。艾什比的著作都非常像“教材”,虽然它们并不是作为教材出版的。在1956年出版的《控制论导论》一书,他中对维纳的《控制论》做了简洁化的处理。因为他坚信控制论的基本概念都非常简单,仅仅依靠基础代数和初等的微积分知识就足够,无需电子学那些复杂的公式和数学知识。他甚至还在每一节末都设置了练习题。
艾什比在伊利诺伊大学的学生和同事都对他的教学赞赏有加,因而他的控制论思想的影响也是非常广泛。其两本著作也都先后引进中国,钱学森院士在1958年出版的《工程控制论》中对艾什比的理论也多有着墨。上文提到的金观涛先生在八十年代将艾什比的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出版的多本著作也都很有价值。
1970年8月,艾什比从伊利诺伊大学生物计算实验室退休。回到英国韦斯顿(Westons),成为卡迪夫威尔士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ales in Cardiff)的荣誉教授,任教于应用数学系。
1972年,罗斯·艾什比诊断有脑瘤,11月15日于韦斯顿去世,享年69岁。
参考:
- 《大脑设计》W.R.Ashby 乐秀成 主熹豪 等译 1991年
- 《控制论导论》W.R.Ashby 张理京 译 1965年
- 《维纳传》张国庆译 弗洛·康韦和吉姆·西格尔曼 2021
- The Cybernatic Brain, Andrew Pickering, 2010
- http://www.rossashby.info/index.html
- “黑箱”简史:如何从专业名词变成大众隐喻? 贺久恒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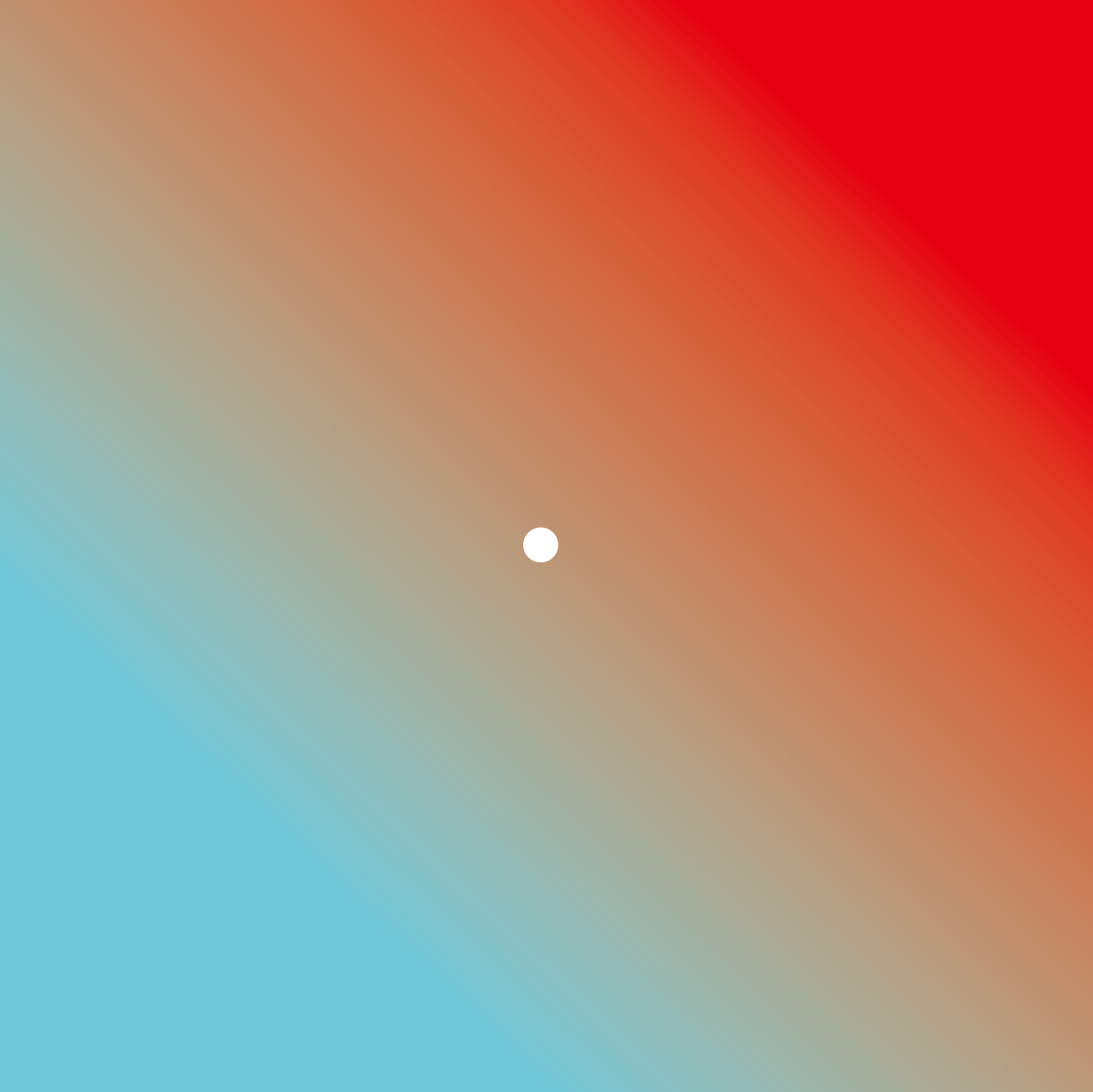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