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落日间链接:电子游戏的药理学 | 落日间
两年前的今天,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选择离开了这个令他绝望的世界。
他曾在南京大学哲学系讲课,那时的我也曾混入各硕博同学中,在哲学系楼和高研院的教室中聆听过他的教诲,只是我当时完全无法跟上他的讲课。数年后,前几日我偶然从书架上翻起《象征的贫困》以《南京课程》,觉得或可做些笔记,并将其与我所熟悉的对游戏的思考做一次对接,而此时恰好是斯老师(如果我能这么喊的话)辞世的两周年,希望以此文表达对斯老师的纪念与追忆。
我并不希望从斯蒂格勒哲学的研究者视角写作这篇文章,即便我希望通过此文与学术圈有所交流,但我更喜欢的身份,是作为认同其视域和试图理解其努力的跨界合作者出发,希望能够借此与其他的研究者一同合作交流,继续推动思索和具体的实践的尝试。
落日间较少主动谈论和引用哲学话语,比起谈论哲学而容易陷入困境,我更愿意以哲学地方式行事,面向更多的非学术化的人群;而即便谈论哲学,我也更喜欢威廉·弗鲁塞尔这样无过多哲学史挂碍的写作,而非背负着千丝万缕哲学史重负。所以这篇文章更多是作为对斯老师哲学的读书笔记的整理拓展,以及自己对游戏思索的对接,并非我所希望进行的学术写作方式。
所以在此不预设读者已了解斯蒂格勒的哲学,故本文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基于个人阅读而形成的对斯蒂格勒概念和思想路线的解释;第二部分则是我希望将自己对电子游戏的思索与其哲学思考对接,希望将电子游戏纳入各位研究者和实践者的视野,或者说,探索电子游戏作为药,作为武器的可能。
此外写作和阅读过程中我也发现国内许多斯蒂格勒的译文间并没有能有统一的翻译和术语协定,往往是一本一个翻译,这使得在阅读的过程中遇上不少麻烦,此处推荐友人整理的 贝尔纳尔・斯蒂格勒之友协会 这个共享的线上页面,有许多带有原文对照版本可供参考和感兴趣的朋友的扩展。
I 斯蒂格勒的普遍器官学
I 斯蒂格勒的普遍器官学
失去知识
失去知识
斯蒂格勒觉得人类在变得无知。
这种目前仍在发生的巨大转变从19世纪就伴随着技术进展在加速推进,他将这一过程称作「无产阶级化」(proletarianization),意思是失去了生产能力,失去了生产的知识。
这里「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被斯蒂格勒分成了三个阶段:
19 世纪的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丧失;20世纪的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丧失,以及21世纪,我们见证的了这个理论知识(savoirs theorique)丧失的时代的诞生。
斯蒂格勒借此「获得知识/失去知识的视角」的思考重新回到对传统哲学文本的批判反思中,例如在《南京课程》最后一讲他展现出对马克思无产阶级理论的局限性的指认:
马克思主义的否定辩证法产生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而不是一种「去无产阶级化」,即在市民的个体化中重新获得知识的政治方案。
而他也谈到了黑格尔的「主奴辩证法」(主人让奴隶直接从事和接触生产,奴隶拥有了劳作的知识,掌控着主人的生产,而实际上他成为了主人的「主人」)也没能预料到的是奴隶并不能因而掌握主人无法掌握的知识而成为「主人」,而转为服务于机器(失去了知识),而永远都是奴隶:
技术会使得工人的知识发生短路和绕避,因而工人就变为一个奴隶,而不再是一个雇工,不再直接服务于主人,而是直接服务于机器。
矛盾的技术
矛盾的技术
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
我们常把技术的发明当作人类的进步,知识和科技的发展。这也是对的,这些被发明出来的,将人的知识外化的技术中有一种内在的矛盾,即带来了上文所说的这种失去知识的过程(「无产阶级化」)而也是获得知识的过程(我们获得了内燃机,电影,电视,互联网),斯蒂格勒将这些能够将人类的记忆和知识外在化存储的技术称作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注:与胡塞尔的心理知觉持存的原生持存,和作为心理记忆的第二持存相对)
任何知识的外化(exteriorisation),都将带来的这一结果——而明显矛盾的是知识的建构恰恰依赖于知识的外化——这样,数字的、模拟的和机械的踪迹就是我所说的第三持存(tertiary retentions)
药性的(the pharmacological)
这种第三持存的既好(创造了知识)又坏(让人们失去了知识)的矛盾特性,斯蒂格勒借用了古希腊中的药(pharmakon)作指代,称这些「第三持存」是药性的,因为古希腊语中的药同时指毒药也是解药,就如同文字和写作,当我们写下的文字帮助我们思考,语言造成的理解的障碍也就开始了。
所以他所说的药性的(the pharmacological),或药理学的,指的就是这个东西有好有坏,在治病的同时也会带来毒性,在毒性的同时也有带来解放的可能,我们可以参考哲学家的评论:
对于斯蒂格勒,它仅仅意味着一个悖论——一个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既带来好处又带来损害的现象。 比如计算机是有“药性的”(pharmacological),因为它们引入的既是解放的可能性,又有新产生的压迫。 如果对德里达来说,这个术语是相当具体的,那么对斯蒂格勒来说,则是非常普遍地意味着一个悖论性的二元论,其中包含了相互矛盾的力。—— Alexander R. Galloway《Bernard Stiegler, or Our Thoughts Are With Control》
而这种第三持存的出现则较为规整的对应于上文所说的三种知识的丧失:
1 数字第三持存(digital tertiary retention,如电脑和数字化网络),或记忆技术制品(mnemotechnical artefact) -> 当前的理论化与审思的智性能力(noetic faculties)当下的无产阶级化; 2 模拟第三持存(analogue tertiary retention,如电影,电视,录音)导致20世纪的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无产阶级化; 3 机械第三持存(mechanical tertiary retention)是导致19世纪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无产阶级化的主导因素。 ——《南京课程》p60
由此斯蒂格勒展开了很多讨论,例如从第三点的机械第三持存的视角出发,他思索当机器取代人们工作,人们就开始失去了技能,不再知道应该怎么做(savoir-faire 就是法语的「知道如何做」的意思),而这就要求回到哲学家西蒙栋等人对机器与人的关系的思考,那也理所当然地会回到控制论(人与机器的控制关系)的思索中;而例如模拟的第三持存出发展开例如审美和艺术的问题,音乐的演奏与欣赏原本是一体的,而后如何分离出解释者-演奏者-欣赏者,从而让艺术走向一种糟糕的境地;电影和各种大众媒体如何进行生活方式的宣传的塑造等等,让我们失去了生活知识的把握(savoir-vivre 意思就是如何生活)。
而回到今天数字化时代的当下,我觉得他最重视和批判的是基于大数据和超级记忆装置等一系列的技术的某种「自动化」给人造成的短路,自动决策(automated decisionmaking)与基于驱力的自动主义(drive-based automatisms),当机器和大算法代替我们决策,那整体上会带来功能性愚蠢,带来了一种思考的无能。
第三持存由于引起了一种中断(disruption)而引起了「无产阶级化」。
想象一个建立在个人,技术,周遭世界之间的循环与回路,而新技术(第三持存)的发明实际上会不断修改这个回路,把更大一部分需要涉及的知识或技能排除在外,让这个回路变得更短,或许换一个互联网人们习惯的词语,那就是「封装」。
举个或许不恰当的例子,过去人们需要耕地,种田,制作工具,收割,运输,处理,清洗,烧柴,烹饪,而今天这个循环的回路只剩下了,打开软件 → 看看推送什么好吃的 → 购买 → 等待后直接收到成品。这个原有的个人与世界之间链接的回路实际上就被短路(short-circuits)或绕道了(by-pass),我们甚至都不再能辨认出可食用的植物,不再能使用人们最初使用的工具,也不再会处理食材和做菜。
语法化、编程化、文法化(grammatization)
这样的机器制造 → 知识外化 (exteriorisation)→ 无产阶级化的过程马克思将其理解为一种物化(materiaization),利用生产资料进行人类的技术自我生产(technical self-production)(p89),所以无产阶级化的问题被提出了,就像刚才的矛盾所说的「即由知识的外化所导致的知识破坏的问题,然而知识的外化又是一切知识得以建立的条件」
这样的外化过程被马克思描述为语法化、编程化(grammatization)。这个描述很形象生动,就如同语言发展过程中在很晚近时才出现语法学家,把人们日常的言语行为变为规范的语言模式,并且由此教育其他人,此后语言的生产和创造就会被纳入形式化的过程中去:
「语法化是一个来描述、形式化、分离人的行为、使之可被再生产的过程」,斯蒂格勒在最近的一本书中解释道。文法化是把人的行为给描述、形式化为字母、词语、书写和代码的进程。在这个概念中,也能听到马克斯·韦伯的「理性化」概念的回响。所以,它的意思不仅仅是书写本身,而是关于还原与形式化的一个更大的进程。 (Galloway) 一种分析的形式化,离散化(discretization),再生产和自动化的过程。……语法化过程就是外在化(exosomatisation)过程和人的智性经验本身的人为再生产,智性经验、智性意义心智的人为再生产,让其变得可再生产与可传递。即建构一种建立在第三持存积累(accumulation of tertiary retentions)之上的知识。这些作为语法化之结果的记录恰恰是第三持存。(p94)
所以从斯蒂格勒自己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意识到,并不仅仅是这些技术物的发明导致了「无产阶级化」的问题,不如说这些技术物本身也是启动并在一个更大的一种「形式化、离散化的」被称作「语法化」的过程不断再生产与累积的结果。今天不断地产生这些短视频恰恰不仅仅是因为短视频的发明,而也恰恰是对整个消费社会,移动互联网的编码过程和视频对心智的影响导致了这些短视频的生产与累积。
个体化/个体生成(l'individuation)
第三持存使人们被「无产阶级化」,但这就涉及到一个过程,即第三持存如何和人们发生关系?斯蒂格勒引用了一个来自于哲学家西蒙栋的术语——个体化/个体生成(l'individuation)来描述了在技术-第三持存的视角下的个人,集体,技术的一系列动态过程。
我认为「个体化」其实和今天常谈到「自我」和个人表达有关,今天说,这个人有想法有自我,往往涉及到借助其他事物(借助第三持存如电影创作,文字创作)进而彰显自我,或者是对于于艺术作品,事物,能够独立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等等。
理解「个体化」这个概念,或许在《人类纪里的艺术:斯蒂格勒中国美院讲座》中说得更加清晰,斯蒂格勒在描述业余爱好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这样表述:
艺术业余爱好者热爱的是艺术作品。而就他们热爱艺术作品而言,这些艺术作品对他们也起了作用。也就是说,业余爱好者被这些艺术作品改造过了:如果从西蒙栋谓之过程的个体化这个概念上来说,他们被个体化了。(p40)
也实际上也是斯蒂格勒对艺术的观点,他认为作为艺术的创作者,「艺术所劳作的对象已不是物质,而是个体化过程」,并且「艺术会想尽办法利用下面这个点:个体化是一种趋势、一种流动、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形式变化、转换和流动」
所以我理解的个体化实际上是一种两者之间相互改造且发生作用和变化的过程,其关涉到一种相互潜能的实现,并且形成了一种独一无二的两者间的关系(singularity)。
这确实听起来很困难,我们可以自问,我们是否在用某些事物/技术独一无二地展现自己?当我们面对某一件艺术品,我们是否能够形成对于这些艺术品独一无二的,属于自己的领会,在过程中与作品之间形成独特的关系?
个体化被设想为一个过程(l'individuation est conçue comme un processus),那总是既是心理的又是集体的,而且“我”和“我们”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两者的间距也构成了这一过程的动力。 Or, Simondon pose en principe que dire l'individuation, c'est-à-dire la connaître en tant que je s'adressant à un nous, c'est l'individuer, autrement dit la poursuivre, et, en cela, l'altérer, la faire-devenir, la trans-former. 西蒙栋在原则上假定说个体化,就是说对身为对一个“我们”讲话着的“我”而认识着它,就是在个体化着它,换句话说就是延续着它,而且由此,就是在变更着(alter)它,使它生成,转-形着(trans-form)它。据此说(哲学地)个体化,我个体化着它,也就是说我奇异化着它,而且我必然在其中奇异化着自己(en disant (philosophiquement) l'individuation, je l'individue, c'est-à-dire que je la singularise – et que je m'y singularise nécessairement.)。 在说着它的时候,我就做出了个体化:这实际上是在奥斯汀的意思上的某种操演性,而就像我成了我所描述的对象的一部分——我介入其中(j'y suis engagé)。
集体个体化,技术个体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
个体化并不是总发生在个人与技术个体之间的,也发生在个人与其他人之间,发生在社会集体与技术之间,就像是语言文字和印刷文化成为了一种整个社会和集体记忆、心理的改变一样,我们也会出现集体的个体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这有点像荣格的「集体潜意识」的形成。
为了阐明这一点,我必须引入吉尔伯特·西蒙栋《形式与信息概念中的个体化》(L'individuation à la lumière des notions de forme et d'information)一书的一些概念。他说,心理上的个体化总会促成一种集体的个体化(collective individuation),而这种心理——社会的个体化就会产生超个体之物(the transindividual),即共享的意义(shared meanings)……在超个体化过程中,基于连续时代的第三持存,共享的意义(shared meanings)是通过心理的个人形成的。由此,这些心理的个人构成集体的个人,即我们所说的「社会」。这些意义在超个体化过程中形成,并被在各种集体个人中的心理的个人所共享。(p81- 85)
当然,以技术为思考核心的斯蒂格勒会认为这一切都是和技术/第三持存息息相关:
一切技术支撑、客体和实践都是技术个体化过程(process of technical individuation)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心理个体化和集体个体化也总是一种技术个体化。(p82)
「个体化的丧失」与加速熵赠的世界
斯蒂格勒认为问题是出现在这些个体化过程中,无论是在人与技术,还是人与商品,其中不再有「个体化」的那种独一无二的关系和欲望,个体化丧失了,欲望变成了一种重复的膝跳反应。这也导致了一种他早期同名著作所说的:「象征的贫困」
所谓象征的贫困,是指个体化的丧失,这种丧失源自象征物生产中参与的丧失。这些象征物既包括知识活动的产物(概念、思想、定理、知识),也包括感性生活的产物(艺术、技能、风俗)。我认为,个体化普遍丧失的现状,只能导致一种象征的崩塌,也就是说欲望的崩塌一换言之,将导致真正的社会的解体:全面的战争。(《象征的贫困》p17)
人们失去了欲望(desire)而只剩下了驱力(drives),我们不再去爱去想,去记忆,而是根据大数据和构成的反应式(reactive)的方式去接受:
多么不幸的结果啊:失去种种欲望,却获得了内驱力! 因为内驱力是一种坏的重复,因为你总想要更多同样的东西;而欲望则是一种好的重复,因为欲望的对象的他性会发生变化(change in alterity)。(Galloway)
这会导致社会中「熵」和混乱度持续增长,斯蒂格勒提出过去工具的创造,人的存在,思考的能力行为等等都是负熵的,即减少宇宙中的混乱,而在他看来,今天的数字化很多带来的是把整个人类带入一个所谓的「人类纪(Anthropocene)时代——生物圈中熵率的巨大而迅速的增长」,而最终的绝望境地就在于我们正朝着那个未来快速前进:「作为一个巨大的、系统的和极其快速的熵增的过程,人类纪必然会导致所有生命的毁灭,而人类生命则首当其冲。」
所以咋办?
所以咋办?
斯蒂格勒希望能够以某种方式做这样的转换,他期待有一种新的理解与新的智慧,能够颠倒药的毒性逻辑(the toxic logic of the pharmakon)从而产生一个新的超级工业时代,一个负熵化地,基于「去无产阶级」之上的一个自动社会。
我认为斯蒂格勒所基于他关于个体化和第三持存的开出的药方都是围绕着这些不同个体之间的循环的打通,让跨越性的个体化更加畅通的过程,「个体化」的术语更多是对于某一个体的视角所谈的,而在更强调不同个体之间的个体化过程,则被称作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
跨个体化(transindividuation)
这个概念来自于西蒙栋的跨个体关系:
西蒙栋提出了跨个体关系(transindividual relation),强调个体须不断嫁接到他人、集体上,不断与其技术场景缔合,才能在心理、社会中成长。比如我跟书有跨个体关系,书一分享,就成了更多跨个体关系的集合。斯蒂格勒则发展出跨个体化概念。 ——许煜《西蒙栋的技术思想》
斯蒂格勒也将其作为作为一种面对技术毒性的一种策略:
如何包扎技术之毒性的伤害? 通过跨个体化:心理个体—集体个体—技术个体,三者构成亚稳态(Metastability)的互相转导关系。然而,技术个体的生长演化总是快于、引领于另两者,技术个体总是将自身与另两者「脱功能化」,只有在心理/集体个体反过头来重新跟上技术个体并再次构成三者跨个体化的转导关系时,「再功能化」,即技术之药性才会生效。尤其数字技术的高速率剧毒,几乎完全短路了这一互相转导的过程,技术完全接管了另两者。其毒性从互相掂量着别被对方绊摔跤,变成了被卡车绑住拖着走。 人必须从「被图像所吸收」,而反过来通过手指与按键(Flusser)来重新主动连接它。在图像或技术个体上创造这一按键(即媒介)的过程,就是解毒,也是接纳、判断、思考、欲望的过程。跨个体化,就是人重新主动地面对技术个体(或它所投映在我们意识中的图像),由此得以重新地主动将自己的心理个体化。每个人的心理个体化,放到公共性中,也就构成了集体个体化,首先构成了心理—集体这两者跨个体化的互相传导关系,由此对技术之毒性进行包扎。(《技术替补与广义器官》p314)
在这个跨个体化背景中我们能更好地理解斯蒂格勒所给出的几条道路:
1 数字化研究 Digital Studies
1 数字化研究 Digital Studies
斯蒂格勒认为我们需要一种对今天的数字化第三持存的深入思考,这便是人应主动地朝向今天的数字化(Digital),去了解和研究这些数字化的核心与优势,「对这种数字化药物的卓越新颖之处(remarkable novelty of the digital pharmakon)进行思考和细致分析(p109)」。
今天的心理个体化和集体个体化的短路是基于实时地、大规模地自动化、通过自动化地超个体过程而发生地,这就要求对这种数字化药物地卓越新颖之处进行思考和细致分析。这种分析就是我所说的研究与创新研究所的数字化研究(digital studies)数字化研究不是简单的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ties),而是一种面向所有知识的新范式,它将建构一种米歇尔·福柯①意义上的新认识型(new episteme),要求一种加斯通·巴什拉②意义上的新认识论(new epistemologies),从而属于我将在下节课上说的一般器官学(general organol- ogy)(p110)。
这和西蒙栋面向机器,或对技术物研究的要求是一致的,即认为今天的文化需要「理解」和认知技术和机器和数码数字化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
如果文化想要扮演它完整的角色,它必须以知识以及价值的形式来将技术物包含在它内里… 我们可以自问,有甚么人可以了解技术现实,并将其引介到文化里?……能有这种了解的可能是工程师,他就好像是机器的社会学家以及心理学家一样,生活在由他负责以及发明的这些技术存在之间。—— 西蒙栋《論技術物的存在模式》(许煜译)
但仅仅是对其中进行认知和研究还不足。
2 跨学科研究 - 作为药理学的普遍器官学
2 跨学科研究 - 作为药理学的普遍器官学
跨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work)
如果说数字研究是强调一种心理个体 → 技术个体之间的学习与追赶的跨个体化过程,那么接下去便是强调 心理个体 → 集体个体 的分享与联结。
在《南京课程》开篇,斯蒂格勒便明确提出了对听众的要求和建议,
我决定改变一下开场讲座(opening sessions)的顺序,即首先概述讲座语境的主要特点,并提出我们要讨论的话题 —— 其目的是向我的听众提出一个特别的建议:从事跨学科研究(transdisciplinary work),这是由作为人类纪、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的技术突变(technological mutation)所提出的要求。
「普遍器官学」(une organologie générale)
紧接着,斯蒂格勒提出了他所说的「普遍器官学」(une organologie générale)作为一种核心的药理学(治疗学),即一种他认为能思考并将目前充满毒性的技术逆转为治疗的角度。
十年来我始终认为,控制论(cybernetics)必须被理解为语法化(grammatization)过程的最新阶段。这只能从我所说的「普遍器官学」的角度进行思考。我认为,在这些问题上,这是比西蒙栋在《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这本书中提出的「机械学(mechanology)」更合适的路径。(p138)
这被称作「普遍器官学」的思考角度本身是跨学科的,是呼唤一种可沟通,可通约的术语,并非常清晰地根据心理 - 技术 - 社会被划分为三个层次:
它本身被理解为这样一种理论平台, 即用来具体说明在每一知识场(field of knowledge)的不同学科之间的可通约(agreement)的术语(terms)。这个平台从三个平行的、但不可分离的层面界定了分析、思考和为人类事实开处方(prescribe)的规则: 心理的(psychosomatic)层面,即有机器官的体内(endosomatic)层面; 人造的(artifactual)层面,即器官学意义上的器官的体外(exosomatic)层面; 社会的(social)层面,即机构组织或团体的组织性的(organisational)层面。
斯蒂格勒将其与控制论(Cybernetics)及生态学(Ecology)对接,而这两个传统恰恰也都是他所要求的跨学科的。
控制论发轫时维纳也早在1940年便在和神经生理学家阿图罗·罗森布鲁斯在讨论跨学科研究的价值了,并且建议军方「组建由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家组成的小型、机动的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将研究成果移交给一个开发团队,再一起攻克下一个难题。」(《维纳传》)
而宣告控制论的影响和形成的梅西会议,恰恰是充分跨学科的尝试,你能发现语言学家赵元任,人类学家 Bateson 等人的身影:
早在1946年的第一次会议上,就已经确定了形成一种普遍理论所需组成部分:当前世代的计算机原则;神经生理学的最新发展;最后是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模糊「人文主义」混合体 ——Claus Pias 《控制论时代》
而斯蒂格勒也指出西蒙栋,海德格尔都抓到了控制论地重要性,这是一种文化和技术之间协调的希望
这种控制论地技术-逻辑视角,即对海德格尔来说地「现代技术」地科学控制论,构成了一种新的概念框架 …… 承载在文化和技术之间建立一种协调的希望。
关于「普遍」(本节可跳过)
这里所说的「普遍器官学」(une organologie générale)在《南京课程》中被翻译为「一般器官学」,在《象征的贫困》中被翻译为「普通器官学」,也有人翻译为「广义器官学」,但我觉得或许普遍更符合斯蒂格勒的原意,在《南京课程》第六讲中斯蒂格勒特别谈到了这个「générale」的意涵,在普遍器官学后有一种形而上学和本体论式的思索,《南京课程》中他简要地提及:
「这种普遍性必然会将我们带回一种普遍形而上学(metaphysica generalis)」,并且认为「这种问题必须分别结合怀特海的宇宙哲学《过程与实在》作为主题的过程和作为西蒙栋《技术客体的存在方式》主要概念的具体化过程(the process of concretization)来加以理解——通过提出过程视角下普遍性的问题,以及从抽象到具体,或从抽象到合生(concrescene)的过程,此后抽象和具体才能从一个根本性和原真性的过程视角来加以思考」(p159,翻译有修改)
此处的核心就在于,斯蒂格勒认为要建立起一种普遍的器官学作为药理学,其基础就在于我们也需要一种普遍的形而上学,这种形而上学能够将世界和存在看作是过程(process)。这或许需要简单提及怀特海的「单一实体的宇宙论」的哲学,借用哈曼对怀特海的解释:「对怀特海来说,最原初的现实就是实际实有(花译为实际存在物,actual entities),这一类型覆盖所有类型的物。但这些并不是实体,而所有东西都是瞬间的,明确的力」(哈曼《迈向思辨实在论》p51),怀特海自己的说法是:「实际世界是一个过程,该过程就是诸实际实有生成的过程。因此实际实有便是创造物;它们也被称之为「实际事态」(或实际发生 actual occasion)」,每个实际实有实际上都是在过程,都是生成,并且「每个实际实有都是在被其他存在物客观化其潜在性……这个过程被称作「合生」(concrescence)」。
而这实际上也与西蒙栋 - 德勒兹的这一延续性很类似:
「理念」概念。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中提及潜在(virtuel)的现实化(actualisation)进程就是将潜在的理念现实化,以获得具体的差异的进程。可以看到这一现实化进程石十分接近西蒙栋的个体生成的现实化进程,德勒兹本人也在书中直接引用西蒙栋:个体生成「作为潜能的现实化和将诸歧异置于交流状态而出现」…… 无论西蒙栋还是德勒兹都一直认为个体生成可以覆盖所有存在的领域:物理、生物、社会、心理,等等。 ——宋德超《吉尔伯特·西蒙栋思想中的动物问题》
在这个意义上的我会觉得 general 的意思就是一种普遍性,可跨学科的宇宙论式的基本观点,这背后是斯蒂格勒接续着西蒙栋和怀特海的这种单一的过程性本体论,即将将无论是在心理、技术、社会层面的器官的变化都可以看作为个体化的过程,那么也都应该被置入「普遍器官学」的考虑范畴中。
关于器官
器官的说法实际上是一种对于工具,技术个体,第三持存放置在一个「机械有机化」的控制论式的认识论下的称呼,例如贝特森所描述的手,斧头,木头之间的循环的视角(参考拙译 Gregory Bateson《「自我」的控制论:酗酒的理论 (1971)》),以及类似于一种「媒介作为人的延伸」的理解。举例来说,拐杖作为工具对于盲人就是其手,而望远镜则是人的眼的器官,而谷歌也并再是一个技术对象的,而是作为一个存储的外脑。
假如器官是自然的工具,那么工具就是人工器官。工人的工具延长了手臂,因而人类的器官设备就是身体的延长。 ——《道德与宗教的两个起源》
3 普遍器官学 → 普遍经济学 → 普遍生态学
3 普遍器官学 → 普遍经济学 → 普遍生态学
斯蒂格勒谈论到了基于普遍器官学的普遍经济学,以及基于普遍经济学的普遍生态学。
积极的外部性和能力的增值,基于贡献的传粉经济(on a contributive economy of pollination)。……这种普遍经济学是一种礼物经济学(economy of gift),一种赠礼性的经济学(economy of potlatch)
这同样涉及到一种力比多经济学,一种关照(care)的行为,而同时也与「本能的去自动化」(dis-automatization of instinct)有关。但这两部分我并不是特别熟悉,还有待后续与相关的研究者交流,希望能继续进而一窥诸如在斯蒂格勒提及的巴塔耶和莫斯的「礼物经济」,耗费的反功利性与生产性之间去探索游戏的传统人类学的意义,这部分其实也与无论是文化人类学中的游戏的传统的研究都息息相关。
|| 电子游戏的药理学纲要
|| 电子游戏的药理学纲要
没必要害怕或希望,只需去寻找新式武器,——吉尔·德勒兹
德勒兹在《控制社会》中这样安慰,斯蒂格勒也将其放置在自己的《象征的贫困》一书的开篇,那所以这个武器到底是什么?我们怎么找到和使用它?
因特网是一种药,这种药将会成为一种实现超级控制(hyper-control)和社会瓦解(social dis-integration)的技术 (technique)。除非有一种新的个体化政治学(politics of individuation),即除非通过有可能产生新的技术环境的特殊第三持存而形成的(新的)注意力,否则,因特网将不可避免地成为一种导致分解(dissociation)的诱因。(p123)
我认为电子游戏隐藏着一种形成新注意力的第三持存的机会,但这并不是说当下的电子游戏就是已经成为了这样的可能/武器,恰恰此刻的电脑游戏是极端自动化,反应化以及踪迹化的,实际上针对于数字网络大部分的批判都可以直接迁移到大部分的游戏中来。而电子游戏的文化领域,用斯蒂格勒的术语来说,在其中跨个体化流动不畅、阻滞,与文化,社会的交流极少,技术进展远远领先于研究与集体意识,是一团漂浮在文化暗层下,社会之中的巨大暗物质(《电子游戏的文化困境 | 落日间》)
但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的研究,创作和体会中,我也逐渐意识到在如同黑洞般的游戏文化领域中中蕴藏着巨大的能量,就如同越猛的毒性中也蕴含着越强大的药性。而其实推动我去写作这篇文章的核心动力就是我对大部分的哲学家集中讨论实验电影而不看向今天如日中天的电子游戏而感到惋惜,很希望以此抛砖引玉,引起更多人的研究和讨论。
心理学家温尼科特在《游戏与现实》中向我们指出,会让大人中毒的东西,儿童却有办法:将老房子当作一个过渡品,放到内心现实和外在现实之外的第三空间之中,也就是放进一个儿童与妈妈之间形成的「潜在空间」里,去戏玩它,不断重新定义它的性质,那就不会中它的毒了。正是这种儿童般的接纳才重新定义了这种第三存留,由毒害变成了对我们的治疗。
在温尼科特自己看来,玩是很重要的,而所谓的治疗就在于让病人变得能够游玩(Playing):
假如病人无法玩游戏,那么我们就必须想办法,让病人变得可以玩游戏,然后心理治疗才能够展开 …… 因为病人只有在玩游戏时,才能够变得有创造力。(《游戏与现实》)
温尼科特的野心「将游戏作为展开对人类文化体验的讨论」并没有很好的遗留下来,但是他很清晰地强调了成年人一直都在玩游戏,都在一个成长的过程中,就像是孩子借助「某一客体,与自身分离的同时保持一种掌控与游戏的能力,得以和客体的融合状态分离的过程」 ,而这里蕴含在游戏中的创造力「也不是指艺术家的作品,而是扩大指「面对外在现实时,兴味盎然的生存态度」,有创造力感觉比什么都更让人觉得「人生是值得活下去的」。是一种有创造力的方式进入生活,用有创造力地态度面对外在现象的能力」(《游戏与现实》p117)。
我们就面对今天的技术就如同初次面对世界的孩子,我们需要一种游玩,体验它,并且将它们与自身分开并且逐渐掌控的能力,这也是一种创造力,一种关于如何生活的知识(savoir-vivre)。
游戏作为跨学科研究平台
游戏作为跨学科研究平台
电子游戏内生有一种充分跨学科,或艺术式研究所强调的非学科性(undisciplinarity)。
且不谈电子游戏行业在诸如AI研究,写实化渲染等等领域都远超其他领域,且笼络了大量的不同背景的消费者,艺术家,计算机科学人员和教育水平最高的一群人,就让我们就谈谈谈谈研究与学术。
一方面,创始人们希望能重视电子游戏的媒体特殊性而希望独立:
「游戏太重要了,不能留给这些领域。就像建筑学包含但不能简化为艺术史一样,游戏研究应该包含媒体研究、美学、社会学等等。但它应该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结构存在,因为它不能被简化为上述任何一个。」 —— 《Espen Aaserth 电脑游戏研究,第一年 Computer Game Studies, Year One》(2001),
而随着逐渐的发展,哲学家 Ian Bogost 则展现出另一种对于跨学科和走出去的需求,
「在这些资源存在之前,事物还在萌芽时是不足的,但也是更加好的,因为它不可能只在游戏的圈子里运行。我们都是从别的地方来的——从绘画,从建筑,从广告,从计算机,从系统理论,从玩具设计,从文学。有时我们把这些联系视为包袱,甚至视为殖民主义,但它们也提供了基础(grounding)。它们帮助游戏在更广泛的背景中扎根。它们将我们与基岩(bedrock)联系起来。」 —— 《游戏研究,第十五年》(2015)
而本身就是物导向本体论的哲学家/游戏设计师 Bogost 更是以平面的本体论,试图为游戏研究引入一种从哈曼和拉图尔的放荡的本体论(slutty ontology),这其实与斯蒂格勒背后的本体论关切有着共同的来源。
而这也正是控制论会议刚开始的样子,每个人从不同的视角汇聚在一起,共同推动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转变,这同样也出现在「系统理论」,「复杂科学」还有其他的学科和新思想的提出过程中。
我更加赞同 Bogost 的努力,或者说我认为要真正达到 Aaserth 所说的游戏的自身合法性的确立,恰恰不是要求封闭,而是开放、接受、转化、创造才可达及。
而这也是下文会提到的 Nicky Case 可探索的解释 Explorable Explanations (2014) 这种方法正做的跨学科方式。在 Explorables 的网站上,你可以看到数百个,涉及哲学、教育、物理、媒体、艺术等等所有不同面向的创造被展示(curated),它围绕着可交互/可探索的文章,而面向各个学科领域开放,在同一页面之间,相互之间发生关联,就如同路标与汇流的节点。
这也正是落日间和我正在进行的实践,无论是正在推进的「界面式研究创作」以及「把游戏作为方法」,以及「日 | 落译介计划」所进行的涉及环绕游戏的跨学科的译介与收录,都是试图在游戏与外部世界中搭建通路和建立关联的努力。
电子游戏作为数字化研究创作
电子游戏作为数字化研究创作
而在我的研究和创作中我逐渐意识到,游戏和电子游戏的思考一定会涉及到一种对数字化(digital)思考。最近的教学实践中,我在尝试引导学生进行跨界创作而思考游戏的一点就在于:要去思考某事物进入了数字世界/比特世界后的存在方式是怎样的?在经怎样地离散与重组再造后能够为其赋予一种新生命?这本质上很类似于斯蒂格勒提倡的数字化研究(Digital Studies),只是我们不仅研究,我们还创作。
其实倘若把电子游戏放在数字化的宽广视角下,无论是 Bret Victor,或 Nicky Case 所探索的一种数字化给我们带来的强大的思想媒介(medium for thought)与教育的可能性,还是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ties)的宣言所倡导的在数字化浪潮之中学术与学术知识生产以及印刷媒介的新样态,甚至就是具体到论文写作自反的游戏形态(playable essay),这都是数字化研究的不同实例。
这需要再强调一遍:对电子游戏的认知与研究创作需要扩展到对其他事物的深入数字化研究的进程中去,因为游戏从来不是关于它自身的,一切游戏都是关于某些其他事物的。动作游戏是关于身体的数字化假肢再造,游戏不同的层次视觉与操控循环,不同的器官和身体掌握,不同的抽象系统,数学,编程的逻辑,视觉,机械流水线,生物等等。就像是 Jonathan Blow 认为「所有的游戏都是有教育意义的」。游戏从来都不是独立存在的 —— 那只是热情的玩家「业余爱好者」群体与创作者/大公司的生产消费循环所营造出来的脱离大地的困境所遮蔽的假象,每当我对某一界面深入,那我一定会找到等待被重新挖掘和建构的谱系。
就如同斯蒂格勒所说,普遍器官学不仅是「数字人文主义」(Digital Humanities)对于学术和大学知识领域的颠覆和反思,而我也认为游戏研究应是普遍器官学中不可被忽略的重要实例,特别的:如果将游戏视作一种个体与当代技术物间跨个体化的过程,或在数字研究的更广泛视角下来说的话,那游戏研究或许就应努力成为当下所需的普遍器官学。
电子游戏研究/设计是数字世界第三持存的制药学与炼金术。
作为器官/乐器的电子游戏
作为器官/乐器的电子游戏
去年的草稿写作中我已做出了这种判断,我谈及了我在制作生成音乐和乐器玩件时的体会,问题是:为什么弹奏乐器(organ)是「玩」(play)?在一个音乐学习者在逐渐掌握乐器的学习过程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简单来回答:玩乐器,就是在将乐器变为自己的发声器官且逐渐掌握熟悉的过程,而这也是动作游戏中发生的事。
这就涉及到电子游戏与艺术的公案:把电子游戏与其他艺术形式以及媒体并列的思路。但我认为这种把电子游戏当作第九艺术的想法是不妥的,一个电子游戏不应被仅仅被看作类似音乐的事而又有某种绝对差异性的新媒介,而更应被看作是一件乐器,一个有待被内化的器官。
电子游戏应与乐器作比较,在这个视角下,书法是操控笔的游戏,做书法-游戏本质上是再造一支笔,马里奥是操控马里奥的替身的游戏,做新的一个跳台游戏本质上是再造一具身体,而诗歌是词语的游戏,诗歌-游戏是再造一个写诗的方法与过程(《写首诗吧》)。
伽达默尔在《真理与方法》中早就指出,游戏不是艺术,游戏是艺术的形式。而完全可以大胆地进一步说,电子游戏也不是艺术,而应是艺术在数字世界/时代的运作方式。
1 不同于理论知识的跨个体化
斯蒂格勒所强调的经验与知识的丧失在审美上有一些不同的工作需要处理,这涉及到当前当代艺术中人们不是一种对于流俗「知识」的缺乏,他批判的正是「有教养的庸俗者」,即,现在人们在艺术作品之前缺少的并不是这个艺术家是谁,他/她在处理什么样的命题,而这又如何如何,人们发生的是「感性知识的无产阶级化」,人们不再能够在作品面前震撼,感动,流泪。
他通过重回康德描述了一种他所推崇的审美判断:「判断必须被理解成一个跨个体化的循环……判断的人被他所判断的东西改造(transformation)」,他认为「只有业余爱好者的审美判断才是完全实现的……作品是开放的、不确定的、未完成的。这种相位差的经验就是个体化 (p69)」所以这就具有某种每个人独异性的秘传性:
兼有综合和分析的审美判断,因而是本质地秘传式的。这意味着,建立在使人目瞪口呆之惊叹基础上的审美经验,是神秘的开启,引向某种审美、某种改造式的神秘之中。恰恰是因为,这一神秘对任何惊讶于此并感到很不可能的人,都是改造式的,而分析是这一开启中的契机,一个第二契机,这是起效的反思的契机,是反思性判断中的反思的时间,但它被重新导入到神秘之中,成了对已然在延异中变化了的惊讶的重复,而这延异,就是跨个体化的线路。(p76)
这在电子游戏的审美中是非常明显,甚至这种开放和相位差的个体化经验是完全可见的。
电子游戏的游玩过程中不仅是一个将游戏器官化的过程,也是将自身与游戏内的替身(avatar)联通,共同构成一个控制论系统的过程;电子游戏或许是最符合也最有在数字化世界中个体化的可能,即每个玩家在实时运算(Real-time)的支持下不断实现(actualize)可能性空间,穿行和具体化一连串的独一的个体化路线。电子游戏有可能不再只是成为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而是复制但却实时计算涌现和独一展开的艺术。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戏设计的讨论是必要的,何种游戏重复大过差异,仅仅只是反应式的驱力(drives)或巴普洛夫的实验?何种游戏仅仅是一种自动化的游戏控制?电子游戏本身就是关于器官的短路方式大全。
2 生产与消费的分离 | 结合
斯蒂格勒在谈论审美的「个体化的丧失」的时候谈论了很多关于「业余爱好者」的问题,并且追溯了音乐爱好者逐渐分化所导致的20世纪欣赏者与生产者的分离。
这是因为过去阅读和写作的是同一批人,而诸如画作和音乐的欣赏者都是在模仿和弹奏的过程中欣赏作品的,他们通过身体性的方式而不是知识性的方式感受作品,并且在其中实践自身,这也就像是作家埃科所说「成为一个好读者的先决条件必须是一个好作者」(《悠游小说林》)。
这也是一个重复的实践时刻,如果不是复制,至少也是一种阅读和破译。一位伟大的20世纪文人,罗兰·巴特,在其著作中,将此称为「开耳」。也就是,懂音乐的耳朵是被训练出来的。在一只耳朵被开放并受训练的过程当中,作品呈现为作品就如手眼相配合的训练。通过阅读乐谱和用乐器来启蒙耳朵,这种方法本质上是身体性的,也就是说,与运动神经相关,必须被理解为是一种通过眼读来进行的演奏。 ——《人类纪里的艺术》p90
这也是我在围绕创作《写首诗吧》的跨界讨论之中揭示出迷思,即在玩家游玩这个游戏时,我们无法明确地分清自己是创造者还是读者(E32 赛博文本中的幽灵作者),而或许要做的并不是分清,而是这正是一种能够将其融贯为一体的方式,而这种对文本和对诗歌的「游玩」本身有更重要的意涵,就像是斯蒂格勒提及的罗兰·巴特在《从作品到文本》中所强调游玩、探索(jouer avec / play with),来作为与消费(consommer)相对应的关系:
事实上,消费意义上的阅读并不游玩文本(En fait lire, au sens de consommer, c’est ne pas jouer avec le texte.)。这里的「玩」(playing)必须在其所有涵盖的意义上理解。文本本身在游戏(作为一扇门,作为一个有「游戏」的装置);而读者则是两次地游戏,他游玩文本(在一种游玩的 ludique 意义上),他寻求一种重新生产文本的实践;但为了使这种实践不被还原为一种被动的、内部的模仿(文本正是抵制这种还原的东西),他游玩文本;我们不要忘记,「玩」也是一个音乐术语。此外,音乐(作为一种实践,而不是一种「艺术」)的历史与文本的历史相当平行;曾经有一段时间,活跃的业余爱好者很多(至少在某个阶层),「演奏」和 「聆听」构成了一种几乎没有区别的活动;然后相继出现了两种角色:首先是表演者,对他来说,中产阶级公众(尽管他们自己还在带着一些恐惧在玩......这就是钢琴的全部历史)委托他演奏;然后是(被动的)业余爱好者,他们听音乐却不知如何演奏(钢琴实际上被唱片所取代);我们知道,今天的后期音乐已经把「表演者」的角色颠倒了,他被要求成为他所完成的乐谱的共同作者,而不是「表达」它。 —— 罗兰·巴特《从作品到文本》
毫无疑问,在电子游戏中玩家是通过玩而欣赏游戏,游戏便是一种做/玩和欣赏,个体化与审美的过程的结合,这恰恰并不是说电子游戏本身多么牛,而或许这引发我们的反思在于,「电子游戏式的」(playfully)应被作为一个副词使用,当作对当前艺术作品审美运作方式的要求。例如我要求电子游戏式的看电影,电子游戏式地阅读小说等等。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应同玩家一样「抵制」云游戏,因为云游戏便是如今在游戏的意义上所发生的,曾发生在阅读与音乐中的欣赏与创作的分离。或许我们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反对所有的「云演奏/云游玩」,去鼓励阅读的人亲手去写,鼓励听音乐的人去把玩合成器,鼓励谈哲学的人亲自去行动言说,也鼓励玩游戏的人自己去做。
教育、去无产阶级的电子游戏
教育、去无产阶级的电子游戏
19 世纪的技能知识(savoir-faire)的丧失;20世纪的生活知识(savoir-vivre)的丧失,以及21世纪,我们见证的了这个理论知识(savoirs theorique)丧失的时代的诞生。
早在1980年代出版的《Mindstorm》的书中就谈论了对儿童使用计算机作为学习工具的设想。而后无论是 Alan Kay 还是 Ted Nelson 等人实际上都在思索这件事,他们这组人延续到今天更多的实践在计算机科学家 Bret Victor 的探索中可见一番,这个被称作 Explorables Explanation 的传统在持续探索试图充分利用数字媒介来探索一种新的领会和学习的过程。
Bret Victor 如此阐述自己的实践努力:
可探索的解释(Explorable Explanations)是我的大型项目(umbrella project),用于实现并鼓励真正地主动阅读的想法。其目标是改变人们与文本(text)的关系。现在人们将文本看作有待消费的信息(information to be consumed)。而我希望文本被当作一个在其中思考的环境(environment to think in)。
这其实很类似与斯蒂格勒所设计的软件的目的尝试:
创新研究所(IRI)通过研发「时间线」(Ligne de temps)软件想要构造的时空 ……「时间线」是电影流的数码式语法化的装置,能把连续的电影流——在我们对它的初次领会中,这个流促成了一种对它的超乎领会,正因此,它构成了电影——离散化,从而让人分析性地触及那构成电影的诸多离散单元,让人批注、排布它们,并在此基础上生产出我们在创新研究所所说的「做标记的观看」。 所以,「时间线」能让人通过分析性判断来支撑(substantiate)综合判断,后者首先是通过对全片的时间性的领会来构成的,然后随着电影的播放,这种领会沉淀为、结晶成了超乎领会。(《人类纪里的艺术》p100)
实际上 Bret Victor 的思想打开了一系列的实践,例如 Nicky Case 等人制作了让人理解博弈论,谢林隔离的 Explorables,而也有大量来自于其他不同学科的关于各种基础学科,软件和技术(诸如傅里叶变换,量子计算,合成器)的互动式,或我们上文所谈及的将电子游戏作为副词的「电子游戏式」的创造。
互动式的领会和可探索的游玩媒介实际上涉及的是一种领会的教育的直观性,作为一种类似于地图,类似于数学符号和语言的一种外在化的技术的新药学。Jonathan Blow 的演讲《电子游戏和教育的未来》正是可以被看作一次斯蒂格勒式的对第三持存的媒介思索,他回顾了语言,数学符号,音乐,视频语言的媒介特殊性,并且他和语言学家 James Paul Gee 都所正确指出的「电子游戏的本质上是学习」以及「所有的游戏都是有教育意义的」。
电子游戏中的这种从不同角度和背景下不断重温,通常就是人们从生活经验中获得的学习。
而我们如同孩童一般在电子游戏的世界中摸索而逐渐学习的过程,这恰恰正是斯蒂格勒试图寻找的丢失了的知识与领域,无论是 savoir-faire(知道做),savoir-vivre(知道生活),以及知道决定知道思考(savoirs theorique)。而制作游戏和游玩游戏都是一种理解(至少一部分)世界的过程。
反自动化 | 非生产性的电子游戏
反自动化 | 非生产性的电子游戏
斯蒂格勒在书中写道:
借助这个概念我们可以研究技术的矛盾(paradox of technology),这就是伊万·伊里奇(Ivaan Il-lich)所说的逆生产力(counterproductivity)。当技术作为体系发展到某一点,它的效果就会发生颠倒,同样地,它就变得具有矛盾性,帕赛特(Passet)将其描述为「趋向极限的过渡(passage to limits)」。我们必须将逆生产力这个概念与一般的药联系起来,一般器官学状况的各种逆生产性效果应该被看作熵的和负熵的药理学效果。
我们应把伯尔纳·舒茨《蚱蜢,生命与乌托邦》(The Grasshopper:Games, Life, and Utopia)的预言作为自动化时代的预言,书中举了很多论证游戏就是克服「非必要的障碍」(unnecessary obstacles)的例子,例如人们就是可以把高尔夫球直接放入球洞,但是却千方百计想办法一定要用不同类的杆子将其打进(并且再拿出),并且发展出了如此巨大的高尔夫球的产业和群体(集体个体化),而基于此判断,舒茨最终想象了这样的一个乌托邦:
想象一个衣食无忧、心灵满足的乌托邦世界,活在其中的人类早已心想事成,无事可做,剩下唯一能做的事,就只有玩游戏,玩游戏将变成人类存在理想的全部。
电子游戏成为一个如此巨大的行业,建立在充满着效率和科技的背后却蕴藏着一种耗费与非生产性的趋向,巨大的资源,技术,消费都被用于画面,情感,不直接以效率和控制为导向的游戏生产,甚至这种趋向反过来成了技术的推动力(例如显卡的需求等等)。
这同样应该从人类学的视角去做考虑,诸如巴塔耶的耗费,礼物经济与游戏;例如格尔茨考察的巴厘岛的「斗鸡游戏」中,那些真的计较得失的游戏者是被当地土著所鄙视的。而非生产性也正是人类学家 Roger Caillois 对游戏的定义之一所说的「非生产性,并不创造财富」(It is unproductive in that it creates no wealth)。
姑且举个例子,前段时间我在游玩 Zachtronics 的游戏《SHENZHEN I/O》。
在这个游戏中,玩家会扮演数十年前的华强北打工者,进行类似单片机的编程,让你的小电路板实现一些十分简单的运算,我需要一边查阅配套的一本41页的 PDF 说明文件手册,一边游玩。我玩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正做着一件什么样的事?我的电脑主机正在运转,里头塞着数百万计的集成电路和计算单元(rtx2060 + Intel i7 处理器),而这样的一台机器居然在运行还远不如它自身的百万分之一的一个简化了的单片机编程的游戏(并且还把我难住了)?我着实为了我电脑中的百万的集成电路而感到不值得,但反过来看,这打开的正是一种逆向的「逆生产力」,以及逐渐地某种「去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些百万集成电路的芯片的运转是「为了」让我理解和认识它们。
控制与反控制的电子游戏
控制与反控制的电子游戏
就像是斯蒂格勒对第三持存的思索中揭示的,我们今天无法不借助任何技术和外化的事物进行思索「A = R3(R/P) → 理性,思考是一种注意形式(form of attention),是一种在持存 R 与前摄(P)期望之间借助技术持存,即R3的运行的安排。」思考一定是在第三持存的函数之内去运行前设与记忆,这某种意义上意味着,我们无法摆脱第三持存谈所谓「自由」。
电子游戏是控制的艺术,游戏设计就是身体、视角、知觉的约束,就如同摄影。
所以自由-控制的对子我觉得并非电子游戏应该重点讨论的问题,我们应该去问的是:电子游戏作为「器官」,作为「座架」的技术个体化过程,以及作为业余爱好者亦或是「庸俗的中产阶级」的欣赏者的个体化过程,两者共同形成和运作的跨个体化控制论系统,是将玩家带向麻木、冷漠、浮浅、无聊;亦或者是惊奇,感动,领会和爱?
电子游戏意义上的「解放和反抗」也不应仅局限在狭义的对单一游戏的元游戏(meta-gaming)和反玩(counterplay)上,因为这不过是将作为人工制品的游戏看作全部和自由的边界,而应把游戏作为在控制社会中的负熵装置去思考更大层面的自由,思考怎样的游戏能够让我们在今天重新获得实践与生活的知识(savoir-faire et savoir-vivre),怎样重新获得思考的能力。
电子游戏和独立游戏一直是充满着先锋与反思创造的,今天的独立游戏和 Game Jam 文化社区实际上沿袭了后控制论时代的某种嬉皮士传统和最Geek的那批人。
《全球概览》的主编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在六十年代访问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时看到了数百名本应为控制与计算服务的计算机技术人员正着迷于聚会和游玩比赛游戏《Spacewar!》,布兰德认为,这完全不同于机器是一种对人的控制,和一切朝向效率的机器,电子游戏是控制时代的反制装置:
这款游戏代表了与已建立的权力原则的决裂。它表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它不是要自上而下地控制, 不是要批量处理,不是要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向制造商发送数据, 不是要被动消费, 不是要最有效地利用机器。这款游戏是所有这一切的对立面。
END
END
我很喜欢独立游戏《节奏医生》(Rhythm Doctor),我认为这是一个对于药理学的一次绝佳隐喻,我在其中扮演一个啥也不懂的入门医生,学习使用远程连线的节奏疗法,用我的节拍去校准和调整那些生活得不那么好的病人,但我分明感觉到,这穿越屏幕而共同律动联结的节奏线中,我在治疗他们的时候也在被他们所改变,被治疗的其实是我,而不是它们。
或许我们应当继续在这莫大地绝望中努力,或许还来得及,就如同舒茨所说的「游戏是未来的线索;趁现在认真培育游戏,或许是我们唯一的救赎」。
而或许可以拿斯老师《人类纪的艺术》结尾处谈及有限与无限游戏的期望作结:
这里,游戏(亦即界面)的设计者,必须致力于一种「即将到来」,一种未来,这也是欲望最宝贵的成果:一种无限的「即将到来」。这样,设计者就不是为消费社会服务,因为为消费社会服务只以有限的游戏为准。——《人类纪里的艺术》p175 谢谢你们的聆听,谢谢你们的默契。
叶梓涛
2022.8.6 于 落日间 xpaidia.com
——
本文的写作我需要单方面擅自感谢许煜老师,陆兴华老师在书中和文章中的启发,也希望此文能够解释先前我主动找到你们的一些动机和原因,此外非常感谢斯蒂格勒协会小组的主理人郑重兄的帮助,以及他所整理翻译的工作。我并非专业研究人士,还请各位多多指正交流。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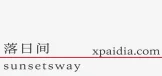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