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The Frog
The Frog
by Henry Kuttner
前言
罗伯特·M·普莱斯:
在这个故事最终问世前,库特纳一直在斟词酌句。早在整整三年前,洛夫克拉夫特曾致信于他——
你提到的《青蛙》让我非常感兴趣,因为它看起来像是我最喜欢的故事之一。如果《诡丽幻谭》编辑法恩斯沃斯·赖特拒绝了它,我相信你会让我看看的。因为我不想错过这种项目,这似乎是!梦境般追逐的气氛对这种性质的任何事情都是理想的。(1936年5月18日)
正如爱手艺预料的那样,赖特肯定把它给筛掉了,三年之后,它才出现在《诡丽幻谭》竞争对手的第零页里。也许赖特觉得它有点像《塞勒姆恐怖》。如果是这样,他是对的。
值得注意的是,库特纳在这里引入了他自己的怪异的地点——蒙克山谷(Monk's Hollow),这个名字唤起了人们对那些叛变的恶魔修道士的孤立的夜间仪式的联想,就像我们联想到洛夫克拉夫特的伊克姆修道院(Exham Priory)和布洛克的《The Feast in the Abbey》中的兄弟会一样。
首次发表:《怪奇故事(Strange Stories)》,1939年2月
正文
正文
诺曼·哈特利(Norman Hartley)对聚集在蒙克山谷(Monk’s Hollow)的黑暗传说知之甚少,且不在乎。它隐在东部群山的幽谷里,这座古老小镇世代沉眠。一种离奇且令人不快的恐怖民间传说从老人们窃窃私语中涌现,那是有关腐烂之北沼泽(the North Swamp)中的那些女巫行可憎巫术时日的传说。那个地区至今仍被村民避开。
他们说,很久以前,这片死气沉沉的泥沼里住着许多怪东西,印第安人把它命名为“禁地”是有充分理由的。女巫们早已不再,其可怕的魔典已被焚毁,古怪的法器也遭破坏。
但是,黑暗的传说已在几代人中悄然流传下来了,仍有人记得有一天晚上,人们被痛苦的尖叫声召集,闯进了老贝齐·科德曼(Betsy Codman)的小屋里,发现她仍然在颤抖的身体在一个女巫的摇篮中摆晃着。
然而,诺曼·哈特利在蒙克山谷里看见的只不过是一个安静,孤独的小村庄,在那里他也许能找到在纽约不可能有的隐私。好交际的朋友们不断地冲进他的画室,哈特利没法在画布上作画,只能去夜总会。
他的工作受到了影响。在离村子两英里远的地方,他租了一间古老的复折式屋顶房,他觉得自己可以重新获得使他的画作闻名的灵感。
***
但是女巫石(the Witch Stone)让他不安。
那是一块粗糙的凿刻灰石,大约三英尺高,两平方英尺,它立在房子后面的花园里。每当哈特利透过他的窗子看见石头之时,他艺术价值观的感知就会被激愤。
看门人多布森(Dobson)曾试图培育花朵,使它不被人看见;他在周围种过攀藤植物,但地面显然是贫瘠的。在女巫石附近有一小块光秃秃的褐色土地,那里什么也不长——甚至没有杂草。
多布森说这是因为珀西斯·温斯罗普(Persis Winthorp),但多布森是个迷信的傻瓜。
不管珀西斯·温斯罗普是否真的埋在石头底下,事实证明,这块石头很碍眼。当不经意地瞥见花园的绚丽色彩,总是会不可避免地被那块石头站立的贫瘠小空地所吸引。对哈特利而言,美几乎是一种信仰。每当他的目光落在女巫石上时,他发现自己变得恼怒起来。最终他叫多布森把它搬走。年迈的看门人,他那布满皱纹的棕色面庞因忧虑而皱起,他的木腿在地板上刮着,表示不同意。
“别害我啊,”他用那双湿润的蓝眼睛斜睨哈特利一眼。“此外,它是一种地标。”
“听着!”哈特利不讲理地生气着。“如果我租了这间房子,假若我不喜欢那石头,我就有权把它挪开。而我没有——它就像夕阳下的一大片丑陋的绿色斑点。它使花园不再匀称。人们会以为你不敢碰它。”哈特利那瘦削殷勤的脸涨红了。
哈特利哼了一声,但是看门人还是认真地说下去:“我记得有一次他告诉我,当他们把老珀西斯放进池塘时,她诅咒了蒙克山谷。而且他们淹死不了她——她的父亲也是淹死不了的,有一天晚上,他从北方的沼泽地里出来,想——”
“哦,看在上帝的份上,”哈特利厌恶地说。“这么说,如果石头被挪开,她就会蹦出来,嗯?”
多布森屏住了呼吸。 “你不该说这样的话,哈特利先生。珀西斯·温斯罗普是个女巫——这一点大家都知道。她住在这儿的时候,这间房子里经常发生可怕的事情。”
哈特利转过头去。他们正站在花园里,他走到一旁察看那块石头。
上面有一些奇怪的图案,似乎是由不熟练的手凿刻的。这些粗略的图形与阿拉伯语有些许相似之处,但哈特利看不懂。他听见了多布森在他身边蹲下。
“他(我的祖父)说,当他们把她按在水里的时候,他们必须让女人们离开。她从水里冒出来,浑身绿色,粘滑泥泞,她的大嘴用嘶哑的声音向无人知晓的哪个异教神明念咒——”
听到马达的声音,哈特利迅速抬起头来。一辆卡车在路的转弯处哐啷哐啷地开进视野。他看了一眼女巫石,拿定了主意,急忙向大路跑去。他听见身后的多布森隐晦地提到了珀西斯·温斯罗普的神秘父亲。
卡车装满了碎石。他招了招手,当它慢慢停下来的时候,他跳上了踏板。
“我好奇你能不能为我干个小活儿,”他对卡车上的人说道。“我想把一块很大的石头从我的花园里搬走,但它有点太重了,我拿不动。这只需要一分钟。”他掏出钱包。
司机是个没刮胡子,脖子粗壮的爱尔兰人,带着询问的神情转向他的同伴,彼此交换了一下眼色,然后朝哈特利咧嘴一笑。“当然,老兄。很高兴效劳。”
“很好,”哈特利说,半是自言自语,“我们可以把它扔在灌木丛里,眼不见为净。”
***
后来,哈特利皱着眉头站在窗前,月亮已从山脊后升起,但花园仍在阴影中。不知怎的,他觉得在这幽暗的黑海中有什么东西在动。蟋蟀单调地尖叫着,他感到莫名的紧张。当多布森在厨房里踱步时,楼下反复传来啪嗒啪嗒的声音。
多布森必须对花园里那块贫瘠的地方采取一些措施。现在石头被搬走了,那儿也更明显了。即使在黑暗中,哈特利也觉得他能看到女巫石立过的位置有一个更深的影子。
那是什么样的古老传说?当卡车司机举起石头,多布森歇斯底里地倾诉着,他恳求他们把石头放回远处,恳求哈特利宽容点。它充满了珀西斯·温斯罗普与住在北沼泽的反常生物间神秘来往的可怕暗示,特别是她与生下她的两栖生物的关系——是很久以前印第安人崇拜的一个恶魔,多布森说。
村民们杀不了她,但有咒语可以解除她邪恶的魔法,有充满力量的词句可以把她束缚在坟墓里——就像刻在女巫石上的那些字一样。看门人抗议道, 恐惧把他的脸扭曲成一个棕色的,皱巴巴的面具。
在蒙克山谷里他们说——他的声音下沉至颤抖的低语——在坟墓里,珀西斯变得更像她那不知名的父亲了。现在哈特利在移动女巫石——
哈特利点了一支烟,皱着眉头朝下望着神秘而幽暗的花园。要么是多布森精神不正常,要么是他对花园里的那个地方感兴趣有某种合乎逻辑的原因。或许——
这个想法闪过哈特利的脑海,他突然咯咯地笑了起来。当然!他应该知道的!多布森一定是个吝啬鬼——事实上,哈特利已经遇到过不止一次类似的情况——他一定把财宝埋在女巫石下面了。
还有什么更合乎逻辑的地方可以把它藏起来呢——那个声名狼藉的老巫婆的坟墓,迷信的乡下人都避之唯恐不及。
好吧,这老家伙活该,哈特利不厚道地想着。他试图编造一个据说还活着的女巫的荒诞故事来吓唬他的雇主——
哈特利惊叫一声,弯下腰向窗外望去。花园里有什么东西在动——黑暗中更黑的影子。他看不清它的形状,但它似乎正非常缓慢地朝房子的方向移动。
忽然他意识到下面多布森的动静已经停止了。厨房地板上不再发出那条木腿的砰砰声。意识到这一点,哈特利咧嘴一笑,三心二意地提起窗户,朝看门人大喊大叫。天呐!那家伙认为哈特利想偷他几分钱吗?
哈特利对自己说,多布森已经老了,脾气古怪,但无论如何哈特利内心的恼怒愈加增多。
黑影离房子越来越近了。哈特利紧盯着,但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古怪地蹲着的轮廓。由于某些极愚蠢的原因,他用手和膝盖爬行着。
那影子敏捷地朝房子奔去,藏在窗台边,不让哈特利看见。他耸了耸肩,捻灭了香烟,回到他一直在看的书上。
潜意识里,他一定是在等待一些声音,因为当敲门声传来时,他吓了一跳,书差点掉在地上。有人抠动了前门的门环。
***
他等待着。那声音没有再重复,但过了一会儿,他听见楼下有人偷偷拖着脚走路,还有多布森那条木腿的嗒嗒声。
那本书遗忘在他的膝上。他一阵初步的搔抓声穿进他紧张的耳朵里,接着是破碎玻璃的叮当声。有一种微弱的沙沙声。
哈特利迅速站了起来。是多布森不小心把自己锁在门外了——然后他在敲门之后,打碎了一个窗户然后爬回房子里吗?不知怎的,哈特利无法想象患着风湿病的,还残废的多布森努力从窗户里爬进来的情景。而且,他刚刚还听见多布森在房子里面的脚步声。
花园里的黑影真是多布森吗?会不会是某个小偷想进去?当他付款时,那两个卡车司机贪婪地盯着他那鼓鼓的钱包——
然后,从下面突然传来一声恐怖的尖啸,刺耳地响彻整个房子。哈特利咒骂着,跳向门口。他打开门时,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是多布森的,因为可以明显地听到木腿的敲击声。
但在这声音中夹杂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抓挠声,好像是狗爪在地板上刮擦似的。哈特利听见后门开了,脚步声和刮擦声停下了。
他三步下了楼梯。
当他冲进厨房时尖叫声又开始了,突然被打断了。通往花园的开着的门那儿传来了阵微弱的咯咯声。哈特利犹豫了一下,抓起桌上的一把很重的切肉刀,悄悄地走进夜色。
月亮升得更高了,在苍白的月光下,花园看上去如幽灵一般,神秘怪异,只有门口的灯光沿着一条黄色的狭窄小路上射出。夜晚的空气让他的脸凉凉的。从他的左边,女巫石所在的那片贫瘠的空地上,传来一阵微弱的沙沙声。
哈特利悄悄走到一边,他心中隐隐油生出一种恐惧。多布森的警告如洪水般涌来,看门人不祥地坚称,老女巫从来没有死过,她躺在坟墓里等着有人来搬走束缚着她的石头。
“多布森,”他轻轻叫了一声,然后又叫了一遍。“多布森!”
有什么东西正向他移动,非常安静,非常鬼祟。
月光显出一块粗笨的影子拖着身子前进。它对一个人类而言太庞大了;此外,人呼吸时不会发出刺耳的口哨声,他们的背部也不是油腻的,绿色的,粘糊糊的——
上天啊!这是什么东西——这个从黑夜里向哈特利扑去的古老恐怖的梦魇?埋在女巫石下面的是多么亵渎的生物啊——哈特利不知不觉地释放了什么黑暗力量?
他们说,在坟墓里,她变得更像她那不知名的父亲了。
哈特利踉踉跄跄地朝着房子退去,疯狂的恐惧与他一生中理性的信念进行着斗争。这样的东西不可能存在——但它确实存在!它大步向他扑去,像个畸形的影子,在月光下微微闪烁。可怕的威胁正在迅速逼近。
他已经耽误太久了。当他转身逃跑之时,那东西几乎追上了他。他双腿颤抖着,在那可怕的一瞬间,他以为这两条腿要撑不住他了,他会在这生物的猛攻下无助地倒在地上。他摇晃着走了几步,几乎听到脖子上淌着口水的呼吸声,然后他恢复了体力,沿着房子的墙壁狂奔。
那东西跟在他后面。他绕过建筑的拐角,向公路走去。当他接近公路时,他偶然回头看了一眼,寒冷的恐惧用冰凉的手指划过他的心脏。它还在追他。
蒙克山谷!一想到这,他转身就朝镇上跑去,手里还握着那把切肉刀。他已经忘了它,但现在,他低头看了眼,握紧了武器,并加快了冲刺的速度。他要是能抵达那个村子就好了——
***
就在两英里外——两英里无尽的空旷道路,孤独又偏僻,几乎没有汽车经过。很少有司机选择这条路;它坎坷不平,年久失修;新的州高速公路更直接。
但是高速公路在山脊的另一边,哈特利知道他没机会站在岩石或不平的地面上。即使在公路上,他也得仔细观察地面上的黑影,看看是否有裂缝和车辙。在他身后,有什么东西在朝着他跳跃,接着传来刺耳沉重的呼吸声。
夜里很冷,但哈特利的脸上冒着像大珠子一样的汗水。他的衬衫湿透了。他那宽松的长衣妨碍了他的奔跑,于是他从衣服里滑了出来。他的身后传来一声刺耳低沉的叫声。一阵匆忙的行动过后,又响起了有节奏的砰砰声。
“他们把她按在水里时候,必须让女人们离开——她从水里冒出来,浑身绿色,粘滑泥泞——”
哈特利紧咬牙齿,克制住因恐惧的尖叫。在他身后传来了平稳的撞击声和急促的呼吸声。那东西快赢了!
他要是能抵达那个村子就好了!他加快了脚步,歇尽全力,直到血液在太阳穴里直跳。他的努力徒劳无功。他身后的东西跟上了他的步伐;砰砰的声音越来越响。有一次,他的脖子感觉到怪物呼出的恶臭热气。他的胸膛像一团火苗;一痛苦的刀刃灼烧着他的肺;他喘息着。
他的脚被车辙绊住了,几乎一头栽下去。经过一番挣扎,他恢复了平衡,继续往前跑。
但追赶的声音越来越响——响得可怕。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迅速冲进路边的灌木丛——月光下的黑疙瘩——中,以躲避追赶他的存在。不——那家伙靠得太近了。哈特利张着嘴挣扎着喘口气。
然后他看到了光明。在一片长方形的黑暗中,黄色的方块是窗户——但离得很远,很远。不——在黑暗中他判断错了——五十英尺以外的房子。它突然出现在他面前。
当他跑向门廊时,他的喉咙痛得直打颤,尖叫起来。
但在抵达之先,他就感到背上有一块很重的东西,把他压倒在地;巨大的利爪撕扯着他的衬衫,用尖如针的爪子扒着他的肉。他的眼睛和嘴巴被泥土堵住了,但他意识到自己仍然握着那把切肉刀。
他设法反转它,往他肩膀后面刺了一下。口水和刺耳的呼吸声消失了,只听见一声可怕的嘶哑叫喊,接着刀子从他手里被夺了去。他拼命挣扎着想挣脱,可是极大的重量无情地把他压在地上。
一阵混乱的叫喊传进他的耳中。他听到急促的脚步声和枪响。突然,他背上的重量消失了;当他翻过身,刮着覆盖在脸上的泥土之时,他听见有什么东西砰砰着消失在黑暗中,透过刺痛的眼睛,他看见一个人苍白的脸正盯着他,那人穿着脏兮兮的工作服,颤抖的手握着一支老式步枪。
哈特利发现他在哭泣。
另一个人凝视着阴影,回头瞪大眼睛看着哈特利。
“那——那是什么?”他颤抖着问道。“以上帝之名——那是什么?”
*****
阿纳姆·皮克林(Anam Pickering)的小农场就坐落在蒙克山谷的近郊。他从床上坐起来,在床头柜上摸索着眼镜,满是皱褶的脸上露出困惑的皱纹。是什么叫醒了他?一些不寻常的噪声——它又来了——窗户底下鬼祟的刮擦声。农夫吓了一跳,眼睛掉到了地毯上。
“谁在那儿?”他厉声喊道。没有回答,但是刮擦声又响了起来。还有另一种声音,一种急促的呼吸声。阿纳姆突然害怕起来,叫道:“玛莎!是你吗,玛莎?”
隔壁房间的床吱吱作响。
“阿纳姆?”一个尖细的声音叫道。“怎么了?”
阿纳姆迅速从床上爬起来,跪在床边,摸索着他的眼镜。突然玻璃碎了,使他急促地喘了口气。
他抬起头来,但他模糊的眼睛只能看到一个模糊的长方形——窗户——在它的衬托下,隐约现出了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一股恶臭扑鼻而来,他患风湿病的四肢不停地抽搐着。
他听到一阵脚步声和他妹妹的声音。“阿纳姆?什么——”那声音止住了,接着是一阵停顿,意味深长的可怕。接着,在闯入者的移动和喘息声之上,那女人发出了叫声,尖厉而疯癫,充满了极度的恐惧。
阿纳姆犹豫着,盲目地环顾四周,发出一阵困惑的呻吟。他试探性地迈了一步,然后弹回床上,摔在上面。他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一个巨大黑色,并不成形的东西完全从他身上跳了过去。
玛莎不再尖叫了。她的喉咙深处发出嘶哑的声音,好像她想哭,却喊不出来。“玛莎!”阿纳姆尖叫着。“玛莎!看在上帝的份上——“
一阵快速动作之后,那女人发出一声低沉的,被捂住嘴的喊叫。之后房间里唯一的声音就是粗的,被哽住的呼吸声,不久,当阿纳姆半昏迷地躺在床上之时,另一种声音,在这个人的头脑里唤起了疯狂的念头——一种微弱的狂乱撕扯,就像锋利的爪子在撕扯血肉。
***
阿纳姆呜咽着站了起来。当他慢慢穿过房间之时,低声重复着玛莎的名字,他的脑袋左右摇晃,模糊的视线试图穿透那神秘的黑暗。撕扯的声音突然停止了。
阿纳姆走着。粗糙的地毯刮伤了他的光脚,他颤抖得厉害。他仍在低声念着玛莎的名字,感觉到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在他面前若隐若现——
他摸到了一种又冷又黏的东西,带着一种令人作呕的油腻感。他听到了一声可怕的野兽般残忍凶猛的咆哮,有什么东西在黑暗中快速移动——死亡带走了阿纳姆·皮克林。
***
因此恐怖降临了蒙克山谷。珀西斯·温斯罗普的坟墓里有一股恶臭的气息,像一层不祥的棺罩,笼罩着整个城镇,就像那世代沉郁在其中的腐朽气息。
当哈特利在十几个村民的陪同下,早上回到自己的家时,他发现花园被践踏毁坏了。花园中央那块贫瘠的地方已经被一个深深的坑所取代,坑里堆着一堆令人震惊的东西,仿佛在可怕的嘲弄之下,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团块,那是老多布森残缺不全的,部分被吃掉的尸体,只有剩下的木腿碎片才能辨认出来。
尸体埋在一堆散发着恶臭的浓稠绿色黏液中,虽然没有人愿意靠近那个可怕的坑,但钉腿上残存的被啃蚀的痕迹却太明显了。
哈特利从昨晚的经历中缓了过来。几个小时的噩梦般的猜测把他带进了难以置信的幻象迷宫,最终得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结论,他固执地认为,对于这种恐怖,总有某种合乎逻辑的,自然的解释。
尽管他昨天晚上在月光照耀的花园里看到有什么东西悄悄向他靠近,他还是坚持着这种看法。村民们不可能知道哈特利不敢接受他们在去魔女屋的路上提出的那些骇人听闻的理论,也不可能知道哈特利坚持自己的怀疑主义,把它作为保持理智的最后一道堡垒。
“我不敢相信,”艺术家绝望地对自己说道。“这样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某种动物,”他坚持说,这是在回答拜拉姆·利格特(Byram Liggett)的评论,他是个矮桩的,古铜色面孔的农场主。“我敢肯定。一些食肉动物——“
利格特怀疑地摇了摇头,他的枪——因为所有人都全副武装——已准备就绪,他的眼睛偷偷搜索着周围的植被。
“不,先生,”他坚定地说。“别忘了,我看见了。那不是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就是——她——从坟墓里出来了。”
这群人不由自主地从藏尸坑里往后退缩。
“好吧,一种——一种杂交,那么,”哈特利争辩道。“一种玩笑——一件怪事。两种不同动物结合的产物。这是可能的。它只不过是一种非常危险的野生动物——一定是!”
利格特奇怪地看着他,刚要说话,一个年轻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打断了他,脸色苍白,大口喘着气。
哈特利有了种灾难的预感。“发生了什么?”他厉声说道。男孩努力控制自己急促的呼吸,直到他能连贯地说话。
“老阿纳姆——和皮克林小姐,”他最终气喘吁吁地说。“什么东西杀死了他们!全都——他们全都被撕成了碎片——我看见他们——”
一想到这些,男孩就打了个寒颤,他因纯粹的恐怖吓得哭了起来。
男人们突然脸色苍白,面面相觑,一阵窃窃私语开始了,声音越来越大。利格特举起双臂,让他们安静下来。他棕色的脸上有些小水珠。
“我们得回镇上去,”他紧张地说。“还得快点。我们的女人孩子——”
当他有了一个想法时,他又转向那个男孩。
“杰姆,”他厉声问道。“你注意到——在阿纳姆的地方有任何痕迹吗?”
那男孩强忍住哭泣。“那儿——是的那儿有。巨大的东西,像青蛙的足迹,一个有我的头那么大。它们——”
利格特刺耳而急迫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大家回镇上去吧。快!把你们的女人孩子留在家里,让他们待在那儿。”
听了他的话,人群散开了,匆忙离去,只剩下利格特和哈特利。哈特利看着农夫,脸色非常苍白。
“当然,这——这是不必要的,”他说。“几个人——带着枪——”
“你个笨蛋!”利格特厉声说道,他的声音因压抑着怒火而变得粗糙。“搬走女巫石——反正也不应该让你租这个地方。哦,我想你们城里人都很聪明,喜欢谈论怪事和——和玩笑——但你们知道几百年前蒙克山谷发生过什么事吗?”
“我听说过那些日子,当像珀西斯·温斯罗普这样的恶魔在这儿有他们的魔法,还有一些异教典籍,我还听说过一些过去住在北沼泽里的可怕东西。你造成的伤害已经够多了。你最好跟我来——你不能呆在这儿。没人会是安全的,除非我们做点什么!”
哈特利没有回答,只是默默地跟着利格特回到路上。
在路上,他们遇见了匆匆向镇上去的人们,有弯着腰蹒跚而行,惊惶地瞥视四周的老人,也有抱着大眼睛孩子的妇女,孩子们紧紧靠着她们的裙子。几辆汽车慢慢驶过,还有一些老式的四轮马车。电话一直占线。哈特利偶尔也听到一些悄悄话,当他们越来越靠近镇子的时候,逃亡者就越来越多了,这些低语越来越多,最后变成了低沉的,充满恐惧的咕哝声,像大鼓的撞击声一样,在哈特利的耳朵里震耳欲聋。
“青蛙!青蛙!”
夜晚降临。蒙克山谷躺在月光下沉眠。一些神情严肃的武装人员在街上巡逻。车库的门敞开着,随时准备响应电话求救。决不能再有像昨晚那样的悲剧了。
凌晨两点,利格特被疯狂的电话铃声从不安的睡眠中惊醒。是镇子外几英里高速公路上一家加油站的老板打来的。有什么东西袭击了他,他对着仪器尖叫。他把自己锁在了加油站里,但那里的玻璃墙几乎无法抵挡那只正在悄悄靠近他的东西。
但是援助来得太迟了。加油站成了火海,燃烧着地下的油库,人们只瞥见了一个巨大的畸形东西,它从大屠杀中逃了出来,在伴随它出现的枪林弹雨中毫发无伤。
但是加油站的经营者至少是干净利落地死了。他已经被火烧化了,因为他的一些骸骨后来在废墟中被发现,没有被尖牙咬过的痕迹。
那天晚上,哈特利在利格特家他房子窗户下发现了一些巨大的痕迹。当他把它们指给利格特看的时候,这个农场主一直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盯着他,但他没多说什么。
***
上一场袭击在接下来的晚上发生。哈特利从他的卧室里逃了出来,砰的一声关上门,正好躲过了那个对着那块薄木板乱抓,流着口水,咆哮着的家伙。但还没等哈特利和兴奋的利格特拿着枪回来,它就吓得从破碎的窗户里逃了出去。
它的足迹通向附近的一片茂密灌木丛中,但如果在夜里进入这片交织着阴影荒野,无异于自杀。利格特在电话前花了半个小时,安排村民们黎明在他家见面,开始追捕。 然后,由于他们无法入睡,这两个人回到哈特利的卧室,一直谈到将近黎明。
“它标记了你。”利格特说。“它在追你,就像我想的那样。我估摸——。”他犹豫着,挠了挠下巴上的胡茬。“我想也许我们可以诱捕它——”
哈特利明白了他的意思。“拿我当诱饵?不行!”
“我们还能做什么?我们试图追踪它,但它白天躲在北沼泽里。这是唯一的办法,除非你想让它杀死更多的人。你不能总是把孩子们关在家里,哈特利。”
“国民警卫队——”哈特利刚开口,但被利格特打断了。
“他们怎么能在沼泽里弄到它呢?如果这东西能马上弄到,我们早就动手了。我们会追踪它,天亮的时候,但这不会有任何好处。你不明白吗,伙计,分秒必争?即使我们在这里谈论,这东西可能正在屠杀某人。不要忘了——。”他停了下来,打量着哈特利。
“我知道。你认为是我挑起的。但是——上帝!我一遍又一遍地告诉自己这是一个怪胎,是不自然交配的毛骨悚然的结果。但是——”
“但你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利格特平静地说。“你知道那是什么。”
“不。”哈特利没精打采地摇着脑袋。“这不能——”
他停了下来,盯着利格特的脸。农夫从哈特利的肩膀后面瞪着他,眼睛里充满了怀疑和恐惧。他惊叫一声警告,把哈特利猛地推了一下,使他旋转起来。
那生物似乎在半空中扭动着,农夫被猛扑下去了。一阵痛苦的尖叫涌了出来,突然停止了。怪物蹲在利格特的尸体上,扬起一张沾满鲜血的嘴,发出一种可怕的咯咯声,让人联想到它的喉咙深处的窃笑。哈特利感到恶心,浑身颤抖,他的手指摸到了门把手,当那家伙跳起来的时候,他猛地把门打开了。
他及时砰地一声关上了门,但是一块木板在巨大的冲击下裂开了。当门崩溃之时,哈特利沿着大厅逃跑。
在房子外面,他迟疑了一下,在犹豫不决的痛苦中向四周张望。在黎明前寒冷的灰色中,他看见了离他最近的一所房子,大约有二百英尺远。但当他准备跑过去的时候,那东西突然出现了,挡住了他的视线。它显然是从进来的窗户爬出去的。
哈特利突然想起了他的自动手枪,并把它抓住来,当生物向他扑来之时,对着它近距离开枪。它发出一阵愤怒的嘶哑咆哮,张开的裂口可怕地扭动着。一股污秽的黑色脓水,开始缓慢地从那东西松弛下垂的喉咙上的伤口中流出。
但是它并没有停下来,哈特利意识到如此庞大的生物一定具有惊人的生命力,然后就转身逃跑了。它位于他和村子之间,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优势,就紧紧跟在哈特利后面,不让他有机会再往回跑。一个念头径直闪现在哈特利的脑海中:那个怪物在驱赶他!
他听到一扇窗子吱吱作响,听到一声叫喊。接着,他又沿着恐怖发生的第一天晚上他逃跑的那条路往回跑。
想到这里,他又看到了一条小路——一条有车辙的小路——和马路成直角相交,他就转到一边,沿着小路跑去。他唯一的希望就是回到村子里去。在他身后传来了喘着气,流着口水,表明着残酷追击的,有节奏的砰砰声。
他冒险越过肩膀开了一枪,但虚假黎明的朦胧光线是骗人的,打偏了。他不敢再浪费子弹了。
那东西在追赶他!有两次,他看到了通往村子的小路,每次追上来的怪物都挡住了他的路,他就会绕着他的右边大跳一圈,直到小路跑完为止。不久,田野变得更荒凉了,植被呈现出一种郁郁葱葱的病态绿色。他本可以尝试爬上一棵树,但是没有一棵树离大路足够近,而且追赶者离得太近了。哈特利意识到这一点,吓了一大跳,他看到了摆在他面前的北沼泽——所有可怕的传说都围绕着这片不祥的沼泽。
东边的山脊在淡灰色的衬托下显出轮廓。哈特利听到远处有一个声音,使他心中充满了希望。一个汽车马达的声音——不,是两个!他还记得从利格特家逃出来时邻居的喊声。那人一定是去求救了,叫醒了全村的人。但那咆哮的呼吸声近得可怕。
有一次,怪物停了下来,哈特利回头一看,只见它正愤怒地用爪子抓着受伤的喉咙。子弹一定阻碍了它的追击,否则哈特利早就倒在撕扯着的爪子下面了。他举起他的枪,但那东西,似乎明白了他的目的,并向前跃起,哈特利不得不冲刺,以躲避巨大的跳跃。马达的声音在黎明的寂静中越来越响。
小路蜿蜒穿过沼泽。其上长满了杂草,坑坑洼洼的,有时,渗入的淤泥会慢慢地爬上来,直到仅剩下一条狭窄的带状干地。沼泽繁茂的绿色向四周蔓延,偶尔还会有一片开阔的,令人退避的黑色水域。周围一片奇怪的寂静,完全没有动静。没有风吹皱草叶的顶尖,也没有涟漪漫过水面。追逐的声音,马达的轰鸣,似乎是对这片死寂土地的一种不协调的入侵。
尽头突然临到,毫无预兆。十几码远的地方,绿色的黏液覆盖着道路。哈特利在冰冷的齐踝深的水中扑腾着,感觉自己的脚坠进了一个洞里,重重地摔了下去,扭伤了踝关节。就在他倒下之时,他绝望地滚到一边,当怪物的的冲力越过去时,他感觉一股风吹过了身体。
哈特利伸出胳膊,却突然被某种被某种柔软而执着东西缠住了,无情地把它们吮吸着往下拽。随着一声刺耳的叫喊,他把它们从流沙中拽了出来,倒在更坚硬的路面上。他听到一声枪响,仰面躺在淤泥中,看见一个狰狞的恐怖面具在他上方若隐若现。马达的声音已增至轰鸣,一声鼓励的喊声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怪物犹豫了一下,退了回去,哈特利想起了他的枪,从腰带上猛地把它拔了出来。他近距离向那个怪物开枪,巧合的是,随着他自己的枪声,从汽车里传来了一排枪响。铅子弹在他上方嘎嘎作响,他感到肩膀一阵刺痛。
***
突然间,这个怪物仿佛是个被刺穿十多个地方大巨大的囊袋,并泄出令人作呕的黑色脓水。随着一声嘶哑的喘息声,它扑倒在一边,跛着腿,跳向一边,落入路边的沼泽里。然后,它开始迅速下沉。
流沙带走了它。它那黑而发亮,肌肉紧绷的巨大后腿,几乎立刻消失了,然后是那肿胀的,白得像麻风一样的腹部。哈特利恶心得快要晕了过去,他感到有只手把他扶了起来,听到似乎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疑问的声音。
但他的眼睛里只看到了在十来码外被吞没的可怕东西,那带蹼和骨刺的,连枷似的爪子拼命地抽打着烂泥,那畸形的,丑陋的脑袋痛苦地从一边摇晃到另一边。那东西大张着的嘴里发出一种可怕的嘶哑尖叫,一种可怕的吼声,突然变得熟悉得可怕,清晰可辨,粗而粗的喉音:一种亵渎神灵的狂怒叫喊,就好像是一具早已死去的尸体腐烂的舌头发出的声音。
所有的人都吓得脸色发白,哈特利跪倒在地,干呕着,在极度的恐惧中呻吟着,而那东西,它的嘴被饥饿的流沙半噎住了,咆哮着:
“啊——呃——你们——打死你们!打死你们所有人!愿珀西斯·温斯罗普的诅咒腐烂你们的肉体,并把你们送到——”
惊人的爆发声突然被可怕的咕噜着的尖叫所取代,戛然而止。淤泥中出现了短暂的骚动。一个巨大的气泡形成并破灭——古老的寂静再次笼罩着北沼泽。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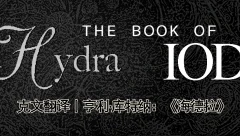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