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照片中的人,留着精心打理的发型和胡须,身着标准的三件套西装,指夹雪茄,一副20世纪中叶典型英国成功商人的形象。他就是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可以说是当时英国最有影响力的管理控制论学者,被维纳称为“管理控制论之父”。
比尔将控制论应用于公司和工业管理,通过为企业担任技术顾问发展出一条颇为成功职业道路。这让他在而立之年就过上了富裕的生活。他拥有一辆劳斯莱斯,和第一任妻子辛西娅·汉纳威(Cynthia Hannaway)住在英格兰萨里郡富人区的一栋大房子里。比尔极尽彰显之能事,他在墙上铺满皮草,甚至还在餐厅里安装了一个声控瀑布。比尔魅力超凡,总是精力充沛,口若悬河,一生著作颇丰,且范围广泛。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比尔都很符合一位有为富裕的成功商人的形象。
至少,在他的前半生。
下文我将介绍比尔的职业生涯以及和他的管理控制论理论,我会略微触及控制论从通信工程和神经科学推向管理学时产生的关于“控制”的争议。当然最后的落点还是比尔为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工作及其对他生活方向的影响之上,这是一位控制论学者在冷战的意识形态对抗漩涡中发生的转变。
1.自学成才的管理专家
1.自学成才的管理专家
开篇的照片拍摄于1960年代初,那时的比尔刚刚离开英国最大的钢铁公司,联合钢铁公司。他曾在这里管理一个70人的运筹学和控制论小组。1961年,比尔离职后与罗杰·艾迪森(Roger Eddison)合作创立了英国第一家运筹学咨询公司SIGMA。1966年,比尔离开SIGMA,加入国际出版公司(IPC)担任开发总监,他负责着这家当时全球最大的出版公司的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的未来发展。1970年起,比尔辞去总监职务,成为一名独立咨询顾问。他的客户不仅包括多家商业公司和工厂,甚至还涉及多个国家的政府。其中以1971-73年间为智利阿连德政府开发的赛博协同系统(Cybersyn)最为著名。虽然该项目非议颇多,但比尔的声望和影响力确实也在此期间达到达顶峰。
比尔职业生涯如此成功,但他其实并未接受过完整的本科教育。
比尔1926年9月25日生于英国伦敦,父亲是劳埃德船船舶登记公司(Lloyd's Register of Shipping)担任首席统计师。少年时期的比尔相当早熟,他从中学起就讨厌专业教学,渴望整体教学(holistic teaching)。17岁时,比尔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哲学和心理学,但大学生涯却被强制兵役中断。1944-47年间,他在印度旁遮普地区的情报部门担任连长,47年回国后在陆军担任心理学家,49年以上尉军衔退役。可是当他离开军队后想要申请博士学位时,却被告知必须要从本科一年级读起。于是比尔索性放弃学术生涯,进入联合钢铁公司分部赛缪尔·福克斯公司,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而他的第一个博士学位,直到2000年73岁时,才由桑德兰大学授予。
比尔似乎将自己学术热情挥洒在了职业之上。在英国陆军的经历使其认识到了运筹学的前景(operational research,通常是利用统计学、数学模型和算法等方法,去寻找复杂问题中的最佳或近似最佳的解答)。入职联合钢铁公司几年之后,他在1953、54年分别发表了两篇论文,阐述了他开发并投入使用的衡量制造工艺生产率的新型统计指数。文中提到的生产力抽样以及系统并规律地收集、汇总和展示信息的想法,颇受管理层的青睐。1956年,比尔因此进入分公司的管理层,担任生产总监(production controller),这是一个专门为他创造的新职位。随后比尔还说服管理层成立了运筹学和控制论小组,这是一个由他领导的70人团队,比尔称其为Cybor House,Cybor是比尔将控制论(Cybernetics)和运筹学(Operational Research)组合后创造的新词。三年之后,1959年,比尔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著作《控制论与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ment)。他的余生从此都将与控制论紧密相连。
2.走入控制论,一种可通约的方法
2.走入控制论,一种可通约的方法
比尔第一次接触控制论是在1950年读到维纳的《控制论》之时,在被震惊之余,他看到了将其应用于管理的可能性。比尔对控制论的兴趣虽然开始运筹学和管理学,但在本质上和其他控制论学者有共通之处:他们都在寻找一种不同学科间可通约的模型。
比尔切入控制论的关键词是“极度复杂系统”(exceedingly complex systems)。他对系统的定义是“任何具有凝聚性的、动态关联的项目(items)集合。更正式地说,这些项目可以被看作是由一个关系网络连接的点。”而极度复杂系统则是组成部分极多、连接关系极复杂、随机性极高以至于无法被完全具体描述的系统。例如公司、经济系统,以及人类大脑。
从举例中我们可以看到比尔迥然不同的分类法,在“系统”的视角下,有机体和社会组织(甚至是机器)可以被归为同类。比尔认为“公司当然没有生命(not alive),但其行为很像活着的有机体。”并且公司为了”在变动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中生存,必须从经验中学习。”这一观点无疑与比尔的心理学的经历有关,甚至可以追溯到他从中学起就在寻找的,跨越具体专业的“整体”(holistic)知识。
控制论从通信科学发展出的一系列术语和概念,恰好在有机系统、机器系统和社会系统间具备可通约性。这和比尔的新分类法不谋而合。既然公司是以有机体(人)为基本单位构成的类有机系统,那么控制论的概念就同样有效。在比尔的管理控制论中,管理公司和工厂的关键之一在于提高各部门之间的信息反馈(feedback)效率,让彼此能实时协同,使公司面对外部环境变动时能快速有效地做出反应,比尔称其为“适应”(adaptive)。
仅从控制论的角度看待旧事物很容易落入“比喻法”的陷阱,重要的是发展出一套对应的方法论。比尔在此受到了长他23岁的控制论学者罗斯·艾什比(Ross Ashby,了解更多请见《黑箱与罗斯·艾什比的控制论》)的影响。艾什比作为精神病学医生,最主要的成就是关于适应性大脑(adaptive brain)的研究,即大脑如何适应外界的刺激并保持稳定运作。艾什比将大脑视为“黑箱”,因其极度复杂且无法通过拆解描述其运作,所以不能用传统的机械式的方法控制和预测其的行为,只能在输入输出的反馈回路中对其建模,加深认识并产生效用。
艾什比在1947年5月公开展示了一个模型“稳态调节器”(the homoestat) 来演示大脑通过自适应调节达到稳定状态的过程。机器由四个能输入输出电流的单元组成,它们彼此联通。每个单元顶部都有一个水槽,水中是一个受电磁影响的叶片。当单元未通电时,叶片在固定位置上保持不动。当通电时,叶片受磁力作用摆动,显示本单元输入端的刺激程度。同时,摆动产生的电压会影响本单元输出电流的强度(同时也是其他单元的输入电流)。因此当稳态调节器通电后,电流在四个单元之间反馈循环,每个单元既是电流的输入端也是输出端。叶片在最初会不停摆动,但四个单元之间经过一段时间的相互调节和适应后,电流便能形成稳定的循环,叶片复位,稳态调节器达到平稳的状态。艾什比认为稳态调节器的表现正是模拟了大脑在接收到外部刺激后回归稳定状态的适应过程。稳态调节器也在当时被英国媒体誉为“最接近大脑的发明”。
稳态调节器本质上是一个模拟大脑部分机制的模型。它不关注大脑/黑箱“是什么”(具体构造和组成部分),而是大脑/黑箱“能做什么”(通过自适应达到稳态的机制)。这种基于黑箱认识论的建模思路启发了比尔处理极度复杂系统的方法。管理者与公司的关系和控制论学者与黑箱一样,他不需要完备的描述或还原公司(黑箱)“是什么”,而是公司(黑箱)“能做什么”,即能在和整体社会经济环境中达到什么经济效用。
比尔从信息交流反馈的角度出发,重新归类公司的各部门,整合出新的框架模型。模型让实际经营中产生的各种数据(业绩、财务和库存等)形成关联,在促进各部门的沟通与协作的同时,也能让管理者从宏观上把握公司状况、作出决策。当然,最重要的是,与有机体的类比总是存在其中。
3.比尔的管理理论,关于生物的方法
3.比尔的管理理论,关于生物的方法
在斯塔福德·比尔的管理控制论理论中,最有名的莫过于可生存系统模型(the viable system model),它因用于智利的赛博协同项目(Cybersyn)系统而广为人知。不过在此之前,我要先介绍他关于控制论工厂(T-U-V机器)的构想,这在某种程度可以被视为该模型的前身。
• 控制论工厂与生物计算机
• 控制论工厂与生物计算机
斯塔福德·比尔在职业生涯早期曾是自动化工厂的支持者,他激进地认为当时的工厂还不够自动。但他改进自动化工厂的方法,不是通过优化流水线进一步异化工人以压缩周期、增加效率来提高生产。比尔宣称要为工厂配备一个“适应性大脑”,它会根据市场波动做出反应,自动安排日常生产活动,甚至能像生物体一样在不断学习中生长进化,几乎不需要人类的干预。比尔期待它可以接手工厂/公司的日常管理事务,从而让管理层能有精力专注于更重要的决策议题。
下图是比尔为其构建的模型,由三种机器组成。左侧的T机器(T-Machine)负责“扫描、分类和模式识别(scansion, grouping and pattern recognition)”输入其中的数据,包括表示财务、订单、原料、库存和绩效等能显示工厂状态的指标。右侧的V机器(V-Machine)负责输出指令,指导生产等其他行为。而位于两者之间的U机器(U-Machine),就是调配这一切的“适应性大脑”。
在20世纪50年代的工厂中,很容易找到与T机器和V机器对应的部门,而对于U机器的样貌却很难想象。如今看来,U机器非常类似一个人工智能决策系统,具备处理数据、解决流程化问题的能力。但在当时“人工智能”这个词语尚未出现,数字计算机的算力也不足以处理逻辑复杂、数量庞大的数据。既然“数字”的方法行不通,比尔就转向生物和化学领域寻找U机器的“控制员”,试图用另一套“极度复杂系统”去控制现有的“极度复杂系统”。
比尔和另一位英国控制论学者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了解更多请见《控制论的华丽公子、激进的对话者:戈登·帕斯克》)合作,尝试利用有机化学原理和简单生物系统来构造生物计算机(biological computing)。通过操控有机系统的适应性行为形成具备简单“智能”的U机器。他们尝试了老鼠、水蚤(daphnia)、甚至是一个微型池塘生态系统。可想而知,这些东西构成的工厂“大脑”几乎不可能产生可控的适应性行为。因此控制论工厂的构想很快就搁置了。在之后的设想中,比尔将人类移回了系统的中心位置。
• 可生存系统模型
• 可生存系统模型
可生存系统模型(the viable system model)是比尔之后工作的重心。理论的重点从构建一个自动化的中枢,转变为优化组织各部分之间的信息沟通和响应效率。但目标仍然是让系统能适应环境,最终具备可生存的能力。
比尔在该系统模型中建立了对人类神经系统更完整的映射,以便使其能应对更为复杂的管理状态。下文我会分别从人体神经和公司组织两个方面对照简述每个子系统。不过要注意的是,虽然多数人将组织的基层(执行子系统)视为高层(管理子系统)的下级,因而只能被动执行后者的决策。但比尔在可生存系统模型中,尽力弱化这种等级制度,仅仅将其视为信息传递回路上的顺序差别。
下图是《公司的大脑》(Brain of the firm)一书中,可生存系统模型人类神经系统和组织(公司)的对照模型。
可生存系统模型具有五个子系统。
系统1是“交感神经系统”(sympothetic system),在右图中是组织的1A-1D四个子部门。它们和其所在的环境直接接触,并且能对局部情况做出反应。例如人体的心脏和工厂的某条生产线。
系统2是“脊柱”(spinal column),是各交感神经汇合的枢纽。在右图中是各子公司或部门之间的横向通信渠道。它帮助系统1中的各个部分交换信息、相互协作,适应其所处环境。类似身体上无需有意识驱动就能做出反应的部位。
系统3类似于“脑桥、延髓”(pons, medulla),是维持生命基本必要行为(循环、呼吸等)的中枢。在右图中则表现为一个负责组织日常管理的运筹学小组,运作所有子部门的业绩模型。并且在此基础上实现两种功能:第一,向系统1传递系统4和5的信息,从全局角度协调系统1子部门之间的合作,保持组织的稳定性;第二,定期汇总系统1的信息,过滤后传达给系统4。
系统4是“间脑和神经节”(diencephalon, ganglia),是脑干和脑半球之间的中继站。在右图中虽然处于系统3的上级,但实际上像是与其互补的管理部门。系统3负责日常管理,系统4则负责责中长期的规划和决策。因为其具备外部视野,正如间脑中的汇集了听觉和视觉神经的后丘脑一样。美国技术史学家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认为系统4的功能就类似于上文中提到的T-U-V机器。
系统5是“大脑皮层”(human cortex),是意识产生的源头。在右图中表现为董事层。通过汇总的信息和对外部环境的认知,主动制定政策,做出方向性的决定。
5级系统中1-3负责组织的日常运作,4和5负责组织的未来发展方向。该模型大体上仍然很像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型,不过比尔希望通过此解决组织中的集中决策和各部门自主性之间的矛盾。这体现在集中体现在两点之上:
第一,比尔鼓励同一层级之间的相互沟通、协调甚至是彼此制约,使其具备一定程度上的自主行动和自我纠错能力。例如系统2对系统1的横向沟通,以及系统3和系4的分工协作。
第二,保持不同层级之间的多通路沟通,在决策层做出错误决策时,其他通路可以通过提供“负反馈”(通过输入来减弱之前的幅度)纠正错误。比尔为了防止系统4、5信息过载,为系统主通路设计了过滤机制。但是他在此之外又提供了信息冗余通路,以消除信息的误传。系统3-5分别由多位成员组成,因此主通路中本身就包含有几条不同的通路。同时,系统1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绕过系统3向系统4、5发送被比尔称为“欣快痛觉”(alegdonic)的信号,以便更快速的解决紧急的具体问题。
由此,整个可生存系统模型就成为了一个相互耦合,各部分彼此协调的的适应性组织。既能集中管理迅速调动资源应对外部变化,也能让各个部门享有充分的自主性,快速纠正内部的错误决定。这一切的关键就是各种数据和信息在系统内快速、有序的流动与反馈。管理者可以通过这套模型来理解公司的状况,迅速响应。
4.Cybersyn与阿连德政府,两个未竟的理想
4.Cybersyn与阿连德政府,两个未竟的理想
斯塔福德·比尔从1971年11月到1973年7月之间曾先后七次来到智利,提供经济方面的顾问服务。因为主导智利经济改革的国家开发公司的第三号人物费尔南多·弗洛雷斯(Fernando Flores)认为,比尔在中心化(一致)和去中心化(自主)之间找到平衡的管理控制论与阿连德政府民主社会主义的执政思路不谋而合。比尔的这段经历几乎贯穿了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的执政生涯,因而他本人连同控制论本身也被卷入了冷战错综复杂的地缘政治之中。下文我将尝试尽量简洁清晰地叙述这段历史,以及控制论在意识形态争论中所遭受的非议和误解。
•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政府
• 萨尔瓦多·阿连德的智利政府
1970年10月,智利的社会主义政党“智利人民团结阵线”在大选中胜出,成为了第一位由选举产生的社会主义政府。此前的一百年里,智利的政权已经通过多党选举实现了多次稳定的政权更迭,在独裁军政府遍地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实属异类。原因之一便是智利自然资源(尤其是矿产)丰富,人民生活尚算富足,人均收入在60年代就已经高达600多美元。稳定的经济造就了相对稳定的社会,军队严守中立不干涉政权更替。但是智利国内贫富差距很大,而且重要产业多有美国资本的介入。
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Guillermo Allende Gossens)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任智利总统。他虽然领导着一个社会主义政党联盟,但阿连德本人一生中从未加入过任何党派。他的政治路线也与冷战时期的两大阵营都截然不同,他决定探索“第三条路”,能兼具苏式的效率和美式的灵活,在政府的集中管理和自主性间找到平衡。阿连德希望在不改变现有社会制度的情况下,用渐进改革的方式向社会主义过渡。因此对产业和经济施行温和的社会主义改革是阿连德政府的执政要点。
智利一直以来稳定的政治局面造就了阿连德这种乐观的想法,但身处美国后花园的南美小国岂能在冷战的漩涡之中独善其身。无论你的路线多么温和,如何宣称不和老大哥站队,一旦身上带有“社会主义”的标签,在美国看来就是需要被颠覆的对象。而且除了意识形态之外,阿连德将铜矿等重要产业收归国有的动作也确实触动了美国的利益。因此阿连德政府从执政之初就不断受到美国的各种舆论干扰和暴力破坏。讽刺的是,由于阿连德宣称不实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智利在此期间几乎从未受到过勃列日涅夫的任何实质性帮助。
阿连德政府最开始实施的工人权益、教育和医疗等方面的政策带来了短时间的上扬,但之后美国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禁运封锁让智利无法获得外汇储备和其他国家的支持。智利的经济状况在内外交困之中持续恶化。到了1973年初,贸易逆差达到4.38亿美元,物价在过去一年里上涨了180.3%。
阿连德政府从最初就希望找到一种新的产业管理方式,既能符合阿连德“第三条路”,又能快速在经济中产生作用。主导这项工作的是弗洛雷斯,他当时作为工程师就职于智利最大的国有企业国家开发公司。三年后,年仅30岁的他升任至阿连德政府的秘书长。1973年9月11日,在皮诺切特发动的军事政变中,弗洛雷斯被阿连德派去和军政府谈判,但立刻被逮捕关入监狱。而总统阿连德拒绝投降,在总统府抵抗到了最后一刻并最终殉职。在此之前,弗洛雷斯始终处于这场改革(以及智利政治漩涡)的中心。
1971年7月,弗洛雷斯寄给比尔一封邀请信,信中表明他希望“在全国范围推广科学的管理和组织方法”,他认为比尔的管理控制论能在智利的新政府中发挥作用。这封信及其产生的波澜或许没能改变阿连德政府的结局。但却切切实实地改变了弗洛雷斯和其他参与智利专家的命运,当然,同样被改变的还有斯塔福德·比尔的人生。
• 赛博协同Cybersyn
• 赛博协同Cybersyn
比尔收到弗洛雷斯的信之后,在1971年11月第一次前往智利,与弗洛雷斯组建的专家团队共同开发Cybersyn系统。比尔的工作是在智利政府的主导下构建一个包含了组织架构设计、软件编写和硬件设计的实时经济管理系统。
比尔面对的不仅是逐渐恶化的经济环境,还有极为有限的技术资源。智利当时仅有四台大型主机,其中三台是IBM System/360。而且智利政府的外汇储备由于经济封锁日益吃紧,也无法再从国外进口昂贵的新机器(智利采购的第一台主机IBM360花费了200万美元的法国信用证)。比尔仅被允许调用一台主机进行数据处理,而与企业和部门之间的数据传输只能使用智利已有的电传打字机。
从最终的结果来看,Cybersyn有四个主要的子项目:cyberstride(统计软件),cybernet(电传网络)和CHECO(经济模拟器)以及Opsroom(指挥室)。
第一个子项目Cyberstride是Cybersyn在1972年3月比尔第二次到达智利之前的名字。之后为了应对智利复杂的经济状况,项目被扩充为Cybersyn。Cyberstride是用于“工业经济信息和控制的初步系统”,用各个产业的变量和数据建立经济模型,通过检测数据的变化控制宏观经济状况,进而指导后续的经济政策。这个系统类似于可生存模型中的系统3。于1972年11月底投入使用。
第二个子项目Cybernet是用智利比较普及的电传打字机构建的全国通讯网络。每台电传机都有一个身份识别号码,可以拨打与其建立连接,但实际上每个公司都每天只能传输一次数据。如果将各个公司视为可生存系统模型中的系统1,那么比尔对Cybernet的最初构想是类似于系统2和其他信息渠道的集合体。但由于硬件短缺,最后建成的网络并不支持公司间的横向通讯,只能作为垂直层级单线沟通的工具,这便让所谓的“自主性”大打折扣。尽管如此,Cybernet还是在智利的关键社会事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而这点之后却让Cybersyn被批评为集权统治的工具,并且最终在某种程度上扭曲了公众对Cybersyn的整体印象。
比尔为了弥补硬件短缺带来的缺陷,比尔设计了一个名为Cyberfolk(实时通讯渠道)的补充措施,类似可生存系统模型中“欣快痛觉”机制,为了让工厂和公众表达他们对政府的态度(满意或者不满意)。Cyberfolk的具体形式是在每个工厂和家庭中设置一个半圆形的量表,表盘两端分别代表”不满意“和“非常快乐”。指针摆动显示仅表示满意程度而非具体意见,指针的不同位置会输出相应电压,最后汇总到政府形成整体的感觉趋势。但是该量表传达的信息过于模糊,政府无法有效做出解读,Cyberfolk最终并未投入使用。
第三个子项目CHECO的全称是(智利经济[CHilean ECOnomy]),旨在建立一个能模拟智利经济的程序,预测未来的经济行为。比尔使用了杰伊·福瑞斯特(Jay Forrester)开发的DYNAMO编程语言,期望CHECO能具有可生存系统模型中的系统4的功能。但由于数据量和更新频率都远远达不到要求,因此该模型的预测结果既不快速也不准确,CHECO项目也随之搁置。
第四个子项目Opsroom是一个参考英国二战时期作战室设计的指挥室,旨在打造一个总览全局制定政策的中控室,相当于可生存系统中制定政策做出方向性决定的系统5。伊登·梅迪纳(Eden Medina)称其为“一个未来主义的梦境”,这是一个六边形的房间,墙上设置了多块屏幕,显示从企业和工厂收集的数据。为了降低使用门槛,数据可视化成为了设计中的重要考量,不过依照当时的技术大部分的可动图表还只能使用叠加幻灯片层的显示方式。七个玻璃纤维材料、红白配色的座椅呈环状布置,扶手上的按钮可以操控屏幕。这些英国生产的屏幕由于美国的封锁,只能通过走私进入智利。
Opsroom于1972年12月底建成,阿连德在不久后曾到此参观。虽然这里从未真正投入使用,但Cybersyn的参与者都将其视为整个项目的象征。Opsroom指挥室中有一个屏幕专门用来演示完整的可生存系统模型,比尔似乎是想提醒参与者们Cybersyn的理想样貌。
1972年4-9月之间,智利团队和英国的外包团队加班加点,终于赶制出了Cybersyn临时套件,并于11月投入使用。但是由于智利复杂的政治经济现实,该项目完整构想从未真正实施过。它当然也未能以比尔和弗洛雷斯设想的方式改变智利的处境,反倒是智利的政治现实形塑了Cybersyn的实际面貌。
• 关于“控制”的争议
• 关于“控制”的争议
1973年1月7日,英国观察者报的一篇报道《计算机掌管智利》(Chile Run by Computer)将比尔和Cybersyn推上了风口浪尖。该文章作者从未采访过项目的核心参与者,仅仅通过其他渠道侧面挖掘消息以爆料的方式写出。报道将Cybersyn系统描绘为政府秘密开发的工具用以实现对智利民众“老大哥”式的控制,是极权主义的象征。这无疑曲解了Cybersyn的形象,该项目虽未主动寻求过媒体曝光,但也绝非以秘密开发的方式进行。报道显示出当时西方社会对社会主义的刻板印象,以及对智利实际社会状况的有意忽视。
某种程度上,对阿连德政府的偏见是一个意识形态刻板印象被自我强化的过程:当阿连德政府被西方社会贴上“极权”的标签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便开始对智利实行政治颠覆和经济封锁。这导致了阿连德政府无暇延续执政初期提高人民福利促进生产的政策,只能加速企业国有化以巩固政府控制,应对紧急状况;而此类措施又加深了西方社会对阿连德政府的偏见。两者形成了相互强化的正反馈恶性循环。在这个过程中,Cybersyn项目自身也被扭曲,成为另一个阿连德政府“极权”的“铁证”。
以电传网络(Cybernet)为例,它最初的设计目的是用于企业间的横向沟通并向政府输送数据,但是政府由于经济封锁而没有财力和渠道从国外购买硬件,最终比尔只能使用现有的电传机打造向上单向传输的网络。而且Cybernet在正式作为Cybersyn组件投入适应之前,意外地在政府应对“十月罢工”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十月罢工”是发生在1972年10月的一次智利全国性罢工,由几千名卡车司机发起,企图通过掐断运输让智利经济陷入瘫痪。而刚刚建好的电传网络恰好为政府提供了与工厂直接沟通的信息渠道,它能绕开效率低下的官僚系统,让政府命令直达各地,快速组织调配最大程度恢复生产。11月2日罢工结束,Cybernet帮助政府挺过了这段艰难时刻。Cybersyn和控制论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在智利“实实在在的影响了历史进程”。
Cybernet的“成功”使其受到了政治力量的关注,他们希望将其从Cybersyn项目中独立出来,作为政府信息协作和沟通的手段。这使Cybernet逐渐脱离了原有的控制论语境,简单地成为了“控制”的工具。这恰恰又强化了Cybersyn在公众舆论中极权政府集中控制民众的工具的形象。
为此比尔不得不出面澄清。1973年的整个春天,他的精力都放在这场关于控制论和Cybersyn论战之中。1973年2月14日,比尔在演讲《为有效的自由欢呼:政府中的控制论时间》(Fanfare for Effective Freedom:Cybernetics Praxis in government)中首次正式对外介绍了Cybersyn系统,希望打消外界关于新的科学技术会导致压迫的疑虑。
公众对Cybersyn的误解一方面源自于观察者报的报道带来的第一印象,另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则是传统观念中对于“控制”(control)一词的误解。比尔早在1959年就曾指出过这一点,他在《控制论与管理》(Cybernetics and Managment)中写道,“控制”总是和“胁迫性的管理”(regulation which is no more than coercion)联系在一起,但是在比尔看来,控制论意义中的“控制”更多意味着类似有机系统的“自我调控”(self regulating),这也是他在之后的实践中所一直贯彻的,赋予子系统或个体足够的自主性。
有趣且讽刺的是,虽然包括比尔在内的所有早期控制论学者都在强调控制论中人本主义和个体自由的一面,但是控制论所留下的诸多遗产如今似乎都成为了“胁迫性的管理”的最佳工具,例如大数据寻址和高速反馈循环的信息网络。在当时,就有学者认为比尔所谓的将“权力下放给工人”不过是在自欺欺人。当我们跳出比尔的理论框架审视时,无论他如何强调系统内的横向沟通和各部分间的自适应耦合,系统的实现都是一个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过程。在多数人看来,这就是将系统的未来寄希望于高位者的能力与道德水平,缺少平级的负反馈机制制衡。
这场论战不久后随着阿连德政府被推翻而逐渐消声。1973年9月11日,军事政变发动后,Cybersyn几位核心专家为了避免项目落入军方手中,成为军事独裁政府的统治工具,用最快的速度整理了项目的资料,连夜离开智利。皮诺切特的军政府上台后,曾经评估过Cybersyn系统,但是其中包含的去中心化和适应性的管理理念,和军队中自上而下等级分明的风格完全不同,因此便废弃了该项目并毁坏了Cybersyn所有已建成的部分。
Cybersyn和阿连德政府一样,都是一条无法与现实兼容的“第三条路”。标榜“自由”的人认为它不够自由,实施独裁的人却又认为它不够有效。或许比尔的理论模型的有效性仅止步于公司层面,这一点从Cybersyn的历史看来尤为明显。即便比尔设计了一个自洽的可生存系统,但是当这个系统被抛入一个“非可生存系统”的国际环境时,它没有足够的适应能力应对外部力量的干扰。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智利的情况太复杂了,但这恰恰也证明了比尔的可生存系统模型所能模拟的复杂程度是有边界的。至少在当时,控制论式的信息反馈回路不足以影响其外的世界。
而戈登·帕斯克就意识到了控制论范式的边界,他的对话理论研究的是个体间的互动如何导向学习和认知,是关于“学习如何学习”的元理论。但是帕斯克划定了一个边界排除了权力的影响,因为权力可以从外部主导对话的走向,导致对话产生的结果很可能与知识无关。而Cybersyn和阿连德政府面对的就是一种权力从外部干扰的情况。
不论如何,这些都只是推论,毕竟比尔的理论模型在国家层面从未真正的实施过,因此我们也就无法验证其完整版本是否真能像比尔所说的那样实现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的平衡,并具备适应外部环境的特性。
5.比尔的另一半人生
5.比尔的另一半人生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斯塔福德·比尔人生的分水岭。
此刻让我们回想本文开篇比尔的精英资产阶级的形象。他以外国专家顾问的角色介入智利的社会主义改革,向阿连德政府收取每天500美元的咨询费,这是顶级欧洲咨询顾问的价格。弗洛雷斯为他安排了头等舱和首都圣地亚哥的豪华酒店。这一切看起来都与社会主义改革、争取工人权益这样的字眼毫无关系,英国的同僚们也认为比尔的“实际生活和他所说的完全是两回事。”这让Cybersyn所宣称的为工人赋权的目标变得极为可疑,而比尔本热被描绘成了一个帮助极权政府控制工人的富裕资产阶级商人。
这种评价当然是不公平的,虽然比尔口若悬河的特点确实让很多人对他产生夸夸其谈的吹嘘商人的印象,但他从来都是一个真诚而善良的人,他对朋友从来都是毫无保留的慷慨。英国控制论学者艾什比和帕斯克的职业生涯和经济状况都并不理想,比尔便为两人在学术机构中谋求职位而奔走。他甚至在推动了伦敦新布鲁内尔大学国家控制论研究所的建立,旨在为戈登·帕斯克提供教职,帕斯克之后在这里培养了英国第三代控制论学家。
智利的经历让比尔在政治和舆论的漩涡中不断挣扎,他看到了两种世界的参差,感受到了现有生活与真实内心之间的割裂,1973年初,正当智利国内的情况恶化反对派政变的流言四起之时,比尔的妻子不希望他再与阿连德政府来往。但比尔仍然坚持先后两次前往智利。1973年7月26日,比尔和阿连德最后一次会面后返回英国。一个多月后,就传来了阿连德政府被推翻的消息。曾与他共事的许多智利朋友也失去工作,甚至像弗洛雷斯一样被捕入狱。比尔在对自己体面而优渥的生活的审视中,正式走向了另一种人生。
自1974年起,比尔放弃了物质财富,独自搬到威尔士偏远地区的一座不通水电的小石屋里生活。他仍然继续着关于控制论的研究,不过他在此后几年里最重要的事情,是从皮诺切特的高压统治下解救他的智利朋友并安顿他们在新国家的生活。直至1976年,他终于在大赦国际的帮助下使弗洛雷斯获释,并帮助其流亡海外。比尔为了帮助这些智利朋友几乎倾尽家财,他在给冯·福斯特的信中提到“这个业务太花钱了。”
比尔在小屋里度过了大半余生,他像嬉皮士一样生活,教授瑜伽,产出了数量和质量都十分惊人著作,包括理论书籍、诗集和许多画作。
2002年8月23日,斯塔福德·比尔多伦多去世,享年75岁。英国运筹学会设立了斯塔福德·比尔奖章,授予“信息系统或知识管理领域哲学、理论或实践最杰出的贡献”。
最后,让我以自译的一首比尔的诗作结尾,该诗收录于1986年出版的《鹅卵石到计算机:线程》(Pebbles to Computers: The Thread)一书中,题为《 Computers, the Irish Sea》。
那片绿色的计算机海洋
及其所有的分子逻辑
覆盖了系统的方寸之地
一个大过我脑的大脑
在跨越平淡黑板水面的船头
写出泡沫状的方程
它所处理的变量
航海家们也无法列出
大过他们的集合
正解层叠涌来
无过无垢
只有绿底上纯白的积分
潦草地书写递归地计算
那片绿色的计算机海洋
在一种震撼你我的规模之上
所有人瞠目呆坐
把难以消化的果皮掷向海鸥
却无人讲清一个方程
所有的东西、流动的丢番图
阶数为亿万无穷
模拟自身。转上一圈
绕过甲板,便理解了
所有发生之奥妙
如是写下,自我因由
参考
- Obituary Stafford Beer, Jonathan Rosenhead 2003年12月16日
- The Cybernatic Brain, Andrew Pickering, 2010,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控制论革命者》[美] 伊登·梅迪纳,熊节 译,2022,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Cybernetics and Management, Stafford Beer, 1959, English University Press
- Brain of the firm: the managerial cybernetics of organization, Stafford Beer, 1981. John Wiley & Sons
- The viable system model: its provenance, development, methodology and pathology,Stafford Beer, 1984. Journal of the operational research society, 7-25.
- The Heart of Enterprise: Companion Volume to Brain of the Firm,Stafford Beer, 1994. John Wiley & Sons
- Cybernetics of development evolved from work in Chile, Stafford Beer, The Zaheer Lecture, 1974年12月5日
- Chile Run by Computer, The British Observer on Jan. 7, 1973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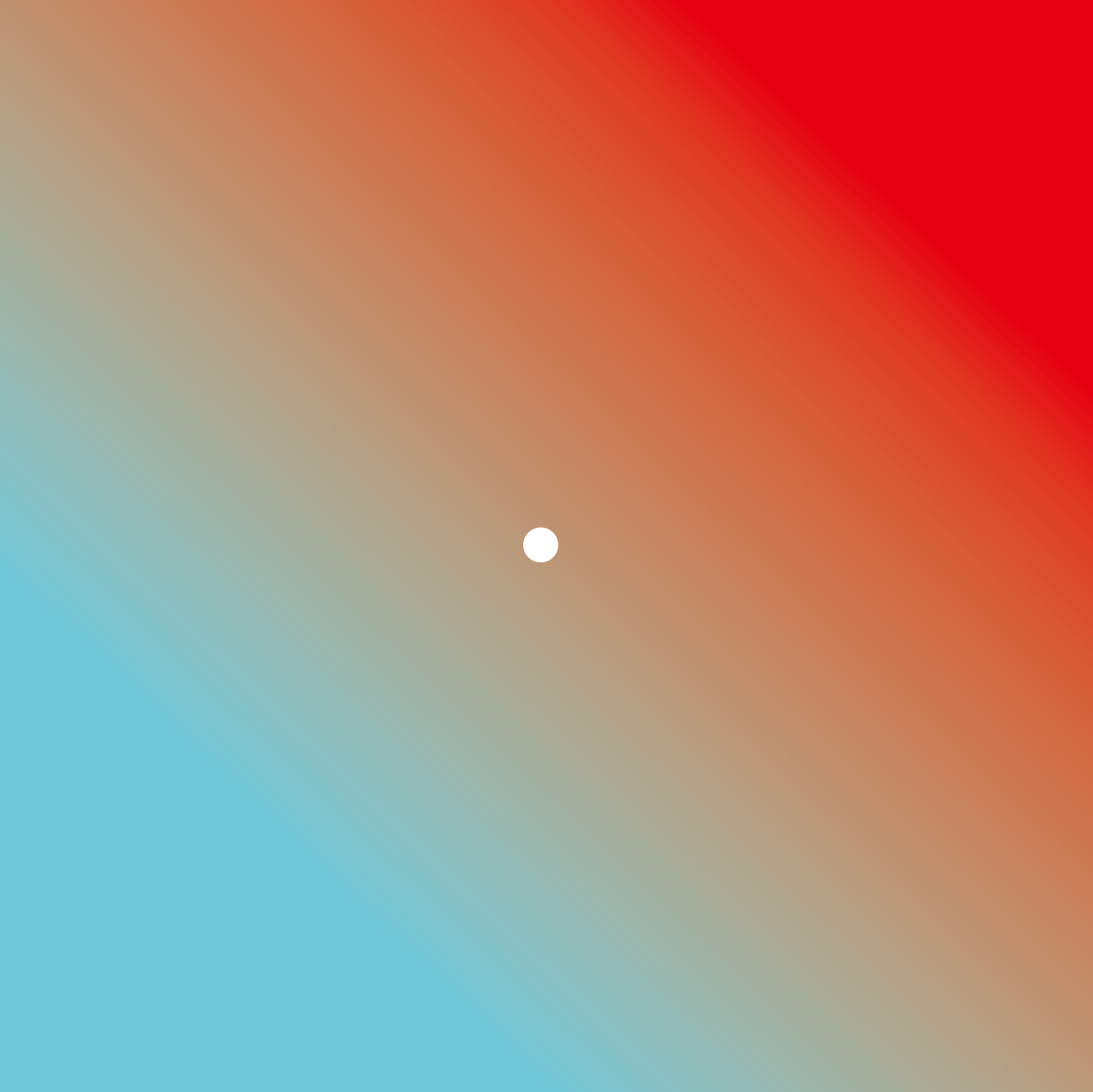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