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编按
编按
电子游戏与心理治疗关系的思考一直是段坏账,过去落日间中已介绍了大量在具体实操时的问题(Theresa Fleming 临床心理学中的严肃游戏与游戏化 (2022)),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对于游戏与心理治疗的某种本体论和内在过程的误解:
面对电子游戏,人们可能要么偏向一种对心理治疗中游戏疗法,艺术治疗,沙盒游戏的直接附会,要么就混淆了温尼科特著名的游戏——文明作为治疗模型的思考与具体游戏的使用,而这游戏的两重性(作为强迫性重复和病理的(电子)游戏,以及作为自由,创造,成长的游戏)也总是令人困惑,特别是在「把电子游戏介入心理治疗」时,这种问题和双重性的张力更加显露出来,在深入这个界面思考时,我们需要对其有更明确的概念清理,才不至于在其中晕头转向。
而本文作为对温尼科特「过渡客体」以及游戏作为主观与客观的「中间地带」思考的扩展,将游戏作为替换梦的模型的新的精神分析治疗的模型,为上述的疑难做了非常好的区分。
原文自法文译出,感谢在法国做精神分析研究的朋友小柏(「例外状态」主播,巴黎圣-安娜医院精神科实习生,巴黎八大精神分析硕士,巴黎大学临床心理学本科)的校对与校按,此外我也邀请了同为英美精神分析心理咨询师的晓萌(「何苦开心」主播,心理咨询师,英国塔维斯托克中心,精神分析研究,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心理动力学项目)为大家写作荐语,希望这些努力能帮助我们在心理治疗-游戏的界面上做更多专业,足够清晰和落地的探索和研究。
落日间
叶梓涛
荐语
荐语
游戏是儿童的自由联想——如果说,克莱因提出游戏治疗之后,早期精神分析文献对于这一观点尚有争议的话,更多理论和实践已经将其证实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基本准则之一。
作者想要深究温尼科特将游戏视作过渡现象的理论,对于其中「模糊化」的部分详细说明,更加深入阐释游戏的治疗机理,说明游戏对于成人的意义。
因为讨论细致,作者同样没有落入「一切皆是游戏」的大而化之的论述,而是讨论了带有父性特征的规则在游戏中的转化力量,与此同时,规则又非刻板、僵硬,留有自由创造的空间。
在我看来,这恰是某种「好」游戏的标准,是作者与玩家的对话,是安全之中的自由探索,是限定范围的逐渐掌控;甚至是玩家创造的一块基石。
我们常在游戏 Mod、同人、衍生作品等二次创作中看到,游戏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索的过渡空间,种种转化、创作在此发生。《Minecraft》出现在治疗室也不是令人惊讶的事。
与之相反,我们可以更加明显地借由这一框架获知,许多当下流行的尤其数字游戏实际上并不属于精神分析所谓的带有治疗性质的「游戏」范畴;带有强迫、乃至成瘾性质的游戏活动反而恰是「游戏」的反面,也就是创伤。
当然,游戏从来不必要去承担治疗功能,游戏「产品」的走向也有更多深层原因,但创作者还是可以把本文抱持在心中,作为一个或可尝试的 guideline,遇见更多「作品」。
乔晓萌
校按
校按
游戏对于一个成人来说,或许是休闲和益智性探索的场域,而对于曾经的成人,也就是孩童来说,游戏却是他们得以区分出主客体的界限,发展思想,面对并掌控孤独所必经的阶段,是从与父母的被动状态的原初经验过渡到主动的、创造性的符号化经验的过程,也就是说,面对母亲的缺席——需求并不得马上得到满足,呼唤并不得马上得到回应——通过把玩客体、游戏客体,孩童学会了把无法把控的异质性的嘈杂的身体情动转换成了符号性质的主观思考。
在游戏中,他们把内在的冲突和自己的侵略性借助手头的客体通过幻想场景表达(fantasmer),并拥有了安排组织架构的思考能力。借用拉康的话,也就是词杀死了物本身。而当孩童主体无法拥有游戏的能力,符号化焦虑时,病理性的行为、躯体化的症状就会作为另一条途径来释放他们的内心冲突,这也是许多儿童来访的主要原因之一。因此,在精神分析诊室的空间中,游戏作为一种内在性的手段,即一方面投射出了儿童的症状,另一方面通过它培养了儿童符号化能力和独立性,是必然的也是必要的,游戏即自由游戏的能力指向了治愈。
这篇论文探索了精神分析视角下游戏的不同层次,以及它的潜能,探讨了游戏的心理治疗功能和象征性游戏空间发展的条件和前提:如何保障以及发展安全和自由的游戏?我们所感兴趣的是面对这一问题时,作者引用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广度和深度:弗洛伊德、温尼科特、Didier Anzieu、Pierre Fédida、拉康……汲取各家理论所长,而非困于一派之言。
跟随作者的论证过程,我们也可以渐渐明晰游戏客体/或「游玩-物」(L'objeu)的几层面向。第一层,由温尼科特提出的理论:玩具是过渡性客体,代替母亲的缺失,慰藉儿童,并在游玩的过程中获得满足感。第二层,补偿性的objeu,它的功能是补偿对象的缺失所带来的不适,就像弗洛伊德的线圈游戏“Fort-Da”一样,是对场景的再现,将缺失的对象转化为可操纵的对象,将创伤性的影响转化为可控制的影响,甚至转化为享受,这里触及到了游戏的享乐层面。第三层,诗意和隐喻的客体,主体在其中创造了新的意义,颠覆了文字符号语言的编码意义,儿童可以自由的符号化符号本身,从中获得自己的主观创造性。这三个层次并非是一种线性的进程关联,而是重叠的,最终涉及到的是游戏作为去性化的升华活动的功能,根据弗洛伊德的定义,即重新定向性驱力,把力比多投注到具有文化、美学、社会价值的客体上的活动。
小柏
René Roussillon
René Roussillon
勒内·鲁西荣(René Roussillon),1947年生于里昂,精神分析家、心理学家和里昂第二大学的心理学荣誉教授,巴黎精神分析协会成员。著有《快乐与重复:心理过程理论》,《游戏与「在我(游戏)间」》(Le jeu et l'entre-je(u) )等书,编著有《心理学和精神病理学临床实践手册》。
(*此处也补充介绍文中提及很多的温尼科特)
Donald Woods Winnicott
Donald Woods Winnicott
唐诺·伍兹·温尼科特(Donald Woods Winnicott,7 April 1896 – 25 January 1971) 是英国的儿科医生和精神分析学家,在客体关系理论和发展心理学领域特别有影响力。他是英国精神分析学会英国独立小组的领导成员,两次担任英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1956-1959年和1965-1968年))。
温尼科特最为人所知的是他对真实自我和虚假自我——「足够好」的父母——的看法,他从他的第二任妻子克莱尔 · 温尼科特(Clare Winnicott)那里借鉴了过渡客体的概念。他写了几本书,包括《游戏与现实》(Playing and Reality)以及《涂鸦与梦境》和200多篇论文。
翻译:叶梓涛
校对:小柏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Dans Revue française de psychanalyse 2004/1 (Vol. 68), pages 79 à 94
游戏与潜能 Le jeu et le potentiel
游戏与潜能 Le jeu et le potentiel
因此,与电子化的记忆(mémoires électroniques)不同,大脑记忆是不精确的,但另一方面,它有极强大的概括能力。 ——G. 爱德曼(G. Edelman)《意识的生物学》(Biologie de la conscience)
玩,阐释:游戏与生命
JOUER, INTERPRÉTER : LE JEU ET LA VIE
玩,阐释:游戏与生命
JOUER, INTERPRÉTER : LE JEU ET LA VIE
在《意识的生物学》中,著名的意识生物学家G. 爱德曼仿佛顺便提到了大脑记忆的这种特殊性:它是粗略的(approximative)。如果它太精确,太忠实于感知,我们的记忆就会太特异反应(idiosyncrasique),太「黏着于」对事件的感知,它就能不容易转移到当下的其他类似的经验中,它就不能被用来为与当下的遭遇做准备,它就不能提供我们对现实的预期所需要的概括的工作。
历史上的事件和不测风云被我们的记忆所保存,它所记录的东西既能保存事件的痕迹(trace),同时又能使记忆在当下的移情和使用成为可能,这种「归类」(catégorisation)工作使经验适用于当下。为了变得能被使用,必须让过去的经验适应新的需要(actualisée),它必须根据当下被「阐释」(interprétée)。
这并不意味着记忆是不忠实可靠的,恰恰相反,它记录了任何东西和任何方式。这意味着主观经验和我们对它的记忆是为了「被阐释」而被组织起来的,如果没有阐释,没有赋予意义、产生意义、进行更新的心理工作,它们的功能是不可想象的。为了做到这一点,它被保存在一个复杂的形式中,允许几种潜在的阐释:根据翁贝托·埃科(Umberto Eco)的公式,记忆是一个「开放」系统。对调整过去的经验以适应当前情况来说,人类的记忆是必要且不可避免的,它意味着一种阐释,就像我们说一个演员「阐释」一出戏,他给出了他个人的版本,这种阐释使得游戏成为必要。
换句话说,生物学告诉我们,人类的记忆,以及所有依赖于它的生物功能,都有「游戏」,如果没有调整的游戏,没有过去和现在间的来回转换,那是无法设想的。弗洛伊德思想将「后遗性」(après-coup)的重新阐释(ré-interprétation)作为精神分析概念中记忆和回忆工作的基石,对于我们记忆的本质来说,这种归类和重新归类的工作必不可少。
正是记忆的近似性给了心理以自由,迫使生命表现出具有创造性(créativité),而这则需要游戏,使记忆具有象征性的潜力(potentialités symbolisantes)。从生物层面看,对游戏的需求表现出来,从生物层面看,「生命」需要游戏,需要有足够的游戏来实现使其行动所必不可少调整(ajustement)。在生物逻辑学中存在着游戏(bio-logiques),一种游戏的生物学。
这是一般生活的真实情况,更是心理生活的真实情况。当游戏消失的时候,病理性(pathologie)就会出现,「以同样的方式」重复的约束往往会对心理功能产生支配作用,阐释就会冻结。正是当事件是创伤性时,主体惊愕,经验无法流动,记忆固定了它,它变得精确、忠实、「写实照相一般」、感知性的,而不及概念分类和概念。它变得「退化性」(dégénérative,反生成),失去了它的生命潜力,它的生命驱力的表达,唤起了死亡驱力的问题,自动化的问题,自我重复「徒劳无益」。
相反,对创伤的转化(élaboration)恢复了阐释的流动性,重新建立了游戏的能力,心理再现的自由流转,联想链的生成性(générativité)。
因此,与温尼科特(Winnicott)一起,我们可以推进这个观点:游戏是治疗工作的模型,是精神分析情境试图重建或促进的心理工作的模型。但这一说法本身并非没有含糊之处。
分析中的游戏模式的模糊与困难
AMBIGUÏTÉ ET DIFFICULTÉ DU MODÈLE DU JEU DANS L’ANALYSE
分析中的游戏模式的模糊与困难
AMBIGUÏTÉ ET DIFFICULTÉ DU MODÈLE DU JEU DANS L’ANALYSE
在法国精神分析中,可能比其他地方更多的是,梦已经成为分析疗程中心理功能的参考模式,至少就成人精神分析而言。M. Fain、A. Green、J. Laplanche、J. Guillaumin 和 C. et S. Botella,仅举几个在这个方向上工作的最有代表性的作者,都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和方向强调了精神分析情景中所提出的心理运作条件是如何诱发一种特殊的,接近于梦的心理状态的会话。运动机能被暂停,现实感知被稀释或中和,分析者不在视野中,条件兼备,就像在梦中,并带来了心理矢量化(vectorisation)的回退路径,引发了无意识再现的准幻觉式的激活(activation)......所有这些现在都很明确了,所以我就快速提过。
然而,这种模式在某类治疗类型中最为贴切,即选择性地针对一种围绕符号联系(liaison symbolique)模式而充分组织的心理功能。安德烈·格林强调需要补充这些符号性联系失败的某些临床情况,在此些情况下,唤起创伤性梦境、恶梦、白梦、梦游或其他形式的夜间精神活动摆脱了伪装欲望的梦境实现模式。尽管精神分析情境为心理提供了约束和支持,但运动机能和知觉的中止可能无法促进梦境模型上的符号化功能,甚至会激起去符号化的破坏性(destructivité dé-symbolisant),一种创伤型的状态可能会威胁到它的实现。梦境模式(le modèle du rêve),无论它可能继续出现,因此也遇到了第一个限制,它要求被扩展到其最初的定义之外,而也许是涉及范式性修改的一点。
另一方面,对儿童,甚至青少年的精神分析工作,以及所有或多或少基于心理戏剧表达的精神分析实践形式,在梦的模式中进行思考的效果很糟。因为在其中,知觉和运动技能会被使用,且往往是相当核心,在场(présence)和遭遇(rencontre)的逻辑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考虑到该模式在思考典型治愈中所观察到的全面性的不足,以及在思考分析延伸方面的不足,导致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去寻找梦境模式的替代或补充。除了对他们来说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儿童精神分析学家外,一些以萨德·费伦奇(S.Ferenczi)和温尼科特为代表性的成人精神分析学家[2],也在游戏的参照中寻求这样一种替代的模式。
然而,提议把游戏作为思考精神分析和治疗工作「一般」的模式,并非不存在某些模糊性,和引起某些问题。
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关于了解,当我们提及游戏时到底意指什么,以及在这样的模式中必须赋予的为游戏所指定的意义。游戏是指游玩的行为(le comportement ludique)、作为被第三方观察以及可被观察到行为的游玩活动,还是指某种类型的心理功能,其以有一些具体的参数为特征。换句话说,当游戏被当作分析心理工作的模型时,它是明确的,形式化的游戏(jeu formel),还是它的心理内部的类似物,一种心理运作的类型,也就是说,游戏是否被当作某种心理工作的隐喻。在儿童精神分析的实践中,只要游戏和游玩活动在治疗中表现出来,治疗和游戏的叠加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是在成人精神分析的实践中,或者在所有不正式涉及游戏的分析实践形式中,认为游戏的模式是一种启发式的模式,这意味着什么呢?
甚至在那些游戏占据明显位置的实践形式中,如在与儿童的工作中,是不是也有一种模糊性,即「游戏模型」的概念中所暗示的游戏并不是在治疗中进行的显性的游戏。在治疗中进行的游戏,有意识的、显性的游戏,在所玩的游戏中「被阐释」的游戏,首先是一种行为的形式,一种「活动,在建立重复的或定型的游戏形式的情景中表现出来」。把游戏作为心理工作模式的想法,更多是意味着通过游戏和在游戏中再度上演(reprise)和转化的工作的概念;它意味着,通过显性的游戏,另一个游戏同时被隐藏和揭示,一个关键,就像在梦中和根据弗洛伊德的术语的「另一个场景」(autre scène)被编织出来。
因此,才有了一种游戏和另一种游戏。
有作为显性行为的游戏,它可以被限制,被定型,而没有真正的创造力,被封闭在这样的规则中,没有为真正的心理工作提供空间,它不变地阐释着同一个场景,同一个情景。所有儿童治疗师都熟悉这些「游戏」,这些游戏从一个疗程到另一个疗程无休止地重复,持续数周甚至数月,这些游戏似乎没有任何动静,在这些游戏中,对情况的掌控似乎是最首要的,聚集了移情(transfert)的本质。对世界的阐释是不变的,被固定的,重复的。人际关系交往(理论)分析师描述了「剧本」和「游戏」[3],在这些情况下,成年人仍然陷入其中,与不同的伙伴重复,总是倾向于重组,并构建倒错的的关系形式,使任何相遇(rencontre)都有相同的特定、封闭的「路线」(tour)。
还有一些游戏的形式,在其中则相反,一个基本的无意识的心理关键被转移,「开放」(ouvert),就像我们说拍卖会是「开放」的,字面意思地「使用」(mise en jeu,译注:法语这个词组直译为「投入游戏」),在游戏中上演,寻找再现与意义,温尼科特称之为「玩」(play)。然后,游戏可以具有「探索」(exploration)主观情境的价值,探索其未知的、甚至是神秘的面孔,具有「创造」和「再造」主观性的价值,发现,或发明出与自己或他人关系的新形式,对自己或世界的重新阐释。
在游戏中具有操作化的东西,对主观经验的符号化过程有贡献的东西,在游戏中必须「听到」(entendre)的东西,必须在游戏中「转移」的层面上加以把握,正是在无意识问题层面上,必须定位并尝试释放它,正是在它所隐藏的尚未发生的潜力中,有待探索,有待发现,在它明显表达的潜在信息中,必须观察或倾听它。倾听游戏中的关键(enjeu du jeu),在显性的游戏中潜伏的、潜在的游戏,这是心理治疗或精神分析空间的特点,正是这种无意识关键的缓慢揭示和塑形,构成了「符号化」的游戏的精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游戏可以为精神分析的工作提供一个模型。
提出游戏模式作为精神分析工作的模式,并不是要把游戏迷信化,把它作为一种先验「自在」模式(a priori, en soi),而是要把它设想为一种媒介,一种手段,一条「进路」(voie royale),一种对梦的工作方式的替代,且要辩证地看待与梦境的相比的,对主观经验的把握和转换过程,以及对梦境的阐释过程。因此,它要提倡一种有两个层次的游戏方法,即两个规定性的层次。
一方面,在不同的「症状」表现中,在不同的重复行为中所倾听或听见的,这种潜在的游戏一直处于展露(déploiement)的痛苦中,这种游戏一直无法找到它的游戏形式,继续呈现为一种不变的,被固定的, 固定的行为心理的构成,而非提供再现性的价值。在心理治疗空间中使用游戏的模式,就是倾听那些可能的游戏,它们是症状性重复呈现的「痛苦」过程的再现或表达。
另一方面,允许那些开始如其自身而表现出自己的游戏,释放它们对试图呈现的主观经验的探索性和适应性的潜能。而要做到这一点,就要为游戏的展露提供可能的条件,使它有可能在临床遭遇中找到揭示隐藏的或潜在的关键的材料,即它所包含和忽视的潜在性(virtualités)。
举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问题。
一位儿童心理治疗师必须在咨询中见到一个八岁的女孩。他已经准备好了一张桌子,摆好了纸片、铅笔和记号笔,并想好了以涂鸦模式(mode du squiggle)进行初步咨询。
(校注:squiggle game,温尼科特发明的开放性无具体规则和限制的涂鸦游戏,旨在运用投射的机制使得分析师可以和儿童沟通,并使得儿童可以发挥其想象力和象征能力。在这一游戏中,首先,由治疗师在一张纸上画出一条曲线,然后让孩子完成这第一次的「涂鸦」,在此基础上完成一个小小的再现性质的画。然后孩子画出他/她自己的另一条曲线,由治疗师完成它。游戏依次重复数次。)
小女孩抓起一支铅笔,扔在了地上。向我报告这一幕的治疗师评论说:「她在攻击框架」(attaque le cadre)。我更加不解了,我回道:「或者她在玩另一个游戏」。我想到的是温尼科特文章中的抛掷游戏(jeté-ramené),即刮刀游戏,这是框架的「典型」游戏的形式之一,在这个游戏中,与他人的连接和阻抗会遭受考验。
(校注:刮刀(类似刮黄油的那种金属刮刀)游戏,刮刀也是一个过渡性客体,第一个「非我的第一个所属物」,温尼科特通过小孩对这个金属异质的反应来观察他或她对主体和客体边界感的区分,另一阶段,通过观察她拥有以及抛弃这一所属物的过程来看小孩与他者的关系。)
在他的这个游戏版本中,我在其他地方详细研究过(R. Roussillon, 1991),温尼科特(1948)治疗一个13个月大的女孩,她处于创伤后的状态中:所有的游戏都停止了,她不再睡觉,整天尖叫...…
温尼科特在这个孩子的愤怒中「听到」了对接触、对一致性的寻求,听到了对一个对象的寻求,一个 「调节它自身的对象」,一个能够抵制充斥着她并威胁到一切的破坏性的对象。他允许自己被咬,并攻击手指,因为他想象传染性胃肠炎已经「攻击和咬」了婴儿,但最重要的是,他允许自己被咬,就好像这种咬只是笨拙的轻咬,只是一个不成熟的讯息。他给女孩提供了一把闪亮的刮刀,他提议把对他的手指所「玩」的东西转移到锅铲上,他将所表现的暴力「阐释」为一种退化性的游戏潜能。在三次二十分钟的这种倾听儿童行为的治疗中,温尼科特能够恢复儿童的游戏能力,她可以探索自己的身体,重新获得游戏的能力。
孩子的咬人和尖叫不是游戏,而是精神病理学症状。另一方面,它们掩盖了一个潜在的游戏,一个在使儿童混乱的疾病发生时无法展露的潜在游戏,一个其形式已经退化为被观察到的表现的潜在游戏。正是在听到这种潜在的游戏,超越显性的内容,精神分析的倾听可以被采用,正是在于允许它找到了「游玩的」的表达形式,使得精神分析的干预发挥最大的相关性。
在温尼科特含蓄地指出的路线中,我提议(R. Roussillon, 1983, 1985, 1988, 1995年恢复)描述在治疗期间伴随着符号化工作的「典型」游戏形式,这些游戏组织了移情的形式和阐释的工作,甚至是阐释的「风格」。
游戏的心理功能
FONCTION PSYCHIQUE DU JEU
游戏的心理功能
FONCTION PSYCHIQUE DU JEU
为了理解游戏的符号化的潜在性,我们必须从心理经验的相对神秘的状态出发。这是一种更经典的精神分析方式,来处理我们在引入思考时提到的记忆的「粗略」特征的问题。
有「意义」的主观经验,即投注(investie)和标记的(marquante),弗洛伊德(1900)称之为心理的「原材料」(matière première),就其性质而言是复杂的,并且由于这种复杂性而可能造成混乱,它不是立即 「被给予」的,它需要一个区分和攫取的工作,它需要被转移以把握、解凝和衍化为其成分。主观经验实际上是混合体(amalgam)[4],是「结合的作品」(œuvre d’union),它是多脉冲的、多感受、多知觉的、多审美的,它混合了自我和非自我,内向感知和外向感知,自己的部分和他人的部分。在它能够被领会吸收之前,而且为了被领会,逐个片段地被消化,它必须被解凝和衍化,被部署和 「展开」,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在其不同的奇异点中被转移和反映。在任何情况下,主观经验不是从一开始就被整合,也不是立即被整合的;它需要不同的时间,不同的阐释。精神分析的经验所描述的用心治疗的工作(perlaboration)的工作不是治疗特定的工作,而是心理运作的过程本身。但这项工作遭遇复杂性,且根据不同的时间展开进行。
近年来,人们强调,在生命的早期阶段,自我的接触和情感时刻的定位是通过对他人(主要是那个年龄段的母亲)所能反映的东西进行映射和镜像来实现的。最初,对自我状态的把握和定位是以他者为中介的,以他者的映射为中介的;它必然要通过他者的「镜子」,其形成(formations),当然也包括他者镜子的 「变形」(déformations);这是移情的第一个形式。
在生命的早期阶段特别真实的东西在整个生命过程中继续存在,即使发生中介化的形式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和转变。我们将他人的「镜像识别」功能内化,然后可以将其转移到不同的情境中,这些情境再现了我们「生产」我们内部状态的代表物和表征的装置。
因此,正如弗洛伊德早在1894-1895年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说出、展示或让对方感受到我们必须听到、看到或感受到的自己。为了重新呈现我们不同的内部状态,我们需要呈现它们以反映它们,首先是在他人的帮助下,然后在我们充分体验和内化其镜像功能后单独呈现。
事实上,在把握我们的主观经验方面,我们至少应该描述两个阶段,无论它是当前的还是更具有创伤性的。
在第一阶段,可以说是我们心理生活的「第一次紧急情况」,我们必须确保「抓住」我们体验到的重要东西,确保我们「抓住」伴随着心理经验的投注的冲动。这就是称之为纠缠(intrication)的整个问题,也就是我上面提到的「混合体」的首要联系。
「过度的」心理经验,这种原初心理「维持」(maintenance),威胁着心理的完整性,并反过来激起一种倾向于避免或疏散它的反应;它代表着一种「创伤」威胁,心理对这种威胁发展出「防备-刺激」(pare-excitations)系统。因此,主观经验的铭写从一开始就只能妥协,因其异常性质,以及心理对这种威胁的防御反应。英国作者们强调了行使心理的主要必要性所必需的「遏制」(contenance)功能:避免主观经验的泛滥和捉摸不透所代表的不愉快的来源。法语国家的作者们更愿意跟随 D.Anzieu,描述这样实施的不同「精神包裹」(enveloppes psychiques)。A. 格林又提出了「精神之手」(main psychique)的比喻,来描述我在这里所说的心理的「维持」功能。这个概念坚持认为,动因因此而发挥作用,以及这种对主观经验的第一次「驯服」(domptage)(Freud, 1895-1925)中的心理活动。
在第二阶段,如此「驯服」的经验必须被重新掌握和重新呈现,它必须被整合,但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必须被「呈现」给心理。这就是游戏问题的全部意义所在。心理将不得不再次「给出」自己主观经验,为了做到这一点,它将不得不「放手」,并且把它收回,以不同的方式重新看待它,再次呈现它,以便能够以不同的方式再次呈现它。
正是这个过程中的这一时刻决定了游戏时间的特点,它赋予了游戏的意义,以及它在心理过程中的位置和功能。这段重新认知的时间之前必然有一个「放手」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要的维持功能必须让位给掌握经验的其他形式,让位给后者的「符号」形式的铭写和整合。
符号化游戏的条件:自由和安全
CONDITIONS DU JEU SYMBOLISANT : LIBERTÉ ET SÉCURITÉ
符号化游戏的条件:自由和安全
CONDITIONS DU JEU SYMBOLISANT : LIBERTÉ ET SÉCURITÉ
可以想象的是,主导将主观经验重新投入游戏可能性的「放手」的经验,在没有事先条件的情况下是无法进行的。这是一种「危险」的体验,因为心理同意抛弃它的防御,抛弃使它能够驯服距离的原初经验的防御。因此,这种体验带来了一种风险,即最初的溢出威胁将在其重新呈现的时刻被重复或重新激活。这种风险只有在存在一些特定条件时才会被遏制,这些条件将标记在初始情境和它在游戏经验中的重新呈现之间的差异。
原初经验是强迫的,主体没有选择它的发生,也没有选择它的性质和复杂性,它是由他的生活和它所暴露的环境强加给他的。而且,即使某种欲望可能导致他把自己暴露在其中,即使必然有一种驱力运动掌管了它心理的呈现,他内在的幻觉,这一经验的发生也是由事件强加给他的,它不取决于他,欲望不是万能的,它的实现需要其他的中介或有利的条件。
当然,「维持」的反应的建立已经是为了「夺回控制权」,已经是为了尝试夺回游戏的主动性、控制权,甚至掌握权,使其内化成为可能。恢复的经验,重新把握的经验,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受到强迫,它不是「来自外部」强迫,如果毫无疑问有某种强迫在其中运作,它是从内部表现出来的,而不再是作为一种内部的「欲望」或「驱力」呈现出来的。主观条件已经改变,主体可以感觉可以「自由」或潜在自由地,重拾原初经验的「给予」。
没有这种程度的自由就不可能有游戏,没有以某种形式的,一种不受外部要求、不受「外部压力」自由的主观考验,那就不可能有参与或移情。这就是为什么所有真正的符号化和内化空间,都在其框架内建立了这种自由,并通过其规则规定了这种自由:自由游戏、自由绘画、自由联想、自由建模、自由表达......这与总是或多或少地包含某种形式的强迫/约束的教育系统不同。
「外部」自由对于「发现」、发明和接受、吸收来自内部的约束、符号化及其规则是必要的。为了对规则的发明和尊重能够实现对自由的另一面的夺取(conquête)——内在的那一面,自由是必要的。这一面向的获得是在游戏中和通过游戏得以实现的。自由必须是构成游戏空间的第一个「赠礼」,但它也代表了游戏的范围(horizon),游戏必须使之成为可能的夺取,它的核心关键。
自由必须是「发现-创造」(trouvée-créée)的,为了被创造而发现,为了被夺取。这也是为什么对玩的事实本身不能有任何限制,不玩的权利也是自由游戏的前提条件,不通过游戏符号化的权利是通过游戏符号化能力的前提条件。也正是当这种基本的自由没有被夺取,还没有被夺取时的自由,而这些「玩家」才从事强迫性和刻板性的游戏,从事「受约束的」、重复性的游戏,没有创造性,除了先决的夺取,和对自由的亲身试验之外,没有其他关键之事了。
真正的「放手」只有在自由中才能发生,没有自由,它只是一个投降和失败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没有某些形式的安全是不可能的。安全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在外部和内部现实之间形成一个「中间」空间(espace « intermédiaire »),并使其运作的过程能够在没有过度风险的情况下展露。安全是必要的,以便这个中间空间能够提供其「过渡」(transitionnelle)价值,这对于游戏的创造性方面的发展、对于探索性的经验、对于发明和发现被符号化的经验中存在的潜力来说,都不可或缺。
过渡过程 PROCESSUS TRANSITIONNEL
过渡过程 PROCESSUS TRANSITIONNEL
我们已经达到了游戏的精神分析理论的困难点,也就是我们遇到其过程的「悖论」,构成它的乌托邦的那一点。
为了发挥作用,让我们说,「在日常制度下」,心理需要保持内部和外部现实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幻觉和内部再现,另一方面则是感知。一种「审查」(censure)和各种「检验」(épreuves,根据弗洛伊德的概念)具有保持活跃的拓扑屏障(barrière topique)功能,将内部世界与被认为或定义为外部的感知世界分开[5]。当内部和外部的现实混合在一起时,主体就会成为心理混乱的威胁的猎物,而这种混乱包藏着重要的创伤性可能性和猝倒的威胁。这就是为什么保持内部和外部的拓扑差异是我们心理运作的首要紧迫性之一。
(校注:检验:使主体分辨外部刺激和内部刺激的区别、感知到的外部世界和他自己表征的世界的区别的过程 / 审查:禁止一些无意识欲望、禁止一些可以进入到潜意识-意识层面的形成的功能。)
为了使游戏具有价值和意义,为了使它能够发挥其变形改造的潜力和符号化的能力,有必要至少部分地解除拓扑对立。内部现实在对外部现实的感知下被「安置」在其空洞之中。用元心理学的术语来说,我们会说,幻觉,对投注的神秘的主观经验的幻觉性再现,即对于将其置入游戏的、运动,要求或需要,将叠加在对外部物体、具现化对象、其他主体或无生命对象的感知上。幻觉在感知中发生,这是根据弗洛伊德(1938)很晚才提出的直觉,由温尼科特(1958)在「发现-创造」过程的概念中被真正发展起来。
但是这个过程,一个内部和外部现实因此「叠加」并紧密交织在一起的过程,在处于上述的混乱威胁的情况下无论如何都无法进行。游戏过程中的「利害关系」涉及一种风险,必须由特定的安全条件来平衡。隔开内外部壁垒的解除,即使仅是部分的,其这所隐含的脆弱性和心理上的不稳定性,也只有在满足某些环境条件时才能面对。
一个人不是任何条件下都能游戏,需要一个基本的安全感来面对进入游戏所带来的风险。游戏的时刻是一个「神圣」的时刻,必须得到环境的尊重,特别是在它所暗示的,以及必须被容忍的悖论中得到尊重。正如温尼科特所强调的那样,其中最主要的一点是,游戏者不会被置于不得不决定他或她所实施过程的拓扑位置上。正是从环境对这一拓扑对立悬置的接受中,对象在「外部」和「内部」之中,从这一接受的共同状态和由此封存的「契约」中,在此基础上,游戏才能发挥其全部价值。
因为在幻觉和感知的对立之外,在「呈现」和感知的对立之外,游戏的经验构成了一种新的经验类型,即主观的幻觉(l’illusion subjective)。它是幻觉经验的本质,是幻觉之于生命过程的价值,它赋予幻觉以现实性,使它能够找到一个领域,在其中它具有符号化的全部价值。通过紧密叠加,通过交织幻觉和知觉,游戏的经验「创造」出来,并允许发现纯「主观」对象(内部现实的对象)和「客观」对象(外部现实的对象)之间的中间对象的存在。这种新型的对象定义了一种新型的现实,一种既非主观也非客观,或者说既是客观也是主观的,赋予主观性以客观性的新型客体,它允许主观性感知自己的客观性层面,允许它感知自己是主观的「现实」,是心理的现实,是符号和符号化的现实。
因此,「游戏」中固有的幻觉是一种基本的主观经验的起源,它使我们能够遭遇、感知和适应这种特殊形式的现实,即符号的现实和符号化的过程。它打开了通往「神圣」的大门。
但它也是一种特殊的、特定类型的快乐(plaisir)的起源,这无疑是「升华」的原型的快乐。在游戏中,正是在升华中,中心的过程中,正如我们刚才所强调的,假定了一个幻觉过程和一个感知的叠加(superposition)。但这种叠加引发了驱力对象的转变,在被感知的对象中产生了幻觉,因此,符号的形成为驱力发现了一个新的驱力「目标」。再现,以及在再现的过程中获得的快乐成为驱动的新目标。再现不再是定位、以及识别驱力对象的手段,它成为满足驱力的东西,通过它,驱力完成了自身,它成为驱动性活动的目标。
拉康(J. Lacan)提议将这种快乐确定为「欣喜」(jubilation)的情感,当它涉及到镜子中的自己的表现时:「欣喜的承担」(校注:表示主体在镜前承担了、接受了自己的形象)。我追随A. 卡雷尔的说法,当超越了「自我的呈现」,他从「欣喜」的概念中定义了游戏的具体快乐。欣喜不是性高潮,根据温尼科特的公式,它应该是「自我的高潮」,是自我对其代表身份的承担,它是经验的二次去性化发生的过程。
正如我顺便提到的,正因为游戏可以允许驱力在再现活动中,达成表征,因此游戏甚至是升华活动的模板。正如弗洛伊德在1907年所预见的那样。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升华不能仅仅通过其社会或文化特征受到重视和认可的,显然的、形式化的特征、行为或活动来定义,而甚至在精神分析学家中也经常出现这种情况。这样的定义会倒向对生或死的升华的描述。
不存在「自在」的升华活动。相反,在我看来,必须从心理运作本身、从其无意识的关键和这些的特殊性、从其在心理中的功能来评价升华。从这个角度来看,升华将是这样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驱力获得了再现,简单的再现作为驱力的目标,并在感知的对象中「具现化」,通过幻觉过程和感知过程的混合,而成为符号。
这导致我们提出对象和游戏的问题,游戏使用的对象,以及作为对象的游戏本身。
游玩-物和它的选择 L’OBJEU ET SON CHOIX
游玩-物和它的选择 L’OBJEU ET SON CHOIX
在成为一个符号之前,物质对象成为一个「游玩-物」(objeu,或译作,游戏-客体,原词由 objet 修改后缀为 jeu游戏构成)。我从诗人弗朗西斯·庞日(F.Ponge)那借来这个词,但我使用它的意义与 P.Fedida 完全不同,后者也是从诗人那里借来的。「游玩-物」(objeu)是游戏的对象,是我们玩耍的对象,是我们在玩耍时与之玩耍的对象,但它也是作为心理的对象的游戏,作为心理投注的对象,以牵涉其关键。
多亏了幻觉,「游玩-物」将具有它的心理价值和意义,由于感知,对象将能够被物质地把握,多亏了运动机能,它能够与它一同被寄予主观经验的东西被探索。多亏了由于其所有的感知-运动特性(perceptivo-motrices),它将开启一个符号化的进程,并对相关的主观经验进行转化。正是从主观经验到物质对象的移情(转移)过程,以及它使之可能的游戏,才会使其新陈代谢和主观内化成为可能。因此,「游玩」的经验提供了一种主观经验的「新」铭文,它形成了一种新的主观经验类型,即主体的原初经验的转化。(校注:例如和主体父母的关系,在原初经验中主体属于被动的位置,要去接受父母的缺席、对其情感和行为等等)
然而,可以想象的是,为了履行其功能,该游玩-物必须拥有某些属性。适合于主观经验特殊性的幻觉感受的对象,必须向知觉呈现在第一经验中存在的,或与之类似的一些感觉品质。对游玩-物的感知必须与幻觉过程「前来相遇」。一个人不容易在一个锋利的,尖锐的,粗糙的和有伤害性的物体中产生幻觉,体验到乳房的柔软!
同样可以想象的是,根据时机和原因的需要,物体的属性必须有所不同。主体的内化可能要求是主体和游戏过程「激活」游玩-物,它没有独立于主体的万物有灵论所赋予它的「客观」生命。相反,有时会要求游玩-物带来一种「分叉」(bifurcation),一种惊喜,一种只有另一个主体才能引入的创造力和自身的生机:只有主体间的游戏才能提供这种可能性。
游玩-物的形式和美学特质可以促进体验幻觉的心灵投射(projection animique),但有时必须体验的首先是游玩-物的「可转换性」(transformabilité)。于是,对那些没有自己的形式而「可转换」的物体产生了一种特殊的吸引力,它们「自由」于自身的形式,为主体提供了他或她想要的,赋予了它们的形式的自由。有不定的「无定形」(informes)的心理状态[6],这需要类似的游玩-物,有初级形式的经验,邀请探索其变形/形式转变。因此,如果有一些游玩-物以自己的形式为价值,通过它们特定的感觉属性「诱惑幻觉」,那么其他的游玩-物则必须提供它们的「可塑性」(malléabilité, M. Milner, R. Roussillon),以允许体验「转化的」对象(C. Bollas)。
(校注:可塑性在于,虽然诊室里的玩具已经是大人、玩具制造商符号过的了 ,但是自由的游戏还是可以允许小朋友有再次符号它的可能性。如在临床的过程中,你觉得这些医药箱的听诊器是用来听诊的,但是可能好多小朋友把它当吸管啊,围栏一样玩,那这个时候分析师就不应该强迫它使用这一玩物的既定功能,而是顺着它的思路进行符号化的游戏)
我对后者特别感兴趣,因为在我看来,它们使经验成为可能,这正是符号化经验本身的原型,因此这些「可塑」、「可转换」的游玩-物就象征着符号化活动本身,它们「符号化着符号化」(symbolisent la symbolisation),它们允许游戏中显出的符号化经验反映其自身。
自我符号化和反思性
AUTO-SYMBOLISATION ET RÉFLEXIVITÉ
自我符号化和反思性
AUTO-SYMBOLISATION ET RÉFLEXIVITÉ
无定形的游玩-物不仅允许玩家重新-呈现和转换主观经验,而且还允许他「反思」自己作为玩家的活动,它们使处理游玩自身的事实成为可能。事实上,正是通过变形/改造,通过重复变形和重塑的经验,主体开始能够通过游戏反思他自己的符号化活动,他开始意识到它,并因此开始能够内化它。
仅仅符号化是不够的,符号化而不自知,就像茹尔丹先生(Jourdain)在散文中所做的那样,而这也同样无疑在他的业余时间,在任何说话的主题,在诗歌中也是如此。也有必要能够符号化一个人正在符号化的东西,把符号化的活动作为一个特定的活动来思考,它拥有自己的规律,它「生产」它的独特对象,构想着它的特定空间,特定框架和特定心理的安排。没有这种「自反」(auto)效应,就没有游戏,没有真正的游戏,就不会有游戏在其自身过程中被引导去自我符号化它自己、它自己的可能性条件、它自己的特定规则的过程。
(译注:茹尔丹是莫里哀《贵人迷》(le Bourgeois gentilhomme)中的主角,在剧中,茹尔丹和哲学教师讨论为贵妇人写信,「散文的东西就是韵文;凡不是韵文的东西就是散文」茹尔丹说「我原来说了四十多年的散文,自己还一点不知道」)
游戏发明了自己的规则,或者说它在开展过程中根据它的需要,它的重新启动,而发现了这些规律,它依靠自身进程来自我反思和自我「挖掘」。正是在这种「自反」运动中,游戏开始使得调动它和构成它的东西,它所激起并赋予它意义的关键可以被内化(appropriable)。也是在这里,在中间领域被「外在化」的东西开始能够被再次拾起,在内部现实中重新把握,开始被再内部化(ré-intériorisé),或者说,向内投射(introjecté)。
然后提出了另一个剧场,一个其后台和舞台都占据了夜晚私密性的剧场,即梦的剧场,另一个舞台,在这个舞台上,真正的心理表征可以最终自我「生产」,并产生自身的形象,在这个舞台上,对心理和适当的心理生活的夺取达到了它的完成。
总结
POUR CONCLURE
总结
POUR CONCLURE
梦的私人剧场上的游戏不再需要一个游玩-物来自我「生产」,为其「制造」符号,正是内在心理的游戏,监管着睡眠和夜晚的质量,它允许一个人独立于任何其他人和任何对象来「回复」(récupérer),来获得绝对的独立......只要环境关照着必要的寂静。
因此,正如我过去已强调的那样[7],主体间游戏、即与另一主体的游戏、自我主体游戏/与自己单独的游戏、主体内游戏/精神深处的游戏,形成了一个三角关系的局面,多亏了它,心理的「原材料」被符号化、转化,而逐步代谢,并逐步被占有。对于这项工作,心理遵循一个进程,其中外在化(externalisation)、移情(transfert)、展露(déploiement)和外部转变的时刻与重新把握、内在化和内部恢复的时刻交替进行。正是在这种心理脉动之中,游戏必须被铭刻,以获得其全部意义,正是作为这种心理呼吸的时间,它提供了其最重要的功能。这也是为什么,正如弗洛伊德在1920年强调游戏和移情之间的类比时已表明的那样,游戏的过程可以为治疗空间的目标提供一个很好的模型。
Notes
Notes
[1] Article remanié et complété à partir d’une première version publiée sous le titre « La fonction symbolisante du jeu » (in Jouer, in press) dont de larges extraits sont repris ici.
[2] On peut aussi rappeler la tentative de D. Anzieu en 1970 dans son rapport des langues romanes consacré à l’interprétation.
[3] E. Berne, Games people play, stock, 1984, trad. franç. Des jeux et des hommes.
[4] Amalgama qui vient de l’arabe amal al gam, littéralement « œuvre d'union ».
[5] Mes formulations tentent de tenir compte du fait que ce que nous appelons « extérieur » est une catégorie « interne » de l’appareil psychique et donc que la « limite » dedans-dehors est une limite « conçue » à l’intérieur et implique ce que A. Green a appelé la « double limite ». 我的提法试图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所说的「外部」是心理装置的一个「内部的」的范畴,因此,内部-外部的「界限」是内部「设想」的界限,A. 格林称之为「双重限制」(double limite)。
[6] Cf. R. Roussillon, Le transitionnel et l’indéterminé, in Symbolisation et médiation, Paris, Dunod, 2002.
[7] R. Roussillon, La fonction symbolisante de l’objet, in Agonie clivage et symbolisation, Paris, PUF, 1999.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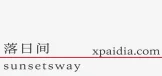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