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本文为1990年海因茨·冯·福斯特在巴黎的一次家庭治疗会议上所做的开幕演讲,会议主题为「伦理、意识形态、新方法」(Ethics, Ideologies, New Method)。福斯特从控制论和二阶控制论(点击阅读关于二阶控制论)切入,探讨形而上学(metaphysics)、对话学(dialogics)和伦理学(ethics)之间的关系。全篇虽然涉及哲学、语言学和控制论议题,但福斯特为了避免晦涩抽象,尽量使用能产生实感的案例和语言。并且最终指向一个本质的经典问题:人的选择、自由与责任。
那么福斯特作为一名物理学家、哲学家和控制论者,怎么会和家庭治疗和心理咨询产生关联呢?这要先从家庭治疗(family therapy)说起,它是心理咨询的一种,起源于19世纪英美的社会工作运动。家庭治疗师通常会同时为几名家庭成员咨询,通过识别成员间的习惯性互动模式,找到问题改善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译注:人类学家、心理学家、梅西会议的重要成员)和杰伊·海伊(Jay Haley)等人将控制论和一般系统理论引入家庭治疗。这使治疗过程不再注重关于个人历史经验的个体心理学,因为这种线性因果/归因类的方式,对解决几个个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几乎没有临床效用。治疗师更倾向于使用循环问题评估(circular way of problem evaluation)的方式,从循环因果的角度,看待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和反馈如何维持或强化既有问题。这往往能帮助治疗师找到家庭成员自己都未能注意到的关系互动模式,并以此作为治疗的要点。因此家庭治疗师通常要具备识别系统与模式、协调和对话的能力。这种处理复杂动态系统问题的思路,极大受到了控制论的启发。
而从家庭治疗师的角度看来,治疗过程中的一个二阶问题也由此浮现:治疗师既是家庭的外部观察者,也是介入家庭关系之中的治疗者。那么他如何评估自己的治疗产生了什么效果?此时,他就需要一种二阶的视角:不仅观察被治疗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变化,也要观察自己的治疗行为在互动中产生的影响。或者用福斯特的语言来讲,治疗师要观察自己的观察和行为。其中的自我指涉循环(self-referential loop)正是二阶控制论中的重要议题。
我认为,以上可以看做这篇演讲的起点。
当然,在福斯特在此想说的远比家庭治疗更多。在他看来,自我指涉循环虽然是经典的逻辑悖论(例如罗素「我是个骗子」的悖论),却也包含着人的自由的新可能。当我们每一次使用「我」这个最短的自我指涉循环时,都是在悄然的变化中决定着那些「不可判定之物」(undecidable question)——我决定相信什么?我决定做什么?我决定成为怎样的人……伦理学、形而上学和对话学也在此过程中浮现。
二阶控制论在这种认知范式转变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一阶控制论中,自适应(selg-regulation)、内稳态(homeostasis)这些概念解释了个体(系统)与既存的外部世界相伴相生的互动关系。而在二阶控制论中,外部世界如何显现,则大部分取决于个体自身的模式与选择。
自由就蕴于选择的自觉之中,它既是礼物,也是负担。因为,责任是自由这枚硬币的背面,相伴相生,不可逃避。
最后,是一点阅读指南,如果正文不是你喜欢的打开方式。你也可以选择直接跳转到访谈部分,其中福斯特用生动的口语讲述了他和控制论的故事。
海因茨·冯·福斯特 Heinz von Foerster
海因茨·冯·福斯特 Heinz von Foerster
1911年11月13日出生于维也纳,曾在维也纳大学学习数学、物理学和逻辑学。1944年在布雷斯劳大学获物理学博士学位。二战期间,他很好地隐藏了自己的犹太身份,在纳粹政府治下幸免于难。1949年前往美国,出席了同年的梅西会议,做了题为《记忆的量子力学理论》(Quantum Mechanical Theory of Memory)的演讲,并编辑了1946年到53年间梅西会议的论文集。福斯特随后任教于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电气工程系。1958年创立生物计算机实验室。该实验室是未来二十年里控制论和认知科学的创新中心。在智利皮诺切特军事政变之后,他曾与斯塔福德·比尔一起营救智利的同事与朋友。1976年,福斯特退休后一直在推动控制论的研究与发展,2002年10月2日,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佩斯卡德罗去世。
伦理学与二阶控制论
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伦理学与二阶控制论
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
海因茨·冯·福斯特
原发表于《家庭治疗的系统、伦理、观点》,Y. Ray et B. Prieur (eds.), ESF editeur, Paris, pp. 41–55 (1991)
尊敬的女士们、先生们:
我为本次会议组织者的慷慨解囊而感动,他们不仅邀请我来到光荣的巴黎,还让我有幸在全体会议上做开幕演讲。他们希望我的演讲以「伦理学与二阶控制论」(Ethics and Second-Order Cybernetics)为题,我对组织者们的这一巧思印象深刻。说实话,我从来不敢提出这样大胆的题目,但必须说,我很高兴为我选择了这个题目。
在我离开加州前往巴黎之前,其他人充满羡慕地问我,我在巴黎要做什么?谈什么?当我回答「我将谈谈伦理学与二阶控制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疑惑地看着我,问道:「什么是二阶控制论?」但好像没有关于伦理学的问题。当人们都在问我二阶控制论而非伦理学时,我如释重负,因为谈论二阶控制论比谈论伦理学要容易得多。事实上,谈论伦理学是不可能的。这一点稍后我会解释,现在先让我谈谈控制论,当然还有控制论的控制论(cybernetics of cybernetics),或称为二阶控制论。
正如你们所知,控制论是这样产生的:效应器(effectors,例如,电机、发动机、我们的肌肉等)与感觉器官相连,而感觉器官又将其信号作用于效应器。正是这种循环组织使控制论系统区别于其他没有这种组织的系统。是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将「控制论」一词重新引入了科学讨论。他观察到,「这种系统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导向一个目标的实现」(点击阅读相关文章)。也就是说,这些系统看起来好像是在追求一个目的!
这听起来确实匪夷所思!让我从其他方面解释控制论是怎么回事,我会引用那些被认为是控制论思想与行动之母或之父的女士和男士们的思想。首先是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译注:美国人类学家,先后提出文化决定论和三喻理论,曾出版《萨摩亚人的成年》,1978年11月15日在纽约逝世),我相信你们都熟悉她的名字。在美国控制论学会的一次演讲中,她说到:
作为一名人类学家,我一直对控制论在我们社会中的效应很感兴趣。我指的不是计算机或电子革命总体,也不是知识对书写的依赖的终结,更不是服饰接替油印机成为持异见的年轻人之间交流形式的这一方面。让我重复一遍,我指的不是这一方面:服饰接替油印机成为持异见的年轻人之间的交流方式。
然后她继续说:
我特别想思考一套跨学科概念的含义,我们最初称之为「反馈」(feedback),然后称之为「目的论机制」(teleological mechanisms),然后称之为「控制论」(cybernetics),这种跨学科思想的形式使许多不同学科的成员能使用一种彼此都能理解的语言轻松地相互交流。
控制论是数学的一个分支,处理控制、递归性(recursiveness)和信息的问题。
控制论是关于有效组织的科学。
控制论是关于合乎情理的隐喻(defensible metaphors)的科学。
控制论对不同的人来说似乎是不同的事物。这是由于其概念基础的丰富性;而我认为这很棒,否则控制论会成为一个有些无聊的问题。然而,所有这些观点都产生自一个中心主题;即循环性(circularity)。也许在半个世纪前,当人们看到这个概念的丰富性,和它对各个领域的一统力量以及对其成果与衍生进行哲学化、认识论化和理论化之时,表现出一种纯粹的欣喜。与此同时,在哲学家、认识论学者和理论家之中发生了一些奇怪的演化。他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看到自己被包含在一个更大的循环中;也许是他们家庭的循环;或者是他们的社会与文化的循环;甚至被包含在一个宇宙大小的循环之中!
在我们今天看来自然而然的观察和思考,在当时不仅难以看到,而且甚至不允许被思考。为什么?因为这将违反科学论述的基本原则,即要求观察者与被观察事物的分离。这就是客观性原则(the principle of objectivity)。观察者的属性不应介入对其观察的描述之中。
我在这里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该原则,以证明其非理智性。如果观察者的属性(即观察和描述)被消除,那就什么都不剩了;没有观察,没有描述。然而,坚持该原则有其合理性,那便是恐惧:恐惧当观察者被允许进入他观察的宇宙时,会出现悖论。而你们都知道悖论的威胁。它们偷偷地溜进一个理论中,就像让魔鬼的蹄子卡在正统的门槛上。
显然,当控制论者在考虑观察和交流的循环性中的合作关系时,他们踏入了一个禁地。在闭合循环的一般情况下,A意指B;B意指C;而C意指A(哦,可怕!)!或者在自反(reflexive)的情况下,A意指B,同时B意指A(哦,震惊!)!而现在,魔鬼的蹄子显示出它最纯粹的形式,即自我指涉的形式:A意指A(震怒!)。
我现在想邀请你们加入我的行列,它在这里不被禁止;相反,在这里人们被鼓励谈论自己。那么还能做什么呢?从观察「外部」的事物转向观察「观察本身」,我认为这源于神经生理学和神经精神病学的重大进展。似乎人们现在可以大胆地提出大脑如何工作的问题。人们敢于撰写关于大脑的理论。
可以说,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数个世纪里,医生和哲学家们一次又一次地推进了关于大脑的理论。那么,今天的控制论者们有什么新东西呢?那便是他们深刻地洞察到,需要一个大脑来书写一种大脑的理论。从此以后,有任何完备性意愿的大脑理论,都必须阐明理论的书写本身。更令人着迷的是,理论的书写者必须对她或他自身做出解释。翻译到控制论领域就是:控制论者由于进入了他自己的(控制论)领域,就必须对他或她自己的活动做出解释。于是控制论就变成了控制论的控制论,或二阶控制论。
女士们,先生们,这一观点代表着一种根本性的变化,不仅发生在我们运作科学的方式上,而且发生在我们如何看待教学、学习、治疗过程和组织管理等方面;我想说,这也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日常生活中的关系。如果一个人首先认为自己是一个独立观察者,眼见世界流逝;而非一个参与性的行动者,身处人类关系循环内给予和获得的相互作用的戏剧之中,那么他就可以看到这种基本的认识论变化。
就第一种情况而言,由于我的独立性,我可以告诉别人如何思考和行动,「汝应……」「汝不应……」这就是道德规范(moral codes)的起源。而在第二种情况中,由于我的相互依赖性,我只能告诉自己如何思考和行动,「我应……」「我不应该……」这就是伦理学的起源。
以上是我演讲中容易理解的部分。下面是困难的部分。我该谈谈伦理学了。如何去谈?从何开始呢?
在我寻找开头的过程中,我偶遇了伊芙琳·雷伊(Yveline Rey,译注:法国临床心理学家,系统治疗师,系统性治疗领域知名学者)和伯纳德·普里尔(Bernard Prieur,法国心理学家、精神分析学家)的迷人诗句,它们润色了会议议程的首页。请让我为你们朗读前几行:
「你说伦理吗?」 喃喃自语已经发展成为一种谣言。 突然间,玫瑰花不再露出刺。 毫无疑问,这是个热门话题。 它同时也是局部的。
让我从外膜(荆棘)开始——我希望,会出现一朵玫瑰。而我开始的荆棘,是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在他的《逻辑哲学论》(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中对伦理学的思考。如果我要为这篇博士论文拟一个标题,我会把它称为《伦理学哲学论》(Tractatus Ethico-Philosophicus)。然而,我不会解释这一选择,我宁愿告诉你们是什么促使我参考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并提出我自己的思考。
我参考的是论文中的第6点,他在那里讨论了命题的一般形式。在讨论接近尾声时,他转向了世界上的真值及其在命题中的表达问题。在他著名的第6.421点中,他得出了一个结论,我将向你们朗读德语原文:
Es ist Klar, dass sich Ethik nicht aussprechen laesst.(很清楚,伦理是不可说的。)
我希望我知道一个法语翻译,但我只知道两个英文译本,它们都不准确。因此,我将给出我的英文译法,我相信同声传译者会把维特根斯坦的观点用法语表达得很好。以下是我对6.421的英译「It is clear that ethics cannot be articulated.」
现在你们会明白为什么我会说:「我的开始将是荆棘。」这是一场关于伦理学的国际大会,而第一位发言者却说,谈论伦理学是不可能!但请诸位稍安勿躁。我刚刚孤立地引用了维特根斯坦的论文。因此还不清楚他真正想说的是什么。
不过还好,接下来我将朗读6.422点,为6.421点提供更多的语境。为了让各位准备好听到接下来的内容,你们应该记住维特根斯坦是维也纳人。而我也是。因此会有一种私下的理解,我觉得巴黎人会和我们维也纳人有一样理解。让我试着解释一下。这是皮尔斯和麦克吉尼斯的英译本中的第6.422点:
当列出一个‘你应该……’的形式伦理规范时,人们首先的一个想法就是:如果我不这样做又怎样呢?
当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我的想法是,并非所有人都会赞同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我认为这反映了他的文化背景。
让我说回维特根斯坦的6.422点,
可是很清楚,伦理与通常意义下的奖和惩没有什么关系……确实应该有某种伦理的奖励和伦理的惩罚,但是这些必须就包含在行动本身之中。
它们必须存在于行动本身中!你们或许记得,我们之前通过「A意指A」的例子和二阶控制论的递归比较触碰了这一自我指涉的概念。我们能否从这些评论中获得提示,关于如何反思伦理,同时坚持维特根斯坦的准则?我认为我们可以。我自己试图坚持以下规则:掌握我对语言的使用,使伦理隐含在我的任何话语之中。(例如,在科学、哲学、认识论、心理治疗等方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的意思是让语言和行动在伦理的地下河上行驶,并确保不会有人被抛下。这确保伦理不会变得明晰,语言不会退化为道德说教。那如何才能做到这一点?如何才能将伦理隐藏起来,让她决定语言和行动?幸运的是,伦理学有两个姐妹,她们允许她保持不可见。她们为我们创造了一个可见的框架、一个有形的组织,我们可以在其中和其上编织我们生活中的小精灵。这两个姐妹是谁呢?一个是形而上学(Metaphysics),另一个是对话学(Dialogics)。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形而上学 Metaphysics
让我先谈谈形而上学。为了让各位立刻看见那围绕着她的令人愉快的模糊性,让我引用英国学者威廉·亨利·沃尔什(W.H.Walsh,译注:英国哲学家,主要从事康德哲学的研究,著有《历史哲学导论》《形而上学的批判等书》)的一篇极好的文章《形而上学的性质》(The Nature of Metaphysics)。他在文章的开头写道:「形而上学中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是有争议的,因此并不令人惊讶的是,那些自称是形而上学者的人,对于他们所尝试的究竟为何,几乎没有什么共识。」
今天,当我援引形而上学时,我并不寻求与其他人就其性质达成共识。这是因为我恰恰想说的是,当我们成为形而上学者时,无论我们是否称自己为形而上学者,事实都是如此。我认为,当我们判定了在原则上无法判定的问题时,就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者。
例如,这是一个可判定的问题:3,396,714这个数字能被2整除吗? 你只需要花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就可以判定这个数字确实可以被2整除。有趣的是,如果这个数字不是7位,而是7000或700万位,你也会花同样短的时间来判定。当然,我还可以提出一些稍微困难的问题,例如:3,396,714能被3整除吗?甚至还有更困难的问题。但也有一些问题是非常难以判定的,其中一些提出于200多年前,但至今仍没有答案。
想想费马的「最后一条定理」(Last Theorem),最聪明的人把他们的聪明头脑花在定理上,却仍未得出答案。或者想想哥德巴赫的「猜想」,它听起来很简单,似乎不难证明:「所有偶数都可以写成两个质数之和。」例如,12是两个质数5和7的总和;或者20=17+3;或者24=13+11,等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哥德巴赫猜想的反例。而且,即使所有进一步的检验都无法反驳哥德巴赫,在能找到一系列能支持他对数字的良好感觉的数学步骤之前,它仍然是一个猜想。我们之所以绝不放弃继续寻找能证明哥德巴赫的步骤序列,是因为这个猜想是在一个逻辑数学关系的框架内提出的。这个框架保证人们可以从这个复杂的连接结晶中的任意节点爬至任何其他节点。
这种思想结晶的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之一是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head)的巨著《数学原理》,他们在1900年至1910年的10年间写成。这部超过1500页的三卷巨著希望一劳永逸地建立一个完美演绎的概念机制。一个不包含歧义、矛盾和不确定因素的概念机制。
然而,1931年,时年25岁的库尔特·哥德尔(Kurt Gödel)发表了一篇文章,其意义远远超出了逻辑学家和数学家的圈子。
现在我告诉大家这篇文章的英文标题,《论数学原理和相关系统中形式上不可判定命题》(On formally undecidable propositions in the Principia Mathematica and related systems)。哥德尔在他的论文中证明:逻辑系统,即使是那些由罗素和怀特海精心构建的逻辑系统,也不免潜藏着不可判定的命题。
然而,我们不需要通过罗素和怀特海、哥德尔或任何其他巨匠来了解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我们可以很容易在周围找到它们。例如,宇宙起源问题就是那些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之一。没人看见它如何起源,这可以从该问题的许多不同答案中看出。有些人说这是大约4、5千年前的一次创造;还有人说宇宙无始无终,因为这是一个永恒平衡的系统;还有人声称,大约100或200亿年前,宇宙从一次「大爆炸」中诞生,人们可以通过大型无线电天线听到其余声。但我倾向于相信庄子的说法,因为他是最古老、最近接近事件本身的。他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
我还可以不停地举出其他例子,因为我还没有告诉各位缅甸人、澳大利亚人、爱斯基摩人、布什曼人、伊博人……他们也会告诉你他们关于的起源的说法。换句话说,你告诉我宇宙如何起源,我就会知道你是谁。
我希望我已经把可判定问题和原则上不可判定问题之间的区别说得足够清楚,以便我可以提出以下命题,我称之为「形而上学的假设」:
我们唯一能决定的,是那些在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
为什么呢?这仅仅因为,可判定的问题已经由两个选择所决定:对提出问题的框架的选择,和对连接我们称之为「问题」和「答案」的事物之规则的选择。在某些情况下,判定过程可能进行得很快,而在其他情况下,则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但最终,我们经过一长串令人信服的逻辑步骤,会得出一个无可辩驳的答案:一个明确的「是」,或一个明确的「不是」。
但是,当我们对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作出决定时,我们没有受到任何强迫,甚至不会受制于逻辑。没有任何外部的必然性迫使我们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是自由的!对必然性的赞美不是偶然,而是选择!当我们对一个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作出决定时,就是在选择希望成为谁。
这是个好消息,但就像美国记者所说的那样,还有一个坏消息。有了这种选择的自由,我们就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对一些人来说,这种选择的自由是来自天堂的礼物;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种责任是一种难以承受的负担。一个人怎么能逃避它、避免它、把它转交给别人呢?
人们用了大量的聪明才智和想象力,想出了一些机制来绕过这个可怕的负担。完整的机构通过科层制度被建立起来,责任在其中不可能被局部化。在这样一个系统中,每个人都可以说,「我被告知要做‘X’。」 在政治舞台上,我们越来越多地听到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e,译注:钉死耶稣的古代罗马犹太总督)的一句话:「除了‘X’,我别无选择。」换言之,即「不要让我为‘X’负责,要怪就怪别人。」这句话显然取代了:「在我的众多选择中,我决定选择‘X’。」
在这里,我会再次提到我曾说过的客观性,它是一种逃避责任的常见手段。各位或许还记得,客观性要求对观察的任何描述中不包含观察者的属性。随着观察的本质(即认知的过程)被移除,观察者就沦为一台复制机器,责任的概念被成功地像变戏法一般消失了。
客观性、本丢·彼拉多、科层制度和其他装置都派生于一种选择,它位于一对原则上不可判定问题之间。这些问题是:「我和宇宙是分开的吗?」意思是每当我看的时候,就像通过一个窥视孔看向一个正在展开的宇宙;或者,「我是宇宙的一部分吗?」意味着每当我行动时,我同时改变着自己和宇宙。
无论何时,每当我反思这两个选项时,我都会惊讶由这一选择造就的深渊之深,它分隔出两个根本不同的世界。这两个选项就是:把自己视为一个独立宇宙的公民,并终会发现世界的法规、规则和习俗;或者把自己看作一个合谋者,正在参与发明世界习俗、规则和法规。
每当我与那些决定成为发现者或发明者的人交谈时,我都对这一事实印象深刻:两者都未意识到自己曾做出过这个决定。而且,当被问及如何证明其立场时,他们构建了一个概念框架,而该框架本身就是对一个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作出判定的结果。
这就好像我在给大家讲一个侦探故事,却对谁是好人/坏人,谁理智/疯狂,谁正确/错误保持沉默。由于这些问题原则上是不可判定的,所以应由我们每个人自行决定,然后承担责任。就像有一个杀人犯,我们不知道他是否患有或曾患有精神病。我们唯一知道的是我了说什么、你了说什么、专家说了什么。而关于他理智还是精神错乱这一点,我说了什么、你说了什么、专家说了什么,是我的责任,是你的责任,也是专家的责任。再一次强调,重点不是「谁对谁错」的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这里的重点是自由;选择的自由。下面是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西班牙思想家)的观点:
人没有本性,而只有历史。人只不过是一场戏剧。他的生活是他必须选择的东西,随着他的发展而形成。而人就存在于这种选择和发明之中。每个人都是自己的小说家,尽管他可以在成为原创作家和抄袭者之间做出选择,但他无法逃避选择。他注定是自由的。
各位可能已经怀疑我把所有的问题都限定为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事实绝非如此。曾经有人问我,我之前勾勒的不同世界的居民(发现的世界的居民和发明的世界的居民)如何能够生活在一起。下面我来回答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发现者很可能会成为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工程师;发明者则是家庭治疗师、诗人和生物学家。只要发现者发现发明者,而发明者发明发现者,两者的共同生活就不会有问题。倘若出现困难,幸运的是,我们有这一整屋的家庭治疗师,他们可能会帮助人类家庭带来理智。
我有一个亲密的朋友,他在马拉喀什长大。他家的房子刚好位于划分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居住区的街道上。作为一个男孩,他与所有其他人一起玩耍,倾听双方的想法和话语,了解他们完全不同的观点。有一次我问他谁才是正确的,他说:「他们都是正确的。」
「但这不可能,」我站在亚里士多德的平台上争辩道,「只有其中一个人可以拥有真理!」但是他回答,「问题不在于真理,而在于信任。」
我明白了。问题在于理解。问题在于理解的理解! 问题在于对原则上不可判定的问题做决定。
在这里,形而上学出现了,并问她的妹妹伦理学:「你建议我把什么带回给我的门徒,即那些形而上学者,不论他们是否称自己为形而上学者?」伦理学回答说:「告诉他们,他们应该总是试图采取行动,以增加选择的数量。是的,增加选择的数量!」
对话学 Dialogics
对话学 Dialogics
现在我想谈谈伦理学的姐妹,对话学(Dialogics)。她有什么手段确保伦理学能在不变得明晰的情况下显现自身?各位可能已经猜到了,那当然就是,语言。我在这里指的不是将空气推过我们的声带时产生的声响;也不是语法、句法、语义、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更不是短语、动词短语、名词短语、深层结构等机制。当我在这里提到语言时,我是指语言这种「舞蹈」。类似于我们说的「探戈舞需要两个人,」我的意思是「语言需要两个人。」
谈到语言的舞蹈,各位家庭治疗师当然是大师,而我只能作为一个业余爱好者发言。由于「业余」来自「热爱」(amour),各位马上就会知道我喜欢跳这种舞蹈。但事实上,我对它所知甚少,只从你们那里学到了皮毛。我的第一课是被邀请坐在观察室里,通过单面镜观察一个四口之家的治疗过程。其间我的同事不得不离开,留下我一个人。我很好奇,当我听不到声音的时候会看到什么,所以我关掉了声音。
我建议各位可以自己做做这个实验。也许你会像我一样着迷。我当时看到的是无声的哑剧,嘴唇的开合、身体的运动、那个只有一次没咬指甲的男孩……我看到的是语言的舞步,仅仅是舞步,没有音乐的干扰。后来我从治疗师那里听说,这次治疗确实非常成功。我想,这些人通过把空气推过声带、开合嘴唇发出的声音,一定有什么魔力。治疗!就是魔法!想想看,你唯一可以使用的药物是语言的舞步和伴奏。语言! 就是魔法!
只有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魔法是可以解释的。魔法无法被解释,只能被实践,这一点各位都很清楚。思考语言的魔力与思考大脑的理论相似。这好比人们需要一个大脑来反思大脑的理论一样;需要语言的魔力去反思语言的魔力。这些概念的神奇之处在于,它们需要自己来产生自身。它们是二阶的。这也是语言通过始终谈论自己来保护自己免受解释的方式。
有一个词表示语言,即「语言」(language)。还有一个词代表字词,即「字词」(word)。如果你不知道word是什么意思,你可以在字典里查一查。我就这么做了。我发现它是一个「言语」(utterance)。我问自己,「什么是言语?」于是我又在字典里查了它。字典上说,它的意思是「通过字词表达。」(to express through words)所以我们又回到了开始的地方。循环性:A意指A。
但这并不是语言保护自己免受解释的唯一方式。为了迷惑她的探索者,她总是在两条不同的轨道上运行。如果你在一条轨道上追赶语言,她就会跳到另一条轨道。如果你追过去,她又会回到第一条轨道上。这两条轨道是什么呢?一条轨道是表象(appearance)的轨道。它穿过一片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土地,而我们正通过一个窥视孔观察这片土地。另一条轨道是功能(function)的轨道。它所穿过的土地是我们的一部分,同时我们也是土地的一部分:土地像我们身体的延伸一样运作。
当语言处在表象的轨道上时,它是一场独角戏。有空气经过声带产生的声响,有单词、有语法、句法和完整的句子。伴随着声响的,是外延的指向:指向一张桌子,发出「桌子」一词的声音;指向一把椅子,发出「椅子」一词的声音。
可有时这并不奏效。玛格丽特·米德通过指向东西并等待适当的声音,很快就学会了许多部落的口语。不过她曾告诉我,有一次她来到一个特殊的部落,指向不同的东西,但总是得到相同的声音,「chumulu」。她认为这是一种原始的语言,只有一个词!但是后来她才知道,「chumulu」的意思是「用手指」。
当语言切换到功能的轨道时,它就是对话性的。当然,这些声音中的一些可能听起来像「桌子」,另一些像「椅子」。但不需要真的有任何桌子或椅子,因为没有人在指着桌子或椅子。这些声音是一种邀请,让对方一起跳些舞步。「桌子」和「椅子」的声音使对方头脑中的弦产生共鸣,这些弦一旦被振动,就也会产生「桌子」和「椅子」的声音。语言隐含在其功能之中。
从表象上看,语言是描述性的。当你讲故事时会如实地讲述:宏伟的船、大海、广阔的天空,以及你的调情使整个旅行变得愉快。但你为谁而讲呢?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正确的问题是:你要和谁一起「跳」你的故事?好让你的伙伴与你一起漂浮在甲板上,闻到海洋的咸味,让灵魂在天空中舒展,甚至而当到了调情的部分时,他会感到一丝嫉妒。
在功能上,语言是建构性的,因为没有人知道你故事的来源。没有人,也永远不会有人会知道它究竟是怎样的,因为「原貌」已经永远地消失了。
各位应该记得勒内·笛卡尔坐在书房里时,他不仅怀疑自己正坐在这里,而且怀疑自己的存在。他问自己:「我在,还是不在?」他用「我思故我在」(Je pense, donc jesuis)或著名的拉丁语版本「Cogito ergo sum」来回答这个疑问。因为笛卡尔非常清楚,这是语言的表象,否则他不会很快就在《谈谈方法》中发表自己的见解,使他人受益。由于他也了解语言的功能,平心而论,他应该喊出「我思,故我们在。」(法文:Je pense, donc nous sommes;拉丁文:Cogitoergo sumus;英文:I think, therefore we are.)
就表象而言,我说出的语言是我的语言。它使我意识到自己。这是意识的根源。就功能而言,我的语言向他人伸出援手。这是良知的根源。而这正是伦理学通过对话得以无形地显现之处。请允许我朗读马丁·布伯(Martin Buber,1878-1965,犹太哲学家)的《人的问题》一书最后几行文字:
思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你会看到动态的二元性,本质的结合。这里有给予和接受,这里有攻击性和防御性的力量,这里有追寻和回应的品质,总是两者合一,在交替的行动中相互补充,共同展示其所是:人(human)。现在你可以转向单独的人,你能认识到他是人,因为他有关联的潜力。当我们将人理解为这样一种存在时,可能会离「什么是人?」这个问题的答案更进一步,那就是:在对话中的存在;在相互存在的双向融合中的存在;在一个人与另一个人的相遇每一刻都在实现和被认知中的存在。
由于我无法对布伯的话作出任何补充,所以以上就是我所有要对伦理学和二阶控制论说的话。
非常感谢。
伊芙琳·雷伊:海因茨·冯·福斯特访谈
Yveline Rey: Interview with Heinz von Foerster
伊芙琳·雷伊:海因茨·冯·福斯特访谈
Yveline Rey: Interview with Heinz von Foerster
伊芙琳(以下简称Y):我第一次听到你的名字,是和「控制论者」(cybernetician)这个词一起出现的。一个人是如何成为控制论者的?为什么最初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在你的人生中,有哪些影响很大的阶段?
海因茨(以下简称H):嗯。一个人如何成为一名控制论者?或许你想让我告诉你,我是如何成为一名控制论者的。
你可能还记得我在演讲时提出的观点:无论我们是否称自己为形而上学者,只要我们判定了在原则上无法判定的问题时,就成为了一个形而上学者。为了回答你的问题,我也可以说,只要我们不使用「because...」(因为......)或「à cause de......」这样的词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使用英语中的短语「in order to...」(为了) ——这句话在法语中更像是亚里士多德的「à fin de...」(在结束时),我们就都是控制论者(无论我们是否称自己为控制论者)。
Y:为什么是亚里士多德的?
H:在《形而上学》中,亚里士多德区分了四种不同的原因,或者用我的说法,是四种不同的借口:其中两种具有时间性,「causa efficientis」(动力因)和「causa finalis」(目的因)。物理学家喜欢前者,过去的原因决定现在的结果:「因为(because)她确实拨动了开关,所以现在灯亮了。」而心理学家更喜欢后者:「为了(in order to)让灯亮起来,她现在拨动了开关。」未来的原因—「为了让房间亮起来,」决定了当下的行动—「现在拨动开关。」
Y:非常有趣,但控制论在哪里出现?
H:物理学家探索的联系是:开关的位置,接触或断开,以及将灯中的电热丝加热到足以辐射出可见光谱中电磁波的温度的电气过程,等等。控制论者探索的联系则是:小女孩希望进入一个有光而非黑暗的房间的愿望,以及感觉运动过程和其中出现的眼——手相关性,使她的手沿着不可预测的路径和一个可预测的结果越来越接近开关,然后她向正确的方向拨动开关,等等。如果人们观察这个女孩,可能会像诺伯特·维纳那样说:「.....她的行为可以被解释为指向一个目标的实现。」在早期的控制论文献中,你会发现一再提到「目标」(goal)、「目的」(purpose)、「终点」(end)等概念。由于希腊语中的「终点」(end)是「telos」,所以我们的前控制论者用「目的论」(teleology)来识别他们的活动。
Y:但是,海因茨你刚刚说我们都是控制论者,无论我们是否这样称呼自己。可当我去拨动一个电灯开关时,我并不是在「探索感觉——运动之间的联系……」等等。我只是走过去打拨动了开关。那么控制论者在哪里呢?
H:(笑)这就是我喜欢女性的另一个原因!你们看透了所有科学的语言迷雾,直指本质。现在……嗯……我还能说什么呢?
我想我可以发明一种新的控制论类别帮自己摆脱困境:「零阶控制论」(zero-order cyvernetics)我认为当活动变得结构化时,我们就有了零阶控制论的案例:当「行为」出现时,人们并不反思这种行为的「为何」(why)和「如何」(how)。他只是行动。这时,控制论是隐性的。
Y:我明白了。但现在「一阶控制论」是什么?
H:一阶控制论出现时,人们会反思自己的行为,反思「如何」和「为何」。然后,控制论逐渐显现,人们发展出诸如「反馈」(feedback)、「信息量」(amount of information)、「循环」(circularity)、「递归」(recursion)、「控制」(attractors)、「内稳态」(homeostasis)、「动态稳定」(dynamic stability)、「动态不稳定或混乱」(dynamic instability or chaos)、「不动点」(fixed points)、「吸引子」(attractors)、「等效性」(equi-finality)、「目的」(purpose)、「目标」(goal)等概念,诸如此类。换句话说,我们达成了「早期」控制论的整体概念机制,即一阶控制论;或如我所说,被观察系统的控制论。
Y: 让我回到第一个问题。你是如何接触到控制论的?
H: 非常简单。控制论向我扑面而来;因为我的英语词汇量最多只有25个单词。
Y:这说不通,亲爱的海因茨。你必须解释得更清楚一些。
H:好吧。亲爱的伊芙琳,那么我们回到必须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必须回到1948年,当时奥地利的部分地区仍被俄军占领,世界正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恢复。那年11月,诺伯特·维纳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市出版了一本名为《控制论》的书,副标题是「动物与机器中的控制和通信的科学」。也是在11月,海因茨·冯·福斯特在奥地利维也纳出版了一本名为《记忆》(Das Gedächtnis)的书,副标题是「量子物理学的调查研究」(Eine quantenphysikalische Untersuchung)。我本来是一名物理学家,在这份调查中,我试图将实验心理学和神经生理学的观察与大分子(生物)物理学联系起来。我认为自己在这方面做得不赖。
现在我必须换到另一个轨道。我妻子最亲爱的朋友伊尔莎,在希特勒上台时从德国逃了出来。到了1948年,她已经在纽约站稳脚跟并且邀请我到美国来,希望我能在这儿建立一个滩头阵地,以便让我的家人更容易跟来。1949年2月,我乘坐玛丽皇后号渡过了大风大浪的大西洋。由于我不晕船,(其他大多数乘客都晕船)我总是在空荡荡的餐厅里享受6个服务员的服务。
在我到达纽约几天后,美国著名的神经精神病学家沃伦·麦卡洛克(他在令人惊奇的情况下拿到了我出版的书)邀请我在几天后在将于纽约举办的会议上介绍我的记忆理论。他还建议我去找一本名叫《控制论》的书,为会议做一些准备。我照做了,我当时用仅仅掌握的一点英语,努力去理解书中的一些基本观点。
带着概念和语言的双重准备不足,我参加了这个会议。会议题目对我来说也或多或少是个谜:「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反馈机制和循环因果系统」(Circular Causal and Feedback Mechanisms in Biological and Social Systems.)。令我惊讶的是,这是一个由20名与会者组成的小型会议,但更令我惊讶的是,他们都是美国科学家中最精英的人物(the crème de la crème)。当然这里有担任会议主席的沃伦·麦卡洛克,他的四卷著作最近刚刚出版。还有诺伯特·维纳本人,他的一本由P·R·马萨尼编著的很棒的传记去年刚出版(译注:Norbert Wiener 1894-1964, Pesi R. Masani, Berlin: Birkhäuser, 1990)。还有约翰·冯·诺伊曼,那个发起了计算机革命的人。还有格雷戈里·贝特森和他的妻子玛格丽特·米德,或者我应该说是玛格丽特·米德和她的丈夫格雷戈里·贝特森,他们用各自的方式为人类学带来智慧、深刻和幽默。
他们只是其中少数几位我认为欧洲朋友会熟悉其名字的人。我不知道是谁发明了「跨学科」的概念,但这次会议正是其体现。如果在一个按字母顺序排列的学科列表中,从人类学(Anthropology)开始,到动物学(Zoology)结束,我估计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位代表出席。
我被要求在靠前的次序介绍我的故事,我勇敢地用我的20个英语单词搏斗,好让别人理解我。如果不是格哈德·冯·博宁(Gerhard von Bonin,德裔美国神经病理学家)、海因里希·克吕弗(Heinrich Klüver,德裔美国实验心理学家)和其他能讲流利德语的人在场,并翻译我的一些论点来拯救我,整件事就会变成一场灾难。
当晚,核心小组举行了一次常务会议。会议结束前,我被邀请进来。「海因茨,」主席说道,「我们听了你关于记忆的分子理论,它和许多其他理论无法解释的观察结果一致。你所说事情的非常有趣。但是,你讲话的方式太糟糕了!因为想让你快速学习英语,所以我们决定任你为本次会议汇刊的编辑。」
当时我哑口无言。我如何能编辑像维纳、米德、贝特森等等这些杰出作家的文章?我如何组织那些我一知半解的材料?但我转念又想「为什么不试试呢?」于是我接受了这项任命。并且立即提议:「本次会议的题目太长,很难记,而且对我来说很难读出:‘循环——因果——反馈——机制……’因此我提议将本次会议称为‘控制论’。」
每个人都看着坐在我旁边的诺伯特·维纳,并鼓掌向他表示敬意,并接受我的提议。他被同侪的认可深深触动,眼泪夺眶而出,然后离开房间试图掩饰自己的情绪。
本次以及另外四次关于该主题(控制论)的会议由纽约的小约书亚·梅西基金会赞助。他们要求我编辑这五卷文集。由于所有这些都发生在遥远的过去,所以控制论迷们把这几册书称为「关于控制论的传奇梅西会议」。
亲爱的伊芙琳,控制论如何向我扑面而来的故事到此结束。
Y:在今天的会议上,会议室和拉维莱特城的廊道里,有很多关于一阶控制论和二阶控制论的讨论;它们大多把两者放在对立面。例如,「但亲爱的你看,这在我看来这是来自一阶控制论的...... 」或者,「我告诉你,人们真的感觉到了不同;这次我们处于二阶控制论中。」你能不能尝试向在座各位澄清一下,一阶和二阶控制论的根本区别是什么?哪些方向或观察的变化意味着二阶控制论?或者借用你喜欢引用的乔治·斯宾塞·布朗(G.Spencer-Brown,英国数学家)的话,「给我设计一个相似物!」(Design me a resemblance!)或者,「给我设计一个区别!」(Design me a distinction!)
H:让我为你指出区别。当你跟随我从零阶控制论转向一阶控制论时。我做了什么?我让显现(emergence)、表征(manifestation)、结构化(structurization)、组织(organization)等过程中潜在的循环性变得明晰。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观察到的事物中反思产生结构、秩序、行为等等的循环过程。现在,伊芙琳,你可以很容易猜到如何从一阶转向二阶控制论。
Y: 我想是的。让我试试。在二阶中,你对你的反思进行反思。
H:没错!
Y:那现在我可以继续转向三阶控制论吗?
H: 是的,你可以。但它不会创造任何新的东西,因为通过上升到「二阶」,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人已经踏入了自我闭环的圆圈。人们已经踏入了应用于自身的概念领域。
Y:你的意思是说,二阶控制论是控制论的控制论吗?
H:是的,正是如此!
Y:你能举些其他的例子吗?
H:当然。例如,将一个典型的一阶控制论概念如「目的」(相当于 「为什么」)与二阶问题「‘目的’的目的是什么?」相比较。(询问为什么当初要使用「目的」这个概念;即它如何影响话语、解释、论证等等?)
这个概念的一个不错的作用是,它使人不必再去解释做事情的方式——它们自有其目的。每次我系鞋带,或者你提上你的高跟鞋,我们的做法都是不同的。而且我们的做法有成千上万种不可预测的变化,但结果是可以预测的:我的鞋带系好了,你的鞋提上了。
另一方面,物理学家不太可能发明「自然法则」,用它来计算我的鞋带或你衣橱里的高跟鞋的初始条件下的行为;即计算我们的身体和肢体在给我系鞋带或给你穿鞋时正在采取的路径、「轨迹」和运动。在这里,物理学家的「动力因」无能为力,但控制论者的「目的因」却能做到。如果意图是明确的,(与初始条件无关)感觉运动回路将调整和重新校正我们的运动,直到我的鞋带系好;你的鞋子穿好。
Y:谢谢你。我穿上鞋后感觉好多了。我现在看到了使用目的概念的目的。一个人不需要知道如何到达那里;他只需要知道那里。这确实是个非常好的作用!那它有不好的作用吗?
H: 是的,有。「目的」、「目标」和「终点」这些概念的丑陋之处在于,它们可以被用来证明达到目的的具体方法是正确的:「终点证明了手段。」而据我们所知,手段确实可以非常丑陋。而问题则应该是:「手段是否证明了终点的合理性?」
Y:如果我们能这样问问题,世界将会变得非常不同。海因茨,请用你的语言,告诉我二阶控制论是如何向你「扑面而来」的吧?
H:当然,是通过一位女士。那就是玛格丽特·米德。你记得我在演讲中引用的那句话吗?来自她的一次演讲,我想那是在1968年。由于她很少为自己的演讲起标题,而且几乎从不准备讲稿,所以我给她寄去了录音听写稿,请她更正并加上标题。但她没有回复。我通过电报催促;仍然没有答复。最后,我尝试通过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电话联系她,她是那里的馆长。我却被告知她和巴布亚人,或特罗布里安人,或萨摩亚人在一起,无法取得联系。因此,我不得不自己编辑她的演讲,并编造了一个标题。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她以控制论的方式谈论控制。因此,我为她选择的标题是:「控制论的控制论」。
今天在我看来,对应用于自身的概念(甚至需要自身才能产生)的特殊属性的兴趣,当时确实已经在空气中弥漫。智利的神经哲学家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把它们称为「自我参照」(self-referential),瑞典的逻辑数学家拉斯·洛夫格伦(Lars Lofgren)把它们称为「自动逻辑」。(auto-logical)
Y:如果我请你对一阶控制论和二阶控制论的区别做一个最简短的描述,你会怎么说?
H: 我会说,一阶控制论是被观察(observed)系统的控制论,而二阶控制论是观察(observing)系统的控制论。
Y:确实很简短!你想展开说说吗?
H:也许只是很简要地说说,因为我的「最简短的描述」只不过是对我演讲中描述的转述。我在演讲中把两种根本不同的认识论(甚至是伦理立场)并列,就有了两种人们看待自己的立场:一方面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观察者,眼看世界流逝;或者另一方面,作为人类关系循环中一个参与性的行动者。
当采取后一种立场时(我认为这正是系统性家庭治疗师所采取的),人们会发展出诸如「封闭」(closure)、「自组织」(self-organization)、「自我参照」(self-reference)、「自我」(self)、「自创生」(auto-poiesis)、「自主」(autonomy)、「责任」(responsibility)等概念,诸如此类。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得出当下控制论的整个概念机制,即观察系统的控制论,因此这非常接近这次会议的主题:「伦理、意识形态、新方法」。
Y:在你发表在保罗·瓦茨拉维克(Paul Watzlawick)的《被发明的现实》(The Invented Reality)一书中的文章《论现实的构建》(On Constructing a Reality)的结尾,你问到:「这一切在伦理学和美学中的后果是什么?」你还写道:「伦理学上的必要性:始终采取行动以增加选择的数量。」以及「美学上的必要性:如果你希望去看,那就学习如何行动。」你能对伦理学、美学和变化之间的联系做一些补充吗;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家庭治疗的三个基本坐标。
H:我喜欢你的三个坐标,因为它们都有二阶的味道。当然,我也很高兴我的两个必要性与其中两个相对应。然而,我感到些许不安的是你的第三个坐标「变化」还没有相称的必要性。让我马上补救,为你发明一个必要性:治疗的必要性:「如果你想成为你自己,那就改变!」这是不是自相矛盾?当然!你还期望从变化中得到什么呢?
Y:你如此确凿地说:「自相矛盾,当然!」你怎么能把变化与悖论联系起来呢?
H:很容易!你还记得悖论吗?当以一种方式理解时,它产生一种意义;而当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时,它又产生另一种意义。当我说「我是个骗子」时,你会怎么做?你会相信我吗?如果你相信,那么我说的一定是实话;但如果我说的是实话,那么我一定是在撒谎,诸如此类。
其中的问题是什么?撒谎吗?不,问题是「我」,这一最短的自我指涉循环。当使用「我」谈论自己的时候,魔法就产生了。一个人通过创造(creating)自己来创造(creates)自己。「我」既是操作员(operator),也是操作的结果。
Y:这对我来说都是魔法。「变化」在哪里?
H:变化的悖论性质比传统的「骗子悖论」丰富得多,后者在动态稳定中从「真」切换到「假」,又从「假」切换到「真」,循环反复。当你以任何你希望的方式来理解「变化」时,变化的非传统性质就出现了,它将产生别的事物,否则它就不是「变化」。我相信,这就是治疗的力量。
Y: 但你说,「如果你想成为你自己,就改变!」你怎么能成为你自己并改变呢?
H:我想诉诸于古老的智慧。它有2600年的历史,来自《易经》。第58卦「复卦」或「转折点」中说,「变化的终极框架是不变。」(译注:从福斯特的意思来看,他指的应该是第24卦,复卦,上坤下震,卦辞为:复,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
Y:(微笑)海因茨,与你谈话真是一个快乐而令人兴奋的学习日。它似乎映照出我们会议的主题:伦理与家庭治疗。感觉我好像在一个精确而严格的框架中发现了新的自由。这个框架由治疗实践的基本准则明确界定,鼓励与他人交流,从而创造一个新的空间。这难道不就是通过重新画出地平线来扩展我们的可能性吗?如果将严谨性与创造性结合,选择的伦理学也可以是变革的伦理学!
至少这是我从我们的接触中获得的非常个人话的理解。我现在有一种强烈的发散感,一扇门通向另一扇门,这扇门又通向下一扇门,下一扇门通向下下一扇门……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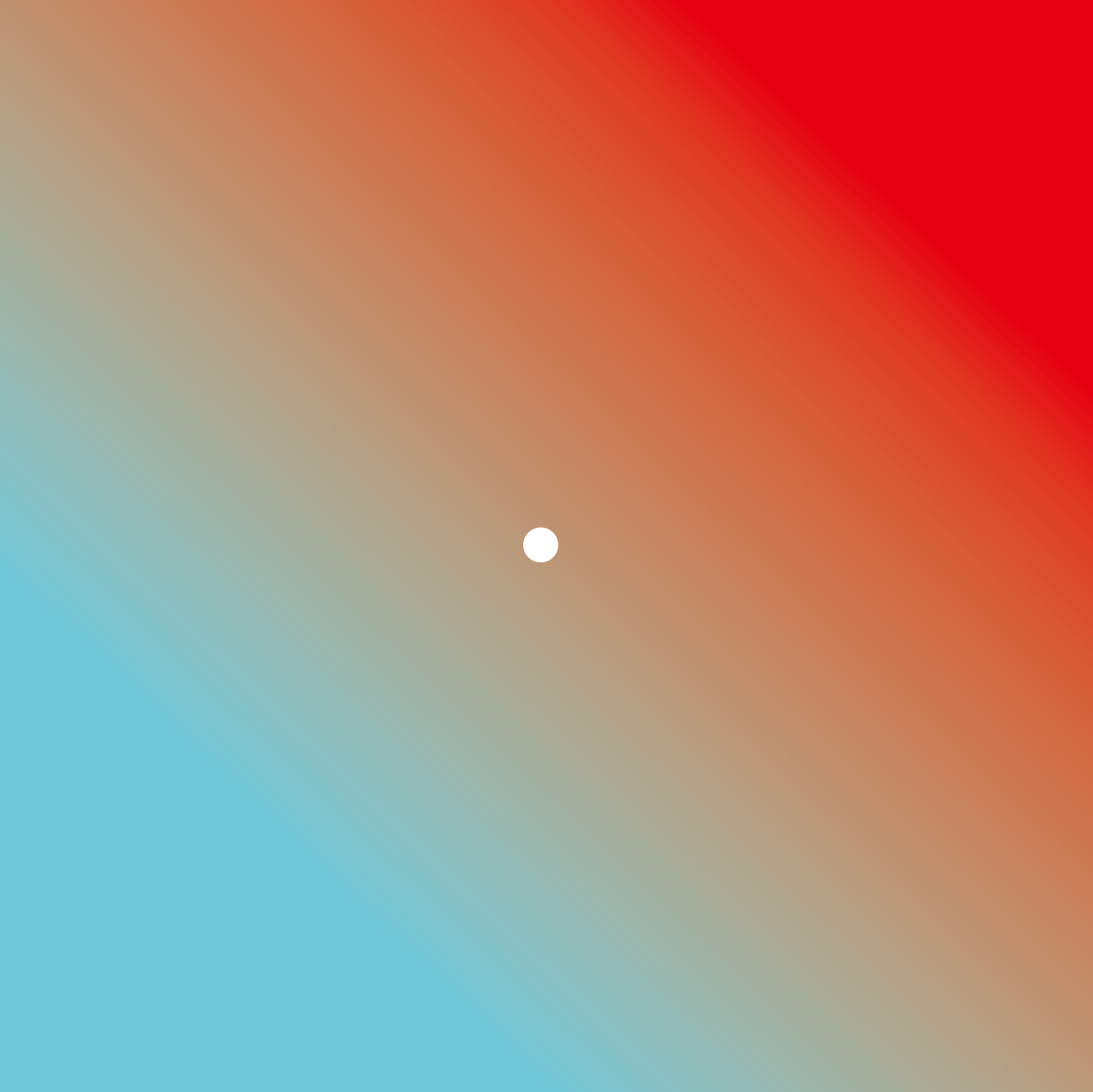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