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最重要的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游戏,就像游戏全心全意地拥抱他们一样。
编者按
编者按
大概每个研究游戏的朋友都读过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但想必会遭遇到许多困惑,这本书中的「游戏」概念如同伊拉斯谟的愚行概念,在文化和人类世界中无所不在,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赫伊津哈对现代文明「游玩的衰弱」的论述也很难将其关联到具体当下的各类电子游戏之中。
而这篇来自荷兰学者们野心巨大的文章,就像终于扛起了延续这位自己国家伟大的游戏理论开创者的工作,深入回顾了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所开启的游戏理论,并且补足阐明了其并未能处理好的游玩所拥有的各种模糊双重的辩证特性,并将这修正过后的理论重新放置在当今媒介技术与后现代文化生活的核心,将其与每个人的身份建构联系起来。
这使得赫伊津哈的游玩理论能被重新升级而与当下相接。从这个视角出发,不再只面向电子游戏,而让「游玩」成为一种文化和生命最基本的范畴。
无论是过去人们在NFT和Metaverse中玩,还有今天人们在chatgpt和AI生成coser小姐姐的游戏中不亦乐乎,要更好地思考这个日益「游玩化」的世界,以及在其中每个人与游玩媒介技术的相互建构的过程,我们需要一种更加扩张的游玩/游戏理论。
而本文或许可成为一个开始。
叶梓涛
落日间
引言
引言
本文是《游玩的身份》(Playful Identities)一书的第一章,可谓「游戏身份」(ludic identity)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本文阐明了赫伊津哈《游戏的人》的内在矛盾,指出游玩/游戏并非赫伊津哈所说的完全置于「普通生活」之外、无涉个人利害的「魔圈」,也并非不受真实处境制约的纯粹自由状态。游玩是一种双重经验,同时发生在「魔圈」内外;通过游玩,玩家在日常生活之上叠加了一层新的意义。游玩技术(playful technologies)是抵达此双重经验的「中介」,正因如此,与赫伊津哈的宣称相反,现代技术的发展不仅没有导致游玩精神(playful spirit)的衰落,反而驱动了整个文化的游玩化(ludification of culture)进程。
身份问题在此视角下展开。保罗·利科(Paul Ricœur)经典的「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理论认为,「我是谁」需要通过讲述一个「生命故事」来回答。在叙事中,自我认同于故事中的角色,身份通过连贯的情节实现了「异质性的综合」。「游戏身份」则超越了「叙事身份」单一媒介(叙事/小说)的视角,指出游玩的诸种媒介提供了一个「游玩空间」,玩家在面向未来的行动与选择的可能性中确定(或永远无法确定)自我。身份的游玩化,或者说,以游玩的态度对待自我的身份,构成了现代人理解自身的基本维度。文中引用的电影《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的台词一语中的:
「选择。问题在于选择。」
刘凯然
清华大学历史系硕士生
作者
作者
Joost Raessens
Joost Raessens
乔斯特·拉伊森斯(Joost Raessens)是乌特勒支大学媒介研究的教授。他关注绿色媒介(green media)与公民参与的关系(Green Mediography))以及「文化的游玩化」(ludification of Culture)问题。其出版和参与编撰的著作包括《语境中的说服性游戏》(Persuasive Gaming in Context)(2021),《游玩的公民:媒介文化中的公民参与》(The Playful Citizen:Civic Engagement in a Mediatized Culture)(2019),《游玩的身份:数字媒介文化的游玩化》(Playful Identities. The Ludification of Digital Media Cultures)(2015),《游戏的人 2.0:媒介理论的游戏转向》(Homo Ludens 2.0. The Ludic Turn in Media Theory)(2012)。
更多信息见学校官网
Jos de Mul
Jos de Mul
乔斯·德·穆尔(Jos de Mul)是伊拉斯谟哲学学院的哲学人类学和历史学教授。德穆尔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哲学人类学、艺术和文化哲学以及信息和传播技术哲学等领域。他已经出版了大约30本书并发表了220多篇论文和文章。他的作品已被出版和/或翻译成十几种语言。他的专著包括《(后)现代艺术和哲学中的浪漫欲望》(Romantic Desire in (Post)Modern Art and Philosophy)(1999),《有限的悲剧:狄尔泰的生命解释学》(The Tragedy of Finitude. Dilthey’s Hermeneutics of Life)(2004)、《赛博空间奥德赛》(Cyberspace Odyssey)(2010)和《被驯化的命运:科技精神之外的悲剧重生》(Destiny Domesticated. The Rebirth of Tragedy Out of the Spirit of Technology)(2014)。德穆尔参与编撰的出版物包括《普莱斯纳的哲学人类学:观点与展望》(Plessners’s Philosophical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2012)和《游玩的身份:数字媒介文化的游玩化》(Playful Identities. The Ludification of Digital Media Cultures)(2015)。
更多信息见个人网站
Michiel de Lange
Michiel de Lange
米希尔·德·朗格(Michiel de Lange)是乌特勒支大学媒介与文化研究系新媒体研究的助理教授。他是新媒体与城市主义研究平台「移动城市」(The Mobile City)的创始人之一,从事(移动)媒介、城市文化、身份与游玩等领域的研究。米希尔现在是荷兰科学研究组织(NWO)的资助项目「负责任的智能城市中的设计争论」(Designing for Controversies in Responsible Smart Cities)的主理人之一,该项目与屯特大学(UTwente)以及大量社会参与者共同合作。他还参与过「黑客城市」(The Hackable City)项目。米希尔的博士论文题目为《移动的圈:移动媒介与游玩身份》(Moving Circles: mobile media and playful identities)(2010),关注移动媒介技术在城市背景中塑造个人和文化身份建构的方式。
更多信息见学校官网
Sybille Lammes
Sybille Lammes
西比尔·拉姆斯(Sybille Lammes)是莱顿大学新媒体与数字文化的教授、曼彻斯特大学的高级访问研究员,曾在华威大学跨学科方法论中心、乌特勒支大学和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媒介研究系担任研究员。西比尔从事媒介研究和游戏研究,包括文化研究、科学技术研究和后殖民研究以及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的跨学科视角。她是《游玩的身份》(Playful Identities)(2015),《绘制时间》(Mapping Time)(2017)、《罗德里奇跨学科研究方法手册》(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Methods)(2018)和《游玩的公民》(Playful Citizen)(2017)等书的作者之一。
更多信息见学校官网
Valerie Frissen
Valerie Frissen
瓦莱莉·弗利森(Valerie Frissen)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哲学系「信息与传播技术和社会变革」(ICT and Social Change)的杰出教授。该教职由荷兰政府的研究机构「荷兰应用科学研究组织」(TNO)资助,她同时也是该机构的信息传播技术与政策部的负责人。
更多信息见维基百科“Valerie Frissen”条目
翻译:刘凯然
校对,编辑:叶梓涛
原文是《游玩的身份:数字媒介文化的游玩化》(Playful Identities. The Ludification of Digital Media Cultures)一书的第一章。
游戏的人2.0:游玩,媒介与身份
Homo Ludens 2.0: Play, Media, and Identity
游戏的人2.0:游玩,媒介与身份
Homo Ludens 2.0: Play, Media, and Identity
无限是游戏的领域(Immense est le domaine du jeu)。 —— 埃米尔·本维尼斯特(Émile Benveniste)
游玩之前
Foreplay
游玩之前
Foreplay
一个游玩的幽灵正在世界上游荡。自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当「游戏的」(ludic)一词在欧洲和美国流行开来以指称游玩的(playful)行为和人造物时,游玩性(playfulness)已经越来越成为现代和后现代文化的一个主流特征。在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们甚至可以讨论 「文化的游玩化」 (ludification of culture)(Raessens 2006; 2014)。在这个语境下,我们首先想到的也许是电脑游戏的极度流行,就全球销量而言,它已经超过了好莱坞电影。在美国,8-18岁的青少年平均每天在游戏机、电脑和包括手机在内的手持游戏设备上玩一个半小时(Rideout et al,2010,2-3)。这绝不仅仅是一种西方现象。例如,在韩国,该国总人口中约有三分之二的人经常玩网络游戏,这使得电脑游戏成为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并成为韩国经济的主要驱动力(Jin 2012)。[1]
(校注:本文中的ludification皆翻译为「游玩化」,以此与所谓的「游戏化(gamification)的商业概念区分开,且大部分的 playful 与 ludic 皆译作游玩,保留其囊括游戏与玩,以及其作为一种不仅仅是日常所指的文化范畴视角的特殊性」)
尽管可能是最明显的,但电脑游戏文化仅仅只是看上去渗透到每一个文化领域的游玩化过程的表现之一(Neitzel and Nohr 2006)。例如,在我们现在的体验经济(experience economy)中,游玩性不仅是休闲时间的特征(有趣的购物、电视上的游戏节目、游乐园、玩游戏的电脑、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而且也是那些过去被认为是严肃领域的特征,如工作(现在首先应该是有趣的)、教育(严肃的游戏)、政治(竞选的游戏),甚至战争(电脑游戏如战争模拟器和人机界面)。根据杰里夫·里夫金(Jeremy Rifkin)的说法,「游戏在文化经济中的地位变得和工作在工业经济中的地位一样重要」(2000, 263)[2]。后现代文化被描述为 「没有总体目标的游戏,没有超越性目的的游戏」 (Minnema 1998, 21)。社会学家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坚称,人类的身份甚至已经成为了一种游玩的现象。他认为,在游玩的文化中,游玩性不再局限于童年,而是成为一种终生的态度:「后现代成年人的标志就是愿意全心全意地拥抱游戏,就像儿童那样」(Bauman 1995, 99)。
本书聚焦于当代文化中游玩、媒介和身份之间的复杂关系。本书中的各章从不同角度研究了数字信息和传播技术在个人和文化身份的游玩化中所扮演的角色。对(新)媒体的关注不仅是出于数字媒体在我们目前文化中的主导作用,而且也因为 「游玩是媒介体验...的核心」(Silverstone 1999, 63; cf. Thimm 2010) 这一直觉。
在这一介绍性章节中,我们将分析构成本书主题的这三个相互关联的现象以提供一个概念背景,使读者能够将每一章与本书联系起来。这个介绍性章节包括三个主要部分,与本书的三个部分相对应,专门讨论游戏、媒介和身份。
关于这个三元组合中游玩的维度,我们的出发点是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在他1938年出版的名著《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发展的游玩理论。《游戏的人》被认为是游戏研究的经典,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尽管已经发表了超过 75 年,但赫伊津哈的核心主张,即文化和文明「在游玩(play)中且作为游玩而产生,并且永远没有离开它」(1955, 173),仍然为研究我们当代媒介景观——或如科尼斯·格根(Kenneth Gergen)在本书中所说的「游玩之地(playland)」——中人类身份的游玩化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框架。这一论断得到了广泛的赞誉。由于最近的游戏和休闲研究等领域的发展,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一种赫伊津哈式的复兴。然而,我们认为,为了将赫伊津哈的游玩理论应用于数字技术的世界,《游戏的人》需要一次重大的「更新」,因为游玩和技术对赫伊津哈来说几乎是完全对立的。
在这个介绍性章节中,我们将把《游戏的人》更新为 「2.0」版本,超越当代游玩和技术之间的对立。在关于媒介的部分,我们将使用新媒体(New Media)和游戏研究(Game Studies)领域的主要学者的见解,通过关注数字技术的游玩维度来进一步证实这一立场。我们在此论证,无论是明确为游玩设计的媒介如电脑游戏,还是一般的数字技术,都有一个内在的游玩维度(ludic dimension)。这个维度与媒介的特定品质如多媒介性、虚拟性、互动性和连接性密切相关。
在本章的最后一节,重点在于这些游玩技术在构建个人和文化身份方面的作用。思考这个问题的有利角度是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的「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叙事不仅是人类身份的恰当隐喻,而且人类实际上是通过故事来建构他们的身份,从明确的传记和自传到小说中对人类生活的虚构描述。鉴于上述提到的数字文化的游玩化,我们提出用一种「游玩身份建构」(ludic identity construction)的理论来补充利科的叙事身份理论,以解释玩和游戏现在如何成为了人类身份的恰当隐喻以及人们反思性地构造其身份的手段。
像 「自我建构 」和 「文化身份的建构 」这样的短语可能暗示,这个过程完全由一个自主的主体控制。显而易见,情况并非如此。「自我」不是给定的东西,而是一种建构,这一事实不一定意味着自我是(主要的)建构者。商业化、全球化和技术同质化将主体的自我建构按照一个外部系统的逻辑来塑造。正如本书中的各章将详细说明的那样,反思性身份建构的实践在交往行为与商业化、本地化与全球化、异质化与同质化之间的张力中持续展开。[3]
玩
Play
玩
Play
从游玩的视野(sub specie ludi)看待人和世界当然不是一个新现象。在西方的早期思想中,赫拉克利特就推测「世界的进程就是一个玩耍的孩子在棋盘上移动棋子——孩子是宇宙的绝对统治者」(Sprague 2001)。人和世界的游玩式论述在每个时代和每个文化中都被阐发过。
在西方文化中,我们可以看到过去两个世纪的一个重要发展。尽管启蒙运动没有表现出对游戏的浓厚兴趣,但浪漫主义运动则预示着对这种现象的新的迷恋。弗里德里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他可以被认为是当代游戏学(ludology)的奠基人——甚至认为玩的驱力(play drive)是人性的核心,因为它使人能够调和必要性和自由。正如他在《美育书简》(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中的著名表述:「人只有在完全意义上是人的时候才会玩,人只有在游玩时才是完全的人」(Schiller 2004, 80)。除了推理(理性人,Homo sapiens)和制造(工匠人,Homo faber)之外,玩(游戏人,Homo ludens)现在被提升到关注的中心。包括尼采、维特根斯坦、海德格尔、伽达默尔、马尔库塞、德勒兹和德里达(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被认为是后现代文化的先驱或代表)在内的哲学家们,沿着赫拉克利特和席勒的游戏学的足迹,试图改变现代的、占主导地位的理性主义和功利主义的本体论和人类学(Axelos 1964; cf. Minnema 1998) 。
此外,游玩和游戏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中都获得了强烈的关注。例如,我们可以想到博弈论(game theory)在生物学(Sigmund 1993)、经济学(Neumann and Morgenstern 1944; Leonard 2010)和文化人类学(Bateson 1955; 1977)中的应用。除了这些已经存在的学科对游玩和游戏的兴趣增加之外,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受到休闲时间的大幅增加和游玩-产业(ludo-industry)与游玩-资本主义(ludo-capitalism)的增长的推动(Dibbell 2008)——数个完全致力于研究玩和(电脑)游戏的新领域诞生了(cf. Mitchell et al. 1934; Avedon and Sutton-Smith 1971; Raessens and Goldstein 2005; Mäyrä 2008; Ritterfeld, Cody and Vorderer 2009; Fuchs et al. 2014)。
如上所述,当代对游玩进行研究的奠基性著作之一是约翰·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文化的游玩要素研究》。这本书于 1938 年首次在荷兰出版,后来被翻译成许多语言,甚至可以被认为是「关于游玩的关键现代主义声明」(Motte 2009, 26)。「这本书令人钦佩的广博视野能够激起丰富的联想,它提供了第一个全面的游玩理论,而且在它首次发表的七十年后,它仍然是任何关于玩的「严肃」讨论的必然参考点」(ibid., 26)。
该书之所以仍然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其宏大的野心和视野。该书的副标题——「文化的游玩要素研究」[4] ——和前言已经表明,赫伊津哈的野心不亚于提供一个谱系学以解释「文明是如何在游玩中,并作为游玩而产生和展开的」(Huizinga 1955,foreword)。在倒数第二章——「游玩视野下的西方文明」中,赫伊津哈总结了他的论点:
不难看出,在整个文化进程中,某种玩的因素都极其活跃,它产生了许多社会生活的基本形式。作为一种社会冲动,游玩的竞争精神比文化本身还要古老,它像一种十足的发酵剂一样充斥着所有的生活。仪式在神圣的游戏中成长;诗歌在游戏中诞生,在游戏中得到滋养;音乐和舞蹈是纯粹的游戏。智慧和哲学在源自宗教竞争的语言和形式中得到了表达。战争的规则,高尚生活的习俗都是在游戏的模式上建立起来的。因此,我们必须得出结论,文明在其最早的阶段就是游玩。它不是像婴儿脱离子宫那样来自于游玩:它是在游玩中且作为游玩而产生,并且永远不会离开它 (ibid., 173)。
这个总结详细解释了《游戏的人》 主要不是对游玩或游戏的研究,而是「对文化领域中游玩原则的创造性品质的探究」(Caillois 2001, 4)。赫伊津哈的书的第一章提供了一个关于游玩现象的定义,这个定义几乎被后来出版的每一本关于游玩和游戏的书所引用。[5]
总结游戏的形式特征,我们可以说它是一种有意识地位于「平常(ordinary)」生活之外的自由活动,因为它是「无真实指向的」(not meant)[6] ,但同时又强烈地、彻底地将玩家卷入其中。它是一种与物质利益无关的活动,不可能通过它获得任何利益。它在自己适当的时间和空间界限内按照既定的规则有序地进行。它促进了社会团体的形成,这些团体倾向于用秘密包裹自己,并通过伪装或其他手段强调自己与普通世界的区别(Huizinga 1955, 13)。
让我们阐释一下这个定义的六个要素。
首先,像席勒和他之前的浪漫主义者一样,赫伊津哈把游玩定义为人类自由的表达(expression of human freedom),与自然和道德相对(ibid., 7-8)。游玩,像与之密切相关的自然和艺术中的美一样,是无关乎无功利的(disinterested);与普通生活不同,「它包含自身的进程和意义」,并作为「间奏曲(intermezzo)——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插曲」呈现自身(ibid., 9)。玩是「非严肃的(non-serious)」[7] ,因为它不关切日常的需要,如食物、住所和其他像我们一样脆弱的生灵为了生存所需的一切。游玩发生在「日常生活的必须性和严肃性之外和之上」(ibid., 26)。我们也可以说,游玩超越了世俗的严肃性(profane seriousness)。然而,这并不表明游玩活动不需要玩家完全投入。游玩不仅仅是「有趣」,而且是非常认真的,甚至是「神圣的热切(holy earnest)」(ibid.,23)。对赫伊津哈来说,这并不(仅仅)是一种比喻性的表达:「在其所有高级形式中,后者(人类游玩)无论如何总是属于节日和仪式的领域——神圣的领域」(ibid., 9)。为了将这种内在的、神圣的认真与世俗的严肃性区分开来,我们可以称之为神圣的严肃性(sacred seriousness)(关于灵性和游玩之间的关系,见本书中 Stef Aupers 的章节)。
第二,游玩是「无真实指向的」,它指涉一种「只是假装(just pretending)」的活动。在游玩中再现的东西不是真的。游玩只是在扮演「假如」和假装。赫伊津哈称这是「它(游玩)与「普通生活」「不同」的意识」(ibid., 28)。
第三,游玩不仅是沉浸式的,即它将玩家强烈地卷入其中;这种精神状态也「伴随着一种紧张、快乐的感觉」(ibid.)。根据赫伊津哈的说法,「游玩-情绪是一种狂喜和热情,根据场合的不同而分为神圣的或喜庆的。一种兴奋和紧张的感觉伴随着行动,欢乐和放松随之而来」(ibid,132)。
第四,游玩在地点和时间上都与普通生活不同。它的特点是有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限制:游玩的「魔圈」(「magic circle」,tovercirkel)不仅是一个空间范围,也是一个时间范围 [8]。同时它也可以在,并作为魔法般的「循环」(magic 「circle」)而发生:「它可以在任何时候重复,无论是「儿童的玩耍」还是象棋游戏,或者像宗教仪式一样有固定的间隔时间。这种重复的能力是游戏最基本的品质之一。」 (Huizinga 1955, 10)。
第五,构成游玩-世界的「规则」对这个概念至关重要:「所有游玩都有其规则。它们决定了在由游玩限定的临时世界中什么是「成立」的。游戏的规则具有绝对约束力,不允许任何怀疑」(ibid., 11)[9]。「只要规则被违背了,整个游玩-世界就崩塌了」(ibid.)尽管作弊者仍然假装在玩,并在这样做时仍然承认「魔圈」和循环,但「违反规则或无视规则的玩家是一个「扫兴者(spoil-sport)」」(ibid.)。
第六,游玩「创造秩序,它就是秩序。它为一个不完美的世界和混乱的生活带来了暂时的、有限的完美」(ibid., 10)。游玩「对于共同体的福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宇宙的洞悉和社会的发展富有创造力」(ibid., 25)。
由于赫伊津哈认为游玩是「生命最基本的范畴(primary category of life)」(ibid, 3),《游戏的人》第一章中提出的游玩定义具有普遍意义。赫伊津哈明确宣称「所有的人都在玩,而且玩得非常相似」(ibid., 28)10 ,他区分了游玩的两种基本形式:「两种不断重复发生的形式是神圣的表演和节庆的竞赛,文明在其中作为游玩成长起来」(Huizinga 1955, 48)。
在《游戏与人类》(Les jeux et les hommes)(1958)中,罗杰·卡约瓦(Roger Caillois)对赫伊津哈的作品进行了批判性的阐述,提出了由四种类型组成的游戏类型学。除了赫伊津哈提到的两种形式,包括「神圣的表演」,卡约瓦称之为模拟(mimicry),从儿童的模仿游戏到戏剧;以及「节日竞赛」,或竞争(agôn),指自由游玩、有规则的体育运动、竞赛等等。卡约瓦还区分了概率(alea)和眩晕(ilinx),前者可以从「点兵点将」和彩票中发现,后者则包涵从旋转木马「转到」爬山的活动。卡约瓦在对游戏类型的切分中识别出了两种游玩的态度:paidia 和 ludus 。Paidia 指的是「自由游玩」(free play)、即兴创作、无忧无虑的乐趣和欢笑,以及自发的、冲动的、快乐的和不受控制的幻想。另一方面,Ludus 则约束和丰富了 Paidia,因为它指的是「游戏」(gaming),拥有更明确的规则掌控的游玩形式,通常涉及具体的技能和对它的熟练掌握 [11]。竞争和概率更倾向于 ludus 一极,而眩晕和模仿则更倾向于 paidia 。综上所述,这种二分法是分析当代文化的游玩化的有用工具 [12]。
在关注当代信息和传播技术的游玩层面之前,我们必须先暂时回到赫伊津哈对历史的分析。尽管他强调所有的文化都 「在游玩中并作为游玩而产生和展开」,但他并没有说文化总是始终在游玩。与斯宾格勒(Spengler)的《西方的衰落(The Decline of the West)》(1991)的悲观论调相呼应,赫伊津哈认为文化在年轻时是最具游玩性的,随着它们的成熟,逐渐变得更加严肃,失去了游玩性(Huizinga 1955, 75)。对赫伊津哈来说,浪漫主义是西方文化中最后一个表现出游玩精神的时期,而在19世纪,社会「似乎没有给玩留下什么空间」(ibid.,191)。而在该书最后一章关于20世纪文化中的游玩要素的悲观论调中,赫伊津哈指出,文化中的游玩要素「正在衰落」:「今天的文明不再玩了」(ibid., 206)。
赫伊津哈承认,这一观察似乎与体育和流行文化已经成为20世纪文化的主要产业这一事实不一致。然而,他在游玩和严肃性的关系方面发现了两种矛盾的倾向,在他看来,这两种倾向导致了游玩和(世俗的)严肃性之间界限的模糊。一方面,当提到职业体育时, 赫伊津哈声称游玩变得越来越严肃,从而导致了游玩性的丧失(ibid., 199; cf. Raessens 2009, 86)。另一方面,他声称我们正在见证世俗的严肃领域中越来越多的游玩性。例如,他指出,在商业竞争中:「体育比赛向我们展示了游玩如何僵化为严肃,却仍被认为是游玩;如今严肃的商业退化成了游玩,但仍被称为严肃」(ibid.,199)。
这些发展并没有导向一种更具游玩的文化,反而展现了欺骗——「虚假的玩(false play)」——并因此破坏了(游玩的)文化本身(ibid., 206)。这个断言实际上在本书中被 René Glas 讨论过。根据赫伊津哈的说法,有几个「独立于严格意义的文化之外的因素」(ibid., 199)要对游玩的文化的衰落负责。他特别提到了文化的全球商业化(global commercialization of culture)[13] 和幼稚病(puerilism) 的出现:一种「青春与野蛮的混合体,在过去二三十年里席卷全世界」(ibid., 205),这些都是「现代传播技术造成或支持的」(「veroorzaakt of in de hand gewerkt door de techniek van het moderne geestelijk verkeer」 ] (Huizinga 1950, 237)[14]。这种文化的特征是「对琐碎娱乐活动和粗俗哗众取宠永不满足的渴求,对群众集会、群众示威、游行等的喜好」,他认为这「(完全缺乏)幽默感、正派和公平游玩的观念」(Huizinga 1955, 205)。
我们不应忘记,赫伊津哈是在1938年写下这些痛苦的文字的,当时人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不安记忆犹新,对新兴的法西斯主义运动同样令人发指的野蛮行径有着恐惧的预期。然而,在我们看来,赫伊津哈的悲观主义不仅源于当时的历史背景,而且也指出了他观点中的真正矛盾所在。如果我们想利用赫伊津哈的敏锐见解,即游玩是生命的最基本的范畴,来更深入地理解当代高度媒介化的文化是如何游玩化的,我们必须首先接受这些矛盾,因为这些矛盾指出了游玩现象本身的根本模糊性。
尽管《游戏的人》的见解很有启发,但它的许多矛盾和含糊之处仍然令读者困惑。让我们看看四个最重要的问题。
首先,赫伊津哈将玩描述为既是现实又是表象(reality and appearance)。一方面,他将游玩看作人类生活的一个关键维度,甚至认为文化只有在游玩中和作为游玩才可能存在。另一方面,他认为游玩完全发生在日常生活之外,只不过是无关利害的「插曲」(ibid., 9)。虽然游玩「对于共同体的福祉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对宇宙的洞悉和社会的发展富有创造力」,但它同时也只是假装的,是「虚构的」(ibid., 25) —— 因此对现实生活是不重要的。由于它的现实性,我们 「神圣而认真地」游玩,然而我们的游玩又是完全不严肃的。
第二,游玩既是自由又是强迫(freedom and force)。根据赫伊津哈的说法,游玩是对人类自由的赞颂,然而他认为游玩「对我们施了咒语」,因为它要求我们完全疯狂地卷入其中(ibid., 10)[15]。对这一观点的批评,见本书 Gordon Calleja 的章节。相反,尽管游戏规则具有「绝对约束力」,但玩家也在不断打破这些规则。
第三,游玩既是确定的,又是变化的(determined and changing)。赫伊津哈强调游戏规则的绝对性,同时《游戏的人》首先是一个关于游玩转化为各种文化形式的永无止境的历史叙事。
第四,游玩既是个人活动也是集体活动(individual and collective activity)。尽管玩家沉浸在他自己的私人游玩-世界中,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身处一个共享的游玩-世界中与其他玩家一起游玩或对战,而且通常在观众面前 [16]。此外,在「模仿」类游戏中,玩家是通过在自己内部创造一个角色共同体来假装成其他人 [17]。
Jacques Ehrmann(1968)和 Warren Motte(2009)等学者也指出了这些模糊不清的地方。他们批评赫伊津陷入了矛盾。按照 Ehrmann 的说法,「等级制的二分法」(hierarchical dichotomy)——将游玩理解为对现实的再现,且这个现实先于游玩并独立于游玩之外——是非常有问题的,因为「没有任何(普通的或非凡的!)现实外在于或先于表达出它们的文化表现(manifestations of culture)」(Ehrmann 1968, 33)。然而,Ehrmann 的替代方案——「游玩、现实、文化是同义词且可以相互替换」(ibid.,56)—— 同样有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概念完全失去了它们独特的意义。
而且,赫伊津哈正确地观察到,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不断地区分游玩和非游玩的差别。每一种文化都基于基本的区分之上,比如自然与文化、世俗与神圣、生命与死亡、男性与女性、善与恶、自由与压迫(Oudemans and Lardinois 1987, 31)。虽然这些区分具备自然基础,但它们并非是简单给定的,它们(至少部分)是历史和文化建构的产物,因而是可变的(de Mul 2004, 146-52)。我们经常发现自己处于异常的、有时是悲剧性的境况中,我们无法明确区分这些对立面,因为事情在根本上就是模糊的或者因为对立的双方都符合我们的境况(de Mul 2009)。
此外,我们在游戏中经常遭遇根本的模糊性。有时,在危险的体育运动或战争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玩和严肃;或者,在游戏或赌博成瘾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区分自由和强迫。然而,在作为现代思维特征的「二分的宇宙论(separative cosmology)」看来,包括赫伊津哈的分析在内,归根结底没有为这些模糊性保留一席之地,它们必须被祛除。但在他不断地、几乎仪式般地将游玩和非游玩(现实、实用、严肃性等)对立起来的过程里,赫伊津哈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上述不可解的概念紧张关系之中(cf. Motte 2009, 25-6)。
不过,Motte 指出,事实上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的几个地方对「游玩的模糊性」(参见 Sutton-Smith 1997, and Jos de Mul 在本书中的章节)表现出了更多的敏感性,高于 Ehrmann 对他的评价。例如,在《游戏的人》的最后一章,赫伊津哈承认「游玩可以是残酷和血腥的,此外,也可以是虚假的游玩……战争以及与之相关的一切都在游玩的魔鬼般的束缚中快速发展」(Huizinga 1955, 208-9)。而在他书中的同一章,赫伊津哈甚至——不情愿地——承认了现代文化中的游玩和世俗的严肃性之间的模糊。然而,就因为上述的「区分的欲望(separative drive)」,赫伊津哈无法解释文化(神圣的严肃性)和普通生活(世俗的严肃性)在游玩中且作为游玩而融合在一起的这一现象,以及它是怎样发生的。
Eugen Fink 在《作为世界符号的游玩》(Spiel als Weltsymbol, 1960)中提供了一个有趣的游玩的本体论。他认为,只要我们坚持现代主义的二分法——在态度层面:游玩和严肃——以及在本体论层面:游玩和现实——我们就不能解释这一现象(Fink 1968, 19)。如果我们想把握这个本体论的意义,我们就应该意识到,人类的游玩从来没有真正发生在日常现实之外。赫伊津哈是对的,游玩的世界有它自己的一种现实。然而,游玩-世界的构件——游玩场域、其他玩家、游玩对象——同时也是我们日常现实的一部分。将游玩既区别于更严肃的存在模式又区别于纯粹的幻想的原因是,玩家同时处于普通世界和游玩-世界中。此外,正如赫伊津哈明确承认的那样,在体验游玩时,儿童、运动员和演员都意识到自己同时处在两个世界里 (Huizinga 1955, 18)。
这里再一次表明,游玩-经验非常接近于审美经验。审美经验的特点也是一种类似的双重体验。当我们观看一部恐怖电影并完全沉浸在叙事中,我们可能会体验到强烈的恐惧。然而,与此同时,我们知道我们所看到的是「只是一部电影」,「只是好像如此」。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说,我们可以说审美经验需要一种自我分裂(ego-split),使我们能够同时拥有两种矛盾的经验,例如,电影中的吸血鬼既被经验为真实的,又被经验为非真实的 [18]。这种模糊的、双重的经验与人类的反身性(reflexivity)有关,即人类不仅经验,而且同时能够经验他们的经验。用普莱斯纳(Plessner)的哲学人类学的术语来说:人类的经验同时是中心的(centric)和离心的(eccentric),一句话:(离)中心的((ec)centric)。成为(离)中心的不仅意味着我们可以超越自己的私人经验,在别人的经验中想象自己,而且还意味着我们可以掩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扮演不同角色。然而,与此同时,我们也仍然沉浸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Plessner 1975, 288ff.; cf. de Mul 2003, 247-66)。因此,当我们参与游玩的活动时,我们并没有像赫伊津哈和卡约瓦所说的那样,走出日常世界进入游玩-世界的魔圈,而是有意地、明确地与作为人类生活特征的双重存在进行游戏。正如 Eugen Fink 所解释的那样:
参与游戏的玩家在现实世界中执行了一个熟悉的动作。然而,在游玩的内部意义的语境下,他正在接管和扮演一个角色。在这里,我们必须区分真正「游玩」的人和由游玩中的角色创造的人。玩家把他的真实自我隐藏在他的角色后面,并被其淹没。他以一种独特的紧张感生活在他的角色中,但又不像精神分裂症患者那样,无法区分「现实」和「幻觉」。玩家可以从他的角色回忆起自己;在游玩时,人保留了对他的双重存在的知悉,无论这种知悉减少到了何种程度。人同时存在于两个领域,不是因为精神不集中,也不是因为遗忘,而是因为这种双重人格对游玩来说是至关重要的(Fink 1968, 23)。
我们可以参考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对玩的分析来进一步阐释这种双重经验。根据贝特森的说法,游玩将交流和元交流(communication and meta-communication)结合在了一起(Bateson 1955)。游玩总是伴随着「这只是玩」或「这只是个游戏」的信号。我们已经在高等动物中看到了这一点,例如,当两只狗互相嬉戏撕咬时。当我们游玩时,我们可以热情地沉浸在游玩-世界中,同时对我们的游玩行为保持讽刺性的距离,正因为如此,我们的游玩行为才能被称为「游玩的」。
游玩的这种双重特性对于正确理解游玩现象有几个重要的含义。
首先,赫伊津哈关于游玩创造秩序的说法获得了更深的意义。游玩创造的秩序与其说是完全在日常现实之外或超越日常现实的临时秩序,不如说是在游玩中叠加在日常现实上的一层意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把游玩行为称为我们与我们之外的世界之间的「媒介(medium)」,通过这个媒介,生活经验被组织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cf. Rodriquez 2006)。在游玩的行为中,世俗的现实被一层神圣的严肃性所充实。这是技术被发明之前的增强现实(校注:可参考 Slavoj Žižek 意识形态是原始的增强现实 Ideology Is the Original Augmented Reality)!但正是因为给我们的经验增加新的层次是我们境况的一部分,所以人类经验才如此容易受到各种技术附加物的影响。
游玩的双重特征的第二个影响是,正因为沉浸在游玩-世界中总是伴随着「这只是在玩」的体验,指导游玩的规则必然被经验为是偶然的、灵活的和可改变的。正因为我们既在魔圈内又在魔圈外,我们能够将这些规则反思为「仅仅是游玩规则」,如果我们想的话就可以修改它们。这与赫伊津哈强调的规则的绝对性形成鲜明对比。此外,与规则一同的游玩内在于许多形式的玩中。我们在儿童的游玩中已经看到,玩规则——「现在我来当警察,而你当淘气鬼」——是乐趣的重要组成部分。
此外,在儿童的游玩中,魔圈(和魔环)的边界相当模糊。儿童游玩-世界的空间边界究竟在哪里?儿童的游玩究竟何时开始或结束?这也适用于许多其他的游玩情境,比如在打电话时玩你的笔,在火车上与人调情,或加入一个无处不在的游戏(Montola 2005; de Lange 2009)。游戏的灵活性和易变性不能只在微观层面上被辨识出来(例如足球规则的小变化),也要在宏观层面上辨识。完全新的游玩性的领域可能显露出来,例如趣味购物或严肃游戏。
与游玩的灵活性相联系,Lourens Minnema 对19和20世纪文化中对游玩的兴趣不断增加这一现象提供了有趣的解释。继卢曼(Luhmann)之后,Minnema 指出,自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已经将迄今为止的社会等级分层结构转变为功能分化的结构,它由许多子结构组成,如政治、经济、法律、教育、科学、技术和艺术,它们是相对自治的并有自己特定的功能和规则。这导致社会的复杂性和灵活性大大增加。根据 Minnema 的说法,20世纪对游玩和游戏的迷恋与这种社会发展密切相关。我们把我们的后现代文化「看作是一个游戏的综合体(a complex of games),每个游戏都有自己的框架、自己的规则、风险、机会和魅力」(Minnema 1998, 21)。游戏成为一种过渡仪式(rite de passage),一个新的(重新)组合行动和思想的空间,一个为生活提供代替模式的数据库 (Turner 1969)[19]。然而,与前现代和现代的仪式不同,后现代的仪式似乎不再有明确划分的转变的(阈限的,liminal)阶段, 而是成为一种永不停息的(类阈态的,liminoid)现象,成为社会经济、文化和多媒介系统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 (cf. Van Gennep 1960; Turner 1982) 。
当我们谈论文化的「游玩化」时,我们会面临这样一个问题:这种「游玩化」指的是游玩活动的增加,还是指视角的转变,即我们用游玩作为一个隐喻来理解那些本身不必然被认为是游玩的实体和领域。我们认为两种答案都是正确的。一方面,与赫伊津哈的宣称相反,自浪漫主义运动以来,西方文化见证了「游玩世界观」(ludic worldview)的显著复兴,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就是这种发展的成果之一。另一方面,这种视角的变化也推动了各种新的游戏态度、实践和对象的发展,这反过来刺激了我们世界观的游玩化。原则上,人类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严肃领域」都不能免于「游玩化」。这甚至适用于被赫伊津哈认为体现了游玩性的衰落的「严肃领域」:现代技术。
游玩的媒介技术
Ludic media technologies
游玩的媒介技术
Ludic media technologies
赫伊津哈宣称游玩的世界观自19世纪初就已经消失,不仅这种说法值得商榷,而且他关于游玩和技术不相容的说法也是如此。媒介考古学家 Erki Huhtamo 提供了一个生动的例子以说明游玩和技术的关联。根据 Huhtamo 的观点,「(19世纪)大规模机器生产的引入伴随着各种娱乐设备的涌现,包括游戏机」(2005, 3)。而那些所谓的「老虎机(slot machine)」则为20世纪60年代初电脑游戏的引入奠定了基础。此外,我们断言,在我们深深扎根于数字技术的当代文化中,游玩是理解这种文化的关键特征,而「游玩的技术」正是我们——如将在下一节看到的那样——反身性地建构我们身份的手段。
当我们谈论数字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特定媒介的游玩特征时,我们决不是指一套本质主义特性(见本书中 Daniel Cermak-Sassenrath 的章节)。正如我们在上面所论证的,游玩性并不存在于一个单一的特征中,而是应该被理解为一组特征,这些特征可以以各种或多或少的重叠组合出现在人类活动中 [20]。问题是数字媒介,如电脑游戏、互联网和手机,通过其设计向用户提供了哪些游玩的示能(affordance)(和限制):「术语示能(affordance,或可供性) 指的是事物被感知到的和实际的属性,主要是那些决定该事物可以如何被使用的基本属性……示能为事物的操作提供了强有力的线索」(Norman 1988, 9; 还可见 Menno Deen, Ben Schouten, 和 Tilde Bekker 的文章)。因此,游玩的示能只是「虚拟的(virtual)」(就其潜能性而言),直到它被用户的游玩态度按照这样的方式所实现和体验 [21]。这种对游玩的示能的寻找,与前述的视角的转换同时发生。将数字媒介视为游玩的实践使我们能够以具体的术语将其概念化,我们将在本节末尾展开更详细的讨论。
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数字媒介的特点是:多媒介性、虚拟性、互动性和连接性。
多媒介性(multimediality)不仅指数字媒介与电影和电视等共享的多种表达方式,包括图像(静态或动态)、声音(谈话、音乐和噪音)和书面文字,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元素共享一个共同的数字代码,具有各种经济和法律意义上的影响。想想看,电脑游戏可以很容易地被(非法)修改、复制和传播,而不会有任何质量上的损失 [22]。
数字媒介的第二个特点,虚拟性(virtuality),传统上是指由新形式的模拟技术提供的沉浸式体验(想想虚拟现实),以及由传播网络创造的隐喻空间(想想你在电话里说话时出现的空间)。但是,正如 Michiel de Lange 所说,这些描述大多 「建立在两个相互排斥的本体论上,即「真实的」和「虚拟的」。目前许多(移动)媒介研究对这种分离提出质疑。手机的「虚拟性」被嵌入「现实生活」。反之,「现实生活」被封装在「虚拟」的交流实践中」(de Lange 2010, 165)。「虚拟的现实」(virtual reality)已经越来越成为「真实的虚拟性」(real virtuality)[23]。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英国布莱顿(Brighton)的艺术家团体 Blast Theory 的在线游戏《我会藏起你》(I'd Hide You)。在《我会藏起你》中,玩家通过一群发光的跑者的眼睛看世界,他们在城市街道上漫游,试图拍到其他人,同时在网上挑战他们的朋友 [24]。
由于第三个特征——交互性(interactivity, 或参与 participation)——数字媒介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介入方式。除了 「认知交互性」(cognitive interactivity)(或「阐释性的参与」(interpretative participation))之外——数字媒介与其他媒体共享了这一点——用户可以用有意义的方式介入再现(representation)本身。根据 Salen 和 Zimmerman 的说法,这种介入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的形式。第一种,他们称之为「明确的交互性:或参与设计的选择和程序」。第二种形式是「超越对象的互动性(beyond-the-object-interactivity):在对象文化中的参与」(Salen and Zimmerman 2004, 60; cf. Raessens 2005) 。例如,我们可以想到在粉丝文化中共建网络游戏,或者使用户能够共同塑造网站的 web2.0 应用程序。Frans Mäyrä 在本书中,通过聚焦于休闲类型的游玩和参与方式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补充。
第四个特征连接性(connectivity)的一个例子是 Facebook,这个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现在声称拥有超过10亿的活跃用户。「由于它的构成,Facebook 既可以被视为个人娱乐的网站,也可以被视为维护和建立社区的工具」(Timmermans 2010, 189)。
由赫伊津哈阐述的游玩概念是分析媒介经验的一个非常有用的出发点。我们的媒介和游玩经验有许多共同的特点。或者,换句话说,数字媒介为用户提供了新的游玩机会。为了说明数字媒介的媒介特性如何为游玩提供了特殊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考虑到我们在「游玩」一节中所区分的玩的六要素(cf. Raessens 2012)。
第一个要素,人类自由的表达(expression of human freedom),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玩的自由,在游玩中做决定的自由,以及对世界的自由(cf. Cermak-Sassenrath 2010, 129-53)。当我们仔细观察这种类型的自由如何在实际的媒介使用中形成时,引人注目的是自由和压迫并不像赫伊津哈所说的那样截然相反,正如上面关于赫伊津哈的模糊性的分析中所论证的那样。在玩家决定游玩时,我们可以看到游玩的自由。但当你为了谋生而被迫游玩时——正如在中国游戏代练的打金农工(gold farmer)的例子中看到的那样——游玩和工作,以及自由和压迫,以最奇怪的方式纠缠在了一起 [25]。
至于手机,这种游玩的自由被 Michiel de Lange 描述为「在手机上游玩、游玩手机和通过手机来游玩」(play on, with and through the mobile)(de Lange 2010; 还可见本书中 Rich Ling 的章节)。在手机上游玩意味着手机可以作为平台随时随地地玩游戏;游玩手机意味着手机设备具有诱发游玩的某些特性。例如游玩手机的相机,在一个叫做「照片大战(photo war)」的游戏中,女孩与男孩竞争,尽可能快地在一张手机照片中拍下尽可能多的对手(Jarkievich et al. 2008; de Lange 2010, 191,校注:男女孩子分为两队,目标是拍出尽可能清晰的图片并涵盖尽可能多的对方队员,因为手机相机快门速度慢,对运动敏感,所以挑战在于保持移动的同时保持团队的分散)。通过手机来游玩的一个例子是游玩的交流方式。例如对文本信息(SMS)的使用:「短信不那么直接,而且对语言和表情的创造性使用使其更加好玩」(de Lange 2010, 209)。
做出有意义的决定的自由指的是数字媒介的交互性或参与性。正如赫伊津哈所说,游玩是一种「自由活动(free activity)」(我们标注的强调)。参与性文化兴起的一个例子是从 web1.0 到 web2.0 的转变。web2.0 不是由少数媒体内容生产者通过有限的电视或广播渠道向大众传播,而是将任何可以访问网络的人变成潜在的内容提供者,他们可以向目标受众报道特定的、异质性的话题。然而,我们应该意识到,媒体用户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控制(in control)」,我们将在后面的游玩规则部分讨论这个问题。Leopoldina Fortunati 甚至在本书中提出,游玩文化可能被用作一种新的控制机制。
最后,游玩也意味着你摆脱了外部世界的约束,它超越了我们前面提到的世俗的严肃性。在今天的游戏文化中,游玩应该有「其自身的目的」(Huizinga 1955, 28)这一说法似乎很难成立,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s)中的物品在 eBay 等在线拍卖和购物网站上被大规模交易,而且严肃游戏似乎将游玩应用到教育目的中。但是,根据 Hector Rodriguez 的说法,情况并不一定如此。游玩式的严肃游戏不仅可以「将教学的「效率」最大化」,而且还可以被用来阐明「所教学科的基本性质」。例如,哲学游戏不应该仅仅被当作使哲学对学生更有吸引力或更有娱乐性的有效技术;游玩行为可以成为对哲学活动根源进行学术探究的真正媒介」(cf. Rodriquez 2006)。这意味着在严肃的游戏中,比如《食物部队》(Food Force)和《达尔富尔即将死去》(Darfur is Dying),世俗和神圣的严肃性并不像一些批评家所说的那样事先相互排斥(见本书中 Joost Raessens 的章节)[26]。
第二个要素,假装(pretending)(无真实指向的),指的是对(数字)媒介的使用和/或理解是「假如(as if)」在做,或者指媒体的双重特性。像游玩一样,「我们的媒介文化包括了接受世界的「假如性(as-if-ness)」」(Silverstone 1999, 59)。在我们的媒介文化中「我们同样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在玩,什么时候没有」 (ibid., 66)。
其原因有两个方面。
首先,它与杰伊·大卫·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和理查德·格鲁辛(Richard Grusin)所说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两种逻辑」有关。(数字)媒介服从透明的直感性(immediacy)的逻辑——这意味着媒介的目的是消失——想想「通过互联网的网络通讯的灵活性和现场性来实现直感性的承诺」(Bolter and Grusin 1999, 197),即便如此,它们也同时服从超媒介性(hypermediacy)的逻辑。这意味着用户不断地被提醒或被带回到与界面(及其建构性(constructedness))的接触中,在网络里,屏幕上充满了窗口,每个窗口都有各种多媒体应用程序(ibid.196-210)。原则上,媒介使用者能够意识到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仅仅是被媒介化的」。媒介教育的明确目标是让媒介使用者更清楚地意识到,媒介是如何试图掩盖其自身的建构性的(例如,其自身的意识形态预设),以便让人以为所谓的「现实」的呈现是自发和透明地的。
其次是一个历史的论点。根据 Gianni Vattimo 的说法,今天数字媒介的扩散「使我们越来越难以设想一个「单一的」现实。也许在大众媒体的世界里,尼采的「预言」得到了证实:最终,真实的世界变成了一个寓言(fable)」(1992, 7)。媒介的诸种现实只是这个世界运作的不同版本,但绝非唯一的客观现实。
为了分析使用数字媒介所产生的「愉悦(pleasure)」(和/或不悦(displeasure)),即第三个要素,我们必须考虑生产、媒介文本和接受之间的特定媒介关系。因此,我们必须关注两个问题:「在由生产者制定的规则和脚本的关系中,愉悦是如何产生的?它们又是如何被用户体验和参与的?」(Kerr et al. 2006,64)。
在我们看来,广告和营销的说法——即数字媒介可以提供比传统媒介更多的乐趣和愉悦——是站不住脚的 [27]。我们确实认为,数字媒介可以提供多种多样的复杂愉悦感——这取决于特定的用户和背景——它们部分与传统媒介相同(如叙事的愉悦),部分比传统媒介更强烈(如沉浸的愉悦),部分与传统媒介不同。具体而言,数字媒介与传统媒介的不同之处在于那些与交互性有关的愉悦和不悦,包括电脑游戏成瘾、无聊或沮丧(「干等网(World Wide Wait)」)、掌控与失控的感觉、赢或输、成功或失败的紧张,还有那些通过服从、确认、谈判或抵抗规则所体验到的快乐。根据 Aphra Kerr、Julian Kücklich 和 Pat Brereton 的观点,游玩是「理解用户与新媒介互动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当控制、沉浸和表演(的愉悦)结合在一起时所体验到的独特快感」(ibid., 69-70) 。玩家体验到沉浸的乐趣,例如在展现他们的技能时(例如玩《舞蹈革命(Dance Dance Revolution)》)[28];或者在他们通过玩系统的规则而改变了设计者的原始目标时,例如教索尼的机器狗 AIBO 跳舞,正如我们将在后面看到的那样。
第四个要素,「具体的时间和空间限制(specific limits of time and space)」,在这个无处不在的计算时代似乎受到了巨大的压力。相反,移动电话的无限制性似乎是当今媒介文化的决定性特征,同时也是其解放和制约:「在它问世的时候,它被赞誉为移动通信的终极设备,可以在自由移动的同时保持「登录」状态,但它也迫使我们进入一种始终可达性(reachability)的文化之中,在接听电话和发送短信上的互易性(reciprocity),以及一种「永远在线」的心态(Timmermans 2010, 134)。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数字媒介没有一个分离的时间和地点:「媒介有能力,事实上它们也完全依赖于这种能力,在独特的时空中吸引受众的兴趣,这些时空不同于——并区分开——日常生活的无休止的混乱。每次我们参与到媒介化的过程中时,都有一个门槛要跨越」(Silverstone 1999, 61)。例如,当我们关注安全问题的时候这一点就很明显。数字媒介的用户可以像玩家一样尝试、测试或试验新的身份,而不会产生现实生活的后果(见本书中 Jeroen Jansz 的章节)。「既惊喜又安全。在熟悉的范围内对新事物的挑战。可掌控的风险。游戏,在其无尽的电子重现中,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失去什么,这与生活不同」(ibid.,61)。当一个用户想继续下去(魔环),但由于外部原因被迫停止使用时,限制的问题也就被凸显出来了。
玩的规则,也就是第五个要素,既可以在个人的微观层面,也可以在媒介系统的宏观层面上被接受和游玩。一方面,数字媒介要求用户服从其规则。在特定的限制内,用户可以自由游玩。个人用户将媒介文本放在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所说的「偏向性阅读(preferred readings)」(这里则是偏向性游玩(preferred play))下理解,同时他们探索和/或选择数字媒介系统中许多预先编写的系统内部的可能性之一(Hall 1996, 128-138)。在这两种情况下,用户都是按照规则来玩的。另一方面,用户可以用——或多或少——颠覆性的方式游玩这些规则。在这里,用户参与了对媒介文本的「对抗性阅读(oppositional readings)」,并在宏观上试图改变媒介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之间的关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围绕着在线游戏《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建立的参与性文化。我们在这里再次看到,在一定范围内,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的传统区别被瓦解了。例如,玩家成为《魔兽世界》创造和演变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cf. Glas 2013)。
参照前面提到的数字文化的编码化(codification),所有基于软件的产品都可以根据用户的个人需求进行修改和改编:「微软的 Xbox 变成了一台 Linux 电脑。任天堂的 GameBoy 变成了一种乐器,索尼的机器狗 AIBO 学会了如何跳舞」(Schäfer 2011, 12)。对这些游玩的产品进行修改的例子是当今文化产业中发生的重要变化的典范。
但我们必须记住,在全球化的经济中,像《魔兽世界》这样的「工业时间性物体」(industrial temporal objects)(Patrick Crogan 在本书中采用的斯蒂格勒式的术语)的基本规则是,为了玩这个游戏,玩家——即使他们已经是「生产-消费者」(prosumer)——也需要购买这个游戏,为玩这个游戏支付月费,除此之外还必须为玩家积极参与(有时是他们自己)而产生的创造性文化修改付费。所以我们需要小心。参与式文化的概念有夸大「自己动手」(Do-It-Yourself)的反主流文化意义的危险,正如本书中 Valerie Frissen 的章节中所讨论的那样。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说:「允许消费者在受控制的情况下与媒体互动是一回事;允许他们参与文化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以他们自己的方式——则完全是另一回事」(Jenkins 2006, 133)[29]。这种「被玩」的感觉就是 Michiel de Lange 所说的「被移动媒介玩」(play by the mobile):「我们不是我们的信息和通讯技术的唯一的主人。移动媒介也在自由和强迫的辩证关系中把它们的逻辑强加给我们」(2010, 215)。
第六个要素,秩序(order),与社会群体的形成有关。一个关于 web 2.0 应用程序的很好的例子是所谓的绿色博客(green blog),它创造了一个基于社区的临时秩序。根据菲力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对后媒介时代(post-media)的分析,「在这个时代,媒介将被众多能够导向其再特异化(resingularisation)的主体群体重新占据」(2000, 61),来自全球各地的人们聚集在网上,为一个更清洁的环境而奋斗。互联网的去中心性「特别适合于草根行动主义。被剥夺了权利的社会群体,在他们的社区与环境的不公作斗争,而不再需要与主流大众媒体和建制的出版渠道等中介打交道」(Timmermans 2010, 164)。这些「绿色博客」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游玩式的社会抵抗」并「很容易处理那些以前经常被视为「抽象」、「不全面」或对个人来说「太大了」的问题」(ibid.,166-7)[30] 。可以这么说,绿色博客——就像玩所做的那样——用(神圣的)严肃性丰富了(世俗的)现实。
这个游玩式的社会抵抗的例子清楚地表明,媒介可以按照上文所讨论的罗杰·卡约瓦的游戏类型学的分类方法,被用作政治战场(竞争,agôn)的一部分。但根据所选择的具体游玩类型来看,世界也可以被呈现为一种表演(模仿,mimicry),一个受到概率规则支配的地方(概率,alea)或人们追求极度兴奋的地方(眩晕,ilinx)。在移动媒介领域,我们可以提供以下的例子。我们已经提到了「照片大战」,作为移动媒介的「竞争」类型的一个例子,「女孩与男孩比赛,尽可能地在一张手机照片上拍到尽可能多的对手」(de Lange 2010, 191)。许多亚洲人高度重视幸运电话号码,希望这能给他们带来财富,这就是移动媒介的「概率」类型的一个好例子(ibid.,195)。移动媒介的「模仿」类型的一个例子是「在舞台上打电话」:「手机的存在可以被用来告诉观众,这是一个有生活的人,一个生活在移动世界的人」(Plant 2003, 49)。最后,居住在他们自己的私人化的声音「气泡 」(bubble)中的 iPod 用户可以被认为是移动媒介的「眩晕」类型的一个很好的例子(de Lange 2010, 164, 200)。
把数字媒介看作游玩的实践(playful practices)使我们能够根据游玩一节中发现的四种模糊性将其概念化。第一个模糊性指的是媒介的「假如」特征;现实和表象不是严格分开的,而是以有意义的方式相互关联。数字媒介,至少在原则上,为用户提供了机会,使他们能够(或多或少地)意识到他们的媒介体验的建构性。
这也意味着第二个模糊性,即自由与强迫的模糊性。就像游玩的情况一样,我们能够将规则反思为「仅仅是游玩的规则」,无论是在基本的微观层面(与媒介文本和/或技术互动的个人用户)还是在宏观层面(媒介生产者、分配者和消费者之间关系的变化),这些规则总是可以修改的。在自由和压迫之间存在着一种辩证关系:我们可以玩,同时也在「被玩」(参见游戏成瘾的玩家)。
第三个模糊性是确定(determination)与变化之间的模糊。每一种媒介都假装是一个长期发展的最后阶段,想想网络所声称的基于其灵活的和实时的网络传播的可能性之上的直感性,以及手机声称其能实现理想传播的愿望(cf. de Vries 2012)。但是,正如历史所显示的那样,许多——即使不是大部分——这样的主张,都被更新的媒介的到来和新的主张所淘汰了。例如,网络的实时性是「广播电视的实时性的改进」(Bolter and Grusin 1999, 197)。
第四种模糊性,即个体性与集体性之间的模糊,涉及到个人媒介在今天的媒介景观中的身份。这个景观可以用一些概念来刻画,比如「融合(convergence)」,它表现了「不同媒介系统之间的一个持续的过程或一系列的交汇」(Jenkins 2006, 282),或者「再媒介化」,即「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中的再现」(Bolter and Grusin 1999, 45)。我们只需要想想网络声称再现或吸收了所有其他媒介就可以理解了。然而,由于目前所有的媒介——游戏机、电脑以及手机——都有游玩的应用,并可以作为游玩设备来使用,它们失去了一部分假定的个人身份,都成为了集体的游玩媒介景观的一部分并在其中发挥作用。例如,随着时间的推移,手机已经从一个严格的通信工具发展成一台多媒介的计算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你可以在手机上游玩,游玩手机,并通过手机来游玩。此外,融合的多媒介景观也为跨媒介的游戏和病毒,以及在线游戏世界提供了极为丰厚的土壤,这些游戏世界以不同的(再)组合方式结合了「竞争」、「模仿」、「概率」和「眩晕」等不同的游玩类型,如《魔兽世界》和《第二人生(Second Life)》。
游玩身份
Playful identities
游玩身份
Playful identities
我们已经探讨了玩和「游玩媒介」的特征和模糊性,我们想解释一下这如何与个人和文化身份产生关联。我们在本节中要捍卫的主张是,近几十年来大量侵入我们生活的游玩的技术对我们身份的建构有着深远的影响。为了捍卫我们的主张,我们从一些关于身份及其建构的普遍论述开始。
「身份(或译作同一性 identity)」一词的词源是拉丁词「identitas」,它又来自拉丁文的「idem」,指「相同」。事实上,当「我」这个词指的是我的数字统一性时:x=x,「我」在我的一生中都是相同的。我就是我自己,而非其他任何人。我们有理由期待,我明天仍然是和今天一样的人,而不会醒来时变成我的邻居。显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会改变。毕竟,在我们的一生中,我们的身体和精神生活都经历了实质性的转变。由于生物学上的生长和更新(我们身体里几乎所有的细胞都会逐渐被新的细胞取代),我们的学习过程、新的经验,以及最后的腐烂,我们的身份从出生到死亡都在变化。然而,当我们谈论「个人身份(personal identity)」,我们通常不是指某种不可改变的实体 [31],而是指一种特殊的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spatial and temporal continuity)。
空间上的连续性在于,构建肉体和心理身份的要素并不形成一个松散的集合体,而是构成内部的纽带,其中各部分和整体是紧密相连的。这在我们存在的物理层面上显而易见,身体的各个部分——细胞、组织、器官、肢体等等——被整合成一个功能性的整体。但我们表现出来的思想、行动、社会角色和欲望也是一个功能性的和意义丰富的整体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整合永远不会是完全的。人类的身份由许多异质的元素组成,它们之间的冲突往往多于和谐。此外,我们的生活显示出各种游离的状态,如(白日)做梦、宗教或性的狂喜、沉浸在电影或(电脑)游戏中、公路催眠、酒精和其他药物的麻醉、身体和精神解体的症状等等。当功能或意义上的纽带在很大程度上或完全被破坏时(例如在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dissociative identity disorders)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人的身份同一性解体甚至完全丧失。
尽管我们在一生中一直在变化,但时间上的连续性在于我们的身体和精神变化大多是逐渐发生的。一个人不会在一夜之间变成青少年、成年人或老人。我们的个人关系、社会角色、职业等也是如此。记忆和预期在时间的连续性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它们构成了时间的持久性 [32]。同样在这里,连续性永远不会完整;它的特征是中断(睡眠)和缺口(遗忘)。这也关乎时间的纽带,有时剧烈的断裂——例如,在精神错乱时失去记忆、肢体丧失、性别转换、恶性成瘾,或激进的宗教和政治转变——可能会导致根本的变化,甚至(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完全扭曲时间性的同一性。
关于个人身份的大部分内容也适用于「文化身份」。一种文化或亚文化也显示出构成部分的某种统一性,同时也可能囊括了中断。仅举两个例子,加尔文主义文化或嘻哈亚文化不仅具有特定的世界观,而且在其成员的生活方式上也有体现,如着装方式、音乐品味、组织社会关系的方式等。此外,文化也显示出时间上的连续性。加尔文主义和嘻哈文化享有一段特殊的历史,这被表达为某种集体记忆。此外,它们包含了指导未来行为的具体目标和理想。就像个人身份一样,文化身份的空间和时间连续性从来都不是完整的,而是显示出各种不同的分离和中断。而且,就像个人身份一样,文化也有从出生到死亡的寿命,在这之间,它们不断地变化并相互影响。
人类身份的第三个重要方面——除了其数字的统一和时空上的连续性之外——涉及「反身性」的特点。我们在关于游玩的章节中已经提到了反身性的概念,当时我们讨论了作为人类游玩特征的双重存在。反身性由「个人对其自身经验的回顾」构成(Mead 1934, 134),或者换句话说,拥有「经验我们的经验」的能力(Plessner 1975, 364)。在身份同一性的语境中,那些个人和文化身份所特有的时空连续性是为谁而产生的?当我们提出这个问题时,我们就遭遇了反身性的维度。尽管其他人可以将我们归于某种个人或文化身份(这显然会极大地影响我们经验自我的方式),但我们自己才是真正最终经验我们的个人和文化身份的人。反身性指的是自我意识、自我反思、拥有自我形象。我们在日常对话中、在穿着方式、生活方式等方面表达自己,同时也经验着别人对我们的描述和对待方式,但对我们的身份至关重要的是我们是否在这些(再)呈现((re)presentations)中认可自己。一个人是否认同自己是女性,认同于伊斯兰教,或认同于嘻哈文化(或可能同时认同三者),这不仅总是由身体特征、行动、习惯、偏好或信仰决定的,而且还取决于这个人是否认为和承认自己是如此 [33]。
总而言之,我们的个人和文化身份并不是一个隐藏在我们「内在自我」或「民族精神」的深处,自足的、不变的实体,而是借助于各种表达方式在社会世界(social world)中被反思性地建构起来的。
根据诠释学哲学家保罗·利科的说法,在这些表达方式中,(生命)故事起着突出甚至是关键的作用。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生命故事特别适合表达我们身份的空间与时间的连续性。在一系列的著作中, 利科将此洞见发展为一套完整的「叙事身份(narrative identity)」的理论 (Ricoeur 1985; 1991a; 1991b; 1992)。他的出发点是这样的:「回答「是谁?」的问题……意味着叙述一个生命故事」(Ricoeur 1985, 335)。只有在我们向别人和自己讲述有关我们自己的生命与别人的生命的(真实或虚构的)故事中,我们才能够充分地清楚表述我们的自我,而只有通过将自己认同于这些故事,我们自己的身份才能形成。因此, 对利科而言,叙事不仅是人类身份的一个恰当的隐喻,而且也是我们用来赋予我们身份形式的卓越媒介。我们甚至可以说,对利科而言, 我们的身份是被包括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之中的。
乍看之下, 利科的叙事模式为「游玩身份(ludic identity)」建构的理论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起点。从赫伊津哈的《游戏的人》的角度来看,文学完全属于游玩的范畴。赫伊津哈在他的专门讨论游玩和诗歌关系的章节中写到:「所有的诗歌都诞生于玩:崇拜的神圣游玩,求爱的节日游玩,竞赛的军事游玩,傲慢、嘲讽和谩骂的争辩游玩,风趣和聪慧的机敏游玩」(1955, 129;cf. Raessens 2009, 88)。在再次列举了我们在游玩一节中讨论过的游玩的六个特征(自由的表达、假如的特征、紧张和快乐、特定的时空限制、由规则支配、创造秩序)之后,他甚至指出:「现在必须承认,这些品质也适合于诗歌创作。事实上,我们刚刚对游玩的定义也可以作为诗歌的定义」 (Huizinga 1955, 132)。其实,在一个变得越来越严肃的文明中,诗歌甚至是游玩最后的避难所:「整个文明变得越来越严肃——法律和战争、商业、技术和科学都与游玩无关了;甚至仪式,这个曾经表达游玩的卓越领域,似乎也共享了分离的过程。最后,只有诗歌仍然是活生生的、高贵的游玩的堡垒」(ibid.,134)。
那么,在利科的论述中,故事是如何帮助我们建构身份的呢?[34]
利科的出发点是,(生命)故事并非提前给定的和静止的,而是通过我们的行动和我们对它们的叙事反思而获得某种形式。根据利科的说法,我们可以在这个过程中辨识出三重「摹仿(mimesis)」 。
第一重,即「摹仿1(mimesis 1)」,与我们日常生活的叙事性的预先构造相联系。在利科看来,这关乎指导我们行动的实践知识。我们在意义的层面经验我们与他人的交往:我们辨别动机与利益,我们设定标准并赋予价值,尝试在生活中实现某些理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的行动已经包含了一种隐含的叙事。我们的生活是一种不懈的「叙事的追求」(Ricoeur 1991a)。
利科将人们所经验的前叙事的连贯性在明确的叙事中的表达称为「摹仿2(mimesis 2)」。他用拟剧理论的术语(dramaturgical terms)来描述我们身份的叙事建构的第二阶段,这源于亚里士多德在其《诗学》(Poetics)中对悲剧的分析。根据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情节(plot,muthos)这一概念是表达一系列相互联系与激励的行动的核心(1984, 2321)。对利科来说,情节 (在法文原著中,他使用的是 mise en intrigue 一词)可被理解为「异质性的综合(a synthesis of the heterogeneous)」(1992, 141)。情节将构成故事的异质性元素结合起来:事件如行动和事故(happenings),以及实存(existents)如背景和人物(cf. Chatman 1978)。亚里士多德的情节可以被看作一个完整的整体。它是一个整体,因为情节中的所有元素都是相互联系的,没有与情节无关的元素。在情节中,每一个元素都在整体的层面具有意义。它是完整的,因为这些元素共同构成了叙事的闭环。一言以蔽之,情节赋予了一个异质的整体以适当的起始、中段和结尾(Aristotle 1984, 2321)。利科将由情节所创造出来的有意义的构造称为「和谐(concordance)」。然而,此种协调并不是静止的状态,而是持续地受到「不和谐」(discordance)的危害,例如命运的逆转,威胁到叙事的意义闭环。一个故事是对一个行为的表征,它不断地被或多或少不可预见的背景和事故所挫败。这使得故事成为了一个动态的整体。由于这个原因,利科把故事称为「不和谐的和谐」(discordant concordance)(Ricoeur 1992, 141)。
叙事身份建构的第三步,即「摹仿3(mimesis 3)」,由对自我的叙事构造的反身性应用构成,这使我们认同于故事中的人物。在利科看来,故事的统一性——情节——是与故事中的人物密切相关的。讲述一个故事就是讲述谁做了什么与为什么这样做。在故事中,我们见证了一个人物的发展。就像情节一样,人物表现出一种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关系。偶然的事件通过人物得到了叙事的连贯性。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说,以「摹仿 3」为特征的身份认同,在于欲望对象(object of desire)——故事中的人物获得的和谐状态——的内在化。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一种内化(appropriation)或同一化(assimilation),导致认同者身份的改变(cf. Freud 1953,IV,156)。然而,正如情节一样,这种内在化所获得的稳定性是相当不牢靠的,因为它不断面临着异质性的回归,这威胁到我们身份的和谐。美妙的爱情、个人的恩怨、危机或成瘾、疾病和死亡——这些事故给我们的生命故事带来意想不到的转折,并不断挑战角色的和谐,最终可能摧毁它。直到最后,(生命)故事的特点都是这种和谐与不和谐的辩证关系。
在我们看来,利科的叙事身份理论为更好地理解游戏技术时代的身份建构提供了一个极好的起点,因为它阐明了人类身份建构的中介特征。然而,我们必须调整他的理论,以便将其应用于流行媒介文化。利科的叙事概念是有局限的,原因如下:
首先,在他的作品中,他几乎只注意到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由于他专注于属于「严肃的」高雅文化的作品,他似乎对在日常闲谈和生活故事中,以及在流行的虚构叙述中——如电影、肥皂剧、漫画和叙事性电脑游戏等——往往更「无关紧要的」(frivolous)的身份建构方式视而不见。
其次,他主要关注经典的小说也导致他更加强调与这类小说有关的形式要素,如单一媒介性(monomediality)、线性(linearity)和封闭性(closure)。我们在上述流行文化体裁中所接触到的各类叙事往往具有不同的形式;例如,它们是多媒介的(multimedial)、互动的、连接的,以及开放式的。如果利科的预设是真的,即明确的叙事结构(摹仿2)对于身份建构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影响了因认同这种明确的叙事结构而产生的身份(摹仿 3),那么具有不同审美形式的叙事也可能导致不同的身份形式。这正是 Ajit Maan 在《叙事间身份》(internarrative identity)中所论证的,她在该书中考察了以开放式结局或多种开端和/或结尾为特征的(后)现代主义以及非西方小说的身份构建(Maan 1999)。这同样适用于数字媒介叙述领域的自我建构。即使它们仍在「摹仿」的范畴内,它们也可能导致比经典叙事更丰富的「身份效应」。
第三,利科对「摹仿」的关注,是他理论的另一个限制。正如我们在本节前面所指出的那样,对赫伊津哈而言,「诗」所包含的内容远远超过了对人类行动的论述。它还包括崇拜的游戏,求爱的游戏,以及竞赛等等。连接到卡约瓦从赫伊津哈那里引申出来的对游玩的划分,我们认为,一个充分的游戏身份建构的理论不仅应该考虑到叙事(即「模仿」类型)是如何组成和建构我们的身份的,无论这种叙事是古典的、当今后现代的还是/或是大众流行的,我们还应该处理其他游戏表达组成与建构我们身份的方式——如「概率」、「竞争」与「眩晕」。
在我们看来,对利科的叙事性身份建构理论的扩展是必要的,因为在我们目前的文化中,经典叙事的自我-建构正日益被使用各种「游戏的」数字技术的自我-建构所补充和部分取代,正如上一节所分析的那样。当我们考虑到如今文化中的身份建构已经变得相当成问题时,我们意识到需要这样一种理论。这与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概念「反身的不确定性(reflexive uncertainty)」(Giddens 1991)有关。由于我们当下生活的复杂性、灵活性和变化性,以及表达媒介的丰富性,驾驭我们生活中那些压倒一切的不和谐特征(discordant character)已经成为了一个真正的挑战。由于其丰富性、异质性和快速发展,目前的信息和传播技术对这种不确定性起了很大作用。然而——此处我们再次触及了上述新媒介的一个模糊性——它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应对它的工具[35]。身份的建构已经成为一个高度反身性的项目,而传播媒介正是这种反身性的核心。主要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坚持认为现代传播技术的游玩性是理解当代身份建构的关键。
为了说明如何将利科的叙事身份理论适用于包括「概率」、「竞争」和「眩晕」在内的游戏类别,我们将在下文中以游玩(play)来取代摹仿(mimesis)(它与「模仿」类型有着紧密的关连)这个关键词。我们将用游玩1(Play1)、游玩2(Play2)和游玩3(Play3)来重新阐述利科的摹仿三部曲。在本节的其余部分,我们将讨论利科理论的这一扩展对当今文化中的身份建构的性质方面所提供的新洞见。
「游玩1」指的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游玩的预先构造(ludic prefiguration)。这一时刻由我们的生活经验构成,我们将自然与人类的世界体验为游玩的。例如我们注意到光或水波的游戏,或者当我们观看动物或儿童嬉戏。我们的一些游玩经验与「模仿」有关,如观察玩耍的孩子,享受一个有趣的笑话,或朋友和同事讲了一个有趣的故事时,「概率」、「竞争」和「眩晕」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提供许多游玩的时刻。「概率」的维度包括像孩子们一样「点兵点将」和与你的同事打赌谁会赢得足球决赛。而特别是「竞争」的经验几乎渗透到我们生活的每个方面。当交通信号灯变绿时,试图抢占先机的汽车司机被「竞争」精神所「感染」的程度不亚于那些想显示自己是班上或办公室里最优秀的人、是酒吧里最能喝的人或最成功的风流郎君的学生和雇员。在体育以及交通方面——仅举几个领域——「眩晕」的经验总是发挥着作用,高速运动、跑步、骑自行车、赛车、高速列车和飞行以及我们从危险活动如爬山或蹦极中所体验到的极度刺激。
然而,除了这些或多或少的传统的游玩的表现形式之外,数字媒介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存在也隐秘地以游玩的方式预构了我们的经验和行动。例如,当我们的日常工作任务、旅行和交流被我们的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上花哨的应用程序审美化时,或者当我们被邀请在粉丝网站上给运动员、女演员或政客排名时,在我们与他人的日常互动中分享随意的推文或手机相机图像时,或者互发短信参与诱惑的色情游戏时,这种情形就发生了。在一个充满游玩技术(playful technologies)的世界里,我们不断地被引诱,变得更容易接受生活中各种游玩维度。在一个游玩技术的世界里,我们被邀请去体验那些跌宕起伏的,在全世界的持续重复中自我更新的游玩运动(Gadamer 1986)。
「游玩1」指的是将日常生活和我们或多或少随意的嬉戏(paidia)看作游玩的(playful),这是一种隐性的理解。「游玩2」则指将这些经验中的游玩联结用清晰说明的、受规则制约的游戏(ludus)表达出来。除了线下世界(offline world)铺天盖地的游戏,新媒体在游玩的四个维度上都提供了大量的线上游戏活动。我们可以想到线上世界(online world)如《第二人生》,以及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mmorpgs)如魔兽世界和《星球大战:旧共和国》(Star Wars: The Old Republic),它们结合了「模仿」、「竞争」和「眩晕」,还有赌博和约会网站(「概率」)。我们在上一节已经介绍了几个例子,本书的其他章节还将详细讨论许多其他例子。我们在这里将只讨论几个例子,以阐述塑造身份建构的一些最显著的倾向。
游玩技术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倾向于将不同类型的游玩混合到一个整体的游玩体验中。在我们看来,这个特点与计算机是一个「通用机器(universal machine)」的事实有关,由于它的数字代码,它不仅能够融合我们的大多数媒介(从而导致上一节中讨论过的多媒介性),而且还能模拟所有可能的机器和实践。电脑、平板电脑或智能手机很容易成为我们生活中的 「焦点设备(focal device)」(cf. Borgmann 1984)。Michiel de Lange 在本书中通过分析印度尼西亚城市中的「根格斯」(gengsi)实践,提供了一个融合「模仿」、「概率」和「竞争」在内的例子。「根格斯」指的是声望或地位的展示,最初是指家庭地位和阶级,但现在被用来指自我定义的「现代」(being modern)。De Lange 描述了移动技术如何成为「根格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拥有和恰当地使用正确的设备「将设备上的高贵品质传染给了它的使用者」。在高度现代化的商场里展示手机,用吊坠、套筒和皮口袋装饰手机,使用「幸运数字(beautiful numbers)」,以及掌握如何正确地使用语言和交流实践的形式,都构成了对威望的戏剧性和竞争性展示。因此,手机成为演员的道具,他们把自己表现为不断发展的现代城市生活的成功主人。此外,「幸运数字」的使用可以被看作「概率」类型的游玩。许多印度尼西亚人高度重视这些幸运的电话号码,他们认为这些号码会带来好运。当然,他们承认这只是迷信,但依然如此...... [36]
游玩技术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们往往与日常生活完全融合在一起。例如,当我们与我们的 Facebook 联系人一起玩《开心农场(FarmVille)》 ,并以游玩的方式塑造和渲染我们的社交关系时,就会发生这种情况。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Sybille Lammes 在她那一章中所提供的,她描述了对地图应用(如谷歌地图)和定位媒介服务(如 Layar 和 Foursquare)的使用,这些应用如今正变得越来越流行。通过以明确的游玩的方式使用这些应用程序,我们能够在后现代城市文化中体验我们的日常生活并赋予其意义,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和 Jordan Frith 在本书中也提到了这一点。Lammes 认为,我们对这些媒介的游玩将我们从单纯的地图读者转变为「旅途中的制图师」。通过使用这些媒介,我们创造了「社会地图(social maps)」,揭示了我们的行踪、行动,以及我们与他人的利害关系。因此,地图应用和定位媒介被明确地用来在我们的日常活动和行动中创造社会和空间的一致性。换言之,它们帮助我们「为生活导航」。
正如前文中已经提到的那样,在游玩技术的世界中,世俗的严肃性和游玩之间的严格划分变得模糊了。所有种类的「严肃的事情」都获得了游戏的维度。政治领域提供了许多例子。尽管选举总是有竞争和互动,但在候选人之间的电视辩论中使用在线投票、平板电脑和智能手机作为「第二屏幕(second screens)」,则再次揭示了政治的游玩维度是如何凸显出来的。毫无疑问,政治仍然是一项就「生活必需性」做出决定的活动,甚至经常关乎生命和死亡。这里的重点是,严肃性和游玩不再相互排斥。引导无人机到达目的地的士兵颇为不可思议地类似于电脑玩家。在其他情况下,政治的游玩化也可能使压抑的政治问题更容易被「消化」。Jeroen Timmermans 的《玩转悖论:网络时代的身份》(Playing with Paradoxes: Identity in the Web Era)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他将游玩性描述为社会运动和政治活动家的战略的明确新特征。像 Treehugger 这样的「绿色博客」将「严肃的」环境问题编织进更不严肃的生活博客中。对于这些新形式的活动主义来说,游玩行为的两个特点特别重要。首先,游玩是颠覆性和批判性的行为;其次是游玩的非严肃性,正如它可以作为一种提高环保意识的不那么严肃的方法。因此,像 Treehugger 这样的博客提供了「游玩空间」(Spielraum),它既是「轻松的」(light)批判反思的平台,也是颠覆性行动的空间(Timmermans 2010, 148ff.)。
在建构游戏身份的第三个时刻——「游玩3(play3)」中,玩家从自身表达的角度理解她/他自己,反身性地将表达的结构和内容内在化。
在(经典的)叙事表达里,我们认同于按照逻辑而结构化的情节或事件的因果链条,而在游戏技术中,「多媒介性」、「交互性」、「虚拟性」和「连接性」被铭刻进我们的身份。当然,这不是被动地由媒介决定的(如技术决定论者可能认为的那样),而是玩家的主动内化,他们自己也可能游玩这些结构。使用游玩技术而产生的身份具有多媒介的特征,而叙事身份主要具有语言特征(尽管语言也可以唤起图像和音乐等媒介),而在游戏身份中,所有铭刻都是多感官的。图像、音乐、姿态都被内在化了。而且,在叙事中,被铭刻的身份具有事件的因果链条的特征,而在游戏身份中则是一个「游玩空间(play area,Spielraum)」,一个可能行动的空间。在「游玩3」的时刻,具备游玩技术特征的可能行动空间被反身地应用于自我。正如吉登斯用「反身的不确定性」这个概念所表达的那样,这种经验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在电影《黑客帝国3:矩阵革命》(The Matrix Revolutions)中,尼奥(Neo)简洁地表达了晚期现代主义的这种关键经验:「选择。问题在于选择」。
古典叙事所提供的模式依附于我们的想象力,而游戏技术所提供的「虚拟现实」则很容易被证明是一种真正的虚拟性。在《魔兽世界》里连续玩了许多小时并认同自己角色的玩家,会体验到想象和现实之间的界限如何变得模糊。「他者」已经是我们叙事身份的一部分,因为他人在我们的生命故事中总是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就像我们在他们的故事中一样,这使得我们的身份更像是一个「故事的织体」(tissue of stories),而不是一个单独的故事(Ricoeur 1985, 356)。然而,就游戏身份而言,由于我们在社交媒体上与他人的互动联系,他者是我们身份的一个更真实的方面。其他人的故事和图像在一个非常真实和明确的意义上成为我们 Facebook 页面的一部分。
尽管不同类型的游玩倾向于融合进游玩技术,但它们的主导地位可能有所不同。这同样适用于因此而产生的游玩的身份。根据主导的游玩类别,后现代身份显示出四个基本维度。「竞争的身份(competitive identity)」维度将一切——从经济生产和消费到教育、科学研究、甚至爱情关系——都变成了关乎输赢的游戏。「模仿的身份(simulational identity)」维度在戏剧性的表演中而不是在(浪漫的)精神性中表达自己。这种后现代的身份维度主要在景观社会(the society of the spectacle)中得到表达(Debord 1967)。「概率的维度(aleatory dimension)」强调了人们是如何因为出生或生活的命运游戏——即吉登斯所说的「命运的时刻」(Giddens 1991,131;cf. de Mul 1994)——而被「抛」入特定的境况中的。同时,它强调了人们如何对生活中幸运的或不幸的偶然事件抱持一种深切的开放态度。对于这种类型的身份,充满风险的社会是其「自然栖息地」。「眩晕的身份(vertigo identity)」维度的特点是寻求刺激。在这里,我们可能会想到宿命论的、狄奥尼索斯式的吸毒行为,或者许多青年文化中危险的性行为(cf. Maffesoli 2000; 2004)。
然而,与不同类型的游戏技术的情况一样,作为后现代社会特征的四个身份维度经常以各种游玩的方式融合和连接在一起。例如,为了应对赌博游戏般的生活,人们可能会采取其他游玩类型的策略。人们可能试图将「概率」拖入「竞争」[37] 的领域来重新掌握生活的不可预测性;他们可能试图过一种「模仿」假象的生活来掩饰某些境况;或者他们可能试图遁入「眩晕」的刺激中来逃避它。军事学校的健美运动员往往不仅喜欢与同龄人竞争,还喜欢在公共空间展示自己的肌肉,和/或喜欢服用类固醇药物。
在这些相互交织的维度中,游玩的人格都无法回避我们在分析游玩和游玩的媒介时所描述的模糊性。
首先,这些游玩的人格在「现实和表象」之间不断摇摆。他们扮演他们的角色,只是假装他们与其角色是一样的,但同时他们的角色扮演又及其严肃,因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现实。此外,他们参与其中的竞赛并不「只是在游玩」,而是会带来现实生活的后果。
第二,游玩的身份在「自由和强迫」之间不断震荡。他们与偶然性游玩,但同时他们也不能逃避这些偶然性的事实性(factuality)。他们在自由中表达自己,但又不断体验着媒介对他们的限制,而媒介本身又受制于市场经济同质化的全球力量。在接下来的章节中,这些力量的各种例子将被更详细地讨论。在比前几代人更激进的意义上,游玩的身份在「确定和变化」之间摇摆。尽管作为游玩的人格,他们享有不断改变人格面具的可能性,但他们仍然感觉到他们主体性的核心永远渴望着休息。
最后,游玩的身份在「个体性和集体性」之间不断摇摆。在我们的游玩中,游玩的身份表达了最深处的主体性,但与此同时,他们又始终追寻着变成另一个人的模仿欲望(memitic desire)(Girard 1961)。
最重要的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拥抱游戏,就像游戏全心全意地拥抱他们一样。
注释 Notes
注释 Notes
- 参见 Julian Dibbell,他声称我们正在见证「一个不寻常的新工业革命的出现,它由游玩驱动,就像第一次由蒸汽驱动一样」(2006, 297)。
- 这些章节的内容概述在本书三部分的开头分别作了介绍。
- 不幸的是,围绕《游戏的人》的接受所产生的混乱部分原因是由于翻译不当。例如,英译本(Boston: Beacon Press, 1955)的副标题是「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我们标注的斜体),这显然是荷兰语副标题的误译:「Proeve eener bepaling van het spel-element der cultuur」(我们标注的斜体)。此外,根据1944年在瑞士出版的德文版和赫伊津哈自己对文本的英译来看,英译本并不完整,而且并不总是按照荷兰语原文逐字逐句地翻译(部分原因是赫伊津哈在「二战」爆发后重写了部分文本)。在本书中,我们引用了英文版的内容,但在不正确或不完整的情况下,我们提供了我们自己对荷兰原文(1938年)的翻译,它被重印在1950年出版的赫伊津哈的著作集中。
- 赫伊津哈在第28页和第132页给出了两种略有不同的关于游玩的表述。在整本书中,他对这些要素做了进一步的澄清,我们在澄清这个定义时提到了这些要素。
- 在英文翻译中,荷兰语短语「niet gemeend」(字面上的 not meant)被错误地翻译为「不严肃」(not serious)。为此,我们将错误的英文翻译替换为正确的翻译。
- 「通过更仔细的考察……游玩和严肃性之间的对立被证明既不是确凿的也不是固定的。我们可以说:游玩不具备严肃性「non-serious-ness, niet-ernst」。但是,这个命题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游玩的肯定的性质,此外,它还特别容易被反驳。只要我们从「游玩不具备严肃性」(niet-ernst)前进到「游玩是不严肃的」(not serious, niet ernstig),这种对立就会使我们陷入困境-——因为有些游玩确实可以非常严肃」(ibid., 5)。
- 赫伊津哈在《游戏的人》中只提到了四次魔圈的概念:两次是作为不同种类的游戏场的例子(10, 20),两次是非常笼统的术语(77, 212)。然而,在游戏研究中,这个概念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流行语,特别是在 Salen 和 Zimmerman 写出《游玩的规则》(Rules of play, 2004)之后。关于这个概念和其他概念(如「魔力节点」(magic node)和「拼图」(puzzle piece))的价值的接受史的讨论,见 Lammes (2008), Juul (2008), Nieuwdorp (2009), and Copier (2009)。
- 尽管在赫伊津哈对游玩的定义中,将荷兰语「naar bepaalde regels」(根据某些特定规则)翻译为「固定的规则(fixed rules)」显然是不正确的,但在《游戏的人》的荷兰语版本中其他没有被逐字逐句翻译的地方,赫伊津哈明确声称游戏的规则是「onwrikbaar」(irrefutable,不能否认的),他还说:「游戏的规则是不能否认的。我们可以改变(vary)一个游戏,但不能修改「modify」它」(「De regels van een spel kun- nen niet gelogenstraft worden. Het spel kan gevarieerd, maar niet gemodifi- ceerd worden」(1950, 235)) 。
- 根据一些批评家的观点,赫伊津哈的定义是普遍主义的和本质主义的,因为它假装涵盖了游玩和游戏的巨大多样性。然而,在我们看来,我们不应该把我们在赫伊津哈对游玩的定义中所区分的六个要素理解为单一的特征,相反它们是一套标准,共同构成了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家族相似性(family resemblance)。当一项活动至少满足这些标准中的几个时,它就属于游玩的家族了。维特根斯坦在他反本质主义的论证中使用了「游戏(Spiel)」这个词作为典范案例(1986, 31-2)。
- Caillois(2001,11-36)。Paidia 和 ludus 通常被理解为英语中 play 和 game 的区别。
- 通常,在游玩和游戏中,我们会发现上述类别的组合。例如,在足球比赛中,不仅有明显的竞争维度,而且「概率」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抛硬币,幸运射门),就像「模仿」(球员的戏剧性行为)和「眩晕」(球员和兴奋的球迷)一样。此外,足球既包括严格的规则管理行为,也包括更多自发的游玩元素,例如,球员的个人风格。此外,这四个类别可能成为彼此的对象。当谈到竞赛和再现时,赫伊津哈指出「这两种功能可以用这样一种方式结合起来,即游戏(spel)「再现」了一场竞赛,或者变成了对某物的最佳再现的竞赛」(1955, 13)。第一个例子是国际象棋,它再现了一场战斗,而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在前苏格拉底的文化中找到,在狄奥尼索斯的狂欢节上,悲剧家们为了赢得最佳悲剧的奖项而相互竞争。
- 「技术、广告和宣传到处都在促进竞争精神,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规模的手段来满足它。当然,商业竞争不属于自古以来的神圣的游玩形式」(ibid.,199-200)。
- 英译本中缺少这一表述。在荷兰语版中,这段话是这样说的:「在很大程度上,它涉及到由现代精神/心理交流技术引起或刺激的习惯,如对平庸娱乐的需求,这很容易满意,但实际上是不会满足的,对粗暴感觉的渴望,以及在权力展示中的消遣」。(「Het betrof voor een groot deel gewoonten die hetzij veroorzaakt of in de hand gewerkt worden door de techniek van het mod- erne geestelijk verkeer. Daaronder valt bijvoorbeeld de gemakkelijk bevredigde maar nooit verzadigde behoefte aan banale verstrooiing, de zucht tot grove sensatie, de lust aan massavertoon」)(Huizinga 1950,237)。
- 参阅伽达默尔对玩的分析,他强调:「所有的游玩都是一种被玩(All playing is a being- played)」(2006, 106)。
- 所有的游玩(Spiel)都至少有可能是「对观众的展示(Schauspiel)」(Gadamer 2006, 109)。另见本书中 Jeroen Timmer-mans 的章节。
- 这与米德(Mead)和戈夫曼(Goffman)等符号互动学家所提出的身份概念相联系(例如,Goffnman 1959,77-104)。正如 de Lange 所解释的那样:「戈夫曼观察印象管理的分析单位是「团队(team)」:一群人在一起相互协助扮演一个角色,并被互惠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一个人也可以是一个团队。他可以是自己的观众,也可以想象有观众在场」(2010, 59)。
- 关于审美经验的双重特征的详细分析,见 Jos de Mul, Disavowal and representation (1999, 173-92; cf. Mannoni 2003, 68-92)。
- 参见 Kücklich:「游玩使符号的意义流动化;它打破了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固定关系,从而使符号具有了新的意义。这可能也是游玩的隐喻在后现代话语中如此盛行的原因」(2004, 7-8)。
- 见我们在注10中对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概念的评论(cf. Ryan 2001, 177)。
- 游玩的示能也可能无法实现,想想中国游戏代练的「打金农工」,他们必须工作而没有游玩的机会。Stephenson 揭示到:「打金农工是被雇佣来赚取游戏内货币的玩家。在离线世界中,这些玩家经常在有问题的工作环境中长时间工作,报酬很低……然后将游戏中的货币卖给其他玩家」(2009, 598)。
- 对电脑代码的关注(解释)是人文学科中新兴的「代码批判研究」(critical code studies)领域的一部分。然而,Lev Manovich 更喜欢「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这个更普遍的术语。他写道:「在20世纪末,人类为其文化增加了一个根本性的新维度。这个维度就是通常所说的软件,特别是用于创建和访问内容的应用软件」(2008, 14)。
- 真实的虚拟性(Real virtuality)「是一个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现实本身(即人们的物质/符号存在)被完全捕获,完全沉浸在虚拟的图像设置中,在虚构的世界里,表象不只是在屏幕上呈现并通过它来传递经验,屏幕本身就成为了经验……「流动的空间」和「永恒的时间」是一种新文化的物质基础,即真实虚拟性的文化」 (Castells 1996,373,375)。
- Julian Dibbell 在他关于中国游戏代练打金农工的文章中注意到,将工作和游玩对立在这里很有问题:「这些年轻人现在会用他们宝贵的少数自由时间做什么?他们会如何娱乐自己?我跟着他们走出房间,看到一些人退到他们公司的宿舍里闲聊,而另一些人坐在休息室里看电视,我并不感到惊讶。但事实证明,他们中相当多的人——几乎一半——直接去了附近的网吧,在晚上做着他们的工作要求他们做一整天的事情:玩《魔兽世界》。而这一点我很难解释」(2008,84)。
- 「严肃游戏」这个词「 很容易招致批评,因为它的字面意思是一个矛盾的修辞。游戏本质上是有趣的而非严肃的」(Ritter- feld, Cody, and Vorderer 2009, 3)。
- 例如,请看索尼的PlayStation Portable(PSP)的电视广告「厕所的遭遇」(Restroom Encounter),一名男子沉浸在玩游戏的过程中而在小便池前尿湿了裤子
- 原视频在Youtube上已无法播放
- 「我们需要仔细拆解《维基经济学》(Wikinomics)、「We-Think」和《融合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主张,以便更好地理解那欢迎我们的勇敢新世界」。
- 荷兰环境网络博客 new-energy.tv 制作了这样一个游玩性抵抗的电影片段,其中有一个演员模仿美国前总统乔治·W·布什就气候变化问题向全国讲话。www.new-energy.tv/overig/opwarming_bush_spreekt_natie_toe.html 。
- 我们的身份同一性的概念不同于基督教-笛卡尔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自我被理解为永恒的灵魂。不过,勒内·笛卡尔把自我定义为「一个会思考的东西」(1968, 106),他把这种会思考的实在设想为一个孤立的、永恒的、没有肉体的实体。与这一传统概念相反,经验主义内部的怀疑论传统(大卫·休谟是其中最重要的代表)否认了我或自我的任何真实实在。根据休谟的观点,意识无非是感知和观念的连续流:「我总是发现这些或那些特定的感知,如热或冷、光或影、爱或恨、痛苦或快乐。在任何时候,我都无法在没有感知的情况下抓住自己,也无法观察到除了感知以外的任何东西……我们赋予人的心灵的身份只是一个虚构之物」(1956,252,259)。或者,用当代的休谟怀疑主义者丹尼尔·丹内特(Daniel Dennett)的话说,它是「神学家的虚构」,可与物理学中物体的「重心」这样的抽象物相提并论,它「并不指世界上的任何现实之物」(1992)。虽然我们同意这种怀疑主义对基督教-笛卡尔式的自我作为永恒实在的概念的批评,但我们认为,当休谟和丹尼特否认了自我的任何真实存在时,他们就把婴儿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不同于物质实体,没有对重心的主观经验,而人能够有意识地经验自身。例如,在休谟引用的那段话中,似乎不可否认的是,有一个人声称在意识的流动背后找不到自己。问题似乎是,笛卡尔和休谟似乎都同意,自我如果存在,就必定是一种实在。与现象学与诠释学的传统一样, 我们认为人的身份的本体论地位与无生命的物体如石头的本体论地位有着根本的区别,因为人是存在于时间之中的 (Heidegger 1996; Ricoeur 1992, 128)。存在并不简单地意味着我们位于(are situated in)时间之中(毕竟这对石头来说也是如此),而是意味着我们的存在具有根本的时间性,而且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时间性。尽管我们总是生活在当下,但与石头不同,在我们的行动中,我们总是面向我们未来的可能性,且也总是被我们在过去实现的可能性打上印记。
- 从洛克以来的分析哲学传统中,这种时间的连续性以及记忆的隐秘作用,也是个人身份理论的核心。在《人类理解论》(An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1690)中,洛克认为记忆对我们的身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为,既然意识总是伴随着思考,而且正是它使每个人成为他所谓的自我,从而将自己与所有其他有思想的东西区分开来,那么,只有这一点包含着个人身份,即理性存在的同一性(the sameness of rational being):只要意识可以向后延伸到任何过去的行动或思想,就可以抵达这个人的身份同一性」(1975,335)。
- 像性别转换这样的现象表明,感知和经验的现实并不一定相符。此外,身份归属方面的冲突很容易出现。例如,在波斯尼亚战争期间(1992-95年),许多自认为是世俗的波斯尼亚公民突然被波斯尼亚的一些塞族人赋予了穆斯林身份。
- 以下对利科的叙事身份理论的解释,部分改编自 de Mul 2005。
- 在后现代生活里,我们每天都暴露在多种经常相互冲突的图像和故事中,这些图像和故事通过许多不同的媒介传递给我们(Vattimo 1992)。同时,这些媒介也为我们提供了工具,以应对这种混乱的环境,并与如今日益交织的真实和想象的世界顺利互动。数字媒介使我们能够在这些世界之间游玩般地来回移动。这种游玩有时类似于命运的演出(play of fate)——或者卡约瓦所说的「概率」。每一次新的互动都可能引起新的探索和新的行动,并可能「打开新的窗口」。我们不再提前计划,而是通过我们媒介化的经验带给我们的偶然的直觉来塑造我们的日常行动。在其他时刻,我们媒介化的生活经验更像是一场剧场演出,或「模仿」。我们利用我们的想象力和潜力去扮演「假如」的情况,以游玩现代生活的复杂游戏。例如,在使用我们的手机时,我们来回移动于不在场和在场之间,并且我们这样做时并未真正地反思它(Gergen 2002)。我们完全能够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将自己从目前的现实环境中「移除」,并参与到一个我们周围的人无法到达的虚拟世界。我们想象着看不见的他者在另一边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发生这种情况的环境。我们周围的人隐秘地参与到这场游玩之中,假装自己好像没有参与,同时又想象着在这场有趣的两个演员的表演中发生了什么。
- 见注释18
- 例如,Sennett(1998)描述了晚期现代工作伦理的转变,在这种转变中,像被解雇这样的意外事件不再被看作是简单的坏运气,而被理解为自己行为的结果。
参考文献可以跳转链接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们!
欢迎赞赏或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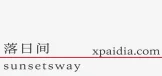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