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来一杯?”
王简接过李师傅递来的一杯液体。樱红色。凑在鼻口闻了闻,粗烈的酒精味儿中夹杂着丝丝腥甜,像这只油腻的不锈钢杯中泡进了无毛的小鼠。但杯底确实有些东西,薄薄一层白色的沉淀,王简慢慢摇晃,粉状物开始在液体中游荡。被厚厚的机修手套裹满的小杯中,像是某种东西浸泡在有机液体里恒温孵化。这样的联想让他的心中不免生出几丝忌惮,即便这远不是李师傅的货船私酒中最奇怪的产物,有次尝酒他竟喝出了一股脏器味儿,气氛像是回到他童年生活的屠宰场。
迟疑地,看着老李的堆笑以及裂出的一口龋坏的牙,王简还是吞服了下去。
“咳!咳!”一股子浓重的糖精味儿裹着高浓度的酒精,像一只蛞蝓挠进了他的喉咙,黏液与软体箍紧他的气管和胸腔。
“……你该少放点儿糖浆。”
据老李追述,他是从那堆集装箱中扒出了一批不明的外星萝状茎,淀粉含量虽然较低,但足以充当为私酒增添风味的“合理消耗”。为了方便发酵,他还加了包合成糖浆。
王简往嘴里灌了一口循环水稀释刺激,塑料瓶身都被捏扁。用手套拭了拭清鼻涕,酒精刷新了鼻腔的感觉,他又闻到货仓内满满的机油味儿。
“再来杯?”
“啊?不必了。”
走进甬道,他向背后的李师傅摆了摆手。即使他试图用嘴唇过滤,舌头上还是有股沙沙的感觉。
——————
翌日,标准时七点。葡萄串号上,底层船工舱室的照明灯集体通电,一曲嗡嗡沙哑的《春天奏鸣曲》从老旧的播放器中传出,之后合成女声空洞而优雅地预祝“我们拥有美丽的一天”。她昨天也是这么说的。
白炽灯照得王简脑门发汗,他用枕头捂住面部,想再多睡一会儿。可嘴唇干涩,鼻腔里那股私酒味儿仍挥之不去,枕头上的发油和消毒水残留也不好闻。
昏昏沉沉地,像脖子上擎着一颗生虫的橡子,他从床上疲惫地爬了起来。
挤了点无水清洁泡沫,镜子里细脆的发间点缀着白色的枯草,酸涩的胡茬,脸色更是一副蜡黄肌瘦的船工苦相。当然,这些都不是他最严重的健康问题。
要知道,远航船工是抑郁症多发的职业,但货运飞船上的随船医师可不多见,一艘船往往只有一名负责大事小情,甚至一些资金紧张的货运公司会让船工接受几个月的医疗培训后应付差事。
“咳!咳!”
抠开锡箔纸,王简服下了一粒常用的感冒药,希望止痛药和兴奋剂的成分会让他神清气爽起来。
“嗡,嗡——”
变压器的响声回绕在暗光的甬道中,只有三四条墙脚的检修灯尚在维持运作。四十七摄氏度的气温烘烤线缆的绝缘胶皮,空气中有一股仿佛橡胶燃烧的臭味(混合其他各种角落的垃圾被烤干的味道),当然电线短路燃烧也并不罕见。葡萄串号是一艘老货船,且易主多次,维修层的恒温系统早已失灵。在某部试图管理广袤银河的《航船管理法》的字句里,这艘老船多年前就:要么该在拆船厂里被熔化为新的标准件,要么干脆坠入一颗荒芜行星的大气。当然,《管理法》更严禁走私。
王简坐在通风口旁,脖子上贴着冷贴,盯着他的小型电视。电视机的电源线插头早被拔去,电线赤裸地接着检修专用的插座。录像带的画面已经泛绿,播放着不知道看过多少遍的《异形1》。打发时间是远航船工的日常难题。相比零头般的有效工作时长,仿佛这座“太空卡车”中一众精神的日渐挤窄,才是对雇主最有益的消耗。
“Bring back life form. Priority One. All other priorities rescinded”
“the damn company. What about our lives, you son of a bitch?”
虽然荧幕被眼膜反光,但瞳孔并不聚焦于晶体管的色彩变化。王简的思维逸散在过去人类对太空运输业的想象中,对他来说最为吸引的是梦幻般的冷冻技术——梦中略过引擎经年的喧嚣,醒来时便抵达港湾。这种设想约在百年前的地球上火过一阵子,甚至还有科学家用财产和遗体进行投资。当然,现在嘛,被普遍视为旧时代包裹技术理想的热门骗局之一。没有一具尸体在一轮又一轮的技术爆炸后死而复生。
片刻,他忽然站起。转过头,甬道仍旧沉闷,但王简好像听到什么声音,像是——“leng!leng!”
——老鼠的细爪匆匆爬过金属栅板,又或是顶上的夹缝塞着一只节肢动物。
可,这儿连蟑螂也不会有。
片刻之后,仍是宁静。
他刚想要坐下——
“王简?”(软舌紧凑耳语)
“wuen!”王简的身体惊得直起,忙用烘热的手套擦了擦右耳,仿佛毛孔还残留呼吸的湿度。
变压器的响声安静得不计,仿佛整个甬道都被他汹涌的心跳灌满。嘴唇干涩,沉重到可以致于静止的呼吸……
“太空型精神分裂”
随着两股蒸汽呲出,检修甬道的气闸被关闭。王简满脑子琢磨着这个曾在员工手册里出现的概念,据说发病率与航行时长正相关。但迎面的冷空气仍给他垫了些快意,何况医师的处理也不过是镇静剂了事。当然严重失常的话,会被关进漆黑的窄仓,日复一日鼻饲流食,直到停靠后随床被送进某个占地庞大的医疗建筑群的某个窄室。
可他还需要薪资,需要精神抗压能力的再生产。也许——他需要来杯老李的那种私酒?对,他舔了舔干裂的嘴皮,像在安抚一种对于甘霖的急切欲望。
对,再来一杯。
——————
“哟!小王,你来啦?”
即使隔着几十步的距离,他都能感觉到老李的神色中带着一股莫名的兴奋,他老化发麻的神经元似乎重启活跃,瞳孔里不断放射异常的生物电能。也许是货仓的循环制冷管道中补充的氟利昂,降下的几摄氏度产卵出克服沉闷空气的活力。
油迹的不锈钢器皿被换成清洗得透亮的玻璃杯,能看见浸泡着脱水果干的淡红与泡泡,果味汽水般液体明显更为纯粹,煞有其事地。他还切了两片薄薄的外星萝卷在杯口,没有气味的殷红果汁汇在杯沿。说是想带来一点含水的清香。
老李声称配方已经做了近乎完美的改良,“老实说,我从来没喝过这么棒的酒”。
即使王简半信半疑,但鼻子凑近杯口所探查到的清水香,不免让他产生嘴唇更进一步的欲望。
“呼!”
汗毛竖起。仿佛周围层层高耸的集装箱被变形的空廊压细,拥挤的金属感在一阵贴近他皮肤的冷后似乎可以概略——细细地爬过衣襟、身体。仿佛机油味儿也成为一种风味,变得好闻起来。
甚至,有点……兴奋?
“再来一杯?”
……
“再来一杯?”
“再来一杯?”
杯杯酌饮。口与鼻间,带有浊气的呼吸不断循环,酒精味儿不断被酌吸进气管的最细端。牙齿间还保留有对于根茎片咀嚼感——沁入酒精的软脆。血液中仿佛不断循环提高的醉度,让王简的眼前蒙上一层淡粉色。视距拉大、加深,仿佛一双鱼眼浸入粉色蛋白液污染的一汤,在水底朦胧地看见另一个世界的细节。
狭长的甬道变成晃动射线的背景,好像自己面朝自己地漫游。点线的两条灯光虫眼般闪烁,一条条叶网缝隙拱起甬道内壁。头上,一桩线缆在扎带崩断后散成低顶。应该是有人在抽烟?卷制的烟叶上火星退行,有一股冲味儿。闻得头晕,胡髭、衣襟的深黄体垢,让我发酸,想呕吐——“妈的!”、重拳、醉中的晕眩、眼眶的肿痛,方向感再次颠抖、跌倒,最后螺钉凑近鼻子的铁锈味儿。钢叶细细的一缝里,仿佛舷窗中无光的宇穹。
舷窗外,白色涌溢、一道强光袭眼——
耳边传来呼啸的风。
漆黑的铆接钢板,冰冷,冰冷与痛,将他的耳朵与裸体粘死上面,不得动弹。头朝黑郁的海面,他大字趴在冲向海底的铁滩。目光可及,一座灯塔缓慢移动它垂败无用的灯光,除了偶尔让王简感到刺眼。海风里有一股腥味儿,令人窒息,仿佛满滩搁浅的鲸群,脂肪正在腐烂——死寂。
天空正在沉没,把把黑色的飓风剌过穹顶边缘,残烧的重雨,淋下天际线。
此时,他的双眼死鱼般看向眼前的另一个人,和他姿势一样,赤裸地趴在钢板上。一半的脸、手掌、胸脯和肌肉没入铁中。
“简?”
嗯?
“王简!”
(激动)
“王简!!!”
(皮肤撕扯,肌肉暴露,流血。愤怒)
王简感到一大团蠕虫正在自己胃里蠕动,细密的体壁顺着食管爬上咽喉。
“唔!”
他,在迷朦中,自己看见自己爬回熟悉的房间陈设。止不住呕吐起来,酒腥、胃酸、烧喉感,随即跌倒在地板上。
灯光闪烁,眼前是他的一摊呕吐物。在阴明不定间,王简似乎看见呕吐物中不断发生细小的蠕动。一根线虫从滩糊中直立,裂出细小的尖牙。
“嘶——!!!”
——————
“********一天”
王简疼痛地睁开双眼。耳里的暴鸣只让他听清末尾的两个字,但词汇细小得仿佛尖指,勾下他喉咙里的两条肉,撕出血痕,让他不禁怀疑咳嗽里会不会带有血丝。
前额昏胀。扶住椅子,他从地板上摇晃地站起,占去视野一边的黄色收小为粘稠地平摊,渗线聚乙烯板材的细缝,在空气循环系统的作用下逐渐干燥。他拧开饮用水口,双手捧起往喉咙吸溜。又将宝贵的循环水泼在脸上,湿淋淋的手抹在后颈。消毒水的气味混入那股酸败气,变成一股奇怪但在船中并不明显的味道。
回到镜前,秽物还在脸颊一侧残留几块黄色的干膜。但右眼周的瘀青与浮肿更加明显,火辣辣的疼痛让他想用冲冷的手指去触碰。
“嘶!”
尝试进行回忆,让他的头有些晕眩沉重。爬回来的路上,究竟谁是给他一记冲拳的面孔,实在模糊不清。邋遢的胡子几乎是船上人人的标配。
他抽出一条新抹布,试图处理那滩秽物。只是擦开发干发深的表层,更新鲜的、黄色与呕吐物中浓缩的酒精腥酸味儿,黏性地附着在更大的表面。一种瘤胃腐烂的气息,王简一脸厌烦的慌忙。捏紧鼻子。白色的细小毛圈已经刮住一片,还具有滴状的流动性。双指将毛巾掷向垃圾桶口,似乎他就此无关。
——————
“物资紧张,先生”,右眼部简单被蒙上冷贴。处理完瘀伤,窄桌对面的医师对他的请求只是没有表情地回应,“你也知道,镇静剂不属于必须保障供应的日用品”。
吊扇吹动着房间中悬挂的塑料帘,响声有些清脆。抵着墙角,滤过白色的床单,一张整洁的检查床笼罩在淡黄色的半透明里。窄小密集的诊室里,有一股整洁味儿。
“或者”,医师话锋一转,“要不要我给你做一次感染检查?”
“感染?”
“你该知道的,现在贸易众多,多少会夹带一些不明的入侵物种。比如说——”,说到这里,医师顿了一顿,转了两圈太空笔,笑意难以揣测,“寄生虫”。
医师站起身来,似乎是要从身侧的药架上取下某瓶检测试剂。
他的大褂明显过度清洗,下摆毛边发硬。显得旧黄。
“现在对货船来说,相比寄生虫,精神分裂能带来的麻烦还算常见和可控。”
“……不必了……”
王简忙从座椅和诊室离开,掀开塑料帘布。即使走进甬道深处,但仍有目光落在他的后背,仿佛医师始终站在诊室门口注视着他。他的后背冒出疙瘩,有如热芒刺进毛孔。
——————
(深吸)
这让他肺叶颤栗。
冷汗,困难地吞咽口水。
即使在逼仄的房间,他仍感觉自己被不明处投来的目光凝视。
十几张药壳板散在洗漱台上。手掌捂住嘴巴,一大把的药片被堵在嘴里。
“草!”
他回头抓起椅子,扔向房间的阴暗处,仿佛那里蹲着一双直勾勾的眼睛。
嘴里的药片抖落地板,还有一些粘连在口腔粘膜。后背紧贴着墙——滑落,抱着双膝,他崩溃地躲在墙角。
在过量的精神压力中,王简思维过度的电流地锢住了某种渴望。
“酒,对!酒!”
指间薅住头发,王简暗自呢喃。
酗酒在船运业并不是一种可悲的现象。他如此劝服自己,即使……这让他与自己糟糕的父亲,事实趋同。
——————
“王简?”
“李师傅?”
“过来。”
我好像在流泪?有液体流了出来。为什么这么昏?这么黄?我的眼睛,好胀。
(声音梦呓般地恍惚)
穿过一栋栋的集装箱,看见一个集装箱打开着,货物滚了出来,堆成一个小斜坡。是那种萝。
王简走了过去。
一个个麻袋被他撕开,漏出来的萝上还挂着干黄的土粉。他的嘴角也有土,还有血。更精准地描述:他齿崩唇裂,嘴上、下巴上淌着混有汁液的血。几颗牙齿断在在被撕开的萝肉里,他就躺在这些被撕开的肉上,后背沾满颜色。
——遇刺的君王。那就应该是红色的,但在王简的眼前,却是近黑的褐色。
“过来。”
李师傅的声色近乎将死,但根本上是一种喜悦。这种喜悦在他的脸上清清楚楚。
“咳咳,过来。”
王简爬了过去,在恰当的位置李师傅抓起一只撕开的萝,流血的指尖扎进韧性十足的皮。王简跪在下面,用嘴去接和着血的汁液。他看见逐渐拧烂的果肉里有蠕动的肉线。
眼角的液体黏稠地流到了嘴边,但触碰到的,不是泪水。
(耳鸣)
(鸣叫——)
鸣叫逐渐清晰,是蝉的声音。他好像背靠在树荫下假寐,阳光暖和,空气清凉。
眼前的模糊中有个悦动的白影,凑近他的耳畔,悄悄许下稚嫩的承诺。
这一切,隐隐,似乎他十岁的氛围。
只是一个呼吸,他睁开双眼,但看见母亲坐在没有开灯的沙发上,背对站在门口的他。电视机的光亮离母亲很近,照亮她侧颊的银发,透明。
房间里一切都很安静,似乎吹进屋里的沙暴声都按下静音。只有荧幕上的人,通过喇叭沙沙地讲话。
“在某种意义上,这些青年成为了我们时代最腐败的产物”。
淀川 真(企业行会代表),如此意志。
而这便是,哥哥死亡的最后通牒。
那个喜欢穿皮夹克,站在秸秆上,对被内脏吸引来的大头苍蝇挥动球棒的青年,他曾经疯狂崇拜那些滥用致幻剂的朋克,崇拜那些反抗。而离开马来亚的屠宰场,往大都会闯荡的他,最后的下落是邮来一封死亡报告和几纸补助:他在参加反公司的大规模游行时,被公司安保用一米长的生锈撬棍打断了脊椎,死于严重内出血。
母亲的失语便是从那时起,直到下葬。
哥哥死讯后的第三年,他在公司收购屠宰场的土地合同上替母亲签了字。病床上的母亲被盖上白布的三年后,他在船运公司的“卖身契”上签了字。
离开地球的那天,他第一次亲眼见证这颗行星:从南极洲到曾经的亚马孙雨林,上面挤满了灯光。
他眼前一黑。
(“hu——en——”)
似乎耳边有什么在呼吸。
像是肉牛鼻息的湿润、
像是母亲哄睡的温柔、
像是——
床上,王简顿时睁开了眼。看着白色墙板。
(“hu——en——”)
他只是自然地鼻息。
——————
“李,死亡。死因:饮酒过量…………”,一阵键盘声后,黑色的屏幕显出几个绿字。
老化的白色塑料壳中,密集型的打印元件“嘶嘶”几声后吐出了一张发热的A4纸,上面是几张现场照片和简要说明。
船工们都聚集在货舱里,一条集装箱间的过道挤满了人,大都穿着工装、皮围裙、厚手套、马丁靴并顶着护目镜。但似乎,他们都在对他小声议议,打量着这个平时最容易忽略的人,用一种奇怪的眼神。忌惮?这让王简有些惴惴不安。
穿着白衬衫的管理层站在前面,但与大家平齐。只有船长站在高处向大家训话,但也基本是些安全手册里的固有词汇。一刻钟后,他跨下台。船工们逐渐分列,好让尸体被抬出。
当担架抬到王简面前时,白布突然被拉开,露出李师傅鼻孔放大的遗容。脸上僵住几丝笑意,显得狰狞。但更明显的,是浊黄的双眼,在发青的脸上几乎分辨不出瞳仁的轮廓。
但。恍惚间,王简看到眼睛在蠕动。眼膜顶破,沿着裂痕长出尖牙的喙。
(啸叫)
他急忙用双手用力抚下眼皮。待一睁眼,白布安然地遮在李师傅的面上。
寒意陡然。
这时,船长走到王简面前,“对了王简,你等会儿来下我办公室,昨晚有人看见你进货舱”,有些不满道,“你们多少该收敛下吧”。
他停在王简身边片刻,又面露难色,“你身上是什么味道?还有你要不去处理下你眼睛?这包扎上都黄了”。
也许是幻觉。李师傅浑浊而不再生动的眼睛,像挖取自一条招苍蝇的死鱼。但他始终觉得那是在盯着自己。
去到卫生间,看着镜子他撕下冷贴。棉质地的中心聚拢了一股黏液,还有,味道。像是死鱼。
他看着镜中的自己,右眼没有感觉地流泪。
不……不是泪,是黄色的脓液。
右眼突然睁开!开始夸张地转动,眼皮与黏液颤抖,它快速地巡视了十几个漩涡。
“啊!唔!!!!!!”
不受控制地,他的双手捂住了自己的嘴。
”唔!!!!!!”
他的右眼凝止在镜中的脸上。他的右眼,正死死地盯着他的左眼。
几只线虫从眼睑钻出,裹着粘液在角膜上扭曲。耳膜边出现了蠕动的声响。
——————
“王简?”
抄起扳手。
哞!呜——(被屠宰时,肉牛的惊惧)。
货舱的一荡中只存在着几声呻吟声。
扯下笼罩萝茎的帆布,王简的喉咙中发出几声非人的喜悦(牙齿密集地敲击)。
撕开萝茎,用牙咬,咬得牙齿松动、脱落,流血。
货舱中,红色警报灯回响时,它黏血的双指从一颗黄色发红的萝中夹出一颗卵。半透明的白,仿佛能看见成千上万的小虫在其中随红色的细光浮动。闪过遇水融化的印象。
他吞下了卵泡,内果皮般的鞘膜在唾液浸湿下溶解。
耳膜蠕动的闷响,清晰,耳膜中蟑螂窝爬行的窸窣,蜂群。
蠕动——蠕动——
眼前的一切都开始剧烈颤抖,不再真实。
恍惚间,仿佛做了一个漫长的梦,混淆了时间与空间。记忆粘着在金色树脂中的飞虫。
古老种族精神的历史,持续亿万年的蠕动和寄生。
母亲的童谣,雨林深处最古老神明的赞歌,鼓声,烟的水味,癫狂的祭司,恶魔狩猎般地收紧肢体。蛇的贴地游动,能听见三角的细鳞摩擦叶片的沙沙声
一个最古老种群的生存形态,寄生精神,渗透漫长记忆的生活方式。
跌落低重力环境的微尘。
一双散着鱼腥气的眼光跌倒在地。
——————
漆黑的舰船,掠过上方行星的大气风暴。
无人听到,它恐惧风声般地呼吸。
“hu——en——”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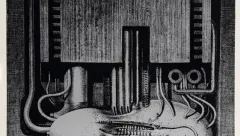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3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