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你有没有碰到过这种情况:熬过一段漫长的飞行,好不容易落地之后,却发现下一班飞机延误了好几个小时。留给你的时间十分尴尬,既不够你拟定一个在中转城市的临时旅行计划,但如果呆在机场里,又会经受一段漫长无聊的等待过程。宽敞明亮的机场变成一个玻璃牢笼: 你要么只能在各种店铺之间游荡,忍受机场里普遍的高昂价格和无聊商品;要么只能赶紧占据一个紧挨电源插座的座位,才能放心地用手机或电脑杀杀时间。 这个时候,如果你手边有一本足够有趣的书,或许会让这个等待过程变得容易一些。在所有那些足够有趣的书里,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的科幻故事集《变化的位面》[注]大概是最应景的一本。
([注]:英文原名Changing Planes用了一个双关。本意为“飞机中转”,中译选择了更符合科幻内容的另一个意思。)
位面旅行的开始
位面旅行的开始
《变化的位面》是一个由十六个短篇科幻组成的故事集,后面十五个故事都依托于第一篇《席达·杜利普位面转换法》里对位面旅行的基础设定。在这篇故事里,厄休拉用她富有幽默感的语言生动准确地表达了自己也曾受到机场中转之苦:
……机场不再是旅行的一个序章,不再是一个用于过渡的地点:它成了一个停顿、阻塞,就如同一块不能顺利排出的大便。机场这个地方的意义就在于如果你进入机场,你就不能去别的地方。在这里,时间不再流逝,所有的希望也都失去了意义。这是一个终点。
……仅有的餐桌全部被悲惨地哭叫着的小孩,威吓小孩的父母,以及身穿短裤、背心,脚穿人字拖的大个子长头发年轻人所占据……机场的书店根本不卖书,卖的都是畅销书,席达·杜利普对于这类东西向来不敢尝试,它们会给她带来相当严重的不适。
于是,在这样令人焦虑烦躁的场景里,来自辛辛那提的席达·杜利普发现了“只要经由某种扭动加上平顺地弯曲”就能轻松实现位面旅行的方法。毕竟,她已经“在班机/位面之间(between planes)”了。从书题到位面旅行方法,借由两次双关的设置,厄休拉开启了这次位面旅行。
戏仿与讽刺:基于现实的位面
戏仿与讽刺:基于现实的位面
在这十五个故事里,有些是对现实的戏仿与讽刺,有些是精妙的想象与创造。我认为,前者中最直白犀利的是《海根的王室》。
在《海根的王室》中,厄休拉是这样描述海根这个位面的:
……有些人驯养一种叫作乔基的短腿而温顺的小家畜……这些交谈是没有重点的……话题包括……万里无云的天气,不过也常有下雨的危险,或已经在下雨了;此外常被提及的还有运动,特别是海根特色的体育活动萨特普球……
……有一个被称为贵族大净化的漫长而充满暴力的时期,发生了一场名叫阋墙之战的战争,其中一段短暂而又血腥的历史称为表兄弟之乱。
上述所有这些描写(柯基、谈论天气、板球、玫瑰战争)都明确地指出,海根位面的原型正是孤悬海外的英国。与现实中的英国不同或者说相反的是,海根位面里几乎所有人都是王室成员,差别仅在于血缘亲密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的先祖里都是公爵以上的贵族,那他就比一个先祖里有公爵以下爵位的人更加高贵。因此,海根位面的人对待外来的位面旅行者总是一副礼貌而冷淡的模样。但“我”有一次来到海根位面时,却发现其中一个国家正陷入巨大的悲伤之中,几乎所有贵族乃至王室都集中在教堂前面。“我”询问了一位相识的子爵,得知竟然是一位平民女儿的去世引发了这一切。原来海根位面的诸多王国里,存在着少数平民,他们的祖先没有任何贵族血统,也上溯不到任何王室族谱里。这是一件多么奇怪的事情:
盖特这个姓,还有盖特夫人的娘家姓塔格,都是《血缘之书》中完全没有提到的。姓盖特或塔格的人从未与皇室的人或贵族通婚过……盖特家的人不知道他们是从哪来的,也不知道他们在这个王国居住了多长时间。他们是世代相传的制靴匠。
正是这样一个平民家庭中的小女儿,成为全国贵族的关注焦点与宠儿。因此,当她不幸英年早逝之后,举国哀痛。贵族们在教堂聚集为她祈祷,做遗体告别仪式,然后上街为她送葬。许多人扶着她的灵柩痛哭流涕,诉说自己对她的喜爱。在这之后,盖特家的大女儿与她舅舅的八卦故事在贵族间口耳相传,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并且经久不衰。
仅仅通过一次身份对调,厄休拉就展现了一种现象中的荒谬之处,即人们对于王室成员私人生活的密切关注。当关注者与被关注者的身份地位发生颠倒,贵族对平民的推崇与追捧成为第一层荒谬的呈现,和人们已经习惯的百姓对公众人物或社会高层的关注与八卦心相悖。然而因为故事里贵族与平民的数量也与现实正好相反,这种推崇与追捧似乎又回到了“物以稀为贵”的正常逻辑中。又或者,这个故事是在讲述差异的重要性:如果海根位面没有平民,贵族的存在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在所有基于现实的位面故事里,厄休拉并不想用刻意荒谬的设定对我们进行简单的嘲笑。她可能更希望给读者展现更多的可能性,从而引发一些思考:我们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为什么不那样?这样有什么合理之处?那样又有什么不为人所容的地方?就像地海系列里的格德对恬娜的教导一样,厄休拉更想引领读者去真的“看到”新事物,而不是仅仅通过口耳相传获取一些“知识”。当然,也有一些超越现实的新事物无法被直接看到,厄休拉就需要像格德向恬娜展现魔法一样,为我们构建一个新奇的世界。
想象与创造:构造精妙的位面
想象与创造:构造精妙的位面
人类的想象其实依然是基于我们对现实的认知,所以无论是科幻还是奇幻,只是用巧妙的语言组合将我们日常无法想到的可能性展现出来。在厄休拉的想象世界里,个人最喜欢的两篇是《安萨的季节》与《恩纳·穆穆伊的语言》。
- 《安萨的季节》
安萨人居住在两块通过陆桥连接的大陆上,北方大陆从北半球中部延伸到北极,南方大陆则往南进入赤道范围。他们在南方温暖的大陆上建立起现代化的文明城市。在那里,他们像我们人类一样拥有正常的社会生活。每一年,他们都会在南方旱季到来时,全体往北方大陆迁徙。当然,因为安萨人的星球公转周期更长,他们的一年大概相当于地球上的二十四年。所以,安萨人的寿命很少能超过三岁。
当他们跋涉过横跨大陆的漫长旅途,他们会在北方大陆过上以家庭为单位的游牧生活。不过,季节性迁徙并不是安萨人最特别的地方。伴随着季节性迁徙,安萨人在南北大陆有着完全割裂的生活模式。在南方城市里,安萨人仿佛摆脱了生殖特性的人类。没有以婚姻家庭为单元的聚居形式,所有安萨人都选择与自己的朋友生活在公寓里。同时,安萨人在南方城市里不再有男女之欲。并非他们刻意压抑这种欲望,而是真的无影无踪。只有在他们迁徙到北方大陆之后,这种欲望才会重新出现。那时,他们的这一动物性将占据生活中的大部分时间。因此,在北方大陆,安萨人就像我们的高原游牧民族一般,不但以家庭为单位聚居,而且每一家都相距甚远。
就这样,安萨人一年又一年地来回迁徙,在南方过着社会性的文明生活,在北方则淳朴地放牧和繁衍。
这不仅是模仿动物界中常见的季节性迁徙,厄休拉还借助动物定期繁衍的特性,用一种独特的方式呈现了灵肉分离的可能。
- 《恩纳·穆穆伊的语言》
恩纳·穆穆伊人的世界千篇一律地富饶美好,但物种单一。没有害虫,没有野兽,所剩无几的植物也都是十分有益的。在这种单调的美好之外,最吸引人的反而是恩纳·穆穆伊人的语言。恩纳·穆穆伊语是一种音节文字,但是每一个音节都包含好几层可能的意思,只有从一句话的上下文里才能确定某一个位置的音节表达的是什么。
这还不是恩纳·穆穆伊语最与众不同的地方。不同于人类习惯的横向或纵向书写方式,恩纳·穆穆伊人是以一个音节为中心放射状地书写他们的文字。最后写成的一段文字可能并不以最开始的那个音节为中心,甚至不以那个音节开头,而且会形成许多完全不同的形状或图案。所以,同一段文字从不同的音节出发,你会得到好几个天差地别的意思。恩纳·穆穆伊人也没有名字,在不同的场合,他们会用表达相应关系与身份的音节组合来称呼彼此。
恩纳·穆穆伊人的祖先为了避免来自生态环境中的各种麻烦,利用基因技术抹除了一切在他们看来毫无用处或者有害的物种。留给他们后代的,只剩一个单调无趣的世界。因此,恩纳·穆穆伊人只能在语言里构思各种新奇或复杂的组合。可是,由于他们复杂语言的封闭性,当他们想了解其他位面的多彩世界时,却因为无法沟通而只能望洋兴叹。
这种对于语言的设定,让人不由想到三年前被改编成电影《降临》的另一篇科幻——特德·姜的《你一生的故事》。那里面的外星语言展现了外星人对于时间的认识,因为他们认知中的时间并非线性的,所以他们的书写方式是对于思维的瞬时,或者说,更完整的直接表达。这些对于语言文字的探索,都基于语言学上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即语言会影响使用者的思考模式,相应地,语言也能反映出对世界不同的认知模式。
结语
结语
相比于地海系列中主人公在漫长旅途里的成长,《变化的位面》更像是一本游记观察。每一篇游记的标题都以一种似曾相识的新鲜感吸引着读者:《阿苏努的静默》《维克西之怒》《玛西古的悲哀故事》。厄休拉在两种身份之间来回切换,既有人类学家的田野视角,也有科幻作家的想象视角。她恰到好处地平衡着对现实的幽默讽刺与写作中的丰富创造,让读者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位面,看到各种独特的可能性。
不同于硬核科幻,厄休拉可能更希望通过她的写作,打破常识与传统加在我们思想上的枷锁。正如厄休拉在“作者按”里写下的:
正因为人的身体受到诸多限制,才会更了解和珍视心灵的自由。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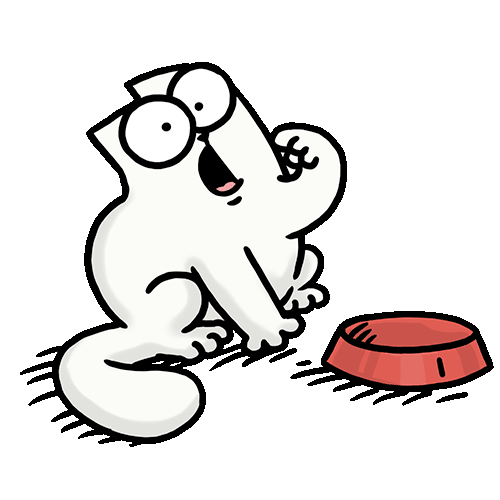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9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