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引言
引言
《黑暗的左手》是厄休拉·勒古恩于1969年出版的科幻小说,荣获雨果奖、星云奖等一众科幻奖项,其有别于传统科幻的独特风格与内容引发了持久的关注与讨论。但遗憾的是,以往的研究往往狭隘地将《黑暗的左手》局限在单一的性别议题之中,忽视了小说的多重意涵与复杂底蕴,甚至还有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攻击勒古恩在性的问题上太过保守。事实上,正如勒古恩本人在《性别是必要的吗?再版》(Is Gender Necessary? Redux)中所指出的,她对“那些坚持认为小说只讨论了‘性别问题’的批评感到抵触与气愤”,这部小说的一部分内容诚然与性别问题密不可分,但这并非小说的真正主题,至少不是全部主题。那么问题就是,在性别议题之外,《黑暗的左手》还包含了哪些复杂主题?在接下来的内容中,我们将先概述小说的故事情节,继而分析小说在伦理、政治、认识论等层面的非二元思想。最终的结论是,正是勒古恩对二元论的反思使其拒绝将《黑暗的左手》简单地视为性别问题的反映与呈现。
小说梗概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黑暗的左手》是“海恩系列”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在遥远的过去,海恩星球上诞生了最初人类,他们的足迹遍布整个星系。后来,随着海恩文明的崩溃,包括地球在内的殖民星球间彼此失去了联系,发展出了形态各异的文明体系。当这些文明再次接触时,八十三颗星球组成了爱库曼联盟,希望通过贸易与交流重现昔日的荣光。来自地球的年轻黑人金利·艾作为第一特使前往苦寒的格森星,希望能够邀请他们成为联盟的一份子。根据前任调研员奥恩的报告,格森星很可能曾经是海恩殖民者的一处实验场所,格森人在绝大多数时间中都不具备任何性征,只有在克慕期才会在荷尔蒙的作用下随机转化为男性或女性。极寒的天气导致格森星上没有诞生任何大型哺乳动物与鸟类,这使得他们无法理解飞翔。这些性别与环境因素深刻影响了格森人的社会构成,使其更加平等与和平,甚至消除了大规模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格森星不存在对峙,卡亥德王国与欧格瑞恩共生区作为格森星上的两大政体,彼此间摩擦不断。金利独自在卡亥德王国登陆,他要在得到肯定的答复后再通过安射波呼叫飞船,从而确保结盟的平等自愿原则。经过两年时间的运作,他终于在首相伊斯特拉凡的帮助下即将觐见国王阿加文十五世。但就在觐见的前一天,伊斯特拉凡却一反常态地向金利表示,自己将不再向他提供任何支持,这种反复无常的态度引起了金利的强烈反感。但他并没有想到,第二天清晨,伊斯特拉凡就被判处叛国罪而驱逐出境。昨夜他的反复无常正是在向金利发出预警。他在卡亥德与欧格瑞恩的领土争端中,因为不忍当地民众受难而将土地拱手让给敌国。这加重了国王对其所引荐的金利的怀疑,加之金利觐见时的话语挫伤了国王的自尊,导致这次觐见不欢而散。失望的金利在卡亥德四处游历,得知国王的表弟兼新首相泰博正在煽动一种仇恨敌国的情绪以加强国家的凝聚力,战争似乎即将出现在格森的大地上。在迷茫中,金利来到了隐居村,那是韩达拉信徒的遁世之地,他们能够进入多瑟状态增强自身力量,并且具有预知未来的能力。但与此相对的是,他们实际上所推崇的却是无知无为的状态。金利从预言中得知,五年后格森星将加入爱库曼联盟。受到鼓舞的金利决定前往邻国欧格瑞恩继续完成自己的使命,不同于卡亥德的君主专制,欧格瑞恩的事务由委员会协商决定,却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金利在这里受到了很好的接待,顺利结识了三位愿意支持他的委员。而这一切都是因为在金利抵达欧格瑞恩之前,伊斯特拉凡就已经九死一生地逃亡到了这里,并且力劝高层批准金利入境,暗中为他铺平了道路。金利无法理解伊斯特拉凡此举意欲何为,伊斯特拉凡则表示如果欧格瑞恩能够加入爱库曼联盟,那么卡亥德势必会紧随其后加入,自始至终他都以一种不靠仇恨敌国的方式深爱着自己的祖国。同时,伊斯特拉凡还暗示金利,欧格瑞恩并不像他所想象的那么安全,这里的民众生活在腐败的政体与集中营的威胁之下,关于金利的新闻并没有得到广播。但当金利意识到这点时已经太迟了,他的存在已经威胁到了秘密警察组织萨尔伏的统治,他们反对自由贸易。金利因此遭到政客出卖而被捕入狱。在监狱中他被注射了吐真剂并受到审讯,他联系飞船的安射波也因此遗失。最终,金利被运往了志愿农场,欧格瑞恩委员会希望他能够死于当地恶劣的环境与艰难的劳动。伊斯特拉凡对金利的遭遇心生愧疚,乔装打扮混入农场,通过进入多瑟状态救出了奄奄一息的他。二人只有冒死穿越戈布林冰原才能重返卡亥德,届时卡亥德出于曝光欧格瑞恩丑闻的目的势必会答应加入联盟。金利的力量与伊斯特拉凡的生存技能互补协作,使得二人在穿越冰原的过程中变得亲密无间。在此期间,伊斯特拉凡还进入了克慕期,尽管两人间并没有发生任何性层面的关系,但却更加了解对方,金利也消除了对伊斯特拉凡及格森人的误会,将他们视作完整的人。金利教给了伊斯特拉凡一直好奇的心语的能力,在那里他听到了他死去的兄长阿瑞克的声音,他们曾经像传说中的夏斯兄弟那样打破禁忌宣誓终生克慕,但最终导致了兄长的死亡与伊斯特拉凡的流亡。最终,二人在登上冰原第五十多天后抵达了卡亥德的边陲小镇,在那里发射了呼叫飞船的信号。他们借宿在伊斯特拉凡曾经帮助过的赛斯切尔家中,但赛斯切尔却告发了他们,以换取泰博的奖赏。为了掩护金利,伊斯特拉凡故意被探子发现而被枪杀,金利则被关进了监狱。随后,金利呼叫的飞船降临,引发了欧格瑞恩政府的垮台与泰德的引咎辞职,两个国家最终都加入了爱库曼联盟。尽管所有人都知道伊斯特拉凡在推动结盟上做出了巨大贡献,但阿加文国王却仍然拒绝收回伊斯特拉凡叛国的判罪。金利带着愧疚的心情拜访伊斯特拉凡家族,在伊斯特拉凡的儿子索伏身上,他看到了与伊斯特拉凡同样的好奇与希望。
只有性别议题?
只有性别议题?
大卫·希金斯(David M. Higgins)在《科幻和奇幻小说中的女性》(Women in 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一书中将《黑暗的左手》视为“第一部在评论界和商业上都获得成功的基于性别的科幻小说”,并将其放在女权主义运动的历史背景中加以看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民众的注意力都在马丁·路德·金等人所领导的民权运动之上,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案》在提升黑人与少数族裔待遇的同时,也顺带包含了禁止就业中性别歧视的条款。随着种族平等斗争逐渐走向平缓,妇女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便成为了新的斗争焦点。1966年,贝蒂·弗里丹 (Betty Friedan)等人注意到,《民权法案》中有关性别歧视的条款并没有得到有效执行,因而成立了美国全国妇女组织,开展女权主义运动。而1969年出版的《黑暗的左手》恰恰诞生于这项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其中关于性别问题的内容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所有人关注的要点。也就是说,《黑暗的左手》中的性别因素受到过度重视实际上出自美国六十年代时代思潮的推动,而在很大程度上并非小说自身的直接结果,甚至违背了小说本身的创作意图。当我们抛开社会因素,仅仅从文本本身出发时,一个问题便油然而生:《黑暗的左手》真的是一部“基于性别的科幻小说”吗?大卫·凯特尔(David Ketterer)在《厄休拉·勒古恩的“冬星之旅”原型》(Ursula K. Le Guin's Archetypal “Winter Journey”)一文中从叙事学的角度指出,格森人雌雄同体的设定并非小说情节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完全可以在完全不提及格森人雌雄同体特性的情况下概括《黑暗的左手》的故事情节,同时保证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也就意味着“格森人的性行为,就像格森星的气候一样,与表面情节的关系不大,而与潜在的破坏或分裂、创造或统一的神话模式有关。”斯坦尼斯拉夫·莱姆也在《错失的机会》(Lost Opportunities)中指出:“卡亥德人奇怪的双性恋只是其有趣背景的一部分,这些本可以抵达本体论深度的元素只是外星现象的多样片段,真令人感到遗憾。”
大卫和莱姆的批评实际上提供了一种正确看待《黑暗的左手》中的性别问题的视角,那便是将其放在与格森星的自然环境、宗教信仰同等重要的位置加以考察,避免对其他元素的倾轧。不仅仅是雌雄同体,严寒气候、缺乏大型哺乳动物与鸟类、奇异的宗教信仰等多种因素共同构成了格森人的独特性。就像勒古恩在《性别是必要的吗?再版》中所清醒地认识到的,如果男女之间实现了真正的完全的平等,我们的社会势必会与今日不同,但性别问题并不是造成社会问题的根本与全部来源。将《黑暗的左手》完全局限于女权主义的解读实际上是在拿表面的性别问题当做挡箭牌,从而忽视甚至加剧了导致性别问题出现的更深层的二元对立思维。只要这一二元思维仍然支配着人们的行为,那么矛盾也只不过是从性别问题转移到了另一个矛盾之上:“天知道等到男女平等时我们的麻烦会是什么,我只知道我们肯定还会有麻烦。”这个麻烦现在是对女人的剥削,之后则可能是对自然环境、底层民众、人工智能、其他物种等诸多处于二元对立中弱势的一方的剥削。必须意识到凡此种种,皆为“黑暗的左手”,而不能仅仅将性别这一个层面无限放大,导致它成为“黑暗的左手”群中处于“光明的右手”的一方,遮蔽了其他问题。这也就是勒古恩这篇文章标题的含义,性别问题是必要的吗?是。但当性别问题被认为是《黑暗的左手》的全部与根基的时候,那便不是了。这并不意味着《黑暗的左手》的女性主义解读是不重要的,只是希望在大量研究已经老生常谈地重复这一问题时,补充一些同样重要的角度。
除了性别之外我们还能谈什么?
正如基思·赫尔(Keith N. Hull)在《什么是人类?厄休拉·勒古恩与科幻小说的伟大主题》(What is Human? Ursula LeGuin and Science Fiction's Great Theme)中所指出的:“《黑暗的左手》将人类定义的拓展与格森星的文化、生物学和地理学如此彻底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像《沙丘》一样,主题过于丰富”,这使得我们不能只关注其中的某一方面而忽视其纷繁复杂的目的与意义。勒古恩所要捍卫的并不仅仅是女性,而是一切被统治、被占有、被利用、被不公正对待的存在。《黑暗的左手》最终要表达的是,“毁掉我们的价值观上的二元论,使其被一种更健康、更合理、更有希望的,关乎融合与完整的方式所替代。”这种替代方案不仅仅体现在格森人的雌雄同体的性别层面,更关乎其伦理、政治与认识世界的方式。
在伦理层面,厄休拉·勒古恩在《性别是必要的吗?》的初版中略带赌气地指出:“事实上这本书的真正主题不是女权主义、性、性别或其他类似的话题,至少就我看来,这是一个关于背叛与忠诚的故事。”背叛与忠诚在伊斯特拉凡身上表现地尤为明显,他继承了祖先“叛徒伊斯特拉凡”的名字西勒姆。伊斯特拉凡式的爱国,爱的是土地上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个抽象的边界。他舍弃了国家的土地,只是为了保障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他流亡海外为欧格瑞恩效力,却是为了以此将卡亥德引入联盟;他犯下不可饶恕的自杀罪,从而帮助金利逃出生天;他离开了自己的家族,却始终遵守着与兄长终生克慕的誓言。背叛与忠诚、道德与劣行的二分法在伊斯特拉凡身上是不适用的。同样的,在金利身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忠诚与背叛的二元对立的消解,他忠诚于自己的使命,为了将格森星纳入联盟耗尽心力甚至差点因此牺牲。但他的这份忠诚却是建立在对伊斯特拉凡的背叛的基础上的,他没能履行对伊斯特拉凡的誓言,没能替他洗去叛徒的污名。更进一步说,背叛与忠诚实际上关涉的是如何处理自我与他者冲突的问题。这首先体现在《黑暗的左手》的叙事结构上,尽管都以第一人称出现,但金利的报告与伊斯特拉凡的日记的指向是不同的,报告隐含着作为读者的他者,而日记则指向自我。在金利的报告中,满是对伊斯特拉凡背叛的不满与猜疑,而伊斯特拉凡的日记则冲淡了这种情绪,二者并置在前后章节之中时,自我与他者、背叛与忠诚便交织在了一起。伴随这一结构而贯穿在《黑暗的左手》始终的,是金利对伊斯特拉凡态度的转变,从最初带着刻板印象而产生的无端怀疑,到二人在冰原上最终袒露真心,金利实现了从与他者隔绝的绝对自我状态转向对他者敞开,也就是乔治·斯鲁瑟 (George Slusser)所说的“在任何关系中保持平等,并通过尊重他人来做到这一点的能力。”
当然,如果我们仅仅将《黑暗的左手》视作背叛与忠诚的故事,那就犯了与过度放大其中的性别问题相同的错误。在再版中,勒古恩对初版将小说核心思想框定在单一维度的行为展开了反思:“‘事实上这本书的真正主题……’这样的话全是吹牛。”她不满足于性别、伦理层面的解读,点明了《黑暗的左手》的政治维度:“在最开始写的时候,我想写一本关于没有战争的社会中的人们的小说。这是最开始的念头,雌雄同体是后来的灵感。”与没有战争相对的,“代替对平衡与完整的追寻的是对权力的斗争”。政治在《黑暗的左手》中扮演着相当重要的角色,芭芭拉·巴克纳尔 (Barbara J. Bucknall)在《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一书中指出: “就像《失去一切的人》一样,女权主义的主题相对于政治来说是次要的。”欧格瑞恩与卡亥德的对峙带有明显的冷战色彩,欧格瑞恩与苏联政体的相似性更是显而易见,二者对爱库曼联盟的兴趣仅仅在于通过它可以起到打击对方的作用,而从来没有真正考虑过联盟究竟可以带来什么,这本身就是对两极化政治盲目状态的隐喻与讽刺。而在这两个对立的国家内部,同样存在着暗流涌动的二元性,从而在批判中避免了二者的乌托邦化。卡亥德是一个“伪封建制度的部落式经济单元”,尽管它的统一已经实现了数百年,但这却是建立在其松散的政体之上的,就像伊斯特拉凡面对戈林亨林部落时所说的,“正是这些领地让卡亥德成其为卡亥德”,人们肆意取笑着掌握最高权力的国王,他们只为自己的家族负责。维系他们的并不是权力,而是“希弗格雷瑟、个人的尊严和威信”。可以说,卡亥德是一个绝对的自由主义之地,是海因莱因设想中理想美国的样态。但勒古恩则在其中看到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可能性,松散的政体意味着权力存在失去约束的可能,当一个像泰博那样的首相上台时,他可以肆意煽动民众对于敌国的恐惧,而将这种恐惧与憎恨包装为爱国主义,就像希特勒曾经对犹太人所做的那样。与之相对的,金利最初认为欧格瑞恩是一个更好的政体,共生区既可以指代国家,又可以指代每个个体,这似乎意味着国家利益与个体利益的高度绑定,三十三人集团群策群力治理着国家。但当他看到叙斯吉斯专员奢靡的生活、人们毫无生气的眼神,以及萨尔伏的恐怖统治时,之前所看到的一切就都变了味道。这两个国家都是建立在二元对立的基础之上的,卡亥德依托的是爱国与仇恨,欧格瑞恩则靠着官僚与底层。本质上都是自我对他者的压制,而只有在平等对待并尊重每个个体的前提下,政治才可能走向乌托邦。这个乌托邦在《黑暗的左手》中就是爱库曼联盟,它“通过协调而非控制来实现其作为政治实体的功能。它不实施法律,决议的基础是审议和一致同意,而非多数同意或命令。”法律意味着一个高高在上的裁决者,而协商则意味着参与者间平等地沟通。
除去伦理与政治层面的非二元主义,勒古恩还将《黑暗的左手》中的性别问题背后的逻辑推向了认识论的高度:“我所追求似乎又是一种平衡——‘男性’的驱动式线性思维:力图超越极限、不容许边界的逻辑——与‘女性’的循环性思维:重视耐心、成熟、实事求是、可持续性。”金利在格森星的活动实际上就是一个循环,他从卡亥德出发,最终又回到了卡亥德,并在那里完成自己一开始未能完成的使命,他的足迹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这种循环思维还表现在格森星的历法之上,每一年都是其纪年的基准年份,人们永远生活在元年。这就打破了西方长期以来的线性发展的思维,时间并不是一个指向未来的箭头,而是在不停地循环。在小说的结构上,《黑暗的左手》同样表现出对线性思维的自觉抵抗,它由人类学报告、神话传说以及日记等多种体裁杂合而成,构成了非连续性的叙事结构。这些插入的章节之间并不存在着明显的前后关系,并在穿越冰原时“不合时宜”地插入大量打断叙事推进的景物描写,破坏了小说的连贯叙事,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黑暗的左手》对线性思维的反思还体现在其对确定性的消解之中,线性思维不容许边界的存在,强调边界两侧的天差地别。但当伊斯特拉凡询问地球上的男女间有何差异时,金利却指出:“将先天差异同后天习得的差异区分开来,是极其困难的。”但二元对立的思维却总是固执地认为先天胜过后天,却没有意识到他们所谓的先天差异很可能也是后天习得的结果。地球人认为性别是一种先天的东西,但格森人的例子则说明了,性别差异并非自然如此,而是海恩实验的结果。这种人为的性别对于格森人来说是自然的,甚至影响了他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其他方面,我们同样无法区分哪些特征是自然如此,而哪些又是世代传承的结果。金利无法向格森人描述自己飞船的工作原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天生愚笨,而是缺少鸟类让他们理解飞这个动作。先天也好,后天也罢,就像小说书名的来源“光明是黑暗的左手,黑暗是光明的右手。生死归一,如同相拥而卧的克慕恋人,如同紧握的双手,如同终点与旅程”所表明的那样,重要的不是差异而是相似性与关联性,不是确定性而是模糊性。酷似道家思想的韩达拉教认为:“造就生命的是永恒而难以容忍的不确定性”,而唯一确定性的事情就是死亡。生命就是变动不居的,就像《易经》中的爻变与阴阳的交融。因此,他们的预言往往只会给出一个模糊的答案,就像第四章“第十九天”中他们对询问自己何时将会死去的勋爵时所做的那样。他们的预言只是为了表明知道错误问题的答案是毫无用处的,重要的不是一个已经死去的答案,而是鲜活的问题。就像勒古恩不厌其烦地强调的,她的小说“是问题而不是答案,是过程而不是结论。我认为科幻小说的主要功能之一正是提出此类问题:颠覆惯有的思维方式,用隐喻表达我们的语言还不能明确的事物,进行想象力的实验。”当我们将《黑暗的左手》限制在性别问题的解读方式之中时,《黑暗的左手》便死了,确定性将裹挟着它一路奔向线性思维与二元对立。而只有充分认识到诸如伦理、政治、认识论乃至其他诸多解释面向,才能重新唤起作为问题的小说的活力,从而向着非二元思维敞开自身。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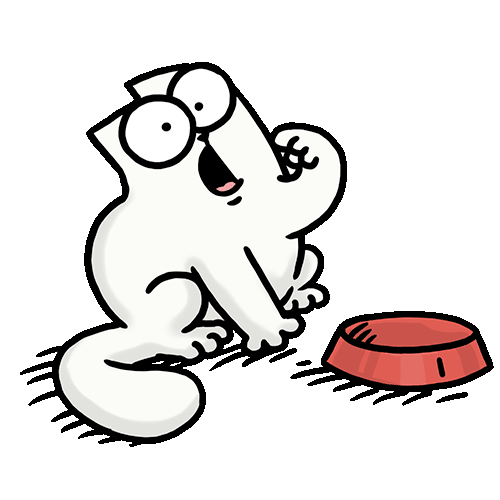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