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文中包含剧透内容,请注意
1976年6月27日的法航139号劫机事件从大范围看来,只是70年代数百起劫机事件中的一次。但是它被很多人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促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跨国反劫机作战行动。1976年7月4日凌晨,一百名来自以色列国防军的特种士兵在90分钟的时间内,在距离出发点4000公里外的敌后完成了成功的救援任务,这次行动就是“雷电行动”。此后,它曾经被多次改编为电影,在1976-1977年就有三部电影基于其改编。
我在这里要谈的是第三部,也是以色列人拍摄的第一部基于“雷电行动”的电影,1977年的《雷电行动》(Operation Thunderbolt,希伯来语罗马音:Mivtsa Yonatan)。虽然说电影的故事、音乐和摄影都不是特别出色,但是它被认为是这三部里最准确的一部,基本上,剧组人员把劫机后的七天七夜都浓缩在了一部两个小时的电影里。不过,如果我们分析电影的细节,还是会发现很多有趣的东西。
电影在片头有提及他们获得了以色列国防军的辅助和支持,使用了定制的服装、兵器、飞机和车辆。不过这并不是以色列国防军全程投资拍摄的宣传片,所以剧组在某些地方其实也下了苦功。
航班生死劫
航班生死劫
1976年6月27日,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卢德机场,乘客们有说有笑地登上了法航139号客机。这是一架空客A300B4-203客机,机组共有12人,机长为米切尔·巴克斯,乘客共计190人,将飞往法国巴黎的戴高乐国际机场。在接受了相关安检手续之后,乘客们排队登机,飞机随之起飞了,随后将会希腊在雅典机场经停。
不过,电影里出现的客机是单通道窄体客机,而A300实际上是两通道宽体客机,因此影片大概是使用了法航客机真实的起落镜头,不过在拍摄时使用了波音707。至于为什么是波音707,在下文会有考证。
四个月前,一架新加坡航空的763班机在雅典降落了,机上有两位被称为“法希姆·萨蒂”和“侯赛尼·瓦伊吉”的乘客。他们的真名分别是法耶兹·阿布都拉西姆·贾贝尔(Fayez Abdul-Rahim Jaber)和贾耶尔·阿尔嘉姆(Jayel Naji al-Arjam),均为巴解组织“人阵”的高层角色。
此外,飞机上还有两个南美洲来的乘客,分别是森诺·加西亚和森诺拉·奥特加,他们实际上都是德国人,真名则是威尔弗雷德·博斯(Wilfried Böse)和布丽吉特·库尔曼(Brigitte Kuhlmann),两人并非是某些资料里“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的成员,而是来自德国的另一个左翼组织“革命之牢”(Revolutionäre Zellen)。
这次他们的目的很明确,控制法航139客机,行动代号“乌干达”。组织这次行动的也不是误传的“豺狼”卡洛斯(不过卡洛斯和博斯关系确实很密切),而是瓦迪·哈达德。之所以选择雅典机场是因为这里的安检体系可谓漏洞百出,是当时最乱的国际机场之一了。
电影里四人通过拉下电闸关闭安检系统从而逃过了检查,不过实际上,当时的金属检测器根本没人看管,四人基本上是直接走过去的。
1 / 4
法航139号升空数分钟后,飞机进入巡航高度,安全带警示灯关闭了。四位劫机犯开始从他们的随身行李里拿出武器,他们随身携带了手枪,同时还在酒瓶里藏了手榴弹,在行李的最底部藏了微型冲锋枪。四人尽可能小心地取出武器,随后当他们取出冲锋枪之后就站了起来,宣布控制飞机。由于武器一般都藏得很隐蔽,所以都要一番倒腾才能拿出来,四人刚上飞机就开始翻箱倒柜的举动确实引发了周围人的怀疑,不过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几个人的真实身份。
博斯在客舱被控制后,利用机械师雅克·勒莫内打开舱门的机会控制了驾驶室,手持一把手枪和一发手榴弹。博斯要求机组人员按照他的命令执行,机组只能照做,毕竟这是法航历史上第一次劫机事件,包括巴克斯在内没有人接受过任何训练。
机舱里,库尔曼挥舞着手枪威胁乘客不得造次,同时其他人在飞机上布设了爆炸物。控制飞机后,博斯宣布这架飞机将代号为“海法”,隶属于巴解组织“切·格瓦拉军团”和“加沙部队”控制下。“乌干达”行动的第一阶段到此结束了,可以说劫机犯控制飞机时完全没有阻力。
事件发生数分钟内,以色列空管就得到了航班被劫持的消息,信息迅速上报总理伊扎克·拉宾,后者此时在议会开会。同时,以色列精英部队“总参侦察营”(希伯来语罗马音:Sayeret Matkal)立即集结部队,准备迎接可能返回特拉维夫的客机。此外,国防部长西蒙·佩雷斯、外交部长伊加尔·阿隆、交通部长加德·雅可比和司法部长哈伊姆·扎多克也得知了消息,几人随后召开了紧急会议。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随后也了解了信息,并通知了还在家中的约拿坦·内塔尼亚胡中校(耶胡拉姆·佳恩扮演)。
飞机上,劫机犯开始收缴众人的护照,同时要求飞机在利比亚的班加西机场降落。电影里没有出现的一个细节是,当时机上有一位以色列空军的导航员,乌兹·戴维森,他一不小心露出了自己的军官名片。情急之下他的妻子萨拉把证件在自己的嘴里嚼烂,然后吐在了一个空的杯子里,逃过一劫。139在中午2点58分在班加西降落,夏季的班加西炎热无比,飞机下方巴解组织人员正在和利比亚方面交涉。直到晚上9点21分,在加了42吨油后139再次起飞。
当飞机在班加西加油的新闻传来后,总参侦察营转为待命状态。总参侦察营是以色列军情局的分支机构,直属于总参谋长。1972年5月8日,比利时萨贝纳571号劫机事件发生后,正是总参侦察营完成了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登机作战任务。当时16名队员在埃胡德·巴拉克带领下,假扮成维修工混上飞机,然后从箱子里掏出乌兹冲锋枪向劫机犯射击,最后成功消灭两人,抓获两人,仅一位人质受伤不治而亡,登机小队仅本雅明·内塔尼亚胡一人受伤。
1 / 3
在得知139再次升空后,总参侦察营再次转为警备,此时他们已经在计划要完成登机作战。然而在得知飞机转向南方飞行之后,总参侦察营被要求返回基地。此时在飞机上,库尔曼对机舱里的犹太乘客破口大骂,极尽羞辱,以至于乘客们都将她称为“活纳粹”。
6月28日凌晨3点15分,139号班机降落在乌干达的恩德培机场。降落后,三名等候在这里的巴解组织成员:弗阿德·阿瓦德(Fouad Awad)、阿布德尔·拉提夫(Abdel al-Latif)和阿布·阿里(Abu Ali)迎接了他们的同志们,并提供了AK-47步枪和其他的武器。乌干达士兵则把其他乘客看守了起来。
1 / 4
旧航站楼当时已经非常破旧,里面尘土飞扬,肮脏不堪,根本没有容身之处。机上人员随后被分为两组,第一组包括106名以色列人和非以色列的犹太人,机长巴克斯和很多机组人员也自愿留下来,其他人员,包括来自巴西、丹麦、法国、意大利、日本、韩国、西班牙和英国的非犹太人均被释放,乘坐另一架法航班机离开。实际上也有少数外国犹太人蒙混过关,机上的两名巴西人据称都是来以色列经学院学习的学生。
影片里乌干达士兵在墙上砸出一个大洞,把第一组人赶进去,和其他人分离开。这一幕确实是真的,只不过发生在第三天也就是29日。就如同片中一样,有以色列护照的都率先被揪出来送进房间,这一幕让一位大屠杀的幸存者想到了集中营里的一幕,所有人也都恐惧不已。
当日下午,乌干达总统伊迪·阿明乘坐直升机到达恩德培机场。一开始阿明用友好的语气说了一声“Shalom”(希伯来问候语),但是在一位乘客称他为“总统先生”后,他很生气地告诉她自己的全名是“阁下,大元帅伊迪·阿明·达达博士,维多利亚十字勋章(VC)、杰出服务勋章(DSO),军事十字勋章(MC)获得者”。阿明告知人质,如果以色列不释放劫机犯要求的人,他不会阻止劫机犯的行动。“乌干达行动”到此算是圆满成功了。
1 / 2
在1976年1月,三名巴解组织分子利用假护照到达肯尼亚的内罗毕机场,随后被肯尼亚警方抓获。警方随后搜出三人携带的两发苏制9K32肩扛式导弹,在肯尼亚安全单位的审问下,三人交代他们的武器是伊迪·阿明提供的,目的是在机场周围埋伏,偷袭在内罗毕起降的以航客机。可见,如果得到了国家级别的支持,劫机犯发动袭击的成功率将极大提升,也更容易获得强力武器。哈达德本人也正是考虑到阿明的态度,才会再次利用乌干达发起袭击。
谈判受挫?反击!
谈判受挫?反击!
以色列方面还是收到了情报,139号已经在恩德培降落,劫机犯要求释放43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和巴解组织密切相关的人群,比如卢德机场事件的犯人冈本公三,耶路撒冷东正教牧首卡普其等等。影片里以色列内阁随即在发布会上表示,可能会释放人质,实际上的情况也差不多。
实际上,虽然没有外交渠道,以方还是没有放弃外交联系。退役将军巴列夫曾和阿明私下通了电话,但是没有结果。埃及总统萨达特也表示愿意帮助联系乌干达,不过最后未能执行。此外,巴解组织高层也派人前往恩德培机场劝说四人释放人质,但是劫机犯们拒绝接见巴解代表(“黑色九月事件”之后,巴解组织一度要求各派别不得发动劫机行动,哈达德随后退出了人阵并另外成立了“特别行动组”PFLP-SOG)。但是谈判最后还是取得了成功,释放日期被确定在7月4日,因为这几天阿明要访问毛里求斯,暂时回不来。
影片里内塔尼亚胡等人很快就开始了训练,实际上作战方案花了不少时间去拟定。最初的方案是在维多利亚湖上伞降,从机场南侧突袭,但是这个方案很快就遭到了反对,因为维多利亚湖面积太大,伞降过于危险,而且水里还有鳄鱼。以色列空军则提出要求发动对恩德培的空袭,然后派出1200人左右的大部队空降机场,这个方案也很难实现,因为以色列空军实际上只有为数不多的一种军用飞机适合突袭任务——C-130“犀牛”。
说到以色列的C-130还得先从1973年赎罪日战争说起。在赎罪日战争期间,以色列空军发现自己暴露出的一个大问题是缺乏战略运输部队,只装备有轻型运输机和直升机的以色列空军不得不借助美国运输机将补给运送到前线。战后,以色列空军装备了C-130E中型运输机,分配给131“黄鸟”中队和103“大象”中队使用。此外,以色列空军还从以航买了5架波音707-302B客机,改装为加油机、空中指挥机、货机和电子战飞机使用。这两种飞机会成为行动的关键,没有那次战争,就不会有“雷电行动”了。
对于机场情况的搜索,摩萨德调用了东非地区的资源进行情报获取。此外,恩德培旧航站楼是乌以蜜月期间,一家以色列建筑公司承包的,他们利用当时的图纸还原了建筑的一部分,让突击队可以完成基本的训练工作。但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是,即使是只有4-6架飞机参与行动,以色列空军也没有加油机来完成加油任务。以色列空军曾设想让一架KC-130参与到行动中,腾空了油箱后用来运送人质,但是这个设想也很不确定。
没有一个东非国家表示愿意协助以色列对乌干达的袭击,一方面他们都是东非共同体成员国,不希望因为这件事惹怒阿明,另外他们也不想惹怒巴解组织或者利比亚。还好最后肯尼亚一家酒店的犹太人老板和肯尼亚农业部长说服了总统,总统同意以色列飞机能够在内罗毕经停,不过那已经是后话了。
行动方案最后也被拟定了出来,执行突击任务的总参侦察营在第一架C-130运输机内,乘坐一辆假扮成阿明专车的黑色奔驰大轿车,以及两辆假扮成乌干达军车的路虎军车,一共29人归内塔尼亚胡指挥。此外,另外两架飞机里还有四辆吉普车,装备有重机枪和火箭筒,由总参侦察营的另一支小队使用,队长是绍尔·莫法兹。莫法兹小队的任务是提供火力支援,防止乌干达军队发起反击。第三支部队来自第35“伞兵”旅下属的空降突击队(Sayeret Tzanhanim),目的是控制新航站楼、主控制塔和航空油库,为飞机加油。第四支部队来自戈兰尼旅下属的戈兰突击队(Sayeret Golani),由乌里·萨基指挥,目的是协助疏散人质,保护飞机。
总共100多人的部队乘坐四架C-130运输机,实际行动的时候还有一架处于待命。此外,两架波音707也被调集起来,第一架被改造为空中医院,将直飞内罗毕降落,准备搭救伤员。第二架707作为空中指挥机,行动总指挥官丹·肖穆龙在上面,飞机会在恩德培上空盘旋,以便于同地面联系。行动需要的最后一架C-130用来运送人质,装备2辆标致卡车,一辆负责加油,一辆负责运送伤员。
给总参侦察营演练的时间并不多,他们一般都习惯提前数周规划演习,但是现在只有两天时间。7月3日下午6点,以色列内阁通过“雷电行动”,但是谁都清楚行动失败的后果,以色列国防军还没有抚平“赎罪日战争”的伤口,一旦任务失败,一百多名人质会和同样数量的精英战士一起被敌人枪杀,羞辱,这不仅是拉宾总理个人的灾难也会是全国的灾难。总参谋长莫迪凯·古尔还记得第一次演练的时候,奔驰车就熄火了,要是正式行动的时候,还出问题怎么办?
绝杀恩德培
绝杀恩德培
7月3日,安息日的下午,5架C-130从卢德机场起飞,一架一架飞往西奈半岛南部的奥菲拉基地(原埃及沙姆·沙伊赫基地)。目的是防备无处不在的潜在间谍和雷达,还有停靠在地中海上的谍报船。同时在奥菲拉基地,内塔尼亚胡开始进行最后的任务简报,但是此时内阁还没有通过“雷电行动”,考虑到从奥菲拉到恩德培需要4-5小时,肖穆龙最后决定先起飞,要是最后不通过再飞回来。四架飞机在热气腾腾的沙漠里,带着一大堆物资摇摇晃晃起飞了。
1 / 4
四架飞机在红海上空飞行,路线要依次通过埃及、苏丹和沙特阿拉伯的领空,所以必须低飞躲避雷达。随后在即将到达吉布提和索马里的时候(法国在吉布提有基地,苏联在索马里有军事基地)转向埃塞俄比亚领空,经过肯尼亚抵达恩德培。机上非常炎热,所有人都在默默等待着行动开始。
晚上10点25分,波音707医疗飞机在内罗毕降落。此时C-130机队正在维多利亚湖上空,一号机随机脱离编队,在昏暗的跑道灯光下降落。刚一降落,飞机就关闭了引擎,伞兵旅的战士们不等飞机停下就跳下来放置应急灯,机上奔驰车也打着了火。副队长摩西·“穆基”·贝茨(电影里名字被修改为“舒基”)下令所有步枪都设置为半自动模式,避免走火。三辆车以25mph的速度向旧航站楼驶去。
影片里的乌干达哨兵很快就发现了不对——阿明换了一辆劳斯莱斯(实际上是一辆白色的奔驰),他立刻抬起了步枪。内塔尼亚胡立刻发起反击,用伯莱塔手枪将哨兵击倒在地。实际上当时的情况略有区别,内塔尼亚胡首先下令右急转,让位于左侧的他可以锁定目标。随着一声枪响,哨兵被击倒,但是伯莱塔的威力没有杀死他。路虎上的一位士兵见状立刻用AK补了一梭子子弹,将他射成了蜂巢。第二名哨兵随即也被路虎上的重机枪打死。
枪战暴露了行动,塔台上当即射来一连串的机枪子弹,以军士兵立刻跳下车来冲向航站楼。电影里一位劫机犯几乎差点就被击中——他实际上就是博斯,博斯跑回航站楼,拔枪要杀人质,不过最后一刻又停了下来。电影中确实出现了这个镜头,但是却又把博斯设定为首个丧命的劫机犯,然而实际上第一个被击毙的是法耶兹·贾贝尔,杀死他的是先冲进来的阿米尔·奥菲尔。
和电影里的场面相比,实际上要“不那么乱”一些,在贾贝尔、博斯和库尔曼倒下后,冲进来的穆基·贝茨和阿摩斯·葛伦看到第四位劫机犯正抬起他的AK准备射击,葛伦连忙抬起他的AK,一枪打烂了那人的枪机,然后又将其打倒。但是已经晚了,那人杀死了一位人质,56岁的苏联犹太人伊达·波罗肖维奇。还有一位人质也倒下了,52岁的帕斯科·科恩,根据他的儿子(当时在场)的回忆,科恩试图爬起来保护自己的儿子,不料撞进了子弹飞舞的交火线。
交火的时候,地上突然又跳起一个身影,葛伦猛然对着就是一顿扫射。然而,那人实际上是19岁的以色列公民,出生于法国的让-雅克·迈摩尼。在电影里他的名字被处理为拉米·魏斯伯格,而且是被库尔曼射杀的,和真实情况有出入。这时,奥菲尔和葛伦对着话筒大喊道:“趴下!我们是以色列士兵!”顷刻间又跳起一个人,佩雷德和葛伦连忙举起AK——突然他们发现那只是一个因为看到以色列军人很兴奋的小女孩,两人连忙收住了枪。枪战到此结束,只过去了45秒钟!
控制航站楼其他地方的战斗还在继续。吉奥拉·祖斯曼和什洛莫·雷斯曼冲进了一间烟雾弥漫的屋子,看到两个人走了出来,看起来像是人质,雷斯曼突然看到其中一人带着手雷,他大喊道:“恐怖分子!快打!”祖斯曼则喊道:“不,那是人质!”雷斯曼于是直接拔枪一顿扫射,两人应声倒地,手雷则爆炸了——幸运的是二人的尸体吸收了冲击力,雷斯曼只是受了轻伤。在电影里完整表现了这一幕,只是省去了大部分对话。最后一位劫机犯在偷袭的时候也被达成了筛子,不过他实际上是和那两人一起完蛋的,至此,七名劫机犯全部被歼灭。
在这之后,在外面指挥的内塔尼亚胡也被击倒了。实际上在小队刚冲入航站楼的时候,内塔尼亚胡就倒地了,大部分资料都认为他被塔楼上的狙击手击中。穆基·贝茨随即成为指挥官,指挥剩下的行动。
此时,其他总参侦察营士兵还在清理旧航站楼里的乌干达士兵,伞兵突击队此时正在进攻新航站楼和燃油设施。电影里没有出现伞兵旅的镜头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没有开火,新航站楼里只有平民和工作人员,但是实际上有一位伞兵旅战士在进入航站楼后被乌干达警察埋伏,一发手枪子弹打进了他的脊髓,他从此落下了终身残疾。
晚上11点8分,第四架C-130降落,卡车随即被释放下来。人质开始有序撤离,戈兰尼旅的突击队员们下来保护飞机。105名人质,包括死伤都被运上了C-130飞机,但是其中一人却不见了,那个人是朵拉·布洛赫,她在之前因为生病被转移到了乌干达的医院。剩下的士兵们开着吉普转移到军用机跑道上,用火箭筒和重机枪炸毁了8架米格-17战斗机,确保不要有飞机能飞起来拦截。
任务到此基本上告一段落,第四架飞机先起飞,飞向内罗毕,2号和3号是最后起飞的,时间:7月4日凌晨0点40分。整个“雷电行动”只持续了100分钟!
内塔尼亚胡,还有迈摩尼最后没能坚持到医院,两人皆在运输机上死亡。科恩在内罗毕进行了急救,最后还是不治而亡,其他轻重伤员最后都活了下来,在内罗毕完成加油后,飞机向东进入印度洋,绕过非洲之角进入红海,飞向特拉维夫。随着飞机们离开东非,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在六个小时的漫长旅途后,运载人质的C-130首先在泰尔诺夫基地短暂停留,军方人员随即告诉众人不可泄露机密,再次起飞后,C-130终于在卢德机场降落了。
人们在兴奋中迎接亲人平安归来,但是对某些人来说,自己已经和亲人天人相隔了。不论是拉米(迈摩尼)的父母还是内塔尼亚胡的两个弟弟(本雅明和伊多),都没能再次见到自己的亲人。为了纪念内塔尼亚胡在行动中的牺牲,雷电行动后来被改名为“约拿坦行动”,他最后被埋葬在赫茨尔山公墓,那里是以色列安葬英雄的地方。
到了这里,电影就结束了。
总体来说《雷电行动》在描绘劫机全过程的方面和真实情况几乎一样,但是在描绘营救行动全过程的方面却又和真实情况有很多冲突之处。至于其中原因,可能是因为剧组获得的资料不够多导致考证不全,也有可能是因为受到军方的保密要求,不可以泄露过多行动细节导致的。但是瑕不掩瑜,电影还是比较精确地刻画了当时以色列士兵的装备,机场的环境和整体作战流程,算是一部写实向的战争片。
银幕之外,后来
银幕之外,后来
朵拉·布洛赫从此人间蒸发了,以色列方面也曾经试图搜寻她的下落,但是从未找到。直到1979年后,她的尸体才在乌干达被发现。阿明为了宣泄愤怒,下令士兵们杀死了还在医院的她,她成为了法航139劫机事件里最后一位遇害者。
阿明阁下的声望从此一落千丈,他的军队直到以色列人离开后才抵达机场,在黑夜里士兵们不分青红皂白到处射击,数十人死于友军枪火。1979年,随着坦桑尼亚军队入侵乌干达,阿明的兵力土崩瓦解,他隐居在沙特阿拉伯度过了自己的晚年,相传他隐居的地方就在四架C-130返航的航线下。在那场战争爆发前,东非共同体就瓦解了。
拉宾的总理生涯也没有因为行动胜利而持续太久,1977年3月,《国土报》发文揭露拉宾夫妻在华盛顿违法开设有银行账户,拉宾在4月引咎辞职。他的老对手梅纳赫姆·贝京担任新总理,当初在行动胜利后,两人还在一起把酒言欢。
法航139号的劫机犯们要求释放的四十多位人员大部分在黎巴嫩战争后释放。然而哈达德没能等到这一天,在“雷电行动”结束后,他被巴解组织永久驱逐,“特别行动组”随之解散。
巴克斯机长因为违抗命令,被法航暂时停职,不过随后他就获得了总统颁发的荣誉军团勋章,其他机组人员也获得了功绩勋章。1982年巴克斯退休,从此住在尼斯,直到他于2019年3月26日去世,享年95岁。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个“不被歌颂的无名英雄”,坚持自己只是在做应该做的。
“雷电行动”结束后,乌干达外长状告联合国安理会称以色列侵犯了这个联合国、不结盟运动和非洲统一组织成员国的主权,以色列驻联大使哈伊姆·赫尔佐格则讲话称“作为一个小国,我们保卫了一百多人的生命、自由和尊严”。安理会最后未能作出决定,不过联合国秘书长对以色列提出了严厉谴责,非洲统一组织和阿拉伯国家也认为此次行动属于战争行为。法国、西德和英国则对拯救人质的行动表示赞赏,虽然很多美国人对以色列抢了独立日200周年的风头感到不满,也对这次“不可能的行动”感到心服口服。
在这之后,美国和西德展开了类似的远程营救训练。1977年10月13日,汉莎航空181号班机被四位巴解组织成员劫持到索马里。西德最后放弃了谈判,派出了由GSG-9特警组成的救援队。在这次行动中,三名劫机犯被歼灭,一人被俘,人质仅三人轻伤,GSG-9仅一人受伤,这是一次完美的跨国反劫机作战,也是一件被全球特种部队所反复研究的跨国救援行动。
银幕外的“雷电行动”并不是完美无缺的,四个平民的家庭和一个军人的家庭从此不再完整。内塔尼亚胡为何会被狙击手击杀,谁应该负责也是很多人都在讨论的问题。同样,这次仓促计划的行动里也有很多“偶然之处”,假如当时跑道灯没有亮,假如所有人质都被秘密转移,假如博斯在听到枪声后就扣下扳机,假如乌干达援军在第一时刻赶到……只需要一个假如就可以宣判行动失败了。
但是对一百多名安全回家的旅客来说,当他们走下运输机,看到挥舞的六芒星旗帜,听到《他要做王》的歌唱声的时候,无疑明白了什么才是自由的力量。要知道,“雷电行动”不仅是针对一架被劫持的飞机的,也是针对一个国防体系完善的国家的。在克服了所有的艰难后,旅客们平安回家比什么都重要。“不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威胁到犹太人的敌人都将面对一个逃不脱的强大对手”,这大概就是银幕内外的“雷电行动”,都在表达的吧。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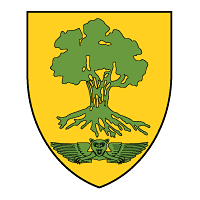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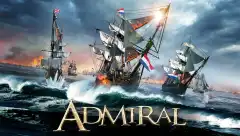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9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