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写在前面的话:这篇文章是我看了十来本日轻之后闲暇时光打出一些没有逻辑的文字的总和,如果想要看到什么干练的文字或是紧凑的剧情那现在建议是直接退出,免得浪费时间。
前后断断续续写了三四个月时间左右,遵循自己喜好来写的小说,叙事在这之中占的比重极低,主要是大量关于高中生活的碎言碎语。不求给读者呈现一个故事,更希望的是能看得轻松开心,从哪里断开都行,从哪里开始也不是问题。
九
这一天我少见地起了个早,但掀开被子的时候面对的困难比我早一点睁开双眼要更为困难,先前说过时间已经步入了秋季,而今早的温度让我怀疑秋季已经被跳过去了。我几乎是怀着必死的决心,直径从床上坐起,被子滑倒了我的腰间。任凭上半身那只有我才能听到的哀嚎声,我向前爬去,将躲在被中窃笑的下半身缓慢抽出,顶着这莫大的痛苦将自己的身体暴露在低温之中。
身体的热量被外界抽离,我的身体在执行冻僵的大脑最后下达的指令,强行从床上下来踩着同样凉得透心的拖鞋站了起来。
待我大脑适应了低温的痛苦之后,重新运转起来后困意已经从我的脑中消失,说到底阻止我们在冷天起床的根本不是所谓的困意,而是我们对于外界严寒的恐惧。一旦将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寒冷之中,恐惧便会伴随着痛苦一起被杀死,从而快速地清醒过来。
虽然起的时间早了一点但依然没有享受到早餐喝粥的权力,因为家里人已经默认我上学日出门的时间之紧迫只配得上吃面包。好在我现在的时间确实也比较急,匆匆换上了衣服便出了家门,但我踏上的并不是上学的方向,现在去学校会整整比早读还要早上十五分钟。
天啊,这十五分钟除了用来抄作业,还有任何可取之处吗?作为绝不把作业压力留到第二天的我来说,这十五分钟就没有任何意义可言。
我按照昨晚在颅内构建附近的街景,规划出了另一条上学路径,当然不是我的,而是属于另一个人的最佳路线。我早起的缘故就是为了能在这条我臆想的路线上堵到她,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想要这么做,很多时候高中生做一些事情仅仅只是因为想做。
很多事情是没有原因与意义的,在事情被完成之后才会被赋予意义,才会出现所谓的起因。
我在一根电线杆子底下打着圈圈,像极了被栓在这里的狗。在寒风中伫立五分钟之后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判断是否出现了差错,但很快现实就打消了我的疑惑,艾怜准时地出现在了路旁。清晨的街坊没有多少人,这里并不是勤劳的商市区,穿着校服裹着一条长长淡棕色围巾的她显得特别显眼。
她无聊地踢着路上的一个易拉罐,哐哐当当的声音像是在向整条街宣誓着她烦闷且无趣的心情,她的脚法娴熟,这可能是她上学路上的固定消遣活动。
“我也喜欢这样干。”在艾怜走过电线杆时,我适时地冲出来表演了一次帅气的劫球,“我的最高纪录是从家门口一直踢到校门口。”
“你怎么在这,你该不会从那时候开始就一刻不停地念我家的地址,牢牢地印在脑袋里就为了这一刻吧?”艾怜头也没有抬,埋在了那卷围巾中间,双手揣在口袋里快步从我身边走过。
“倒也没有那么变态,我在刚听到的时候就记下了。”我将易拉罐传回了艾怜脚下,“我只需要记下最后的几个字,毕竟我们就隔了三条街。”
“三条街的距离,让你一年都没有发现我是和你统一战线的踩线战士。”我看不到艾怜的表情,但从他的口气来看她应该是笑着说的,“顺带一提,我的最高纪录是踢到学校,然后放学后又一路踢回家门口。”
“那个易拉罐呢?你应该将它裱起来,做成永远的奖杯才是。”
“我把它藏在我家楼底下的停车间里,可是那些收瓶子的婆婆可能有瓶子雷达,这些被丢掉的瓶子绝对不可能独自生存超过一天的时间。”艾怜说,“它们会被回收换成钱,而它们自身则会进入回收站,被融掉还是怎么着地重新变为瓶子。”
“那它们不还是瓶子吗?某种意义上的永生。”
“可这个瓶子的构成只有一小部分是它的,其他部分都是其他瓶子来凑的,就像是弗兰肯斯坦,你不能说他就是某只手臂主人的永生形式吧?”
“艾怜女士,你犯了一个错误。那就是用人类的角度去看待瓶子,这可不属于你们外星人的思维。”
“诡辩,难道外星人就没逻辑吗?”艾怜白了我一眼。
她的脑袋本来就不大,这一半躲在围巾下显得更为小巧,声音从围巾里传出来也瓮声瓮气地,像是有点老的录音机。
“你的声音有点怪怪的,感冒了吗?”
艾怜叹了口气,转过头打量了一下我,但她脚上掌控瓶子的脚步没有出一丝差错,或许我应该考虑为她写一封自荐信给学校的女足队伍。她的控球技巧,在水平相对比较低的女子足球中,绝对可以带领学校队伍拿下足以裱与校史的荣誉。
“是的,我感冒了。然后我真羡慕你,因为白痴是不会感冒的。”
“我这可就被冒犯了,先前你对我的评价不都是夸我的吗?”
“我只是说你特别,可没有说过是哪方面的特别,这么冷的天起早来这里等我,我觉得是挺白痴的。”艾怜说,“如果是我的话,我肯定不会干这种事情。”
“可不要看不起心血来潮啊!不过你怎么感冒的,昨晚没盖好被子吗?”
“这可说不准,感冒这件事到底哪里才是起点呢?”艾怜摇着头摆手说,“等我察觉到的时候已经晚了。还有,接球!”
艾怜一脚把易拉罐送到我的脚下,我快速地调整自己的脚步,在保持跟上艾怜的快走同时,将易拉罐稳当当地控在自己脚底下。
“说起来,外星人也会感染感冒吗?”
“你是真的笨蛋,阻止我们入侵地球的一大原因就在这里,某种意义上你们还要感谢感冒这些病毒呢。”艾怜说,“我来给你上一堂历史课,请问美洲大陆上的原住民是哪个种族?”
“印第安人。”
“Binggo,那么下一题,美国的发展史是什么?”
虽然有点跳跃,但我还是做到了即答。
“印第安人的血泪史。”
“前后问题的衔接太过明显,居然又让你答对了一次。那么最后一个问题,殖民者是怎么做到将整个原住民种族屠杀地只剩下百分之十的呢?”
“枪支……呃……”我有点答不上来,“我记得那时候还有悬赏令,如果能拿下一个成年印第安男性的头皮,可以换上十美元,是这些原因吗?”
“错误!这就是答案,大量杀死原住民的武器是病毒……啊啊啊……阿嚏!”艾怜话还没说完就被自己的喷嚏打断了。
“是感冒病毒?”
“答对了,但不全面。”打了喷嚏之后的艾怜声音更加瓮声瓮气,“每个殖民者身上都携带着印第安人这些原住民从未接触过的病毒。与经历过黑死病、安东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这些乱七八糟的外来者相比,印第安人身上的抗体就像是没有穿着盔甲就上战场的士兵,轻而易举地就被击垮了。”
“这样看来,只要一个普通的地球人,就能将你们整艘舰队摧毁了?只需要一个简单的阿嚏。”
“这倒不至于,我们只是比你们更容易生病而已,至少我是这样。”艾怜拿出纸巾擦了擦鼻涕,“但只要经常生病,就能拥有更多的抗体,断掉的骨头才会更坚韧,我们外星人肯定会比你们地球人更强大的。”
“话是这么说,但现在你的对这些似乎还没有多少抵抗力,得多点物理抗性才是。”我说着将她的围巾又往上拉了拉,现在她只有眼睛露在外面了。
“你这样会闷死我的。”艾怜说。
虽然她这样说,但她一直到进入班级前,都保持着这个犹如银行劫匪的围巾造型。
十
一来二去我们彼此之间已经产生了一种熟悉感,有些人即使相互知根知底也视如陌生人提放着;有的人第一次相见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将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分享出来,甚至在可以的情况下想要将内裤的颜色托盘而出。熟悉感并不一定会随着相处的时间而逐渐增长,它并非是简单的正函数,而是更为复杂的某种公式。
我对艾怜的熟悉感属于后者,我想这源自于我对于生活的一种期盼,不只是对于与美少女交往的期待就是了。我希望的是一种反日常,希望着有另一个世界闯入我平凡的世界之中,这个时候艾怜带着她口中外星人的身份闯进了我的世界,而她恰好是一个美少女。
在我蹲守在艾怜上课路上的后一天,艾怜出现在了我的上学路上。虽然说这一天我也想要重复昨天的作为,但没想到的是意志力坚定如我的人,也会在第二天就放弃昨日的决定。这一切都怨与今天早上的天气实在是太冷,比昨天还要冷上一点,打碎了我和昨天一样坚定的信念,早知如此昨晚的我下的决心就应该再大一点了。
决心是一种消耗品,一次用了太多的话,像我们这种慵懒的人类在第二次就会不够用。所以说要慎重使用,下定决心去做的事就要去做完,我今天份的决心就都浪费了。
艾怜出现在我上学路上,不知为何我心中涌起了莫名的喜悦感,难以言喻,难以描述,难以表达。她自然地和我打了招呼,自然地走到我身旁结伴而行,就像是我昨天做的那样。
“你怎么知道我家的住址的?”
“如果你知道我家的住址,我却没有记住你家的,那么我总有点吃亏的感觉。”
我们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搭着话,像是我们平常会做的那样,和她总是有说不完的话能够讲。真是一个巧舌如簧的女孩,我说的每一句话她都能接下去,而她说的话我也能够接下去,要是我们有足够的水与食物,或许能够一直讲到生老病死。而且我们的脚下总是配备着一个易拉罐,我们都是易拉罐界的足球大师,我们的组合就是最强的易拉球组合,总是能够将易拉罐送到学校中不知道那个班级的卫生区中。
我们交流的内容大多数都是关于她的外星人世界,如果这一切都是她的想象,那么她的想象力可真是够丰富的,好在我的想象力也不赖。幻想的世界真是永远不会腻的话题,能够创造出一个属于自己的世界,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而能够在脑中将其完整建设出来的人,就是大梦想家。
至于要想在现实中建立,我认为没有人能做到,除了那些最为无趣的人,因为他们脑中的世界就是这个现实世界。
而现实世界是由每一个人一起铸造的,它如此的无趣和每一个人都逃不开关系,每一个人都是无趣现实的缔造者,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
艾怜除外,她认真地在缔造她的外星世界。
上学路上我们交谈,放学后便会在校舍后头集合,继续交谈,每一次艾怜都会有新的花样为我展示。上一次是纸条触角,下一次是橡皮拼的自走机器人,动力源泉是圆珠笔后边的弹簧,再下一次是铅笔构造的金字塔,这是外星人给地球人的遗产之一……她过于认真的模样,以至于我都要信以为真了。特别是她操作那台最初的联络机的时候,那是我最为相信的时刻。那台简陋的机器似乎真的连接着某一个我们无法观测到的外星舰队,由这个普通的女子高中生向它传递讯息,而这讯息决定着人类的生死存亡。
当然那是不可能的,作为十二年义务教育的产物,我对于这些事情还是保有着一种即使是摆在我面前,也会选择性地失明的态度。我就是会把房间中的大象的皮肤硬说是墙壁,把大象的粪便硬说是厕所水管爆炸的人。
我被无药可救的现实毒害得如此之深,以至于我无法涌起哪怕一丝动摇现实的想法,即使是我希望这个现实崩塌,却无法去相信它会崩塌的事实。真是一个充斥矛盾的人,简直就像是敢做不敢当,敢想不敢做的懦夫,我对此无法原谅,却又无能为力。
我尽力了,我真的办不到啊。
但这个女孩似乎能够轻易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我对此感到敬佩,近乎是仰慕的情感在我心中升起,但我却依然无法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这又是一种矛盾。
谈论起去谁的上学路上一起去上学的问题,我们最后选择了一个折中的决定,出门之后就朝对方家的方向前进,相遇之后就从这折中的路线前往学校。我们都是十分理性的高中生,如果说哪一方吃了亏,至少在我们眼中多花时间就是吃亏,那是十分不好的影响。
一寸光阴一寸金,即使这些时间没有任何意义,对方为你花费时间也是一种最高的敬意,这样的敬意又怎么是我们一届高中生承担得起的。一旦想起来艾怜为了等我多花费了十几分钟,这让我心中惶恐不安,这十几分钟都赖我在床上做懒狗的缘故,实在是罪不可赦。
十一
半个学期的时间过去,时间已经进行到了冬季。
我们对对方的了解更深了一层,但之间的关系却和一开始没有什么差别,正如我一开始所说的一般,两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正函数,至于如何去理解就全靠读者们自己想象了。我们对于对方的情况只是浅谈而止,相反更多的兴趣还是放在那个奇妙的外星人世界之中,那真是令人沉迷的世界,无可自拔。
“哇!幸运!”
有一天艾怜在地上捡到了一百块钱,前面这句话描述出来就像是小学生的造句一般不可信,但事实就是如此。
“你捡到了钱,那就有人丢了钱,这可说不上幸运。”
“那我分你一半,见者有份。”
“哇!幸运!”
我们两人轻松地花掉了这笔不义之财,没有任何的心理负担,我们都为自己的这种心理承受能力而感到自豪。而且我们都喜欢吃作为丑恶舶来品的洋快餐,汉堡包是世界上最为美味的食物之一,我们一直认为这是事实,有着我们两位有着长达十七年进食经验的美食家的担保,铁证如山,不容辩解!
将我们喜欢的食物叠加起来,就像是把所有喜欢的食物用乘号相互连接一般,最后产生的效应是令人无可相信的幸福,这就是汉堡包的魅力所在。认真地品尝一个汉堡,用心去感受与想象,你的牙齿最开始接触到的是烤得松软发酥的面包,上面还撒着像是有魔力一样散发着油香的白芝麻,此时麦香已经抢先占领了鼻腔,宣布着呼吸道已经成为了它的领地。
紧接着上牙会先接触到生菜,生脆的生菜就是能吃的水,这样的形容真是贴切极了。像样的,不对,应该是能被称作汉堡的汉堡都应该夹有西红柿以及洋葱才是。因为生菜之下应该就是西红柿以及洋葱,新鲜的西红柿被牙齿切断时,那些被称作细胞壁的薄膜便被破开,叶泡中的汁液迸射而出,快速地充斥口腔,带来无与伦比的新鲜酸甜味。与之而来的是洋葱那惹人流泪的味道,切洋葱时若是溅到眼中便会流泪,所以说洋葱的味道是让人流泪的味道,独一无二,冲洗干净了先前残留在鼻腔中的麦香味,带来另一种绝妙的体验。
这个时候你的下齿已经抢先到达了汉堡的重头戏,那就是肉。天啊,肉,肉,肉,如此美妙的食物,虽然说这些食物都是美妙的事物,但无论什么事物都能够对比,肉永远都是排在第一位。必须要是新鲜的牛肉,鸡肉和猪肉都无法做到这一点,这是只有牛肉才特有的,那种充满嚼劲的韧道。下齿真是幸运,它能抢先于上齿切断牛肉,新鲜的,被煎烤得恰到火候的牛肉被咬下,灾难般的肉汁涌现,一瞬间那些麦香,那些酸甜,那些流泪的味道都沦为了它的陪衬品。舌头为什么在底下?那是因为吃汉堡的时候,它能够更先品尝到那牛肉饼的汁水啊!
肉香统治了口腔,吸引下一口,下一口,再下一口!舌尖翻卷,由下将面包,牛肉,洋葱,西红柿,生菜统统卷入口中,不知疲倦地向我们的肠胃运输这些美妙事物的混合物。纵使融为一体的它们外观已经不再美观,如果就此吐出来还会显得恶心。但我们的身体从来就没有以貌论物的坏习惯,这是我们那可悲的双目才会去做的事情,我们的身体对这些混合物无一例外地选择接纳,包含着宽容,因为它明白,这些都是无上的美味。
这笔不义之财我们就用来吃了汉堡包。
十二
不知道为什么我脑中浮现起了这个回忆,那是因为正好赶上打折,我们一百块钱满打满算换成了一桌子炸鸡汉堡,虽然说我们都是暴饮暴食的好手,可惜最后也没能将其全部解决。当时只有少许的懊悔,但被更为强烈的满足感轻易淹没,过了十来天后那些懊悔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卷土重来,简直势不可挡。
这时我正在食堂排队打饭,因为冬天的关系,天气变冷之后大家都喜欢往人多的地方挤,使得原本拥挤的食堂变得更加拥挤,使得原本饥饿的学生变得更饥饿。我不禁设想当时剩下的炸鸡与汉堡,若是放在当下该是怎样的一顿佳肴,当时没有把那些玩意吞下去的我简直罪该万死,过去的自己总是被未来的自己痛恨,在各种各样的事情上。
“吃什么?”排在我前面的同桌转头问道。
“我连宇宙的尽头都不知道在哪,怎么知道我今天中午要吃什么?”
“别打岔,快给我点参考意见。继续吃糖醋肉我会死的。”
“是怎么,你糖醋肉上瘾又糖醋肉过敏?”
“是腻死的。”
“那点叉烧吧。”
“菜呢?一荤一素,营养均衡。”
“上海青。”
“我不喜欢吃上海青, 我上海青过敏。”
“花菜。”
“不是叫菜花吗?”
“没差别吧这种。”
“昨天点过了,虽然只吃了一次,但我也腻了。”
“自己想。”
“就是自己想不出来才要问你啊。”
“这就是你提意见的态度?”
我们两人之间的对话每天,对于无聊的高中生来说,在食堂排队等菜的时候用这样没有营养的对话来消磨时间真是再好不过了。如果上了大学,如果是在未来,我肯定不会参与今天吃什么这种营养程度和养生文中的洋垃圾相同的话题了吧?很可惜,写下这篇文章的我来自未来,至少上了大学文中的高中生还在为参与垃圾话题的制造。
“糖醋肉和上海青。”
长队终于走到了尽头,轮到了同桌点菜,一张口就是这两道菜,而我已经丧失了吐槽兴趣了。此刻的我正在享受长队的结束的喜悦,脑中暗念着一会要点的菜品,同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排在我身后的人。
妈呀,比我刚来的时候还要长。想到我身后这条长队的尾巴那个倒霉家伙要排这么长的队,而我马上就要点餐,我的喜悦又高了一分。我就是能将他人的不幸当作自己喜悦佐料,而后配上这股喜悦我今天能吃三饭碗。相反若是身后已经没有人在排队,那我排队之路的终结就会显得苦涩而无趣,因为我知道我就是迟个半小时过来也是在同一个时间打到饭,这显得我浪费时间排队的举动十分愚蠢。
端着饭的我东张西望,每一次我都十分悲观,因为想要在着五六百人的食堂中找到同桌的身影简直是大海捞针,更何况我们并没有实现约好位置。但每一次我都奇迹般地被命运女人牵着鼻子走到同桌的身旁,不得不让人感叹命运之奇妙,生活中无处不在。
提前拿好两份筷子与汤匙的同桌分给了我一份,这让我能直接开始进食。
“好像后天就要开始演讲了啊。”
“啥子演讲?”
“语文的搭档演讲,你该不会全忘了吧?”同桌给我提示到。
“啊!我忘掉那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啊。”我嘴里嚼着饭惊呼道。
但同桌给我提醒的时候,我脑中最先想起来的并不是关于我没有任何准备的事情,也不是同桌这条大腿会带着我飞的事情,而是半个学期前的一段对话。
【如果你没有搭档的话,我倒是可以当你的搭档啦。】
话说回来,艾怜还有邀请过我来着。
“不过如果是我的话,带着你混这种活动没有任何问题就是了。”
“完蛋,我有一个问题不知道能不能问。”
“说。”
“现在让你找其他搭档,你能找到不?”
“你出啥事?”
“我想和艾怜组一队。”
“发展这么快……不对,按照现在的标准来看,发展也太慢了吧?”同桌改口说道,“半学期的时间了,你们怎么连手也没牵上。”
“拜托了,这件事算我的错。”
“别放在心上,像我这样的人,要再找一个搭档很轻松的。”
幸好有他这样的同桌,我想,真正的朋友就是随时放鸽都能被理解原谅的人。
但现在不是感叹这件事的时候,我更为我之前的迟钝而感到不耻,虽然我十分容易忘记些什么,但有些重要的事情是不应该忘记的。有些人的要求你可以选择无视,尤其是你的讨厌的家伙。而后你在意的人的要求需要进行区分对待,如果说对方天天提要求那也可以选择性无视,若是那人从来对你没有任何请求,在某此不经意间透露出请求,那务必要好好记下,应该要像星期一的早晨连续设下五个相同时间的闹钟一样将它记下。
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请求的水平,而应该是求救了。
十三
囫囵吞枣地解决了盘中餐,我先行向同桌告别独自一人赶往教室,但走到一半我稍稍思索一番便调转了方向朝校舍的背面,也就是我们两人的秘密集会所。
虽然当下的室外冷得可怕,我把脑袋裹得严实,又觉得丢人,将上半脑部分的围巾往下拉了几分,同时暗骂自己若是冷就应该全部包起来,何必在意他人的目光,可还是没能做到。在校舍背面我找到了艾怜,她又一次做到了我没做到的事,用围巾把自己头包得像是防毒面具。
她没有注意到我,蹲在地上低头专心摆弄着那台小机器,我双手在口袋中揉了揉走上前去。
“不冷吗?这个时候呆在这里。”我走到她背后说道,“虽然说是大中午,但冬天的中午根本算不上正牌的中午,一点都不暖和才是。”
“啊!”艾怜暗自惊叫一声,像是低头专心啃食蔬菜的兔子被人拧起脊背,下意识地缩成一团,转过头来紧张兮兮地东张西望。
在看到是我之后长舒一口气,拍了拍裤腿站了起来,仰头稍稍皱眉看着我。
“我在这里怎么了嘛?倒是你这样不打一声招呼走得这么近,要不是我反应过来是你,你已经被我用念力击倒了。”
“我可没听说你还有念力这种能力。”
“那是因为没有必要的地方,如果说有可疑男子趁着不注意悄悄地靠近我,那么我会果断使用我的外星念力将其击溃。”艾怜仰着头,像是在吹嘘着什么,“不过你为什么能找到这个地方,平日里中午我可没呆在这里。”
“所以说我问你为什么现在这个时间你还在这,这是我最开始的问题。”我将对话拉到了最开始的地方,“中午不睡,下午崩溃,平日里这个时间你都趴在桌上装尸体才是。”
“那是因为现在正好有要紧的事物……”
“我知道,我知道。”我打断了她的陈述。
我没有继续追问下去艾怜呆在这里的原因,但我心里明白这一点,艾怜会出没在校舍背面的时间我基本上已经摸得一清二楚。平日里放学时间是五点二十分,一般来说她会来校舍背面呆上一个小时,在六点二十左右的时候离开这里直接回家。
但在有些时候她会在这里呆上更长时间,那是一些阴晦的迹象,比如我们的初次相见时她被叮嘱要六点三十前回家,带着绷带来上课的时候,她考试考差的时候……这些我都知道,因为我是除了她之外在这个地方呆最久的人。
那么在后天就要进行在全班面前进行演讲,这样的情况下,她或许不只是会在放学在这里多呆一会,而是会在中午的时间就前来这里消磨时间。正如我所推导的一样,我多希望我的推导过程是错误的,能让我白跑一趟该多好,可惜的是这次的我尤为聪明。
“好好地把人说的话听完啊,你这样打断别人很没礼貌的。”艾怜叉着腰鼓嘴说道,“那你来这里找我有什么事呢?”
虽然我来这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件事,但要我说出来还是需要不少勇气,主动向女孩提出邀请,无论是什么邀请对我来说都是一项艰巨的挑战。能够轻易做到这件事的人,在我眼中是不可思议的存在,虽然说这可不思议遍布在我的周围,可并不妨碍我这样认为。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这个时刻永远都不会到来,但又盼望着我能够尽快做到这一点,最好就在下一刻。我深深地吸了口气,向艾怜伸出了手。
“后天的演讲,你愿意做我的搭档吗?”
“怎么突然……这是什么邀请,这种事情不是半学期前就已经定好的吗?”艾怜挑了挑眉毛。
“我被我同桌鸽了,目前急缺一名搭档。”
“那也不用专门找上我吧?我能给出两点拒绝你的理由,一是我们两个一看就都不是擅长演讲的人,一起上台一定会是两人三足里摔得狗吃屎的搭档;二是我看起来想没有搭档的人吗?”
这两点都让我答不上来,答上来也都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这会与我最初的目标背道而驰。
“那是因为半学期前你邀请过我,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就想到了你。”我的手依然尴尬地伸在空中,“而且我发现我有点喜……”
我说话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卡在喉头,说不出来。
“什么?”
“我觉得你要是演讲的时候能像平常说话一样,那水平就足以应付这种随堂活动了。”
“如果有那么简单,那人人都是大演说家。你这话的意思就像是放屁,每个人都梦想成真那么世界就会太平,事实上没有人能够梦想成真,人们梦想成真世界也不会太平,所有的前提条件都成立最后的结果也不会和预期的相似。”艾怜突然用极快的语速反驳我的夸赞,急迫地想要表达着什么,但最后又沉默了好一会儿。
“但是我答应你,就让我暂时成为你的搭档,一起应付这场演讲吧。”
她伸出了手,我们双手相握,什么感觉我现在已经说不清楚。我想每个人都能明白这个感受,也就不用花费笔墨过多地去描述。总而言之我永远不会忘记当下的感受,如果连这种感受都会忘却的人真是可悲,我打从心底里怜悯他们,他们的生命缺少了一次永恒的回忆,这样的回忆可不多见。
艾怜笑了笑松开了手,我急忙也收回手以免显得我太过留念。
“那也没其他事,要是闲谈下去又要没完没了。”我强行让自己回到了平常的状态,就像是漫画中的忍者一样控制自己的心跳,“我得回教室睡一会儿,下午上课要睡觉也得留到第二节生物课才行,第一节是班主任的课。”
“是呢……”
艾怜绕过我走出这小片空地,背对我时她突然没有预兆地哼起歌来,这种事情可不多见。但她随即注意到自己不自觉的行动被我察觉到,侧过头来不好意思地嘻嘻笑了笑。
“对不起,想到高兴的事情了。”
“有些时候就是没来由地高兴。”
“是啊。”
我们两人结伴离开了这里,往教室地方向走去。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我为这个故事构想了一个Bad end,但又认为这样的故事不应该有所谓的结局,那便让它在这里结束吧。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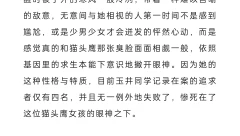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