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赛博朋克,科技与生活的张力
赛博朋克,科技与生活的张力
2020年,波兰工作室CDPR的新游戏《赛博朋克2077》发布,赛博朋克(Cyberpunk)在其宣传期则已作为一种文化模因(meme)在大众视野中病毒式增殖。《银翼杀手》、《攻壳机动队》等赛博朋克作品中西方异想的高密度东方霓虹未来城,在乏味的矢量平滑美学中脱颖而出,成为怀旧千禧年的视觉秀场。而作为文本的赛博朋克在过程中逐渐抽象为所见即所得的符号。
但这并不是另一个“精英文化”在流行化中逐渐空壳化的标本。
那些符号是赛博朋克文本在我们真实生活的投射。赛博朋克的文本意涵逐渐模糊的过程,即是我们的日常向其无限趋近的过程。没错,我们已经身处赛博朋克之中,其表现不仅在于无限逼近科学幻想的技术水平,更在于高技术背景下呈现出“High tech,Low life”的趋向。
“High tech,Low life”可以说是赛博朋克作品最核心的特征,即“高科技、低生活”。一高一低的反差精准的概括出赛博朋克世界中最主要的矛盾和故事动机——高度成熟的人工智能和生化技术让权贵掌控一切甚至永生,底层个体(人类、机器人,人造人)却被彻底异化剥削,甚至朝生暮死如蝼蚁。
如今,人类已经可以像《神经漫游者》一样在网络中神游世界,也可以像《攻壳机动队》一般接驳义体,然而个体在系统前渺小和无助的状态却依然如旧。技术引发的关于伦理与阶级的反省探讨不再是艺术家和哲学家的高谈阔论,而越来越成为迫在眉睫的现实问题。
从这一层面看来,Cyberpunk这个组合词几乎与“High tech,low life”同构同义,即“High tech=cyber,low life=punk”,因为在20世纪60-70年代,将两个词语并置本身就体现出科技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其中Cyber代表的控制论连等一众尖端科学描绘出一个高效高质的未来乌托邦,而工人和底层阶级——Punk文化生发之处则处在战后的贫困和失语之中,这种状态无疑是对科技乌托邦的讽刺。
两者间的张力成为10多年后赛博朋克文学的现实源泉。赛博朋克作品中的主角大多是像Punk乐队性手枪一样对女王竖起中指的角色。但是在现实世界中弥合科技与生活间裂缝的人,当不会是《赛博朋克2077》中强尼·银手一样的混小子。
而在20世纪60年代与Punk文化最近的伦敦,恰有一群兼具行动力与理想力的实践者,他们用带着些许天马行空的方案试图去解决——或至少曾经指出了可能的方向。
一个关于社会、戏剧和建筑的激进想法
一个关于社会、戏剧和建筑的激进想法
一切的开始是一名戏剧导演和建筑师的合作。
60年代,塑造了当今大多数城市面貌的现代主义建筑正处于全盛时期,其中功能和空间的严格对应对与其说是技术限制,不若说更近乎于一种对建筑师的道德约束。
而当时伦敦街道上充斥着无处发泄的叛逆荷尔蒙,无所事事的小青年们蔑视陈规,目空一切。日后成为英国著名的戏剧家,社会活动家的琼·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也位列其中。她与红喇叭剧团经常在街道上随时演起左派即兴戏剧,激进内容和形式让她的每次演出都是一次和警察的斗智斗勇。不过这位“老朋克”显然不仅仅满足于挑衅和发泄,她决定采取更为彻底的“反叛”:探索一种崭新的公共教育形式,让劳工阶级从根本上脱离“low life”的状态。
林特伍德从早年的街道表演和布莱希特的理论中得到启发,认为戏剧或广义的娱乐拥有启发心智、介入社会议题的能力。因此她的方式是建造一座开放式的情境剧院:人们在这里不再是被动接受的观众,而是在情境中主动探索的参与者。这种体验近似于角色扮演游戏,而游戏的主题通常有关于合作、知识或者纯粹的身心放松。
林特伍德希望这种迥异于日常的体验能激发人们心中的自主意识,充实他们的业余时间。更确切的说,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街道大学。她最初称其为“欢乐拱廊”(Fun Arcade),这个项目在随后有一个更为响亮名字“欢乐宫”(Fun Palace)。
林特伍德对剧院空间的设想非常激进:
这里没有什么是强制性的,万事皆可。这里没有永久的结构。没有什么会持续十年,有些甚至不会超过十天:视线里没有混凝土、污点或裂缝,没有那些高贵的当代建筑的后遗症……
简言之,她希望建造的是一个可以经常变动,没有功能同时也意味有无数功能的建筑。以当时的技术水平来看,林特伍德对于建筑的设想几近天方夜谭,幸运的是,她找到一位同样大胆与反叛的建筑师——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
当时的塞德里克·普莱斯正在拥抱新兴的控制论(Cybernetic)、博弈论和电子计算机技术,探索着一条和现代主义建筑截然不同的道路。普莱斯并不将建筑看做结构搭建供人容身的空间,他认为建筑存在的目的是为了人的持续性对话(continuous dialogue),即,建筑作为一种人造环境,应该对人类行为及心理的促进和塑造承担应有责任。
因此普莱斯不仅仅满足于硬件设计(通常意义上的建筑物),更在软件设计(辅助建筑环境与使用者发生互动的控制系统)上投入了大量精力,而处理复杂系统中动态互动的控制论无疑成为了一种合适的方法。
普莱斯这一想法的实践起点,便是与琼·林特伍德的合作的欢乐宫。
赛博建筑会架上钢筋混凝土梁吗?
赛博建筑会架上钢筋混凝土梁吗?
如果要说控制论和电子计算机给了普莱斯什么启发,其中一定包括人类可以通过控制信息参数系统化的输入输出实现无机系统的自动化。这给了普莱斯打造一座互动式动态建筑的信心,他将“欢乐宫”视作因使用者参与而不断变化的事件,建筑物的各部分可以随着使用者的行为即时变动。普莱斯将其设想为:
一个包含了剧院、电影院、餐馆、工作坊、集会区域的大型船坞,能够不断组装、移动、重新安排和销毁。
因此,欢乐宫的设计逻辑和运作逻辑都更接近电子计算机:通过算法和逻辑让建筑具有可由使用者定义的自组织性。
在“硬件”方面,普莱斯找到了曾经在伦敦鸟舍合作过的结构工程师弗兰克·纽比(Frank Newby)。后者提出了一个具有足够灵活性的结构方案:主体结构是由14排间隔18米(60英尺)的“服务塔(service tower)”组成的巨型结构矩阵,238米(780英尺)长110米(360英尺)宽。建筑顶部装有两台起重机,沿长边移动组装预制模块——包含空气、温度和光线调节设施的空间单元。
在“软件”方面,英国控制论基金会首席科学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给予了无私的帮助。当他1963年第一次从林德伍德的信中得知欢乐宫项目后,便被其超前的想法深深吸引。他非常赞同普莱斯对于建筑本质的看法,并认为控制论设计能赋予建筑师社会工程师(social engineer)的角色。
欢乐宫项目的基调与帕斯克对技术和社会控制的浪漫主义态度不谋而合,随即他便成立了欢乐宫控制论附属委员会(the Fun Palace Cybernetics Subcommittee),负责欢乐宫的控制论设计工作。工作组通过社会调研列举了多种使用者可能发生的活动。
随后欢乐宫的设计工作完全脱离既有的建筑设计流程,转入统计学、心理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数学模型编译,进而通过使用者的行为习惯和活动种类编写控制建筑的算法程序。帕斯克和他的委员会为建筑赋予了大脑,而他也因此成为了团队中除林特伍德和普莱斯之外最重要的成员。
最终,欢乐宫为使用者提供了这样一种使用体验:当你进入建筑后,会领到一张用于电子打卡的卡片。电子打卡系统和其他传感器搜集记录你对空间尺度、电子设备、声环境、光环境的需求。之后这些数据被汇集到当时最新的IBM360-30型号电脑中进行编译,设置调整空间的参数。随后建筑中会重新放置可移动墙体和走廊,设置环境调节标准。形成符合使用者要求的空间。此外,欢乐宫是最富预见之处是引入了“机器学习”的概念,以上全过程将会根据使用者使用参数的累积,不断自我改善,通过先前的使用痕迹描绘出之后的使用模式。
建筑未竟,赛博已来
建筑未竟,赛博已来
1965年,欢乐宫的设计工作接近尾声,林特伍德与普莱斯在伦敦的里河(Lea river)附近找到了实际建造的地址。项目却最终由于伦敦规划区域变动在各级管理机构的相互拉扯中被无限期的推延。
随后的几年里,欢乐宫的参与人员都在与官僚机构抗争。但最后,欢乐宫项目被普莱斯亲自叫停。虽然欢乐宫在结构方案和美学上对后世的建筑影响巨大——法国蓬皮杜中心的建筑师伦佐·皮亚诺直言该建筑曾受欢乐宫的影响,但普莱斯依然认为随着技术和社会的发展,欢乐宫已经错过了属于它的时代,已经没有再被建造的必要。于是他在1975年公开宣布终止该项目。
没错,欢乐宫确实只能属于60-70年代。那是一个充满无尽乐观和希望的时代,一个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时代。控制论学家戈登·帕斯克在欢乐宫时曾提出过一个设想:通过算法规则“诱发快乐”,以行为矫正的方式刺激多巴胺,这是一个类似美丽新世界中“唆麻”的危险设定。而当时林特伍德和普莱斯却对即将成为“社会控制装置”的欢乐宫持有天真而乐观的态度,因为他们认为整个系统可以足够自动且透明,允许使用者自行控制。
但现如今的我们,对信息技术在社会控制领域的应用,很难再怀有欢乐宫时的乐观态度。因为欢乐宫的运行逻辑对我们来说已是熟悉的日常,手机上的每一个app都在方寸之间做着和它一样的事情——学习、预测并影响使用者的行为,攫取你的时间,改造你的思维方式。而这一切背后的算法是一个巨大的黑箱,没有人可以完全掌控整个系统。
如今,控制论和算法让现代生活产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却也塑造了更多束缚住人的系统——监督送餐员效率的外卖计时系统、掌握工作时间甚至如厕时间的公司监控、中小学课堂上的表情监控系统……“high tech, low life”就在我们身边,一张赛博之网将我们紧紧罩住,赛博朋克作品中描绘的情境并不遥远。
尼尔·波兹曼认为一切媒介自其诞生起就附带有预料之外的意识形态倾向,控制论和信息技术诞生之初,这个预料之外的倾向还并未被察觉。普莱斯兴奋地拥抱它,将其作为一种社会改良的工具,并在随后的诸多项目中应用,试图用技术完成个体的解放与赋权。例如在他另一个项目,陶器思考带项目(Potteries Thinkbelt,1963-67 )中,他将废旧的陶土矿区铁路运输网改造成一所移动的大学,用教育产业振兴废弃工业区并希望改变传统英国大学的贵族意味。甚至在为J.Lyons & Co食品公司设计的旗舰店中(The Information Hive,1965-66),他也不忘将店铺和图书馆、广播电视系统远程连接,打造一个“信息蜂巢”,让前来体验的人不仅获得食物上的满足,而且能充实头脑与精神。
知识赋权的信念,对信息技术和控制论的兴趣贯穿着普莱斯的职业生涯,虽然他的建筑鲜有建成,但这个无限拥抱技术的建筑家始终明确,技术及其造就的系统不是目的,在设计和工作中远有比这更重要的需要关注。
2004年,普莱斯在他去世前不久回望这个项目时,说道:“欢乐宫不是关于技术,是关于人。”
后记
后记
欢乐宫作为一个建筑项目,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夭折了。但其最初的构想,却被林特伍德的后辈们以另一种方式延续下来。
2014年,在林特伍德百年诞辰之际,以Stella Duffy,Sarah-Jane Rawlings为首的一群戏剧人决定重启欢乐宫项目,他们以分散式社区活动的形式,鼓励人们利用自己社区的公共场地,自发举办各种与科学和艺术有关的活动,希望人们在此分享、交流和学习,激发自我探索,团结协作的能力。如今的欢乐宫虽然“科技”渐远,但它却在这个被算法和系统紧箍的时代,连续举办5年。回归人与生活,可谓是返璞归真,或许这就是“欢乐宫”应有的样子也未可知。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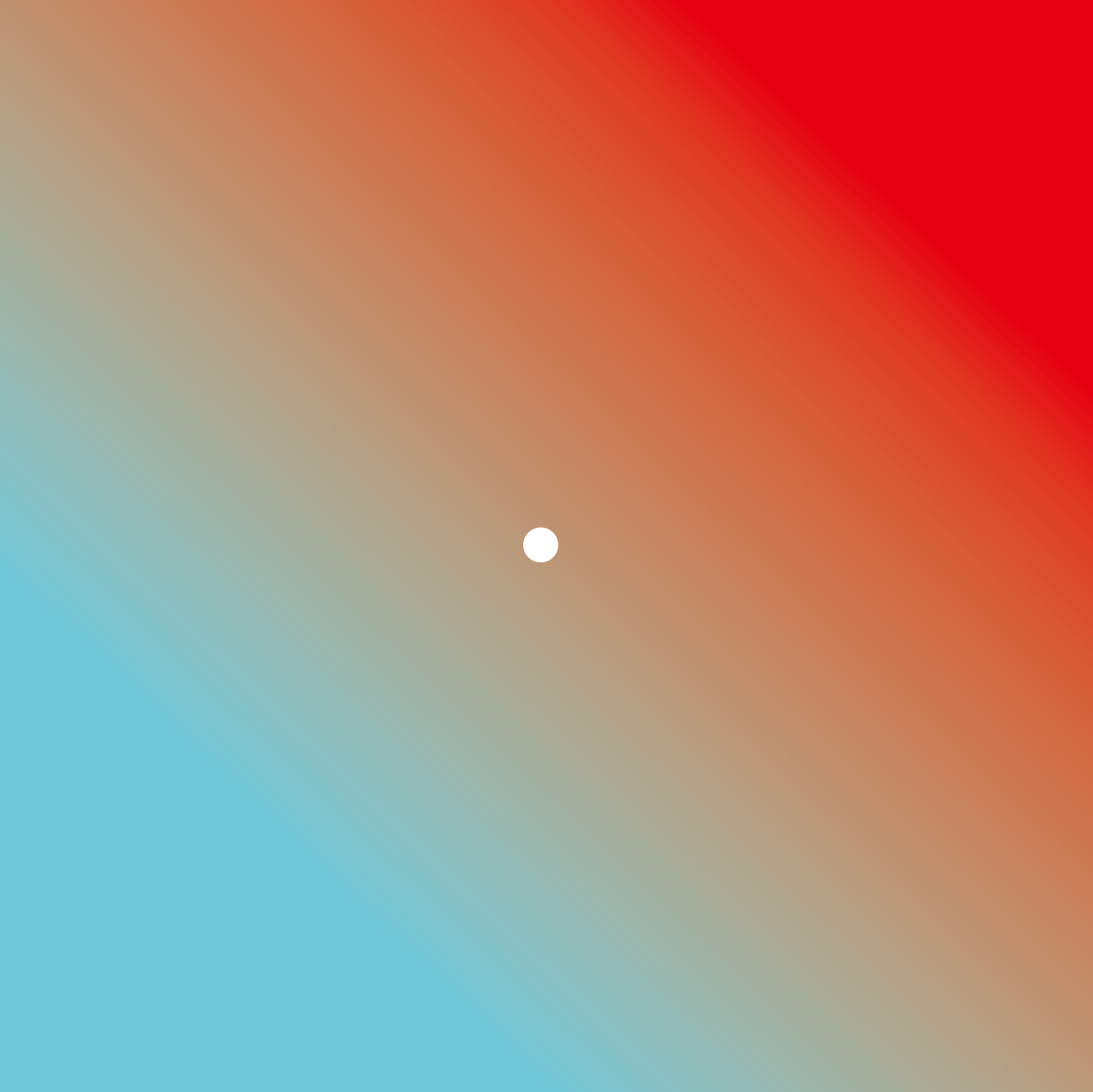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