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首先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幅1968年的拼贴,当修女听到“Yes, my child.”时,她会知道告解室中不是神父而是一个头顶光环的笨重机器吗?如果知道的话,她会觉得这是对上帝的亵渎吗?她会想到人造机器和上帝造人之间的联系吗?这么想下去的话,拼贴多少带着些讽刺宗教的意味。
又或许图中的挑衅意味并没有那么浓厚,相反作者可能更多在畅想机器可能具有的智能。尤其考虑到拼贴展出的情景:一场1968年8月2日在伦敦开幕的展览Cybernetic Serendipity——the computer and the art。
一、意外发现的控制论珍奇
一、意外发现的控制论珍奇
在那个计算机屏幕和绘图机还只能输出黑白图像的年代,英国当代艺术协会的策展人贾西亚·赖卡特(Jasia Reichardt)敏锐的察觉到计算机对艺术产生的影响。于是她筹备策划了展览Cybernetic Serendipity,中文译作“控制论的意外发现”。其中Serendipity意为“意外发现珍奇的才能”,由十八世纪英国作家Horace Walpole 创造,源于他读过的寓言《Serendipi的三个王子》。
这是一个关于三个锡兰国王子的探险故事,他们在路上并未刻意寻找却意外获得了极其珍贵的宝物。贾西亚选择该词语作为展览名称,连同其背后的寓言恰好是控制论产生及发展过程的隐喻。
控制论学科由诺伯特·维纳创立于1948年,脱胎于他在二战期间为美国军方开发的对空火炮自动控制系统,与同年发表的信息论共同奠定了信息技术的理论基础。两年后,第一台商用电子计算机投入市场。直至1964年,市面上最先进的电脑是IBM研发的System/360系列,每台售价在250~300万美元之间。虽然System/360系列的内存只有8MB,却在美国的阿波罗登月计划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控制论与早期计算机发展关系密切,然而这门学科却不止于此:控制论学家们发现了动物神经信号和电子电路在信息传递层面的共性,并以此消融两者的界限,英国的控制论学家更是着力研究机器智能和人类大脑之间的关系。控制论表面上看是关于自动化、机器智能的技术科学,但本质是一种关于生活在人机共存世界的认识论与方法论。那么,在这样的世界中,最能体现人类直觉与想象力的艺术创作将会怎样?
正像展览的副标题the computer and the art所示,展览内容包括当时计算机与艺术所有可能的交叉领域,并将其划分为三大类:
- 以计算机为创作工具的艺术
- 控制论机器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装置
- 对计算机历史和其技术环境有参照意义的发明
可以看出,展览展出的并非传统的观赏性艺术,而最令当时的观众迷惑的是,他们无法分辨这些艺术品是来自艺术家、工程师,还是控制论学家。
二、计算机,艺术创作的新工具
二、计算机,艺术创作的新工具
第一个类别可能是展览中最容易理解的部分:将计算机作为一种新工具,创作已知的艺术形式。新的媒介改变了创作方法,以绘画为例,相比于动动手指就能在电容屏上画出灵动线条的当代人来说,当年的艺术创作方式可谓相当硬核——日本团体Computer Technique Group描述了使用计算机创作图像的方法:
1.编写一个计算机程序;
2.安装并确保计算机自动运行程序;
3.用穿孔带给计算机输入的信息;
4.经过程序控制的绘图机器转变成图形。
那么这样复杂的过程产出了什么样的作品呢?一个地狱笑话级别的简单图像:《射击肯尼迪》(Shot Kennedy),由耳部(中弹部位?)发出的射线组成的肯尼迪总统肖像。
展览中利用各种不同方式自动生成图像的作品还有很多,例如利用简单的钟摆机械原理绘制复杂重复图形的《双摆谐振绘图器》(The pendulum-harmonograpgh:a drawing machine),Ivan Moscovich。以及D.P.Henry的《绘画计算机》(The Henry drawing computer)等等。这些“简单”的图形不过是今天Photoshop中点几下鼠标就能完成的水平。但在20世纪60年代,交互界面是什么?用户友好是什么?不存在的。
当时计算机图像最主要的使用领域是工业和科学研究,computer graphic这个术语便是由波音航空公司创造。1960年代波音公司为了改进飞机着陆的精确性,使用计算机图形生成一系列飞行员与座舱环境互动的图形,用来研究飞行员反应。
以上的所有“作品”似乎与传统印象中的“艺术”相去甚远。策展人贾西亚也这样认为:“此时此刻,计算机仍然只是一种工具,离那些关于艺术的议题还尚远。”但她也相信计算机会提升艺术创作的视野和维度。
使用电视和显像管创作的韩国艺术家白南准曾声称电子显像技术取代了颜料和画布。信息技术不仅改变了作品的呈现方式,而且改变了作品的创作方式。展览该部分的其他作品也是如此:自动生成俳句的机器、电子音乐合成器等等。我们可将它们看做如今批量生产视觉内容的Adobe套件的雏形,社会分工的细化,让创作者们离文艺复兴时代的大艺术家渐远。那些大艺术家们往往身兼数职,例如为大教堂绘制天顶画时,他们不仅绘画,而且包揽了从透视法、颜料、绘画工具甚至工程器械等一系列创作工具的发明。如今的大部分创作者甚至不再深入探究创作工具的运作原理,而是使用科技公司开发的打包封装的创意软件。创作者和创作工具的渐离让艺术品缺少了某种与事物规则相关的深刻性,联合大众媒体成为无尽拟像的一部分。但这却界定出一种新的社会身份——数字创意者,他们从传统艺术家的群体中划分出来,与商业联系更为紧密。
那么除了计件收费的创意工作者们之外,那些占据更高生态位的数字创意者如何跻身艺术家行列?或者更直白点,具有无限复制属性的数字内容凭什么进入作品价值与独一性绑定的艺术品资本市场?或许在很多人看来答案就是NFT(非同质化代币)——2021年Beeple的数字绘画作品《每一天:最初的5000天》(Everydays: The First 5000 Days)买出了6934万美元的价格。同年12月,Pak的作品《融合》(Merge)以9180万美元刷新Beeple的记录。但就在不久前的2022年1月12日,维基百科刚刚通过投票将Beeple和Pak的NFT艺术从“最贵艺术品清单”里删除,维基的大部分编辑似乎不认为NFT艺术能被称为一种艺术形式。
让我们比较一下两名艺术家的作品:Beeple的作品是几千张数字绘画的打包,NFT在这里更多等同于作品价值的锚定物。他本人认为NFT艺术虚高的价格是一场泡沫,并在之后很快套现离场;而Pak的作品《融合》的拍卖本身就是作品的重要组成——《融合》是一次无限量发售,藏家买到的每个虚拟小球都代表一个NFT,单个藏家购买的越多,他拥有的球就会吸收更多的小球变得越大,反之亦然。拍卖结束后,藏家手中球的大小还会随着二级市场中的交易不停变化。理论上讲,只要二级市场的交易仍在进行,《融合》的形态就不会固定,它是一个永远处于动态过程中的“未完成”的作品。
如此看来,前者被踢出名单尚情有可原,但后者也遭受同等待遇,只能说维基百科格局小了。仅从创作角度来看,NFT在《融合》中不是创作或锚定某种已知艺术形式价值的工具,去中心化的数字账本实时变动的特性就是作品自身,能用更合理的价格买到更多小球的人就可以得到比其他人更大的球,而这种实时性和互动性恰恰是计算机(或者说控制论)为艺术引入的全新维度。
三、控制论机器,一种艺术装置
三、控制论机器,一种艺术装置
说到这里,让我们先回到展览中的第二类展品:控制论机器本身作为一种艺术装置。需要注意的是,展览的技术顾问马克·道森(Mark Dawson)是英国控制论学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的合作者。展出的“控制论装置”不是一个作为审美客体的静态机器雕塑,而是一种能和环境动态交互的反馈装置。
例如Wen Ying-Tsai的《控制论雕塑》(Cybernetic Sculpture)是一组顶端带有金属板的不锈钢条阵列,能够根据观众的靠近和环境声音,发出频闪光或摆动。如今这种简单的电子互动装置已经是当代艺术和景观装置中屡见不鲜的小把戏了。但在电子计算机尚未家用的60年代这绝对是个令观众无法理解的魔法物件。
同时代的欧美主流艺术界,盛行波普艺术、抽象表现主义、观念艺术等流派,不论这些艺术家们在观念上以何种程度挑战以往的艺术形式,他们创作的艺术品仍是一个静止的客体,观众“欣赏”的方式仍是观看。它们创造的体验很难超越文艺复兴时期的教堂天顶画基于解剖学和透视法打造的艺术和技术的双重奇观。
在这次展览上,法国艺术家Nicolas Schöffer就展出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城市奇观:《控制论光塔》(Cybernetic light tower)——一个位于巴黎拉德芳斯区的巨型户外互动装置:高307米,平均跨度59米,采用方钢管内灌钢筋混凝土的框架结构,外覆抛光不锈钢板和铝板。180个安装平面镜的悬臂从主体结构的不同方向伸出,由计算机控制的电机驱动以不同速率旋转,在周围形成反光和弥漫的光线。
我将其称之为“控制论的第三国际纪念塔”,因为两者都是一座巨构纪念碑、一段宣言以及一个运动的装置。但不同的是,控制论光塔的运动不是预设和象征式的,而是即时和行为的。光塔的传感器识别环境中的声音、温度、交通状况甚至空气湿度,数据传到计算机实时控制改变塔的运动方式和亮度。Nicolas还设想通过运动和光电表示天气甚至股市涨跌情况。从根本上,“控制论光塔”是一个能对环境作出即时反馈的自动机器,当它扩大到城市尺度时,对于观众们来说就是奇观无疑了。哦,对了,它和第三国际塔还有一点相似之处——都没建成。
另一个展品《运动的对话》(The Colloquy of Mobiles)是最符合展览主题的作品,它的创作者是英国控制论学家戈登·帕斯克。这是五个分成两组悬挂在天花板上的可旋转装置,其中一组是两个安装了发光器和感光元件的悬挂物,被称为“雄性(male)”;另一组是三个被曲线形态的反光玻璃纤维包裹的物体,被称为“雌性(female)”。“雄性”旋转并发出光线寻找“雌性”,当后者接收到光线后会反射给前者,并用一种同步的识别声音回应前者,随后两者完成配对。但是两个“雄性”会彼此竞争,打断对方和“雌性”的配对。观众也可以通过阻挡或反射光线加入这场配对游戏。
《运动的对话》中单个装置的运动和配对过程会被各种无法预料的随机情况打乱,它们会改变自己的行为并寻找新的目标。人类也可以以它们的交流方式加入这场“对话”。这个作品是戈登·帕斯克探索人类适应性行为的试验成果,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审美有效环境(aesthetically potent environment)的概念:“审美有效环境是一种能调用各种媒介(声音、画面甚至触觉)使人乐在其中并参与改变周遭的环境“
“一个审美有效环境应该具备以下属性:
- 必须提供充分的多样性,为人所需的潜在的、可控制的多样性做充分的准备(但是不能让多样性淹没人本身,如此将只会令人费解)
- 必须包括人可以学习理解的各种抽象的不同层次。
- 必须有提示和说明来引导人的参与过程。
- 最好能回应人,引发人适应它特有的交流模式并与其对话。”
帕斯克认为人在观看绘画或雕塑时,静止的作品不会回应人,人只能作为观看者通过视觉和想象力引发思维内部的对话,并未真正的参与到艺术品之中。而具备“审美有效环境”特征的艺术品,可以通过自身具有的实时反馈特征激发人的适应性,将这种脑内的对话“外部化”。在控制论的语境中,变化是艺术品的天然属性,人可以在画家和观众的角色间随意转换,甚至能以某种方式和艺术品的生产与演化同步。
控制论装置的审美维度不仅仅停留在视觉或智识的愉悦,而是一种参与到即时反馈过程中的体验感。“反馈(feedback)”是控制论中非常重要的概念,维纳在1948年的《控制论》一书中赋予了反馈现代意义:“反馈即一种能用过去的演绩(performance)来调节未来行为的性能。”控制论以信息交换的视角看待世界上所有的行为,“审美有效环境”带来的体验感的就是建立在人和机器之间的信息反馈循环之上,只不过我们如今有一个更熟悉的词语——人机交互。
四、那么电子游戏呢?
四、那么电子游戏呢?
这次展览呈现了控制论和计算机对艺术创作的诸多影响,但最重要的是它将“人机交互”的概念引入艺术领域——人和带有输入输出设备的系统进行互动。让我们再回过头看看Pak的作品《融合》,藏家通过NFT和艺术品以及其他藏家实时互动,这难道不就是一款利用区块链原理开发的、玩法简单刺激、真金白银的网络电子游戏吗?
倘若将艺术品看做是现实世界的局部副本或变形切片,其中的优秀作品能充分调动体验者想象力和情绪。那么,近20年来的电子游戏在电子图形和叙事层面的进步无疑使其具备这种能力。玩家与游戏程序两个系统,通过摇杆、键鼠、手柄、体感、屏幕、扬声器……各种输入输出信息的方式激活无数次的信息反馈循环。电子游戏就是信息时代人与世界关系的反复演练,是真实的极限映射。
那么,为什么电子游戏不能被称为新的艺术形式呢?难道只是因为没有艺术品市场的资本投机者入场吗?当艺术品变成投资对象,那些使其保值的也必是使其钝化的。朋克如班克西(Banksy)对资本市场的嘲弄也被这个体系迅速吸收,碎掉一半的《气球与女孩》反而拍出了更高的价格。“体验”和“沉浸”的互动欣赏方式会不会反而是传递价值的更优方式?
这些问题我也没有答案,关于电子游戏是否能被称为艺术的争论很多,在此我不做展开。但可以肯定的是,定义一种艺术形式的一定是那些凝结了劳动力与智慧的精品。我们难道要用街边书摊的粗劣故事来否定文学作为一种艺术形式吗?显然不能。艺术的边界在不断拓宽,定义也在变化。或许期待技术的下一次飞跃能给我们带来更确定的答案。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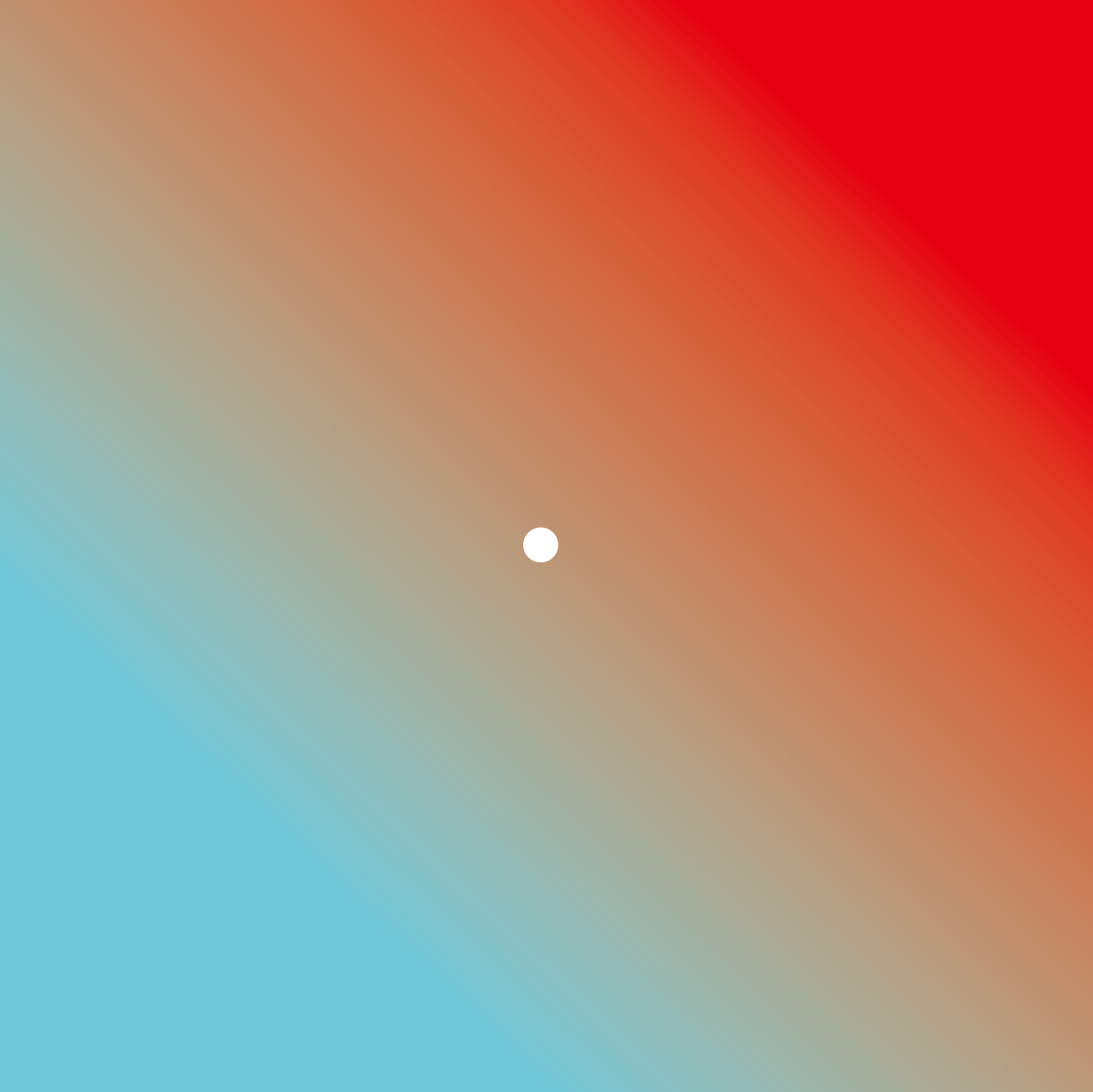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6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