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前段时间我有幸观赏了《尚气》这部电影,在感到好笑的同时又有些头疼,想要在这篇文章里稍微论述一下我对这部电影的看法。
首先,《尚气》的争议相信中国的网民不会陌生。所谓“傅满洲”作为漫威漫画角色“尚气”所面对的反派的形象所含有的屈辱历史刻板印象,以及该形象在这部《尚气与十环传奇》里的“去刻板印象”化(根据维基百科,导演自称“改变了漫画中的不当元素”)。作为一块亚洲电影市场的敲门砖,却尴尬地在亚洲最大的市场门前碰壁的争议性电影,《尚气》究竟为我们带来了什么?
我想说的是,它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对中国——乃至东亚——文化的穷凶极恶的拆解与重塑,以符合看似属于亚裔实则属于传统欧美的价值观。说的更直白一点,一次文化软殖民。
为何我会抛出这么夸张而吓人的论调?《尚气与十环传奇》(以下简称《尚气》)不就是一部爆米花电影吗?它拍出来的本意不就是想赚钱吗?它凸显的不就是白左(或者说美国自由主义左派)虚荣而伪善的文化同情吗?不是。这部电影在市场反馈的结果上也许呈现了类似的样态,但这仅仅符合一种不属于文化阵营的宣传,《尚气》在内容上的别有用心惹人发笑。
首先,我们来看看这部电影的女主。女主角在这部电影中的表现非常关键,女性在影视作品中地位的改变本来就值得被文化研究所重视,更何况《尚气》的女主直接被赋予了一部分亚裔“新女性”(不确定该角色——名为瑞文——在人设上属于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移民)的特质,比如富有主见和开放性的生活方式,向往自由,抵触家庭中老一辈的传统说教,等等。可问题是,瑞文的这种“独立自主”的生活态度没有在整部电影中存在过哪怕一丝一毫的展现。
她和男主尚气被卷入一系列由尚气的父亲徐文武造成的事件当中,随后完全被牵着鼻子走。不论身处任何险境,我们足智多谋的瑞文永远选择“随大溜”心态——反正她也是被迫卷入一系列让她不知所措的情况。她的历险不具备任何主动性,完完全全成了一个没必要存在的角色。这使得她主动提出同男主冒险的动机很成问题——她基本就像个参加了一场夏令营的孩子,而其表现一言以蔽之就是听话顺从。
瑞文在整部戏一以贯之的顺从同她登场时所表现的“独立自主”的信念产生了无法调解的矛盾。
通过电影开头对瑞文家庭的展示,我们可以确知瑞文想要从她母亲的说教中解放出来。她希望维持一种年轻的,享乐的,做着自己热爱的工作(也就是在旧金山的酒店帮客人泊车)的生活方式,于是电影团队大发慈悲给了她冒险的机会,让她成为陪伴尚气的背景板,我们看不到这个角色究竟从冒险中获得了什么,而这种“收获”又能在她回归她那“中式传统家庭”后为自己的生活带来什么改变。
那么,这段最开头对瑞文家庭的展示又有什么意义呢?它当然承载着非常重要的宣传刻板印象的功能。一个移民美国的中式家庭,男人外出经商,因此完全隐去了“父亲”的形象,而老一辈的外婆念叨着迷信,以一种被驯服的文化姿态被电影的价值观所接受(迷信当然比不过“科学”,老奶奶的价值观已经无法再影响追求“自由”的年轻人了hh),至于瑞文的母亲,则是年轻人的最大宿敌——她既是美国人,又排斥美国的理念(食古不化hh),瞧不起瑞文的工作,认为瑞文理应获得更“高端大气上档次”的工作来报答家里对她的培养(电影中瑞文母亲有提到“Waigong didn’t move here (San Francisco) from Hunan so you can park cars for living”,即“外公从湖南搬到旧金山不是为了让你泊车度日的。”)。啊,多么让人透不过气的“中式传统文化枷锁”!
如果现场的演员换成白人,以意义相同的台词,完全可以呈现出一幅平淡如水的家庭情景剧。长辈对晚辈生活方式的问询和关切,以及晚辈对长辈这种关切的不耐与反抗,不正是美国主流家庭最常见的情况吗?母亲不满女儿天天帮别人停车,拿着微薄的薪水以“享受生活”的名义当朝四暮三的月光族,这很不正常吗?合着非要拿对“中式家庭”的刻板印象来硬套这个场景?理念冲突?还是撕了那无聊的面具吧!
其次,我们来看看一场尚气和瑞文在公交车上对一个赶论文的亚裔女性的探讨。这场戏大概在电影开场16分钟左右。
开题是瑞文借机提出对自己母亲的不满:“That is exactly the daughter my mom wish to came out from her vagina”。
尚气则表示:“I’m sorry about her”。
这个“her”很有意思,因为它似乎指代了三个意向——这个“her”可能是指赶论文的女性,指瑞文比喻中的那个她母亲理想中的女儿,或者是瑞文母亲。尽管尚气的台词在文本的意义上很模糊,但从演员当时正盯着赶论文的女性,且露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表情来看,我的第一反应是他在替那位赶论文的女性感到“sorry”。我真觉得大可不必。这是什么意思呢?美国大学很容易上?研究生、博士生很容易读?还是说公交车上不允许赶论文?或者“年轻人要潇洒一点”?这戏拍的就莫名其妙,完全抓不住意味。追根究底,我对这位赶论文的女性的登场,以及她所代表的关于所谓“亚洲学生”的社会形象是摸不着头脑的。我身边的很多美国本地大学生也经常赶论文,室内写,室外写,站着写,坐着写,在草地上躺着写,在砖墙上靠着写,听着音乐写,晒着太阳写……为何不对他们的生活严加批判一番呢?
然后,有意思的地方来了,尚气遭遇了一群打手,其中一个安了一副很酷的义肢,可以从中弹出热能刀片。尚气在同此人的搏斗中抢过那位女性的电脑(大概在电影18分钟左右)挡刀,然后电脑被劈成两半,尚气又给还了回去。我没兴趣知道这是在致敬什么情节,我只觉得这种无厘头的损非常可笑。拿电脑挡刀?那把热能刀既然能刺穿和切断整节车厢,一部笔记本挡得住?不还是因为刀身短砍不中尚气吗?拿笔记本挡刀纯粹是一种刻意和恶意,是一种实质的嘲弄:“你的奋斗毫无意义,所以献祭给更要紧的剧情推动吧。”
关于男女主就先说到这儿。因为男女主也就这点可说了。电影中后部分对中国文化乃至东亚文化的“探讨”主要体现在大罗村和十环帮。大罗村是所谓的“仙境”,十环帮则是尚气的父亲徐文武建立的“刺客组织”。
首先我们来看看“仙境”。
在设定上,大罗村是一个为了守护尘世不被来自其他维度的邪兽入侵而设立的军营。大罗村的村民靠神龙获得神力,炼制特殊的武器以战胜和封印邪兽,尚气的母亲也来自这一族。不过很神奇,大罗村村民的祖先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们的文化到底能不能算作东亚文化?大罗村存在了四百多年,所以大罗村村民相当于中华神仙?这个仙境十分“美妙”,我们可以看到帝江——其实是混沌(参考《淮南子》,《左传》,《庄子·内篇》,《山海经》)——九尾妖狐、麒麟、戴狗项圈的石狮、龙、克苏鲁,等等一系列神奇的东西都齐聚这竹林掩映的湖边小村周围。祥瑞之兽和妖邪之兽其乐融融地生活在这里,简直是加了五颜六色颜料的滚筒搅拌机。
仙境的村民,你就说不清这帮人的穿着和建筑属于哪一民族风格。从语言上看,他们说中文也说英语,可以和外来人自如交流,通古晓今。但穿着上又具有东南亚风格。建筑特点上,普通村民住草房子,而祭拜祖先和神龙的庙宇却修得金碧辉煌,这就仿佛是中世纪基督教村庄中,村民的住宅都十分简谱,而教堂却建得华丽恢弘。大罗村的庙宇主要用来祭拜祖先和去世的亲人,但这庙十足的“创新”,庙四面开口,完全透风,而祖先与亲人的牌位和画像就杂乱无章地摆在内壁的架子上,用几块屏风隔出所谓的内室。如果没有镜头推进,我甚至一时间都发现不了尚气母亲的牌位在哪儿。
说句题外话,这里有些灵牌旁边摆着画像,另一些则没有。我还没搞明白如此区分的缘由。将所有逝者的灵位都聚集在这一间庙堂里,是为了凸显大罗村“是一个大家族”吗?但我看这儿的人都各拜各的,且毫无私密性可言。
坦白来讲,我认为电影团队想借用东亚文化创造出一个架空民族,但又要重点参考中国文化,结果就是把中国文化抄了个四不像,还非要用资本主义电影工业那粗制滥造的创意极不合理地将其拼凑和表现出来。为什么说这是资本主义粗制滥造的创意呢?因为大罗村完全没有一个内核,他们看似很古老,却没有一丝发展的痕迹得以体现在画面上(历史的刻痕);他们看似很了解外部环境(说英语),却又恪守传统,且自信用手中的长棍就能同外部工业化的世界平起平坐。这种视角完全抹掉了东亚各民族各国家的现代化历史,也就是抹掉了东亚民族不得不挥别传统的伤痛史和奋斗中迎来希望和新生的发展史,而代之以虚伪的、想象的,用以装点欧美文化披萨饼的无机文化碎屑。所谓的“东方文化”大罗村毫无东方文化的灵韵可言——这是一种没有人生活过,也没有人会去生活的文化,一种只供消费的景观设计图。
让我们再来看看另一个承载“东方文化”的实体——十环帮的首领徐文武。这个人在设计上带有欧陆文化叙事中典型的对父权制的批判,但同时又被电影团队塑造成一个柔情、重视家庭、痴迷于爱的形象。他无比地思念失去的妻子,也爱着自己的儿子尚气。然而,我要先声明我的立场——徐文武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满大人”。梁朝伟扮演的这个角色非常遗憾地并没有洗刷掉欧美创造傅满洲的劣迹,反而用一种新的形象重现了它的功能。
徐文武是谁?一个来自黑暗而古老的大陆的侵略者、征服者。他征服了世界,用十环延续着生命,用十环帮暗中操纵世界,还想征服大罗村。然而他遇到了自己的妻子应丽,并诞下尚气和夏灵兄妹,从此隐世而居,不再过问江湖。直到自己的仇人为寻仇杀害了应丽,徐文武再一次戴上十环,并开始训练儿子尚气作为自己的接班人。在一次行动中,尚气借机叛逃十环帮以远离对自己控制欲极强的父亲,但徐文武早已无暇他顾,因为他听到已逝妻子的声音在自己脑内回响,告诉他自己被大罗仙人们抓走并囚禁起来,希望徐文武能拯救自己……
让我来摘下徐文武的面具,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货色。
徐文武的“东方形象”指向的是征服者,他想征服一切、操纵一切,但在遇到妻子应丽后,感到了满足,在那之后的生活,直到应丽死前,徐文武都是一个随和的“文明人”。然而,这种“文明”是装出来的,他本质上仍然漠视人命,只是妻子的存在填补了他的欲望,让他对尘世失去了兴趣。在妻子死后,他戴上十环,无视女儿,执意将儿子训练成杀手,他又回到了他原本的生活方式中去。
那么这和中国文化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
中国文化从来就不应该绑在徐文武这个角色身上。然而宣发上一定要说这是“傅满洲的改良版本”,一个征服欲极强的“好父亲”。他率领着一帮手持十字弩,穿着仿古代中国铠甲样式(?)的战斗服的战斗人员,让一个戴京剧面具,手拿苦无的忍者和一个断臂的罗马尼亚人作为副官,组成了一个四不像中的四不像军团十环帮。然而就是这帮被强行拼凑起来的马戏军团的领导者,一个从人设上跟中国文化毫无联系的徐文武,却又被赋予了凸显中国文化特征的任务。
诚然,他不是唯一的一个领受该任务的角色。杨紫琼饰演的大罗仙人和尚气的母亲应丽,也都有体现中国文化的任务在身。可我们要注意,大罗仙人和应丽在电影中一直在强调“传承”,这也是我个人认为《尚气》的主题——传承。亚裔如何传承中国文化,又要如何看待自己的母文明?《尚气》十分出色地完成了该任务——它证明某些美籍亚裔妄图靠割裂与母民族关系的方式装傻卖乖地玩弄“传统文化”的企图必将失败,最终只能靠虚构一个塑料般的“文化情景”麻醉自己,实则将自己所仅存的对母文明的追忆拱手让给欧美文化披萨饼,在资本主义文化符号的迷梦中沉湎。
扯远了。我们回到传承这个主题上。在大罗仙人训练尚气的过程中,曾说过这么一句话:
You are the part of all who came before you. The legacy of your family, the good and the bad, it is all the part of who you are”(大概在电影1小时19分钟左右,大意即“你与你的祖先一脉相承。你家族的传统,不论好坏,都会成为你的一部分”)。
这句话其实直击尚气的痛处,也就是他不断逃离其父亲的真正原因——他透过父亲的行为见证了这个男人的邪恶。在尚气的童年记忆中,母亲一直代表着一种温婉和善的概念,而父亲——尽管有时严厉——也具备慈祥和蔼的要素。这种向善的平衡在父亲外出,父亲的仇人跑来寻仇并杀死母亲的记忆里轰然崩塌。母亲死在了父亲造成的因果里,而父亲解决此事的方式是重新戴上十环(一种回归,可参考电影1小时24分钟左右的剧情)并以一种儿子从未见过的暴力毁灭了自己的仇人。于是乎,父亲在儿子眼中变成了恶,不论徐文武如何在儿子面前尽力展现和蔼的一面,这种定性的印象一直停留在尚气心中,不曾磨灭。
我们需要注意,尚气对父亲的恶感是如何产生的。父亲迟到的复仇仅仅是对这种恶感的确证,恶感的源头是儿子意识到母亲的死来源于父亲,善的泯灭来自于恶业。徐文武的暴力复仇仅仅是加深了这种印象而已。在电影1小时28分钟左右,尚气向瑞文坦白,自己也参与复仇并最终杀死了杀害母亲的仇人,他说:“She would hate the person that I become”,这个“She”指的正是自己的母亲。尚气逃离父亲,是要遗忘自己成为了和父亲相似的人的这个事实。然后尚气说:“My mom is dead because of him (Wenwu)”,他使用这个谎言,为自己开脱的同时,将恶的源头指向了自己的父亲。
有意思的是,徐文武也同样认为(1小时34分钟左右)尚气应该为自己妻子的死负责:“You were there when they came for her, yet you did nothing. You stood at the window and watched her die”。徐文武以此嘲笑尚气的逃避源自他不愿面对自己弱小无力的那一面,正是弱小无力的儿子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在别的男人手上。然而这仍是一种谎言,对徐文武而言,应丽对应的也是自己心中的善。在他体验过善与和合的生活方式过后,只能靠压抑对善的向往而继续领导十环帮,为此,他创造出将善的消亡推到自己儿子头上的借口,好让自己摆脱面对记忆中的妻子的羞愧,也因此正当化了自己入侵大罗村“解放妻子”的行为(为了追回善)。
这种角色矛盾的塑造是否有问题?我个人认为没有问题。问题并非出自对角色内在矛盾和冲突的设计,而是象征儿子所面对的恶的父亲,其身上也承载着传统的、家乡的、文化母体的要素。
儿子逃离父亲,正如亚裔逃离自己的母国,因为贫穷,因为政治因素,因为历史趋势,亚裔不得不背离自己的家园。家对他们是陌生的,异化的,他们从自己的文化母体中割裂出来,在北美形成了另一种文化认同。这本来不关文化母体什么事,可在这部电影里,文化母体却被强行拉下场来为年轻亚裔的“解放”和“文化繁荣”陪嫁。在电影1小时28分钟左右,瑞文回应尚气时说尚气7岁被训练成杀手14岁就被父亲派去出任务,这“对一个人伤害很大”。首先这是在什么视角下以什么标准衡量徐文武和尚气的关系?要明确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得知道此时的瑞文代表的是什么价值观——美式价值观。这是一种伪装成现代视角的西方视角在凝视这种东方的现代化叙事——父亲的仇人杀死了母亲,导致儿子背负仇恨进入江湖,这正是武侠式的叙事,是中国小说在现代形成的叙事模式——过后进行的一番高傲的质评:你们还是太野蛮了。尽管“野蛮”,中国的叙事和影视要素还是被“拿”到了这部电影里。竹林,石狮,龙,这些要素暂且不提。电影开头徐文武和应丽的武斗,其动作要素和拍摄技法完全照搬中国香港和中国内地武侠片,有人可能会说这是致敬,但我要提醒的是,他们已经学会了,而他们不会刻意说明这是来自中国的东西。而来自中国的是什么呢?是徐文武,这个黑暗、暴力,让“儿子”敌视、逃避的古老“父亲”。尚气在追忆父亲时说:“血债必须要血偿”。他失去“母亲”的创伤,必须得由“导致母亲消亡”的“父亲”负责,而负责的方式就是“父亲”付出“放弃梦想”的代价。但是,真正杀害“母亲”的“入侵者”已经被“父亲”解决,“儿子”因不再体会“入侵者”的威胁而将其遗忘。“父亲”真正的“梦想”则被“儿子”(或者说《尚气》)看作克苏鲁一样的怪物。这部电影想表达什么,我就不用多说了。
然而,正如前文所述,《尚气》强行将徐文武和“父亲”的意向相结合的尝试在该电影的叙事过程中失败了。首先,我们可以看到,尽管电影团队“拿”了那么多中国文化的要素,却始终只是呈现了一个欧式的“反父权”的故事。在这个故事里,父亲和儿子的创伤都围绕着应丽(妻子/母亲),应丽的缺失让他们互相仇恨。最终儿子对母亲死亡意义的阐述在电影的叙述中超越了父亲(尚气承认了母亲的死亡,但徐文武一直在逃避),这正是对古希腊悲剧中儿子争夺母亲消灭父亲的戏仿。其次,父亲的意向成为了一种落后的意向,而这种落后不应由我们的文化负责。徐文武刻意地疏远女儿(这也是非常诡异且不符合中式价值观的,不要把某些农村里重男轻女的那一套搬出来,那才多少年?恶就是恶,没有什么冥顽,只有落后和闭塞的借口),尽管这个女儿天赋出众,且渴望父亲认同,父亲徐文武还是像瞎子一样无视了她。这种尴尬的价值观并非“来自于中国”或“来自于欧洲”这种幼稚的分野所能区分的。这种父权制的价值观来自于落后。而持这种保守落后价值观的徐文武,却在电影中以“征服了世界”,“暗中操纵世界”,“十环帮的幕后主使”的头衔登场。这种露出的马脚,证明了电影团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与理解之匮乏,以极不负责任的手段生搬硬套,尝试着装作反思(作秀),实际上做出的电影却让观众开始替他们反思:这帮人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总而言之,他们对母文化的误解,以及自娱自乐的井蛙行径,不应该由其母国与母文化负责。
我最后想说的是,对文化的反思不应该抛弃整体而只分析局部。不同民族文化的融合,现代化的进程,都是需要考虑复杂因素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然而在分析具体问题的同时,我们决不能抛弃整体的大局观,以片面的正义取而代之。如果只想着割裂和独走,那成为“孤儿”的人将不会得到世界的大潮中任何一方的无偿接纳,对文化的追忆和价值观的取向也不会帮这些人融入到任何已存有的群体中去,只能在无迹可寻之地漫无目的,惶惶一生。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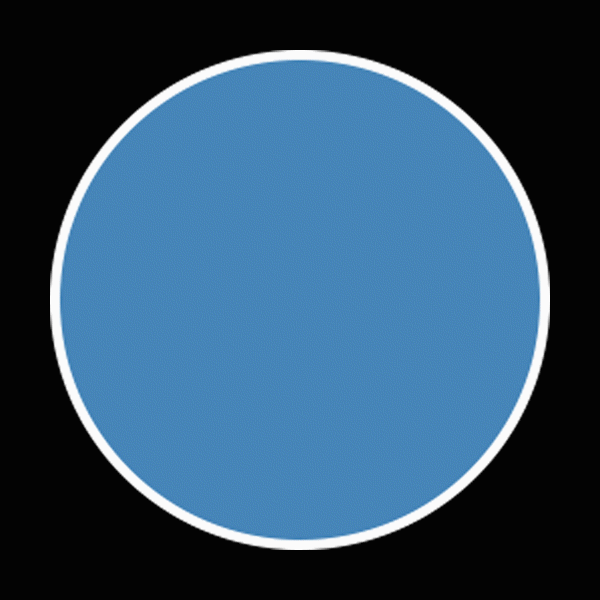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8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