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前阵子在暴君7200的文章《怀旧、阈限空间与现代意识》里了解到了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我便对这种和建筑空间关系密切的互联网视觉标签产生了兴趣。带有阈限空间标签的视觉内容通常是空无一人的建筑空间,例如走廊、停车场、大型超市等等。这些是当代城市中的常见场景,其中没有什么高辨识度的特征,不仔细观察很难判断出其所处的文化或地域背景。看向这些带有“阈限空间”标签的图片,就算你无法从其中感受到某种情绪,也会发现它们共享某些特征。
Reddit上的一个meme总结了几条阈限空间的特征:
- 多在建筑内部;
- 过渡性的空间;
- 怪异的;
- 不自然的灯光;
- 奇怪的熟悉感;
- 令人不安;
- 与“阈限”的概念有关(由人类学家Victor Turner提出);
- 无人的。
那么为什么这样无趣又带着些许诡异的场景会成为一种引起共鸣的视觉标签,甚至辐射到中文互联网?
我看到过从精神分析角度的解读,将阈限空间和“怪核”、“梦核”放在一起讨论,认为其唤起的感觉是潜意识或童年记忆作用的结果。“怪核”、“梦核”是一种包含早期计算机图形、低分辨率业余摄影、超现实主义等等元素的复古千禧年数字美学,传递一种诡异怀旧的感觉。阈限空间有时会作为元素的一种出现在其中,不过本文无意讨论互联网早期的数字美学复古风潮,而是更多聚焦于阈限空间为何会引起共鸣?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首先放出我的解释:阈限空间的流行是商业社会和城市化到达一定阶段后才会有的现象,它意味着当代城市已经产生了自己的乡愁。
阈限空间是一种反“阈限”
阈限空间是一种反“阈限”
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中的Liminal源于Liminality一词,源自拉丁文limen,有“门槛、阈值、边界”的意思。最初是一个人类学术语,由法国人类学家阿诺德·范盖内普(Arnold VanGennep)提出(不是meme中提到的特纳,但是特纳发展了该概念),作为“过渡仪式”(Rites De Passage)中的第二个阶段(所有过渡仪式都有三个阶段:分离阶段、阈限阶段、聚合阶段),该阶段“很少带有或不带有任何过去的或即将到来的状态的特性”,而且位于其中的个体“状态含糊不清”。过渡仪式可以理解为个体的不同人生阶段之间的转换阶段,通常表现为由社群约定俗成的特殊事件,例如成人礼、婚礼等等……而仪式中的个体通常会进入一种暂时的、模棱两可的、不稳定的状态(例如成人礼中的人既非成人也非儿童)。
回看阈限空间图片中出现的建筑空间,很容易发现此概念中对“阈限”一词的使用其保留了过渡、转换的含义,图片中的建筑空间所具有的过渡属性包括空间和情境的双重含义。首先,是空间上的:这些建筑空间中有相当一部分是楼梯间、走廊、停车场这些人类不会停留的交通空间,是建筑的“附属设施”。其次,这种过渡是情境上的:还有一类阈限空间图片是超市、停车场、候车厅等公共场所,这些空间虽然是某一栋建筑的主要功能。但是将其置于更广大人类活动中时,它们只是纯粹功能性和过渡性的“服务设施”。而且这些空间通常缺少个性的,过于平常,以致于人们总是匆匆走过不予注意。而一张聚焦于没有个性的过渡空间的图片,总是略显诡异的。
比较阈限空间和人类学语境中的“阈限”,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虽然仪式中的“阈限”对于个体的一生来说只是几段短暂的过渡阶段,但其往往极具象征意义,能对个体的日常生活产生相当的影响力。英国人类学家维克多·特纳(Victor Turner)认为这是因为仪式中具有强烈的象征符号,这种符号能统合个体的自然欲望(感觉极)和社会道德规范(理念极)。象征符号“指的是仪式语境中的物体、行动、关系、事件、体态和空间单位。”它们是“仪式中保留着仪式行为独特属性的最小单元,也是仪式语境中的独特结构的基本单元。”因此,仪式及其“阈限”往往是日常路径的重要节点,通过高密度的符号暗示或告知个体生命阶段正在发生转换。
但是阈限空间图片中所呈现的场景显然是去仪式化,无语境的,空间中的符号被缩减最低——建筑法规规定的指向标识。人类学中的“阈限”的含义随着语境的变化发生了迁移,甚至走向了原本意义的反面:乏味且缺少意义、毫无特殊性。因此从人类学的视角看来,阈限空间是反阈限的。正因如此,其反阈限的特性反而让网络上对阈限空间的共鸣变得格外耐人寻味。
日常与非常的反转,“建筑学式脑白质切除术”的后遗症
日常与非常的反转,“建筑学式脑白质切除术”的后遗症
我们可以将人类学中的“阈限”与个体生命中的其他阶段视作一组二元关系:如果说其他阶段的微小、重复、琐碎的状态是种“日常”。那么仪式和“阈限” 则是一种“非常”。同样的,基于转换和过渡功能的阈限空间和其他建筑空间的关系也近似于此:供人停留的房间是“日常”,人们在其中工作、休闲、进食;供人通过的阈限空间是“非常”,其中不应有人生活的痕迹。
从建筑设计的角度来看,各种空间本应如此按部就班,容纳其该有的人类活动。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只是“阈限空间”之外供人日常使用的建筑空间已经从生活的容纳者变成了生活的催促者(在与商业有关的建筑之中尤其如此,而这基本是城市中大部分公共空间)。它们被卷入商业、消费和资本的狂奔中,增生变异。单体建筑的体量激增,以便于容纳更多本来毫无关联的场景和功能。想象一座几十层高、外表是精致玻璃幕墙的高层建筑(这在大城市并不罕见):其中几层是办公室、几层是商改住、几层是餐馆、几层是健身房、几层是购物区……我们几乎无法从建筑外部想象其中的全部场景,这些场景之间也没有可被理解的关联逻辑。
曾经,在学院建筑学的语境中,建筑外观和内部产生有效关联是一种关乎诚实的道德。但是荷兰建筑师雷姆·库哈斯通过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纽约的发展,呈现了传统建筑学在大都市中的失语。纽约的摩天大楼中几乎没有欧洲式建筑家的身影,反而是商业和资本手执柳叶刀给摩天大楼做了“建筑学式的脑白质切除术”。这产生了大建筑的两种特征:
一种是大都会外表的建筑,它的责任是为城市提供雕塑般的经验。一种是室内设计的突变,采用最现代的技术,它回收利用、转化和制造记忆,以及辅助这些记忆的图像,印证和摆布大都会文化中的各种更替。
自此建筑各部分之间的断裂不再是一种值得忧虑的情况,人们甚至建筑师也开始坦然与“精神分裂”的建筑共处。
建筑内部场景的变化不仅仅是空间上的,也是时间上的。生活在这种建筑中的我们,被卷入了一种和速度相关的断裂之中:商场中的店铺随季节调换主题,租户品牌每隔一段时间也会更替。这些和商业相关的场所变成了“美术馆”:根据商业周期重新创造一个布景、一种情境。周期过去后,所有的痕迹又都被抹去。容纳日常的空间成为了不断增生变异的非常,它不断抽打着我们进入崭新的场景,让我们沉浸享受,又突然变脸将我们踢出,在我们来不及怅然若失前又催促着进入下一个周期。不再是我们需求建筑,而是建筑制造我们的需求。
原本属于日常的空间变成了让人应接不暇的光怪陆离,反而是连接它们的阈限空间,因为其通用、乏味、安静的特性化成了稳定的日常的虚像,日常和非常的场景被反转了。网络上对“阈限空间”的共鸣潜意识里是对日常感的追寻,但是“阈限空间”从被设计之初就带着流动与不安,所以它无法成为日常的替代品,而只能是高速狂奔中的喘息。
当代都市里的虚幻乡愁
当代都市里的虚幻乡愁
阈限空间唤起的情绪还有更多的维度。
正像开头的meme所中提到的“怪异的熟悉感”,认为阈限空间带来感觉的人不在少数。Reddit上有人将其同déjà vu联系起来,认为图片中的场景带来一种似乎去过但实际上又没去过的感觉,是对从未发生过的记忆的怀旧。这造成一种不适的平静,为其增添了某种都市怪谈的气质。但其实这并不是什么玄学,反而是一种非常容易理解的建筑现象。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上文提到了阈限空间通常是功能性出发的交通空间或大型的公共场所,而此类空间通常是成本控制最极致、建筑法规执行最为严格的部分,因为涉及建筑的安全底线(防火疏散),这里杜绝矫饰,通常只包含最低限度的设计,这里是商业周期的“法外之界”。
阈限空间的形式外表被建材产业链的标准化所决定:颜色趋同的人工照明,工业制式的地面铺装和吊顶,法规强制的标识图形。这一切的直接结果就是:在共享类似成文法规和产业特征的区域内,阈限空间具有趋同的特征。甚至在不同国家的现代城市中也是如此。下面是一张reddit上的图片和我几年前在北京某地下通道拍摄的照片,乍看之下似乎是同一空间的两个角度。这不仅仅是巧合而已。
在大部分人看来,这样的空间毫不浪漫,亦无诗情可言。但是当其成为了一种通用的城市景观,是城市居民共享的空间记忆,就存在了投射情感的可能。正像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Charles Pierre Baudelaire)一样,他将“煤气灯与夜空相连,让花香与焦油的气味并列”。他在泥泞的街道、吵闹的工坊、刺鼻的煤烟这些“丑陋肮脏”的景观中找到了诗的意向。波德莱尔就是这样在《巴黎风景》中,通过对19世纪巴黎城市景观的描绘,完成了早期现代化过程中个体诗意的迁移.
人们对阈限空间的共鸣也是如此,对变化、速度、丰富的厌倦,反而让这些通用、乏味带着些许诡异的场景变成了情感公约数。人们注意不再是那些精心营造的场景、仪式和事件,对平常事物的凝视激发了更多的想象。这不是某个艺术家和创作者有意识的调用,是原子化商业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追溯。这些原子生于产房死于医院,终其一生活动在“向独居的个体,向转瞬即逝的、暂时的和朝生暮死屈服”的城市自然。而对阈限空间的共鸣是当代都市人虚幻而无根的乡愁。
最后,附上一节我从英译版《巴黎风景》翻译的诗句:
工坊中传出了歌唱与喋喋不休; 烟囱与尖顶,这些城市中的桅杆 伟大的星空使我们梦到不朽。
参考
参考
- 《象征之林——恩布登人仪式散论》 [英]维克多·特纳,赵玉燕 欧阳敏 徐洪峰译
- 《Non-Places Introduction to an Anthropology of Supermodernity》[法] Marc Augé, John Howe译
- 《癫狂的纽约》[荷]雷姆·库哈斯,唐克扬译
- 《恶之花》[法]夏尔·波德莱尔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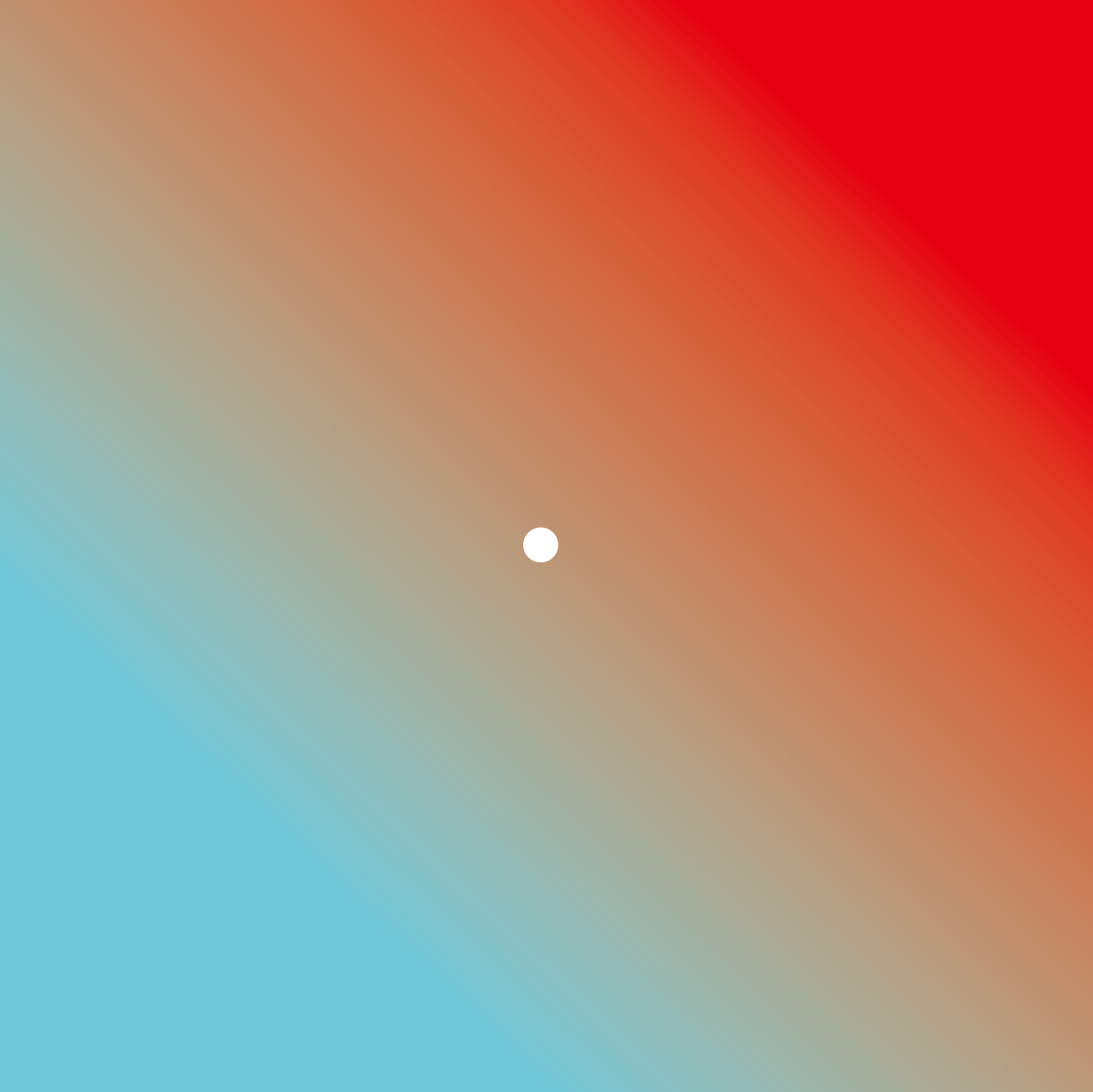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