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我的宿舍在四楼,拖着行李箱爬楼梯很不容易。我是那种很缺乏锻炼的人,每次爬上四楼都能让我气喘吁吁。此刻我只想赶紧到自己位子上坐下,什么都不干的先缓个五六分钟。
宿舍是六人间,独卫独浴上床下桌,条件还不错。我们每天都打扫宿舍,它总是一尘不染的样子,几乎每次都能评得上十佳宿舍。虽然不算什么很耀眼的荣誉,但也是对一段美好时光的纪念。
比起冷冷清清的家里,宿舍对我来说就是一个相当熟悉、相当有安全感的地方了。在楼梯上的时候我曾想过宿舍里可能也会有什么妖怪,因此开门的时候还是小心翼翼的。推开门之后迎面扑来的就是空调送来的凉风,宿舍也一如既往的干净明亮,看不到有任何妖怪存在的痕迹。
一个早到的舍友正抱着吉他边弹边唱。吉他弹得还行,唱的却像是刚学会中文的外国人一样,听不出来是什么调。由于他是安静的宿舍里唯一在动的“活物”,所以我的目光自然就被他给吸引了,注意力都在他身上。
怪哉!该不会有什么让人唱歌很难听的妖怪吧?
我仔细地打量他,他看上去很正常;我又看那把吉他,吉他也很正常,不像是会有什么吉他精琵琶精的样子。
我完完全全放松下来,坐在位置上的时候被口袋里的硬物给硌到了。是我的钥匙。我一边看着他弹吉他一边抽开抽屉要把钥匙放进去。抽屉里有一个硕大的黑色妖怪,在我拉开抽屉的那一瞬间,我感觉我和它四目相对了。
我其实并没有找到它的眼睛在哪里,但我觉得是有目光接触的。那一瞬间我像是触电一样,完完全全地被定在了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美杜莎对视大概就是这样的感觉?
它很大,足有一个巴掌那么大,通体黑色,背上覆盖着油亮的甲壳。甲壳是一节垒着一节的,层层叠叠像是一只蜈蚣。它突然发出“簌簌簌”的声音,身体都膨大了一些,甲壳的连接处像是要爆开般。我大叫着往后猛缩,没有包垫子的金属椅子腿在地面上划出令人头皮发麻的响声。在这样的响声与我惊慌失措的叫喊中,它像一只跳蚤一样猛地弹射出来直冲我的面门。我顺手抄起桌面上的一本书向它砸去——或者叫格挡。砸是砸到了,但它没有“实体”,书本穿过了它拍在桌面上发出巨响。弹吉他的同学惊到了,抱着吉他站起来看向我,一边喊着“怎么了”一边在观望我这边的情况,样子像一个抱着冲锋枪的哨兵。
这个妖怪直扑我的脸然后从我脑子里穿了过去。我目光跟着它猛地回头,看见它落到了我身后的地板上,又向斜上方窜去,在门框上一个借力,跳到走廊上去,消失在我的视野里了。我松了口气,放下了手中的书,擦了擦冷汗。额头上湿的像是刚洗完头一样。
“怎么了怎么了?”那个同学依然抱着吉他,琴头到处乱指,像在扫射一样。
“蟑螂。”我说。我依然惊魂未定,像骗他又像安抚自己似的,又加了一句:“蟑螂。”
我们宿舍都挺怕蟑螂的,说这个不丢人——总比说是“妖怪”然后被当成疯子强。他一边嘀咕着“我们宿舍居然还有蟑螂”一边低着头四处看,谨慎地坐下了。
指南翁学着我的语调说:“哟哟,蟑螂。”
我瞪了他一眼,又懒得和他计较。我确实是被吓到了,现在还没缓过劲。我扯过一张纸,写下:那是什么?
“那是柜鼠。”指南翁说,“喜欢阴暗干燥的地方,所以经常躲在米缸啊、抽屉啊、衣柜啊之类的地方。”
长得不像老鼠啊。我写。
指南翁说:“以前人们经常在存放食品的柜子里发现它们,以为它们是像老鼠那样偷吃食物的,所以就叫‘柜鼠’。后来人们发现不吃食物,但都叫习惯了,就一直‘柜鼠’‘柜鼠’的叫了。”
他又阴阳怪气地加了一句:“我看就叫‘蟑螂’也不错。”
我不理会他的嘲笑,在纸上写:人们还是妖们?谁起的名字?
“‘人们’和‘妖们’,”指南翁说,“具体我怎么说得清,流传好几百年了。”
我写:几百年前的柜鼠和现在的柜鼠是同一种吗?
指南翁想了会,说:“应该是,我也没见过那玩意。”
我还要再问的时候又有舍友到宿舍了。我的位置在门口,在那写东西容易被人看见,于是我也没再问,把纸揉成团扔进了垃圾桶。这之后我开每个柜子都特别小心翼翼,不过再没看到柜鼠。天黑之后舍友也陆续来齐了,我们一起到食堂吃饭去。
食堂分上下两层,我们一般都去二楼的窗口吃饭。我在学校里一般只带要用的书去班上,很少背着书包,指南翁也就被我连带着忘记在了宿舍里。
我感觉他刻意想让我多跑这么一趟,因为我出门的时候没看见他,估计是躲起来了。
“我东西忘记拿了,先回去拿一下。”我说,“你们先走吧。”
他们也没多说什么。我快速地吃完了剩下的饭,加快脚步往宿舍方向走。
在楼梯上,我遇到了我前桌叫瞿清鹤的女孩子。我们打了个招呼就擦肩而过。我想多和她说几句话,不自觉地就回头说了一句:“那个……”
“嗯?”她回过头笑着看我,“怎么了?”
整个楼梯间就我们两个人,没有别人也没有妖怪,空气都安静下来了。我也想不到我为什么要叫她,可能只是我内心中一个无意识的念头而已。僵持了两秒多种我实在想不到该说些什么,脱口而出的是一句:“一会英语作业,那个……你懂得。”
她有一些惊讶的神色,但这惊讶的神色只持续了很短暂的一瞬,就好像她对于这句话并不意外。她笑着说:“我还以为有什么事呢……好啊。”
我还能说什么?我催促自己快想,但实在编不出来了。
“先走了,拜拜。”最终说出口的是这句。
“好,班上见。”她说着微笑了一下,转身上楼了。我也正要往下走,她突然叫住了我。我回过头茫然地看着她,她小跑两步走下来,手握拳头伸到我面前有东西要给我。我伸出手,一颗椰子糖落在了我手心里。
我愣了一下。她解释说:“我打算带到班上去的,不过正好在这看见你了,先给你一个。”
“谢谢。”我说着把糖揣进口袋。
她莞尔一笑,又小跑着上楼了。我抬起头看她进了食堂的门,伸手在口袋里揣着那颗糖。塑料的包装纸都像是有温度一样,我感觉还没吃都已经尝到甜味了。
我一边回想着刚刚碰面的场景一边往楼下走,心情十分愉悦。食堂后门的楼梯离宿舍近,也比较靠近后厨。路过后厨的时候我往里面张望了一下,看见了一个肥硕的、像是蠕虫一样的妖怪,横亘在备料间门口。
它就这么大喇喇地出现在我的视野里,我脑海中那些粉红色的回忆全被它冲的一干二净。那是一只有着马苏里拉奶酪般黄颜色的妖怪,体长大约是两米到三米,像是一只被剪开了茧的蝉蛹,非常肥硕,两头尖中间粗。两头长得差不多,看不出头是哪个。
我本来想根据五官来分析哪个是它的头的,但它身上的嘴巴实在是太多了,全身上下都覆盖着嘴巴,光我看见的就得有十多个。它的嘴巴很像是章鱼的嘴,圆形,有很多小尖牙藏在嘴里,时不时地回外翻出来。它有一端有两个触角,触角上吊着两个发光体,像是灯笼鱼的灯一样,我不知道那是眼睛还是诱捕器感受器之类的器官。看到我向它走过去,它全身的嘴都裂开了,发出吸气的声音。
这谁敢靠近啊?我尽量绕着远处走,然后向宿舍飞奔去。穿过蛛丝目的时候我迟疑了一下,打了个趔趄,生辅老师端着他的搪瓷杯在我身后叮嘱:“哎呀!慢点慢点!”
我以高中三年中最快的速度蹭蹭蹭地上了四楼,找到了指南翁。
“还知道回来啊。”他说。
我懒得和他说话,先确定了一下书确实在包里,然后背上它边下楼边问:“你知不知道一种黄色像蝉蛹一样的妖怪?我刚刚在食堂里看见了,很大只。”
“你这个描述太宽泛了。”指南翁说着又想了想,“不过食堂里看见的很可能是饭虹,我还是要看见才能确定。”
“就在后厨趴着。”我说着加快了脚步。
当我再次看见那个饭虹的时候,它已经膨胀到原来的两倍大了,正在食堂窗口前蠕动着前进。
我脱口而出了一个本来是脏话的语气词。
“就它?”指南翁问。
“是的。”我说。
指南翁捋着胡子,点头:“是了,就是饭虹,靠饭菜香气为生,不常见。”
“吃人吗?”我问他。
指南翁笑了:“妖怪又碰不到人,想吃它也吃不到。”不过他又正色道:“但它有时也难免吸一些很小很小的妖怪进去,比如说各种昆虫妖啊鸟妖啊,名目太多了。”
“危险吗?”我问。
“对于小妖怪来说很危险。”他说,“你见过鲸鱼捕食吗?一张嘴就全吞下去了,它那里在乎自己吃的是哪种鱼。饭虹也是这样,虽说是靠着香气为生,但它吃起来的时候也难免吸一些小妖怪进去,它也不会把它们给吐出来。”
我点头表示了解了。
指南翁又说:“叫‘虹’的妖怪都有一定的危险性,比如还有一种妖怪叫‘肉虹’,是专门捕猎其他妖怪的妖怪,长得也和这个饭虹差不多,只不过是粉红色的,像是放过血的猪肉——见到你就懂了,不过不常见。”
“彩虹呢?”我问。
我觉得我是在抬杠,但指南翁相当严肃:“彩虹应该是所有‘虹’里最可怕的。”
“那不是自然现象吗?”我说。
指南翁说:“你说的那个是天上的彩虹,我说的是妖怪的‘彩虹’,妖怪的‘彩虹’名字就来自于那个‘彩虹’。它是很凶暴的,你见到就知道了。”
我有点不信,但还不等我说话,指南翁又说:“希望你永远也遇不到。”
他没有了往日的轻浮样子,反而异常的严肃,严肃地足以配得上他这老头的外表。我不敢再问话了,也有意避开了那个饭虹。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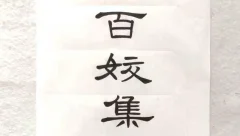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