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周六上午语数英各一节课,原本精神许多的我又昏昏欲睡。我一直觉得没有什么能比连着三节主科课程更能消磨人类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了。就这样半睡半醒地熬到下课,精气神一下子又都回来了。我兴冲冲地第一个跑出教室,直奔校车集合点。校车停在图书馆前的广场上,隔着老远就能看见有很多烟灵子漂浮在上空。我拖着行李箱在前面跑,指南翁看快要追不上我了,就躲回了书里。
车厢下面密布着车蛎,还有一些车蛎从别的地方爬来,我已经见怪不怪了。我将箱子放在了有车蛎爬来爬去的行李厢中,快速钻入车中占了个好位置。不久之后又陆陆续续的有一些像我一样的先锋队员登上了校车,争夺最早发车的这班车的座次。
我收到了瞿清鹤发给我的消息:帮我占一个位置。
这事不用说,自然是要做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发现她正好和我顺路回家,于是我们就常常结伴而行。这样的短途旅程算是漫长六天的学习结束时一个令人期待的事情。这样的期待并没有过多的意思,仅仅是期待而已。
我看到她在外面四处看,便向她招手。她看到了我,笑着向我挥手回应,拉着行李走过来。司机师傅提醒了一下发车的时间,坐在了驾驶座上。
瞿清鹤是最后一个上车的,坐在了我旁边。
我尽量往里边靠了点。虽说是一人一座,但我还是尽量给女生多留点位置,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绅士风度。
“差点就没赶上。”她说。
“是啊。”我说。我想多说一点的,至少不止是一句“是啊”,但一时间又什么都想不起来,最后说出口的还是一句是啊。
不过她也不在意我的内心活动,这只不过是独角戏罢了。
此时的车厢经过一段时间的曝晒,车里十分闷热。大巴的车窗还无法打开,车内气温估计得有五十摄氏度。司机上车之后打开了空调,但是多年未洗的空调又带来浓烈的灰尘味,在这样的环境下,我捱了半小时,总算是到达了位于市区的老校区,在那里我还要坐二十分钟的公交车才能到家。这半小时中我几次想搭话,又觉得话术实在太笨拙了,最终都没说出口,当我最终说出“今天天气不错”的时候,校车都开到目的地了。
“哪里不错了?”瞿清鹤说,“热死了!”
她把天又聊死了。她用手扇了扇风,刘海并不像小说或者电视剧描述地那样“轻轻拂动”,而是被汗水浸湿紧贴在额头上。
“今天我妈来接我,我先走了。”她说这话算是告别,“下周见!”
“下周见!”我说。
她下了车,我紧跟其后。我比较怕指南翁这时候揶揄我,不过好在他什么都没说。
老校区坐落在吉祥山上,但所谓的吉祥山百米不到,也就是一个小土包而已。宋朝的时候这里是城界,上面有城墙遗址。这里原来还有个吉祥庙,也不知是山因庙得名还是庙因山得名,总之这个庙在文革的时候被拆除了,现在只剩两面残墙和一个香案。
话说回来,就算吉祥庙没在那个年代被拆掉,放到今天也迟早被拆。这个庙里既不供神佛也不供土地,谁也说不出里面供的是什么。据说当年拆的时候,工人们看见神座上空空如也但又香火旺盛,都说这里供着狐仙,之后以讹传讹,就有了点吓人的传说。有说供着城隍的,有说供着什么尊者的。还有的说这是曾经的地下联络点,在这里送出的情报传遍了周边所有县城;更有甚者说这里下面有个导弹发射井,整座山就是个军事基地,也不知道怎么想出来的。
进入新世纪之后,为儿女找对象这种大事使得大妈们想起了早就只剩残垣断壁却仍然屹立不倒的吉祥庙,将这里重新利用了起来。这对于这个庙来说倒也算是个好事,比起被征做广场舞场地而言,做个婚介所倒也算是功德一件。
不过它又是一个极普通极普通的所在,普通到即使路过一百次你也不会因这里有个什么庙而感到稀奇。就是这么一个普通的相亲圣地,指南翁却对我说:“和我上去看看。”
我有点摸不着头脑:“去干吗?”
指南翁露出不耐烦的神色:“叫你和我去就和我去,哪那么多话?”
他应该要说“带我去看”而不是“和我去看”的,毕竟主动权在我这,他无法离了那本书独自行动。但最终还是我做出了妥协。我将书包和行李箱寄存在学校保安室,带着他上山去。
我们来到了吉祥山上,在那个颓败的破庙前面,无数根挂着个人简介的红线交织在一起,像是一张情网网住了过往的单身男女。在这情网面前,我大概是个漏网之鱼,母胎单身到现在。远在国外的爸妈不断叮嘱我不要早恋,但这完全就是杞人忧天。我看着交错的红线与后面坐着的边嗑瓜子边攀谈还把瓜子皮扔的到处都是的大妈们,有点时空交错的恍惚感。我问指南翁:“我们来干吗?”
红线之间还有很多小妖怪游来游去,穿行在这红线之中。它们也是情网的漏网之鱼。
指南翁用命令的口气对我说:“庙后面有算命的摊位,你过去看看。”
我正要走呢,他又说:“我看那边那姑娘长得还不错,你看看?”
我本来对姑娘是没有什么兴趣的,但既然指南翁这么说了我还是顺便瞟了一眼。当我看到那张贴着四十三岁带着两个孩子的离异妇女照片的简介的时候,指南翁大笑起来,说:“叫你看你还真看啊。”
我无意和他纠缠,反正看见个中年妇女我也没亏什么。我按照指南翁的指示穿过密密麻麻的红线,转过一棵大樟树,路过了三四个在茫茫红尘边上下棋的大爷,拒绝了一个卖脚气药的小贩之后,吉祥庙后山的真面目总算出现在我面前了。这里是一个小平台,旁边围着青石的矮墙,矮墙前面水泥树桩垃圾桶旁竖着一块“宋城墙(仿建)”的牌子,仿佛就怕你摸着现代工业的制成品来一场跨越时空的历史对话似的。这里有许多明明不瞎却还要戴着墨镜的人支着算命的摊子。他们本来一个个都在看书或者玩手机呢,看到我来全都收了手上的东西,一本正经地摸索着自己面前的摊子,这个场景像是一群人在隔空打麻将。无数印着黑体或仿宋的“算命”字样的大黄旗下面挂着蓝色和绿色的二维码,它们的尺寸一点也不比“算命”两个字小。
“什么意思?”我问指南翁,“不都是些骗人的吗?”
指南翁点头又摇头:“上来就说你印堂发黑的肯定骗人,那都是唬你的。你往里走,我刚刚在山下就感觉到一阵很浓的妖气,就像叫你上来看看,我感觉这上面应该有个人有真才实学。”
我感觉有点害怕:“不好吧……万一我……”
指南翁一脸嫌恶的表情:“你怕什么?那些大妈都不怕!”
我还是感到害怕:“大妈们什么做不出来?而且她们又看不见妖怪,我就是怕我看见什么妖怪,万一看见个贞子那样的,就算碰不到我我也……”
指南翁摇头:“少来,贞子她有护照吗?能从日本过来吗?你慢慢往前走,我说停就停。”
我照着指南翁的话慢慢往前走。周围古树茂密,还有不知名的鸟或妖在树林里叫,即使是白天这也显得有些阴森。每往前走一步,我的恐惧就加剧一分,我生怕他叫我走到平台外的树林里去。
“停!”指南翁指着路边一个算命的和我说:“上去和他聊聊天。”
这个位置不算很偏僻,我松了口气,问:“聊什么?”
指南翁觉得我问了个很蠢的问题:“算命该聊什么你就聊什么呗!测学业测姻缘,再不成你问问明天的体彩开奖号码,你看他靠不靠谱。”
“真有人能算出彩票号码?”我不相信。
“算出来才不靠谱哩!”指南翁说,“算出来不就自己去买了?你就上去搭个话,哪那么多废话?”
我只好走上前,在算命先生面前的小马扎上坐下。先生抬眼看了我一下,推了推墨镜,端着架子说:“这位兄台,何事造访?”
我刚想回答,指南翁回答:“我也不是什么古老的妖怪,你就用白话就行。”
我这才知道所谓的“兄台”是对指南翁的称呼。
算命的靠在竹椅上,口气变得有点痞气:“我就混口饭吃,很少有妖怪主动找上门。”
指南翁说:“我刚刚在山下就感觉到了很重的妖气,看起来你的水平挺高的。”
算命的拍了拍他的肩膀,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都高到了能摸到妖怪的程度。他说:“你俩来这干吗?要不算命就赶紧走吧,别妨碍我做生意。”
指南翁笑了笑:“就你还有什么生意,看你坐半天也不见有人上门。算命就免了吧。我猜你也有些拿得出手的东西,卖点给我们?”
算命的一听起劲了,往手心啐了口唾沫,搓了搓,从摊子下拿出一个盒子,热情的介绍着:“别人来了聊半天都还不上套,就你俩一来就往坑里跳!既然你俩这么坦诚,咱也就不玩虚头巴脑的,给二位看看新近刚收的好货,要有看得上的就随意给点,当交个朋友。”
这样的热情多少有些奇怪。
盒子里面转满了珠串符石,这些物品上或多或少的都有些妖气,闪着不同颜色的光芒,有的亮有的暗。我看见这里面甚至还混有一个十字架,它与周围的东西格格不入。算命的注意到我在看那个十字架,讪笑着解释:“这东西虽然和周围的物件不太一样,但是效果都差不多。对于外来文化咱是什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有用的咱都摆一块。咱这叫什么?和国际接轨,引进外国技术……”
指南翁很严肃地打断:“对宗教你还是尊敬一些吧。”
算命的轻扇自己一个巴掌:“您老别介意,我就是嘴贱。”
指南翁转而对我说:“挑一挑吧,留着可以也可以用来对付一些妖怪。既然你看的见,总要会点驱逐之术。”
算命的主动对我推销自己:“有麻烦可以找我,我可以上门驱鬼,按时辰收费,一个时辰一百二,两个时辰只收二百,一次买五个时辰收五百还饶你一个珠子,合算的呢。”
指南翁也没有什么表情,只是冷笑。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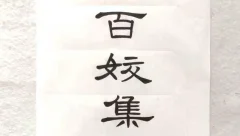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