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荷兰艺术家康斯坦特·纽文惠斯的新巴比伦项目在建筑学和美学层面对后世的启发,无需在此多言。北京央视大楼的设计者,同为荷兰人的建筑师雷姆·库哈斯的早、中期实践都可以直接追溯至此。
从时间角度总体看来,新巴比伦方案处于20世纪中后期对现代主义建筑反思的浪潮之中,康斯坦特在情境主义国际时提出的「统一城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中就提出要「反对欧几里得几何学,城市和建筑设计中过度的功能主义」。「纸上建筑」在这一时期层出不穷,它们随着媒体传播成为夭折的创造力的注脚。
从建筑形式来看,它们多采用巨构建筑和可动建筑的方式:从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的欢乐宫(Fun Palace)到建筑电讯派(Archigram),再到日本的新陈代谢派(Metabolist),以及尤纳·弗里德曼(Yona Friedmen)的移动建筑(Mobile Architecture)等等……这些无一不通过空间与生活的关系论证一种新建筑的可能。
但要注意的的是,现代主义建筑最活跃的旗手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也曾这样做过。他的「光明城市」不过是一种在工业革命上升阶段的乐观氛围下产生的新乌托邦。构建一种空间乌托邦,似乎一直是现代主义以来的建筑师最深切的愿望。
那么,新巴比伦及其同时期的其他思潮与现代主义建筑的区别又在何处呢?
那应该是一种对流动与变化的迷恋,对效率与秩序的厌恶,对被既定位置所捆绑人与建筑的慨叹,一种对德勒兹和瓜塔里的「游牧」(nomad)的向往。正像情境主义国际所宣称的那样「唤醒和追求真实的欲望,体验生命和冒险的感觉」。
新巴比伦实现的基础是一个生产性活动完全自动化、人类只需专注于创造的「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一个「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实现的时刻。虽然新巴比伦在技术层面完全具备可操作性,但这一社会前提使其看起来无比天真,其中关于游牧社会和控制论未来(自动化)的畅想甚至经不起一点深究。在如今职业化程度如此之深的商业社会,《新巴比伦》甚至读起来像一篇没有情节的科幻文学。有趣的是,这恰恰也是它迷人且令后人神往的地方。
建筑师不关心也无法关心他们所设想的社会前提如何实现。作为一个全球性的整体方案,新巴比伦只能实现在如此剧烈的社会变革之后。倘若它只是一块「功利主义社会」(Utilitarian society)中的飞地,那就只能面临被误解和排挤的宿命。欢乐宫一样的例子我们已见过太多。建筑的建成不仅仅关于技术和空间,而是关于资本和雄辩,关于权力与征服。
即便是可动建筑中少数建成的那部分,也几乎从未真正的「移动过」。日本新陈代谢派建筑师黑川纪章1972年建成的中银舱体楼,在设计之初宣称可以移动和组合舱体模块来满足不同需求。可在建成之后,它唯一的一次移动,便是在2022年9月被拆除的那一刻。
正像塞德里克·普莱斯的讣告中写道的那样「这类尝试总会失败,因为我们似乎离不开墙体和纪念碑。但这总是值得的。」
建筑的故事通常在这里结束,但另一个故事才正要开始。完全剥离生产性的嬉戏社会或许不是一个空间,而是一段穿插在现实中的时间。新巴比伦不断变化的互动网络,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游戏」。假若康斯坦特生活在现在,可以交互的虚拟模型一定会是新巴比伦最优先选的表达手段。至少在那里,新巴比伦不是他一个人的创作,而是所有人参与其中的动态模型。所有人能(部分的)「自由地支配其整个的生命……自由地将他所期望的形式赋予其自身的存在」。
又或许,这是嵌套在虚拟的现实中的另一层乌托邦。这无所谓。乌托邦是烟花,一场场的燃烧与绽放,让低头的人望向天空,这就是创造的意义。
大目妖(樊昌林)
校按
校按
就正如作者康斯坦特·纽文惠斯所言,「新巴比伦」这样建筑/城市规划的「思想实验」是基于对人的创造性本能的发展而构想出来的建筑/生活/空间/创造的模式。
他这种构想的基石,实际上就是一种「耗费」与「游戏」的思想,而这也来源于开头他所提及的赫伊津哈的经典作品《游戏的人》,可以把整个巴比伦的方案看作是一种从「游戏的人」的思考在建筑与城市规划构想中的实现。(虽然他显然无视了诸如马塞尔·莫斯等人的对古代原始社会的考察,武断地认为功利主义的社会贯穿了人类历史的始终)。
这种乌托邦的幻想与耗费的推理法与游戏哲学中著名的伯尔纳·舒茨(Bernard Suits)在《蚱蜢:游戏、生命与乌托邦》(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and Utopia)中的假设类同,即同样假设人类的所有的生产性的,必须性的诉求都可以被机器和自动化所满足,那么剩余的就只有游戏:
想象一个衣食无忧、心灵满足的乌托邦世界,活在其中的人类早已心想事成,无事可做,剩下唯一能做的事,就只有玩游戏,玩游戏将变成人类存在理想的全部。
在这个意义上,在康斯坦特看来精力对应的最佳发展生命所需要对应的是一种游牧的,创造的空间模式,人类可以在这种对空间的自由创造中升华自身的原始本能。即文章所说的「作为心理维度的空间(抽象空间)无法与行动的空间(有形空间)分离」,而「抽象与有形空间」之间的龃龉也就是成了规训、强制、压抑之所,那么也只有在一种适合创造且鼓励创造的空间中,人们才会倾向于打破常规,构成一种人所生活的空间与其创造性的心理维度的契合。
这篇文章中所强调的「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的 Ludic 我更经常是翻译为「游玩的」,但这个词语在赫伊津哈和游戏研究中隐含着一种规则性,在今天也有被游戏设计师 Eric Zimmerman 用来描述指代时代,展望一个「游玩的世纪」(Ludic Century 见「游玩」世纪宣言),加洛韦那里则用作一种批判性的视角描述这个「游玩的资本主义时代(ludic capitalism)」,但其中的自由,和反生产的内涵近乎消失,所以我更希望保留原译者原先翻译的「嬉戏」的意涵,其中不是某种疯狂,而是有某种倦怠与孩童般的创造:
每天傍晚,在西班牙的利纳雷斯,我都观察那些幼小的孩童,他们逐渐变得疲乏:不再有贪欲,手中不再抓取任何东西,而只剩下游戏。(彼得·汉德克《试论疲倦》)
但从现在看来,这篇文章当然充满着乌托邦之感,历史并没有走向他指明的方向。但是反倒能在互联网的实践中似乎形成了某种对应关系。康斯坦特的研究者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认为新巴比伦的连接性预示着互联网及其「新的社会生活模式」,而今天也能看到有些人试图在所谓的「元宇宙」中再次尝试使用这番概念去畅想一个虚拟世界版本的「新巴比伦」。
确实,游戏设计作为「隐形的建筑学」可与此对应构想,而本文中谈论的各种氛围变化以及乐高积木式的空间组合似乎都颇符合沙盒化的多人游戏,这些对多人场景交往与创造力的想法实验也似乎完全可以在电子游戏的情景中得到验证,甚至成为今天的多人游戏设计思考的一种新视角。但这是否有可能达及他所说的「对空间的创造和演练与社会关系的创造一体,并且与自我生命的创造所相连接」的程度,依旧需要存疑而有待验证。
康斯坦特曾经说过「创造与革命式的斗争都有同一个目的:生命的实现。」(Creation and revolutionary struggle have the same objective: the realization of life.)
但这就像是一篇文章中所提到的:
直到20世纪70年代初,Constant才意识到他的计划不会实现。这不是因为新巴比伦本身的矛盾,而是因为人类没有认真看待20世纪60年代的可能性,他们不想改变他们的生活,不想追求乌托邦。社会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并没有为玩腾出时间,反而导致了人类能量的过剩,并且往往以侵略性和日益平庸的休闲活动的形式释放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康斯坦特的项目被降级为一个不可能实现的梦想,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人们对乌托邦形式的兴趣普遍消失。
这也是今天我们所遭遇的难题,即便今天人们获得了脱离为生存必需而劳作的「自由」,但人们「创造力」似乎在崩溃,人们的感性经验逐渐贫乏,人们对于如何创造,对于什么是美,什么是有价值,这些都在被更大的景观和规则所遮蔽,就像在游戏中,创造的可能性空间背后的,是那无限生产力(算力)的提供者所构想和设计的规则。
一种真正「嬉戏」的生活方式何以可能呢?「新巴比伦」的乌托邦幻梦仿若是历史中的新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二世所建造的空中花园,这个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一,至今我们仍未找出正确的位置,也无人知晓它是否真正的存在,亦或者未来能否有存在的可能。
叶梓涛
落日间
Constant Nieuwenhuys
Constant Nieuwenhuys
康斯坦特·纽文惠斯
荷兰艺术家
1920年7月21日-2005年8月1日
1920年7月21日出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1934年-41年就读于荷兰国家美术学院,接受了良好的艺术和工艺美术教育。早期创作受立体主义影响很深,创作形式以绘画、雕塑为主。1948年,与Corneille、Karel Appel 和 Jan Nieuwenhuys 在荷兰创立了「反射」实验艺术小组(Reflex Experimentele Groep)。他们认为,创作过程比作品本身更重要,它丰富精神的手段。康斯坦特对流浪生活的偏好在这一时期就显现出来。该小组随后演变为眼镜蛇 CoBrA 艺术小组,宣称反对资产阶级的艺术美学。
1952年,CoBrA 小组解散后,康斯坦特开始对空间、建筑和三维创作产生兴趣。1956年,康斯坦特加入情境主义国际运动(SI),和居伊·德波共同提出了统一城市主义(unitary urbanism)。1960年因与德波的理念分歧退出情境主义国际。一直到1974年,康斯坦特放弃了绘画,将全部精力投入在新巴比伦项目之中。
晚年的康斯坦特在创作形式上重返绘画,创作主体却越来越受到当代政治议题的启发。
2005年8月1日去世。
关于其人的更多资料作品可以参考网站 stichtingconstant.nl,在这篇文章 The Utopian Failure of Constant’s New Babylon 中有更多关于康斯坦特在其不同阶段对新巴比伦项目的可实现性/乌托邦的思考。更多可以参考 Mark Wigley 所编写的 Constant's New Babylon: The Hyper-architecture of Desire。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一个游牧的城镇 A nomadic town
一个游牧的城镇 A nomadic town
康斯坦特·纽文黑斯为由 Haags Gemeetenmuseum 所发布的展览目录所写,The Hague, 1974。
一个没有边界、没有武器的自由世界,我们是这里的鲜活象征。这里每个人都可以不受阻碍地旅行,从中亚的大草原到大西洋海岸,从南非的高原到芬兰的森林。 ——世界吉普赛人社区主席瓦伊达·沃伊沃德三世(Vaida Voivod III,引自1963年5月18日阿姆斯特丹Algemeen Handelsblad 发表的一篇采访。)
许多年来,在阿尔巴的皮埃蒙特小镇逗留的吉普赛人都有在他人屋檐下露营的习惯。每周六,屋檐下都会组织牲畜市场。他们在那里生火,把帐篷挂在柱子上以保护或分隔自己,借助商人留下的箱子和木板临时搭建住所。每次吉普赛人经过后,市场都需要清理,因此镇议会禁止他们进入。作为补偿,他们分配到了塔马罗河(Tamaro)岸边的一块草地,小河穿镇而过:那里是最悲惨的地方!
1956年12月,我在画家朱塞佩·皮诺特·加里齐奥(Guiseppe Pinot Gallizio,译注:意大利画家,场景工业绘画的创始者和情景主义国际的创始成员)的陪同下到那里去拜访这些吉普赛人。加里奇奥是这片不平整、泥泞而荒凉土地的主人,是他将这里赠予他们。他们用木板和汽油罐封堵住大篷车之间的空间,做了一个围墙,一个「吉普赛镇」(Gypsy Town)。
就在那天,我构思了一个为阿尔巴的吉普赛人建造永久营地的计划,该计划是新巴比伦系列模型的起源。这是一个新巴比伦(New Babylon),一个在栖身处可借助可移动元素而建立的共同居所;一个临时的、不断改造的生活区;一个行星尺度的游牧民营地。
定义 Definitions
定义 Definitions
功利主义社会 Utilitarian society
功利主义社会 Utilitarian society
这个术语指向所有已知的社会形式,包括现代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它声称一个基本的现实;所有形式的社区生活无论新旧,都是相同的,即对人的工作能力的剥削。「效用性」(Utility)是评价人类及其活动的主要标准。创造性的人,游戏的人(Homo Ludens),只能在极少数情况下能要求自己的权利。
功利社会的反面是嬉戏社会(ludic society),在那里,人类借助自动化从生产性的劳动中解放出来,这起码可以发展他的创造力。「阶级社会」或「无阶级社会」这两个词无法表达,或未能完全表达这种冲突。但很明显,一个嬉戏社会只能是一个无阶级的社会。社会公平并不能保证自由或创造力(即自由的实现)。自由不仅取决于社会结构,而且还取决于生产力;而生产力的提高则取决于技术。在这个意义上,「嬉戏社会」是一个新概念。
游戏的人 Homo Ludens
游戏的人 Homo Ludens
约翰·赫伊津哈(Johann Huizinga)在一本名为《游戏的人》(Homos Ludens)的书中首次使用了这个词,该书的副标题是「文化中的游戏元素研究」(A Study of the Element of Play in Culture)。在前言中,赫伊津哈用仔细斟酌的术语来称谓游戏的人:「在时间的进程中,尤其是十八世纪带着它对理性的尊崇及其天真的乐观主义来思考我们之后,我们逐渐意识到我们并不是那么有理性的;因此现代时尚倾向于把我们这个人种称为Homo Faber,即制造的人。
尽管 faber(制造)并不像 sapiens(有智力的)那么可疑,但作为人类的一个特别命名,总是不那么确切,因为看起来许多动物也是制造者。无论如何,另有第三个功能对人类及动物生活都很切合,并与理性、制造同样重要,即游戏(playing)。依我看来,紧接着 Homo Faber,以及大致处于同一水平的 Homo Sapiens 之后,Home Ludens,即游戏的人,在我们的用语里会据有一席之地。」(译注:此处引文采用1996年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版本中的译文)
对该术语的谨慎使用也许可以从功利主义社会对玩(play)的轻视来解释。 游戏的人(Homo Ludens)只是智人(Homo Sapiens)的一种罕见表现形式,与制造的人(Homo Faber)不同,前者基本上未被注意到。对赫伊津哈来说,玩(playing)是对「真实」生活的逃避,这种解释没能和功利主义社会的规范拉开距离。而且,在对该主题的历史分析中,他自然而然地将「游戏的人」与社会的上等阶层联系起来,更确切地说是有产的休闲阶层,而非劳动的大众。然而,通过工作(work)和生产能力(production)的分离,自动化技术为游戏的人的大量增加铺平了道路。 尽管如此,赫伊津哈的价值在于他指明了我们每个人体内沉睡的「游戏的人」。人的嬉戏潜力的解放与他作为社会存在的解放息息相关。
社会空间 Social space
社会空间 Social space
社会学家将这一概念扩展到社会关系和纽带的集合,它们定义了人在社会中的行动自由,以及更重要的,其限制。我们不赞同这种对空间的符号化解释。对我们来说,社会空间确实是集会、人与人的联结的有形空间(concrete space)。空间性(Spatiality)就是社会。
在新巴比伦,社会空间就是社会空间性。作为心理维度的空间(抽象空间)无法与行动的空间(有形空间)分离。只有在一个社会关系被抑制的功利主义社会中,两者的分离才是合理的,而处于其中的有形空间必然具有反社会的特征。
新巴比伦:一种文化的草图 New Babylon: Outline of a culture
新巴比伦:一种文化的草图 New Babylon: Outline of a culture
社会模型 The social model
社会模型 The social model
有一个令人不安的基本问题:在一个没有饥荒、剥削和工作,而且任何人都可以毫无限制地自由发挥其创造力的社会中,人将如何生活?该问题在我们心中唤起了一个形象,它与迄今为止已知的在建筑或城市化领域实现的任何环境都完全不同。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先例可供借鉴,因为大众从未自由过,确切的说,自由地创造过。至于创造力,除了人类的产出之外,它还意味着什么?
现在,让我们假设所有的非生产性工作都可以完全自动化;生产力提高到直至世界不再有短缺;土地和生产资料社会化以及随之来的全球化生产合理化;结果是,少数人不再对多数人行使权力;换言之,让我们假设马克思主义的自由王国可以实现。假若如此,我们在问出同样的问题时就无法不想立刻尝试回答它,并同时设想(尽管是以最简单化的方式)一种社会模式。在此模式中,自由的理念将成为自由的真正实践——那是这样一种「自由」:对我们来说不是在许多选项中做选择,而是每个人的创造能力都能得到最佳发展;因为没有创造力,就没有真正的自由。
如果我们将所有已知的社会形式都置于一个单一的共同标准——「功利主义」之下,那么将被创造的模式则是一个「嬉戏」(ludic)社会——这个术语指的是那些摆脱了所有功利和功用的活动,是创造性的想象力的纯粹产物。现在,当人类作为,且只作为一个创造者时,才能实现并达到其最高的存在层面。
想象一个社会,那里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创造自己的生活,根据自己最深切的愿望塑造社会。我们将不再依赖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的形式与想象,那里的人类不得不在永不停息地生存挣扎中牺牲了自己大部分的创造能量。 我们的社会模式将,真正地,且在根本上不同于以往的模式;它也将拥有更优越的品质。
让我们从一些基础开始:
- 所有「有用的」重复性活动的自动化,这将在大众层面释放一种从此可用于其他活动的能量。
- 土地和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以及消费品生产的合理化,促进能量向创造性活动的转化。
- 随着生产性工作的消失,集体性的计时会失去其存在理由;另一方面,群众将有相当多的自由时间。
网络 The network
网络 The network
显然,一个人在其一生中可以自由地使用他的时间,想去哪就去哪。然而在一个被时钟左右、要求固定住所的世界里,他不可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他的自由。「游戏的人」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将首先要求他满足自己对玩、冒险和流动性(mobility)的需要,以及所有有利于自由创造他自己生活的环境。
在这之前,人类的主要活动是对其自然周遭环境的探索。而游戏的人将根据自己的新需要,寻求转变、重新创造这些环境和这个世界。对环境的探索和创造刚好可以同时进行,因为游戏的人在创造其探索的领域时,也会投身于探索他自己的创造。因此,我们将看到一个不间断的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而维持该过程的,是体现于所有活动领域的普遍的创造力。
从这种时间和空间上的自由开始,我们将抵达一种新的城市化类型。流动性,人口的不断波动(这种新自由的逻辑结果)在城镇和聚居地之间创造了一种不同的关系。由于没有时间表和固定居所,人类将必须在一个人工的、完全「被构建」的环境中熟悉一种游牧式的生活方式。让我们把这种环境称为 「新巴比伦」(New Babylon),要补充的是,从传统意义上的「城镇」看来,它(几乎)空无一物。
城镇是功利主义社会特有的城市化形式:是一个保护人们免受外部世界侵害的坚固场所。它作为商业中心,而变成了一个「开放的城镇」;然后随着机械化的到来,变成了一个生产中心——在所有这些不同阶段,它一直有一群稳定的人口以某种特定的生活方式扎根并居住于此。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城镇之间的某些联系使少数人能改变他们的居住地,并引发了一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的过程,在其中,除了功利主义的功能外,城镇还获得了文化中心的功能。但这种现象相对来说并不常见,且涉及的人数也不多。
新巴比伦的文化不是来自于孤立的活动和特殊情况,而是来自于整个世界人口的全球性活动,每个人都在与他周遭环境发生着动态联系。任何人之间都不存在先验的连接。每个人移动的频率和他将跨越的距离都将取决于他自发做出的决定,而他同时也能放弃这些决定。在这些条件下,社会流动呈现出一种万花筒式的整体形象,强调突然的意料外的变化——这种形象不再与,受效用原则所支配,行为模式总是相同的社区生活结构有任何相似之处。在我们的案例中,城市必须对社会流动性作出反应,这意味着与稳定的城镇相比,它在宏观层面上有更严格的组织,同时在微观层面上有更大的灵活性,即一种无限的复杂性(infinite complexity)。在任何情况下,创造的自由都要求我们尽可能少地依赖物质的偶然性。因此,它的前提是一个庞大的集合服务(collective services)的网络,相对于功能城镇的稳定人口,这对流动的人口来说更有必要。另一方面,自动化导致生产大规模集中在巨大的中心,位于日常生活的空间之外。
处在日常生活空间之外的生产中心,以及其内的集合设施决定了宏观结构的总体线条,在不确定运动的影响下,这将定义一个有更多区分度、且必然更加灵活的微观结构。
物质条件的最优化的组织,以及每个人主动意识的最大发展,从这两个先决条件我们可以推导出一个结构的基本要素,这个结构不再像传统的居住区那样由核心组成,而是根据个人和集体的跨越的距离和自由度来组织的:一个单元的网络(a network of units),彼此相连,并因此形成可以向各个方向发展和延伸的链条。在这些链条中可以找到与社会生活组织有关的服务和一切,在网络的「链接」(links)里,是完全自动化的无人生产单元。
该网络的基本元素,即「区段」(SECTOR),是有自主性的建造单元,但也相互连通。区段网络从内部被视为一个连续的空间。
新巴比伦没有尽头(因为地球是圆的);没有边界(因为不再有国家经济)或集体(因为人们是波动不定的)的概念。每一处场所都能为所有人所用。整个地球成为了其拥有者的家。生命是一场穿越世界的无尽旅程,这个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似乎永远都是焕然一新的。
实现 Realization
实现 Realization
只有当经济在最广泛的意义上完全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为目标时,新巴比伦的建设才能开始。只有这样的经济才允许非创造性活动的完全自动化,从而使创造性得到自由发展。
新巴比伦的实施是一个区段化世界缓慢增长过程,并逐渐取代了原有的城市结构。起初会看到,在聚合体中独立区段的出现将成为人们的吸引点,以至于随着工作时间的减少,定居点将瓦解。在这一时期,这些区段是聚会的场所,是某种社会文化中心;之后,随着它们数量的增长,彼此间的链接也会增加,区段内的活动变得专门化,而且与住宅区相比越来越具有自主性。
随后,一种新巴比伦式的生活方式开始被定义,它开始于重组的区段形成一个网络之时,该网络是一个能与定居点结构竞争的结构,定居点的重要性将随着人不再参与生产过程而逐渐降低。同样的现象会出现在许多地方,人们会看到许多区段形成组团,结合为一个整体。从那时起,波动(fluctuation)将会增加。
在第一阶段,各区段和区段组团之间的距离要求更快速的移动方式。穿越住宅区,从一个区段到另一个区段的时间必须尽量缩短。随后,当区段世界成为一体且波动加剧时,就不再需要通过快速移动来变换周遭环境了。区段内部空间的灵活性允许在相对有限的平面上实现环境和氛围的多种变化。至于运输工具,将不再是移动所必需。它们的原有功能将扩张,而随之出现了一种新功能:从工作的用具,变成了游玩的工具。
地形学 Topography
地形学 Topography
鉴于区段网络中社会空间的规模及其连续性,新巴比伦人的生活方式与快速移动的空间不再相吻合。新巴比伦的生活方式是通过缓慢而持续的流动(flux)实现的,迁移只是区段内活动的形式之一。但毫无疑问,人们仍然会不时地寻求快速移动,通过陆路短途或飞行。
关于空中运输,人们可以想象露台屋顶上的飞机跑道和直升机停机坪。至于地面上的快速交通,我们必须设想一个尽可能独立于区段网络的道路网络。一种多层次布局将保证网络和干道通路的自主性。缓解地面堵塞的最佳方案是将各区段底层架空,并尽可能地拉开间距。这种结构的一个优点是能够布置一个不间断的平台屋顶。通过这种方式,创造了第二层的户外,在自然景观之上的第二重的人造景观。
鉴于其巨大的规模,区段内部要依靠照明、通风和空调所需的能源分配系统,但这种「依赖性」意味着某种自由:摆脱单调的昼夜更替,而这是人类自古以来便追求的自由。
从整体上看,新巴比伦将呈现为一个巨大链接的网络,大部分抬升到空中。而在地面上,有第二层网络——交通。「链接」是通常没有建筑物的区域,但其中仍会有生产中心和无法放置在区段社会空间中的设施,例如,发射机天线,也许还有钻井平台、历史纪念碑、天文台和其他科研设施。这些空地(链接)的一部分被用于地面自身的不同工作和牲畜饲养;另一部分用于自然保护区和森林公园。网络结构为进入这些地区提供便利,每次间隔的距离都相对较小。
新巴比伦的地形测量所带来的问题无法通过传统的制图学方法来解决的。一方面,由于其组织处于不同高度(地面、区段内部、露台屋顶),因此相互之间的连接、联通特性和连续性的解决方案只能以模型的形式出现。另一方面,这些结构并不是永久性的。实际上,它更像是一个不断变化的微观结构,其中时间因素,即第四维度,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任何三维再现,本身只具有快照的价值。即使承认每个区段的模型可以简化为不同水平面的数个平面和剖面,并且设法将其编成一本详细的区段图集,仍然有必要使用类似航海日志中的象征记号,记录从一个瞬间到下一个瞬间产生的所有地形变化。而要解决这样一个复杂问题,无疑需要求助于计算机。
区段 The sector
区段 The sector
区段是最小的元素,是新巴比伦网络的基本单位,是构成网络的链条(chains)中的一个「链接」(links)。正如人们所期望的,它的尺寸明显大于他们所知道的构成城镇的元素(建筑物)的尺寸。这些元素的规模取决于社会关系系统。在人际关系和家庭纽带紧密相连的农村社区,基本要素是独立的家庭住宅。而在工业城市,鉴于生产工作的社会性质,人际关系建立在学校、工作或休闲场所、政治和其他会议之中——这些都是对家庭关系的补充。因此,家庭的每个成员都在其外建立了个人联系。在这些条件下,出现了更大的住宅单元,容纳多个家庭的街区,有时其中还配备了公共服务。但在那里,就像农村社区一样,我们面对的是一种定居的人口,一种固定的生活方式。
当家庭群体解体,时空划分不再由生产性工作来决定时,当一个人可以决定自己的逗留地点和时间,亲密纽带就被打破了。就所有这些而言,虽然人与人之间或多或少的持续关系不会消失,但限制性的社会关系将被更加多样和变化的情感纽带所取代。与稳定的社区相比,波动社会(fluctuating society)更倾向于偶然的接触和相遇。
区段是一个基本的构筑(宏观结构),环境在其中被构建。 作为支撑结构,宏观结构必须保证内部空间的永续建设(微观结构)的最大自由。在其最简单的形式中,区段包括一些叠加的水平空间,通过垂直元素相互连接并与地面,以及一个或多个固定的服务核心相连。这个空间可以被一个更复杂的结构所占据,其由多样的更小空间衔接而成。作为支撑结构的替代方案,我们也可以想象一个「漂浮」(floating)的结构,固定在一个或多个桅杆上的悬挂区段。另一个可能的选择是自承重结构(self-bearing structure),优势在于只需要有限的支撑点,但是,由于微观结构的模块和尺寸更直接取决于宏观结构,所以内部空间的组织也就不再那么自由。选择何种解决方案,是底层架空或悬挂结构或自承重,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地理位置。
那么,宏观结构便容纳了一个可移动的内部结构。由于区段的尺寸很重要,所以任何对基础结构的拆除或改造都必然是一项浩大的工程。然而,新巴比伦居民嬉戏生活的先决条件就是要频繁地改造区段内部。为使改造过程不出现问题,围护(containing)结构必须尽可能地保持中立,而且从构造的角度来看,可变的围护结构将[不得不]完全独立于基础结构。
可变结构从可移动的装配系统(墙、地板、端钮、桥梁等)中生长出来,轻质而易于运输,安装和拆除都同样容易,从而[使它们]可以重复使用。任何装配式项目都需要模块的规范化和生产的标准化。宏观结构的尺寸由标准元素的模块所决定。但这当然不意味着限制可能的组合或简化形式,因为大量的标准装配类型和系统能以多种方式组合。
有了这些数据,就能对区段有一个大致的概念。它的主体是一个延展至10或20公顷水平构架,在距地面约15-20米的上空:总高度在30-60米之间。在内部,单个或多个固定的核心区(nuclei)包含了一个技术中心和一个服务中心,后者同时也是一个配备独立房间的酒店接待中心。一些区段配备了公共卫生和教学设施,以及日常用品的仓储和配送设施。其他区段则配备了图书馆、科学研究中心和其他任何可能需要的设施。核心区占据了区段的一部分;其余部分,即新巴比伦最重要的部分,是一个带有可移动关节(moveable articulations)的社会空间:游戏的人的游乐场。
与较小尺度的建筑相比,具有新巴比伦区段跨度的体量相对于外部世界来说更加独立。例如,日光只能照入几米,室内的大部分都是人工照明。日照热量的积聚和低温天气下热量的散失都会非常缓慢,以至于室外环境气温的变化几乎不影响室内温度。气候条件(照明强度、温度、湿度、通风)都在技术的掌控之中。在室内,可以随意创造和改变各种不同的局部气候。气候成为氛围的游玩中的一个重要元素,更重要的是,由于每个人都可以使用技术设备,而且去中心化(的分配)鼓励区段或区段的组团有一定的自主权。更小型中心组团会比单一的中心更受欢迎,这有利于再现最多样化的气候。为什么不发明新的气候作为对照?改变季节,根据与空间变形(metamorphosis)所一致的无穷变化的同步性来改造它们。
视听媒体的使用也将本着同样的精神。各个区段的波动世界需要既去中心化又公共的设施(发射和接收的网络)。鉴于很多人会参与图像和声音的传输和接收,完善的电信通讯将成为嬉戏社会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
新巴比伦人 The New babylonians
新巴比伦人 The New babylonians
创造性和侵略性 Creativity and aggressivity
创造性和侵略性 Creativity and aggressivity
他们在新巴比伦的各个区段徘徊,寻求新的体验和未知的氛围。他们没有游客的被动性,能充分意识到自己有能力对世界采取行动,去改变它,重新创造它。他们拥有一整套的技术工具可供使用,毫无延迟地做出所需的改变。就像画家仅用几种颜色就能创造出无限的形式、对比和风格一样,新巴比伦人可以通过使用技术工具无尽地更新和改变他们的环境。
这一对比揭示了两种创作方式的根本区别。画家是一个孤独的创造者,只有在创作行为结束后才会面对另一个人的反应。而另一方面,在新巴比伦人中创作行为同时也是一种社会行为:作为对社会世界的直接干预,它引起了一种即时的反应。在别人眼里,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似乎摆脱了所有的约束,并且孤立中成熟。而只有当很久之后,作品获得了不可否认的现实性时,它才不得不面对社会。在新巴比伦人创作活动的任何特定时刻,他都与同侪直接接触。他的每一个行为都是公共性的,每一个行为都作用于一个环境,而该环境也是其他人的环境,并会引起自发的反应。因此所有的行动都失去了其单独的特征。另一方面,每一个反应都能反过来激发其他反应。这样一来,干预就形成了连锁反应,只有当一个已经变得危急的情境「爆炸」并转化为另一种情境时才会结束。这个过程摆脱了单个人的控制,然而知道是谁引发了过程以及谁会反过来影响过程并不重要。在这个意义上,关键时刻(高潮)是一个真正的集体性创造。新巴比伦世界的标尺,它的时空框架,是一种每个刻都接替上一刻的节奏。
从制造的人(Homo Faber)的角度来看,新巴比伦是一个不确定的宇宙,在这个宇宙中,「正常」的人任由各种可能的破坏性力量和侵袭性的摆布。但我们要注意,「正常性」(normality)是一个与某种历史性实践相连的概念;因此其内容是变动的。至于「侵略性」(aggression),心理学给予它相当的重要性,甚至定义了一种进攻的「本能」。研究领域因此发现自己被简化成为了生存而挣扎的人,被卷入这场亘古不变的争斗中,与仍在其中的其他物种一样。
一个不必为自己的生存而斗争的自由人的形象是没有历史依据的。自我防卫的本能也被认为是人类和所有生命的原始本能,而且所有其他的本能都与其相关。
侵略性是权力意志的表现,它是一个高度发展的生命(人)的预见能力。在一个生存受到威胁的世界里,他能够及时组织,即根据计划为自己找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因此人的侵略性不会随着他的即时需求的满足而消失。显然,在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富裕」国家,侵略性行为退化得最少,尤其是在有产阶级中。为了阐明物质安全与侵略性的持续存在之间的明显矛盾,也许有必要承认存在一种除自我防卫之外的「本能」:创造本能(the creative instinct),只要物质条件足以使自卫转化为开放的自发(spontaneity)行为,它就会伴随原始本能的升华而出现。
在功利主义社会中实现创造性的生活,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这种社会的基础就是对创造性的压制,但其中却包含了有利于其发展的所有条件,这能使我们理解生存斗争之外为什么会发现侵略性。在当代社会,有产阶级本身不能以创造性的方式行事,而且很容易明白他们比大众感到更加沮丧,大众一无所有却为自己的未来自由而奋斗。这些奋斗的目标是改造现有社会,冲突(conflict)本身就是创造。
创造本能 The creative instinct
创造本能 The creative instinct
在推测一个嬉戏社会可能的出现时,应从一开始就预设,每个人都感受到了表现出自身创造力的潜在需要,它出现在原发的本能形式的升华中。这种需求在我们一成不变的社会中得不到满足,在这里,通过创造来实现它还只是未实现的。所有为未来的成年人所准备的、使其在社会中扮演「有用」角色的教育,都倾向于压制其创造本能。然而,随着技术的发展,甚至在孩子完成学业之前,「效用性」往往就会消失。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压制了所有自发的创造力,只能发挥消极作用。如果情况并非如此,那成人应该会比儿童更有创造力,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
但是,人们能设想出一种旨在发展创造力的教育吗?我们可以怀疑并自问,所有的教育,或者由这个词所指定的事物,是否都是极其有限的?其主要功能是否不是在限制创造力的基本条件——自由?唯一有利于创造的教育是释放创造力发展的教育。但游戏的人(Homo Ludens)无需教育。他通过玩来学习。
那些不能适应功利主义社会结构的人注定要被孤立。这些人是「反社会」类型的人,这个词通常与「犯罪的」同义。「犯罪性」(Criminality)被预设为对既有社会关系的违反,这便能解释对其对象的不同阐释。犯罪,即「犯罪行为」,扰乱了这些关系的秩序,而社会的反应即是消除罪人。当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时,「犯罪行为」可被视为是一种被阻碍的权力意志表达,需要承认的是,权力意志经过升华可以被转化为创造力,那么「犯罪」不过就是一种失败的创造尝试。罪犯对现实的态度并不比艺术家更被动,因为他也在特定的情况下进行干预。但创作行为把破坏和建造结合并使其平衡,而罪犯却把破坏放在首位。然而,艺术家的干预,至少就功利社会而言,显示了一种「反社会」的态度,其效果与犯罪几乎没有区别。
在新巴比伦,没有「秩序」(order)会受到尊重,社区生活在永续变化的情境中形成。这种动态激活了那些在功利主义中被压制的,或至多被容忍的力量。这就是为什么无法想象像新巴比伦那样的生活可以被强加于当代社会,哪怕只是很短的时间。当社会规范不再受到尊重时,比如在狂欢节期间,增长的不是创造力,而是侵略性:这种侵略性与社会对创造力施加的压力成正比。
在新巴比伦,所有侵略性的理由都被消除了。生活环境有利于升华,活动变成了创造。这种高级的存在形式只有在一个完全自由的世界里才是可能的,在这里人类不再为维持某种生活水平而挣扎,而是把活动聚焦在对自己生活的持续的创造上,将其引向一个更高的水平。
新巴比伦人 The New Babylonian
新巴比伦人 The New Babylonian
争取生存的斗争把人类分为一些利益团体,这些团体往往是相互竞争的,但总是反对联合组成更大团体的想法,因为这很难维持。这种斗争的历史条件可以解释长期以来的种族、部落、民族和社会阶层的分裂。在一个无需为生存而斗争的社会中,个体和团体层面的竞争都会消失。障碍和边界也随之消除。道路将通向人口的混合,这将导致种族差异的消失,人们会融合成一个新的种族,即新巴比伦人的世界性的种族。
新巴比伦人拥有完全的行动自由,但这种自由只有在与所有同侪的互惠关系中才能得到实现。一个以所有人的利益共同体为基础的嬉戏社会中,不会存在功利主义社会所特有的个人或集体冲突。在这种情况下,利益冲突、竞争和剥削的概念将不复存在。新巴比伦社区包括了新巴比伦居民的总体,正是他们的共时性的活动创造了新的集体文化。
即使「制造的人」的行动跨越了很远的距离,他也仍在一个受限于返回固定住所义务的社会空间中移动。他是「被绑在土地上的」。他的社会关系定义了他的社会空间,其中包括他的家、工作地点、家人和朋友的家。而新巴比伦人摆脱了这些强制性的联系。他的社会空间是无限的。因为他不再「扎根」,他可以自由流动:他穿越无休止变换的空间与氛围,不断地更新,而他因此变得更加自由。流动性,以及它所产生的迷失感,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接触。纽带的建立和解除都不会有任何困难,这使社会关系具有完美的开放性。
关于新巴比伦文化的一些要素 On some elements of New Babylonian culture
关于新巴比伦文化的一些要素 On some elements of New Babylonian culture
新巴比伦文化的本质是把玩探索那些构成了环境的各种元素。对所有元素的整体性的技术控制使其成为可能,且将游玩变为对环境有意识的创造。
环境有很多组成部分和种类。为了想象它们的多样性,有必要用两种不同的标准:客观和主观的标准,来将其区分为几组:
- 空间建造的要素,这决定了新巴比伦的外观,是优先规划的对象。它们可以被归入「建筑性要素」的范畴。(例如:空间的形式和尺寸,建筑材料,结构和颜色)。
- 定义空间品质(quality)的要素。由于它们需要更具可塑性,因此不能以同等程度被规划。这些是「气候性条件」(温度、湿度、气氛等)。
- 不决定空间品质但影响空间感知的要素。它们的被即兴使用,效果短暂。这些是「心理学要素」(例如:运动、饮食、使用语言或其他交流方式,等等)。
另一种分类,使用更多的主观标准,根据环境元素对我们的影响来进行分配。在这里可以分辨出视觉、声音、触觉、嗅觉和味觉的元素。
但无论采用什么标准,都很难孤立某个元素,将其与其他元素分开。而大量的重要元素又是许多不同类别的一部分。因而,在根据第一个(客观)标准选择的元素中,空间结构与气候性条件以及空间中的运动有关。无论氛围如何,在每一个空间中进食和饮用所带来的乐趣都是不一样的。
至于第二条(主观)标准,它使我们能够发现更复杂的关联。例如,一个结构可以被视觉和触觉所感知;而语言同样能作用于两者。食物和饮料关于味觉,也与嗅觉、视觉和触觉相联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元素,它们彼此紧密地相互作用。以上的分离式分析只有从技术控制的角度来看才是合理的。当人们在感知一个环境和一种氛围时,不会想象区分构成它的各种元素,就像在看一幅画时不会区分画家使用的不同材料一样。
行为的形式 Forms of behavior
行为的形式 Forms of behavior
众所周知,行为受到环境因素的强烈影响。在精神病学中,对这些因素的操纵被称为「洗脑」(brain-washing)。在新巴比伦,每个人都可以自由使用技术设备,并积极参与空间的集体组织,这些元素无法根据预定目标进行选择。任何倾向于某个方向的倡议,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被不同甚至是对立的倡议所阻挠。
如果新巴比伦人可以通过使用现有的技术材料来改变环境和氛围,如果这样做他可以暂时影响他人的行为,那么他相应地也会受到他人的影响。在任何情况下,他的干预效果都不会持续太久,因为每一次干预作为一种挑衅都不可能没有回应。
或许会有一种异议,即创造力对所有人而言并不相同,最活跃和最有天赋的人会比精力不足和没有创造力的人的影响更强。不过,这种反对意见带有功利主义心态的特征,它认为智力和精力上的优势是获得权力最可靠的手段。而在集体文化中,个体行为与总体的社会活动交织在一起。它不可能是孤立的,其结果无迹可寻。集体文化是一种复合的(composite)文化,是所有创造性活动紧密而有机地相互依存的产物。它是我们所知道的竞争性文化的反面,后者以最强者、以「天才」的绝对优势作为衡量所有活动的单位——其结果是对创造性能量空前的浪费。
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在某个特定的时刻,有X个个体发现自己在其中一个区段。该区段被划分为许多不同规模、形式和气氛的空间。每个空间都正在被改造:被建造、被摧毁、被安装、被拆除…… 所有在场的个体都积极地参与到这种不间断的活动中。每个人都可以自由地从一个空间流动到另一个空间。新人和那些暂作停留后离开的人不断地穿越区段,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这种流动的复杂性,由空间条件和「人口」构成,决定了新巴比伦的文化。
各个区段根据正在发生的活动不断改变形式和氛围。没有人可以回到过去,重新找到他离开时的地方,找到他记忆中保留的形象。现在没有人再会落入习惯的陷阱。
「习惯」的整体构成了一个社会的「行为模式」,在功利主义社会中,它是一种稳定的生活方式的特权:其中有如此多的自动性(automatism)。然而,持续创造的生活动态性(dynamism)则排除了所有自动性。就像艺术家不能也不想重复他的作品一样,创造自己生活的新巴比伦人也不会表现出重复的行为。
动态的迷宫 The dynamic labyrinth
动态的迷宫 The dynamic labyrinth
在功利主义社会中,人们通过各种手段努力实现空间的最优朝向,保证时间效率和经济性,而在新巴比伦中,能够促进冒险、玩和创造性转变的迷失方向(disorientation)则享有特权。新巴比伦的空间具有迷宫式空间的所有特征,在其中,运动不再屈从于特定的空间或时间性组织的限制。新巴比伦社会空间的迷宫形式是社会独立性的直接表现。
环境氛围所具有的特定塑形和声音特征,取决于在那里发现自我的个体。一个单独的个体可以被动地遵从这种氛围,或者根据他当时的心情改变它。但是,随着第二个人的进入,一个新的存在被感受到了,二人的互动便排除了任何被动性(passivity)。环境和其氛围的质量不再仅仅取决于物质性的要素,而是取决于它们被感知、欣赏和使用的,以及被看待的「新方式」。而当第三或第四个人来到这里与其他人一起时,情况由于更加复杂,就不再受在场任何一个人的控制。随着来访者的人数逐渐增加和群体组成的改变,复杂性也随之增加,同时个体对空间的控制减少了。
空间的集体使用带来了质的变化,因为它倾向于减少被动性。一个空间的居有者的活动是氛围的一个组成部分,从静态变为动态。在一个个体数量和他们之间的关系都不断变化的社会空间里,每个人都被鼓励改变他个人的氛围。所有这些脉动汇集在一起,表现为一种明显作用于空间秩序的力量,而在新巴比伦的公共空间持续地发挥作用。整个空间将遵照于最出乎意料的影响,我们可以想象,一种类似的过程同时以无限多样的方式在众多空间中同时展开,其数量和它们之间的联系一样多变。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巨大的社会空间图景,它永远都在变成另一个:这是一个最广泛意义上的动态迷宫。
技术 Technology
技术 Technology
技术是实现实验性集体主义必不可少的工具。没有技术帮助而寻求主宰自然纯属空谈。没有合适的交流手段的集体创造也是如此。一种更新的、重新发明的视听媒体是不可缺少的辅助工具。在一个没有固定基础的波动的社区中,只有通过密集的电信通讯才能保持联系。每个区段都将提供最新的设备,每个人都可以使用,要注意的是,这种使用从来不是严格符合功能性的。在新巴比伦中,空调不像在功利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为了重新创造一个「理想」的气候,而是为了尽可能地改变环境。至于电信通讯,它不仅仅,或并不主要为实用的利益服务。它是为嬉戏活动服务的,它是玩的一种形式。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们举一个本地咖啡馆的例子,在一个非常安静的咖啡馆,当一些新来的人把钱放进点唱机时,气氛会突然变得活跃起来。在新巴比伦,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通过调整声音的大小、灯光的亮度、嗅觉氛围或温度来改变气氛。如果一小群人进入一个空间,那么这个空间的秩序就会换种模样。通过将许多小空间相衔接,人们可以创造出一个宽敞的空间,亦或相反。人们还可以通过新增入口或封锁旧入口;增加或取消楼梯、桥梁、梯子、坡道等改变空间的形式。只需花最少的工夫,就可以完成任何想要的改动。此外,人们手头有各种不同材料、质地和颜色的隔板;它们的热工-声学性质也各不相同。楼梯、桥梁和管道本身具有不同的结构和形式。通过组合几乎不可行的不规则表面、光滑的坡道、狭窄的通道、锐角等,某些空间变得是精挑细选的。那些需要通过绳梯或爬杆到达的空间便是如此,它们将是儿童和年轻人最喜欢的地方。而边缘区段,即栖息在山边或海岸线上的区段,鉴于其少有访客的位置,将是退休人员或病人的首选。
从建造和技术设施的角度来看,这些区段必须尽可能地独立。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任何一个区段都必须能够在重建时不破坏通过移动桥与之相连的邻近区段。当然,为各区段供电的大型发电站或核电站的选址要尽可能远离网络。
空间的集约化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pace
空间的集约化 The intensification of space
在新巴比伦,空间的性质和结构经常变化,人们将更密集地使用全球空间。社会空间的体量和空间中的社会活动的数量会带来两个结果:可供个体使用的空间远大于定居人口的社会;然而却不再有空置的空间,即使是短暂不使用的空间也不复存在。而且,当人们创造性地使用空间时,它的各个方面变化如此之多之频繁,以至于一个相对小的平面就能提供和环游世界一样多的变化。跨越的距离、速度,不再是运动的标准;而空间以更加集约的方式被居住,似乎在扩张膨胀。但是,这种空间的集约化只有在创造性地使用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才有可能实现——而这种使用方式是我们这些生活在「用有尽途」(use has a finality)的社会中的人所难以想象的。
在生活中取得成功,即是不断地创造和再创造。人只有自己创造,才能有一个配得上其自己的生活。当为生存而进行的斗争成为一种遥远的记忆,人类将能够首次在历史上自由地支配其整个的生命。他将能够完全自由地,将他所期望的形式赋予其自身的存在。在一个他愿意使自己,或好或坏地,适应外部环境的世界中,人绝不会保持被动。他将渴望创造另一个能实现其自由的世界。为了使他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他义不容辞地创造那个世界。而这种创造,就像其他的创造一样,意味着同样再创造不间断的更迭。
新巴比伦是新巴比伦人自己的作品,是他们文化的产物。对我们来说,它只是一个反思和游玩的模型。
非常感谢老合作者大木爻的合作翻译,他本身就是建筑学相关的背景,除了此片外,先前他也有关于欢乐宫 Fun Palace 的分享与研究,欢迎关注他 欢乐宫 Fun Palace:未竟的赛博建筑,一个关于改善低生活的社会装置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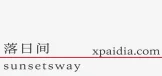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