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为什么当代最重要的影像作者之一的法罗基,在他去世前最后留下的影像却是一部对电子游戏影像的风格记录与考察?
作为法罗基相关论文集《Harun Farocki: Working on the Sight-Lines》的编者以及电影研究的重要人物,Thomas Elsaesser 的这篇文章意图似乎在于为法罗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部作品《平行 I-IV》(Parallel I-IV)进行某种意义上的定位与「正名」,以避免人们对其简单化地理解。
他尝试将《平行》与法罗基过往的作品全体(body of work)建立连接,而不仅停留在一部「电子游戏从抽象到写实的风格变化」的记录片。就像文中所说,也如法罗基一如既往擅长做的,这部独特的作品实际上贯通着一种对影像媒介的考古:「《平行》所描绘出一个平行,是早期电影和早期的电脑动画之间的平行,是在电影的起源和所谓电影之死之间的平行」。
这也使得本文的叙述,读起来对法罗基过往创作的大回顾:从法罗基对弗卢塞尔「操作性图像」的引入,从涉及监控与军事影像的《世界的图像和战争的铭文》和《我以为我看见的是罪犯》,从模拟和角色扮演在生活中怪异感的《Leben BRD》,再到计算机动画中对模拟的模拟(再一次的模仿),以及其中的不可见性的劳动,以及劳动的不可见性(《深度游戏》,《严肃游戏》)。
而我也在过程中看完了我能找得到的法罗基的影像作品,并且意识到法罗基无论是在影像创作还是在创造性的职业生涯中,是一个深刻且不断思索的图像研究者:我们如何通过图像创造价值,图像又是如何影响我们的价值观。(见 Harun Farocki Institut 驻地艺术家李起万(Kevin B. Lee) 的驻地回顾视频)
在这个意义上,就像是 Thomas Elsaesser 将《平行》看作是法罗基在思考图像中的未竟工作的一部分,因其突然的离世而中断,而作者自己在19年的离世某种意义上也再度中断了这一进程,那么今天我们应当如何接续这种从电影至操作性图像,再至计算机、模拟图像,后期制作和电子游戏,及电影的「游戏化」影响下的电影本体论,乃至生活现实与劳动变化的思考?
搜寻资料时,我找到了一段法罗基和弗卢瑟尔,两人的一同抽烟相谈,分析着当天的报纸上的图像哲学的对话视频,这种不断投注于当下的思考是我们所亟待进行的,而或许也是法罗基连续不断的,触及时代变化与脉络的思索和创作所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与鼓励。
叶梓涛
落日间
校按
校按
Thomas Elsaesser在 2014年 接受e-flux的采访时谈及他和 Farocki 的第一次相遇是1956年,当时他还是分发报纸的报童,「我一定分发了刊登法罗基文章的那一期。那么,我可以自豪地说,近六十年来,我一直在帮助传播法罗基的作品」。
这篇评论是 Thomas Elsaesser 为法罗基的作品 Parallel I-IV 所写,不仅总结概括了法罗基的理论语境和创作风格,还将 Parallel I-IV 视为一部未完成的作品,在设想作品的可能性时结合法罗基早年的创作倾向,回到了「劳动」与「可见」组成的创作坐标。
文章先是从电影史的角度出发,用巴赞认为电影有「相信影像」和「相信真实」两类的划分作为引子,指出法罗基就是那类对图像抱有的创作者。事实上,法罗基的确曾经在一次采访中提到「图像」是他的创作核心,其灵感来自萨特的自传式作品《文字生涯》。正如萨特用「文字」而非「文学」一样,法罗基选择「图像」是为了能够把图像拆开以揭示它们内在的元素。而 Thomas Elsaesser 将法罗基定位为相信图像的创作者则是为了让法罗基从电影史的脉络转入媒介史的世界——图像如何作为将逻辑与想象力相结合的思想装置。
值得一提的是,Thomas Elsaesser 作为媒介考古学在电影研究方面的代表,在这段分析里指出法罗基绘制的平行线其实是早期电影和早期计算机动画的平行,为法罗基作品里那句「在电影中,有吹来的风,也有由风力机产生的风。计算机影像则没有两种风」 补上了电影史语境: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众所周知的轶事,即卢米埃尔电影的最早的观众更惊讶于树叶的移动、卷曲的烟雾、漂移的云朵或撞向海岸的海浪,而非人或马的运动,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瞥见,《平行》所描绘出一个平行,是早期电影和早期的电脑动画之间的平行,是在电影的起源和所谓电影之死之间的平行
Thomas Elsaesser 以自己对 Farocki 未竟事业的假设作为结尾:「一种后期制作成为默认值的生产模式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过程(procedure):它改变了电影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本体论)」。可惜的是,虽然 Thomas Elsaesser提到《平行》里早期电影史和动画史的交集,但却没有谈到法罗基创作里非常重要,同时也是在《平行》里反复出现的「运动图像」。
此前我们曾翻译过拉图尔的视觉化与认知,可以作为此文背景,从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几何光学到 19 世纪的生理光学再到如今虚拟成像对现实的捕捉,图像已经不再只是描绘或再现,更是跟踪、导航、激活、监督、控制、可视化、检测和识别。法罗基的操作图像为电影史研究或者视觉研究引入的不仅是媒介考古学对或然历史及其可能的阐述,还增加了政治维度。可见性本身就是政治的,在可见缺席的地方就会有叙事的构建。我们今天面临什么叙事,又需要什么叙事呢?
徐露
Thomas Elsaesser
Thomas Elsaesser
托马斯·埃尔赛尔(Thomas Elsaesser)是德国电影史学家、电影理论家,电影研究奠基人。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与文化系的名誉教授,自2013年起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他撰写、编辑和共同编辑了大约20本关于早期电影、电影理论、欧洲电影、好莱坞、新媒体和装置艺术的书。有著作《German Cinema – Terror and Trauma: Cultural Memory Since 1945》 (Routledge, 2013)。(与 Malte Hagener 的)《Film Theory: An Introduction through the Senses》(第二版,Routledge,2015年)和《Film History as Media Archaeology: Tracking Digital Cinema》(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16)。他是《Harun Farocki: Working on the Sight-Lines》(阿姆斯特丹大学出版社,2005)的编辑。2019年12月应邀在北京做学术讲座,4日在旅馆突发急病逝世,享年76岁。
原文链接:点击跳转
翻译:叶梓涛
校对:徐露
译注:本文中 images 统一翻译作图像,主要考虑到其思考超过出了对电影的讨论,涉及到诸如 Flusser,早期的图形测绘等,但大部分的也可以作「影像」,本译文在此并无特殊倾向。
标记之外的图片都为译者所添加。
Simulation and the Labour of Invisibility: Harun Farocki’s Life Manuals
Simulation and the Labour of Invisibility: Harun Farocki’s Life Manuals
Thomas Elsaesser
摘要 Abstract
摘要 Abstract
这篇文章的重点是法罗基的四段落式影片系列《平行I-IV》(Parallel I–IV),它探讨了计算机动画的图像类型。在《平行I-IV》中,法罗基追溯了视频游戏图形的发展,从1980年代早期的粗糙的二维图像到当代游戏的超写实(hyper-realistic)的环境,如《侠盗猎车手》。文章将这部电影系列与法罗基更广泛的作品和主题兴趣联系起来,同时也考虑了《平行 I-IV》是如何对电影史进行一种媒体考古学式的重估。本文讨论了五个相互关联的主题:再现与复制;操作性图像;监视和军事;模拟和角色扮演;以及不可见性的劳动和劳动的不可见性。
关键词 Keywords
- computer animation 计算机动画
- film theory 电影理论
- Harun Farocki 哈伦·法罗基
- labour 劳动
- military imaging 军事成像
- simulation 模拟
- surveillance 监视
- video-games 视频游戏
天真的现实主义者 Naïve realists
天真的现实主义者 Naïve realists
安德烈·巴赞(André Bazin, 1999: 43)在他的「电影语言的演变」中,将电影世界分为「对图像有信念(faith)的电影人和对现实有信念的电影人」。虽然这种区分常常被解释为反蒙太奇和反爱森斯坦,但二者的区别在巴赞的体系中,并不完全偏向长镜头/深焦(或雷诺阿-罗塞里尼 Renoir–Rossellini)美学,对于1970年代的激进的建构主义者而言,巴赞被习惯性地斥为「天真的现实主义者」那样。[1]
同样,哈伦-法罗基的《平行I-IV》也有一种欺骗性的天真(deceptive naivety),我们应毫不犹豫地直面它,以便看看它在关于今天图像的性质,以及数字时代照相写实主义(photographic realism)的本体论地位,还能告诉我们什么。
就巴赞的区分而言,法罗基和他的导师让·吕克·戈达尔(Jean Luc Godard)一样,把蒙太奇作为他的「美丽的挂念」(Montage Mon Beau Souci, Godard, 1965: 30–31),因此属于对图像有信念的导演,但他的其他导师:让·玛丽·斯特劳布(Jean Marie Straub)和达尼埃勒·惠勒特(Danièle Huillet),则很可能是对现实有信念的导演的象征,或者至少,是对电影镜头前的(pro-filmic)现实的信念。然而,两者结合在一起的地方是,「对图像的信念」很可能是在「对图像的不信」之后,而非之前,而「对现实的信念」很可能是基于一种深刻的认识,即「你所看到的并不是在那存在的」(what you see is not what there is)。
因此,让我正视《平行I-IV》中似乎很天真的地方。乍一看,它似乎是一部非常缩略的计算机图形史,带领我们经历着「进化」,从水平和垂直的严格网格上的树木和灌树丛的线条图,到越来越写实的风景和人物、树叶和水的涟漪、运动和移动的渲染(见图1与图2)。换句话说,它似乎是一个奇怪的线性和目的论的「从……到……」的叙事,仿佛它服从于臭名昭著的,关于越来越大的现实主义的电影历史目的论,而甚至巴赞对此提出了质疑,他在读了乔治·萨杜尔(Georges Sadoul)的作品后感叹道:「电影还没有被发明出来!」
尽管人们很快就意识到,法罗基对水、土地和空气等元素的引用为自己设定了「回到最基础」(going back to basics)的任务,但我确实发现自己很困惑,尤其是考虑到油管上数以百计的视频,即工业光魔、皮克斯工作室、The Mill 或 Rhythm & Hue 等特效公司的展示片。[2] 他们中的大多数都试图解释 CGI(电脑生成图像 Computer-generated imagery)图形,带领我们通过层层叠叠建立起逼真的图像,详细介绍动作捕捉和表演捕捉之间的区别,或者让我们惊叹于为了让《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中的全数字化老虎看起来像活的孟加拉虎,必须对数百万根数字毛发进行编程。
诚然,《平行I-IV》并不是一个为了促进生意的的公关活动,它的目的是对不同风格的图形进行艺术史的沉思。它甚至可以说是支持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1995)的论点,即照片式写实图形(photo-graphic)只是图形渲染世界的几种(历史上偶然的)可能性中的一种,在抽象(abstraction 语言的、数学的、图示的)和具象(图标的、指示的、模仿的)之间摇摆不定。
尽管如此,《平行》看起来像是奇怪的老式作品,不仅因为法罗基使用的大部分材料可以追溯到电脑游戏的早期,并依赖于粗糙动画的过时魅力,而且还因为《平行》避免了将其游戏的社会或政治背景化的做法,就像法罗基的早期系列作品《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既令人不安又充满诗意地所做的那样。最后,在化身们互相绕圈、互相碰撞或互相拔枪的长段与富有哲理的画外音评论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脱节。就像其他几位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有句话尤其打动我:「在电影中,有吹来的风,也有由风力机产生的风。计算机影像则没有两种风」 [3]。
如果我们再加上一个众所周知的轶事,即卢米埃尔电影的最早的观众更惊讶于树叶的移动、卷曲的烟雾、漂移的云朵或撞向海岸的海浪,而非人或马的运动,那么我们已经可以瞥见,《平行》所描绘出一个平行,是早期电影和早期的电脑动画之间的平行,是在电影的起源和所谓电影之死之间的平行。这一点在下文还会再次谈到。
以下是法罗基自己对作品的描述,当时《平行I-IV》作为装置作品在纽约的格林·纳夫塔利(Greene Naftali)画廊展出,然后在巴黎的萨达乌斯·罗帕克画廊(Thaddaeus Ropac Gallery)展出:
《平行 I》开创了计算机图形的风格史。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批游戏仅由水平和垂直线组成。这种抽象被视为一种失败,而今天的表现形式则以照片写实主义为导向。
《平行 II》和《平行 III》(见图3)找寻游戏世界的边界和物的本质。结果发现,许多游戏世界采取的形式是漂浮在宇宙中的圆盘,让人联想到前希腊化时期的世界概念。这些世界有一个前缘(apron)和布景(backdrop),就像剧院的舞台,而这些游戏中的事物没有真实存在。它们的每一个属性(properties)都必须被单独构建并为它们指定。
《平行 IV》探讨了游戏中的主人公,不同的玩家作为主人公穿越在1940年代的洛杉矶、后启示录、西部背景或其他类型的世界中。这些主人公没有父母或老师;他们必须主动找到要遵循的规则。他们几乎没有一个以上的面部表情,只有很少的性格特征,他们用一些不同的、几乎可互换的短句来表达自己。他们是人造人,是拟人化的生命。扮演他们的人都有份于创造者的骄傲。[4]
Anselm Franke (2012) 给了《平行I-IV》一些非常有用的背景:今天,模仿(mimesis)已经成为一个生成算法的问题,由此产生的技术越来越能够计算、预测和控制复杂的过程,从制造业、到战争,再到大众娱乐动画世界的情感体验。法罗基对当前图像技术的创新前沿的调查基础是这样一个假设: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技术化生产的图像世界中,其中的图像已经成为他所说的「理念-典型」(ideal-typical)。在数字「现实主义」的新的模仿性的范式中,现实不再是衡量总是不完美的图像的标准;相反,虚拟图像日益成为衡量总是不完美的现实(always-imperfect actuality)的标准。
与其扩展 Franke 的评论,我想走一条有点不同的路线,首先,《平行》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其中奇怪而神秘的效果,这种印象挥之不去,甚至不断加剧。引用法罗基曾对我说的话(我认为其只有一半是玩笑),以他典型的随意而自嘲的方式:「在艺术界工作的好处是,当你拍了一部你还没有完全完成的电影时,你总是可以把它切成几段,然后把它们作为一个视频装置安装在画廊里。」我并不是说他是以这种方式来考虑《平行》的,但它在某种程度上确实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是正在进行中的研究的一部分,并可能因为他在2014年7月的英年早逝而中断。[5]
本着这种进行中的工作的精神,我将提供一些不同的背景,在这些背景中,《平行I-IV》作为法罗基其他主要关注的事物的一部分是有意义的,以及这项工作——无论默认它是正在进行还是其必然不完整的——可能如何展开。这项工作将如何阐明我们的现状、电影的命运,以及生活的重塑(Life Remade)。这些背景大致是:再现和复制;操作性图像;监视和军事;模拟和角色扮演;以及对不可见性的劳动和劳动的不可见性。
再现和复制,或法罗基的物质主义
Represen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r Farocki’s materialism
再现和复制,或法罗基的物质主义
Representation and reproduction, or Farocki’s materialism
法罗基也许最为人熟知的是他探索了图像、图像机器和图像生产与相应的社会/政治现实之间的关系。在许多方面,他是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者,他意识到,在20世纪的某个时刻,图像开始有了自己的生命,而不是代表它们之外的某种现实,或与它们不同。但他也知道,图像是作为吸收社会现实和人类劳动的商品流通,在马克思主义意义上是「幻影」(phantasmagorias)和「商品拜物教」(commodity-fetishes)。这使他对「再现」作为我们主导的图像范式进行了相当持续的批判。在最后一次采访中,法罗基最后说:「复制的时代似乎或多或少已结束,而构建新世界的时代似乎即将到来,或已然在此。」(Saoulski, 2014)。
我认为他对本雅明的「复制」(reproduction,或再生产)一词的使用也包括了更广泛的「再现」,正如「构建」(construction)在这里代表或包括「模拟」(simulation)。再现模式的这种根本性转变会有什么进一步的影响,我将留到本节末尾,但法罗基似乎预示着默认值的改变,如今,数字图像是所有类型图像的主要参考点,包括模拟的图像(analogue images),就像留声机唱片不得不重新被称为 「黑胶」(vinyl)一样,因为它们从此会被从(默认是)CD或MP3下载的隐含角度来看。
这就是法罗基所建议的,他称这种模拟为「理念型」的再现,并将其与更普遍的现实的数学或算法建模相比较,包括通过剖析人类的喜好和偏好来「格式化」(formatting)人类。在某种意义上,这将意味着世界的计算机模型「竞争和击败」世界的物质性和物理的表现,而且,更具体地说,摄像机前的现实(pro-filmic)不再是图像的起源和基础,而只是成为其可抛弃的原材料。那么,从表面上看,法罗基对模拟的兴趣(或者如果你愿意,他的「对数字化图像的信仰」)似乎与他的物质主义截然相反,但就目前而言,我们可能要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这里,物质主义与模拟(materialism versus simulation)的悖论,将通过揭示自己是同一硬币的两面来解决。一方面,一种没有物质(without matter)的物质主义,现在受到哲学的青睐;另一方面,它是一种否认物质性的模拟,因此也是它自身物质存在的条件。
操作性图像 Operational images
操作性图像 Operational images
处理这个悖论的一种方法是考虑法罗基是如何悄悄地改写电影史的,在他作为电影人的漫长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偏爱某种类型的图像,他称之为「操作性图像」(operational images)。这些图像和电影的序列有非常不同的来源,并为非常不同的目的而制作:来源可能是科学实验、时间和运动研究,从医学影片、军方拍摄的监控图像,训练影片,工业影片,以及传感器和控制设备重组的巨大图像档案中提取。最初的目的可能是训练、测试、实验、监测,以及记录对人眼来说过快或过慢的现象[6]。这样的影像材料往往被称为「拾得影像」(found footage),现在是电影人和艺术家在电影和装置艺术界面,或是跨越纪录片和论文电影的互渗边界上的追求。法罗基很谨慎,不把这些图像当作「被发现的」,而通常不遗余力地指出这些电影是如何和为何制作的,并且由谁,以及在什么机构的支配下制作。
通过挖掘图像的工业、科学、官僚和军事用途,这些图像常常模拟景深(depth of field)和远距离行动,同时对比我们惯用的将图像视为「可看到的景象」方式和将图像视为待扫描、分类和操作的信息源的方式,从《世界的图像和战争的铭文》(Images of the World and Inscription of War, 1989)到《眼睛/机器》(Eye/Machine, 2001-2003),从《我以为我看到的是罪犯》(I Thought I Was Seeing Convicts, 2000)到《深度游戏》(Deep Play, 2008),法罗基对处于「观看」和「行动」这两个极端的历史背景的图像进行了解构和分析(见 Paglen, 2014, and Christa Blümlinger, 2004)。无论是19世纪建筑和土地测量中的立体摄影,安保监狱和超市的监控录像,工厂中的时间和运动研究,还是传感器和视觉机器跟踪的2008年柏林足球世界杯决赛,法罗基一次又一次地表明,图像不仅是可以沉思,可以沉浸其中,以欣赏或漠不关心的眼光看待的东西,而且现在更多的是作为行动的指令(instructions for action,由机器),或作为处理和转化为行动的数据集(由机器)(见 Antje Ehmann and Kodwo Eshun, 2010)
简而言之,将这些操作性图像(一个最初来自媒体理论家维兰·弗卢瑟尔(Vilem Flusser)的概念(见 Christa Blümlinger, 2014))带入电影史,作为电影的一个被忽视的谱系,这一事实必须算作法罗基对媒体考古学最重要的贡献之一,也是数字图像史前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例如,在《世界的图像和战争的铭文》中,法罗基沿着操作性图像的系谱追溯到阿尔布雷希特·梅登鲍尔(Albrecht Meydenbauer),他是摄影测量学(photogrammetrics, "Messbild-Photographie")的发明者,不仅可以记录教堂或尖塔等历史建筑,还可以计算比例和尺寸,以便以建筑平面图和示意图的形式准确呈现它们。在《世界的图像》中,法罗基将梅登鲍尔的发明与试图在现场测量这类建筑时差点死亡的震惊和创伤联系起来,因此,操作性图像是携带着对地方的记忆或对人类无法亲临的危险情境预期的图像。我们可以看到,从梅登鲍尔的摄影测量学到远程制导导弹、智能炸弹和无人机,可以得到一条相当直接的路线。
在这方面,法罗基预见了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 (1998))所区分的,我们用来「说谎」(lie)的图像(模拟、假想场景、假信、虚构)和我们用来「行动」(act)的图像(远距离采取行动、提取可操作的数据、启动一个进程、记录一个测试、进行一个实验)之间的区别。
就操作性图像而言,它们不再像「世界之窗口」那样发挥作用,它们为图像的新定义指明了方向。这些变化我们倾向于与数字转向联系在一起,但操作图像正提醒我们,运动与静止的图像有许多历史,而并非所有这些都历史都通过电影传达或属于艺术史。数字图像可能只是使这些平行的历史更易被察觉的存在,而正如法罗基清楚看到的那样,操作性图像一直是围绕着我们的视觉文化的一部分。
例如,法罗基在1983年拍摄的一部关于《花花公子》杂志的中间插页的电影《一张图像》[An Image, Ein Bild](顺便一说,这部电影有时会与《平行 I-V》一同放映),以有时令人折磨的细节,记录了在创造操作图像时,需要投入多少地劳动,即使是那些说:「看,我是多么美丽」的那些。
人们甚至可以进一步宣称,操作性图像(作为行动指令的图像)是所有图像制作的新的默认价值,与之相对的,是更多的那些仅是为了沉思、无趣地观看或为了其审美性质的传统图像,正在被重新定义为操作性图像的具体的实例(我甚至主要不是在谈论广告、宣传或色情制品)。毕竟,已经有一代用户长大了,他们不再想看着图像(look at images),而是越来越期待能在他们的 Facebook 时间流或 Instagram 上点击这些图像。
监控和军事 Surveillance and the military
监控和军事 Surveillance and the military
法罗基在1990/91年左右以《世界的图像和战争的铭文》取得了国际上的突破。这部电影酝酿了很长时间,实际上是在1990年柏林墙倒塌和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完成的。然而,它正好与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的《战争与电影》的英文出版碰上。这三件事结合在一起,为法罗基电影的接受创造了一种完美的风暴,它似乎变得非常及时和有先见之明。
在我们大多数人第一次认识「智能炸弹」时,这部电影在美国引起了轰动,似乎是对维里利奥的书的评论,另外还包括施瓦兹科夫将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我们在晚间新闻中看到他拿着指针向我们展示对伊拉克阵地、公路或桥梁进行「外科手术式打击」后产生的小股烟雾。这是我们对《严肃游戏》的第一次介绍(见图5)。施瓦兹科夫不仅有一个从托马斯·品钦的《万有引力之虹》中走出来的名字,而且他的演示让他看起来像是从法罗基的电影中走出来的。
另一个快乐的意外,如果你原谅我的说法,是《世界的形象和战争的铭文》谈到了奥斯维辛,当时冷战后、苏联解体后,大屠杀即将成为我们理解二战和20世纪的重大事件,并随之开启了历史和记忆的危机。在《浩劫》(Shoah, 1985)和《辛德勒的名单》(Schindler's List, 1993)之间,世界的注意力已经从广岛之后的核威胁和欧洲土地上的美国原子武器(法罗基电影中的一个主要主题,以及可再生能源)转移到对大屠杀遗产的关注,以及大多数欧洲国家在摧毁犹太人方面的共谋,以及电影和摄影所扮演的暧昧角色。法罗基电影的这一解读的核心是侦察机拍摄的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照片,以及一名士兵在选择人群的坡道上为他的个人战利品相册拍摄的照片。这两种类型的图片都是「盗取的」(purloined),在「偷」的意义上,以及埃德加·爱伦·坡在他的「失窃的信」中使用的意义上。[7]
在这里,「拾得影像」这个词可能是对「盗取的」的准确补充,而这些图像在当代监控范式中具有可追溯的意义,因为它们证明了监视行为中固有的一种特定法医动态(forensic dynamic)[8]。但监视图像既是致命的也是无知的,它们可以是愉悦的也可以是威胁的,这取决于人们把自己放在哪一端。法罗基提到,如果1944年这些美国侦察机的飞行员看到的是奥斯威辛(用他们的相机),而不是看到「奥斯威辛」(用他们的心眼),那就说明监视可以是一种愚蠢的形式,给人一种被控制的欺诈感。飞机在寻找别的东西,他们还不知道奥斯威辛意味着什么,而在奥斯威辛坡道上拍照的人也在寻找别的东西——一本战利品相册,而只是无意中记录了世纪的罪行。
在每一种情况下,图像都是见证,但就像它并不带着,或甚至违背了那些见证者的意图。如果考虑到这些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监控照片之所以被发现,是因为1970年代末的一位官员被电视连续剧《大屠杀》所感动,他记得曾经在五角大楼的文件柜中看到过集中营的照片,这种讽刺就更加令人感慨。一个虚构的(fictional)电视节目才让这个文件证据曝光。作为一个旁观者,它还证实了盟军的战争目的不是拯救犹太人(如果人们参观华盛顿大屠杀博物馆的话,现在美国的官方说法是这样的),而是使纳粹德国的战争机器失效、即拆除和摧毁作为奥斯威辛附近莫诺维茨奴隶劳动营的一部分的布纳合成橡胶厂(Buna synthetic rubber)。
正是这些旁证,这些参考和相关性的滑落,这些追溯性的重写突然揭示了我们世界中意想不到的联系、不可思议的巧合或令人惊讶的脱节,使《世界的影像》成为一部不可磨灭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一部允许连续重构如此多关键辩论的经典。从那时起,法罗基在他后来的许多电影和装置作品中挖掘了这些对战争、摄影和监视的调查线索,特别是《我想我看到的是罪犯》和《眼睛/机器》(Eye/Machine)。
事实上,人们已经可以在这些早期的作品中找到《平行》中对第一人称射击者视角的偏爱,因为在《我想我看到的是罪犯》的开篇中,摄像机的眼睛和枪支的视线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译注:这里选用的是结尾处的影像)。然而,在这部影片的结尾,法罗基踌躇满志地表示,鉴于新的标记、追踪和「去领土化」的电子监控技术出现,这种基于视觉监控的控制设备已经过时。
似乎这种欺骗性的天真开始得到了回报:我们突然看到法罗基是如何摆脱「越来越写实」的论点,当他表明使用CGI时,无论多么「写实」,海底没有深度,山丘没有坡度,山脉也没有斜度,森林或城市街景可以直接掉到边缘,消失或漂浮在太空。
数字图像的世界可以作为法罗基的隐喻,因为它提醒我们,我们每天看到和体验的现实可能与实际影响我们生活和决定我们命运的现实全然不同。只需要想想高速电子交易,数十亿欧元、英镑或美元在纳米级的时间内转移到各大洲,或者当我们用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上网时留下的无形的脚印。因此,虽然《平行 I-IV》表面上的相似之处是在模拟照片(analogue photographs)和它们的数字克隆之间,但更隐晦的相似之处是尖锐的政治性,因为它们表明细节越密集,现实就越具有欺骗性。感知、感觉、视觉性:如此多的伪装(法罗基恰当地引用了著名的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小品),[9] 或者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 1999)所说的:「感知和这些感觉都成了洗眼液(骗局,表面文章)」(sense and the senses turn into eyewash)。
法罗基的几部电影和装置作品,无疑是自1990年代初和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对于或许可被称为「新型不可见性(new invisibility)」之物的延伸探测。它与法罗基自己所说的「控制性观察」(controlling observation)相对应,意味着一种视觉性(visuality),没有人类观察者与之相对应,而身体和感官(触摸、听觉、运动、情感)已经成为保护性和防御性的替身或假体。这种新的不可见性给电影制作者带来了特殊的挑战,因为正如法罗基(2004, 294)认为:监狱探视时间的场景(对监狱电影类型如此重要)很快就会发现自己在现实中没有对应关系。电子现金的引入将使以银行抢劫为主题的电影也几乎不可能......随着电子控制设备的增加,日常生活将变得像日常工作一样难以描绘和并且难以戏剧化。
我认为法罗基在这里的观点不仅是他想在视觉机器的时代描绘出可见性的极限,而且,作为这些视觉机器的结果,不可见性本身已经成为一种商品,特别是其在商业上的高利润,而这些在前维基解密,前斯诺登的日子里,在政治上仍然低调地在计算机软件公司,安全专家和消费者服务行业之间建立自己,起到「协同作用」(synergies)。
换句话说,不可见性(Invisibility)是一种主动生产的东西,而不是简单的缺席、缺乏或缺陷。似乎是为了回应这一挑战,法罗基开始了一系列的视频和装置创作,特别是《严肃游戏I-IV》(Serious Games, 2009-2010),当然还有《平行I-IV》(2012-2014),这两部作品都将模拟作为这种新的不可见性的重要策略之一,并且将对虚拟现实和计算机图形的研究与他早期作品,包括已提到过的,以及也包括《深度游戏》(Deep Play, 2007)以及《如何生活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下文简称 Leben BRD, How to Live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1990)和 The Creators of Shopping Worlds(2001)。
在《眼睛/机器》中,已经形成了另一个在《平行》中再次出现的想法,即夜间新闻中媒体战争的众多讽刺之一是,我们愿意为智能炸弹的破坏能力的鸟瞰图而兴奋。 《眼睛/机器》I 和 II 描绘了人类的手、眼睛和机器之间越来越不对称的关系(asymmetric relation),因为身体似乎成为了自动化互动链条中最弱的一环,它以牺牲手为代价来促进眼,推动把「看」(seeing)作为记录与控制,而非是识别和理解:从而也结束了认识论上的等式,即「眼见为知」(to see is to know)。
身体和感官在机器和武器方面的这些转变,在法罗基那里常常被视为对于距离和切近的沉思,在遥远的地点进行的行动,而其结果则是在基地中负责。因此,距离和切近往往被一种关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展示的审问所反身性地倍增(reflexively doubled),有时甚至伴随着一种非常个人的、身体性的自我指涉(self-reference),如在 Nicht löschbares Feuer(1969)中,某种战争现实的不可比性及其电影表现已经预示着《严肃游戏》(Serious Games, 2009)中无人机袭击和摇杆战争(joy-stick warfare)的伦理僵局和身体创伤。
《平行》重复的第一人称射击视角让我们想起了安装在导弹上的「主观」摄像机,这种看似优越的视角让我们忘记了摄像机会和目标一起被杀死,也就是说,分享摄像炸弹视角的乐趣是有代价的:它不仅对目标是致命的。好莱坞电影如《American Sniper, Good Kill》或装置艺术家 Omer Fast 的《Five Thousand Feet Is Best》都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说服我们这种特权视角的道德代价,这种远距离的行动可能会扼杀我们对最亲近和最爱的人爱和同情的能力,但法罗基也在一个更广泛的背景下看到它,包括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战区的模拟,也包括基地近旁的角色扮演。
模拟、动画和角色扮演 Simulation, animation and role play
模拟、动画和角色扮演 Simulation, animation and role play
虽然我刚才提到的新不可见性是「新」的,只是因为法罗基的装置可能有助于更清楚地识别它,但我想提请注意的另一个方面是法罗基将其对不可见性的探索与不同类型的劳动结合起来的方式。其中最重要的是隐身的军事劳动(military labour of invisibility),这可能始于各种伪装(camouflage)——士兵的制服、强化的审讯中心或隐形轰炸机,但也包括官方的假消息散布运动,以国家安全为名的保密。它包括武装冲突中伤亡人员的不可见性,不仅是智能炸弹和无人机袭击对平民造成的间接损害,甚至连死去的归国士兵的尸袋也不被看到,还包括精神创伤的隐形性,特别是伊拉克和阿富汗旷日持久的战争对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及其家庭造成的心理创伤。
《严肃游戏》(见图6)将这种隐形的劳动联系起来,它通过将这些创伤从他们的生活现实中二次移除(twice removing)以将其遮蔽,非常有说服力地与电脑游戏和其他模拟技术联系起来,因为它们在战场和电影大片之间迁移,这表明数字图像可能试图向我们推销「增强的可见性」(enhanced visibility),但在输送时,我们收到更密集的纹理的不可见性(ever more densely textured invisibility)。这背后是工业劳动力和军事机构之间可能的平行关系,后者越来越多地将其劳动力外包给商业承包商,这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当不仅工人离开工厂,被机器人取代,而且士兵离开战场,被遥控无人机取代时,可能会产生什么后果。
另一方面,《严肃游戏》中的模拟治疗咨询,提醒人们注意另一个更传统的不可见性劳动的场所:医院工作人员和护理人员、家务劳动者和儿童照料者,简而言之:典型性别化的劳动,即移情和专注倾听,或者是在自助团体和健康中心的情形下,那些为西方所遭受的或已施加在自己身上的自恋创伤提供服务的劳动。除了其他几项内容外,法罗基的《Leben BRD》还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对我们将其称作情感劳动(affective labour)不同情况的汇编。然而,它现在有了一个名字,这表明,这种劳动可能已经变得不那么的不可见,但至少需要两代女权主义者的共同努力才能将其置于聚光灯下。
在《Leben BRD》中,游戏和对现实生活场景的模拟变成了生活的训练,被理解为在已很糟糕的情况下预测突发事件和预测结果的尝试。法罗基起初受到保险公司的启发,他们经常要通过探索(play through)生活史,以计算可能的结果和评估金融风险。但他很快意识到,将生活经验转化为脚本化的情景(scripted situations),将脚本化的情景转化为实战训练,比他想象的要普遍得多。
他发现自己在学校、办公室、产科诊所、脱衣舞俱乐部、无家可归者收容所、管理培训中心、警察局进行拍摄,观察儿童治疗师和军队野外演习。操作性的图像对应着生活的操作指令。正如影片的画外音告诉我们的那样,原因是:随着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关于生活的规则和条例的不确定性,有越来越多的游戏,将生活训练成一项运动。
几年后,法罗基将通过《深度游戏》(Deep Play)形象地展示体育和运动场是如何成为工作场所的,并从1910年代和1920年代 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 的「时间和运动研究」(time and motion studies)时代开始,就一直受到密切(见 Wood and Wood, 2003)。
《Leben BRD》是一个绝佳的,同时也是悲伤的、有趣的、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调查,它调查了这种对尝试生活的痴迷,以及潜伏在表面之下的恐惧和焦虑。一个博客上的评论捕捉到了它们的怪异(uncanniness):《Leben BRD》......包括训练人们杀人,提供产科护理,如何分离那些卷入家庭争吵的人等等。所有这些都穿插着工厂里测试设备寿命的影像(例如一个汽车门被机器打开和关闭了一千次)。这一切都显得相当平庸和呆板的程序。我有听过感觉(feeling)是如何被外包给专业人士(即精神病学家)的,而这里的精神病学家[就像机器]一样没有人情味(impersonal),让病人画出他们恐惧症的时间序列图,而无法提供病人所需要的东西,一个可以哭泣的肩膀,一个可以拥抱和理解的人。作为一个[自己]参加过角色扮演课程的人,我可以说,我觉得它们让人很不适,而且,我发现其他人不觉得它们如此,所以我更加不适了。[10]
《Leben BRD》记录了角色扮演、试驾、取样和紧急情况下的演习,简而言之,社会和个人生活的展演性方法(performative approaches),正日益定义社会领域以及我们与他人的互动。仿佛我们正与生活本身保持着「安全」的距离,不断要求提供如何生活的现场手册,以及如何进行战争、恋爱或对身体进行压力测试。然而,法罗基也展示了这些生活手册所替代的东西:它们是一种更积极的、富有成效的、与人进行的对这个世界参与(engagement)的安慰剂(placebo),而这对他来说,一直是由「工作」定义。
但是,这也有一个双重遗产,例如,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作为奴隶劳动的雇佣劳动(wage labour),被谴责为资本主义剥削的证据和表现,而工作(work)被认为是自我满足成就感和自我实现的手段,忠实于「各取所需,各尽所能」(to each according to his needs, from each according to his abilities)的座右铭,其中「劳动带来自由」(Arbeit macht frei,译注:源于德国的一句口号,该口号在十九世纪时开始流行,因被纳粹用来镶嵌于纳粹集中营的入口而别具意义)和「各得其所应得」(Jedem das Seine)成为冷酷无情的变态回声。[11]
法罗基的很多电影都是对劳动的尊严和经常强加给它的非人化的条件之间的这种紧张关系延伸的自我审视:体力劳动、智力劳动、工人团结、工会和有组织的工人阶级、手的工作或「Handwerk」(工艺和技能)。有时,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是主要主题,如法罗基的第一部长篇电影《战争之间》(Between the Wars),有时工业工作是以忧郁的回顾为其特色,如《离开工厂的工人》(Workers Leaving the Factory),有时工作间接出现或通过其焦虑的模拟,如《Leben BRD》,最后是他最后的项目(与 Antje Ehmann): 《单一镜头下的劳动》(Labour in a Single Shot)提供了当今劳动多样性,以及从事往往是体力耗尽和重复性工作的男人和女人的汇编,而正是由于其日常性和重复性,这些工作通常是不可见的,在遥远的城市,如班加罗尔和柏林,波士顿和布宜诺斯艾利斯,杭州和河内,里斯本和罗兹,墨西哥城和莫斯科,里约热内卢和特拉维夫。 [12]
换句话说,这种新类型的不可见性和投入其中的劳动,需要重新思考使之可见的策略,而我认为《单一镜头下的劳动》就是对此的一次英雄式的尝试:在这种劳动的不可见性和对不可见性的劳动的视野上,《单一镜头下的劳动》被看作是反转不可见性的一种方式,也是对外包劳动的主导逻辑的反击,同时也非常清楚,不仅仅是苹果、奔驰或宜家这样的跨国公司在实行外包。博物馆的策展人在缺乏新鲜材料的情况下,也会在全球范围内寻找新的人才,而电影节也同样急于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挖掘新的创作潜力,通过组织人才校园或提供种子和发展资金,将这些潜在人才与他们的机构或品牌联系起来。[13]
《单一镜头下的劳动》通过再溯源(re-sourcing)的方式来反击外包,但不是像1970年代的工人电影试图通过向罢工的工人发放摄像机那样,也不是像人类学家向亚马逊部落发放摄像机,让他们大声反对伐木和破坏巴西雨林的不公正行为那样(见Ginsburg, 1995; Shohat and Stam, 1994; see also Tierney, 2001; Bloom, 1999)。《单一镜头下的劳动》通过反身性地倍增了任务,而避免了这两个传教士赋权的陷阱。 法罗基(1975: 168)曾谈过同为导演的 Christian Ziewer 拍摄的工人电影:导演让自己成为他自己任务的仆人——「他把自己送上去」(er hat sich selbst geschickt,he sent himself up) 。法罗基小心翼翼地没送自己上去,而任务被多重过滤和中介,重新聚焦和变得反身性,通过他在这些城市举办的大师班,从而赋予有抱负的电影制作人的眼睛和手、技能水平和气质,所有这些都是被访问的城市的土生土长的 [14]。
再一次的模仿 Mimesis once more
再一次的模仿 Mimesis once more
那么,对于我的感觉,即《平行 I-IV》比它的看起来的事实情况似乎更加神秘,它可能是「正在进行的工作」,而不是一个独立的作品,是什么给了我这种感觉?
声称在游戏(game-play)和非模拟(dis-simulation)之间的界限,角色扮演和现实之间的界限越来越相互渗透以及反转,这已成为我们后人类话语的陈词滥调的一部分。《平行 I-IV》提供了任何数量的此类声明、意见和描述,然而我认为,如果认为法罗基就是这样就完了,那将是一个错误。
对于法罗基,我们最好用没说出的东西来补充说出的那些东西,并去感受被蒙太奇所带到一起的元素之间的间隙(gaps)。因为正是法罗基自己不可见的劳动进入了这个蒙太奇,并通过他不可见的剪辑而变得明显:把习惯上认为属于一起的东西分开,并把以前没有人想到的东西联系或连接起来。
因此,在《平行》中,在语音解说间的长时间沉默并不只是为了让我们附和正在说的话,或应用于跟随的图像,就好像这些图像仅是文字的说明。相反,这些沉默本身就是一种反驳(counter-argument),或者像法罗基喜欢说的那样,它们是 「反音乐」(counter-music)。换句话说,正如标题已经暗示的那样,《平行 I-IV》很可能是某些东西的负面衬托,就像我认为《Leben BRD》的生活手册将作为自我实现的手段「工作」的消失,来作为其无形的印记。那么,如何将《Leben BRD》的怪异(uncanniness)与《平行世界》的恐怖谷(uncanny valley)效应放在一起思考?
为了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我必须再次回到巴赞,即把他们的信仰放在图像上的电影人和那些把他们的信仰放在现实中的电影人的区分。在我到目前为止的论证之后,一个结论是,这种区分不再仅仅适用于电影制作人,而是适用于整个社会,在那里,被不同种类的不可见性所中介,那些把他们的信仰放在角色扮演和生活手册上的人,那些用他们的身体在跑步机上锻炼,把自我优化(self-optimization)当作自我启蒙(self-enlightenment),或把自我剥削当作创造力的人。还有那些用计算机图形动画来完善越来越逼真的世界的人,这样做不仅是为了把世界当成一个洋葱,只由一层层的东西组成,核心是空的,而且恰恰是为了把那些除了对现实的信念外别无选择的人,也就是那些经历了一个现在靠模拟图像生活的世界的残酷物质性和致命的后果的人给挡在门外。
他们的信念必须是,现实有一天会改变,而法罗基的电影也正是要表达这样的希望,例如在《比较》(In Comparison,关于世界不同地区的制砖业),或者他的装置作品《银与十字架》(The Silver and the Cross,关于一幅玻利维亚城市波托西及其传说中的银矿的画,它为西班牙领导的第一次西方全球化支付了费用)。这些都是图像表面的非物质性的反面(reverse-side)物质性的例子,这表明,《平行》也可能有一个隐含的,但乍一看看不见的反面。
多年前,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法罗基承认,作为一名电影制作人和图像制作人,他是那些任务是「使世界变得多余」(make the world superfluous)的人的一部分,这意味着一个将其信仰放在图像中的世界,变得不在乎这个世界在现实中的命运。显然,这些关于电影使世界变得多余的言论与他后来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劳动的非物质化和不可见性的劳动产生了共鸣。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看到的《平行 I-IV》可能,如果你愿意的这么说的话,是一个更广泛的辩证法的论题的第一阶段,而《严肃游戏》,尽管制作时间较早,也是类似于反题的东西,因为《严肃游戏》向我们展示了使世界变得多余的心理和道德后果,这也可以解释为何《平行》避免指出电脑动画的物质后果。[15]
那么,如果《平行》是论题(thesis)(即,展示计算机模拟的世界在我们看来是如何使一切成为可能,没有阻力和物质阻碍,但在每一个城市的十字路口或海岸都可能陷入虚无)的话,如果《严肃的游戏》是反题(antithesis)(向我们展示这种虚无的后果,就在我们视野的角落和边缘:一个没有阴影的世界,一个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世界,如果我们记得那些关于丢失阴影的表现主义电影的话),那么可能的合题(synthesis)是什么呢。
对一种模拟的模拟的向下螺旋的一种合题(或仅仅是另一种结果)将把我们带向一些永远后退的柏拉图式的天堂,属于理念类型(ideal types),完美,带向对现实及其风险的预见性、先发制人的行动和预先的调解,试图通过对「现实」越来越有丰富数据的模拟来控制意外情况。
另一种合题(或仅仅是另一种反音乐)将是重新评估当我们失去我们的影子时我们失去了什么,也就是说,当我们从「现实」到「电影」,从电影到「后电影」,即,数字模拟,或者用一个不同的词汇,当现实的想象图像(imaginary image)让位于现实的模拟图像(simulated image),或再用另一个词汇,当作为主体效果的现实效果(即主体位置的想象性构建)让位于作为玩家化身效果的现实效果(即互动位置的模拟构建)时,我们失去了什么。
在《平行 I》的结尾,法罗基引用了相信图像的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一位,即希腊画家宙克西斯(Zeuxis)。画外音是这样说的:「根据传说,宙克西斯能把水果画得如此逼真,以至于鸟儿们纷纷飞来啄食它们」,接着是一个长长的停顿,然后换了一个话题。除了屏幕左边是一片空白,没有图像,电影没有显示的是,故事是如何发展的,而这至少可以关联历史学家普林尼(Pliny the Elder, Naturalis Historia; see the entry on Parrhasius by Chisholm in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11)的说法。当宙克西斯向同行的画家帕拉修斯(Parrhasius)吹嘘时,后者邀请宙克西斯到他的工作室,渴望向他的对手展示类似的壮举。宙克西斯在作品前要求帕拉修斯把挂在画布上的窗帘拉开,以便能够亲自判断他的同事的技巧。但这窗帘其实是画。宙克西斯承认帕拉修斯是两人中画得更好的那位,他说:「我骗到鸟,但你骗到了我。」[16]
翻译成我们当代的情况:栩栩如生、自然的葡萄给了我们一个版本的照片写实主义,它是严格为鸟所做的,通过模拟「在那」的东西,产生的只是一个造假(fake),而遮住帕拉修斯的「画」的窗帘则在观看者的头脑中达到效果,从而产生了一个「真相」(truth):不是关于世界,而是关于这颗心,关于想象力,我们的欲望和/或我们(自我)欺骗的能力,从我们脚下扯去地面,或把我们放入(强迫性的)重复循环中。
换句话说,宙克西斯和帕拉修斯是两种「现实主义者」,然而他们的策略是不同的,且几乎是截然相反的,在这个意义上,第二个是对第一个的元评论。这并不是说帕拉修斯只是一个「巴洛克式」的错视画派(trompe l'oeil)的现实主义者,而反对「古典式」的具象派的宙克西斯。重要的是两者之间的互动或交错(interchange),宙克西斯的「看的要求」错误地将帕拉修斯的窗帘插在他和他希望看到的再现之物的中间。宙克西斯的范畴错误(category mistake)正是帕拉修斯的画,或者换句话说,宙克西斯画的是葡萄,而帕拉修斯画的是(对葡萄)欲望(desire)。
因其自身对占有的不可能的欲望,而产生的这种模仿的双重性(doubling of mimesis)(以及在再现的悖论中常是致命的缠绕,准确地说,涵盖了虚无的深渊或最终没有任何东西「在那」的恐惧)指出了我们在这个没有阴影的新世界中可能失去的东西,因此,在《严肃游戏》和《平行》中都不可避免地、必然地「缺失」了什么:我们曾经知道的电影,现在象征性地体现在导演身上的电影,而对于巴赞来说,导演是一位相信图像的电影制作人的缩影,即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关于他,我们可以说,就像帕拉修斯一样:那些导演中的宙克西斯拍摄了玛丽莲·梦露或朱莉娅·罗伯茨,就好像她们是真实的一样,而希区柯克拍的是那遮蔽物(veil):对梅兰妮、对玛尔尼和对玛德琳的渴望。
这些是法罗基没有得出的结论,也许也不会得出。因此,让我以一个我自己的假设来结束。模拟电影制作(analogue filmmaking),以制作(production)为中心,试图「捕捉」现实,以「驾驭」它成为一种表现,而数字电影制作,从后期制作的角度来设想,以「提取」(extracting)现实的方式进行,以「收割」(harvest)它成为一个数据集。
后期制作的电影不是披露和启示(从 Jean Epstein 到 André Bazin,从 Siegfried Kracauer 到 Stanley Cavell 的电影本体论),也不是为心灵和感官体验其自身的快乐和恐惧而遮蔽世界(如希区柯克或弗里茨·朗),而是将世界视为待处理或开采的数据,视为待开发的原料和资源。换句话说,在数字电影制作中,从制作到后期制作的重心转移,主要不是由与「现实」的不同关系所决定的(正如围绕数字影像中的指涉性的丧失所声称的那样)。相反,一种后期制作成为默认值的生产模式所改变的不仅仅是过程(procedure):它改变了电影的内在逻辑(以及它的本体论)。
数字化所允许的对后期制作的强调,从根本上说不再是基于感知(perception):它的视觉性是植物性的(vegetal):可与生物遗传学或微型工程过程中对基因或分子材料的种植、收获、提取和操作相提并论。因此,难怪法罗基的《平行》一开始就回到了树叶和树木,回到了草叶和海浪的拍打:这就是一切的开始,因为它又是如何开始的:「在电影中,有吹来的风和由风力机产生的风。计算机图像没有两种风」,那是因为真正的风暴在吹,这里无意冒犯沃尔特·本雅明 [17],从边缘和底层吹来,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之为进步的像素的「天堂」。另一方面,后期制作作为新的默认值,也可能意味着工业资本主义对世界及其资源的这种剥削关系的结束。这也将是一股清新的空气:也许终究是进步的风。
Notes
Notes
1.最臭名昭著的是,巴赞在 McCabe (1974) 中扮演稻草人。麦凯布(2011:66)后来承认把他当作「一个理论上天真的经验主义者,家里的白痴。」
2.www.bfi.org.uk/news-opinion/sight-sound-magazine/features/video-essay-animal-menagerie-rhythm-hues; vimeo.com/147743032
3.见 www.harunfarocki.de/installations/2010s/2012/parallel.html
4.见Youtube视频“HARUN FAROCKI | GALERIE THADDAEUS ROPAC | PARIS MARAIS | 2014”
5.为纪念法罗基而出版的相关回顾,见 e-flux 59 特刊(2014年11月),专门介绍法罗基, www.e-flux.com/announcements/issue-59-harun-farocki-out-now
6.正如艺术家特雷弗·帕格伦(Trevor Paglen, 2014)所指出的:图像世界正在发生一些新的事情,一些视觉研究和艺术史的理论工具无法解释的事情:机器开始自己看。哈伦·法罗基是最早注意到图像制作的机器和算法即将开创一种新的视觉体制的人之一。机器和它们的图像不再简单地代表世界上的事物,而是开始在世界上「做」事情。在从营销到战争的各个领域,人类的眼睛正变得不合时宜。正如法罗基所称的那样,这是「操作性图像」的出现。
7.拉康、德里达以及他们各自的追随者和批评者对于爱伦坡的这篇短篇小说意义的争论可以在 Muller and Richardson (1988) 中找到。
8.偷窃和监视之间的平行也由 Hull (1990) 指出
9.Monty Python’s Flying Circus (1969–1974), 2nd series, episode 11 (‘How not to be seen’, 1979).
10.See Cinema of the World. Available at: worldscinema.org/category/harun-farocki
11.这是分别贴在奥斯维辛集中营和Buchenwald 集中营大门上的标语
12.见 www.labour-in-a-single-shot.net/en/project/concept/
13.例如,印度艺术家 Bose Krishnamachari 认为自己是西方的星探:当我在国内旅行时,我的目标总是发现一个新的人才,看看他或她在做什么,并理解他或她为什么这样做。有些批评家说我是一个「星探」(talent scout)。是的,我是一名星探,我是一名军事训练师,我是一名诡计多端的指挥官,因为我所寻找的是一个结果……由于思想、商品、文化、政治、关切、意识形态、战争等等的全球自由交流,艺术也变得跨越国界。不仅是印度当代艺术正在走向世界,世界艺术也正在走向印度。这并不是因为世界突然爱上了印度的艺术和文化,才引起了全球的关注。不,这是因为经济和全球政治参与……此外,艺术具有投资价值;通过对艺术的投资,跨越国界的人们在经济层面上也相互信任。所以我们面临着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局面,即全球玩家来到印度观看我们的艺术,购买我们的艺术,并在其他地方展出我们的艺术。(www.aaa.org.hk/en/ideas/ideas/interview-with-bose-krishnamachari/type/conversations).还有可见 Flores(2008) 和 Demos(2013)。在电影节方面,鹿特丹和柏林率先推出了「发展基金」和「人才园区」。到目前为止,几乎每个大型艺术节都有这样的人才校园。一个目的是将这些新兴的人才与最初赞助他们的艺术节结合起来。
14.For a more detailed analysis of the ‘Labor in a Single Shot’ project, see Moeller (2014)and Hoof (2015).
15.由于没有进一步的证据表明法罗基策划了这样一个三部曲,由于他的英年早逝,三部曲可能还没有完成,所以这个假设只能停留在推测阶段。但毫无疑问,法罗基是一个深刻的辩证思想家,因为他相信通过对立力量的冲突来进行改变,这些力量在表面上的对立和分离中揭示出互补的可能性条件,从而形成一种统一。鉴于这个思想实验的不完全性,我自己假定的合题更多的是对话式的而非辩证的。
16.见wikipedia“Parrhasius painter”
17.参考瓦尔特·本雅明在《关于历史哲学的提纲》中的 Angelus Novus 的段落 members.efn.org/~dredmond/ThesesonHistory.html
References
References
Bazin A (1967) The myth of total cinema. In: What Is Cinema? Vol. 1, trans. Gray H.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1–22.
Bazin A (2009) The evolution of the language of cinema. In: Braudy L, Cohen M (eds) Film Theory and Critic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41–53.
Bloom L (1999) With Other Eyes: Looking at Race and Gender in Visual Cultur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Blümlinger C (2004) Harun Farocki: Critical strategies. In Elsaesser T (ed.) Harun Farocki: Working on the Sight-Lin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318–320.
Blümlinger C (2014) An archaeologist of the present. e-flux 59. Available at: www.e-flux.com/journal/an-archaeologist-of-the-present (accessed 28 June 2017).
Chisholm H (1911) Entry on Parrhasius. 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1th ed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Demos TJ (2013) Return to the Postcolony: Specters of Colonialism in Contemporary Art. Berlin: Sternberg Press.
Ehmann A, Eshun K (eds) (2010) Harun Farocki: Against What Against Whom. Cologne: Walther König.
Farocki H (1975) Schneeglöckchen blühen im September. Filmkritik, March: 168.
Farocki H (2004) Controlling observation. In Elsaesser (ed.) Harun Farocki: Working on the Sight-Lines.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289–296.
Flores P (2008) Past Periphery: Curation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NUS Museum.
Franke A (2012) Modern Monsters/Death and Life of Fiction. Taipei: Taipei Fine Arts Museum. Available at: http://www.taipeibiennial.org/2012/en/participants/harun_farocki.html
Ginsburg F (1995) The impact of Aboriginal media on ethnographic film. Visual Anthropology Review 11(2): 64–76.
Godard J (1965) Montage mon beau souci. Cahiers du cinéma 65: 30–31.
Hoof F (2015) Labour in a single shot: Harun Farocki/Antje Ehmann. Aniki 2(1): 170–174.
Hull R (1990) ‘The Purloined Letter’: Poe’s detective story vs. panoptic Foucauldian theory. Style 24(2): 201.
Kittler F (1999) 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Manovich L (1995) What is digital cinema? Available at:manovich.net/index.php/projects/what-is-digital-cinema (accessed 28 June 2017).
Manovich L (1998) To lie and to act: Cinema and telepresence. In: Elsaesser T, Hoffmann K (eds) Cinema Futures: The Screen Arts in the Digital Age.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198–199.
McCabe C (1974) Realism and the cinema: Notes on some Brechtian theses. Screen 15(2): 7–27.
McCabe C (2011) Bazin as modernist. In: Andrew D (ed.) Opening Bazin: Postwar Film Theory and Its Afterlif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eller R (2014) Antje Ehmann and Harun Farocki at work. Hyperallergic. Available at: hyperallergic.com/162960/harun-farocki-and-antje-ehmann-arrive-at-work(accessed 28 June 2017).
Muller JP, Richardson WJ (1988) The Purloined Po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Paglen T (2014) Operational images. e-flux 59. Available at: www.e-flux.com/journal/59/61130/operational-images/ (accessed 28 June 2017).
Saoulski N (2014) Interview with Harun Farocki, Galerie Thaddeus Ropac, Paris. (accessed 28 June 2017).
Shohat E, Stam R (1994) Unthinking Eurocentrism. New York: Routledge.
Tierney P (2001) Darkness in El Dorado: How Scientists and Journalists Devastated the Amazon. New York: WW Norton & Company.
Virilio P (1989) War and Cinema: The Logistics of Perception (Radical Thinkers). New York: Verso Books.
Wood MC, Wood JC (eds) (2003) Frank and Lillian Gilbreth: Critical Evaluations i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New York: Taylor & Francis.
关于 哈伦·法罗基 国内进行过的讨论可参考由 CACHE 缓存 在 2018-2019年《哈伦·法罗基:图像搏击者》展览期间进行的两场研讨会,政治散文与图像起义 与 算法治理下的操作图像 或可以作为参考。
此外可参考:托马斯•埃尔塞瑟 作为思想实验的电影
Transversals: From Video Essay to Playful Essay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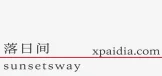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