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以通信、控制和统计力学为中心的一系列问题在本质上具有统一性,无论是在机器中还是在生命组织中……我们决定用控制论来称谓控制和通信理论的整个领域,既在机器中又在动物中,这个词构成来自希腊语κυβερνήτης,即「掌舵人」。——Norbert Wiener, Cybernetics, 1948, P11
控制论(cybernetics)提出的从动力学(dynamics)视角通过「连续输入-输出的动态反馈循环」考察系统的理论,被认为是复杂系统科学的肇端之一。该理论由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在1948年提出。它脱胎于维纳在二战时期为美国军方研究的自动火炮控制系统, 而其最终成型实际上是跨学科交流的的产物。即使只考虑控制论工程技术应用的面相(我称为「狭义控制论」),它本身也已整合了自动化控制、通信理论、神经生理学和计算机理论这些「硬科学」。
至于控制论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推及,虽然维纳在1948年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像个体一样的组织,由通信系统联结在一起,它自有其动力学,在其中具有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Norbert Wiener, 1948)可他却对控制论的数学方法「治愈当前的社会病不抱太多希望」。
但是在梅西会议上(一般指1946~1953间的十次跨学科研讨会),控制论还是被抽象为关于复杂系统和反馈的认知方法(我称为「广义控制论」),其影响扩展至人类学、心理学和社会学等「软科学」。
在1949年后的中国,也不乏将控制论应用于社会管理和人文科学的尝试,然而其始终保留着关于数学及其工程技术的「硬科学」内核,并以「狭义控制论」的一面为人所知。比较控制论在美国和苏联的历程,可以发现控制论在新中国独特的内外部环境中呈现出的不同特征。
控制论在美苏
控制论在美苏
在美国,1946年~1953年间,纽约比克曼酒店的梅西会议上,控制论在十次会议中经历了快速的演化过程。
最初,它还只是维纳在电机工程学和神经生理学的交叉地带发现的略显模糊的反馈理论。随后,在经历了会议主席沃伦·S·麦卡洛克(Warren S. McCulloch)精心安排的议程后,它在数学、物理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个学科的交流甚至是交锋中,逐渐混合成「控制论」。最后,1948年《控制论》出版后的5次梅西会议主题也由「生物和社会系统中的循环因果和反馈机制」更改为「控制论」。控制论甫一成型的核心概念,很快在这几次会议上的跨学科高频思想交锋中变得多元而模糊,甚至与会者都难以总结会议内容。但是控制论关于复杂系统和反馈的认知方法却影响了这次会议涉及的所有学科。
二阶控制论的提出者海因茨·冯·福斯特后来将控制论称为「一组似乎在所有领域都起有用的概念模型的一场试验」(Heinz von Foerster,1951)。可以说,控制论在其最初诞生的十几年间,快速的经历了「提出——确立——扩展——耗散」的过程,以致于许多如今的学科都有控制论的影子但却不再继承其具体的知识。
在苏联,控制论的经历可谓一波三折。20世纪40年代末《控制论》出版之初,就已在苏联科学家圈子内流传。但是,维纳基于神经系统中电信号的循环反馈模型,在当时却被认为相悖于苏联生理学界主流的巴甫洛夫反射理论。控制论因此被卷入了荼毒苏联生理学和遗传学界几十年的「李森科事件」中,随后更是被学术界斥为服务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伪科学。
然而就在1953年后赫鲁晓夫的「解冻」时期,控制论在苏联的形象发生了180度的转弯。控制论先是因为苏联军方对计算机技术的迫切需求而成为一门显学,这直接促成了1960年维纳访苏。紧接着在60年代,控制论在官方机构和公共舆论的推动下形成了一股狂热。即便是相对于「广义控制论」来说,这时的控制论的效用也被无限夸大了,它成为了投机学者们的绝佳工具。讽刺的是,这反而使控制论在公众的印象中更接近先前被批判的「伪科学」。而苏联计算机先驱安纳托利·基托夫(Anatoly Kitov)和维克多·格鲁什科夫(Victor Glushkov)先后提出的EASU(经济自动化管理系统)和OGAS(国家自动化系统),也都在舆论误解和官僚系统惰性中不了了之。
有趣的是,苏联发生的一切反而决定了控制论在其诞生地美国的命运。冷战中的美国既要开发阿帕网等军用信息设施,同时也希望与这门和苏联官方有关的学科撇清关系。于是控制论在冷战漩涡和麦卡锡主义的余波中被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在美国成了鲜有问津的冷门研究领域。
控制论在美苏的遭遇虽不尽相同,但它们都经历了向各个领域迅速扩散的过程。回看控制论成型之初,它所带有的「普遍理论」基因几乎决定了控制论的核心知识(数学方法)向外耗散是一种必然:控制论包括了「当前世代的计算机原理;神经生理学的最新发展;以及精神病学、人类学和社会学模糊的“人文主义”的混合体」(Claus Pias,2016)。
工程、控制论与中国
工程、控制论与中国
在中国,控制论向其他学科的扩展大约发生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1983年,钱学森在与宋健合著的修订版《工程控制论》的序言中,修正了他在1955年原版中对控制论的看法:「控制论的现代发展证明维纳1948年的观点是过于保守的。把这些工程技术方法推广应用到社会领域也不是“过分的乐观”,而是现实,运筹学已用于经济科学,并将应用于更大的社会领域。」
其实,控制论与中国的联系并非始于钱学森,而是始于数学家李郁荣(维纳是他在MIT的博士生导师),1936年他邀请维纳来到清华大学数学系和电机工程系任教。维纳结束中国之行返回美国后,还曾推动约翰·冯·诺依曼访问清华,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只得作罢。李郁荣的相关研究也因战争而被迫中。
而1955年才归国的钱学森,则是控制论在中国的真正的关键人物。他不仅主导将「工程控制论」从理论实践应用于新中国的国防军事,而且推动了控制论向系统工程的发展,及其在科学规划和生产领域的应用。
钱学森最初是在美国的航空航天工作中接触到了维纳的控制论,「导弹就是这样制导的:控制器接收有关速度和俯仰的信息,将信息发送给伺服机构进行更改,然后在反馈回路中接收更新的信息。」(Dylan Levi King,2004)1950年起,钱学森被卷入麦卡锡主义风波,被禁止接触军事研究,并被当局审查了五年。在此期间他撰写了Engineering Cybernetics一书。1955年归国后,他将该书译为中文出版。控制论以《工程控制论》的面貌被正式引入中国。
1960年,苏联正式停止对华援助,钱学森及其同事归国后的工作恰好填补了国防计划中核工业和弹道导弹领域的空白。随后,他和同事们在短短几年内就成功制造出了氢弹、原子弹和卫星的运载工具。
1970年代末,钱学森重返公众视野,此时正值计算机技术高速发展。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指导下,钱学森开始思考控制论在更广阔领域的应用,1978年,钱学森提出以「系统工程」整合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和运筹学,以此来管理工业和农业生产,规划国民经济发展。1984年,时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的宋健认为「传统上属于社会科学的问题可以通过工程学的方法来解决」。同年出版的《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对中国封建社会超稳定结构的探索》(金观涛)一书,就是将系统工程和计算机模型应用于历史研究的尝试。
暂且不论控制论在欧美语境中与信息论、系统论和运筹学的包含关系,仅就中国的科学话语而言,可以看到它们被统合在「工程学」之下,因此也便可以理解钱学森为1983年修订版《工程控制论》新作的序言。在这样的语境中,控制论始终保留了其核心知识,没有向外做过多的耗散。这部分核心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流入控制理论(control theory)和自动化等工程学科,与逐渐发展为认知科学与哲学话语的控制论(cybernetics)渐行渐远。
控制论与预测治理
控制论与预测治理
在应用层面,「工程」的视角反而让更容易使人意识到控制论在「预测」和「治理」方面的效用。随着计算机等数字化技术的发展,工程学(控制论)的方法得以应用于参数更为复杂的社会治理领域。
1978年5月,第七届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IFAC)世界大会在赫尔辛基举办,宋健与陈翰馥、杨嘉墀等中国专家组团前往。荷兰数学家惠伯特·夸克纳克(Huibert Kwakernaak)关于控制理论在人口政策中的应用引起了宋健的注意。归国后,宋健着手应用系统工程的理念研究「人口系统的反馈机制」,依托国家数据库建立综合自然资源、社会经济、生活水平和生态平衡的人口系统数学模型。根据该模型的计算,如果在2000年可以达到1.7的最优整体出生率(即平均每个家庭生育1.7名子女,宋健认为这是唯一的可控参数),那么全国总人口将有可能在2100年达到7亿的最优数量(宋健,1989)。这个结论直接影响了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的推行。
在夸克纳克的论述中,社会心理和经济是实现人口最优控制的两个重要约束条件。这二者无疑都是规模极大的「极度复杂系统」(exceedingly complex system),此类系统组成部分极多、连接关系极复杂、随机性极高以至于无法被完全具体描述(Stafford Beer,1959)。而当时计算机技术的新发展,无疑为此类复杂系统的动力学预测带来了相当的(或许是过度的)信心。
系统科学家杰伊·弗雷斯特(Jay Forrester)1971年为他的著作《世界动力学》(World Dynamics)设计系统动力学模型时候认为,为了预测未来,从世界年鉴(纸质出版物)中获取的数据已足够。然而如今看来,实际问题要比他预想的复杂得多。对如此大尺度高复杂度的系统进行动力学预测,要求数据统计(传感器,sensor)和调控手段(效应器,effectors)的精度和时效性极高。而从延迟和汇总化的数据中只能推导出失真的「未来」,只有大尺度的、分散的和实时的数据才能更有效地实现预测与治理。但由于种种技术和现实原因,不论是人口统计还是其他社会系统的状态,中心化的管理机构都无法获得准确、全面且实时的数据。用控制论的术语来说就是:传感器的失灵会导致效应器无效化。
这里,我们有必要回到维纳关于控制论社会应用的保守表述:
要得到一个好的社会统计,我们需要在基本稳定的条件下长期测量……由于缺少合理可靠的常用数字技术,在确定社会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量的估计值时,专家判断的因素非常大。——Norbert Wiener, 1948
在计算机算力突飞猛进,常用数字技术更为发达的今天,人们对统计与预测的热忱似乎又重新燃起。不得不说,这种通过系统动力学预测并控制未来的想象是控制论如今被重新提起的原因之一,虽然所谓「控制」(control)并非控制论(cyberbetics)最初的愿景。克劳斯·皮亚斯认为,这种「有针对性地控制未来的某些方面来控制未来」的「幻想般的过度信念」,是「控制论的持久遗产」。
技术作为一枚棱镜,总能折射出不同社会文化背景下的观念光谱。其中的个体不论担忧抑或激动,皆因身处于浪潮之中。而这浪潮本身,亦将新技术推向它自身未曾设想的方向。
无论如何,我们已经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审视控制论了。面对这门通信、控制和统计学视角下关于复杂系统的的动力学,固然需要像维纳一样忧虑于其过度工具化后产生的道德伦理问题,但同等重要的是再次聚焦于控制论的核心知识,在严格的科学范畴内了解系统、自适应和控制等概念在新技术条件下的含义与关联。
本文最后原本是一个福利:《控制科学前沿理论与方法》系列课程的免费听课名额。该课程主要内容为对控制论核心思想、框架与方法的深度科普,由集智学园联合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多位控制科学与工程领域专家共同开设。课程适用对象为「对复杂系统的行为和控制机制感兴趣的跨领域研究者」,「学习电气工程、机械工程、自动化、计算机科学等工程和科学领域的学生」和「从事自动化与控制的工程师」。需要学生有一定线性代数、微积分和概率论等数学基础。
在机核就不放抽奖链接啦,感兴趣的机组成员可以移步「大目妖」公众号参与。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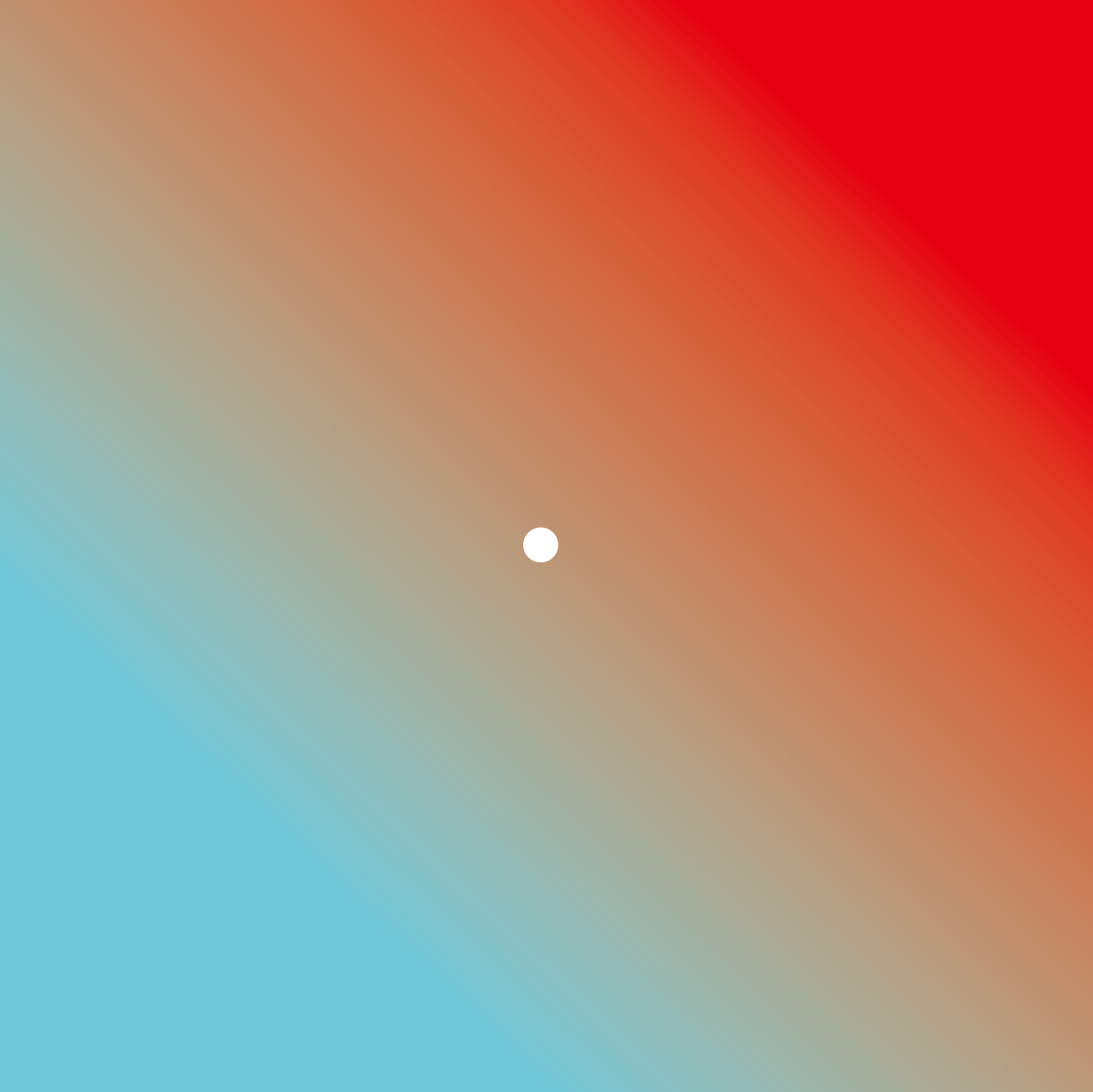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