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本文是温贝托·马图拉纳为《技术形态学》(Technomorphica)文集撰写的文章,该书1997年出版,收录了14篇文章,探讨共同的主题「基于智能机器模式的有机体重组是否会成为我们时代的主导进程?进化是否已经进入人类自身适应技术,而非自然发展的阶段?」
编者乔克·布劳威尔(Joke Brouwer)和卡拉·霍肯迪克(Carla Hoekendijk)邀请了14位不同领域的作家学者,除了智利生物学家和哲学家温贝托·马图拉纳之外,还有法国文化理论家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德国计算机学家克斯廷·道滕汉(Kerstin Dautenhahn)、法国动物系统学家路易斯·贝克(Louis Bec)、荷兰建筑师拉尔斯·斯伯伊布里克(Lars Spuybroek)等人。他们从不同角度就生物与技术融合的边界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
马图拉纳的文章《元设计》(Metadesign)是文集的最后一篇,却似乎否定了该书的命题。他认为,生物体与其生理/心理环境之间递归影响造就了如今这个人类世界与技术时代,虽然技术、知识和进步在其中的角色愈发重要,但人类的核心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人类如何面对自身的情感、欲望和责任。
马图拉纳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到「爱的现象」(the phenomenon of love),便是强调「爱」这种让人类得以共存的重要情感。因为人永远置身事内,永远在互感(consensual)、在与其他实体的关联中存在,而语言则提供了对此进行递归反思的可能。马图拉纳的学生与合作者弗朗西斯科·瓦雷拉延续并发展了这一观点,瓦雷拉在其生涯晚期强调理性的局限性,并关注直接生命经验。
本文共7节,其中1-3节是马图拉纳对自己从「自创生」以来的观点的概述,作为后半段观点的铺垫。更切文集主题的核心表述从第4节「技术与现实」开始。如果觉得译文晦涩冗长,可以直接阅读第4节。此外读者可以阅读本号译介的马图拉纳早期文章《自创生与认知:生命的实现》,更充分地了解他的思想。
最后,这篇文章用马图拉纳的话来说,也是一篇「宇宙论」。马图拉纳在其中所传达的人本主义关怀,可谓是他作为控制论者的返璞归真——一种源于技术却超越技术进步主义的对人的关切。
大目妖 2024年10月23日
温贝托·R.马图拉纳 Humberto R. Maturana
温贝托·R.马图拉纳 Humberto R. Maturana
1928年9月14日-2021年5月6日,智利生物学家与哲学家,同时也与海因茨·冯·福斯特等人同样被认为是二阶控制论社群的成员。他在1960年创办了智利大学认知生物实验室,并在皮诺切特政变后坚持留在智利大学进行教学工作。马图拉纳的研究涉及生物学、神经科学、语言学、控制论和系统论等领域。他与J·莱特文,W·S·麦卡洛克和W·皮茨共同完成了一系列重要文章,为认知科学和神经生理学,甚至神经网络都奠定了重要基础。他基于实验提出了神经科学的认识论关联,并将其工作延伸到哲学、认知科学甚至家庭治疗。马图拉纳还提出了认知生物学,创造了「自创生」(Autopoiesis)理论。他的学生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继承了他的思想,发展出了具身心智(Embodied Mind)等理论。
以下为正文部分,共约14,500字
元设计 Metadesign
元设计 Metadesign
温贝托·马图拉纳
Technomorphica, Joke Brouwer,Carla Hoekendijk (1997)
人类 VS 机器,还是作为人类设计工具的机器?
这两个问题的答案早在几年前就显而易见了:机器当然是人类设计的工具!但如今,当我们大谈进步、科学和技术,似乎它们本身就是值得崇敬的价值时,却有许多人认为,机器在人类的设计下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智能,甚至它们可能会变得有生命,从而取代我们,这是人类崇敬的智能进步与扩展的自然结果。此外,许多人似乎认为,进化的本质正在改变,因此技术正在成为与我们相关的宇宙变化流中的主导力量。
我不认同这种观点。我不认为进步、科学或技术本身就是价值,也不认为生物或宇宙进化的本质或特征正在改变。我认为,人类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们希望自己身上发生什么,而非关乎知识或进步。我们必须面对的问题不是生物学与技术的关系,不是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也不是知识与现实的关系,甚至不是元设计*是否塑造了我们的大脑。我认为,我们在这个历史时刻必须面对的问题是我们的欲望,以及我们是否愿意为其负责。
*元设计,metadesign,出自保罗·维利里奥,智技术对人类大脑的重新塑造,后文会提到。
我想谈谈这个问题,但在此之前我想先谈谈生命系统、人类、技术、现实、机器人、设计和艺术,以此作为我最后要谈的欲望与责任的总体基础。让我们继续。
01 生命系统 Living systems
01 生命系统 Living systems
- 存在条件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生命系统是结构决定型系统(structure determined systems),也就是说,它们是这样的系统:任何瞬间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取决于它们的结构(即它们在该瞬间是如何形成的)。任何作用于结构决定型系统的介质(agent)只会引发系统的结构变化。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日常生活中得知。此外,结构决定论(structural determinism)是我们从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和一致性中抽象出来的,因为我们用日常生活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来解释其自身。所以结构决定论的概念所反映的是,我们不使用独立现实的任何超验层面来解释生活的规律性和一致性,恰恰是生活的这些特性解释了它自己。
我们的确经常说,似乎我们看到的外部介质对系统的影响确实决定了系统中发生的事情,但同时我们也知道事实并非如此。此外,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也知道,当我们聆听他人时,尽管我们听到的声音由他或她发出,但其实我们真正听到的发生在我们内部,而非出自他人之口。毫无疑问,我们倾向于认为对方能听进去我们所说的话,但这通常不会发生,除非双方彼此递归互动的时间足够长,以至于在结构上变得一致,从而使双方能够通过彼此交谈而做出一致的行为。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理解了彼此。结构决定论是我们存在的基本特征,甚至连天主教会也承认这一点,并将违反结构决定论的事件视为奇迹。
从这个意义上说,生命系统就是机器。然而,它们又是一种特殊的机器:它们是以闭环分子生产网络(closed networks of molecular productions)的方式运行(operate)的分子机器,分子产生自网络内的相互作用,并进一步地产生分子网络,这种网络即是生产分子自身并在任何瞬间指定其扩展的网络。在与弗朗西斯科·瓦雷拉(Francisco Varela)合著的《知识之树》(The tree of Knowledge)一书中,我把这种系统称为自创生系统(autopoietic systems)。生命系统就是分子自创生系统。作为分子系统,生命系统向物质和能量流开放。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生命系统是在其动态状态中形成闭环的系统,只有当它们的所有结构变化都保持了其自创生时,它们才是有生命的系统。也就是说,当一个生命系统的结构变化无法保持其自创生时,该系统就会死亡。
生命系统具有可塑性结构,系统在存活过程中的结构变化进程取决于其自身结构变化的内部动力。同时,系统都存在于媒质(medium)之中,它们在媒质中的相互作用引发的结构变化又调节了系统的内部动力。这即是说,只有当一个生命系统在媒质中沿着相互作用的路径滑移,并且这所引发的结构变化保持了系统的自创生(系统生命)的时候,该系统才会保持生命活力。而且这还意味着,在观察者看来,当一个生命系统存活时,它和其所处环境是共同地合谐变化着的。事实上,这是结构决定型系统的一个一般条件:对于一个特定的结构决定型系统和它在递归互动中所处的媒质,两者的运行一致性(operational congruence)以及该系统的特性(即它的决定性组织)的保持,不仅是此类系统自发产生与保持的条件,而且也是它实存于媒质中的递归互动的系统结果,系统的决定性组织在过程中得以留存。
- 存在领域 Domains of existence
生命系统存在于两个运行领域(operational domains)之中:其一是生命系统的构成领域,即生命系统的自创生存在,确切地说是一个闭环分子生产网络的运行领域;其二是生命系统在递归互动中作为整体产生和存在的领域或媒质。第一个领域是观察者从解剖学和生理学角度看到的,第二个领域是观察者将它们辨别为有机体或生命系统的领域。这两个领域并不相交,尽管生命系统作为一个自创生系统,由一个有界(整体)或单一(离散)的整体构成,这使另一个作为此类实体运行的领域成为可能,但这也无法从由一个领域推出另一个。也就是说,由于生命系统(或一般的复合实体)的两种存在领域并不相交,因此它们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或可被观察者称之为因果的关系。两种领域之间存在互促式(reciprocal)生成关系,观察者在识别其中发生的操作、现象或过程之间的动态关联时,可以看到这些关系。观察者所看到的是,生命系统的构成领域(解剖学和生理学)的结构变化导致其作为一个整体的动态构型(dynamic configuration)发生变化,从而导致其与媒质相互作用的方式发生变化,而生命系统与媒质的相互作用又反过来引发其构成领域的结构变化,进而导致生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的构型发生变化……实际上,我在上一节中已经描述了这种动态及其对一般复合实体(系统)的构成和留存的一些影响。
作为整体或总体的生命系统同时也被我们辨别为那种特殊的离散或单一实体,它们所在的运行领域同时也是每个系统在实现其生命的过程中所处的领域。在我就生命系统的存在说了这么多之后,以上情况中最根本的一点在于,在生命系统中发生或作用于其上的一切,在运行上都从属于其生活方式的留存,而这种留存又在其作为整体或总体运行的领域中定义和实现了系统自身。或者换言之,生命系统的自创生实际发生的身体实存是该系统的可能性条件,但其构成和持续实现的方式本身又不断受到领域中的生命流的调节,生命系统在其中作为整体运行。例如,在这一运行领域中,大象作为大象而存在,我们人类作为人类而存在。因此,身体实存和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方式在本质上是动态交错的;因此两者缺一不可,并在生命的流动中相互调节。身体根据生命系统(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方式而变化,而有机体作为一个整体的运行方式则取决于身体实存(bodyhood)的运行方式。
- 媒质 The medium
媒质作为一个整体运行系统的空间,尽管它通过与其包含的系统交会而受到调节,但它与这些系统的结构动力是相互独立的。因此,媒质和其中的系统都处于持续的结构变化之中,每个系统都依据其自己的结构动力,并且都被它们通过递归交会彼此引发的结构变化所调节。在这种情况下,所有与生命系统相互作用的系统都构成了该生命系统的媒质。此外,根据上述互促式交互的递归动力,所有处于递归互动中的系统都会发生一致的变化。
02 人类 Human beings
02 人类 Human beings
- 使用语言 Languaging
作为生命系统的人类是结构决定型系统,所有适用于此类系统的也适用于我们。不过,人类的特殊之处在于我们存在于语言这个运行空间(operational space)中,我们在其中意识到自己的生命。也就是说,我们存在于共同生活的流程中,语言就是行为的递归协调(recursive coordinations of behavior)。请让我就此展开。
语言是一种共同生活的方式,是协调互感行为*(coordinations of consensual behaviors)的互感协调流,因此也是协调行为的协调领域。所以,我们人类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语言中进行的。因此,为了协调我们的语言行为,语言中出现了对象(objects);为了协调我们的语言行为之中不同的行为领域,语言中产生了我们所生活的不同世界;我们生活中不同种类的人类活动(无论是具体的还是抽象的,操作性的还是想象的,实践的还是理论的),它们处于不同的行为领域,这些领域是一种对行为协调进行协调的互感领域,而其中的行为协调又出现在我们语言生活中的不同行为领域。所以,使用语言是我们作为人类而存在的方式。
*互感行为,consensual behaviors:即双方都同意且默认的行为。
与此同时,我们的身体实存则是会使用语言的灵长动物,它既是我们作为语言性存在的可能性条件,也是我们所属的语言生活的特殊进化史的结果。这段历史应该始于300多万年前,当时我们生活在互感的行为协调中,而这又通过孩子们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来。在生物学层面,我们300万年前的祖先与我们现在非常相似,但他们生活在不同的世界,拥有不同的大脑。生物进化史这样定义一个世系(lineage):世世代代保持着一种不变的生活方式或方法,而其他一切都会随着代际更替而变化。我们这一世系形成于语言生活的留存之中,我们祖先的身体在过程中发生了变化,他们生活的世界也随之改变。因此,我们现在的身体实存和生活,都是始于300万年前的语言生活史的结果。但不止如此。
当我们的祖先开始生活在语言之中时,他们的语言生活交织着他们的情感流动。在语言互感行为的递归协调(recursive coordinations of consensual behaviors of language)之前,我们的祖先和所有不使用语言的动物一样,通过互感和与生俱来的情感来协调自己的行为。当我们声称我们在其他人类、非语言动物或我们自己身上分辨出一种情感时,我们所指的是自己或他者所处的关联式行为领域(the domain of relational behaviors)。也就是说,我们在他人或自己身上看到的是可能产生的关联式行为,而不是任何特定行为。因此,在我们的情感流动中(即在我们的情绪表达中),我们从一种或一类关联式行为转向另一种或一类。如果我们改变情感,我们就会从一类关联式行为转向另一类。此外,大多数动物都是在与个体生活的互动中学习如何表达自己的情感,如果它们生活在一个社群的反复互动中,它们就会学习其情感流动方式,并将其作为互感生活的一个特征。非语言动物通过与生俱来的或互感的情感表达来协调它们的行为。我把语言和情感的互感编织称为会话(conversation)。
人性始于世代相传、以语言为基本关联式特征的生活,这定义了我们的世系,而其真正的开端则是会话中生活的隔代留存。人类生活在会话之中,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会话网络中进行,该网络由情感的互感编织和协调互感行为的协调所构成。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就是一种闭环的会话网络(culture is a closed network of conversations ),由生活在其中的孩子们学习并保持。相应的,作为人类,我们生活的世界产生于我们的会话之中,即协调互感行为和情感的特殊互感协调领域。而在我们生活中保留的任何初始会话构型,从此都会变成我们生活的世界,或其中之一。这就是我们人类历史上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此外,在这一历史进程中,我们生活在每一个世界的留存之中,仿佛它是我们存在的基础。我们在一种留存的动态中如此生活,其结果是我们的一切都开始围绕着被留存的世界所带来的被留存的生活方式而改变。
但是,在我们生活的不同世界里,我们作为人所需要的东西并没有太大差别。区别在于我们在每个世界中成为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会随着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成为这样或那样的人。
- 特性 Identity
将一个系统定义为一种特定类型系统的那种特性,并非系统的固有特征。系统与包含它的媒质的递归互动作为一个整体而运行,系统特性作为一种运行方式在其中被构成并保持。系统特性的构成和保持是经由系统与媒质元素的递归互动而发生的动态系统现象。而且,当定义系统关联和互动的构型开始得到系统性保持时,系统就产生了,这种保持得益于系统在其所处媒质中的相同互动,以上过程我称之为自发组织(spontaneous organization)。与此同时,系统内部结构变化的流动将从属于系统整体运行的保持,正如我在上文谈到人类起源时所描述的那样。在生命系统世代相传的流动中,某一特定世系成员的内部结构(身体实存)越来越从属于该世系所保持的特性。
对人类来说,我们生活的文化构成了我们得以为人的媒质,人的特性在我们文化的历史进程中产生并保持,我们的身体实存也依此而发生转变。但与此同时,作为生活在会话中的人类,我们是反思性的存在,可以意识到自己的生活方式,意识到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当我们有所意识之时,我们就可以根据自己的美学偏好来选择生活方式,并根据我们希望保持的人类特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生活。因此,在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文化的会话网络所界定的系统动力中,我们的人类特性得以构成和保持。根据我们生活并保持的文化,我们可以是现代人(Homo sapiens sapiens)、友爱人(Homo sapiens amans,即作为爱的主体的人)、侵略人(Homo sapiens aggressans)或傲慢人(Homo sapiens arroggans)*,但与此同时,随着文化的改变,我们也可能不再是这样或那样的人,这取决于我们赋予文化的特定特征的情感构型。
*这几个概念是温贝托·马图拉纳在《爱在生物学中的人类起源》 (The Origin of Humanness in the Biology of Love)一书中提出的分类法。他在提出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将爱的留存作为合作的基本领域,通过相互尊重、关心、接受和信任等情感表达的智人被称为Homo sapiens amans,而以竞争和侵略做情感表达的智人则是Homo sapiens aggressans或Homo sapiens arroggans。
- 情感与理性 Emotions and rationality
如上所述,情感是一种关联式行为。因此,我们的情感时刻指导着我们的行为,它指明了我们在任何瞬间所处的关联领域,并让我们的所作所为具有行动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人类身份的,正是我们作为智人的情感构型,而不是我们的理性行为或对某种技术的使用。当我们的祖先在日常生活中使用抽象连贯的语言时,理性行为就开始成为他们生活的一个特征。但那时和现在一样,情感明确了他们在任何瞬间的理性行为领域。只是我们的祖先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但现在我们知道,每个理性领域都建立在被接受的基本前提之上,也就是说建立在情感基础之上,是我们的情感决定了作为理性存在的我们在任何瞬间所处的理性领域。同样,根据我们的行为目标,我们使用不同的技术作为不同的运行连贯性领域(domains of operational coherences),也就是说,我们会根据自身的偏好或欲望而使用不同的技术。如此一来,尽管我们说得好像技术而非欲望决定了我们的行为,但真正引导着我们的技术生活的是我们的情感,而非技术本身。我认为,我们可以从祖先的技术史中看到这一点。事实上,我认为,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祖先几千年来一直在使用不同的技术规程(technological procedures),这种技术演变与他们的欲望、品味或美学偏好的变化有关,无论他们此后的生活方式如何变化。
我们的理性生活中会发生两件事。一种情况是,我们用理智来支持或掩饰我们的情感,我们经常如此却意识不到。另一种情况是,我们通常无法充分意识到自己是在什么样的情感下选择不同的理性论点的。其结果就是,即使我们声称自己是理性的,也很少意识到是情感在引导着我们的生活。
而且,由于我们不了解自己所作所为的情感基础,所以便会囿于一种信念,即人类的冲突与难题都是理性的,因而必须通过理性来解决;我们还囿于另一种信念,即情感破坏了理性,它是人类生活中无序和混乱的根源。长此以往,我们便无法理解自身的文化存在。
- 神经系统 The nervous system
通常来说,神经系统是一个由相互作用的元件组成的闭环网络,它以活动关系不断变化的方式运行,并在感觉区和效应区与更大的系统发生结构性交会,通过这些交会,神经系统在同一种媒质中相互作用,并成为一个动态的整体。在多细胞动物中,我们通常会发现神经系统是由神经元元件组成的闭环网络,其中一些元件在结构上与动物的感觉和效应表面相交。我把这种神经系统称为神经元神经系统。而原生动物等单细胞生物系统则具有分子神经系统。现在,让我从神经元神经系统的一般角度来描述神经系统的构成方式的运行性结果。
- 神经系统是一个由活跃的神经元元件组成的闭环网络,这些神经元元件之间相互作用,网络中某一部分神经元之间活动关系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其他部分的活动关系的变化。此外,在神经系统的运行过程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这种变化,这由神经系统的整体细胞和分子结构(结构连接性、神经元膜的特征等)所决定。
- 神经系统作为多细胞生物系统的组成部分之一,在结构上与后者的感觉和效应表面的感应器和效应器相交。因此,多细胞有机体的感应器和效应器具有双重特性,它们既是有机体的构成要素,又是神经系统的构成要素。然而,它们的工作方式不会混淆,在分别作为有机体和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工作时,它们的工作方式是不同的。因此,作为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时,「感应器 」和 「效应器 」在有机体的存在领域中相互作用,而作为神经系统的组成部分时,它们作为其他神经元元件的活动关系的闭环动态变化而运作。这种情况的基本结果是,有机体与媒质相互作用,但神经系统却并非如此。
- 有机体和神经系统在运行上存在于不同的非交叉领域:有机体处于生命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领域(例如大象和人);神经系统则存在于一个闭环神经元网络之中,即一个活动关系变化的闭环网络的领域。这两个领域之间的相互关系或联系发生在感觉和效应元件上,有机体和神经系统在两者之上发生结构性交会。在感觉元件那里发生的是:a) 有机体在其感觉表面与媒质相遇,b) 这种相遇会引发有机体感觉元件的结构变化,继而会引发与之相交的神经元元件的结构变化,最后,c) 这些结构变化会导致这些神经元改变参与以下变化的方式,即作为神经系统组成部分的闭环动态变化活动关系。而在效应器表面发生的则是:a) 当效应元件被与其相交的神经元元件改变活动状态时,它们会引发结构变化, b) 媒质的结构构型会被其中的有机体的相互作用所改变。
- 神经系统作为一个闭环神经元网络,它唯一做的就是在组成它的神经元元件之间产生活动关系的变化。也就是说,神经系统的运行并不涉及关于媒质的信息或表征。神经系统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一切就是在其中产生感觉/效应相关性,这使得有机体在其与媒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产生行为。此外,神经系统产生的感觉/效应相关性会随着神经系统活动流的变化而变化,神经系统活动流也会随着自身结构的变化而变化。
- 神经系统的结构并非固定不变,它以下述方式不断变化着:a) 在神经元元件层面,神经系统通过两种方式与有机体内部和外部的感应器相交,一是有机体在外部媒质中的相互作用,二是外部媒质之内的生物活动成为前者的内部媒质;b) 通过神经系统的神经元组件的结构变化,这种变化也以两种方式产生,一是有机体内分泌细胞所分泌的激素,二是由其他神经元元件作为神经内分泌细胞运作; c) 神经元组件因参与神经系统运行而引发了递归结构变化,这使神经系统成为了一个活动关系不断变化的闭环网络;以及 d) 作为神经系统内在生长和分化结构动态的结果。
神经系统运行的结构和动态方面的基本结果是:虽然神经系统不与媒质发生相互作用,但其结构却遵循着一条变化的路径,该路径与有机体在实现和保持其生命过程中的互动流相一致。这导致了另一个结果,尽管神经系统作为有机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产生连续不断的感觉/效应相关性,这使有机体在其存在领域内以其结构所决定的方式产生适当的行为,但神经系统在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就是如此,因为它的变化方式取决于有机体生命的实现方式。我把这种有机体和媒质的连贯结构变化的历史动态及其动态结构一致性的状态称为结构耦合(structural coupling)。
鉴于神经系统的运行方式,因此在其中发生的一切都是同类过程,即神经元活动关系的动态变化。在神经系统的运行中,尽管走路和谈论一朵花的名字是神经元活动变化关系的不同流动,最终会产生不同的感觉效应相关性,但它们属于同类过程。然而,走路和谈论一朵花的名字在有机体关联性动态中则是不同的现象,在观察者看来是不同的行为。神经系统因其运行方式而不作用于媒质的表征,同时有机体(包括神经系统)与媒质之间的运行一致性是两者之间结构耦合的结果,而这种耦合又是有机体的进化和个体发生史中结构一致性变化的结果。那么,鉴于有机体与媒质之间的结构动力的特性,因此两者结构性互动的任何维度只要与神经系统的结构变化流相耦合,都可以成为一个感官维度,并扩展有机体的行为空间。
03 有机体与机器人 Organisms and Robots
03 有机体与机器人 Organisms and Robots
无论是作为自然实体的生命系统(有机体),还是作为人类设计产物的机器人,都是结构决定型系统,它们与结构决定型媒质或环境之间存在着动态的运行一致性。 两者之间的区别在于,它们在其起源历史中各自与环境的运行一致性是如何产生的。机器人是通过设计产生的。艺术家或工程师在设计时,会将一组元件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构型安排成一个动态的整体,而这个动态的整体与同样是被设计出来的媒质是动态一致的。因此,机器人及其运行的媒质或环境,以及两者之间的动态一致性,都是在没有历史背景的过程中有意设计的结果。所以机器人是无历史性的实体。然而,由于它们是试图在未来获得某种运行结果的产物,因此它们存在于历史领域之中。
生命系统有不同的起源方式。现在地球上的所有生命系统,都是仍在延续的生命系统的世系产生史的产物,这种延续依靠的是生命的生殖留存和生命实现方式的变异。这一历史进程就是通常所说的生物进化或种系发生进化(philogenic evolution)。根据上文谈到结构决定论时所说的,这一历史过程中的生命系统和它们所处的环境共同发生了一致的变化,因此它们在实现自己的生活时,总是自发地发现自己与媒质在动态上是一致的。生命系统就是历史性系统。尽管如此,它们是以种系发生进化的方式存在的,因为它们存在于与和自身同步变化的生活环境中,所以它们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当下之中。
生命系统之所以不同于机器人,是因为它们具有历史性,而不是因为它们是分子自创生系统。机器人的起源是非历史性的,这才是它们与生命系统的本质区别,而不仅仅是因为它们并非自创生系统。而且由于生命系统是分子系统,所以如果尊重生命系统构成的运行一致性,它们就可以像任何其他分子系统一样被操控。
我们生命系统是结构决定型系统。只要我们愿意,这会是我们获得幸福的可能;但如果我们漫不经心且不负责任地对待自身的境况(存在于不断变化的当下的历史性存在),这也会是我们的痛苦之源。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本文的核心观点。
04 技术与现实 Technology and reality
04 技术与现实 Technology and reality
- 技术 Technology
技术的运作依照的是人类可能参与的不同行为领域的结构一致性。因此,技术既是一种有效开展意图性行动的工具,也是一种为生活方式提供合理性或导向的价值取向,在这种生活方式中,一切都从属于经由实践获得的愉悦。当以这种方式生活时,技术就成了一种瘾癖,成瘾者希望通过理性论证来证明其合理性,而这种论证本身就建立在现代技术大发展的历史现实基础之上。
技术作为一种有效行动的工具,逐步扩展了我们在所有领域的运行能力,让我们对这些领域的结构一致性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生物技术就是这种扩展产生递归结果的一个例子。生物技术的扩展导致了对生命系统的认识的扩展,而反过来,对于作为结构决定型系统的生命系统来说,对其认识的扩展又导致了生物技术的扩展。然而我们对作为系统的生命系统的认识并未因此而扩展,我们对作为人类的自身的认识也是如此。另一方面,生物技术的发展与对基因决定的还原论或明或暗的信念交织在一起,而且我们沉浸在一种商业文化之中,它渗入精神存在各个层面,遮蔽了我们将自己视为具有系统特性的生命体的视角,而我们本可以根据自己的生活方式成为这样或那样的存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代人生活在两种基本且具有穿透力的文化启示之中,一种是市场将一切合理化,另一种认为进步是一种超越人类存在的价值。这表现为我们现代人所做的一切实际上都以其市场价值为依据,同时我们的言行举止就好像我们被一种必须服从的进步潮流所引导。
例如,现在有很多关于拟人化机器设计的工作和研究,很多人认为,人类应该适应进化迈入技术科学阶段的时代,并将进化视为一个进程,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它都会伴随着我们。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必须屈服于一种宇宙力量,在这种力量中,我们无关紧要且终将消失?我们是什么?
关于人类生存的技术形态化趋势(technomorphisation),即按照智能机器的模式重组有机体的趋势,已经有很多论述。 之所以如此,可能是因为在技术和科学似乎大获全胜的情况下,人们的信心正在消失,我们不再相信机器无法实现那些曾被认为是人类应有的东西,诸如灵魂、精神、自主思想、自我意识的条件等。在邀请撰写本文的信函中写道:「保罗·维利里洛(Paul Virilo)认为,适应电子媒体而形成的新大脑框架(元设计metadesign),比旧结构更能深入人类的神经过程(关联性过程?)。元设计让活体的神经传输冲动再生,从而创造出一种认知人体工程学。其结果是在人与机器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麻痹关系。元设计的方法使人类行为基础设施变得迟钝。」但是,在这一切中,我们这些有责任感的人类个体又在哪里呢?我们可以如此轻易地被其他人类操纵,只是因为他们声称在开发机器力量中取得了进步,并同时满足了他们的野心、欲望或幻想?
毫无疑问,作为结构决定型系统,我们经由自己的结构动态而存在。 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作为结构决定型的动态系统,我们存在于持续的结构变化之中,而且我们的结构可以被有意操纵,以便在生活中获得某些预期的结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是机器,分子机器。 但是人类的存在与特性并非产生于我们的结构之中,而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于关联性空间之中。 这句话适用于任何机器。如上所述,人类作为系统实体存在于持续发生结构变化的关联性空间之中。 此外,只有当我们参与到产生自身的系统动态中,并通过与其他人类共同生活来保持自身作为人类的存在的时候,我们才得以成为人类(现代人或侵略人)。 我们在生活中成为的那种人类,并非由基因或其他方面所注定。
我们以一种系统的方式生活,这使我们得以成为我们,并保持这种存在。此外,我们认为自己是什么,递归地构成了系统动态的一部分,我们在其中成为并保持着自己的特性。不仅如此,由于我们的所思所想构成了会话网络的一部分,而这又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因此在我们使用语言的流动中,我们的情感和行为交织塑造了我们自身。因此,既然我们的情感指明了我们在任何一瞬间所处的关联领域,那么决定了个体的生活轨迹以及我们的文化历史进程的,正是我们的情感而非理性。然而情感在定义历史进程中起到的核心作用,并非我们这种文化性存在所特有。事实上,进化过程的本质就是通过对生活方式的生殖留存来形成世系,而生活方式则被有机体的关联性偏好或选择所决定。生物进化并没有随着技术和科学的发展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但人类的进化却越发取决于我们的选择——面对科技带来的愉悦和恐惧时到底是享受还是厌恶。
这就是为何「我们想要什么」才是核心问题,而非关乎技术或现实。
因此,既然我们是结构决定型系统,那么只要尊重我们所在的结构领域应有的结构一致性,我们就可以接受任何结构性的操纵。或者,同样的说法可以用更笼统也更耸人听闻的方式表述:如果我们的设计尊重其所在领域的结构一致性,那么我们选择设计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实现。
- 现实 Reality
现实这个概念在不断变化,但我们的生活却没有随之改变。现实是一个命题,我们用它来解释我们的经验。而且我们会根据自己的情感以不同的方式使用它。这就是为什么在不同的文化或历史时期会有不同的现实概念。然而,即便不使用「真实」一词作为论点,我们也在以同样的方式将其作为我们经验有效性的基础,也就是说,我们将「真实」视为经验的在场。我看到了,……我听到了,……我触摸到了,…… 诚然这就是为何我认为人类无法仅凭经验区分出所谓的日常生活的感觉和幻觉,这是我们这种结构决定型系统存在的一种基本情况。我们对感觉和幻觉的区分是后验的:当面对两种经验,且其中一种被认为是有效的时候,我们就会在比较中贬低另一种经验的价值。但我们不知道的是,此时有效的经验的价值,以后是否会因为与第三种经验比较而被贬低。实际上,这就是虚拟现实被称为现实的原因。没错,我们现在说虚拟现实因为与现代科技相关联而具有特殊性,其设计涉及诸多感官维度,理想情况下是所有可能的维度。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所谓的真实,也正是虚拟现实所虚拟的,它们正是那些被我们当做基础参照物的经验,用以解释其他经验。两种经验在我们的生活流程中同等真实,但我们却想要贬低后者的价值。
我们的人类生命发生在关联性动态中,生活在其中的我们是会话中的语言性存在。正因为我们生活在会话中,所以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就发生在持续产生的行为协调域中,这些领域漂浮在我们作为生物实体的生命的留存之上,发生在人类现实不断变化的流动之中。这种流动之所以可能,原因仅仅在于我们的生物生命能够留存,而与其留存方式无关。这种历史动态以下述方式发生:倘若我们存在的生物学具现不受到直接干扰,它就会持续的从视野中消失,成为人类日常运行的无形背景。因此,自从祖先开始在会话中生活时,我们作为人类的历史就已经开始了新现实的递归创造。相对于我们作为生物性存在的基础现实而言,这些新现实都是虚拟的,但它们与基础生物性生命的存在结合,从而成为了某种新虚拟现实的基础,而这又使其在人类生活流中变得真实(非虚拟)。因此,我们应该关心的(如果我们想的话)是我们对人类存在有何要求?我们希望人性遵循怎样的轨迹?
现实不仅仅是一种解释人类经验的方式,它还是我们作为人类生活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现实不是能量,不是信息——无论这些概念多么有力地解释了我们的经验。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及其一致性来解释经验本身。也就是说,我们用自己的生活来解释生活本身,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人类构成了自身认知领域中所有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事物的基础。
- 基础现实的扩展 Expansions of basic reality
不同种类的生命系统在进化史中发生的结构耦合维度的变化,构成了它们所处的基本现实领域的进化转变。设计也可以实现相同的情况,例如有意使用义肢可以为有机体创造新的互动维度,并使其变为新的感觉领域。由于神经系统是一个由不断变化的活动关系组成的闭环网络,因此它在处理其所整合的有机体基础现实的扩展时并不存在内在限制。如果有机体的互动领域由于媒质的某些独立结构变化而扩大,那么神经系统在处理生活中可能出现的新感觉维度方面,同样没有任何内在限制。
如果特定生命系统的生活方式定义了它的种类特性,并且在经过其基础生物现实的转变之后仍得以留存,那么该系统仍属于同一类,只不过是其特定特征以及其所处的关联性空间发生了变化。但是,如果这种生活方式没有被保持,那么此类生命系统就会消失,而新的关联性空间中则会出现一个新生命系统。
- 人类的身体实存 Human bodyhood
爱、精神、我们的意识和自我意识、责任和自主思维是我们作为人类存在的核心,但除此之外还有我们的身体实存。如今的人类身体实存不是随便得来的,它是人类世系成员的身体性转变的历史结果,是在会话中生活的结果。如果现代人制造了一个机器人,它在行为上与我们没有区别,也能表现出精神关怀、自我意识、情感和自主的理性思维,但考虑到其身体实存的历史,它仍然是一个机器人而非人类。在宇宙的历史中,这样的机器人可能会取代我们人类,我们可能会像其他许多已经灭绝的动物物种一样彻底消失,那将是我们的终结,也是人类在宇宙中的终结。这重要吗?对我来说很重要,我不希望它发生!因为我并不认为进步或技术本身就是价值。
人类有可能正在适应医学手段对我们生活中自然过程的干扰,包括器官移植、人造器官或人工胚胎发育等。我们之所以接受这些做法,可能是因为在我们看来,它们并没有改变人类的地位,反而似乎有助于其保持。但与此同时愈发明显的是,在实质上威胁人性的是我们现在所处的商业心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随时准备将自己所做的一切服从于商业,仿佛不论人类历史的洪流中发生什么都无关紧要。在一个商业心理性存在那里,最优先和最根本的关切是商业价值。
但是,这种与人性的身体实存的关系对于人类是否至关重要呢?我认为是的,因为那些使我们得以为人的特征:爱、社会责任、宇宙意识、精神性、道德行为和不断扩展的反思思维……它们是我们人类身体实存的动态特征,在留存了身体实存的关联性人类生活之中产生、被保持、被培养。人性不是某种计算机程序的表达式,运行方式已然被规定;人性是一种关联性的生活方式,它需要以基本的身体实存为基础。我们的许多器官确实都可以替换成人造器官,但只有当后者取代了前者在人类生活具现中的位置之时,它们才能被称为替代品。没错,最终我们有可能制造出和我们行为表现相同的机器人,但这种机器人的历史将与其身体实存相联,而且由于它们这种复合型实体将会和我们处于不同的组件领域,因此它们也将产生不同的基础现实领域。
05 艺术与设计 Art and design
05 艺术与设计 Art and design
艺术产生于设计,而美学体验则产生于我们与周围环境和谐相处时的幸福和喜悦。因此,艺术具有意图、表达或目的的人为性,一切都可以成为实现艺术的手段。如果没有打破艺术的意图或目的,并以此为人类生活带来一些关联性维度或反思机会,那么艺术就会这样存在于它所处文化的精神领域。在我们所处的所有关联领域中,人类都生活在美学体验里。美学体验有其生物基础,而人类生活的一切都属于关联性存在,基于这些事实,艺术与我们的社会存在和技术存在始终交织在一起。
我认为,爱是构成社会性共存的情感。爱作为一种容纳了关联性行为的领域,在其中,一个存在作为合理的他者与另一个存在共存。由于不同的技术打开和关闭了不同的关联性维度,因此它们既为社会性和非社会性的共存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也为艺术家创造他或她想要唤起的关联性体验提供了不同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在各种情况下,无论艺术家做什么,他(她)都将会是某种虚拟现实的参与者和创造者。在人类历史进程中,这种虚拟现实或许会成为基础现实,也或许不会。当然,这并非只有艺术家能做到。无论我们是否意识到自己是作为人类的存在,我们都生活于不断变化的现实之中,我们都是现实的共同创造者,只不过艺术家的处境非常特殊。艺术家是日常生活的诗人。相比与其他人类,艺术家们更多地行动在有意图的设计之中,因此他们对人性历史进程所做的一切通常都非同小可。作为日常生活的诗人,艺术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看到、把握并揭示他们所属的人类社群生活的当下的一致性。
06 欲望与责任 Desires and responsibility
06 欲望与责任 Desires and responsibility
即使我们认为自己总在被迫做一些不喜欢的事,但是人类始终在做他们想做的事。当我们被迫做不喜欢的事的时候,我们更希望看到其后果。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欲望(不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决定了我们的生活轨迹和人类历史进程。我们在生活中希望留存与实际留存的那些东西,决定了我们的生活中哪些能被改变,哪些不能。这同时也是我们经常不愿反思自己的欲望的原因。只有我们对自己的欲望视而不见,那么我们才能面对自己行为的多数结果不负责任地活下去。
艺术家,日常生活的诗人,经常能意识到人类存在所遵循的轨迹。这一点在科幻小说家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他们通过推断我们关联性当下的一致性,展现出一种未来。此外,艺术家们还能经常意识到当前人类关系中缺失的东西,如爱、诚实、社会责任感和相互尊重,但他们展现或唤起这些东西的作品却经常被当作乌托邦而遭到摒弃。在以上两种情况下,艺术家作品的核心并不是媒介,而是他们的意愿。媒介始终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不论对其了解多少我们都能使用它,但能否随心所欲地使用,却始终是一个奉献和美学的问题。然而我所关心的是目的,是艺术家想要唤起的情感。
07 反思 Reflections
07 反思 Reflections
技术变革没有打动我,生物技术没有打动我,互联网也没有打动我。我这么说并非出于傲慢。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运用手头不同的技术方案,我们所做的很多事情都会改变,但除非我们的情感发生变化,否则我们的行动将不会改变。我们生活在一种以支配和服从、不信任和控制、不诚实、商业和贪婪、占有和相互操纵为中心的文化中……除非我们的情感发生变化,否则我们生活中的一切变化都将延续原有的方式,就像在战争、贪婪、不信任、不诚实以及虐待他人和自然中发生的那样。事实上,我们将一如既往。技术无法解决人类的问题,因为人类的问题归属于情感领域,它是关联性生活中的冲突,当我们有欲望时,对立行为就会产生。在我们接触到新技术的那一刻,无论是作为使用者还是观察者,我们如何使用它或从中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是哪种人:友爱人、侵略人或傲慢人。
我们经常说,似乎人类历史的进程独立于与个体之外,我们似乎被自己无法控制的强大力量所推动。但是这种思维方式在多大程度上是有效的呢?我们的生活被自身的情感所引导,因为我们的情感决定了我们行动的关联性领域,进而决定了我们的所作所为。每种文化都被特定的情感构型所定义,这种构型指导着其成员的行动,并通过这些行动以及其成员的孩子对情感构型的学习而得以留存。如果构成和留存这种文化的系统动力被打破,文化也就终结了。因此,我们并没有被困住,关键不在于我们做了什么,而在于背后的情感。引导现代生活的不是技术,而是情感,即对权力、财富或名声的欲求……我们在它们的驱使下使用或发明技术。如果我们尊重所处领域的结构一致性,人类就可以做到任何想象的事情。但我们不必做我们想象的一切,我们可以做出选择,而作为具有社会意识的人类,我们的行为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的大脑并未因技术而改变。技术在保持我们所属的文化(情感构型)之时,它实际上改变的是我们的行为。当然,只有我们在反思使用或思考技术给我们带来的影响时,我们的情感才会发生变化,并同时经历着一场文化变迁。事实上,只要我们愿意回到起点,人类便无需改变大脑就能处理和理解未来可能带来的任何技术变革。大脑所做的就是抽象出自身活动关系的构型,在再加上语言操作,我们就可以把生活中的任何情境都当作一个起点,从此开始递归反思。这个过程实际上可以有任何种复杂度。由于情绪作为一种关联式行为发生在关联性空间中,因此,正是通过文化变迁的留存(如在后代的学习过程中代际留存下来的情绪构型的变化),我们的生物历史进程才可能改变我们大脑。
生物进化并没有改变繁殖性有机体的特性。世系的构成、留存和多样化依靠的是生活方式的系统性留存,该种方式一代又一代的从诞生延续到死亡。文化的进化也是如此。文化是一个闭环的会话网络,通过生活在其中的孩子的学习,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来。因此,如果孩子所学习的闭环会话网络发生变化,那么文化也会随之改变,而新的闭环会话网络则会通过他们的生活一代又一代地保持下来。用常用的系统术语来说就是,一个或一组系统的成员之间的关系中保存下来的东西,决定了这个或这组系统中可以或不可以改变的东西。
生物技术并非一种新实践,尽管相比一百年或五十年前的人类,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已经有相当大的不同。互联网作为一种极具丰富性的网络,与其他方便图书馆和博物馆使用的互动系统并无本质区别。毫无疑问,互联网带来的互联互通比我们一百年或五十年前通过电报、无线电或电话所实现的要多得多。如果我们的欲望没有改变,那么就没有任何实质上的改变,因为我们仍然用互联网按照过去的行动构型(情感)生活。我当然知道在信息流的全球化领域中流传和发生的许多事情,但现实并非由信息构成。我们所生活的现实经由情感构型一刻不停地产生,而这种情感构型又一刻不停地被我们的生活所保持。但是,如果我们知道现实产生自我们的情感,而且我们知道自己知道这一点,我们就能够依此行动——我们对自己生活所带来的现实的喜好或不喜好的意识。也就是说,我们将对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想要一场文化变革,我想要投身于人类的存在领域中的艺术创作,我想要唤起一种共存方式,在其中,爱、相互尊重、诚实和社会责任这些情感构型一刻不停地自发产生于生活中,因为它是由我们在生活中所共同创造的。我们不能将这些情感构型强加于人,也不能一味地要求别人的认同,它必须理所当然的自发生长,只因我们在童年时代便已学会如此生活。对它的违背将是可以改正的合理错误,因为错误仅仅是错误而已,它本质上并不可耻。倘若我们的生活真的发生了这样的文化变革,那么最引人注意之处就在于, 随之而来的情感构型会自然而然地出现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已然生活在产生它的生活方式之中。此外,如果我们的孩子因我们而生活在其中,那么这种情感构型就会成为我们的文化生活方式代代相传。诚然,这正是每个人在追求物质与精神幸福过程中想要的生活方式。这是乌托邦吗?是的,因为与之对应的那种生活方式已然存在于我们的进化史之中,而且多数人都知道它是我们童年时代的一种经历或向往。无论如何,如果我们想作为友爱人(Homo sapiens amans)去生活,那么依照此种方式去生活,将是一件伟大的动态艺术作品,也是一种负责任的创造行为,这是毫无疑问的。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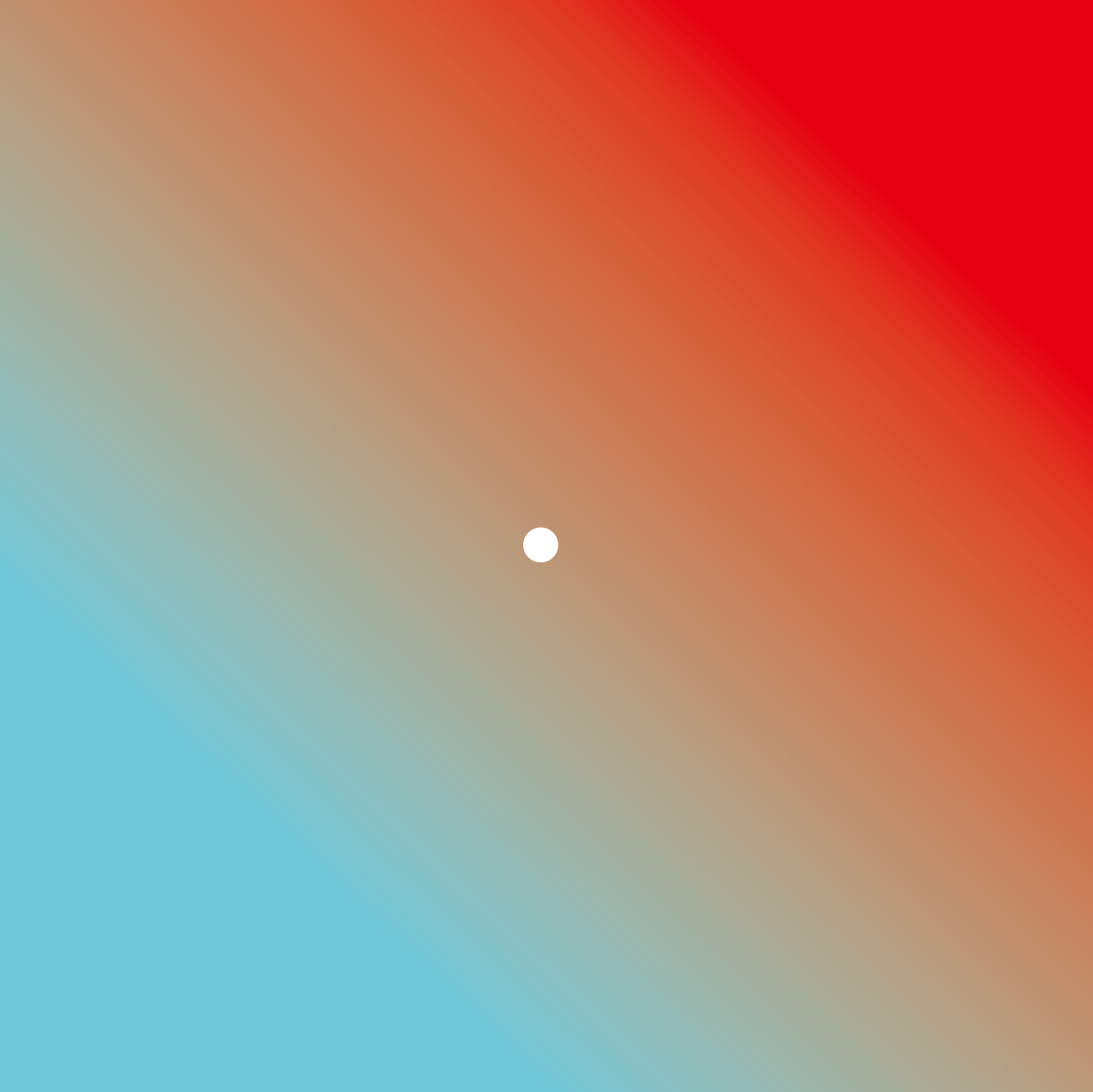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