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上世纪末,在中国西南的一个偏远乡村中,曾发生过一个凄美的故事。石子投入潭中,雪花落到泥里,时光如水流逝,故事的原貌已无从寻摸,但仍有几处边角,在当地村民的口口相传与缠绵想象中,反射出些微细碎的遗痕……
那村寨照例只是一个普通的村寨,西南多高大伟岸的山峦,山势挺拔,沟险涧深,难得在一处夹山遇水的所在,得到一块稍宽敞的平原,安置一座祥和平静的村庄。
这村庄,嘉树四合,水流潺潺,岁月静长。那是一个晚春时节,村寨中,土坡山岗上草木花朵饱饱地喝了整一个春天的雨水,晒足了黄灿灿的温暖日光,都在蓝蓝天空下懒懒伸腰。这时节的村寨,人不论站在何处,望向何方,只要有心,无处不能见到活泼妩媚的风光。
空气中,嗅得到晨露湿气、泥土腥气、昆虫气味、牛羊粪便气味,混杂着草香,叫人发晕;山坡上,听得到牛颈上铜铎庄严沉静的声音,放羊人吆喝声,孩童追逐嬉闹声,屋前溪流,跌着清亮细碎音符,快乐地歌唱下坡。
寨子里,一切事物都仿佛挥发着快乐迷人酒气,却在某处不起眼的一隅,独自生活着一个总与快乐缺少点缘分的女孩子。
女孩子名字叫做清儿。清儿天一放亮就背着竹篓上了山,采些金银花、蒲公英、野薄荷等各色草药。
从孩提时起,每次上山,这女孩子都会费力攀上山顶,去看望一株孤立在那里的树。
那是一株年逾千岁的树,茕茕孑立于崖边,凸起盘结的树根深嵌于土石之中,粗壮的树干,遒劲的枝节,棕褐色纵横开裂的树皮,仿佛千年岁月凿下的铭文。
但,这棵树毕竟太老,早已失去盛年时的挺拔丰茂,枝干虽依然粗壮,叶子却不再繁密,而是稀稀疏疏,偶尔紧凑一簇,像老头的斑秃。
很久以前,山里人家对这样的古木是心怀崇敬的,先人们在距古树不远的崖边修建了一座小小庙宇。那时,庙里有人看守,上山祭拜古树、祈福许愿的村民络绎不绝,痴男怨女们更是在高高的枝条上绑起道道红绸,以求情事得偿所愿。
然而,如今这崇拜没落许久了,古庙老败,梁残瓦摧,崖边古树,红绸带被日月风雨揉搓,夺去往日鲜艳,终日暗淡,摇摆不定。
清儿放下背篓,依树而坐。山下寨子里,远远地望见砍柴人、打渔人、放牛放羊人小小的影子,朦朦胧胧,剪纸似的,慢悠悠走在长长土路上。太阳半起,家家户户瓦顶上已升起袅袅白烟,幽幽扬扬飘走不见。清儿于是想到,这每家每户的屋顶下,肯定有一个女人在操持饭食,或是蒸糕粑,或是煮茶,肯定也有一个小孩在她身边吵嚷,要吃要喝。
清儿没有家了。父亲从军后音讯全无,母亲年初已病死,留下她孤零零在寨子里,每天看花数云过日子。
清儿坐在树下许久,看日头缓缓上移,空气中浮起一股动人的暖意,倚在古树边,让她觉得自己正躺在一位长者的怀里,一颗冷了的心就短暂地热了几分。
瞧瞧天色,张阿翁的鱼该捕好了。他老人家每天这时候都要上镇上打酒。清儿答应替他卖鱼,张阿翁便酬谢她几尾,好让这女孩子把肚子填饱。
清儿下山来,傍着贯穿寨子的一条清清小河慢慢走,河边有妇人洗衣,妈妈还活着,脑子也还清明的时候,清儿也常同她到这里洗衣……
她跳上张阿翁的船,瞧了瞧船上的几个大鱼篓,果然,许多活泼泼的鱼儿在里面挤动。
有人来买鱼,清儿便总是挂着笑脸。
“清姑娘,今天可采到什么好药草,送到我那里去,吃饭没有?就到我家吃去嘛!”英阿婆说。
寨子里上年纪的长辈皆知晓清儿家的状况,都对她有些可怜。
不过,面对这些好心,清儿总是张皇失措,只因得到的怜惜越多,她心中的寂寞就扎得越深。
清儿替英阿婆把鱼串好,阿婆却突然变了脸色。
“清姑娘,瞧,顺哥儿来了!”
清儿听了,忙丢下鱼,转身躲进矮矮的船舱里。
这个顺哥儿是寨子头领的第三子,大名叫路顺。他父亲在附近村寨中皆有很高威望,虽已年近半百,身子依旧强壮似公牛。既然本领高,他家中余财自然累积不少,况且头领这人,为人豪放爽直,不拘小节,因此便有许多年轻汉子同他来往,声势愈大,却从没听一个人说过他的不好。
虎父无犬子,他的三个儿子也个个出息。大儿子从军去了,听说已做上了军官。二儿子在省城读书,每年都回寨子,生得斯文白净,和父亲长相性格皆无相似。三儿子路顺,预备接父亲的班,自小在寨子长大,脾气也最像父亲。
路顺打小就喜欢清儿,在众人面前从不掩饰。他长到今年十八岁了,正合婚娶,清儿的母亲去世后,他便执意娶清儿过门,即便不成亲,也非把女孩儿接到家里来住不可。
可惜,路顺虽好,但年轻男子的心性毕竟粗漏,路顺的坦诚与直白没能赢得心爱女子的同等回报,清儿像夜里的月光一样,极轻盈美丽,又极遥远缥缈,让人抓握不着。
于是,男子愈热烈大胆地追求,少女就愈畏缩羞怯地躲藏。
英婆婆懂得清儿的心,被一个过于冒进的男子示爱对少女来说是一种烦恼。
眨眼间,路顺已走到了船边。
“英婆婆,看见清儿了吗?”男子问。
“许是在山上耽误了,还没下来呢!”
男子露出一个灿烂的笑脸,邀功似的,抬起壮实的臂膀给英婆婆看手里提的东西。
“瞧,新裁的布,给清儿做衣裳!”
“好鲜亮的布!”英婆婆赞道。
少年得了赞赏,欢喜地去了,英婆婆重重地叹了口气。
船舱里露出一个小鸟似的怯怯的脑袋,清儿冲英婆婆笑。
“路顺还不好?多少女孩子想做他的新娘!瞧他多记挂你!”英婆婆说。
清儿不张口,手脚麻利地替英婆婆摆弄好鱼,递给她。
“草药我卖完鱼就给您送去!”
“你呀,你呀……”英婆婆摆摆头。
也难怪,这些年来,这女孩子就是心里有话,怕也只能说给溪边石头听。世道乱,她刚会走的时候,父亲就从军去了,石头落到深沟里,一去不返,下落不明。母亲累得呕出心肝,将她带大,然而,鸳鸯失了对,大雁离了群,她思念丈夫太深,日月煎熬,渐渐神志不清,缠绵病榻,临死前,已经连女儿也不大认得。
好命苦的清儿!或许,这女子和世间人情缘分浅薄,又或者,日子过得难,心淡了,把一切看轻了。
英婆婆提着沉甸甸的鱼,走回家去。
日升月落,又过了二三年,枪声炮影,战乱更甚,连这个偏僻的村寨也不能幸免。征粮的,抓壮丁的,吆喝着,穿着各样军装、扛着枪的大兵饿狼似的,每隔一段日子就来寨里搜刮。
一开始,尚有头领从中周旋,不叫他们祸害村民,日子一长,头领也招架不住了。
偏他是个虎豹一样的血性汉子,照拂村寨本是大山般压在他肩头绝不敢卸下的担子。然而几年下来,苦心经营,寨里百姓的日子还是越发惨淡,眼见要饿死人了。
头领终于领悟,要改变贫贱艰难的日子,不能一味忍受求全,非得和生活赤膊对赤膊,斗上一斗才行。
固守这个小村寨是不行的,非得跨出门槛去。
那段日子,入了夜,头领的家门总是被人拍响。有猎人深夜回家,走到田埂处,也时不时看到头领家昏黄的窗户和窗户里闪烁交叠的人影。
路顺这年二十一岁,身子高大挺拔如山间松柏,四肢孔武有力,行走如风,然而,那张成熟坚毅的脸上却嵌了一对忧郁的眸子,这对眸子便时时在山坡上用那心事重重的眼神望着山下村寨。
天晴时,清儿采完草药就在山顶等他。
将背篓放下,清儿靠坐在那棵熟悉的古树之下,望着山坡上莽莽榛榛的树木皆一色沉默低首,山下寨子可怜地蜷伏在山窝里,心里便也难得地打翻了各种滋味,竟觉出那微微秋风中的许多冷来。
这女孩子因年少就于种种事端中煎熬,人便如山涧中被瀑布冲洗过久的青石般低首沉默。回忆是尖刺不可触摸,心弦上再承受不住哪怕一片沉重的羽毛,而人生中将来的日子,可见的欢乐又如此稀薄,于是在少女时候,就干脆把眼耳口鼻连同心上的门都关紧了,不留一扇小窗。
却有一个男子,一日不辍地向她的窗上掷小石子。
那男子为她披上一件衣裳,挨着清儿坐下。
路顺不如往日热忱,两人竟在树下沉默地望了好久的天空,谁也不曾开口。
那女子细细浅浅的呼吸在男子耳旁,散发她天生的魅力,即不惊动世间一切,如一头小鹿,洁净美丽,男子便从来觉得有一种天然的责任——必不叫这美破掉。
路顺爱惜风口中清儿单薄瘦削的身子,终于按下惶惑的心,将眼睛从一片白云上收回,望向他心爱的女子。
“我父亲若真要走……”要说的话梗在口中,清儿的眸子投向他,他便说不出口了。
然而……
“做儿子的必不该叫父亲独自冒险……”路顺吐出这些字句,像从喉咙里挤出刀片,“我的二哥哥业已成亲,在省城置了房子,我已写信予他,预备将你送到他那里去……”
路顺知道,清儿必不喜欢他的这些话。
果然,她仍把目光放到天上。
“不要说这样话,怎么把我送到省城去?我的家在这里,你的家也在这里。”
“不可,若我走了,你一个人怎么行?”
“雀儿习惯在山间唱歌,山茶换了土便开不出花,清儿看惯了寨子里流水和溪石,到了别处去,就不是清儿。”
“虎豹不拘在哪儿,总是虎豹……”
清儿皱了眉。
“便是男子皆以为自己是虎豹,于是通通去了不回,来生,我偏要做棵树,咬定一处土石,日头落下升起多少遍,都必站定在原处。”
“树自然是美的,你瞧咱们身后这一棵,多么安静,却又容纳了多少鸟儿虫儿落脚……”
两人托着手下山去了。
半月后,路顺随父亲离开了村寨。
日月流转,此去又三年,路顺不曾回家。清儿天天在山顶树下等他。
村子里人口凋敝,田土荒芜,房舍倾倒,日子更显漫长。
贫瘠的土壤养育不出富足的心,古老的信仰便死灰复燃,成了村民们可攀附的最后一棵浮木。
那事是由村中的老人先提起的。
这样艰难的岁月,过去也曾有过,不过不必慌张,大家还记得山顶那棵古树,那座荒庙吗?
这样一种说法开始在一张张焦渴的口中流传:必须重新修葺古庙,必须铺上新瓦,清理灰尘,收拾香桌,必须重新摆上贡品,支起横梁,必须在古树的枝桠上再次系上红绸……必须献上一位纯洁的处女,做古树的新娘。
然而,哪个年轻女子不想嫁予心爱的儿郎?哪家慈爱的父母愿自家阁中明珠蒙尘?
附近村寨中,这流言虽传播甚广,却也有许多心软明理的人嗤之以鼻,即便人们的种种目光皆不由自主地投到清儿身上,在这可怜的女子面前,却也无一人多嘴,给她本已哀愁的眉眼上再添一点哀愁。
又过了二三年,路顺还不曾回来。
凡需到省城办事的寨中人,都有一件事必办不敢忘,便是到城中二公子家里替清儿探问路顺的消息。
次次失望而归。
山中庙宇已然重新立起,于是那一年,清儿自告奋勇,穿上嫁衣,进了山中,做了树新娘。
后人不曾知道清儿在山上待了多久,也不知道路顺到底有没有回家,只是熬过了那段艰难漫长的岁月后,子孙辈上山来,看到山顶庙宇中供奉的不是土地城隍,也不是神佛菩萨,而是一位眉清目秀的年轻女子,唤作清娘娘,也有人叫她做藤娘娘,因为庙前古树枝干上痴缠的那株藤条的缘故。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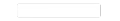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