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2024 年 11 月,天鹅与花朵的第二张全长专辑《月下世界》由美丽唱片发行。这是一张厚重的的作品,脱胎于乐队早期所浸润的新民谣与暗潮的风格,融合独立摇滚的色彩,获得一种更加宽广和丰富的听感。这张专辑的叙事概念完整,分为三幕,层层递进,描绘了一幅光怪陆离却又让人十分熟悉的“月下世界”图景。它也成为去年各大独立音乐榜单中,最佳专辑的热门候选之一。
春节前,我和乐队进行了一次采访。在聊天中发现,乐队的主创周建不仅是一位热爱科幻与奇幻文学的读者,也是一位写作者。并且,据他回忆,自己之所以喜欢暗潮音乐,说不定还与小时候游玩《暗黑破坏神II》的经历有关系。他还有一个小小的期待是,有一天能为一款自己欣赏的游戏做配乐。于是,我跟他说,那不如把这次访谈的内容也发布到机核吧!
以下是这次采访的正文。
序 · 从《科幻世界》与刘慈欣说起
序 · 从《科幻世界》与刘慈欣说起
自 2014 年研究生毕业之后,周建已经在水利工程行业工作十年。
从表面看,他的日常生活十分安稳。不出差的工作日,他每天早上八点出发,从东三环的家开车,横穿半个北京,抵达西二环的公司。和频繁加班的互联网行业相比,工作不算忙碌,偶尔摸鱼的时候,还能跑到会议室去做会儿编曲,或者干脆去到车上弹吉他。晚上下班回家,看看书,玩玩游戏,就睡觉。
在目前的公司,他待了差不多四年。其他的同事眼里,周建与大家并没有什么不同。除了一位关系特别好的同事外,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自己的音乐身份——天鹅与花朵乐队的主创。
可能他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毕竟刘慈欣在发电厂写科幻小说的那段日子,同事也不知道,后来就算知道了,也很少有人关心。工作对周建而言,只是一份谋生的事务罢了,没有多少热情。往好一点想,他觉得这是让自己保持和他人接触、获取外界信息的一个途径。
由于工作性质,他经常出差,有时会把吉他带上。一天结束后,他就躲在酒店或者宿舍,对着电脑写歌。天鹅与花朵在去年发行的新专辑《月下世界》里的大部分作品,便是他在唐山出差期间,见缝插针完成的。
只不过,有时在出差的城市醒来,看着周遭的陌生景观,周建会忽然感到困惑:“我到底在这里做什么?”
在能够回答它之前,不妨让我们先把这个深奥的问题放下,把故事的时间再往前推推。
就在刘慈欣在《科幻世界》杂志连载《三体》的那几年,正在读高中的周建,同样十分热爱科幻以及奇幻文学。业余时间做兴趣爱好的习惯,大概是周建从那时就保留下来的。他开始尝试写小说,并投稿给《科幻世界》,其中有一篇被编辑选中发表。
据周建的猜测,自己能在高考前拿到四川大学的自主招生录取加分,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段发表小说的经历。
无论如何,他在 2009 年凭借“《科幻世界》赐予的加分”,考上了川大,离开雅安,来到成都。
而在他念大学的第二年,天鹅与花朵成立。
一 · 天鹅与花朵的初组建
一 · 天鹅与花朵的初组建
若要说到底从什么时候,自己对新民谣及暗潮类的音乐产生兴趣?周建甚至觉得可以回溯到早年玩《暗黑破坏神II》的时光。那些阴森、诡异的背景音乐,辅以游戏本身黑暗的哥特式风格,总是让周建觉得毛骨悚然。现在再回去听那张原声专辑,其中由吉他、提琴和管乐构建的神秘氛围和奇幻图景,已然在周建的心里埋下几颗种子。
与生俱来的创作的欲望,是抑制不住的。刚上大学才学的吉他,周建就迫不及待地尝试写歌。
四川话里有一句谚语叫做“瓦片装稀饭”,意为容易自满,高情商的说法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周建觉得新民谣是一种“蛮简单”的风格,自己也能做。而且很快,他就写好了几首小样,想要试着找找合适的主唱。
周建在学校的社团认识了几位有着相同喜好的学长,其中一位推荐了袁田。然而,和音乐经历尚浅的周建不同,彼时的袁田可以说是已经置身于中国新民谣的浪潮中心。
她已经在为 Bloody Woods 担任客座主唱与设计师,为白水和王三浦担任和声。就在周建联系她的前后,袁田正参与白水 2011 年发行的专辑《花拾叁樓主人》,其中她唱了包括「美人吟」在内的五首作品。
周建很率真,反正是试试,也没犹豫,便拜托学长做介绍,加上了袁田的联系方式。
袁田回忆起和周建相识的经历,她说特别简单。两人加上 QQ,互相寒暄之后,周建就发来一首小样,她试听完,“一瞬间就被打动了”,就试着唱了一段,录完返给周建。
“加上袁田姐的唱之后,歌的感觉突然就不一样了。”周建补充说,“那瞬间才觉得,似乎这个计划真的可以做下去。”
这首歌即是后来收录于小样合辑《阴天》里的「风景画」,其中除了袁田与周建的唱段以及吉他外,还有一位角色:来自佳子的小提琴。
大学时期,周建最欣赏的新民谣乐队中有一支来自俄罗斯的冷门组合 Neutral,后者的作品中小提琴占据着标志性的部分音色。并且,新民谣作品的神秘主义质地,往往是来自于古典乐器的选择。因此,周建一边自己在宿舍对编曲做着更丰富的尝试,也一直想要找一位能够提供帮助的人选。
碰巧,遇到佳子的出现。佳子那时的男朋友是周建的同班同学,也是后者在大学最好的哥们儿。佳子回忆认识周建的过程时,说:“大概是 2012 年吧。有一天他和我说,自己有个同学也是搞音乐的,问我能不能帮个忙听一听。”
尽管佳子在古典音乐世家长大,从小浸润在古典氛围中,但她依然喜欢听一些被认为是小众的音乐。和袁田一样,佳子与周建加上联系方式之后,也立马收到了发过来的试听作品。佳子听完,说:“特别喜欢,很像我高中时期特别喜欢的一位音乐人,Elliott Smith。”——不意外,Elliott Smith 也是周建最喜欢的音乐人之一。
佳子的加入完成天鹅与花朵前期创作的最后一块拼图。
2012 年 5 月,他们在豆瓣小站上传了乐队的第一张作品、探索性的 demo 合辑《阴天》。
二 · 川西的雨一直下
二 · 川西的雨一直下
在过去需要自我介绍的场合,天鹅与花朵通常会讲自己“成立于成都”。但在加入美丽唱片,开始筹备新专辑《月下世界》之后,乐队需要一份更加正式的简介来配合发行。周建考虑过,要不干脆删掉这句话算了。毕竟,乐队生涯中,在成都的日子只占四分之一不到的时间。
《阴天》发行的第二年,周建大学毕业,远渡英国念研究生,而后的工作地点选在北京,才与如今的乐队木管手李琳相识。佳子则定居新加坡,在那里开设了自己的音乐工作室。唯有主唱袁田一直生活在自己的家乡成都,成为他们与这座城市仅有的连系。
天鹅与花朵从那之后,就再也没有线下排练过,始终处于远程创作状态。通常来说,周建负责词曲的创作和编曲,交由袁田负责主要的人声演唱,最后到佳子手中时,基本上就只差弦乐部分。
当然,整个过程中可能会有反复修改的步骤,但乐队的创作流程大致如此。他们通过这样的方式完成了《遇雨而生》和《月下世界》两张全长专辑。不过,2020 年发行的 EP 专辑《涣散的眼》的词作,是周建的高中同学余骁的诗——他们曾在读书时期一起疯狂地听歌,并互相分享波德莱尔与兰波的诗歌。
不过,思前想后,周建最终还是决定保留,改为更具有暗示意味的“起始于 2010 年的成都”。地理位置对于天鹅与花朵而言,蕴含了太多超出它本身的意义。来自于西南的雨味和那种怪力乱神的精神状态,早已浸润在天鹅与花朵的所有的作品中。
在四川盆地的西部边缘,存在着一条被自然学家们称为“华西雨屏带”的地理区域。北起绵阳平武县,穿过雅安和成都,南抵凉山雷波县,是川西平原向高原的过渡地带。由于平均海拔高度差近 2000 米,从太平洋和孟加拉湾北上的暖湿气流与高原冷空气汇聚于此,带来异常丰沛的降水。
雅安是周建的故乡,一座平均降雨天数超过 200 天的城市,甚至有一块被命名为“雨城”的行政区。而成都位于雨屏带的边缘,降雨虽少于雅安,但一年的平均日照率也往往不到三分之一。没有在这里常住过的人,或许很难体会这般气候会滋润出何种心境。
在雅安、成都两地生活二十余年,周建早该习惯抬头望向天空时,只能见到连绵的灰色阴云。但偶尔他还是会放下理工科出身的理性,耽溺于幻想:是什么样的悲伤,能让天空陷入永恒的阴雨?——这是他在作品评论区,留下的对于「阴天」的创作解释。
以现在的标准去听,「阴天」是一首稍显青涩、稚嫩的作品,却清晰地拓印着如今的天鹅与花朵的轮廓。在 2019 年发行专辑《遇雨而生》后,接受《腾讯音乐人》采访时,周建谈到了天鹅与花朵和经典新民谣的表达主题上的区别:“比起古老的神话或是关于历史的隐喻,我们更倾向于关注自己眼前的生活。”
由日常生活触发灵感,延伸出泛着浪漫光泽的、魔幻现实主义的诗性表达。吉他筑成框架,小提琴和人声(以及后来的更多乐器)是明暗的彩线,编织出想象世界的图景。
《遇雨而生》显然是西南的“阴雨天”意象的一种更加完整的延续。而这种来自西南的、地理文化所孕育的潮湿气息,始终贯穿天鹅与花朵的创作,生长为他们的表达根基。
诚然,随着生活的变迁,天鹅与花朵的创作背景自然而然地发生了变化。离开四川十年后的周建,开始像万能青年旅店一样,唱起“华北平原”稠密的迷雾。然而,就在这句话的前头,是他为这首「恋曲」写下的第一句歌词:
“总在最严峻的时刻想起你,想问南方的风,是否依然潮湿。”
三 · 一段画龙点睛的帮腔
三 · 一段画龙点睛的帮腔
Elliott Smith 不仅帮助周建认识了佳子,还帮助他认识了后来新专辑《月下世界》的制作人胡希可。除天鹅与花朵之外,周建在北京还加入了另外一支乐队 Uncle Hu 担任贝斯手,它的主创正是这位四川老乡、Elliott Smith 忠实拥趸老胡。
老胡在认识周建之后,一直非常欣赏天鹅与花朵的作品,但也看到了他们在录音与制作上存在的问题。在一次偶然的情况下,他跟周建提过一嘴:不如天鹅与花朵的下一张专辑,我可以来给你制作。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制作 Uncle Hu 于 2020 年发行的 EP 专辑《The National Moment》的过程中,周建体会到了作为完美主义者的老胡,对待专辑制作的态度。
在此前做《遇雨而生》的期间,无论是录音还是制作,天鹅与花朵的成员都缺乏经验,在一些技术性的问题上反复打磨很久。尤其是混音阶段,周建尝试自己做,却一直没有达到想要的效果。绝望与愤懑中,他一气之下干脆不做了,直接把半成品专辑上传到了豆瓣小站。
“过了几天冷静下来,觉得不行,还是得想办法完成,又把专辑下架。”周建现在说起那段经历都觉得好笑,“后来我们总结经验的时候,认为解决办法就是,技术问题就找专业的人来做。”
老胡可不仅仅出现在制作人一栏,他以乐手的身份参与了每一首歌的录制,有时是和声,有时是贝斯手,有时是吉他手——既有电吉他,也有原声吉他,甚至是打击乐。用周建的话说,在这张专辑里,老胡就是一位实打实的乐队成员。不过,最能体现制作人闪光时刻的是在「草芥的歌谣」。
起初,这首歌的版本只有 AB 两段。老胡听完周建给过来的小样版本,总觉得段落之间似乎少了些什么。他想起川剧中用于烘托和推动情节发展的帮腔,于是找了一段给周建发去。周建第二天就以此为参考,补充了现在保留在歌曲里的那句:“梦醒时,月亮还在那夜空之上。”
为了这张专辑能在音乐上能更有张力和起伏,乐队做了许多的尝试。例如在「她和她的城堡」里,邀请朱小姝来担任主唱;以及「死神的午夜」对以前从未尝试过的风格,进行即兴的探索。
「死神的午夜」是周建邀请了帮助《遇雨而生》解决混音问题的刘家仁,来共同完成的一首歌曲,这也是新专辑中最晚完成的作品。其实在确定曲目时,由于这首歌的完成度和风格上的挑战,他们一直没有定下来是否要放到专辑里。
作为最后拿到 demo 的人,佳子说自己只能给出一个框架,连要拉什么音都不能确定。而目前听到的成品里,小提琴的部分基本都是佳子在录音的当天写完、录完的。
“现在想到那个过程也挺不可思议的。这是我们第一次做这种类型的作品,都很想完成它。”佳子语气兴奋地说到,“又勾起我读书的时候,听重型摇滚的那种感觉。”
四 · 魔幻的现实和梦境
四 · 魔幻的现实和梦境
第一次见到“月下世界”的概念,是周建看到的一篇讨论基督教的文章,月上世界象征永恒,月下世界则是黑白不分明、持续变化。不过,在这张专辑的成形过程中,它原本的意义已经在曲折的意象化的虚构中,变得晦暗和模糊。
想要创作一张概念完整的专辑的念头,盘旋在周建的脑袋里许久,但始终没有找到合适的切入点。
直到有一次闲聊,有老胡和达闻西乐队的主唱猴子。老胡和猴子都是在重庆念的大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一次川渝老乡会。那大概是疫情初期,聊天中,猴子提到了达闻西此前的关于《1984》题材的作品。老胡思忖了一会儿,或许是有感于现实,开口说:“这种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写一部自己的《1984》。”
“这句话一下子就触动了我。”周建说,“作为创作者,我觉得必须对这个主题有所回应,这是我们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回避的事实。”他用了“呕吐式”的创作,来描述当时自己遭受外界刺激后的反应,突然间写作的进展就加速了。
对于写作的主题,佳子和周建有种默契。这既是长期磨合创作积累下来的东西,也源自于他俩对相同的文学题材的兴趣,例如阿斯塔菲耶夫的《鱼王》和出现在新专辑里的布尔加科夫的《大师与玛格丽特》。
所以,尽管乐队成员之间很少交流具体的文本主题,佳子依然敏锐地捕捉到从《遇雨而生》到《月下世界》的改变。
“《遇雨而生》是我们从读书时期就积累下来的动机,是一种为自己营造的单纯的、私密的氛围。它更像是一部古典音乐的作品,而《月下世界》则是一部戏剧化的文学作品,我们从自己的房间走出门去了。” 佳子在对比两张专辑的创作时说,“我一直挺佩服他的,把很多我想说,但又不敢说的东西,直接表达了出来。”
五年前,他们在「自恋」里歌唱沉醉于自我幻象的水仙少年,在「菌类」里怀念童年与爷爷采食鸡枞菌的无忧时光,勾勒的是如梦境般唯美的景象。
然而如今,仿佛恍然梦醒,故事化为「她和她的城堡」里双手双脚沾满泥土的疯女人张素英,讲述的是带着乡土传说笔触与腥味的「草芥的歌谣」。
「草芥的歌谣」的灵感来自于一个梦。梦的讲述者是 Uncle Hu 乐队的鼓手老高。梦发生在疫情防控期间的某天,在梦里,一群穿着白色衣服的工作人员忽然闯入家中,想要将他的妈妈带走,他很害怕,于是拼命抵抗。第二天醒来,老高把自己做的这个梦发在了乐队群里。
在周建眼里,老高是一位内心很敏感的人。他的恐惧让周建觉得十分悲伤,也让他感到愤怒: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产生这样的恐惧?
五 · 欢迎来到月下世界
五 · 欢迎来到月下世界
再回到文章开始时,周建忽地向自己问出的那个问题。或许正是这种意识到世界的荒谬的瞬间,让一个人从月上进入了月下的世界。
近几年,有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在中文互联网被重新打捞起来,是美国学者纽加滕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提出的“社会时钟”。即处于同一个社会的人们,往往会使用一些关键的事件节点来衡量一个人一生的进程,比如上学、毕业、结婚以及生孩子等等。
在东亚社会长大的我们,可能尤为在乎“什么时间该做什么事”的规训。假如一旦脱离自己、家庭和社会的预期路线,或者仅仅是稍显落后,我们就开始焦虑、担心,又试图赶紧追上。很少有机会去问自己:这样做真的对吗?再或者,在这些事情上,真的有所谓的对和错吗?
“东亚小孩都是被按照月上世界去教育,遵循着一些被认为是黑白分明的恒定的规则去生活。” 周建还是尝试着向我解释了新专辑的概念,“但真实的世界是模糊的,没有规则的,如果我们还是按着月上世界的观念去生活,会非常痛苦。”
从月下世界的角度去看,这样过生活的人就好像是疯了一样,拿着明明不存在的标尺,努力地让自己融入世界。
反过来讲,还不如疯掉算了。就好像这几年在社交媒体上留下的“发疯文学”,借着发疯的理由打破过去不敢碰触的东西,反倒是能给予我们一些暂时的、浅显的宽慰。
“欢迎来到月下的世界,这里的一切都很模糊,发疯能让你变得更清醒。”周建在《月下世界》的第一首歌「黄昏与夜」里写到。
但清醒的代价是什么呢?他补充写下:“这里的月光,它有毒。”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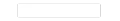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