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半个多月前,大卫·林奇的家人在社交媒体发布了一则讣文:「现在他已不在我们身边,世界从此留下了巨大的空洞。但正如他所说,眼睛要盯着甜甜圈本身,而不只看到甜甜圈的洞。今天是个好日子,一路上都是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一个月前,我还在看大卫·林奇的电影大师课,画面中的他已有些苍老和疲惫,双手不时微微地颤抖,但声音和话语间依然流露着对电影的深深热情和着迷,犹如即将燃尽的柴火仍在努力散发着光芒。突然听到他离世的消息,虽称不上意外,但内心仍感到非常不舍和惋惜。
熟悉大卫·林奇的观众都知道,他的电影中总是充斥着悬疑、犯罪、黑暗,甚至是暴力,因其拍摄使用的迷幻手法,运用大量的象征符号,常常模糊现实与梦境的边界,使他在电影界初出茅庐时,即给观众和影评人带来强烈的震撼。时至今日,他的作品仍是各大影视论坛的影迷们热衷解读的话题。
但罕为人知的是,与他的电影正好相反,大卫·林奇本人总是出乎寻常的温和、平静与快乐,时常还带些孩童般的好奇心和调皮。那一抹温暖的底色,对人的关怀,让他在探索复杂、幽微的人性世界时,总能游刃有余而又不被其吞噬。
这两种矛盾的特质是如何结合在一起的?大卫·林奇给我们留下的,除了精彩绝伦和别具特色的电影之外,还有什么?如果说梦境就像谜题,那么解谜的钥匙,或许就藏在创造谜题的人手里。
电影之路
回顾大卫·林奇的电影历程,虽然年少成名,但是职业生涯也并非一帆风顺。筹备了五年的第一部长片作品《橡皮头》起初只在「午夜场」受到追捧,但其独特且强烈的风格,噩梦般的故事结构,奠定了其在「邪典(Cult)」电影里的代表作地位。第二部《象人》打入主流市场,直接获得当年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导演提名。至此,大卫·林奇算是在电影圈打响了名气,片约纷至沓来,但是没有人想再要一部《橡皮头》,都期待他能再造一部《象人》。
当时大卫·林奇没靠电影赚到什么钱,因此当有人拿着科幻小说《沙丘》的改编剧本来找他,并愿意承诺大手笔投资时,他心动了。但是,电影《沙丘魔堡》最终却落得口碑和票房双输的境地,大卫·林奇回顾这段经历,将之归结于自己无法掌控电影的走向:「当你无法自由拍摄自己想要的东西,最后还拍出了一堆垃圾时,你就会觉得从一开始就出卖了自己,现在不过是咎由自取。我知道迪诺(投资人)喜欢看什么,也知道自己没有最终剪辑权,所以一路都在妥协——实在太可怕了。我体会到了失败,某种意义上来说,失败是很美好的东西,因为当一切都尘埃落定,你无路可走,只能继续向上,这就是自由。」
《沙丘魔堡》的大败是大卫·林奇电影之路的重要转折点,无论是内在的创作理念,或是外在的创作风格,都从《沙丘魔堡》之后变得越发清晰和坚定。
于是,他决定放手一搏,拿出自己亲自创作且酝酿多年的剧本《蓝丝绒》,把心里压抑着的许多想表达的东西,都一次性释放出来。不过,他这次只找到1000万美元的投资,后来还被削减成400万,竟与初出茅庐的《橡皮头》成本相近。对许多导演来说,预算不足相当令人困扰,报酬缩水更是一种耻辱,但大卫·林奇似乎毫不在意,他说:「我们是制片厂里最穷的影片,不仅规模最小,也最不重要。但拍《蓝丝绒》就像从地狱回到了天堂,因为我拥有无尽的自由。」
在那个电影业还没有那么多规矩的年代,即使预算被砍,也能透过灵活调度来节省成本,况且大卫·林奇还在高中兄弟会担任过会计职位。因此,他终于有机会可以尽情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编排和导演电影了,《蓝丝绒》因而也成为大卫·林奇最具个人风格,也最具有自由气息的作品之一。同时,也因其清晰的主线故事,又不乏悬疑和离奇的象征物和氛围,成为最适合观众入门的首选,同时也是了解导演的最佳线索来源。
蓝丝绒
《蓝丝绒》的拍摄地点距离大卫·林奇的家大约5小时车程,和他童年成长的地方相似,同样是个不起眼的小镇,但正是这种小镇式的、社区式的日常空间,总让人感觉到表象之下隐藏着什么。在看似波澜不惊的生活表面之下,涌动着更为黑暗、躁动、复杂的人性和故事,这是大卫·林奇注定要拍的那种电影,也为他划定了一片今后都将持续探索的区域。
电影的故事讲述的是高中生Jeferry因父亲意外住院而休学回家照料五金店生意,无意中在邻居家的荒地里发现了一只被割下的人耳。他去警局报案,并亲手将耳朵交给了与父亲相识的警探。由于案情保密,Jeferry只能从警探女儿Sandy的口中探听到此事与近期搬来镇上的女歌手Dorathy有关。于是,闲来无事又好奇的他大胆密谋潜入女歌手家中一探究竟……从此卷入了离奇复杂的地下犯罪、女歌手的秘密人生,以及自身情感与欲望漩涡的故事。
故事主线并不复杂,但每个角色身上都掺杂着善良与邪恶。黑暗与光明就像一朵双生花,内嵌于每个角色的内心,也外显于电影的视觉表现。其中最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莫过于性虐待Dorathy并绑架她儿子的毒贩Frank,上一秒还沉醉在音乐中流泪,下一秒就能把人打得满地找牙,在那残暴的硬汉心中,有着诗意和柔情的一面。男主角Jeffery有纯洁无辜的味道,天性好奇,喜爱奥秘,但更爱女人。虽然迷恋Dorathy的美貌和肉体,但更想救她于水火;对Sandy告白,却不愿让她知晓自己内心阴暗的一面。
为了呈现这种复杂感和双面性,大卫·林奇特地以两种色彩来区分光明的黑暗。平静、温和的情节多发生在白天,在高中校园、小镇街道、Jeffery的家和五金店、与Sandy聊天的餐馆。尤其是Sandy总是带着一缕柔光出现,穿着淡粉、鹅黄的轻盈裙子,讲述着自己关于「知更鸟」的梦。当Jeffery来到治安不佳的街区,走上阴暗的楼梯,进入Dorathy深红与暗绿色调的公寓,也如同伴随着低沉嗓音的爵士乐,走入了那闪烁着深蓝丝绒光泽的酒吧光影里。
两个世界同样迷人,都令Jeffery无法自拔。他既爱Sandy的好奇与纯真,又爱Dorathy的神秘和绝望,或者说,他对于这两个女性的情感,象征着的是他对平凡的日常和深处的奥秘同样强烈的渴望。大卫·林奇本人又何尝不是如此。饰演 Jeffery 的演员说道:「大卫很擅长把自己生活中遇到的问题转化为艺术的一部分,他在作品中的情绪坦诚程度让人惊讶。至于我是否在这些电影中扮演了他的『另一个自我』,只能说在出演这个角色时,我很轻松地吸收了他的个性,并把一部分的他投射其中。」
如同阴与阳、动与静、黑与白彼此相生、互相平衡,当大卫·林奇发现故事的走向过于阴暗时,他最终选择了一个光明的结局。以内在稳定的「平衡感」来呈现幽微的复杂性,使得大卫·林奇的作品总能以温暖幽默的底色,去探索罪恶、黑暗而不被其吞噬。
不过,如果电影里只有四平八稳的「平衡感」,未免也太无趣了些。或许因为预算有限,又或许是大卫·林奇对于现实有一种随心所欲的态度,他几乎从不追求「时代的精确性」,反而喜好模糊时间的边界,带来一种时间错位的趣味。比如 Dorathy 在酒吧表演时,用的是 1920 年代的复古麦克风,她的公寓处处透露着类似 1930 年代电影《瘦子》(The Thin Man)的艺术装饰风格,但她的电视机却装有 50 年代的兔耳朵天线。Jeffery 和 Sandy 密谋计划的餐厅,也有着 50 年代的风格,但是他们穿的衣服却属于 1980 年代。年轻而活泼的 Sandy 有着明显的 80 年代个性,但卧室里却贴着活跃于 1950 年代的男明星蒙哥马利·克里夫特(Montgomery Clift)的海报。
如同我们的大脑在创造梦境时,总喜欢从现实中随意截取元素进行拼贴,大卫·林奇同样如此。我们理所当然接受了这种「混乱」在梦境中的合理性,但偶尔又会隐隐地怀疑自己究竟身处现实,还是梦中。在这里「时间感」被打乱了,人们似乎掉入了一个「时间错位」的空间。不知有意或是无意,大卫·林奇总是以「梦」的形式构造着自己的电影,或许这正是他追求的「自由」,把信手拈来的元素以充满直觉的方式进行拼贴,不在意历史和现实的约束,因而给观众带来了奇妙的体验:勾起你内心隐隐的不安,又说不上来究竟哪里出了错。这时,大卫·林奇或许会露出狡黠调皮的笑容,制造梦境的圈套,谁都不是他的对手。
造梦之旅
尽管梦是最自由且最具创造力的表达形式,但制作电影总有各种各样的限制,仅有 400 万美元预算的《蓝丝绒》更是如此。
演员片酬向来在电影的制作成本中占比很高,但大卫·林奇偏偏对大明星嗤之以鼻,相反,他总是在名不见经传的演员身上寻找着最符合角色的特质,他说:「人们已经习惯了按照某种程式化的英俊与美丽。但你走在大街上,看到那些真实的面孔,会发现他们其实更有故事。」饰演 Dorathy 的伊莎贝拉·罗塞里尼(Isabella Rossellini)就是如此。那天大卫·林奇和投资人兼好友迪诺在餐厅吃饭,恰巧遇见熟识的朋友,过去打招呼之际,第一次见到伊莎贝拉,大卫·林奇立刻说道:「你简直可以当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的女儿了。」旁人插话:「傻瓜,她就是英格丽·褒曼(Ingrid Bergman)的女儿!」除此之外,她还是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Charles Scorsese)的前妻。
即便有众多名人加持,伊莎贝拉当时也不过是没有太大名气的模特,只出演过一部反响平平的电影。可大卫·林奇一眼就看出了她饰演女歌手 Dorathy 的潜力,因为她有令人屏息的美貌,但孤身一人在美国的境遇却让她有着独在异乡的脆弱,仿佛很容易受人操控。眼神中带着恐惧,似乎是个麻烦重重的人。更有趣的是,她不成熟的演技呈现的些微生硬与刻意,也恰好符合 Dorathy 在扭曲且高度紧绷环境下的精神和行为状态。
大卫·林奇不仅能巧妙地把演员的缺陷化为特色,甚至重塑了这些演员在观众眼中的形象。与 Dorathy 有多场对手戏的毒贩 Frank,其演员本人丹尼斯·霍普(Denis Hopper)也因刚从戒毒所回归社会而声名不佳,曾与他合作的人都在背后称他是个「疯子」,但是大卫·林奇却力排众议,愿意给他机会。如同大卫·林奇所说,Frank 这个角色是个典型的 1950 年代柔情硬汉,「你不一定和他握过手或一起喝过酒,但只要和他交换过眼神,你就知道自己一定遇到过这样的人。」丹尼斯也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一改往日不负责任的习惯,以精彩绝伦的演出回报大卫·林奇对他的肯定。二人因惺惺相惜而成就了一部影史佳作。
即便搞定了演员,片场状况也相当有挑战。由于电影制片厂仍在建造中,对于拍摄场地附近的居民来说,有人来拍电影依然是不得了的事情。虽然电影大部分时间都在夜间拍摄,但感兴趣的旁观者还是风雨无阻地出现。有一天,他们要拍摄一场情绪饱满的戏份,Dorathy 憔悴地在街头徘徊,全身一丝不挂。那天整个小城的人都出动围观了,还带着野餐食物和小凳子。以至于第二天警察告知制作部门:决不允许在附近的街道上拍摄《蓝丝绒》的任何一场戏。大卫·林奇常遇到这类问题,对他来说,围观的群众常在旁边晃悠,但他得让自己专注于演员,全神贯注地做事情,他说:「如果我在乎身后发生的事情,只会让我发疯。我屏蔽了一切,你应该紧盯着甜甜圈,而不是它中间那个洞。」
终章
「造梦」是在这个充满局限的世界中,尽可能地实现自己所想的自由。大卫·林奇享受自己的造梦之旅,就如他所说:「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在乎其他人的想法的,但这是件好事。你爱上了某种想法,就像爱上了某个女孩,坠入爱河的感觉很美,你也忠于自己的感受。」
他回顾《沙丘魔堡》,认为自己因妥协而制作出自己不满意的作品时,已是一种失败,当电影上映后再遭遇票房失利,更是双重失败。但如果遵循自己的心意创作,即便最终仍然风评不佳,那么最多也只失败了一次。他谈到:「《吠陀》有句话:人只能控制行为,而不能控制行为的结果。你尽自己全力,事情如何收尾不在你的控制之中。但忠于自己的感受,整个过程的自我感觉就会非常完美。」
我想,大卫·林奇的一生都在不遗余力地创造和捍卫自由的梦境,并且乐在其中。生命终将走向终点,每一部电影都会迎来落幕。但我们是否也能像大卫·林奇一样,每一刻都忠于自己的感受?即便在充满局限的世界里,也能把阻碍和劣势化作更有趣的游戏与梦境。
在 1980 年代那个偏远的小镇,悠哉拍摄《蓝丝绒》的日子里,大卫·林奇总是骑着一辆粉红色的自行车,车的把手上飘扬着彩条装饰带,口袋里塞满了M&M花生巧克力豆。
那是个晴朗的日子,一路上都是金色的阳光和蔚蓝的天空。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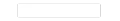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