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本文是我在听完《“艺术已死?” 聊聊艺术的过去和现在》电台后,对自己艺术观的一次梳理。第一、二部分关于艺术创作中的技术与叙事,以及该视角下怎样看待“艺术之死”。第三部分讲述了一段关于电视艺术鲜为人知的历史,提出一个关于电子游戏和艺术的开放性问题。笔者能力有限,行文多有疏漏,望大家提出建议多多交流。
一、技术和叙事视角下的艺术创作
一、技术和叙事视角下的艺术创作
首先我要叙述一个关于光线和视觉的知识:低压钠灯可以发出波长约为589纳米的单频光,光谱分布极窄,能让人类的视锥细胞对其他波长的光的感知度大大降低。在高功率的低压钠灯照射下,环境中充满了高饱和的黄色光,人眼中的其他颜色会变成不同程度的灰色。到此为止,这个小知识仅仅是一个小tips而已,可以说对99.9%的人都没什么意义。
接下来,让我们想象这样一面白墙:墙上挂着色卡,旁边分别放着一盏低压钠灯和一盏白炽灯。打开低压钠灯后,黄色的单频光“夺走”了色卡的颜色。这时,我们打开一旁的白炽灯,会发现越靠近白炽灯的色卡,就越还原“本色”。现在,上面的知识进入了感官层面,并且通过体验让我们意识到视觉和颜色感知的主观性。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下面让我们更进一步:想象一个长百米、宽几十米、高几十米的空间,其中充满雾气,空间中悬挂着一个直径十几米,由低压钠灯组成的单频光源。你驻足其中,周遭雾气朦胧,巨大的“黄色”太阳让身边的一切都褪了色。你看着身边的人,再看向自己的身体。被巨大的陌生经验冲击,惊诧之余你会不禁质疑自己感觉的真实性。甚至开始思考那些平时想都不会想的玄妙问题,我日常体验的那个世界是真的客观存在的吗?我和这个世界是怎样的关系?
内容因剧透、敏感不适等原因被隐藏
点击查看其实上面这个空间曾经真实存在过,它是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2003年创作的装置《天气项目》(the Weather Project)。埃利亚松创造了一个沉浸式的气候环境,通过陌生体验让人们关注天气现象,进而在这个被人造环境包裹的时代重新审视身体和自然的关系。
那么,这是艺术品吗?在引出有关艺术的讨论之前,让我先说明几个概念:
- 技术(广义):人类认知世界规律产生的工具及相关知识系统。
- 叙事:某种语境中对事件、现象的表述。
- 创作者:利用技术传递某种叙事的主体(个人或集体)。
而艺术,是创作者将技术作用于感官,向接收者传达某种叙事的行为及其结果。例如在《天气项目》中,埃利亚松创造性的使用技术(以单频光为核心的一系列空间塑造手段)重新校准观者对周遭环境的感知,完成了一次属于彼时彼刻的叙事(人类对自然的改造达到新高峰时,重新审视两者的关系),并且在成功制造奇观的同时引发观者恰到好处的思考。因此我认为,《天气项目》不仅是艺术,而且还是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创作之一。
对于我来说,与其鉴别风格和比较创作者技艺的精湛程度,从技术和叙事两个方面去考察艺术创作更为有效。本文不会用这个框架从石器时代起考察个遍,而是只举出两个我认为比较特殊的节点。
1. 透视法,文艺复兴时期的壁画
在画面中科学的表现空间透视,是当代绘画者的基础技能。但是在中世纪,这是画家们花了几个世纪才习得的技术。直到15 世纪布鲁奈列斯基( Brunelleschi ) 发现了解释透视规律的数学和几何学方法之前,画家只能使用遮挡、阴影等手段表示物体的远近关系,这导致了许多透视诡异的画面。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透视法普遍应用在绘画中,尤其是壁画和教堂天顶画开始和其所在的建筑空间呼应,画面和实际建筑结构和构件混在一起,造成一种画面是真实空间延伸的错觉,这一技法在巴洛克时期到达顶峰。
当时人的感官对于拟真环境的阈值远远低于现代人,这些和真实空间混合的画面足以通过沉浸感刷新观者的感官体验,让拜访教堂的人产生“天国降临”的错觉,传达某种天主教叙事。
这里插一点关于透视法的有趣阐释:被大规模应用于宗教题材的透视法其实隐含着一种人本视角的叙事:所有的视线从人眼发出,空间由人眼确定,画面因人而非神的存在而如此安排。
2. 信息流与电子交互艺术装置
我在《控制论的意外发现:艺术与电子游戏》一文中提到的60年代出现的电子交互艺术装置,现在看来也是随处可见的小玩意儿,毕竟逛个商场都有人工智障跟你搭话。但在商用计算机都未普及的年代,能和人类“对话”的机器就是一种魔法物件。此类装置中应用的技术——将人类的行为(神经反射)纳入机器的反馈回路中的电子控制系统——脱胎于二战期间盟军的制导技术。这些艺术装置虽然没有精美的图像,但起中也隐含了一种叙事:人类和机器在信息流动的层面被一视同仁,一个关于信息时代的预言。
二、关于“那种艺术”的死亡
二、关于“那种艺术”的死亡
上文提到的两个节点除了能体现技术与叙事和艺术创作的关系之外,它们之间还有一种近似新陈代谢的关系:控制论装置出现的时间,恰好是文艺复兴那种绘画艺术没落的年代。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各种艺术流派层出不穷的,抽象表现主义、波普艺术、欧普艺术、极简主义、观念主义、抽象现实主义、新表现主义……“艺术家们的创造力似乎是由创造时期而非创造作品构成。”这种现象直接启发美国哲学家阿瑟·丹托(Arthur Danto)写出《艺术的终结》一文,这应该是“艺术死亡论”的肇始。
其实该文多少有点翻译造成的误会,文章的英文标题“The Philosophical Disenfranchisement of Art”,直译为《哲学对艺术的剥夺》。丹托受到黑格尔和贡布里希的影响,持有一种进步的艺术史观。他认为自从电影等能创造真实世界副本的技术出现后,为了创造“知觉相等物”而进步的艺术(主要是绘画和雕塑)就失去了目标,失去了与客观世界参照的标准。从后印象派开始,艺术家不再描摹客观世界,而是专注主观体验和情感。艺术从此以自身为对象,因而无法获得一种普遍的本质,每种流派都要依靠一种理论支持才能成立,哲学就此剥夺了艺术的权利。在这之后,纷繁的流派呈现出“文化之熵”的状态,艺术从内部被耗尽,什么都可以创作,但任何创作都不再具备历史意义,所以艺术终结了。
丹托的讨论是建立在深厚的哲学和艺术史语境中的,我在此只能做出粗浅的解读。不过我还是要指出丹托的历史叙事中包含的一条重要线索:关于机械复制如何导向“艺术的终结”。
设想一下,身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油画家,你画上几天甚至几个月才完成的作品,机器一开,分分钟就印出来了。身为画家的你当然可以为自己精湛的技法和付出的精力自豪。但是对更广大的人们来说,你的油画与印刷出来的画片没有太大的区别,都只是图像而已。本雅明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认为这些复制品贬损了艺术品存在的质量,扰乱了其本真性。或者,用更简单粗暴的说法—绘画这种艺术被机械复制降维打击了。
马歇尔·杜尚(Marcel Duchamp)恰好在合适的时间捅上准确的一刀:小便池——《泉》、雪铲——《断臂之前》、印刷的蒙娜丽莎——《L.H.O.O.Q》,这些工厂流水线的产品也可以是艺术品。杜尚的叙事是:机械复制已经杀死架上绘画了,人的灵韵(本雅明提到的aura)也将被工业吞噬了。你们都是能被复制的,你们都是没有灵魂的。这是一个大工业时代的谶语。
不难看出,杜尚的多数作品都是关于艺术自身的指涉,是对艺术的元叙事。许多伟大的艺术创作都具有这种特性,它们在一定程度上能反过来定义它的父集——艺术。这往往是艺术家创造性地使用他所属时代的技术达到的,因此它所传达的叙事一定能被那个时代的多数人所感知。当你在美术馆或艺术展上看到小便池时问出“这也是艺术吗?”的一刻,你就已经接收到了杜尚的讯息。由此看来,“死亡”的仅仅是“那种艺术”:以视觉为媒介描摹现实的艺术。那种艺术日益个人化、主观化,与影像工业及其所代表的技术相比,既无法冲击感官体验,也无法讲述一种被多数人理解的叙事。
本雅明曾在《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中提出“艺术应该通过对技术媒体的运用,来克服手工制造的原作的品质局限,由此抵达新的观众,并社会性地动员这些观众。”如果说照片和电影只是将“那种艺术”逼到边缘的话,那么3D建模技术打造的虚拟拟真环境可以说在事实上终结了“那种艺术”,从此艺术史上的诸多视觉风格变成特效列表中的选项。对真实世界的视觉描摹已经完成了,接下来的艺术出现在哪里?是否要通过在拟真环境中添加其他感官维度来创作呢?比如电子互动艺术装置引入的多媒体交互?
这就来到了上文提到的第二个特殊节点,关于电子交互装置我在此不多赘言,感兴趣的可以阅读这篇文章《控制论的意外发现:艺术与电子游戏》。这里我直接说结论:(电子交互装置)“…的审美维度不仅仅停留在视觉或智识的愉悦,而是一种参与到即时反馈过程中的体验感。”近年的创作也已经证明,电子工业和软件产业背后的技术,完全能被创作者用来进行新的叙事。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作品是2010年前后曹斐基于电子游戏《第二人生》(second life)的创作。该游戏2003年上线,是web2.0时代的标志性网络游戏。玩家们在其中创造自己的虚拟化身进行类似现实世界的交互。曹斐在游戏中化身名为China Tracy的女孩,并将Tracy在虚拟世界中的事件和活动记录剪辑成短片,仿佛这是自己真实生活的一部分。此外,曹斐还在游戏里创造了一个叫RMB city(人民城寨)的主题公园,以艺术品收藏的方式在现实世界中出售RMB city的房产和使用权。
电子游戏(作为虚拟空间的表现形式)在这里成为一种艺术创作媒介,而且在近些年随着电子游戏相关技术(交互设备、游戏引擎、光追技术……)的发展不断完善。那些高成本投入的拟真游戏受众越来越广,它们在总体上似乎进行着一种有关后人类虚拟身体的新叙事(见《从'刺客信条'对历史古城的还原,聊聊“赛博déjà vu”》)。创作者(包括游戏制作人和以游戏为媒介的艺术家)能在其中完成何种程度的个体叙事,是电子游戏这种媒介技术能否具备艺术特征的关键之一。
在之前一篇文章的留言中,老白认为“游戏能否被称为艺术已经无须再作争论,当前的主要问题是游戏的创作方法论与评估体系远未成熟…现有的社会结构和理论体系根本还没做好推进游戏发展到下一个层级的准备。”某种程度上讲确实如此,我们能看到创作者们在资本之外的各种努力(此处可移步重轻老师的《资本·游戏》系列电台)。电子游戏具备个体表达叙事的潜力已经是一种既成事实,但是除去浪漫化的英雄主义色彩,这能在多大程度上抗衡资本,从而改变这种媒介技术的整体面貌?
说到这里,我想先讲一段鲜为人知的艺术史故事。这段历史展示了当一种通用技术被更具现实感的力量(资本或政治)攫取,创作者为其灌注个体文化叙事的努力显得多么的渺小。
三、没有艺术家的媒体
三、没有艺术家的媒体
这段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它是关于电视广播和艺术家的故事。
在web2.0时代之前,电视曾是家庭生活的中心,它是娱乐、教育、新闻的集散地。普遍来说,电视被视为一种“大众媒体”,并未和艺术搭上多少关系。但是在1920年代直至80年代之间,电视广播曾被视为潜在的艺术形式。瓦尔特·本雅明、未来派和卢西奥·丰塔纳都曾认为广播和电视是艺术的延伸。也曾有诸多创作者做出尝试,甚至在1960年代出现过一种让艺术家接管电视的想法,让电视成为数千人家中的艺术馆。
70年代,维拉·埃斯科佩(Valie Export)在ORF电视台进行了一系列将普通家庭生活搬上电视的项目。1971年的《面对一个家庭》(Facing a Family)中,客厅里的电视播放其所在家庭的日常生活,使其成为这个家庭的一面“镜子”。埃斯科佩使用这种大众媒体探讨私人和公共领域界限的模糊。几年后,真人秀娱乐节目出现,至今都是一种受欢迎的节目类型。关于电视媒体中公共与私密的艺术讨论也就此被淹没在商业娱乐的浪潮中。
电视艺术最坚定的守护者白南准曾声称屏幕取代了画布和颜料,他进行了一系列将艺术通过电视带向大众的尝试。在1973年的《全球音轨》(Global Groove)中,白南准试图使用卫星电视建立一个全球电视画廊。他提供了一本“像曼哈顿的电话号码薄那样厚重”的电视节目单,邀请欧美国家的观众参与在不同频道来回切换,欣赏数不尽的节目。但是实现效果并不理想。于是白南准在1988年实施了一个更大规模的项目《将世界包裹》(wrap around the world),据称有来自而多个国家的五千万观众。他似乎跨越了先锋艺术和大众之间的界限。但是代价是他的作品不再被视为艺术,项目由于其娱乐性几乎没在艺术圈内制造声浪,又因为其过于概念在电视领域也没能有后续影响。
1953年电视刚刚进入西德时,媒体学家格哈德·埃克特(Gerhard Eckert)曾在《电视艺术》(Die Kunst des Fernesehens)一书中写道“电视已经是一种艺术形式。他一定是明日的艺术。”但是同时,经历过美国电视语境的德国哲学家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却认为,电视是一种“文化工业阴谋”,它“……延续产业的意图去全方位地包围和捕捉公众的意识,乃电影和广播的集合体……只要文化产业还没有全权控制一且可见的维度,私人在文化产业面前就仍可保留存在的空隙,而如今这一空隙已被堵塞。”
关于电视广播艺术的尝试和争论背后,是欧洲和美国代表的两种不同的电视广播模式:美国的电视台靠广告商业化运作,欧洲则是由国家完全掌控,后者的节目通常更有文化内涵和政治目标。但是这种争论和差异在1980年欧洲引入商业电台后结束,终于是美国式的商业模式获得了胜利。收视率几乎成了评价电视节目的唯一标准。
对这段历史颇有研究的迪特尔·丹尼尔斯(Dieter Daniels)认为“(电视)是一个坚固的媒体系统,其技术资源比相应的媒体美学发展得更快,且没有给试验留出什么空间。”他描述了那些艺术家的尴尬状态“电视和其他大众媒体中的商业和政治权重远在美学和文化之上,艺术家在另类模式下工作,只能象征性地赢回媒体,但他们对媒介整体的商业和政治变化却毫无办法。”
而德国艺术家乌尔里克·罗森巴赫(Ulrike Rosenbach)则更加刻薄:“我们小看了电视的权力地位、它的固执和社会意识形态,它必定觉得我们的瓦尔特·本雅明理论幼稚而可笑。”
本文到此为止。我并没有什么结论或者答案,讲述这个故事并不意味着我认为电子游戏的命运也会如此,我们仍身处于这段历史进程之中,难以窥见全貌(至少以我的能力是如此)。而这个关于电视艺术的故事,哪怕当做一个微小的提醒也好。
延伸内容
延伸内容
1. 网飞出品的纪录片《抽象:设计的艺术》第二季第一集,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B站就有熟肉,建议安静的时候找一个大屏幕欣赏,将会是非常有趣的观看体验。
3. 展览:《布鲁斯·瑙曼:OK OK OK》,2022年03月11日-2022年06月12日在北京木木艺术社区展出。布鲁斯·瑙曼曾以电视/录像艺术家的身份参与到电视艺术的尝试之中,在他身上可以一窥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在电视/录像媒介上做出的努力。主观提醒:观展的时候不要报过高的期望,在我看来这更类似于一个网红化的历史回顾展。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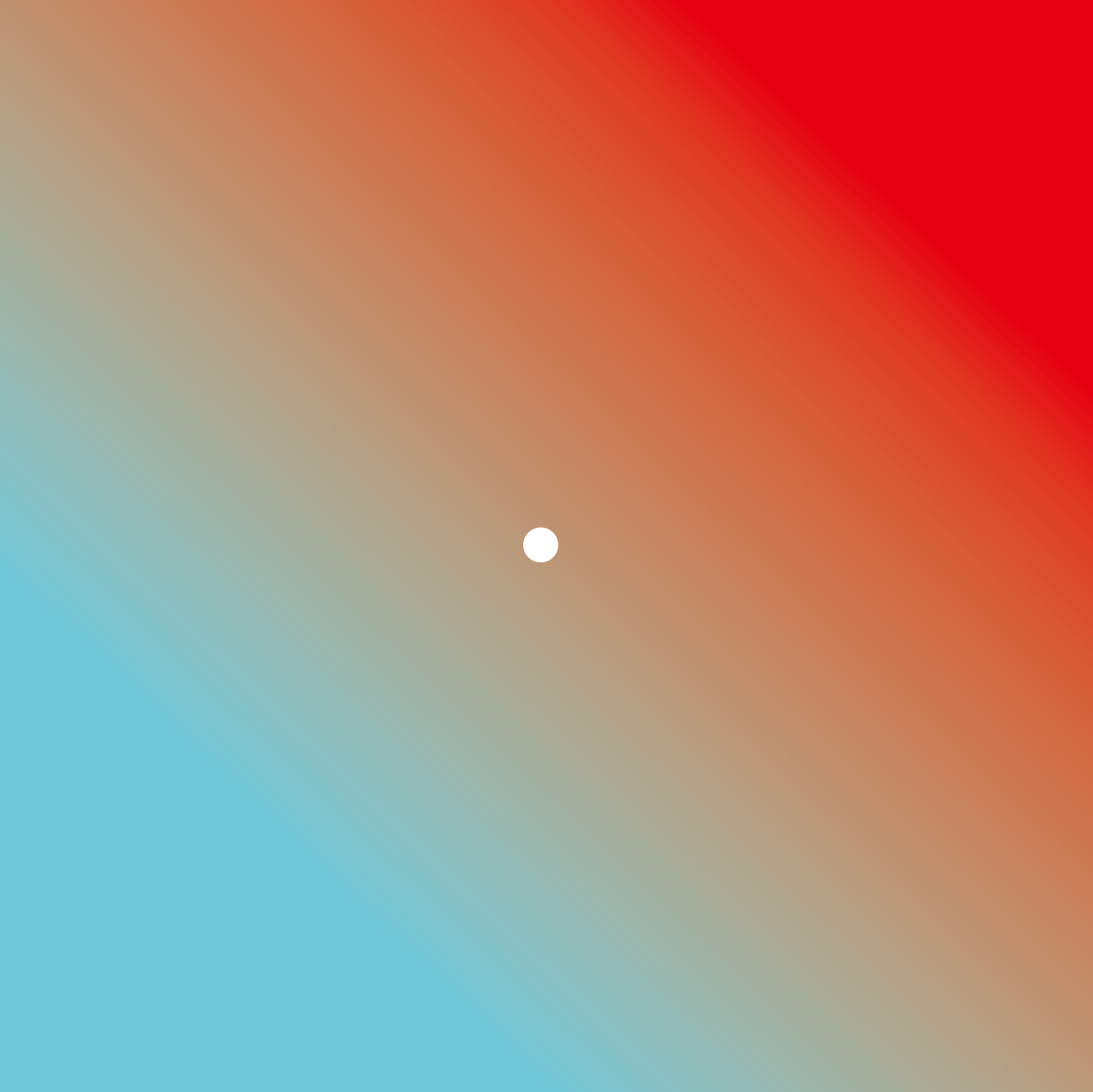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6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