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对研究-创作的研究丨落日间
对研究-创作的研究丨落日间
我意识到最近大概两年中,我在逐渐地转变自己的工作方法,将其朝向一种我称之为界面式的研究/创作(Interface Research Creation)的方法论靠拢。
且不谈界面,最近在分享教学过程中我觉得自己并没有完全地厘清研究和创作之间的关系:与同行不同,或许是我自身的学术化的人文背景缘故和探究方法,但总之,我觉得值得从这点部分的思考出发去尝试寻找更多的联系。
问题来自于,艺术(游戏)创作需要研究吗?在印刷媒介依旧统治学术圈的时候,艺术创作能够作为研究的形式吗?艺术创作在什么地方需要引入研究的方法(人类学/在地研究/艺术史等),这种科学化或学术化进程对于人文社科还有艺术的创作的影响是怎样的?而这正确吗?
基于研究展开创作,首先破除了灵感天才的浪漫传统,使创作/创造力成为一定量的研究工作投入之后可预期的必然的结果,并能以研究的态度及时总结创作方法,更新创作方法。对创作方法论有研究能力与反思能力的艺术家,必定是能够不断地自我发展,不断进步的艺术家。到最后创作和研究将会浑然一体,创作也是一种研究,研究也是一种创作。
游戏设计师 Pippin Barr 所在的魁北克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游戏研究与设计跨学科平台 TAG 的工作方式是我对自身方法命名的来源,他们有开展使用游戏进行的诸如对赌博的电子游戏社会学研究、通过游戏设计探索人工智能形式的不可靠的用户界面等:
游戏研究无疑是 TAG 的一个主要方面,我们有许多教师和研究生积极从事游戏研究工作。然而,TAG 一直对关于游戏和可玩媒体的学术研究有着更广泛的理解。特别是,我们非常强调制作游戏(和类游戏体验)作为一种研究方法的重要性。在加拿大,这种学术研究方法被称为研究创造(Research-Creation),是一种公认的研究方法。
而当然,作为一个认同数字人文宣言 2.0 The Digital Humanities Manifesto (2008) 的在野研究和创作者,落日间提倡一种研究与创作、理论与实验、多种媒介共同作用的混合,就像是《非平面》用漫画写作学位论文,《电影史》用电影书写电影史,Jesper Juul 与 Gualeni 也用游戏自身去谈论和做游戏研究,希望这部分的工作能有所启发,让一种「非正统的」但却饱含生命力的学术/创作得以生长。
译按
译按
Artistic Research 这个传统在国外已经有接近了三十年的讨论,而对其的翻译在国内也并没有完全确定。
先前 陈淑瑜丨可以正确地误解我吗?——对“研究型策展”的思考 中将其翻译为「艺术研究」,而科技史在介绍其期刊 Journal of Artistic Research|期刊 时则译作「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为了避免造成误会(对艺术的研究),且基于通俗化的传播理解,在此采用后者,并且在短语中使用为「艺术式研究」以区分。而实际上也有其他表述诸如:「基于艺术实践的研究 art practice-based research」,或「作为研究的艺术 art as research」等等。
我认为这个传统中蕴藏着一种艺术内在的张力与争夺:既要将自己从天才式、灵感式或神秘主义/浪漫主义的谈论中接受一种「理性化」,而又要与如日中天的技术与科学研究保持一个合适的位置,并且不让自己被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论的扩展所侵占,这是要害之处。
科学与艺术,研究与创作,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争执,这也并不稀奇,不过是又回到了牟宗三先生说得很清楚的外延真理-内涵真理两分的讨论,让我不经想起胡塞尔那本著名的标题:《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还有保罗克利、康定斯基的艺术理论研究。
本篇翻译为三部分组成:
- 近来来自 w/k 期刊的引入性文本《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2021)
- 经典的定义性文本,来自 Julian Klein 的《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11)
- 一部分的 JAR 近期的研究课题的简介
希望能够通过这样的介绍-文本-例子的三重内容作为整体对于「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的领会。
Angelika Boeck, Peter Tepe 什么是艺术化研究?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21)
Angelika Boeck, Peter Tepe 什么是艺术化研究?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21)
February 25, 2021
Translated by Rebecca Grundmann.
摘要:为了使「用艺术方法做研究」(Artistic Research)这个话题更容易被不太熟悉的观众接受,Angelika Boeck 介绍了她对「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的理解,并推荐了她认为重要的文本。此外,Peter Tepe 提供了关于主题的整体信息,并试图确定其定义性的特征。
1. Angelika Boeck:我对「用艺术方法做研究」的理解
1. Angelika Boeck:我对「用艺术方法做研究」的理解
自1999年以来,我一直在利用我艺术实践的手段和方法进行研究。我题为《西方凝视的去殖民化:肖像作为一种多感官的文化实践(2019年)》的论文也致力于这一立场。「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是一个宽阔的领域;它包含了许多不同的概念。
我更愿意使用 「基于艺术实践的研究」(art practice-based research)这一术语,因为我认为它是建立在特定艺术实践基础上的研究:
首先是艺术家通过采用艺术手段和方法来寻求一个具体问题或一系列尚未明确定义问题的活动,其次是以艺术作品的形式来展示这一过程/或结果。其与科学策略实践相近的地方在于都试图寻求「尚未知晓」之物(Klein 2011);都渴望展示和理解;在于艺术家经常使用人种学、社会学、收集/存档或实验室工作的实践;在于他们通过过程进行试验以产出图像货处理新媒体和技术科学(例如巴西媒体艺术家/理论家 Eduardo Kac,他根据美学标准操纵生物体,作为其90年代早期生物艺术或转基因艺术的一部分)。
因此,「用艺术方法做研究」可以被认为是处理人类主体(包括自身)、对象和背景(当下的或历史的)的一种手段,这种检视往往与获得具体经验,并努力以可感的形式传达这些经验(以激发思考、娱乐、干扰或挑衅)的兴趣相结合。因此,「用艺术方法做研究」不仅仅是分析某个给定的环境或某些情绪的问题。
反思是在艺术生产过程中发生的。其他形式的知识生产(特别是在自然科学领域)需要使用被验证的方法(approved methods),成为理论性话语,以及对研究过程的可验证、可归纳和可理解的描述的一部分。
「用艺术方法做研究」则以不同方式运作:方法和理论方面往往只能通过逆向工程的过程(reverse engineering)来回溯性的确认。这意味着艺术作品的创作过程被检视并与其他艺术家、科学家和理论家的工作相联系,以提取出它们的构成部分。艺术家的书面反思(提出问题,确定背景和条件,提供方法和理论的信息,自我反思)是可能的,但不是绝对必要的;尽管我认为这是有益的。
2. 「用艺术方法做研究」:信息和定义
2. 「用艺术方法做研究」:信息和定义
为入门,Peter Tepe 采取了一种有限范围的示范性方法:他从《「用艺术方法做研究」作为一种美学科学:对科学和艺术的跨学科混合的贡献》(Kunstforschung als ästhetische Wissenschaft)一书中选择了不同的有意义的引文,这也与即将进行的讨论有关。所选的引文一方面传达了关于艺术式研究的整体信息,另一方面则是试图确定其定义性的特征。
让我们从五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开始。
引言1
「艺术式研究(以及该术语的其他变体)已成为经常被引用和审视的关键词,它们已进入了艺术学校、科学机构以及(欧洲)文化和创意产业政策指导方针的理论话语和实践。它们导致了新的研究所、期刊、协会、补贴计划等建立。同时,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人文学者和艺术家对艺术式研究的概念、形式和方案持批评态度,甚至拒绝接受。」 (IX) J-B. Joly/J。Warmers。
引文2
[......] 艺术研究、艺术式研究或基于艺术的研究是目前流行的术语,但我们可以猜想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如果我们关注国际辩论[......],我们可以确定一系列的概念。(XV) M. Tröndle.
引文3
在科学与艺术接触的传统中,哪些形式的知识可以通过艺术,且仅仅是通过艺术而获得?这个问题仍然有很大的意义。艺术实践传达了什么;哪些是无法通过科学研究而传达的?艺术在认识论上的贡献是什么? (21)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4
「在博洛尼亚改革的压力下,艺术院校为了获得博士学位并在全球竞争中生存,使用'艺术式研究'一词的动机是可以理解的。[......]许多讨论以及2010年在伯尔尼成立的艺术式研究协会的高价机构会员资格,清楚地告诉我们在此处理的是政治上形成的动机。此外,艺术式研究领域的补贴计划对申请者来说太有吸引力了,而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其之外[...]。艺术理论家也从新术语中获益,因为它开辟了新的交流渠道和影响领域。」(27) K. van den Berg/S. 奥姆林/M。Tröndle.
引文5
「'艺术式研究'是一个时髦的术语。它为我们提供了机会,在当前话语中为我们的思想和行动贴上一个新的有吸引力的标签」。(267). S. Grand
让我们继续讨论艺术研究的各种定义。
引文6
'以艺术方式的研究 Researching in the arts',也被称为'作为研究的艺术'或'通过研究的艺术',目前在艺术家和艺术学校的代表性话语中被称为艺术式研究。研究目标是创造新的艺术作品或审美过程,并通过这些作品,艺术家成为了研究者,或换句话说:艺术家作为研究者的形象占了上风。(24) K. van den Berg/S. 奥姆林/M。Tröndle。'所有好的艺术都是研究的结果'这句名言也属于此范畴'(26)。
引文7
艺术研究可以[......]被译为 künstlerische Recherche 而不失其意义"。(28)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8
'通过艺术的研究'有时也被称为'艺术研究'或'应用艺术研究'。[......]以这种方式理解,艺术研究更具有跨学科和实践导向性(practice-oriented)。由于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人们可以认为,研究过程不能由单一学科的人进行,而必须采用跨学科方法,产出也不一定要采取艺术品的形式,而应主要在科学的背景下进行感知。艺术家与科学家合作进行研究,研究过程作为一个团队进行,结果以文本、图像、声音、过程的形式出现。[......] 以这种方式设想的艺术研究以跨学科的方式,将艺术式研究的实践与科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从而改变研究本身的社会实践"。 (25) K. van den Berg/S. Omlin/M. Tröndle。
引文9
艺术式研究试图在艺术生产之中,并通过艺术生产,不仅对艺术领域做出贡献,而且对我们'知道 know'和'理解 understand'的之事做出贡献。(80) H. Borgdorff.
引文10
艺术式研究有助于 "对知识和知识结构的破坏;对既定真理和边界的瓦解。它更多的是一个舍却所学(unlearning)的过程,而不是对所教知识的重复(reiteration)"。(133) M. Brellochs. "艺术式研究允许事物的状态保持流动、敏捷和变异"。(135)
引文11
"艺术式研究首先提供了一种迷人的可能性,可以自由质疑艺术和科学中被认为是不证自明的东西[...]。艺术式研究使我们能够更仔细地观察艺术和研究中的 "他者 Other "——不是观察其"是什么",而也观察 其 "可能成为的"。 (269) S. Grand.
引文12
"艺术式研究,或者我更愿意称之为:艺术式思想和行动(artistic thought and action),与科学的工作方式不同[...]。在艺术工作中,重点主要是在人身上[......]。出发点是的真实个人的艺术家具有识别价值的'签名',主要是以视觉形式出现"。(298) U. Bertram. "一个重大的误解来自于这样的假设:艺术式思想必须引向艺术,而这并不存在于科学的范畴。然而,艺术式思想和行动十分适合作为科学发现过程中的启发式的边缘(instructive marginals):'创造力不是艺术的俘虏'"。(310)
引文13
"艺术式研究真正有趣的地方" 是 "一种研究概念的可能性,它并不意味着科学研究,但仍然符合研究的标准(即寻求知识)。(345). J. Badura. "当前讨论的新颖性在于[......]明确而高调地要求艺术的认知能力与科学的认知能力相当"。(346).
3. 开始的文献:个人建议
3. 开始的文献:个人建议
对于那些不太熟悉「艺术式研究」这一主题的读者,Angelika Boeck 推荐了对她来说特别重要的各种文本,她认为这些文本提供了进入这一思维方式的途径。她还分享了这些文本对她的启发。
作曲家和戏剧导演 Julian Klein 在他的文章《什么是用艺术方法做研究?》(2011)中指出,作为文化事业,艺术和科学都「在传统和创新之间取得平衡」;所有的研究,无论是艺术还是科学,都是一种系统的知识生产的创造性活动,在「求知欲」的推动下,在 「尚未知晓」的状态下运作。Klein 认为,艺术式研究可以帮助回答当下的问题,如:我们如何在不同的文化、传统和观点中相互理解?(Klein, 2017)。虽然我怀疑自己能否通过自己的工作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但对我来说,不忽视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于默奥大学(Umeå University)文化和媒体研究系的民族学教授 Billy Ehn 分享了对我有类似激励作用的洞察。他研究了文化研究者和艺术家在策略上的异同,并认为他们各自的工作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似的:都提出问题,选择方法和阅读理论,收集材料并通过观察、采访、上网和参加社会活动获得新想法,并据此追求不同的问题。他发现,艺术家采取了一种更有趣的方法,并遵循直觉;他们更倾向于将平凡之物视作某种不寻常之物。他认为特别重要的是,他们有能力把自己看作是行动者(actors)以及研究对象(objects of research),他们愿意以实验性的方式生活,并渴望产生自己的经验,而不仅仅是分析它们。据他说,科学研究也可以受益于艺术家将自己暴露在不寻常的环境中并追求不寻常的想法的特殊性质(Ehn 2012: 14 ff)。
艺术和人类学是在我的论文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两个实践领域。例如,Arnd Schneider 和Christopher Wright 在他们的作品 Between Art and Anthropology(2010年)和 Roger Sansi 在 Art, Anthropology and the Gift(2015年)中讨论了这两种实践间的联系点。
对我来说,这两种立场都很重要,原因各不相同:Schneider 和 Wright 处理的是将两种传统结合起来的亲属关系(这在于视觉媒体的使用以及视觉理论使用),而 Sansi 也将注意力转向文化实践、媒体和感官之间的联系,这对我很重要。这些作者的作品帮助我更清楚地定义了我自己基于艺术实践的研究,它位于「作为人类学的艺术 art as anthropology」(Sansi, 2015: 29)的领域,在这种艺术形式中,艺术家处理的问题和想法也是社会和文化人类学所感兴趣的。
在她的书 Eine epistemologische Ästhetik (艺术式研究:一种认识论美学, 2019),哲学家和艺术家 Anke Haarmann 研究了艺术式研究的原始方法、历史先驱、特定的衔接形式和具体的行动模式。其中,她揭示了围绕艺术式研究的讨论与博洛尼亚进程(Bologna Process)密切相关:博洛尼亚进程是欧洲范围内的高等教育改革,建立了一个统一的专业资格的学术学位体系。她反对于对艺术的方法性规定(methodical regulation),并在其认识论美学的框架内,主张为作为一种方法和实践的艺术式研究找到新的术语。为此,有必要将重点转移到艺术家的具体的方法和实践上,而不是仅仅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已有的方法和实践来衡量它们。基于我在论文期间获得的经验,这是我支持的一个立场。
Literature
Literature
Ehn, Billy (2012): Between Contemporary Art and Cultural Analysis: Alternative Methods for Knowledge Production. In: InFormation – Nordic Journal of Art and Research, 1 (1), S. 4–18.
Haarmann, A. (2019): Artistic Research. Eine epistemologische Ästhetik.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Klein, Julian (2011): Was ist künstlerische Forschung? In: kunsttexte.de/Auditive Perspektiven,Nr. 2, www.kunsttexte.de
Klein, Julian (2017): Seven Answers. In: Jan Kaila, Anita Seppä and Henk Slager (Hrsg.): Futures of Artistic Research. At the Intersection of Utopia, Academia and Power, Academy of Fine Arts, Uniarts Helsinki. https://helda.helsinki.fi/bitstream/handle/10138/246117/Futures_of_artistic_research_kirja.pdf?sequence=1&isAllowed=y
Schneider, Arnd, and Wright, Christopher (Hrsg.) (2010): Between Art and Anthropology: Contemporary Ethnographic Practice. Oxford: Berg.
Sansi, Roger (2015): Art, Anthropology and the Gift, London: Bloomsbury.
Die bis 2017 veröffentlichte Literatur zum Thema „Künstlerische Forschung/Artistic Research“ ist vom Zentrum Fokus Forschung der Universität für angewandte Kunst Wien gesammelt worden. Diese Liste lässt sich hier einsehen.
二:Julian Klein 什么是用艺术方法做研究?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11)
二:Julian Klein 什么是用艺术方法做研究?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2011)
Julian Klein
Julian Klein
Julian Klein 是德国柏林艺术研究所的所长。他学习作曲、音乐理论、数学和物理学。他是跨学科表演艺术团体a rose is的创始成员和艺术总监。从2003年起,他是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和德国国家自然科学家学院 Leopoldina 的青年学院成员。目前,他是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研究所的合作学者和加拿大蒙特利尔 Concordia University 的研究员。自2007年起,他在柏林艺术大学教授导演。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Gegenworte 23, 2010, Berlin-Brandenburg Academy of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最初发表于: Gegenworte 23, 2010, 柏林-勃兰登堡科学与人文学院。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WHAT IS ARTISTIC RESEARCH?
抱歉,这个问题提得不对,古德曼(1978)。我们应问:什么时候研究是艺术的?(When is a research artistic?)- 但让我们从结果开始。
Research 研究
Research 研究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定义,研究是「为增加知识储备而进行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性活动(any creative systematic activity),包括关于人类、文化和社会的知识,以及利用这些知识来设想新的应用。」(OECD统计术语词汇表, 2008)。
因此,研究意味着未知(not-knowing),或确切地说:尚未知晓(not-yet-knowing)和求知欲(Rheinberger 1992, Dombois 2006)。研究似乎也不是科学家的独特卖点,而是包括例如艺术家等人的许多活动。他们中的大多数创造性地、且常常是系统地工作,这恐怕无可争议。另一方面,即使其中提升知识的动机在整体上并不明显,他们肯定需要通过使用自己以某种方式获得的知识来进行和反思他们的创作,他们的研究也是如此,这不仅是最近的事,从一开始便是如此。
正如 Baecker(2009)所描述的,由于许多原因,对于研究和艺术交叉(junctions)的反感主要是开始于它们的实证性(substantification):在科学主义的世界观中,艺术家们「做研究」似乎比他们在逻辑上必须属于「研究」的工作产出更为容易。Lesage 怀疑这种拒斥是担心资源获取的限制,并以「谁在害怕艺术式研究?」作为他文章(2009)的标题。
在我们把 McAllister(2004年:「我认为,艺术式研究是存在的」)作为倒数第二个论点引用之前,我们也许可以通过提供一个分类区分来保留下几分,例如根据 Jones(1980年)、Frayling(1993年)和 Borgdorff(2009年)等人的说法的:可以区分区分,基于(其他)研究的艺术(art, which is based on (other) research);研究(或研究方法)被用于其中的艺术(art, for which research (or research methods) are used for),最后,以研究作为产出的艺术(in art, whose products are research)。Dombois (2009)通过交错法补充(chiastic complements)而扩展了这种三分法:「关于/为了/通过 艺术的研究 | 关于/为了/通过研究的艺术。」
正如 McAllister (2004) 所指出的,即使是自然科学研究,其对象、方法和产出也非常多样化。而这也多么适用于包括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进一步的,行业的市场或舆论研究。毫不奇怪,这对艺术式研究来说也是如此。这里引用的作者中,大家都一致认为,这种多样性必须被保留下来,以抵制规范化的限制(canonical restrictions)。
没有研究的艺术缺乏必要的基础,正如科学中的情形。作为文化发展,两者(科学与艺术)都处在传统和创新之间的平衡上。没有研究的传统将是盲目的接管,而没有研究的创新将是纯粹的直觉。但凡科学家不做研究,而是教书、评论、建议、治疗、应用,或者或多或少地公开说话(所以:「推下」......按钮),他们可能仍然在搞科学(operate science),但如果他们不做研究就承担这一切,他们就不太与他们的事业相符。对于艺术家也可以这么说。而另一方面,很明显,并非所有的艺术都会算作研究,就像科学也一样。
然而,主要的判断是,就如同没有多少单纯的「科学」或「艺术」,单数的「研究」也很少存在。它们都是集体的复数,集合了非常不同的过程,这些过程往往在类型边界上,它们与其他事物(如学科)的关系比与其自身学科内一些其他成员更密切,并且在如主题、方法或范式这样共同的跨学科屋檐下更好地集合。这种「单一化的冲动」(urge of singularization)可能是艺术和科学之间所谓顽固对立的最强大根源。Baecker(2009)称这是「功能性差异的组织原则 organizing principle of the functional difference」,根据 Mersch & Ott(2007),它出现在19世纪。
艺术和科学不是独立的领域,而是共同文化空间中的两个维度。这意味着某些东西可以有更多或更少的艺术性,也没有事物可以说一定有科学性的数量。这对许多其他文化属性也是如此,如音乐、哲学、宗教或数学。它们中更多依赖于彼此而不是孤立。在这方面,拉图尔的判断在这里可以作为参照:「没有两个部门,而只有一个部门,它们的产出将在之后,在联合检查(joint examination)之后被区分出来」(1991年,第190页)。然而,至少不是所有被认为是艺术的东西都必须是不科学的,也不是所有被认为是科学的东西都是不艺术的。Dombois 为「作为艺术的科学」(Science as Art)提出了五个标准(2006)。大量的例子表明,艺术和科学内容独立的对象、活动和事件能以更多且不同的剂量混合。如果研究是由艺术家开展的(尽管他们的参与或许是有帮助的),那么研究就不是或不仅仅是艺术的,而是应该具有「艺术」的属性,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由谁来做,都形成一种特定的性质:艺术体验的模式(the mode of artistic experience)。
Artistic Experience 艺术体验/经验
Artistic Experience 艺术体验/经验
在审美感觉的模式中,知觉是存在于自身的,不透明的且感知性的。艺术体验可以被确定为类似于感性介入框架的知觉模式(perception mode of sensible interfering frames,详见 Klein 2009)。根据这一判断,拥有一种艺术体验意味着从一个框架外看,并同时进入到框架内。以这种方式穿越我们的知觉的框架,是相当在场并可感的(Fischer-Lichte 2004 称之为「阈限状态」(liminal state))。艺术体验和审美感觉是我们的知觉模式,因此,即便在艺术作品和艺术场所之外,也持续是可用的(available)。
在体验中,主观视角被构成性地包含在内,因为体验不能被委托(delegated),只能进行二阶的主体间的协商(negotiated intersubjectively in second order)。这也成为了艺术知识的的奇异特性构想的一个主要原因(Mersch & Ott, 2007, Nevanlinna 2004, McAllister 2004, Busch 2007, Bippus 2010. Dombois 2006 指出 Barthes 在1980年提出的 "mathesis singularis" - 译注:指某种独特存在的不可能性科学 impossible science of the unique being )。艺术经验特别依赖于潜在的经历,并与之密不可分。艺术经验是一个积极的、建构性的和审美性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模式和实质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这与其他通常可以与它的获取分开考察和描述的隐性知识不同(见 Dewey 1934, Polanyi 1966, Piccini and Kershaw 2003)。
Artistic Research 艺术式研究/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
Artistic Research 艺术式研究/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
如果「艺术」只是一种感知模式,那么「艺术式研究」也必须是一个过程的模式。因此,「科学」和 「艺术」研究之间就不可能有绝对的区别:因为这些属性独立地调制着一个共同的载体,即研究中的知识目标。因此,艺术式研究总可以也是科学研究(Ladd 1979)。由于这个原因,许多艺术式研究项目是真正的跨学科,或者更准确地说:非学科(indisciplinary)(Rancière in Birrell 2008, Klein & Kolesch 2009)。
在这种背景下,「作为研究的艺术 art as research」的说法似乎不太准确,因为并非艺术以某种方式演变成研究。然而,存在的是成为了艺术的研究,所以它应该被命名为「作为艺术的研究」,其核心问题是:何时研究是艺术了?When is Research Art?
在研究过程中,艺术式体验可以在不同的时刻发生,具有不同的持续时间和重要性。这使项目的分类变得复杂,但另一方面也允许有一种动态的分类法(dynamic taxonomy):在什么时候,什么阶段可以进行艺术式研究?首先,在方法上(如搜索、存档、收集、阐释和说明、建模、实验、干涉、请愿......),但也在动机、灵感、反思、讨论、研究问题的提出、构思和构成、实施、出版、评估、话语方式上,在此仅列出开头。这些阶段只能事后总结和分类,例如在通常的对象、方法和产出三者之间。这个顺序很重要:因为关于艺术研究的讨论不能落入规范系统的标准限制中(Lesage 2009)。
艺术式研究的反思将发生在哪个层面?一般来说,是在艺术体验本身的层面。这既不排除在描述性层面的(主观或主体间性的)解释,也不排除在元层面的理论性分析和建模。但「反思只可能来自外部,这是一个神话」。(Arteaga 2010)。艺术体验(Artistic experience)就是一种反思的形式。
Artistic knowledge 艺术知识
Artistic knowledge 艺术知识
我们是谁?我们想怎样生活?什么是事物的意义?什么是真实的?我们能够知道什么?某物何时存在?什么是时间?什么是原因?什么是智识?感知在何处?这一切会不会是其他的?这些都是共同的艺术和科学所兴趣的例子。对它们的处理并不总是导向可靠和和普遍有效的知识(就科学史而言: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不是吗)。艺术被授予权力,以其特定的方式阐述和处理这些基本而又复杂的问题,而不一定比哲学或物理学所反映得少,并能够获得其他方式无法提供的独特的知识。
对知识的艺术性渴求是否可以作为把调查(investigation)也称作「研究」的理由,显然取决于这样一个问题:哪些类型的知识被归入认知(cognition)的概念,或哪类的认知构成了知识的范畴。即使我们能同意知识是「有理由的真实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我们也必须进一步争论,因为我们必须对一个观点何时是信念的理解,以及究竟什么能成为这种信念的辩护达成共识:真理的概念仍然散落。
这条道路偶尔会导致最终的争论,在每一种情况下都会出现我们可以接受或不可以接受的情况(见 Eisner 2008)。对于那些最终成为元语言(如知识)的部分术语,我们经常体验到:我们越是试图确定它们,我们就越是被迫进行着规范性的判断,而这些判断主要是基于我们希望它们意味着什么。而可行的是,或许能够让知识囊括经验,作为认知(cognition)和技能(skill)之外的第三个类,或者知识和经验作为认知的形式并肩而立,它们至少应该被认为是等同的。
一些作者要求艺术知识还是必须是言语化的(verbalized),然后才可与陈述性知识相提并论(例如,琼斯1980年,2004年AHRB)。而其他人说它体现在艺术的产出中(例如Langer 1957, McAllister 2004, Dombois 2006, Lesage, 2009, Bippus, 2010)。但最终它必须通过感官和情感感知,恰恰是通过艺术体验来获得,它不能与之分离。无论是无声的还是言语化的,陈述的还是过程式的,隐含的还是明确的,无论如何,艺术知识都是感性的和身体的,是「具身的知识 embodied knowledge」。用艺术的方法做研究所追求的知识,是一种可感的知识(felt knowledge)。
(引用见原文链接)
三:JAR 期刊研究举例
三:JAR 期刊研究举例
声学调查(Acoustemological Investigation): 声音日记 # 德黑兰是一个以研究为基础的项目,作为我正在进行的博士研究的一部分。通过使用感官方法论作为研究工具来观察和分析建筑和城市设计来实践。在我看来,艺术和建筑总是具有社会变革和改善现有社会秩序的潜力。它们可以是解放的、有助于自我发展的、促进社会正义的,甚至在一些小方面改变我们所生活的世界。
我的研究探索了rangoli 和 kolam 的地板艺术实践,以了解他们的研究植物的教育性潜能。这项研究包括分析 rangoli 和 kolam 图像的个人档案和一系列的艺术合作。作为本土的艺术实践,rangoli 和 kolam 已经超越了传统媒介,包括哪些用我们的手指在水稻种子上撒粉画点和线条,用各种各样的花朵、叶子和树枝装饰地面等。
作为一种艺术-学术研究的混合式方法,研究-创作(research-creation)在解决复杂的社会-技术问题方面已被证明有效,并同时有效消除了在更传统的研究实践中出现的二元性。鉴于在食品领域中,构成食品文化和系统的知识是多元化的,这点尤其重要。此外,粮食蕴含着我们当代面临的一些最关键的挑战,如饥饿、移民、贸易、气候变化和正义。
一般来说,动物园的建筑将人们的注意力引向动物。正如约翰·伯格在他1977年的文章《为什么看动物》中所说的那样,建筑物在动物周围创造了「画框」。在这个前提下,我的作品探索了框架的视觉和心理方面,与动物居所有关。Judith Butler (2009) 解释了(视觉)框架如何总是创造意义和评价其中包含的内容。因此,动物在人类文化中的代表性影响着我们在社会政治上对待动物的方式。
Raising the Voice: Sculptural and Spoken Narratives from the Flat Sheet 扬声:来自平板的雕塑和口语叙事
本论述通过雕塑和从平板上升起的文本来探讨叙事和讲故事的想法,这是一种既特殊又多元的视觉和口语诗歌。在本文中,调查的关键领域将是我的实践中雕塑和口语叙事之间的关系。这将在四个主要领域进行讨论:作为讲故事的场所的平张和折叠、故事讲述所固有的多重性、建筑性和身体与建筑之间的空间、言语、文本和声音,以及它们与雕塑的关系。
Beyond the Visual - A research curriculum for explorations in spatiotemporal environments 超越视觉-一门探索时空环境的研究课程
虚拟现实和空间音频技术给建筑和音乐领域带来了一个新的模式。在这些媒体中开发的作品产生了超越物理世界可感知的体验,因此扩展了我们设计/创作的能力以及我们对空间和时间感知的感觉。通过在时空领域的操作,这些新媒体动摇了我们对空间和时间的学科理解以及它们的美学,需要一个全新的后学科的设计/创作和体验的概念。"超越视觉"是一个调查时空美学的研究课程,在建筑和音乐的界面上,关于感知和创造力以及设计/构图。
Ephemer(e)ality Capture: Glitching The Cloud through Photogrammetry 短暂(e)性捕捉:摄影建模中的云干扰成像
短暂(e)性捕捉。摄影测量中的突变实践,详细介绍了使用基于云的摄影测量的艺术实践,通过利用光学现象干扰成像算法,主动调用突变。反射的、透明的、镜面的和有图案的/重复的物体被用来混淆成像算法,在产生的三维物体的网格和纹理中产生尖峰、孔洞和故障。这项研究测试了摄影测量学的极限,以努力实现新的图像制作方法。
(以上研究都可以在浏览器直接打开浏览)
对「研究创作」的研究
落日间是一座有关「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迷宫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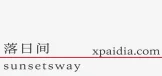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