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去学校的这段路程可以说是“颠沛流离”,整个人像是被装在一个雪克壶里荡来荡去的。我有些晕车,本想睡上一觉的,但这样的颠簸实在是让人不得安宁,我在半睡半醒之中到了学校,自然是满腹怨气。指南翁闭着眼睛不知是睡着了还是正在闭目养神,总之都让我又气又嫉妒。
当车子停稳之后,他慢悠悠地睁开眼睛,慢悠悠地伸了个懒腰,那慢条斯理地样子像是刚从一个美好的清梦中醒过来。我坐在比较靠后的位置上,所以我得等前面的同学都走了才好下去。等待的过程挺无聊的,我又不想和指南翁搭话,便自己望着窗外发呆。
下午三点的天空阳光很毒,隔着充满霉味与灰尘味道的窗帘都觉得刺眼。阳光下飞过去了一只鸟,它身后跟着一个飘在天上的妖怪,像是拖着个风筝在飞。那个妖怪以蝶泳的姿势飞行,长得样子看不太清,穿着一件栗色长衫,像是相声演员穿的那种衣服。
我正想看个仔细呢,这个妖怪飞到车顶上去了,再也看不见了。
指南翁肯定也看见了那个妖怪,但他故意不说,摆出一副高深莫测的样子,等着我发问。我已经知道该如何对付他了,便说:“要是黄雨潇在就好了,她一定知道那是什么。”
说话间我叹了口气,火上浇油地加上了一句:“偏偏和你在一起。”
这话像是锥子一样扎在指南翁那不可一世的骄傲上,他最受不得的就是这种激将法。他气的说:“那不就是个破麻雀妖,谁不知道?不过倒是不常见。”
说法的时候他的胡子都在颤动,我生怕它掉下来几根。
“为什么?”我很不解,“麻雀不是到处都是吗?为什么罕见?”
“麻雀到处都是,成精的麻雀难找,”指南翁说完还昂着头暗示自己,“就好比书本多了去了,书卷灵却很难找。”
我装作没听到,继续看窗外。
指南翁又说:“就好像蠢材一大堆,天才万里挑一。”
我根本懒得理他的挑衅,起身就往下走。指南翁在我背后“哼”了一声,如皇帝般趾高气昂。
我的学校建在江口的一片湿地上,四季的风都从这里涌向大海,妖气也被风从各个地方带来了。我拎着行李站在校门口,像是面对着一座魔窟。学校并不很恐怖,但妖魔鬼怪是真的很多。
原来附在车底的车蛎都爬了下来,步履艰难地往旁边停着的另一辆车爬去。它们蠕动的是如此缓慢,若不是知道它们是妖怪的话我还以为这是渔民在晒海货呢。借着弯腰从行李厢拿行李的工夫,我故意把包甩到了地上,这样可以蹲下装作收拾东西的样子观察它们了。经过观察我发现,与其叫它们车蛎,倒不如叫它们“车鲍”,它们并不是像牡蛎那样靠着壳粘附在车底的,而是靠着腹部——或者说应该是“腹部”的那么一个东西——把自己吸在车上的。他们像是背着一个牡蛎壳的蜗牛或者鲍鱼,动起来的时候软软的边缘像波浪一样往前翻涌,也看不出到底有脚没脚——反正在我看来是没有的。
综上所述,这东西是不是叫“车蜗”或许会更合适?或者说“车鲍蜗”、“车蜗鲍”?我不明白当初取名字的人为什么会想把这种东西叫车蛎,于是我问指南翁:“为什么它们叫车蛎啊?谁命名的?”
指南翁估计也不知道。他想了一会,含糊其辞地说:“自然有人命名。”
原来他也不是什么都懂啊。这么想着我的心情一下子好了许多。
我拖着箱子的时候有意绕着车蛎走,尽量不去妨碍它们。尽管我知道我不会踩到它们,但是我还是选择绕开了它们前进的路线。这些小妖怪有一点可敬:虽然不知道目的在哪,但却勇往直前;但反过来想这也很可悲:虽然一直前进,但永远不知道目的在哪。它们很像西西弗斯,一直重复着很盲目的工作。不同的是西西弗斯看得见终点,尽管它遥不可及;这些小东西们看不见,尽管它就是前面的另一辆面包车。
学校里花花草草很多,从我多年求学经历来看,再没有什么学校比我高中更美丽了。从校门进去就是图书馆前的广场,两侧栽种着桃花树,虽不至于有世外桃源的感觉,但也确实是“落英缤纷”了。在合适的季节里,这个广场像是个能卖60块门票钱的公园一样美。往宿舍楼走的路上还有许许多多的树和灌木,但我除了那些很有特色的棕榈以外什么都不认得。各种各样的妖怪盘踞在树丛花间,像是花果山的景色一般,即使此时有只猴子撵着个什么花妖从我面前跑过我也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可惜没有。
这里的妖怪很多,挑个我很有印象的树妖说说。由于我不知道他是什么品种,就不把他放在标题里了。
这个树妖并不像我在大多数游戏或者影视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是个充满智慧的老者,相反的,这个树妖是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头上的头发形如树冠,是个墨绿色的爆炸头,肆意地向四周伸展着,完全不在意禁止染发烫发的校规校纪。它通体都是褐色的,就像树皮一样,但又紧致又光泽,并不显得粗糙。仅仅是远远地望上一眼,我也能看得出他那一身的肌肉丝毫不输施瓦辛格或者巨石强森。他的下半身并不是两条腿,而是错综复杂的根须,看起来倒像是裙子一样。这些根基绕绕地扎在地下,估计是他的妖气还不足以把他变成一个人型的妖怪。
他站在那一动不动,像是雕塑一样,倒也很符合“树”的形象了。
指南翁照例没有给我介绍,所以说他是树妖也只是我觉得是而已。我不想再去问指南翁,问他让我觉得很不好开口。我一直都是那种不太好意思向老师提问的学生,更何况我身边这个老东西比老师还不好招惹。老学究自顾自地飞,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
宿舍门前有一条布满鹅卵石的道路,箱子拖在上面咯吱咯吱响。我发现男生宿舍楼的门口基本都会有一个蛛丝目,我这栋也不例外。一只蛛丝目吊在门口,它被这咯吱咯吱的声音吸引了,目不转睛的盯着我看,舌头耷拉在地上淌着口水。
我一边走一边看着它,正发呆呢,突然有一个圆球从它眼睛里飞了出来,我吓得叫了一声。接着有一个男生从后面跑出来,对着门上挂着的“安全出口”的告示牌来了个扣篮——十七八岁的男生都爱这么干。生辅老师在房间里站起来骂了他两句,他装作没听见,跑出去接住了从前面墙上反弹回来的篮球,我这才知道原来之前飞出来的圆球不是蛛丝目的眼珠子。
我松了口气,却听到了指南翁的嘲笑:“胆小如鼠。”
嘲笑别人的时候都要用成语的人也是蛮少见的。
我拖着箱子从蛛丝目旁边走过,它的舌头弹起来在我身上舔了一下,怪恶心的。指南翁为了躲开它没走正门,从侧门花园的栏杆缝隙里进来的。
我想起黄雨潇曾对我说过蛛丝目是靠着“阳气”为食的,说明它会挂在“阳气”重的地方,但它怎么去寻找“阳气”重的地方呢?于是我问指南翁:“蛛丝目会动嘛?”
指南翁抬着下巴用鼻孔对着我:“为什么这么问?”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摆出这样一个姿势,大概是想体现自己居高临下吧——他都飞在我头顶上,根本不愿意比我飞的低,挺晃眼睛的。
我指着那个蛛丝目对指南翁说出了我的猜想:“这栋楼原来是女生宿舍,去年才变成男生宿舍的,这个蛛丝目这么大,应该不止生长了一年多吧?”
指南翁点了点头:“对。蛛丝目需要搬迁的时候,会自己把丝收回来,然后借助丝和舌头缓慢移动。”
我:“啊?”
指南翁想了一会,颇为不耐烦地对我说:“简单来说,就是撑杆跳,懂了吧?”
我没忍住笑了出来。我原来以为它会像风滚草一样,用蛛丝把自己包裹起来,在地上滚动前进,靠着舌头像舵一样调整方向;听指南翁这么说,它是靠着舌头做棍子撑着自己跳着走,就像是跳跳虎的尾巴一样。
这得多好的韧性啊!拿来卤着吃一定是久煮不烂的那种吧?我问指南翁:“有没有吃妖怪的……或者说妖怪界有没有专门煮妖怪的厨子?”
他厌恶地说:“你真恶心。”
说完他也不等我,自己就飘上楼去了。走到一二楼拐角的时候又回头说了一句:“令人作呕。”
还不过瘾,又加了一句:“人面兽心、稔恶藏奸。”
最后一个词我甚至都没听说过,上网查了才知道是什么意思。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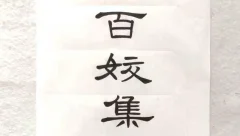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