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指南翁给我挑了一个手串和一个项链,全是些很难看的东西,黑黑的,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做的,摸上去像是石头。我很不喜欢这些东西,但既然指南翁给我拿了,我也不好拂了他的面子,只好戴上了。
“多少钱?”我掏出手机准备付钱。
算命的比了个“八”的手势:“不贵,两样合起来两百八。”
我的手停在半空中,回过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那些东西摘下来。算命的看出我的意图连忙按住了我:“别,戴上了就不能脱了。”
我看向指南翁,指望他说几句公道话,没想到他说的是:“付吧,你家又不是没钱。”
“不觉得很贵吗?”我反问他。
指南翁满不在乎的样子:“物有所值。”
我差点气死,但看那个算命的强买强卖的嚣张气焰,考虑到周围可能都是他的人,我只好忍气吞声,认了哑巴亏,心中默默想着该怎么想向消协举报这事。当我准备输密码的时候,指南翁对算命的说:“买这两样,再搭个东西,可以吧?”
算命的嘴角一挑:“看上啥了您随便挑。”
他那大方的样子像是占足了便宜,而我就是待宰的羔羊——已经被宰或许更为贴切。指南翁飞到他的摊位上,来回转了几圈,指着一把刀对我说:“就这个吧。”
所谓的刀还没有巴掌大,手柄与刀鞘都是木头的。我拔出刀仔细端详。这把刀开过刃,刀刃泛着幽幽的蓝光,感觉像是在火上烤过一样。这把刀上的蓝光没有忽暗忽亮的闪烁,而是一阵持续的蓝光,再看似乎是淡淡的妖气。我有点兴奋,悄声问指南翁:“这是神器?”
指南翁被我问的一愣,接着摇摇头:“不是。你别那么幼稚好吗?”
指南翁说我幼稚让我有点不服气,但我也懒得和他计较。我悄悄瞄了一眼算命的,看他的表情有点肉疼,我就知道这把刀绝对不太一般。我付了款,将刀揣进了口袋里。刀显得很重,放进口袋里的时候猛地往下一沉,我觉得裤子都差点被扯下来了。
“怎么这么沉?”我脱口而出。
“你要好好用它。”算命的没头没脑地来了一句。我没理会他,转身要走,他从摊位下摸出了一张名片,一手拉着我胳膊一手将名片塞到了我手里:“在下温三金,这是我的联系方式,婚丧嫁娶算命抓鬼都可以叫我,我这用的都是科学算命法,老美的什么NASA啊、FBI啊、BBC啊,经常请我去的,我还有其他业务也可以了解一下。”
我笑了笑:“BBC是英国的。”
温三金尴尬地陪着笑,接着一摆手:“没事没事,英国美国都一样,洋鬼子都一个德行,都好糊弄。”
名片正中画着个八卦,下面写着“吉祥观温三金道长”。正面毫不起眼,背面可就大有乾坤了:婚丧嫁娶算命抓鬼、按摩推拿修脚拔罐、电脑维修空调加氨、白蚁查杀灭治蚊虫,四句话都是隶书字体,两两对称和对联似的。我开玩笑地说:“业务范围这么广吗?”
温三金“哈哈”一笑:“技多不压身,前两天在送外卖,不过我没电动车,就不送了。”
我印象中的道士总是仙风道骨谈吐优雅的,眼前的温三金实在很难和这两个词扯上关系。我随口问了一句:“你不是真的道士吧?”
温三金捋着下巴不存在的胡子思考了一会,眼珠一转,反问:“你不会信基督吧?”
我不明就里:“啊?”
他蹲下来,又在摊子下面翻来覆去地找了很久,再站起来时手里多了一张名片。正面写着“吉祥堂文森金神父”,下面是英文的“VencentKing”,背面的内容完全一模一样。
“神父是天主教的吧。”我小声嘀咕。温三金听见了,一拍脑袋,嘴里说着“忘了忘了”又蹲了下去。我拦住他,问:“都没有信徒找你麻烦吗?没有什么宗教协会找上门?”
温三金袖着手靠在墙上:“人家各信各的,有信仰的怎么会来找一个算命的?我这就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信仰完全为顾客服务。那叫什么,‘顾客是上帝’嘛!”
他不知从哪又掏出了一张名片塞到了我手里,问我:“佛教的要不要?还有本土信仰的——什么夫人来着,保胎的,你应该用不着。”
虽然我不信教,但我对宗教是持有一种敬畏态度的,我十分反感他把宗教当做自己牟利的工具。我不好当面扔了名片,就随手塞在口袋里了。温三金要送我们下山,被我们婉言谢绝了——这几十米的小土坡有什么好送的呢?温三金也并不真的想要送,看我们拒绝之后他立刻坐回了自己的位子上,戴着墨镜翘着脚,嘴里还哼着曲。
山下的大妈们依然热闹非常,为孩子找对象的劲头完全不输跳广场舞时的热情。在穿过万千红线组成的情网的时候,指南翁突然对我说:“别躲躲藏藏的了,出来吧。”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一团蓝色的烟雾已经从我裤子口袋中冒出,在天上聚集成一个人形。我顿时觉得口袋里的重量变轻了,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他的衣着像是沙漠里的人,身上是蓝色的长袍,只露出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没有瞳仁,只是蓝色的光点。我注意到他的右手缠绕着蓝色的火焰,火焰似乎是一把刀的形状。
这个妖怪看起来就比较有威胁,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你怕他干嘛,”指南翁似乎在嘲笑我,“这是锋刃灵,就附身在你刚刚拿的那把刀上的。理论上来说,你现在是他的主人。”
锋刃灵没有说话,只是右手搭在左肩上微微一鞠躬。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回应,下意识地也鞠了一躬。指南翁赶紧拉住了我:“你干什么?周围的人看不见他的!”
我看了看周围,大妈都用一副看戏的眼神看着我。我羞地无地自容,装作无事发生地样子继续往山下走。路上,我问锋刃灵:“你有名字吗?”
锋刃灵摇头:“但凭主人吩咐。”
指南翁想起了家中的“大黄”,警告我:“不许叫大刀大锋什么的。”
我试探着问:“那……阿锋?”
指南翁一副失望的样子,锋刃灵倒是点了点头。我真不擅长给别人起名字,小猫小狗都还无所谓,当他们有了自己的思维之后,再让我来起名字就显得班门弄斧——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想到这个词,大概是因为我自认为自己的水平远在他们之下。
“锋刃灵是附身在刀上的妖怪,但不是随便一把菜刀都会出锋刃灵,就像不是每一本书都会出书卷灵。”指南翁刻意在这里停顿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我以为他已经说完了,没想到他还有后半句话:“大多数以‘灵’结尾的,都是一些妖怪附身在器具上。他们附身的器具往往很普通,但实际上这些妖怪一般都比较厉害——比某某‘妖’之流厉害许多。”
指南翁又在拐弯抹角地夸自己了,我没有接他的话茬。他的夸耀毫不掩饰,如此直来直往地夸耀倒也不显得做作。
回到家,我把东西都放好,然后也没来得及坐会就马不停蹄地去邻居家接大黄和黄雨潇。大黄看到我之后,亲切地扑了上来,我将它抱在怀里;黄雨潇隔着大黄抱我,我感觉到一阵风扑来,大约这就是她的拥抱。拥抱过后,她突然很诧异的瞪大了眼睛看着我,接着马上把目光转向了指南翁,眼神少有的凌厉:“你对他做了什么?”
“什么我对他做了什么?”指南翁眼神躲闪显得有些不高兴,“大惊小怪,我只是让他吃了个战场火。”
黄雨潇的眼神从凌厉变为了惊讶:“这怎么行?”
指南翁转过身进屋去了:“没什么不行的,吃一点不会有事的,而且他也需要这种能力来对付一些妖怪。”
“那这样妖怪不也能伤到他了!”黄雨潇对着指南翁的背影喊。她跟了上去,留下我一个人站在原地发呆。
指南翁喊回来:“得了吧,所谓伤到也就是损一点妖气而已,总要有东西保护自己吧?”
“我来保护他啊!”黄雨潇这句不假思索的话让我有些感动。
“那为什么不让他自己强大起来?”指南翁的声音很大,把黄雨潇噎住了。她还想说什么,但是最终话到嘴边还是被她咽了下去。此时的我依然站在邻居家门口,邻居疑惑的表情告诉我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了。我向邻居道了谢,抱着大黄转身进屋了。
我和黄雨潇坐在沙发上,大黄趴在我脚边,黄雨潇有点失神的样子。
我问她:“你刚刚和指南翁说的都是什么意思?”
黄雨潇的担忧溢于言表:“妖怪之所以无法伤害人类,是因为人类身上妖气很淡,妖怪碰不到他们;但你身上的妖气正逐步提升,更容易成为一些有攻击性的妖怪的目标。当他们吸取你的妖气的时候,你很可能因为妖气与阳气失衡而受到伤害的。更关键的是,你的妖气变多了,你就能摸到妖怪了。”
我有点茫然。指南翁在里间说:“你听她扯淡,一个犬妖懂什么?你的目标大了是没错,但这年头哪来怎么多强大的妖怪?一般的妖怪也会吃弱小的妖怪,你妖气弱也会成目标。现在你有了保护自己的手段,这样不好吗?再说了,妖气多了能摸到妖怪?别逗了,所谓摸到就和感受风一样,你以为呢?还真的觉得自己能捉妖了?”
黄雨潇被呛了一下,说不出话,别过头显得很委屈,眼睛里还有点泪光。我觉得指南翁说的没什么错,因此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哄她,就摸了摸大黄的脑袋,进屋去了。指南翁坐在书柜上,看到我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连彩虹都不怕,你还怕什么乱七八糟的小妖怪?遇到情况你就叫锋刃灵或者用战场火,大多数情况你都能对付。”
我觉得他也不像是安慰我的语气,应该是实话实说,就也没太在意。我打开空调,往床上一倒就一动都不想动了。吹了一会,我想到大黄还在外面热着,就跑出去把它抱了进来,黄雨潇破涕为笑:“算你有良心还记得我。”
我将它放在地上,黄雨潇就直接躺在了床上。由于我现在也能感受的到她,我就往旁边挪了一点,给她腾出地方。指南翁瞥了一眼,又转过头去了,黄雨潇也没有理会他,只是盯着天花板发呆,大黄也趴了下来,将脑袋埋在前肢里。有那么一段时间,我觉得时间都静止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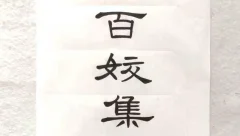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