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译按
译按
编译这篇文章的原因主要是因为 Alexander R. Galloway 是一位蛮有趣的学者,研究者的同时自己也是程序员,并刚刚发布了自己根据 Guy Debord 的理论做的游戏《Kriegspiel》,已可在 Mac Apple Store 下载游玩。
他很早就开始进行了游戏相关的研究,写作了《Gaming》(2006),里面涉及到包括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电影镜头来源,社会现实主义的游戏(文章发布在 Game Studies),以及「反玩」(CounterPlay)的概念等等。但他并不是一个专门的电子游戏研究者,而是更多从传统哲学和媒介研究的视角切入,并且与政治性的某种诉求与激进思考相结合;此外他的哲学视野也异常广阔,引入和介绍了许多法国哲学家。
恰好自己在思考界面(Interface)的概念来作为正在发展的研究创作方法论,所以希望能够深入到媒介研究中去厘清一些有关界面的充分意涵,以确保自己没有武断的使用。但这篇文章的主要的着力点则不仅仅是在界面,而实际上这是其将界面作为一种政治性与美学的批判分析方式来提出,并且希望媒介研究不再仅仅把注意力放在界面内外,界面是一个他所强调的「丰富多产的交汇点」(a fertile nexusa fertile nexus),我们应该去分析和理解到界面之内所发生的事情(诸如他提出的内界面 intraface 概念)。
虽然确实这种眼花缭乱的写作令人头大,但我还是蛮喜欢文章前段对于界面常用理解的拓展,以及其对当下「游玩的资本主义」(ludic capitalism)的控制论与浪漫主义化的两组游戏要素的分析;而文章中段所进行的,对于两幅漫画,以及《魔兽世界》的内界面分析也颇有趣,或许可以成为一种思考「元游戏」(meta-game)或游戏的元层面的批判视角,令人想起福柯在《词与物》中对委拉士开兹的《宫娥》所做的经典的分析:
在这幅画中,表象在每时每刻都被表象了:画家、调色板、背着我们的画布的巨大的深色表面、悬挂在墙上的画、观察着的观众以及那些环绕并观察着他们的人;最后,在中间,在表象的中心,接近重要的东西,是一面镜子,它向我们显示什么被表象了,但是作为反映,这面镜子是如此 远、如此深埋在一个不真实的空间中、对指向别处的所有目光 来说是如此的陌生,以至于它仅仅是表象的最微弱的复制(le redoublement)。画中所有的内部线条,尤其是那些来自中央反映的线条,都指向那个被表象但不在场的东西。有了客体,由于正是艺术家所表象的东西才被复制到他的画布上去了——同时有了主体——因为在工作中表象自身时,画家眼前所有的正是他本人,因为画中画出来的目光都指向王室人员所占据的虚构位置,这个位置也是画家所处的真实位置,因为最后,那个模糊位置的主人(画家和国王在这个位置中交错着并且不停地闪现着)是观众:他的目光把画转变成客体、那个基本空隙(manque)的纯表象。还有,那个空隙并不是空白,因为除了话语费力地分解这幅画,那个空隙还不停地有这样一些东西光顾,并且真的如被表象的画家的注意力所证明的:画中画出的角色的敬意,背朝我们的巨大画布的在场,以及我们的目光(这幅画是为我们的目光而存在的,并且在时间的深处被安排的)。
叶梓涛
落日间
按
按
Interface Effect 这本书是 Galloway 控制寓言三部曲(前两部分别是Protocol 和 Gaming)的最后一部,是个人觉得三本里比较好的一本。也可以从这本书看出Galloway 后面著作的理论特点:一种拓扑式的关系阐释,比起新的对象(相比传统理论讨论的对象更时髦的code、data、game等),更关心新的关系(比如兼及内与外的界面)。
正如Galloway很少或者说是很小心翼翼地防止自己掉入 digital/analog 的二元对立中,他比起「界面是什么」也更关心「界面如何成为一个可以检测到到不同力量发挥作用的场所,如何去调节个人的情感经验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
梓涛增添段落的第一句「Interfaces are both surfaces and thresholds」就很好地体现了Galloway 内外兼顾的特点。在Galloway的讨论里,具备行为倾向的动作(存储、传输、处理)才是中心。这种灵活在《界面》里可以用他的一个关键术语「控制寓言 allegory of control」为例说明,这是个缝合术语,寓言(allegory)受 Fredric Jameson 寓言阐释的影响,指文化生产和社会文化相遇的辩证法,而 control 则受德勒兹 Societies of Control 的影响,指一种由特定网络和信息逻辑主导的社会语法。
在Galloway这里,界面(interface)就是寓言在当下的形式,一个可以检测到历史和政治力量如何发挥效应的场所,也是 Galloway 在数字时代对 Jameson 的寓言阐释的真正运用——要历史化。界面向外是文化生产置身的社会经济与历史物质的脉络,它们常常会内渗或者说是介入内界面的感知叙事和美学分配,这在《魔兽》部分有详细阐释。理解 Galloway 的interface,与其说是想象一个界面,不如想象穿过界面的渗透与转换如何发生。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有趣的学者,Galloway 的好玩也是多面的。比如他早期在成为学院里教书的学者前,其实是 Rhizome 的技术顾问和内容编辑,也做一些艺术创作。这种动手实践的精神延续到他最新一本书,书里不仅有他复原德波的战争游戏的细节,还讲了编织和代码之间的关系,并且和他的游戏研究一样,也真正尝试了使用代码完成织布机的编织工作。同样是这本书,最后一章对马克思的理论阐释也很有新意。还有《界面》里 Galloway提出的四种以希腊诸神命名的很有趣的文化创造模式,这四种模式也可以在后来他合写的《绝罚》中找到呼应。阅读 Galloway 是一个很难空手而归的旅程。当然,旅程总会有冒险,而且Galloway可以说是越写越好的学者,早期的文章不算好读,感谢梓涛的翻译。
徐露
科学史图书馆
Alexander R. Galloway
Alexander R. Galloway
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R. Galloway)是一位作家和计算机程序员,致力于哲学、技术和媒介理论方面的问题。他是纽约大学媒体、文化和传播学教授,著有多本关于数字媒体和批评理论的书籍,包括《Uncomputable》(Verso, 2021)和《The Interface Effect》(Polity, 2012)。他与尤金·塞克和麦肯齐·沃克合著的《Excommunication: Three Inquiries in Media and Mediation》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Galloway 与Jason e . Smith 共同翻译了 Tiqqun 的《Introduction to Civil War》(Semiotext[e], 2010)。几年来,他一直与RSG合作开发 Carnivore、Kriegspiel 和其他软件项目。
加洛韦获得了古根海姆奖 Fellowship、柏林奖和 Prix Ars Electronica。加洛韦的著作已被翻译成十一种语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形容他的实践「在概念上犀利,在视觉上引人注目,与政治时刻完全合拍」。自2002年以来,加洛韦是纽约大学的教员,他还在宾夕法尼亚大学(2012年春季)和哈佛大学(2016年秋季)担任访问教授。2019-2020年任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学院院士。
加洛韦的博客:点击跳转
Interface 界面 - Flusseriana
Interface 界面 - Flusseriana
编按:在 Galloway 的博客上提到自己参与写作和编撰的《Flusseriana》(收录了关于弗卢塞尔大量条目的书),他展示了两个条目,其中一个条目便是本文的主题界面(Interface),短小精悍,可作为此文的简要引入
界面既是平面(surface)也是临界(threshold)。一方面,界面是一种表面的屏幕,无论是文字化的还是图形化的,它包含意义和操作。另一方面,界面是一个窗口或门道,方便通行。
界面就像窗户或门一样,起着边界(boundary)的作用,例如,在人体和外部世界的装置和设备之间。更一般地说,一个界面是任何对事物和事物的区分(distinction):HTML(超文本标记语言)是可读文本和标记标签之间的界面;冰点是水和冰的界面。界面是差异的物理或符号标记。它们构成了两种媒体之间的人为区别,并允许媒体被再媒介化为(remediated)其他形式。
考虑到它们作为区分者(differentiators)的角色,界面以系统性的、分层的或嵌套的关系存在。为了使得这样的系统性架构得以可能,界面需要错综复杂的编码化和管理。界面是交换的区域(zone of exchange),作为临界,是有生产性和生成性的。而作为调节者(regulators),它们也限制了或延迟了通过。因此界面呈现出一种在直接与神秘、清晰与复杂、显然与不可思议之间的辩证张力。
然而,界面不仅仅是临界,它们也是平面或屏幕。正如弗卢塞尔所说,界面是一个「意义平面」(significant surface)。因此,除了作为一个促进交换和通过的决定区域之外,界面也是一个「内部和外部之间的「游移不决的区域」(zone of indecision)」(Gérard Genette)。不只是门道,界面也有自己的内部现实;它们支起一个自主的美学空间。边缘和中心在界面内的结合将框架和作品与作品联结起来。因此,界面同时连接了内部和外部。
《Interface Effect》- Preface
《Interface Effect》- Preface
编按:由于后续《Unworkable Interface》被编入其专著《Interface Effect》的第一章,故为了能够呈现出本文在 Galloway 整体的界面分析理论中的位置,故在此编辑与翻译其书的前言部分(Preface)。
这本书是关于窗户、屏幕、键盘、信息台、频道、插座和孔的——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些东西都不是特别的,而是同时发生的。因为这是一本关于临界的书,那些在不同现实之间连接(mediate)的神秘互动区域。这本书的目标有两个,定义界面,也解释它。界面不是简单的对象或边界点。它们是活动的自主区域。界面不是东西,而是影响结果的过程。基于此,我将不再谈论特定的界面对象(屏幕,键盘),而是界面效果(interface effects)。在谈到它们时,我不会满足于只说界面是这样或那样定义的,而是要说明它是如何因特定的社会和历史原因而以这种方式存在。界面本身就是效应,因为它们带来了物质状态的转变(transformations in material states)。但与此同时,界面本身也受到其他事物的影响,并因此展现出产生出界面的更大力量。
尽管涉及界面文化的许多不同方面,本书的各个章节都或多或少地说明了一种特定的解释方法。该方法与詹明信(Fredric Jameson)所说的「认知绘图」(cognitive mapping)有很多相似之处。自从他第一次提出这个话题以来,时代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当下的关注点也与他的时代有所不同。但其核心概念是相同的,那就是「文化是表现形式下的历史」(culture is history in representational form 如果詹明信允许这样一个不成熟的解释的话)。
然而,表现形式从来不是简单的类比。它是一种映射(map)、化约(reduction)或索引和符号的地图(indexical and symbolic topology)。这种「化约」是一种必要的创伤,它源于我们不可能在此时此地思考全局,不可能将当下进行历史化地解读。因此,整个社会生活的真相与它自己的表现越来越不相容。文化从这种不相容性(incompatibility)中产生。界面也是如此:它产生于这种不相容性;并且正是这种不相容。
然而,人们也可以反过来断言:社会文化生产确实「表达」了整个社会生活,而社会生活本身就处于某种永久的危机之中——无论这种危机是被称为星球内战、全球变暖和生态崩溃、日益加剧的物质碎片化和剥削,还是简单来说的资本主义(毕竟资本主义是其他一切的引擎)。(詹明信无可否认地遵循了同样广泛的衰退叙事(declension narratives),这在从沃尔特·本雅明、西奥多·阿多诺到马克斯·韦伯、费迪南德·托尼斯(Ferdinand Tönnies),甚至当然还有后来的马丁·海德格尔的各种现代性批评中都很明显。因此,特定的历史创伤转移到过多数量的可能的表现形式之中。
但认知地图也不仅仅是地缘政治危机的镜子。这是一种简单明了的主体形成,就像个体在世界系统中找到他或她自己的朝向。这意味着认知地图也是阅读的行为(act of reading)。它是解释过程本身,充满了所有的矛盾和半真半假的解释过程。因此,这是一种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的创伤,作为构成自我的必要切割。而在现象学意义上,它同时是一个以主体为中心的对世界经验的感应(induction)。界面效应停留在那里,在自我与世界沟通的临界点上(mediating thresholds of self and world)。
在接下来的几页中,我将尝试将詹明信的方法论稍微向新媒体的方向迁移(译注:这里指本书的 Introduction 部分),这是当今任何历史特殊性所要求的。读者需要准确地确定迁移是如何发生的,它意味着什么,以及它是否成功。但这件事的精神在于,正如在第二章关于意识形态的部分将会更加明显的那样,数字化媒介提出了一个问题,而政治性的解读是这个问题唯一连贯的答案。换句话说,数字化媒体询唤政治性的解读。如果「数字媒体」被理解为我们当代的技术文化,而「政治解读」被理解为一种将当下解读为物质历史的尝试,那么我们确实深入到了詹明信的领域。
为了诗意的华丽,如果没有别的,我可能会为这个项目提出一个新名字,「控制寓言」(the control allegory)。正如它在从界面文化中提取大量人造物的分析中揭示的那样,对这种方法的进一步定义是未来的项目。
不在运作的界面 Unworkable Interface
不在运作的界面 Unworkable Interface
这篇文章是应 Eric de Bruyn 的邀请,于2007年10月24日在荷兰格罗宁根大学举办的「界面」(the interface)研讨会上首次提出的。发布在 New Literary History, Volume 39, Number 4, Autumn 2008, pp. 931-955 (Article) ,并收录在其著作 The Interface Effect (2012) 中作为第一章节,本文翻译为论文而非专著的版本。
(译注:unworkable 是一个翻译的过程中有纠结的词语,从开头来看,Galloway 更多是在一个似乎不可见的角度去论述的,就是例如我们每天的网络成为了一个我们察觉不到的东西,正是因为它已经非常充分和完美的运转了而让自己变得 unworkable,而这种封装化自动化与让其变得习以为常的过程实际上正是技术某种的最高理想——努力变得不可见,直觉化,好像不存在似的,所谓「就好像不存在似的」因为运作的很好所以好像没在运作似的,
所以本文的标题也可以翻译为(仿佛)「不在运作的界面」。而这可能也就导向了第二层,即也让自身变得不可操作 unworkable,你看不见存在的界面,那就更难去操作和去探索,unworkable 还有描述未开采的矿层的意思,或许也可以将其看作今天我们日常生活所建立在的层层累积的技术与囊括着意识形态的界面的挖掘。除了这个层次外呢,在讨论界面和中段有关于两张图片的批评的时候,Galloway 又谈到界面的起作用,运作与否的问题,在这个意义上谈论的 unworkable(布朗肖)更多接近于一种运行,不运转的(désoeuvré)——不运作的、无生产性的、无效的、难运转的(nonworking, unproductive, inoperative, unworkable)。此外理解不足或错误处,还请各位指正)
I. 界面作为方法 Interface as Method
I. 界面作为方法 Interface as Method
界面回来了,或者说它们从未离开过。
我们熟悉的苏格拉底式的自负,来自《斐德罗篇》(Phaedrus),认为交流是直接书写对方灵魂的过程,自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又回到了围绕文化和媒体的话语舞台中心。景观社会的反射光学(catoptrics)现在是控制社会的屈光学(dioptrics)。反射的表面被透明的临界值(thresholds)所推翻。金属探测器的拱门,或图形截锥体,或 Unix Socket,这些都是这个时代的新标志。
窗户、门、机场大门和其他门槛/临界(thresholds)是那些透明的设备(device),做得越少完成越多:对于每一个艺术沉浸和连接的时刻,对于每一个体积性传递的时刻,对于不透明的时刻,临界变成了一个更加不可见的,更加无法操作的缺口(notch)。
作为技术,一个透视设备越是抹去其自身运转(在实际交付其所再现的事物时)的痕迹,它就越是成功地完成了其功能性任务;然而,这一成就本身就削弱了最终目标:一个设备变得越直觉化,它就越有可能完全脱离媒介,变得像空气一样自然,或像泥土一样普通。那么,要想成功,最好的情况是自我欺骗,最坏的情况是自我毁灭。必须努力运转,以投射出没在运转(unwork)的光晕。
操作性产生了不可操作性(Operability engenders inoperability)。
奇怪的是,这不是一种按时间顺序的、空间、甚至符号学的关系。它主要是一种系统的关系(systemic relation),正如米歇尔·塞尔在他对功能「同侧性」(alongsidednes)的沉思中正确地指出的那样:系统之所以能运转,是因为它们不运转(Systems work because they don’t work.)。非功能性(Non-functionality)对于功能性来说仍必不可少的。这可以被形式化:假装有两个站点通过一个通道交换信息。如果交换成功了(如果它完美的、最佳的、即时的),那么这个关系就会自我删除。但如果关系仍然保留,如果它存在,那是因为交换失败了。它仅仅只是一种协调(mediation)。关系是一种非关系(relation is a non-relation)[1]。
因此,自柏拉图以来,我们一直在与宏大的选择作斗争:(1) 如果没有对他者(因而同时也是对自我)的直接实现(immediate realization),中介化就是即将发生的过程,或者 (2) 正如塞尔的辩证法立场所表明的,中介化是自我和他者的不可还原的分裂(disintegration),且变成矛盾 [2]。表现(representation)要么是清晰的,要么是复杂的,要么是内在的,要么是外在的,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是已知的(known),要么是马上可解释的。简而言之,要么是伊里斯(Iris),要么是赫尔墨斯。
(译注:伊里斯是希腊神话与传说中的彩虹女神,众神的使者。古代的人认为,彩虹是连接天和地的,故伊里斯就被认为是神和人的中介者,她负责将人的祈求、幸福、悲哀、怨怒、祝福传递给神;同时,她亦将神的旨意传递给人,被认为是神音的传递者。这里更多是指一种直接的理解和传递)
在不希望颠覆这种整齐划一的表述的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当代,看看是否有什么稍微不同的事情发生,或者,至少通过对一些实际的文化人造物的仔细分析来「证明」似乎已知的东西,还是很有用的。
但首先,我想迂回谈谈关于方法论的简短前言。就本项目的寓言(allegorical)性质而言,在游玩的资本主义时代(ludic capitalism),对寓言式阅读的过程进行一些阐述,以说明如何或为何可能首先进行这样的阅读。
在过去,为了证明自己的批评手法的有效性,以及政治效力,通常可以诉诸一些被合法化的方法论基础,通常是马克思或弗洛伊德或它们的某种组合。这并不是说这些来源不再可行,恰恰相反,因为过时的说法往往能带来权力的增长;即使在今天,马克思的死亡驱力在安东尼奥·格里、保罗·维尔诺或 麦肯锡·瓦克(McKenzie Wark)的假名下依然存续,就像一代人之前,在让·约瑟夫·古斯(Jean-Joseph Goux)或居伊·德波之下存续一样。
然而,今天从十九世纪中叶和二十世纪初继承下来的批判传统(马克思和弗洛伊德是其中的两个关键人物,但肯定不包括全部)的过时的光泽,甚至被认为是不合逻辑的情形,使得人们很难像过去那样团结在欲望的红旗下。今天,普遍传播的马克思主义的形式仍然是路易斯·阿尔都塞在一代人之前发明的防腐剂(antiseptic)形式:马克思可能会被戴上的橡胶手套进行解剖,其思想的理性内核被切割出来,并被挤压成某种形式的科学分析话语,或你也可以称之为批判什么的。在另一方面,现在提及精神分析,即使不是居高临下的轻笑,那也大概会得到一个假笑,这与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情况完全不同,当时各种形式和规模的弗洛伊德主义充斥着大众的想象。在意识到这一点后,许多人转向其他地方寻找方法论的灵感。
然而,马克思和弗洛伊德仍让我们有能力做两件重要的事:(1)提供一个所谓的深度解释模式的说明;(2)提供一个关于某事物如何以及为何以其相反形式出现的说明。
在我们的时代,各方面都很忧虑新自由主义经济的到来,这两件事加在一起仍构成了批判的核心行为。因此在目前,马克思和弗洛伊德即使不是绝对主要的,也仍然是有用的,尽管它们被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消毒阉割。
但是时代已改变了,不是吗?今天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与一百年或一百五十年前的情况很不同。从Manuel Castells 到 Alan Liu 再到 Luc Boltanski 的写作者已描述了一个新的社会经济景观,其中灵活性、游玩、创造力和非物质劳动——我们称之为游玩的资本主义——已经取代了纪律、等级制度、官僚主义和权力等旧概念。特别是,在这种新的游戏经济(play economy)中,有两个历史趋势非常突出。
第一个是对浪漫主义的回归,今天玩的概念从它那里得到了永恒的禀赋。弗里德里希·席勒的《论人的审美教育》(On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of Man, 1795)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在这本书中,哲学家用辩证的逻辑得出了游玩驱力(play-drive)的概念,其对象是人的「生命形式」(living form)。这个游玩的概念是一个丰富和创造的概念,是纯粹的、不受玷污的本真性,是永久地从人的核心中涌现出来的孩子般的、捣鼓的活力。而后,人们在约翰·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关于游戏的书《游戏的人》(Homo Ludens)中听到了同样的说法(这本书在政治光谱中被广泛引用,从法国情境主义者到社会保守派),甚至在后结构主义者的作品中也听到了同样的表述,而他们常常对其他看起来 「未经审视 」的概念充满敌意 [3]。
第二个因素是控制论(cybernetics),这是一个跨越数个科学学科(博弈论、生态学、系统论、信息论、行为主义)的综合体,虽然发展于二战期间和之前,但在1947年或1948年似乎迅速凝结,很快成为一个新的主导。随着控制论的出现,玩的概念表达对内稳态(homeostasis)和系统性互动的特别兴趣。世界的实体不再是封闭(contained)和无背景的(contextless),而是永远在相互影响和通信的生态系统中运作。这是一个以经济流和平衡为中心的游玩概念,是事物之间的多方关联,是对复杂的系统关系通过相互试验、相互妥协、相互衔接的解决方式。因此,在今天,人们「把玩」(play around)一个难题,以便找到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回顾一下这与笛卡尔的「论方法」或其他现代实证主义理性的主要作品之间语言上的巨大差异)。
今天的游玩是这两种影响的综合体:浪漫主义和系统论。如果说前者的象征性表达是诗歌(poetry),那么后者就是设计(design)。一个是表达性的,在瞬间便达到极点;另一个是迭代性的(iterative),向所有方向延伸。两者在二十世纪下半叶不可避免地融合在一起,归入当代游玩的概念中。因此,德波所说的游戏的「法学-几何学」性质并不完全完整[4]。他非常了解系统性互动的成分,但他低估了浪漫的成分。
今天的游玩最好被描述为一种「法学-几何学的崇高」(juridico-geometric sublime)。看看网络本身,它展示了所有这三个要素:协议逻辑交换的普遍规律,在聚合和传播的复杂拓扑结构中蔓延,并产生了「涌现」生命力的令人惊叹的力量。这就是浪漫主义-控制论游玩(romantico-cybernetic play)的含义。
因此,今天游玩的资本家(ludic capitalist)是至上的诗人-设计师(poet-designer),永远从原始的、系统的互动中劝诱出新的价值(考虑谷歌的例子)。而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改变了,以遵循同样的规则:劳动(labor)本身现在就是玩,就像玩变得越来越耗时费力(laborious)一样;或者想想市场的模型,在这个模型中,游玩的无形之手介入评估和解决所有的矛盾,并且被认为是所有现象的模型,从能源期货市场,到代议制民主的「市场」,到排废限额的讨价还价,到电磁波谱的拍卖,到艺术界的各种过份给予的投机方式。玩是克服系统性矛盾的东西,但总是通过求助于那个使我们成为人的特殊的、难以形容的东西。就像它一样,是一出根茎的情节剧(a melodrama of the rhizome)。
在这些类型的分期化论证后,有人指出,随着历史的变化,阅读行为也必须改变。因此,这种论点认为,随着新自由主义的经济主义利用网络游玩的灵活性,批评家也必须求助于扫描、播放、采样、解析和重组的新方法论。这样一来,批评家可能更适合作为一种混音艺术家,一个心灵DJ。
也许是这样的。但是,尽管游玩的娱乐力量很大,它们却共同围绕着一个清晰的号召:要更像我们自己(be more like us)。追随这样的号召并给它贴上自然的标签,仅仅是为了具体化(reify)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历史关系的东西。新的游玩经济实际上是一种呼吁,要求用最邪恶的技术从上到下对社会结构进行暴力改造。今天以谷歌或孟山都的名义出现的这些,只是一个注脚而已。
因此,让我首先承认,目前的方法论在精神上并不是特别的根茎性或游玩性,因为游玩和根茎式革命的精神在最近这些年已被消解。相反,它是一种材料和符号学的「细读」(a material and semiotic “close reading”),渴望的不是重演历史关系(新经济),而是将关系本身确认为历史。我希望这能产生一种视角,而揭示当文化生产和社会历史状况融合在一起时,它们会采取何种形式。或者说,如果这太过行话的话:艺术和政治采取何种形式。如果这将被视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充分的融合,并有一些绕道回到吉尔·德勒兹和其他地方的必要,那就顺其自然吧。
然而,这篇论文的最终任务并不是简单地说明目前分析当今游玩的界面所需的当前的方法论作用的混合,因为那是本末倒置的。最终的任务是揭示这种方法论混合其自身就是一个界面。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表明界面本身,作为一个「控制的寓言」(control allegory),指明了通往特定方法论立场的道路。界面提了一个问题,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暗示了一个答案。
II. 两种界面 Two Interfaces
II. 两种界面 Two Interfaces
首先,从关于界面的广为接受的普遍看法开始。人们往往会想到各种形状和大小的屏幕:电脑屏幕、ATM 自助终端、电话键盘等等。这就是维兰·弗卢瑟尔(Vilém Flusser)所说的「有意义的平面」(significant surface),意思是一个二维的平面,意义嵌入其中或通过它传递。甚至有一种特殊的说法来描述或评价这种意义平面。我们说「它们是用户友好的(user-friendly)」,或者「它们不是用户友好的」。「它们是符合直觉的(intuitive)」或「它们是不符合直觉的」。(译注:弗卢瑟尔 image as “a significant surface on which the elements of the image act in magic fashion towards one another.这个词主要就是指图像,用来与线条区分-感谢章伯帮助)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很容易不把界面理解为一个表面,而是一个门户或窗口。这是在一开始就被提到的临界(threshold)和转换(transition)的说法。根据这一立场,一个界面并不是出现在你面前的某物,而是一个打开并允许你进入到某个地方的通路(passage)。
二十世纪围绕着信息科学、系统论和控制论的大趋势为这其增添了更多内容。界面的概念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在控制论科学中,因为它是肉身与金属相接触的地方(flesh meets metal),或在系统论中,界面是让信息从一个实体到另一个实体,在系统内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地方。
门/窗/临界的定义在今天非常盛行,以至于界面常常被认为是媒介(media)本身的同义词。但如果说「平面」和「媒介」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这又是什么意思呢?答案是在层模型(layer model)中可以找到的,其中媒介在本质上不过是容纳其他媒介的形式化容器(formal containers)。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一书的开篇对此主张有着最清晰阐述。麦克卢汉喜欢从媒介历史的角度来阐述这一主张:一种新的媒介被发明出来,其本身而言,它的作用是作为之前的媒介格式的容器。因此,电影是在十九世纪的尾巴上发明的,作为摄影、音乐和各种戏剧形式(如歌舞杂耍)的容器。而视频是什么,不过是电影的容器。网页(Web)是什么,不过是文本、图像、视频片段等的容器。就像洋葱层一样,一种格式围绕着另一种,一路下来都是媒介。
这个定义今天已被确立,从这到界面的概念是一个非常短的跳跃,因为界面成为了任何嵌套系统中不同媒介层之间的过渡点。界面是一种「扰动」(agitation),或不同格式之间的生成性摩擦(generative fiction)。在计算机科学中,这非常确切地发生;一个「接口」(interface)是用来描述一个封装代码与另一个代码的互动方式。由于任何给定的格式都能在「它是另一种格式的容器」这一事实中找到自己的一致性,所以界面和媒介的概念很快就会折叠变成同一回事。
但这就是界面的全部故事吗?那些盲目迷恋屏幕媒介的人的狭隘主义地暗示着还有别的事在发生。如果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论点有任何诉求的话,那其提醒我们,把分析的范围限制在单一媒介,或在「数字化」(the digital)这样的旗帜下限制在一个单一的集合上,那都是短视的。临界的概念会警告我们不要这样做。因此,一个因其通用而非特殊性才被选中的古典资料现在是合适的。赫西奥德(Hesiod)是如何开始他的歌的?
永恒的不朽者……
是他们曾经教给赫西俄德他那美妙的歌声……
他们告诉我,要为受永恒之神祝福的族歌唱。
但总把他们自己放在我歌唱的开端和结尾。[5]
类似的惯例在荷马和任何的古典诗人中都可以找到:「缪斯在我身上歌唱,通过我讲述的故事」。诗人与其说是创作了自己的歌曲,不如说他是作为从外部接收的神圣表达的通道(conduit)。在这个意义上,诗人被缪斯所包裹着,或者像苏格拉底在《斐德罗篇》中所说的那样,被占有(possessed)。「把他们自己放在开头和结尾」,我认为这是我们关于界面是什么的第一条真正的线索。
大多数媒体(如果不是所有的话),都会唤起一个类似的阈限转变时刻(liminal transition moment),在这个时刻,外部被唤起,以便内部能够发生。就古典诗人而言,什么是外部?是缪斯女神,神圣的源泉,它首先被唤起和被赞美,以使得外部能够占有内部。一旦被外部所占有,诗人就会唱歌,故事就会发生。
当然,这种观察并不限于古典语境。对「很久很久以前」这种形式的开头唤起在各种媒体形式中都很常见。法国作家弗朗索瓦·达戈内(François Dagognet)这样描述它:「界面......本质上包括一个选择的区域(area of choice)。它既分隔了又混合了两个世界,这两个世界在此处相遇,在此处碰撞。它成为了一个富饶多产的交汇点(a fertile nexus)」[6]。达戈内提到了预期的临界、门和窗户等主题。但他把它复杂化了一点,承认在临界面之中发生了复杂的事情;界面不是简单而透明的,而是一个「富饶多产的交汇点」,他更接近弗卢瑟尔而不是麦克卢汉[7]。对达戈内来说,界面是一个特殊的,有其自主性的地方,并有自己能产出新结果和影响的能力。它是缪斯和诗人之间、神性和凡人之间、边缘和中心之间的一个「选择区」。
但什么是边缘(edge),什么是中心(center)?图像的终点和框架的起点在哪里?这是艺术家们几代人都在玩的东西。数字媒体特别擅长技巧/诡计(artifice),而挑战往往来自于维持边缘和中心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像纸牌屋一样随时都有可能崩溃。例如,在一个网页上的可读 ASCII 文本与同一网页上用于HTML标记的ASCII文本之间的区分完全是人为的(artificial)。这是一个编码的语法技术问题。为了创造这些人为的区别,人们强加了某种语言和风格的构造。从技术上讲,一路下来都是人为的区分:数据和算法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异(essential difference),这种差异化纯粹是人为的。界面是这种「处于边界上」(being on the boundary)的状态。它是「一个意义材料(significant material)被理解为不同于另一个意义材料」的那个时刻。换句话说,界面不是某个东西,界面总是一个效果(effect)。它总是一个过程或一种转换。又或是达戈内所说的:一个富饶多产的交汇点。
把这些开场白提炼成一个口号,我们可以说,艺术的边缘总是参照媒介本身(the edges of art always make reference to the medium itself)。诚然,这是一个常见的说法,特别是在围绕现代主义的讨论中。但我们可以更广泛地扩展这一概念,使其适用于普遍的中介化行为。荷马调用了缪斯,诗歌的文字形式,以设定(enact)并体现(embody)同样的神圣形式。但即使是在诗歌本身的歌声中,荷马也脱离了叙事结构,通过称呼语,对某个人物说话,就像他是一个直接称呼的对象:「还有你,阿特里德斯......」,「还有你,阿克琉斯」。
为了进一步发展这一线索,我转向两个案例研究中的第一个。
诺曼·洛克威尔(Norman Rockwell)的《三重自画像》(Triple Self-Portrait, 1960)展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界面。从根本上说,它是对界面自身的沉思。艺术家的肖像出现在画面中,只是被翻了翻,多了几倍。但这幅插图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再现系统。图像内部有一个连贯的循环,它向外部探看,而终仍害怕外部。三个肖像紧接出现:(1)坐在凳子上的艺术家的肖像,(2)艺术家在镜子里的投影,以及(3)画布上完成一半的画像。然而,图像并没有就此结束,因为额外的层次补充了这三个明显的层次:(4)画布左上方的早期草图的原型界面,作为粗略绘制的图像生产的前史(5)右上方,欧洲大师的自画像阵列,为艺术家提供一些灵感,以及(6)右侧中央的(真正)艺术家的厚重签名,巧妙地嵌入图像中的另一个图像中。
这种复杂的图像生产循环产生了一些不寻常的附带作用,必须逐一说明。首先,艺术家在一堵米白色的墙前作画,与后来成为科幻电影(如《五百年后》(THX 1138, 1971)或《黑客帝国》)主打的非常整洁的、白色的无名之地没什么不同。在这个白色的无名之地内,似乎没有任何可见的外部,根本没有景观来定位或引导艺术家图像生产的连贯循环。其次,以及更重要的是,镜子里的影像和画布上的绘画在表现上和道德及精神活力方面的巨大差异。镜中的形象是作为技术或机器性(machinic)的形象出现的,而画布上的绘画是主观的、有表现力的形象。
在镜中,艺术家衣衫褴褛,在两片不透明的眼镜片后面目眩神迷,执行着他职业的繁重任务(显然并不对此感到非常兴奋)。而相反,画布上是一个完美的、特别的自己。他的视力在画布的世界里得到了矫正。他的烟斗不再下垂,而是以一种欢快的姿态抬起。甚至艺术家眉毛上的线条在画布上也失去了预兆(foreboding),而象征着一位长者的柔和智慧。其他不同之处比比皆是,特别是尺寸的两倍增长和画布图像中色彩的缺失,虽然看起来更加完美,但最终却显得弱化而贫乏。
但这个界面还有第四层,是对三层自画像的「四重的」(quadruplicate)补充:插图其本身。它也是一个界面,这次是在我们和杂志封面之间。这通常是最不可见的界面层次,特别是在洛克威尔所擅长的平庸媚俗的格式中。这是一幅自觉的自画像(self-conscious self-portrait),这也有助于使第四层变得不可见,因为观众的所有精力本来可以保留下来,用于解决那些关于反射和层次以及意义的自反性循环的困难「元」问题,但在他们有机会审视插图本身的框架之前,就已经精疲力尽了。
用相当愤世嫉俗的话来说,图像是符号化的宣泄(semiotic catharsis),旨在使观众的眼睛不至于游离得太远,同时又避免将图像视为符号的任何责任。 图像声称要解决观众在图像内容中的关切(在应该被称为正确名称的地方,即图像的情境性空间)。但它只是提出了这些关切,以便它们可以被悬置起来。在更大的意义上,这也是一般的体裁形式,以及媚俗、巴洛克和其他发自肺腑的表达模式所进行的符号学劳动:在观众中植入他们认为一开始就想要的欲望,然后满足这种相同的人造欲望(artificial desire)的每一次恳求。人造的欲望,还能有其他种类吗?
但仍然,什么是边缘,什么是中心?我是否回避了这个问题?洛克威尔是在唤起缪斯女神,还是仅仅将她悬置?文本和副文本(paratext)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回答这些问题的最好方法不是指向图像中的一组实体,洋洋得意地宣布这五六个细节是文本的,而其他七八个是副文本的。相反,我们必须始终回到以下概念。
一个界面不是某个东西;一个界面是一种关系效果(relation effect)。我们必须审视图像之中的局部关系(local relationships),并问:这种特定的局部关系是如何创造出一种外在化、不连贯、边缘化或框架化的? (或者反过来说:这装置中的这种其他特定局部关系是如何成功地创造出一种连贯性、一种中心化、一种局部化的?)但这意味着什么呢?把你自己投射(project)进洛克威尔的图像中。在艺术家、镜子和画布之间存在着一个情景内的回路(diegetic circuit)。这个回路是一个强度的循环(circulation of intensity)。然而,这并不禁止观众走出这个回路。
这里强调的是,我们必须始终将图像视为一个过程(process),而非作为一组离散的、不可变的项(items)。在这个意义上,副文本(或者说,非情景性)只是一个过程,它被称为外围化(outering),外部性(exteriority)。
(译注:diegetic 意思就是可被故事叙事所解释的,诸如 diegetic UI,例如如果是屏幕上有子弹数量的字,那么这就是外在于故事的(non-diegetic,除非是个元层面,或什么头戴显示界面),如果这个数字被设计在了游戏内的枪械上的屏幕显示,那么就是可被游戏内显示的,即 diegetic)
洛克威尔的三幅自画像暗示了这个笑话,但从未使其达到完美,我们应该转向几年后理查德·威廉姆斯(Richard Williams)为《疯狂》(Mad)杂志制作的讽刺作品 [8]。幽默来自于《疯狂》的整蛊吉祥物。作为一个如此有才华的艺术家,他不仅为自己画了一幅肖像,而且还是从观众的主观的优势地位的视角来画。这是个短路(short circuit)。
与洛克威尔的角色不同,《疯狂》的吉祥物并不关心让自己在艺术上看起来更好,而只是为了让自己显得更聪明。在这幅图像中没有焦虑。没有烟斗;没有眼镜。它是彩色的。是同一个头,只是更大。并且当然,这也是后脑勺的图像,而不是脸部,前额和正面。朝向对象的模式(mode of address)现在是图像的核心:洛克威尔的眼睛炯炯有神,但这里的《疯狂》的吉祥物很明显是在朝向着观者。在洛克威尔的图像中,有一种强度的循环,每增加一层都会给观者的视线带来一个弯曲,总是朝向中间的向心引力。但在威廉姆斯《疯狂》的讽刺作品中,这些循环的连贯性被三个将画面分割开的正交尖峰(orthogonal spikes)所取代:(1)镜子里的脸垂直地向外看着杂志读者。(2)坐着的人物垂直地向内,而不是像光学定律所规定的那样看向镜子,同样(3)画布上的肖像也垂直向内,模仿着正交垂直的大他者,杂志读者的样子。画面中的每一盎司能量都是以其自身的外在化为目标的。
回顾艺术创作的历史,人们会记得,朝向观众讲话的是一种非常特殊的表现方式,常常被保存、隔离或抛弃,并留待特殊场合使用。它出现在像色情文学这样的低劣形式中,或像家庭录像这样的民间形式中,或像布莱希特戏剧这样被边缘化的政治形式中,或像夜间新闻这样的意识形态的质询形式中。(面向观众)直接的讲话(direct address)总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被对待。在许多媒体中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叙事化形式,几乎完全禁止使用它。例如,20世纪30年代的电影,直接的讲话是不能做的,至少在经典的好莱坞形式的范围内是这样。它成为相当前卫的一个标志。然而,《疯狂》的第四个界面,即图像本身的直接指向,是作为框架的一部分被包括在内的。它完全被折叠进了图像的逻辑中。画布上的巨大脑袋,在转过去时,实际上是在将边缘转向,并且带入中心。
洛克威尔和《疯狂》展示了对同一难题的两种思考方式。前者是一个将自身的朝向界面主题的界面;洛克威尔的是一个设法解决一般图像制作的图像。但它通过压抑的神经症(neurosis of repression)来回答界面的问题。在将其自身朝向界面的过程中,它也同时暗示了界面并不存在。它把重点放在一个连贯的、封闭的、抽象的审美世界上。
另一方面,第二幅图像通过精神分裂的精神错乱(psychosis of schizophrenia)解决了界面的问题。它永远返回到界面本身的原始性创伤(original trauma)。第二幅图像陶醉于破碎的连贯性带来的迷失,而没有试图隐藏界面。相反,它所关注的正交轴,从图像中向外延伸,抓住了观众。在它之中,图像的逻辑被分解成不连贯性(incoherence)。因此,这两幅图像之间的张力,是在连贯性与不连贯性,是在创造了一个自主逻辑的中心,与创造了一个流动、变化、运动、过程和逃逸线的边缘之间的关系。边缘在第二幅图像中被强有力地唤起,而在第一幅中被消解了。
因此,第一个图像是一个内部一致的(internally consistent)图像。它是一个运转的界面。这个界面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可以由界面本身知晓和阐明。它能运转;它很好地奏效。
另一方面,第二种是一个不运转的图像。它是一个不稳定的界面。正如莫里斯·布朗肖(Marurice Blanchot)、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或迈赫迪·贝尔哈吉·卡西姆(Mehdi Belhaj Kacem)所说,它是不运转的(désoeuvré)——不运作的、无生产性的、无效的、难运转的(nonworking, unproductive, inoperative, unworkable)。
III. 内界面 Intraface
III. 内界面 Intraface
早期关于界面是门或窗的常规认知现在显示了它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必须越过「界面的临界理论」的门槛。一扇窗户举证它没有把任何表现方式(mode of representation)强加给通过它的事物。一扇门也说类似的话,只是它承认它可能不时关闭,阻碍甚至封闭里面的过客,从而使这个公式稍微复杂化了些。
因此,这种话语永远陷于围绕开放性和封闭性、围绕完美传输和意识形态封锁的无意义辩论中。这种话语有非常长的历史,一直到法兰克福学派及以后。而来自二十世纪先锋派内部的反面论述,也同样沉闷乏味:围绕装置批判(apparatus critique)的辩论,人们必须使装置可见的概念,「作者」必须是「制片人」(producer),诸如此类。一种布莱希特模式,一种戈达尔模式,一种本雅明模式。《疯狂》的图像隐含地参与了这一传统,尽管它是庸俗和讽刺性的基调。换句话说,就《疯狂》的图像对装置的关注重心而言,它与新浪潮、现代主义和二十世纪前卫艺术的其他角落中的各种形式技巧并无不同。
《疯狂》的图像说:「我承认图像的边缘是存在的,因为这个边缘在我自己构造的结构中是可见的,(即使到最后这全都是个笑话)」洛克威尔的图像说:「边缘和中心可能是艺术的主题(对象),但它们从来不是任何会影响艺术技巧的东西。」
发明一个新的术语来描述这种运转的和不可运转之间的虚构的对话将会是有帮助的:内界面(intraface),也就是,界面内部的界面(an interface internal to the interface)。这里的关键是,界面是在审美内部的(within the aesthetic),而不是隔开从这里到那里的空间的窗户或门。杰拉德·热内特(Gérard Genette)在他的《阈限》(Thresholds)一书中称其为「内部和外部之间的'犹豫不决的区域'(zone of indecision)」[9],这不再是一个选择的问题,就像达戈内那样。现在是一个非选择性的问题。内界面是非决定性的(indecisive),因为它必须总是同时尽力推动两种东西(边缘和中心)。
但究竟什么是犹豫不决的区域?哪两个东西在内界面中对峙?它是一种暗含中地将边缘和中心结合在一起的美学类型。因此,内界面可以被定义为边缘和中心之间的内部界面,但它现在完全被纳入并包含在图像中。这就是构成犹豫不决的区域的原因。
现在事情变得稍微复杂了一些,因为考虑到以下疑问:政治性艺术在何处发生?在许多情况下,我现在指的是现代主义中所产生的历史上特定的政治艺术创作模式——(图5)右栏是政治化或先锋文化发生的地方。例如,亚里士多德和奥古斯托·波尔(Augusto Boal)之间的经典辩论: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文本中描述了一种以恐惧、怜悯、心理逆转和情感宣泄(catharsis)等原则为导向的内聚式的表现模式(cohesive representational mode),而波尔则致力于打破表现模式中的现有惯例,以唤醒人类的政治本能。因此,作品的边缘是一个指向外部的箭头,也就是说,指向作品所处的现存社会和历史现实。从这个角度看,热内特的「犹豫不决」是另一种东西的代号: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作品的边缘是作品的政治学(The edges of the work are the politics of the work)。
但要理解这两列(图5)在今天的真正含义,我们必须考虑当代游玩文化的一个例子:《魔兽世界》(World of Warcraft)。
人们会立即注意到这个图像(图6)的什么?首先,情境内空间(diegetic space)在哪里?它是山洞的背景,是直接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绘画透视技术的深度体积化的表现模式。另外,非情境空间在哪?它是包含图标、文字、进度条和数字的薄薄的二维附加层。它采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意义模式(mode of signification),更多地依赖于文字和数字、图标图像,而非逼真再现性图像。
这个界面充满了信息。即使是不熟悉这个游戏的人也会注意到,界面的非情景性部分(nondiegetic portion)与情境性部分同样重要,甚至比语言部分更重要。 计量表和仪表盘已取代了镜头和窗口。书写再次与图像被相提并论。它代表了媒介构成的一个巨大变化。从本质上讲,《魔兽世界》中所发生的过程与《疯狂》杂志封面所发生的过程相同。图像的情境空间在价值上被降级,最终由一个非常复杂的非情境性的意义模式决定。所以《魔兽世界》是另一种思考媒介内部张力的方式。它不再是屏幕这一侧和那一侧之间的「窗口」界面问题(当然它也必须履行这双重职责),而也是抬头显示器(HUD, heads-up-display)、前景的文字和图标,以及游戏本身的三维、体积、情境空间之间的内界面的问题——一边是文字;另一边是图像。
还有什么由此产生的?媒介中的内部界面的存在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表明了外部在内部的隐性存在(implicit presence)。以及为了明确起见,「外部」意味着一些相当具体的东西:社会。先前对立的每一个术语:非情境性/情境性、副文本/文本、布莱希特的离间效应/亚里士多德的情感宣泄——每一个都是指进步式的美学运动(同样主要与二十世纪有关,但不限于二十世纪)和更传统的美学运动间的紧张关系。
现在,对《魔兽世界》的分析可以发挥其全部潜力了。因为问题从来不是简单的形式主张,即这个或那个形式上的细节(文字、图标、抬头显示)的存在,有意义或无意义。不,这是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如果非情境性的东西占据了中心位置,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外部」或社会,已经比先前的时代更紧密地交织在审美的结构中。简而言之,《魔兽世界》是布莱希特式的,如果这不是在其实际存在的政治价值观中,那么至少也在媒介形式层面上的价值观。(关于这对今天的进步运动意味着什么的犹豫不决,这是一个有效的问题,我把它留给另篇文章和另一时间来讨论)。
换句话说,像《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允许我们进行一种非常特殊的社会分析,因为它们在告诉我们一个关于当代生活的故事。当然,流行的媒体形式讲述自己时代的故事是很常见的;然而像《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所提供的毫不掩饰的证据的程度仍然是惊人的。它不是一个前卫的图像,但尽管如此,它强有力地传递出了一个前卫的政治教训。从根本上说,这个游戏不仅仅是一个由龙和史诗般的武器组成的奇幻景观,而是一个制作车间,一个信息时代的血汗工厂,为合作的游玩劳动(ludic labor)而定制每一处细节。
到现在为止,我们应该明白为什么界面的门窗理论是不充分的。从麦克卢汉那里传下来的门窗模型只能揭示一件事,那就是界面是一个重写本(palimpsest)。这种模型只能揭示出,界面是对先前东西的再加工(reprocessing)。界面确实可能是一个重写本;然而,更进一步,表明重写本的各层本身是可被阐释的「数据」(data),则更为有用。在这个程度上,使用并行审美事件(parallel aesthetic events)的原则来思考内界面的问题更为有用,这些事件本身告诉观众一些关于媒介和当代生活的信息。一个更简单的词是「寓言」(allegory)。在这一点上,现在应该重新审视在关于方法论的开篇中提到的「宏大选择」:表现要么是美丽的,要么是欺骗性的,要么是直觉的,要么是可解释的。还有第三种方式:不是伊里斯或赫尔墨斯,而是「仁慈的人」,欧墨尼得斯(译注:欧墨尼得斯(Eumenides)是专司复仇的三女神。在希腊文中意为「仁慈的人」,这是由于希腊人敬畏神祇,担心直接说出女神之名会招致厄运,故而对女神使用的敬称与讳称。)。因为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表现是一个无节制的身体(incontinent body),一个从社会身体(合唱团)发出的激动的狂乱。因此,这是一种基础性的方法论关系,在我的三个中心主题之间:(1)今天的寓言结构,(2)内界面,以及(3)文化和历史之间的辩证法。
IV. 意义的制度 Regimes of Signification
IV. 意义的制度 Regimes of Signification
我们现在能够回到诺曼·洛克威尔和《疯狂》杂志,并从这两种模式种,推断出关于某些类型的游玩性文本如何处理界面的初步主张。警觉的观察者可能会争辩说:「但是,洛克威尔的图像难道不是像《疯狂》杂志的图像一样,对观察和镜像、边框和中心坦白了自己精通的知识,只是少了那幼稚的单行线?如果是这样,那不就成了一个更复杂的形象吗?为什么要诋毁图像的制作精良?」 而这是事实。洛克威尔的形象确实是制作精良,且对界面的运转方式展现出了高度的理解。我的主张与其说是对一种模式的规范性评价,不如说是对意义流如何组织出,对世界的某种认识和承诺的观察。
因此,我将提供一个关于信念(belief)和划定(enactment)的公式:洛克威尔相信界面,但不制定(enact)它,而《疯狂》制定了界面,但不相信它。
前者相信界面,因为它试图把观众作为一个主体,放入一个想象的空间,在那里,界面在众目睽睽之下传播与发生,没有焦虑。但与此同时,作为媒介,作为一个有自己边界的插图,它并没有设定界面的逻辑,它使其不可见。因此,它相信它,但不设定它。
相比之下,第二部作品航行到了一个充满激动和犹豫不决的奇怪之地,在到达时,把整个陈旧的系统变成了一个愚蠢的笑话。因此,它设定了它,但并不相信它。如果前者是界面的去对象化(deobjectification),后者则是界面的对象化。前者旨在消除媒介的所有物质性痕迹(material traces),支持一种狂野的观念,即所有临界的必要创伤可能升华为单纯的「内容」(content),而后者则将创伤本身对象化为「过程-对象」(process-object),其中社会形式的动荡保持其野性状态,但只是在漫画的不相信的安全范围内。
我们现在可以对上述连贯性和不连贯性的概念进行更多的普遍性观察。首先,重新审视一下术语:连贯性和不连贯性构成了一种连续体(continuum),我们可以将其置于审美和政治这两个领域内。这两个领域如下:
- 一种「连贯的美学」(coherent aesthetic)是一种运转的美学。美学的重力倾向于艺术作品的中心。它是一个中心化的过程,是围绕着一个特定的存在而逐渐聚结(coalescing)起来的过程。这方面的例子可以在许多媒介中广泛找到。巴特的「意趣」(studium)概念是它的基础。(译注:概念来自罗兰巴特的《明室》:studium is the element that creates interest in a photographic image, The studium **indicates historical, social or cultural meanings extracted via semiotic analysis)
- 一个「不连贯的美学」(incoherent aesthetic)是一个在此处(Here)的美学,重力不再是一种统一化的力量,而是一种降解(degradation)的力量,倾向于把整齐的聚块解开,变成它们不整齐的、无节制的元素。「不连贯」不能被理解为任何规范性的负面含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美学在某种程度上是没法看的,或难登大雅之堂的。连贯性和不连贯性指的是对象内部力的能力(capacity of forces),以及它们是否倾向于凝结或散布。因此,「刺点」(punctum),而不是「意趣」,才是这第二种模式的正确启发。(译注:刺点指的是照片的某些特征,其似乎产生或传达了一种意义,而不需要调用任何可识别的符号系统。这种意义对于图像的个体观众的反应是独一无二的。刺点穿透了「意趣」,从而刺向了它的观众。为了达到刺点的效果,观众必须否定所有的知识。)
- 「连贯的政治」(coherent politics)是指围绕一个中央机构组织的倾向。这种类型的政治产生了稳定的制度,涉及运作的中心、已知的领域和调节身体和言语流的能力。这被称为「国家」(state)的形成过程或「辖域化/领土化」(territorialization)。连贯的政治包括高度精确的语言,用于表述社会。 在各种实际存在的政治系统中,包括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以及自由化民主中,都可以看到它们存在的证据。
- 「不连贯的政治」是一种倾向于消解现有制度束缚的政治。它既不倾向于一个中心,也不希望将现有的形式汇集成运动,或以「解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之名出现,即一些作者乐观地称之为的「激进民主」。这里的原则不是重复过去的表现,渐进地抵制资本主义,或者其他什么,就像在马克思的鼹鼠的例子中那样。相反,人们必须遵循与当下决裂的原则,而不是简单地实现自己的欲望,而是革新欲望本身的意义。
(译注:马克思试图从鼹鼠及其地下通道的角度来理解19世纪欧洲出现的无产阶级斗争循环的连续性。马克思的鼹鼠会在公开的阶级冲突中浮出水面,然后再次隐藏起来——不是被动地冬眠,而是挖掘它的隧道,与时俱进,与历史一起前进,这样当时机成熟时它就会再次浮出水面。 )
(让我重申,连贯和不连贯是非规范性的术语;它们必须更多地被理解为「固定」或「不固定」,而不是「好」或「坏」或「理想的」(desirable)或「不理想的」。我已经暗示了德勒兹使用的类似术语,「辖域化」和「解域化」,但不同的作者使用不同的术语。例如,在海德格尔那里,最接近的同义词是「沉沦」[falling, verfallen]和「被抛」[thrownness, Geworfenheit])。
有了列举的四种,我们可以把它们以不同的组合方式搭配起来,以达到一些不同的意义制度。首先,将连贯的美学与连贯的政治配对起来,就是通常所说的意识形态(ideology),更讨人喜欢的术语是「神话」(myth),不那么讨人喜欢的则是「宣传」(propaganda)。因此,在意识形态制度中,美学的固定性(fixity)和包含其中的政治欲望的固定性之间实现了某种同质性。(这并不是说,对于任何意识形态的形成来说,在审美和政治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天然的关联,而只是说由于它们都是连贯的,所以存在着一种相似性)。因此,所有形式的意识形态和宣传性文化形式,从情节剧到迈克尔·摩尔、马修·阿诺德,还有马克思,都将被纳入这一制度。鉴于前文所述,将洛克威尔与这一制度联系起来也是合适的,因为他的形象显示了一种连贯性的美学(精细的插图技艺,作为天才的艺术家,创作过程的复杂漩涡),以及一种连贯性的政治(妈妈和苹果派,以及只有妈妈和苹果派 mom-and-apple-pie,代表一种美国的健康和传统的价值观)。
然而,如果这些术语被稍微改变,第二种配对就会变得明显。把不连贯性的美学和连贯的政治联系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伦理的(ethical)意义制度 [10]。这里总是有一个「固定的」政治渴望,通过在美学装置中应用各种自我揭示(self-revealing)或自我否定的(self-annihilating)技术而产生。例如在二十世纪进步文化的典型故事,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的《世纪》(The Century)中所讲述的故事,伦理制度围绕着各种现代主义启发的左派进步主义的味道。因此,在布莱希特那里,有一种不连贯的美学(离间效应,装置的前景化),与一种连贯的政治(马克思,并且只有马克思)相匹配。或者说,为了唤起上述的中心参考,《疯狂》图像提供了一种不连贯的美学(打破第四面墙,拥抱视错觉),与一种连贯性的政治(通俗趣味并且只有通俗趣味)相结合。当然,还有更多的名字可以被堆积起来:让·吕克·戈达尔在电影中(将电影拆散以支撑马克思列宁主义);Fugazi 在朋克中(将声音拆散以服务于 D.I.Y. 的生活方式);等等。
然而,应该指出的是,受现代主义启发的左派进步主义并不是伦理制度的终点。我已经暗示过了,我称这个游戏为布莱希特式的,我希望将《魔兽世界》归入这一制度。但为什么呢?我已经给出了所有的理由:这个游戏显示出了一种不连贯性的美学,因为它前景化了装置(统计数据、机器性功能、怪物刷新的循环、物品界面、多线程等等),同时一直在推动一种特别连贯的政治(协议化的组织、网络化整合、与传统社会秩序的疏离、新的信息劳动实践、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群体互动、新自由主义市场、博弈理论等等)。因此,《魔兽世界》是一个「伦理」的游戏,仅仅是因为它一方面开放了美学,另一方面又关闭了政治。同样,我使用的是伦理一词的普遍(而非道德 moral )定义,即在某些规范性框架内的一套广泛的实践原则。《魔兽世界》与信息经济有更多的关系,戈达尔的《中国姑娘》(La Chinoise)与毛泽东思想有更多的关系,并没有削弱两者在伦理制度中的作用。
现在出现了第三种模式,它可以被称为诗意的(poetic),因为它将连贯性的美学与不连贯性的政治相结合。这种制度经常出现在某些现代主义一类的作品中,特别是被称为「为艺术而艺术」的高度形式化的、对外界漠不关心的一派,但更普遍的是,在所有形式的美术作品(fine art)中。它被贴上 「诗意」的标签,只是因为它与「产出」(poesis),或与普遍意义上的意义创造相一致。风险不是形而上学的,在形而上学中,任何图像都要与它的原始图像相衡量,而是艺术的半自主的「物理学」(semiautonomous physics),也就是说,在模仿性表现中促成成功或失败的技巧和方法。
亚里士多德在他的《诗学》中首次记录了这些技巧和方法,而整个诗学体系的一般的品性自此几乎没有改变。在这一制度中,存在着他们技艺的伟大天才(因为这是「天才」这一概念找到其天然归宿的制度)。阿尔弗雷德·希区柯克或比利·怀尔德(Billy Wilder),德勒兹或海德格尔,大部分的现代主义,所有的极简主义等等。但你反驳说:「当然,海德格尔或德勒兹的作品是政治性的。为什么要将他们进行分类到这里?」答案在于政治在这两位思想家身上的具体性质,以及哲学的艺术被提升到其他关切之上的方式。我的主张不是说这些不同的人物没有政治性,而只是说他们的政治是不连贯的。埃亚尔·魏茨曼(Eyal Weizman)曾写道,以色列国防军在战场上应用了德勒兹和费利克斯·瓜塔里的教义。这并不说明德勒兹和瓜塔里思想的堕落,而是说明作品对各种政治性实施的接受性(即其「不连贯性」)。
把德勒兹和瓜塔里带到加沙,并非要亵渎他们,而是要利用(deploy)他们。迈克尔·哈特和奈格里,以及其他人也已经表明根茎是如何被采纳为霸权主义权力系统的结构图的。这并不是要诋毁德勒兹和瓜塔里,而只是要指出他们的工作在政治上是「开源」(open source)的。这些思想家的具体政治内容的无法固定,本身就证明了它在根本上是诗意的(而非伦理的)。换句话说,「诗意的」制度总是能接受不同的政治适应,因为它让政治问题开放。这也许是接近「诗化本体论」(poetic ontology)概念的另一种方式,这是巴迪欧给德勒兹和海德格尔的标签。虽然就他自己而言,巴迪欧的思想也不乏诗意,但他最终离开了「诗意化」的制度,而这要归功于一种错综复杂的、激进而具体的政治理论。
最后一种模式是四种模式中最难以捉摸的,因为它在现代文化中从未取得任何形式的真实存在(bona fide existence),无论是在主导地位还是在各种「被接纳的」次要地位。这是一种肮脏的制度,其中审美的不连贯性与政治的不连贯性相结合。我们将简单地称它为真理(truth),尽管其他术语也足够了(虚无主义、彻底的他异性、非人类)。真理制度始终处于旁观者的位置。它的出现不是通过「被压迫者的回归」(return of the repressed),因为它从来都不仅仅是统治者的被压迫者。相反,它最好被理解为「被压迫者的被压迫者」,或者用另一个时代和地方的术语,「否定之否定」(negation of the negation)。我们是否可以将某些名字与这种模式联系起来,与美学和政治中的不连贯性联系起来?我们可以把尼采的名字联系起来吗?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名字?前路并不那么确定。但目前也许最好还是保持这种状态。
所以总的来说,这就是意义的四个制度:
- 意识形态的:连贯性的美学,连贯性的政治。
- 伦理学的:一种不连贯的美学,一种连贯的政治。
- 诗意的:一种连贯性的美学,一种不连贯性的政治。
- 真理:一种不连贯的美学,一种不连贯的政治。
在结束之前,有必要对这个系统做一些评论。首先,整个分类系统似乎在说明艺术和正义之间的关系。在第一个制度中,艺术和正义是相连的。人们只需将其中一个内化,就能达到另一个。在第二种制度中,这个过程略有不同:人们必须摧毁艺术,为正义服务。在第三种情况下,它是颠倒的:人们必须完全放逐正义的范畴,以见证艺术的神化(apotheosis)。最后,在第四种情况下,救赎来自于对所有现有艺术标准和所有公认的正义模式的平等摧毁。
其次,在对这四种制度进行仔细研究之后,很明显存在着一种等级,如果不是针对所有的时代,那么至少是针对我们所处的特定文化和历史形态。也就是说:第一种模式是占主导地位的(尽管经常被诽谤),第二种是有特权的,第三种是被接受的(tolerated),而最后一种则是相对局外的。因此,我在这里按优先级顺序介绍了它们。
但是,除非能将其历史化,否则这个等级就没有什么价值。因此,一个额外的主张是有帮助的,从上面关于《魔兽世界》的章节中重申:如果对这些制度在游玩经济时代的用途变化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我们今天正目睹着其首要地位从第一种转向第二种,也就是说,从「意识形态」制度向「伦理」制度的总体转变。今天,意识形态正处于衰退之中;意识形态的效率也在下降。意识形态在传统上被定义为「对现实状况的想象性关联」(imaginary relationship to real conditions)(阿尔都塞),在某些意义上,它已经成功得不能再成功了,可以说,消灭了自己的工作。相反,我们有了模拟(simulation),它必须被理解为某种类似于「与意识形态状况的想象性关联」(imaginary relationship to ideological regime)的东西。简而言之,意识形态在软件中被建模(get modeled)。因此,在意识形态制度的完美中,以其纯数字化的模拟形式,带来了意识形态制度的死亡,因为模拟作为意识形态世界的绝对的地平线(absolute horizon)而被「加冕为冠军」。计算机是终极的伦理机器。它与意识形态没有任何真正意义上的实际关系,只有一种虚拟关系(virtual relation)。
然而,我毫不含糊地强调,这并不意味着今天的社会风气比过去更「道德」(在做好事的意义上)或更多或更少政治化。请记住,伦理化模式(#2)被贴上了「伦理」的标签,因为它采用了各种规范性技术,其中给定的美学主导因素被打碎(通过对装置的前景化,离间效应等等),以服务于一个特定的期望的风气(ethos)。
最后,鉴于意识形态形式(#1)和真理形式(#4)都可以被至于括弧内,一个因被蔑视,而另一个因被恐惧而被驱逐出受人尊敬的话语,这个系统可以大大简化为两个制度(#2和#3),并揭示出一种原始的公理(primordial axiom):一部作品在美学上越是连贯,在政治上就越不连贯。反过来也是如此:一部作品在美学上越不连贯,它在政治上就越连贯。
因此,原始公理(当然它不是这样的东西,只是对实际存在的文化产品进行分析后产生的一套倾向)提出了两个典型的案例,即伦理学和诗意性。用简单的语言来说,第一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具有政治意味的艺术;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所说的纯艺术(fine art)。前者是戈达尔,后者是希区柯克。或者,如果你愿意,前一种是《魔兽世界》,第二种是《半条命》。前者制定了媒介性条件(mediatic condition),但并不相信它;后者相信媒介性条件,但并不制定它。
在最后,我们可能会回到我们的真言,即界面是一种不会中介化的媒介(interface is a medium that does not mediate)。它是不运行的(unworkable)。然而,困难并不在于这种困境,而在于界面从未承认过这种困境。它把自己说成是一扇门或一扇窗或其他某种临界,而我们必须简单地跨过它们来接受外在的慷慨。但是一个事物和它的反面从来没有被界面以这样一种整齐的方式连接起来。这并不是说「不连贯性」最终胜出,而使其他模式失效。这只是说,在作品的美学形式和它所处的更大的历史物质背景之间,会有一个对象内部的内界面。如果「界面」可以在任何地方找到,它都就在那里。我们所说的「文字」、「图像」或「对象」,只是试图解决这种无法运作性的问题。
NOTES
NOTES
[1] Michel Serres, Le Parasite (Paris: Éditions Grasset et Fasquelle, 1980), 107 (my translation). 对于「windows」这个主题,还应该引用软件行业在设计图形用户界面方面的努力。微软给这个神话打上了烙印,但它却在所有个人电脑平台上传播,包括「进步」的(Linux)或不那么进步的(Macintosh),以及各种更小、更灵活的设备。许多书也讨论了这个问题,包括 Jay David Bolter and Diane Gromala, Windows and Mirrors: Interaction Design, Digital Art, and the Myth of Transparen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and Anne Friedberg, The Virtual Window: From Alberti to Microsof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2] 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在他的书《对空言说》(Chicago: of Chicago Press, 1999) 中雄辩地阐述了这一点。对彼得斯来说,这个问题存在于心灵感应和唯我论之间,他提出的第三个综合选项是塞尔的一些不那么愤世嫉俗的版本:媒体化(mediation)作为一个永久的、有意识的自我与他者之间协商(negotiation)的过程。
[3]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 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50).
[4] Guy Debord, Correspondance, 5, Janvier 1973 - décembre 1978 (Paris: Librairie Arthème Fayard, 2005), 466 (my translation).
[5] Hesiod, Theogony, trans. Richmond Lattimore (Ann Arbor: of Michigan Press, 1959), 124.
[6] François Dagognet, Faces, Surfaces, Interfaces (Paris: Librairie Philosophique J. Vrin, 1982), 49 (my translation).
[7] 诚然,麦克卢汉比我的快照描述得更清晰。在描述哈罗德·英尼斯(Harold Innis)的方法论时,他将界面描述为一种媒介之间的摩擦(friction between media),一种生成刺激的力量,而不是构建一个人视角的简单装置:「(英尼斯)将他的工作过程从使用「观点」转变为使用化学中所称的「界面」方法产生洞察力。「界面」是指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一种相互刺激。」马歇尔·麦克卢汉,《媒体与文化变革》,载于《麦克卢汉本质》(纽约:基础图书出版社,1995),89。(译注:有近来观点认为麦克卢汉所说的是 干涉(inference)而非界面)
[8] 我首次学到这种令人愉悦的讽刺是参与 Art Spiegelman at New York University on October 6 的讲座,
[9] Gérard Genette, Seuils (Paris: Éditions du Seuil, 1987), 8 (my translation).
[10] 我从雅克·朗西埃的惊人小书《Le partage du sensible: esthétique et politique》(Paris :La Fabrique, 2000)中获得了一些术语上的灵感,该书的英文版本为《美学的政治:感性的分配》,New York: Continuum, 2004)。与他的伦理学-诗歌-美学三角关系的任何相似之处充其量只是表面的,尤其是,他的「伦理学」与柏拉图式的道德哲学紧密相连,而我的主要指的是一种积极的、政治化的实践伦理。然而,在「诗意」一词的两种用法之间存在着重叠,在他的「美学」和我的「真理」之间也存在着一种融洽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术语都指的是一个自主的空间,在此空间中,美学开始回返自身,并开始自己的绝对旅程。
日 | 落 译介计划最近也收录了来自友链 观察者的技术 公众号所发布的 Alexander R. Galloway 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的起源 Origins of the First-Person Shooter (2006) (翻译:冬寂網路)以及 Marco Benoît Carbone 论游戏作为媒介的研究 On The Study of Games as Media (2021) (翻译:周子寰)
落日间是一座有关「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迷宫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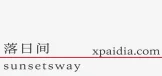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1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