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编者按
编者按
未来是如宇宙般的孤独(The future lies in cosmic solitude)
在现实变得如此魔幻的日子里,一个问题困扰着我,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怎样地对游戏的思考?而什么样的游戏能以怎样的方式来回应这个世界,还是我们应该缄默不语,假装一切从未发生,在美好的花园间继续沉醉。
确实很难想象,当世界发生的事情关涉到灾难、悲剧、自由时,我们还能将心力放在如何制作一个纯粹如娱乐幻梦的产品中去。至少对我来说很难。
至少接下去的时间中,我会努力尝试回答自己的这种困扰。
在进行漫无目的地搜索中时,我发现了法国激进哲学家 Virilio 这一篇小访谈,很少见地,正面地多少谈论了电子游戏,在1995年,那个 3D技术都还只是萌芽之初时。
他谈的不仅仅是电子游戏,而这正是其有趣的地方。
我很喜欢他谈论事物的方式,合适的切分,有趣的双关语,还有惊人的预见性。他说「无法想象这在几代人之后最终会产生什么」。
而在二十五年后的今天,整整一代人过去,Virilio 也在四年前过世,今天人谈论战争的方式,或许就如同谈论「游戏」一般,不仅游戏失去了严肃成了戏谑,而现实的严肃也被这种戏谑所侵扰。
我们正看见重影(we are seeing double)。
Paul Virilio
Paul Virilio
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32—2018 )是1970年代以降最富原创力的法国哲学家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城市建筑家、随笔作家。1963年,维利里奥与建筑师克罗德·巴宏(Claude Parent)成立“建筑原则”(Architecture Principe)团体,并发行同名刊物,宣扬建筑的“倾斜功能”(水平与直角被彻底弃绝),曾先后完成两栋建筑作品。1973年起执教于巴黎建筑专业学校(ESA),直到1999年退休。维利里奥的哲学著作围绕着一系列以科技、速度、城市、虚拟、事件、意外及失序为核心的概念群,他出版了《速度与政治:论速度学 Vitesse et Politique : essai de dromologie》、《战争与电影》、《无边的艺术》、《解放的速度》《Pure War (with Sylvère Lotringer)》、《Popular Defense & Ecological Struggles》、《消失的美学》、《视觉机器》、《The Art of the Motor》等。他最出名的是他所谓的「dromology」 速度的科学,以及对速度的研究。
The Game of Love and Chance: a discussion with Paul Virilio
The Game of Love and Chance: a discussion with Paul Virilio
采访者:JÉRÔME SANS(简称桑)
受访者:PAUL VIRILIO(简称维)
桑:当代世界正见证着休闲社会的巨大演变。通过家庭购物和付费电视、视频游戏和虚拟现实,我们正在发展一种成熟的游玩的美学。
维:对于这些新技术,可以有两种态度:一种是宣布它们是奇迹;另一种(也是我的态度)则承认它们的有趣的同时保持批判态度。在家中安装的家用模拟器和准备用于游戏的虚拟空间房,这些提出了许多问题,特别是这个:「当虚拟一旦侵入了现实,游戏是什么?」
对游玩的概念(notion of play)有两种理解方式:打牌、多米诺骨牌、跳棋;或者是一个机械部件在其外壳中松动时的游戏(the play of a mechanical part when it is loose in its housing)。我认为,事实上第二种方式才是我们今天应该设想游玩的角度。
游玩不是带来愉悦的东西;相反,它表达了现实中的转变(shift),一种相较于现实不寻常的流动性(an unaccustomed mobility)。
今天的游玩,在某种意义上,意味着在两个现实之间做出选择。一个具体、真实的现实:遇见某人,爱那个人,和那个人做爱。或者,游戏的现实:使用赛博性爱(cybersex)的技术,远程地认识那个人,没有触碰或污染的风险,没有接触的接触(contact without contact)。
在这种情况下起作用的是一种不同于与传统游戏相关的、由运气激起的病。赌徒离不开运气——他们对运气上瘾,且无法打破这个习惯。我相信,与那些对运气、轮盘、纸牌或任何游戏上瘾的人一起,一种新的上瘾者正在形成:对虚拟上瘾的人(the addict of the virtual)。
那些离不开虚拟的人将会迷上它,并会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尴尬的位置,在这两个现实之间纠结。我们可以在华尔街和股票市场上看到这一点,在那里,「交易员 traders」 或 「黄金小子 golden boys」玩弄着国际市场的虚拟性,而这些市场与世界的经济现实越发脱节。
桑:这是一种电子上瘾,导致了虚拟上瘾。
维:你可以说,毒品是一种「人们上瘾的游戏」那。些沉迷于纸牌游戏或轮盘赌桌的人,最后总是在玩「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游戏和死亡,游戏和意外,都是相关的。当你把玩运气时,你就在被迫,而不再自由地玩;并且身体或精神上的死亡开始发生。现在视频游戏或明天虚拟现实的更复杂的游戏将引发这种同样的死亡欲望。一种跨越边界的欲望。
我不是一个大玩家。在今天的游玩状态中,我感兴趣的是网络性爱,因为它似乎是社会放松管制中最特殊的一面。除了今天的离婚流行——这可以归因于其他事情,而不是缺乏道德(我在这里不是在扮演道德家)——另一种类型的离婚正在酝酿。
现在人们不再生活在一起,而是分开生活。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没有网络性爱,但在网络性爱将培养出的氛围中)是一对学生夫妇,他们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婚礼,仪式结束后,分别回家了。他们告诉我,「这样我们就能保持自由。」「那很好,」我说,「如果有一天你们离婚了,你们的孩子也不会感到震惊,因为无论如何他们都会在你们的两个家里分配时间。」
网络性爱把这种逻辑推得更远。这不是离婚,而是伴侣之间的解体。你不再做爱了,因为这很危险,因为有时会出现问题——一个人可能不是很熟练,或者情况可能变得很混乱。所以你使用一种机器,一种通过电波传递身体和性接触的机器。起作用的不再是外壳中的连接杆,而是我们对身体经验中最亲密事物的丧失。
演员 Louis Jouvet 写道:「除了身体和它的感觉,一切都很可疑」。从现在起,随着虚拟性和电子交配,甚至身体和它的感觉也将被怀疑。在网络性爱中,人们可以看到、摸到和闻到。唯一不能做的是品尝对方的唾液或精液。这是一个超级安全套(super-condom)。
桑:社会学家 Michel Maffesoli 谈到了「新部落主义」(neo-tribalism)的发展,一种通过远距离通信的所有可能性来重新组合的愿望。尽管如此,我们似乎仍然在处理一种孤独的满足感。
维:我不相信部落的回归,我也不认为一个帮派(gang)是一个部落。正如我在《L'Inertie Polaire(极端化的惰性)》一书中所说,即将到来的是地球人,一个自给自足的人,在技术的帮助下,他不再需要向他人伸出援手,因为别人会来找他。有了网络性爱,他不需要在伴侣的家里做爱,爱情会立即来到他身边,就像电子高速公路上的传真或信息。未来在于宇宙般的孤独(The future lies in cosmic solitude)。我想象一个失重的个体坐在人体工程学的小扶椅上,悬浮在太空舱外,下方是地球,而上方则是星际的虚空。一个有着自己重力的人,不再需要与社会、与周围的人、至少是与家庭的关系。Maffesoli 的部落化是一种完全过时的观点;未来在于一种无法想象的孤独——游戏(play)是其中的一种元素。
桑:人们的印象是,玩家的追寻以自恋的高潮结束。
维:是的,但这是一种正在扩张的自恋。
桑:有人甚至说,电子游戏标志着圣像的现代凯旋(modern triumph of the icon)。
维:这些人都是奇术士(thaumaturgists),是奇迹传道者。你必须对批评家 Jacques Ellul 所说的「技术虚张声势(the technological bluff)」保持极大的警觉。今天,我们有一些崇拜者,甚至是专家,他们整天都在说技术是多么美妙。他们正给它以死亡之吻。通过保持批判性,我为新技术的发展做了更多的事情,而不是屈服于我的幻想,而拒绝质疑技术的消极方面。
当铁路被发明时,脱轨现象也被发明了。然后有像我这样的人立即说,他们并不关心火车是否伟大,是否比驿战马车更快。更重要的是他们不能出轨,火车特有的事故不能阻止它的发展。这些人致力于解决铁路事故的问题,并发明了信号的「块状系统」(block system),这使得法国的高速列车 TGV(Train à Grande Vitesse) 成为可能。航空业也是如此,等等。虚拟现实的事故,电子通讯的事故,比脱轨事故要少得多,但它们有可能同样严重。只要我们听信快乐的预言家,那就不会有「块状系统」了。
桑:电子游戏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想象力的一面,一个奇妙绝伦的叙事,一个玩家可以通过它踏上一段英雄的旅程。
维:这很关键。在写作的社会中,叙事就是旅程。梅尔维尔在《白鲸》中的第一句话——「叫我伊什梅尔」——让故事开始运转,开启了伊什梅尔的旅程。在写作中,叙事带着你走。在屏幕上,是旅程,是视觉而非描述性的旅途的模拟让你感动(沿着轨道航行,穿过迷宫,穿过隧道)。
因此,模拟器成为新的小说。而这段虚拟旅程的模拟质量(simulation quality)取代了故事的诗意质量(poetic quality),无论是《一千零一夜》还是《尤利西斯》。
桑:所以新玩家是一个旅行者( traveler)。
维:是的。但现在旅行者是被旅行的。梦想者是被梦想的。他们不再是自由活动,而是被程序所旅行。他们不再有做梦的自由,他们被程序所梦。
桑:这个玩家是匆忙的英雄(a hero in a hurry)。
维:他是一个被机器催促的人。心理图像(mental images)被机械装置(mechanical instruments)所取代。在阅读时,人们制造了一个精神电影: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不同的包法利夫人在她的窗边。而在包法利的视频游戏中,将只有一个包法利夫人,程序中的那个。
桑:我们又回到了你的老本行:「图像即武器」的观点。
维:网络性爱实际上是性爱的内战,因为人们被它所分割。更复杂的游戏可以完全取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说,民意调查——电子民主——不就是正在取代政治现实的大型电子游戏吗?
桑:电子游戏和战争程序产生的模拟有什么区别?
维:正如我在《荒漠的荧屏》(L'Ecran du désert)(我的海湾战争记录)中写道,许多战略家说,通过购买美国的电子游戏比看电视新闻更容易理解海湾战争。在某种意义上,他们是对的。我们没有看到具体的事件——例如,地面部队是如何突破伊拉克边境的——但我们确实看到战争被转化为电子游戏,同样的画面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一把武器击中了它的目标。这种形象仍强烈地存在。感知被分割成两个现实,导致了一种堪比中毒的模糊(blurring):我们正看见重影(we are seeing double)。无法想象这在几代人之后最终会产生什么。生活在一个现实中,而不时地进入另一个,度过一夜的饮酒或迷幻剂是一回事。但是一直通过电信和电子高速公路而生活是另一回事。我认为我们甚至无法想象,始终生活在这种 「立体现实」(stereo-reality)会在人们的头脑和社会中引发些什么。这绝对是没有先例的。
桑:面对过剩的可能性,我们应该玩什么游戏?
维:做一个批评家吧(Play at being a critic)。解构游戏,以便于它一同游玩。与其接受规则,不如挑战和修改它们。没有批判和重建的自由,就没有真正的自由游戏:我们仅是瘾君子而已。
西方游戏中的暴力讲的都是权力,然后愈演愈烈。那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并没有经历过战争。我们在电视上观看战争,听著有关战争的故事长大,但根本没有接触过真的战争。
封面图为:1993年,灵感来自海湾战争的游戏《Desert Strike:Return to the Gulf》
落日间是一个探索「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媒体实验室。
感谢朋友们:@小雨 @阿伟 @11 @昕仔 @某小熊猫猫 @少楠 @Bob傅丰元 @小河shan @希辰Xichen @小乐 @DC @Bynn @webber @绅士凯布雷克 @侯晨钟 @Minke @Roam @兜&敏 @KIDD @菲兹 @喵呜 @李喆 @特特 @Skellig @阿和 @某大王akak1dD @solsticestone @鱼片与花卷 @Stoney @树袋熊 @MrNewton @鸭脖拉罕 @松果 @五香丸子@纪华裕 @李朵拉 在爱发电的赞助及所有关注者的 支持!:)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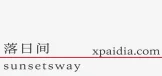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