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落日间链接:采访:电子游戏、艺术与正名 | 落日间
前段时间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学生找到我,说他们在做大创研究,题目是电子游戏评价的两极化研究,电子游戏是《「第九艺术」还是「精神鸦片」》,希望找我做一个访谈。
在后来进行访谈中,借着学生的问题,我展开且即兴谈了不少当下那个时间点中自己对游戏的本质,对创作游戏,以及正名游戏的一些看法。收到访谈整理稿后我稍作和编辑,希望能为后续正式分享「界面式研究创作」方法,和未来更加不确定和晦涩的思索铺下一条坚实和平实的道路,也留下当下的印记。
感谢访谈的同学的邀请,记录和整理。
叶梓涛
落日间
访谈正文
访谈正文
Q1
先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我们是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的一支课题团队,我们目前在参加学校的大创活动,我们做的课题是电子游戏被污名化的成因以及其成为艺术的可能性。
首先还是想对叶先生的基本情况做一个小小的调查。我想问一下您最早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电子游戏的?早期对您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几款电子游戏是什么?
A1
六七岁跟家里的亲戚有一起玩过小霸王,然后小学时正值电竞正名的一个浪潮开始,2003年电子竞技被国家体育总局列为正式开展的第99个体育项目,那段时间我蛮激动的,就关注电子竞技比较多,而电竞官方化的这个过程我感觉可能也和你们在做的游戏正名蛮有关系的,对我当时作为一个小朋友的情感来说也是如此。这是一个基本经历,当时也有接触过一些单机游戏等等。但其实是要到大学本科时才有这种游戏自觉去主动接触各种各样的电子游戏,包括独立游戏这些。
Q2
您目前游玩游戏的频率是什么样子的?一周几次?一次大概多久?
A2
很多都是工作需要,比从业之前要玩得更多,特别的散,特别的泛,比如说一天可能会突然看两三个小游戏,比如之前去帮忙游戏评奖,你就得玩三四十个游戏,或者参加一些那种GameJam,你要给别人打分,你得等于是一口气玩个一二十个小的游戏,很多样。而有些时候也会去看一些大一点,但也可能就玩开个开头就没玩下去了。然后就是说可能会区分,区分为有些是工作或研究的诉求,有些是纯消费(体验)。我也会反思是不是自己玩得不够深入,是不是一个游戏玩了就要把它完成(就像一本书读了就要读完一样)就像最近也有在补的一些,比如说《小小梦魇2》《Splatoon3》《密特罗德》《汪达与巨像》《最后的守护者》这种,把以前这些可能只玩了开头的游戏玩掉。但其实对我来说,游戏太多了,各个平台加起来几千个,大大小小独立游戏什么的。而其实「消费」是不重要,因为当你想把游戏玩完(完成),那还是一个消费的思维逻辑。远不如还是无论是研究,学习或其他的目的去进行,或者纯粹的体验(而非完成)去面对一个游戏。
Q3
您目前玩了这么多电子游戏,您最喜欢的类型是什么?最喜欢的作品又有哪些呢?
A3
这很难说,我玩的类型很多,我感觉我会喜欢一些体验丰富的和一些比较有实验或者开创性的,除此之外的话,其实我也蛮喜欢的偏动作的游戏,比如魂系,还有一些小众的独立游戏,其实以前那些平台动作包括《蔚蓝(Celeste)》这种就基本挑战还算在合理范围内的,比如说像《只狼》这种,对我来说可能当时那个时间节点就会蛮喜欢的。
但你说最喜欢真的很难讲,但随便举几个想到的,比如说吹哥的《见证者(witness)》,Jason Rohrer的 《Passage》,然后《只狼》可以算一个。
因为喜欢有很多不同的喜欢,比如说你特别欣赏他的一些设计,然后有些是你玩完之后觉得体验很完整,还有一些比如说他在某方面做的挺极致的或是做到一些我想要的体验,可能我也会觉得说他做得挺棒。我觉得每个游戏或它背后的创作者,其自身的设计哲学和他的游戏有这整体的关联。不同的创作者都会处理一些自己的课题,如果他处理得有意思,我就会挺欣赏的。比如Bennett Foddy的《掘地求升(Getting Over It )》我觉得他处理得特别棒,比如陈星汉就一直在做陌生人社交的工作探索(《Journey》《Sky:光遇》等),虽然说我没有说玩得很多,但是我也很喜欢,我觉得他们都在做一些很重要的工作。
Q4
好,基本情况我们就问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开始聊一些课题内的东西。首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电子游戏的定义和定位分别是什么?然后这个定义和定位会在游戏制作者和游戏玩家身份之间出现割裂吗?同时拥有两种身份的您是如何去评价、如何去感知的?
A4
对我来说这个割裂更多是在游戏研究者和游戏创作者之间。我觉得这两者默认都得是玩家,不太应该存在不是玩家的游戏设计师,或者不是玩家的游戏研究者(不排除极少数)。
我对游戏的定义本体论层面我觉得比较难直接说出来。我最近在尝试把我对其的想法写出来,我会把游戏制作定义为它是「对某种制作的制作」,比如说游戏设计师他并不是做出一个盘子,加工出来一个盘子给别人,他是加工出来一种「加工盘子的方式」去给到别人,让别人去制作出盘子。
在这个角度来说的话,这就是一种涌现,一种创造,如果你们是哲学系的你们可能会知道亚里士多德或者海德格尔谈的 poiesis(ποίησις, the activity in which a person brings something into being that did not exist before),就翻译成制作、创作吧。但你也可以把它看成一种涌现,或者说一种带出、自然的东西的生发。
我觉得游戏制作者是在处理这样的一种事物涌现,和创造的过程。这个是比较抽象的意义上我一直在考虑的,如何把比如说那种解谜游戏、偏自然研究的这种游戏,和那种偏动作的,偏身体和器官创造的那种游戏,去找到一个共同的概念将其贯穿起来加以深入思考。
我现在简单来说,自己现在对游戏的理解,我是觉得每个游戏一定是关于某个其他一件什么事的,是关于一件游戏外的一个事情,游戏它是不能独立的,不能是非常单纯的或者是形式化、纯洁化地存在的。
前段时间翻译的一篇文章(Brendan Keogh 穿越世界和身体 Across Worlds and Bodies (2014))就是一个游戏研究者,他在批判说在游戏研究中,其实也是在我们玩家里,有一种对于纯洁性的渴求,就觉得游戏是非常独特的,游戏有一种之前所有媒介所没有的一个很特别的东西,然后觉得我们要找到一个纯粹的游戏,它和其他东西都不一样,这本质上就是一种格林伯格当时在评论《现代主义绘画》说,现代主义绘画就是有一种康德式的反思,就觉得我们要去反思是什么让绘画成为了绘画,那就是一块平面,它就是它最就一幅画最少能够构成的要素,所以它就是绘画的本质。但是按这个思路去推的话,那实际上有点混淆了「一幅画的本质」和「让一幅画成为一个画的最基本的条件」。
所以说在这个意义上,这种对游戏纯洁性的追求,就是我现在慢慢开始反思的。到底要怎么去给游戏正名?包括玩家在内的很多人会觉得我们要去说,游戏特别强、游戏特别厉害、游戏有交互性、游戏是第九艺术。但这个思路其实你会发现他最后到的是一种自恋,一种封闭的状态。
我现在对游戏的理解和思考的话,更像是一种:我们总是可以发现游戏是在处理其他的一些事物。你能找到很多化学-游戏,你能找到很多视频-游戏。游戏在这个意义上可能更像一个副词或是一个形容词,你可以找到一些电子游戏化的电影,电子游戏化的文学,然后你就可以去关注它们两种事情(游戏 | 电影、游戏 | 文学)可以怎么样结合,并且相互去改变和影响,然后以此去带给其他的这些东西一种更多的生命、一种新的形态。
我现在可能就会以这种方式去开展研究,包括有一些和声音、和哲学、和文学等等这种方式去做,然后去尝试能够连通双方的一个共同的谱系。因为你也可以在音乐里面找到很多很有游戏逻辑的这种生成式音乐,或者是互动音乐里,他们以参数化的音乐去生成。你也可以在文学里面找到很多像乌力波(Oulipo),像这种非常有游戏性的,或者是其实它某种程度上就可以变成游戏的一种文学实践。
这些共同的地带我称之为界面(interface),就是游戏和另一个事物/领域的界面。我觉得这样的挖掘。它会有助于我们处理我所说的游戏的文化困境。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也暗含着一种对游戏的本体论的定义,至少在操作层面上,它就是一个和其他事物结合在一起的东西,它是一种运作方式,它并不是一个单独的一种独立的媒介去独立存在的。
Q5
我有一个想追问的地方就是,您刚刚在论述的过程当中我感觉有一个地方没有讲清楚的是,关于游戏和电子游戏之间,我觉得是存在有一个沟壑。因为比如说你说游戏作为一种运作机制,其实电影也可以作为一种运作机制,比如说电影它也是关切于电影之外的东西,对不对?没有一个只是为了电影而存在的电影。那电影肯定也会分,比如说纪录片也好,或者说悬疑片也好,我感觉什么东西它都不会自在自为,它肯定都是为了自己以外的东西去存在的。
A5
电子游戏和传统游戏差异的这个问题其实我之前和阵地Lefront做巴塔耶研究的朋友有聊过(E36 劳作是奴役,游戏才是至尊 ),他就觉得这之间有某种断裂或者有某种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但其实比如说后面我去写《电子游戏何以神圣》这篇文章,我就是希望把这两个东西串联起来看的。
我觉得我目前思考的是,计算机的出现给科学研究带来什么?海德格尔说控制论的诞生是哲学的终结,计算机出现在洛伦兹那个时代,它给他发现的非周期流(《决定性的非周期流(Deterministic Nonperiodic Flow)》),就是所谓的混沌现象或者涌现的现象,给今天的很多这种物理研究,自然研究,带来了一种新的模式,就是它可以去建模,去计算。而计算,也慢慢成为了一部分学者对自然运作方式的核心的一种认知(比如《复杂》中提到的 Stephen Wolfram)。
比如说围棋它本身就是一个二进制的游戏,或者说围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计算机的东西,或它本身就是一种计算机,甚至可以说是围棋发明了计算机。这种二进制的模式,它本身也是图灵完备的,就有点像元胞自动机。在这个意义上,我完全可以把围棋这个东西直接搬到电子游戏上,不需要改动什么东西。实际上是我们引入的这种计算机的能力,它会带来一定的从模拟转换到数字的一个过程。所有的这些在现实生活中离散和连续的东西,在游戏中都会被以一种离散的方式进行数字化。我们会有像素,现实生活就像是一个无限像素无限放大的世界,但是在游戏它会被像素化。我现在说的这段话它被传输过去,信号是不怎么损失,但是实际上它会被麦克风的振膜接受,从一种连续的变化变换到一个离散的一个信号,离散信号再重新被接收。电子游戏它设计的时候,就在处理这种离散化的不同的媒介,所以说一方面它可以把这些不同的媒介以一种打平(即全部还原到同质的离散化的比特后再编织)的方式,比如说我可以让这几个媒介同时在同样一个平面上发生新的一些关系、连接和操作,所以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也就是说计算机可以把万物比特化并且编织出来。
等于说过往这种游戏的创作方式,它可以有了一种解放,但纯粹的数字化,它可能也会带来另外的风险,因为它可能会把连续的那部分东西给它取消掉。比如说你练一个手指的舞蹈,转一个球,能感受到自己的身体和这个球的连续的体验,这个空间可能性是无限的。或者说你在一个世界上最小的这种普朗克时间意义上来说,基本上是近乎无限的嘛。但是在做一个电子游戏的时候,某种意义上它也是无限的,但是它是一个相对来说被离散化的,因为你所有的输入都不可能超过60帧每秒的。这个意义上来说,它是被切开的。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去批判的,但是其实在很多时候你可以凭借这60帧每秒的离散的过程,构建出来一种连续的感觉。比如说电影的24帧每秒也是一种运动再造,也是一种连续的绵延的一个过程。所以如果游戏或计算机能用一种离散的方式创造出来一种新的连续,那这种连续和原来的连续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区别?
这是刚才所说的对各种媒介的扁平化、数字化的能力,以及对它的操作、汇聚和编织的一种能力,这个是在计算机出现之前的游戏所没有或少有的。之前的游戏庆典,你的现场要有人奏乐,比如在教堂里的壁画,一起来进行多媒介的游戏/仪式。现在可能比如很多电子游戏是用一种虚拟建模、数据的方式再造。过去的游戏比如说你小时候的游戏在地上拔根草,这些游戏过程更加贴近自然,更加和生活结合在一起。而电子游戏打开了很多可能性的同时,也会带来很多新的危险,我觉得这个过程中我觉得不存在一个根本性断裂,而是对于旧有游戏的一种赋能(empower)吧,用互联网黑话说的话。
Q6
通过您刚刚的论述,我会更愿意把这种由电子游戏带来的解放、新的创作,归结于计算机的能力而非游戏本身,您认可我这个说法吗?假如说电子游戏真的能够相较于之前传统的游戏做出某种新的解放的话,这种新的解放或者说这种新的创造实际上是由数字化和计算机带来的是吗?
A6
电子游戏的翻译就是computer game,它本身也包含计算机(笑)。
但我觉得这两个主体其实没有什么区分,你在计算机设备上面玩一个游戏,你说这个体验到底是计算机带来的还是游戏带来的?这其实是在计算机基础上用创作者的方式去使用它带来的。当然电子游戏或许能够成为在计算机的世界中的一种解放的可能,或者说是它是计算机的新的应用和使用的,一种耗费的可能性。电子游戏可能能够不同于以前用机器学习的人工智能算法去操作、判断你的喜好、约束你的目标、重复推送类似的东西,电子游戏可以摆脱这种传统的计算机的目的性而去追求一些其他的可能。计算机的世界对设计师来说一方面是助力和基础,但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敌手。
其实如果你真要说这种新的创造是数字化和计算机带来的,我觉得也没什么问题。拉图尔觉得过去这些很多的大词,这种文化、科技,都可以把它拆解为成一种绘图技术带来的一种转变(Bruno Latour 视觉化与认知:把事物画在一起 Visualisation and Cognition (1986))。从这个视角上来说,绘图技术的发明以及它所引起的这种汇聚,它就是推动整个科学和人类往前发展很重要的点。所以我觉得当然可以说计算机它就是特别重要,而确实它可能是20世纪或21世纪最重要的发明。
你可以说整个计算机文化中有一种解放的文化,它就是电子游戏。但没有必要把电子游戏放到计算机的前面和比它更高的位置,去正名、去合法化。我们希望的是正面,而不是把别人统治或者超越。越显得自大,越显得心虚。
Q7
下一个问题,您认为使一款电子游戏成为电子游戏本身,它的必要条件是什么?让它具有和其他文化形式相区别开来的独特地方是什么?
A7
我之前说的Uniqueness独特性的思维陷阱吧。可能你觉得顺着这条路这个问题追讨下去可能会有所得,但是它并不可以给我们带来更多的理解。比如说沉浸式戏剧、游戏戏剧和游戏的区别在哪里?
Q8
我无法进行区别,所以说我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让它称之为电子游戏,而另外一个只能叫做沉浸式的或者互动式的系统。
A8
概念是后验的。用一个语言去描述一个东西,说它是电子游戏,说它不是电子游戏,这本身就是语言或概念本身在起作用。但我就是要去找到这种概念的区分失效(broken)的地方,只有在感受到它们之间,以及电子游戏和其他媒介、概念之间的连续性之后,才能在这点上面做出更多的连接、证明和创作。
比如说我做的游戏《写首诗吧》,你怎么去判断它到底是一个写诗软件还是一个游戏?就算你说区分了,虽然它全部都是由诗人写的,它也不是诗了,因为有电子游戏的交互性,那你怎么解释说乌力波,这个文学团体他们做的《百万亿首诗》?如果采用纯粹的交互论,那看书也不要翻书了,得自动翻书。但你就会开始纠结假如真的有个自动翻书,我是不是眼睛不用动就让屏幕自己滚,屏幕自己滚有没有一种操作性在里面,你的脑子会不会在里面去探索(交互)?
当玩家的行为能够带来他面前的事物的某种改变、涌现或创生,那这个过程就可能是(或可以是)一种游戏。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翻书也是一种游戏。如果你能转换这种方式去看,那你就能看到像超文本、galgame之中就有很多游戏和小说之间的共性,并且能看到很多边界中的事物。如果你要说电子游戏引入了交互性,而过去媒介都没有,那你就看不到它们的结合点,只能把它们两个分得远远的。
其实每个人在谈论游戏这个大概念的时候,大家脑海中的那个游戏都不太一样。比如我想问问你,你现在说这句话的时,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游戏?
Q9
我想的也有很多,比如说《只狼》,比如说《史丹利的寓言》,比如说我昨天晚上正在玩的《太吾绘卷》。我觉得使它们成为电子游戏的必要条件,我觉得可能是可玩性,也许是某种交互性,但这种交互一定也是会出于某种目的去进行的。如果是创作者的话,可能是某种娱乐的目的,或者是传达情感的、出于审美情感的目的;如果是游玩玩家的话,就是消遣享受的目的。
A9
我想聊聊的是作为游戏作品内在的目的,比如《模拟人生》没有什么目的,这个游戏,你其实可以看作你在玩了消遣,但也可以看作是在做一种社会学的建模研究实验,将它可以看作是一种对于社会抽象和重建的方式,以此去做某种研究,它也有这样的潜力,我们可以尝试这样去看它。比如说你想到的《只狼》,那它和过去的击剑活动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它们都可能都涉及到是一种对新的身体的掌握。这种动作游戏其实和毛笔也很像,我会把写毛笔看作是一种和动作游戏非常类似的一种体验,我因此做了一个游戏,验证了我的想法。
大部分人是通过自己的游戏经验建构起对游戏的认知的。每当我们去思考游戏整体的时候,我们脑中往往会出现某个游戏,然后就会忽略掉很多其他的你不熟悉的游戏,甚至是还未被制作出来的游戏的可能(作为制作者创作的思考)。比如说大部分人想到影像和游戏的结合,那大部分人就是想到《底特律变人》,但比如我昨天发的文章 Tracy Fullerton 的访谈(Tracy Fullerton 访谈 | 何为独立,何为实验)之中,她所制作的就不是一种改变电影剧情分支的游戏,而是一种行走和影像结合的新形态。而《Her Story》也很经典,它对影像有操作。
所以我觉得思考方式是这样的,你要把游戏去和这些媒介的创作者的创作去类比,这个事情其实在《写首诗吧》里面最明显,这里面玩家角色更像是一个诗人,或许可以去思考电子游戏玩家和导演、或者是写剧本者的类似性而非产物的表面不同。最近有一个游戏,也是IGF拿过不少奖的,叫《Storyteller》,它就是用一种结构化的方式去构造故事,他会给你一个故事的结局,然后给你一些基本的这种元素,然后你要去尝试如何组合,而让它能达到这个故事的结尾,当然,你也通过组合这些元素去解锁、探索出其他的结局,它其实更像是一种剧本的创作而不是消费。
poiēsis 它本身就是创造的意思,它就是技术和艺术的最早的来源、最先的本质。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那篇文章里面有谈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游戏其实更接近于制作。《Her Story》这个游戏,梦霏老师谈得蛮有趣的,将其看作历史学者的一个技艺,在这里面玩家就像一个历史学家一样,去尝试处理这些材料,去伪存真,尝试找出真相。
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你也可以把《太吾绘卷》看作是一种武侠小说的辅助创作软件。你是借着这个引擎你去写出自己的故事,去创造出自己的体。这可能揭露出来一个重要的观点:所有的媒介,无论是电影还是什么,它都有一层在读者这边的一个重新再创作一个过程,就你需要把它和你头脑中的符号系统去做结合,需要一个创作的思路去理解这些事情。这个也是艾柯(Umberto Eco)在他的哈佛演讲《悠游小说林》说的,读者就是一个玩游戏的人,他要去追随的作者这个线索去在里面去探索,行入一片密林,在里面理解这个游戏/文本它的一个结构,重新去以这种方式去进一步地阅读它。因为你理解的越多,你能看到东西就越多。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视角,我觉得要一下子去扭转还是挺难的,但是这确实是我过去直到现在慢慢在尝试地以一种比较少有,和比较特别的一种方式重新看待游戏的尝试,并且这一种概念本身,也确实是有生产性的,且能揭示和捕捉到某些游戏的晦暗的,所以在发明概念的这个意义上,我觉得确实是在做一种游戏哲学的思考,而它也确实可以带来一种新的对游戏的认知和对它的可能性的创作。
我们当前在NExT Studios的「Gameplus 游戏+」也在找清华和中传的学校学生在一起做一个工作坊,想看能不能去以这种界面式的思路去做出更多的这类游戏。我也希望你们哲学系的学生能投入到其思考之中,共同推进对游戏的探索和创作。
Q10
我还是想去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刚刚的那种解读下,您好像倾向于对电子游戏的本体论做一个取消,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因为你不会去承认什么东西叫做有一个本体论意义上的电子游戏,而你会更倾向于把电子游戏理解为其他事物的某种生存方式,或者说某种新的呈现方式,是这个意思吗?
A10
我觉得某种意义上可以这样说吧,但是它并不是一种对本体论取消。它也是一种本体论,或者说看你怎么在什么意义上使用本体论。如果比较宽泛地理解本体论的话,就是说这东西它到底是什么?我当然是在努力的尝试去解释,包括以写作的方式去解释它到底是什么。但我回答的方式,可能不是一种对象化的思维,不是一种你要把它和其他的事情分开来的这样一种思维。
我觉得随便一个玩过一点的游戏人,他都可以说「游戏和其他事物有某种本质的区分,就是在于它的互动性,它把之前所有的媒介都结合了」这样的话,我觉得这种这套说法是很普遍认知的,或者说已经很普遍的。并且我们期待这个视角还能说出点,或做出点什么新东西,但它可能并没有,所以我希望能够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切入这个问题,而不是取消。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到底一个事物要如何才能得到承认?所谓完成「正名」?游戏研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到底需不需要一个独立一个学科?所有的人都并不是专门研究游戏,然后他们去接触游戏的时候,就会带有自己学科的一个视角和思路。游戏极度需要一个跨学科的研究,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是要创造出一个游戏学、培养游戏学的专家,还是说游戏学应该成为一种同时存在于所有学科内的一种存在,其肉身应该分散在所有的学科之中?哪种做法能更好地使游戏走出目前不被理解不被接受的困境?
对于我来说,我倾向于放下游戏的骄傲姿态,倾向于后者。因为我觉得当你把自身取消的时候,你才是真正的无处不在。在媒介混杂的世界里面,没有那种很规整的媒介,就是所谓那种第八艺术、第九艺术的叙事。在这个短视频,公众号,各种混杂的后媒介时代,如果游戏人还在做一种非常现代主义的这种思路,以这种方式思路去进入的话,它实际上是不太符合时代的。说每个艺术形式都有一个这种非常核心的本质的一个东西,这套思维其实就是现代主义的思维,是要被反思的,或要被拷问的。
Q11
在您的讨论语境里,艺术是什么?在您的话语体系里面,请您给艺术下一个定义。
A11
理论上来说艺术就是游戏,或者某种意义上来说,伽达默尔的话说,游戏就是艺术的存在方式或者艺术的运作方式。
Q12
您刚刚说的的艺术是一种比喻性的用法,它是某种价值判断。您认为,我说它是艺术的,说明它是优秀的、好的、美的,还是说它其实是某种本体论意义上的承诺、具有类的本质?您认为艺术是哪一种?
A12
不谈概念的话,情感上我比较接近说,比如它向你揭示了什么,或者向你披露了什么,它可能就像一个座驾,能够把你带到这一种审美状态、一个世界中,它能揭示出一些世界中存在的事物,或者揭示出某种所谓的真理。
Jonathan Blow 他谈游戏设计的真如时(Jonathan Blow 游戏设计的真如 Truth in Game Design (2011)),说所有游戏的底层都有一种世界的慷慨或者世界的神秘在里面,在这个意义上它就是一种揭示。它不是一个纯主观或是一个纯客观的东西,这种主客二分的观点还是很古典的思路。在梅洛·庞蒂视角下面没有什么所谓的这种完全的区分,你拍个东西你就是在去触摸它,去感知它。比如说你看到一个橘子它是酸的,是因为你有长舌头,所以它是酸的,酸可以成为它本身的一个性质,你对事物的感知和你的身体触觉是紧密相连的。
Q13
刚刚您在论述的时候,我记得有说过,玩家他其实是在扮演某种角色,比如说《太吾绘卷》作为武侠小说生成器,我是作者对不对?其实我可以把它理解成玩家在其中是享有相当的自由的吗?直观上来说,我会觉得游戏玩家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的,因为作者他会给你一个平台,然后你在那个平台里可以去发挥你的想象力,或者说发挥你的创造力。
A13
我想问你个问题,你觉得你玩游戏更自由,还是你看一本书更自由?因为比如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你是可以随便翻的。
Q14
我觉得同样自由。自由在于这本书最后呈现在我面前的方式,比如说游戏最终呈现给我的样态,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我决定的。但书的呈现样态我最多只能把它倒过,或者撕掉,但是这些撕掉和倒过来看是没有意义的,但是游戏的最终的呈现样态是有意义的,是有秩序,就是它不管怎么生成,不管怎么去塑造它,最后呈现出来的是可理解,所以你可以用审美情感去把握它,但是书或电影它就没办法。
A14
这个问题我和厌氧菌有彻底的讨论(E32 赛博文本中的幽灵作者)包括对创作者、阅读者的讨论,包括他对自由还是不自由的一个模糊性的讨论。我不喜欢从自由角度去谈,我觉得谈论自由会给人一种游戏是元宇宙的那种错觉,以及控制反控制的这个我觉得不是很有效的问题。
之前和善超聊的时候我们有聊到这个问题(E30 电子游戏作为快感治理术),他说我们应该用承认去替换所谓游戏中的能动性的自由概念。我们说玩家在游戏里有一种能动性的时候,并不一定说他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对游戏中的自由如果有一种泛滥的定义的话,就好像说你在一个剧场里,比如你去看剧对吧?台上台上在演奏音乐会,你在座位上跳起来大叫跳舞,你觉得这是可能的吗?我觉得你在游戏中去追求所谓的极致的自由,就在做类似这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自由这种思考方式,包括游戏自由、游戏内自由意志的讨论,这种思考方式它会导致你可以在任何艺术作品里问自己,你是不是自由的?我觉得自由这个因素它并不构成对作品审美的某种要点,或者是这种自由是在都要脱离艺术作品的一个视角里面去讨论,比如说你能不能看电影的时候去上厕所,这种自由你有没有?很多我觉得对游戏的自由,我觉得是在讨论这种东西。比如说我能不能在这个NPC说话的时候打他一拳?说我能不能NPC说话的时候,我跳到桌子上面(跳桌效应)?
其实它本质上是在说这样的事:我们玩家的这种输入,它能够带来输出的一种改变。比如在一个步行模拟器里,玩家肯定是所谓自由的,他有这种操作能力,就是能够他的某种方式能够去改变图像的生成,图像的涌现。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已经确定了说游戏中有个人,这个人他可以做a做b做c,从这个意义上去讨论自由,他已经是在一个很文化性、很高层的、很符号性的角度去讨论这种自由。我觉得这不够深入,不够有力量,也只能带来一些泛泛的讨论。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游戏都不是自由,所有艺术作品也都不是自由的。对于艺术作品,它是希望最后让你达到的可能是思想层面的一种新的可能性的自由和发现,但是你这个过程你得通过一个受限的审美过程对吧?你得去接受这套新的身体。
比如说平台游戏《蔚蓝》中的自由,你能够操作得很好,你能跳到你想要去的地方,但这个时候你的身体是完完全全被这套新的操作模式所规训的,这个意义上你又是不自由的,所以说到底讨论是哪一种自由,我觉得得搞清楚。
Q15
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成是审美状态上的零状态。就是说在审美发生的时候,你是不会考虑整个过程,都是你想象力、知性、概念的自由运作,当然这个是从美学的角度说的。
A15
就是像踢足球的人,他的足球掌握已经非常好,神乎其神,好像在踢一个艺术一样,他就非常自由,审美自由就是身体和周遭事物和游戏中的这种要素,它能形成一种统一的,自然而然地,非常自在自如的一个状态(flow,或 in the zone)。但是这个意义上的自由不是那种我想把球踢出去的自由是吧?所以你要区分你思考的自由是哪一种。
Q16
刚刚其实聊了很多关于游戏的定义、游戏艺术性的问题,接下来我想问的是关于游戏污名化的问题,就是您认为电子游戏存在危害性吗?如果有的话可能是哪些危害性?
A16
有危害性。斯蒂格勒说所有的新媒介既是毒药又是解药,我觉得现在的游戏可能某种意义上毒药的部分可能盖过了解药的部分吧。游戏有一种非常强的使人短路的可能性,它能够直接以一种新的逻辑去重新构造你的知觉方式,去构造你的对世界的认知,本身就它以非常物质性的方式将世界呈现在你面前,它恰恰不是虚幻,因为它直接把这个世界显示出来了。不是告诉你说我们人有马斯洛需求理论,12345,而是直接把这个需求所形成的世界的运行方式放在你面前(《模拟人生》)。
而当你觉得无聊的时候,你前面有个如此之切近如此直接的一种获取反馈的方式,你就会倾向于去使用它,而不是沉下去来去探索更多其他的东西。还有,很多游戏它的目的因太强了,它让你追求的是一个游戏内的一个目标。比如说你去看高尔夫球,你把球打进洞里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游戏的目标(Bernard Suits 前游戏目标),实际上是让你出来贴近自然,打进洞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目标。但很多游戏里它就好像成了最终的目标,你要搜集到所有的东西,你要去打倒最后的boss。
Q17
但是打倒boss这个过程当中,你去收集游戏里的东西也好,或者说你给自己的学秘籍、给秘籍加点也好,你学会各种各样的技能也好,这个东西它是一个持续的给你乐趣的过程。
A17
但是它和里面这种数值化的变动其实关系不大,如果你着重于这种数字化的变动(比如你看到你的等级从一级升级到十级),那这变化本身可能并没有比如《只狼》里面的真正乐趣。重点在于你怎么去掌握新的技巧,怎么去观察到新的场景,并且发现新的地方,发现到新的物品,这是探索的乐趣,不是说你获得升级成长的这部分乐趣。当然为什么现在有些人就喜欢这些东西,因为就是资本主义逻辑,大家就觉得我希望有增长,我希望看着自己的钱向上增加,你会发现有纯放置游戏,纯增长,你在游戏里面从头到尾没有任何思维技巧、没有任何的变化,你的心灵就是一个僵死并且高速获取反馈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所以说在这里面很难说清楚,因为游戏它有一些引导的部分在,《马里奥》或老任的游戏有大量的金币,但它是想让你去可以享受探索,它的方法就是在探索里面加奖励,你就会不自主地受到引导去探索它;但是你又要认清楚,这些奖励在某种意义上其实是无所谓的。这些奖励的重点,是让你鼓励,让你愿意去发现和探索,保持对这个世界充满好奇的状态,奖励只是一种引导。
比如说我最近在玩 Tracy 的《瓦尔登湖(Walden, A Game)》,没有什么奖励,比如说你在一个树林里面,你用放大镜去看一棵树,它会冒出这个树的介绍说这个是什么树,没有给我积分,但它一样可以的,因为它本身有一种内在性的奖励。比如《The Witness》它自己也没有奖励,也没有积分,只有两个成就,一切都是基于对世界的好奇,所以我觉得最纯粹的,或者说,不叫纯粹吧,这个是一个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你觉得玩家动力不够,那你可以再去加点奖励,可能会让他更积极一些。所以商业等于是把这个过程给倒置了,它没有前面的部分,就只有后面的奖励部分,走到极端就是放置类游戏。
Q18
你觉得像刚刚那些危害性是电子游戏的原罪吗?是这种文化形式所固有而且不可剔除的吗?有没有可能存在一种完全没有任何危害性的游戏?
A18
可以的,一个很无聊的游戏就没有什么危害。但我觉得这个不是这个重点,比如说一个原始人他从来没看过电视,他第一天看到电视的时候,他就觉得这电视也太好看了,然后一直在看电视,可能……可能就沉迷饿死了。电子游戏的生产,这里面肯定是一个很复杂的事情,因为你的生产、资本和技术需要运作,市场需要运作,我们毫无疑问也需要这种「罪恶快感(guilty pleasure)」对吧,比如马桶时间,我们也会有希望放松一点,不去想有的没的的时候。
和这个比起来,可能怎么样提高人对于游戏的认知才是关键。你要去让人们看到现有存在的,以及有待制作出来的(潜在的)电子游戏的多样性,就好像电影并不因为它自己是运动-影像的媒介而成为艺术,而是比如像亨利·詹金斯(Henry Jenkins)说的,要到1915年格里菲斯制作了《一个国家的诞生》之后,电影中有一些特别烂的好莱坞大片,也有齐泽克的电影,也有新浪潮什么的,我现在策略是认清这种多样性。比如说我现在做的这种游戏,无论《写首诗吧》还是《时间的形状》,其实它们都是那种可能吸引游戏圈外的人会多于游戏圈内的人。因为它们就比较特别,也拓宽了大家对游戏的一种想象。这是去魅的第一点。
此外,重要是你要认识到游戏背后有个设计师在和你对话,这个也是我在做游戏作者系列的原因,如果你能认识到电子游戏背后是有个设计者的,他想用游戏跟你说点什么,他想和你在游戏里有怎么样的交流的话,这能帮助游戏的去魅和去妖魔化。比如说我最近在和一个港中文的文化研究的博士做一篇文章,标题是《现在就要针对你:虐待性游戏设计 On Abusive Game Design (2010)》,有点标题党,但它的点就在于用一种虐待性的方式,让你感受到你是在和游戏设计师在一种交流之中,而不是说设计师做系统就是为了服务你的欲望。这个思路其实就是每个游戏背后都有作者,你要怎么去看到作者。我觉得这个是去魅的第二点。
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你让大家来自己做游戏。做游戏能够成为一个平民化的过程,比如我会带一些小孩子做,然后会介绍和翻译做一些低门槛,低程序要求的那种东西。当你开始做游戏的时候,你就能有一个新的思路去构想游戏的可能,因为你自己做的游戏肯定不是要把别人怎么样,要怎么去操纵和控制,你可能是做游戏送给朋友,送给家人。哪怕体验一下这个感觉,这自然而然会改变你对游戏可能的认知。
Q19
总结您刚刚的发言,电子游戏其实是存在被妖魔化或者说被污名化的现象,我们去帮助它摆脱这种现象的方法就是,一个是让大家认识到电子游戏也是有很多种的,第二个是让大家认识到其实它是一个和创作者对话的过程,第三个就是说能够改善好环境,让大家都能来做点游戏试一试。我可以这么总结吗?
A19
可以,但我觉得它本质上怎么让这个东西能够和更多的事物有接触和连接,而不是说把自己正名得很好的了,很自洽了,然后照旧如此地这样发展下去。
Q20
您一直以来制作游戏的理念是什么影响?您想通过电子游戏实现什么?
A20
我想知道电子游戏是什么。做游戏是我回答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我现在自己回顾定位下来,感觉自己不是那种纯粹的游戏制作者,而总是带着这种问题去不断想的。
我在有些访谈里有谈,我觉得自己比较像押井守,他也是说他不太喜欢电影,他不热爱电影,但是他好奇电影是什么,我觉得有点像这个吧。我会想得也会很多,做的时间反而会少一点。虽然都是自己做的,虽然我也对一些具体的技术会感兴趣,但是我觉得对我来说是一种本体论的困惑可能更多吧,可能是因为当时是在一个人文的环境,包括院系里面在做这种探索的缘故。我前面跟你说的,我前面说的那三种方向,其实不只是我对它建议,它就是落日间现在在做的事情。
Q21
其实我看您给落日间的定义,它是某种媒体实验室,我想知道您实验的东西是哪些?实验的方向有哪些?
A21
落日间的一个使命,我觉得它主要在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各种各样的界面,这个界面它可以是游戏和文学的、游戏和历史的、游戏和什么任何的……我需要把游戏制作者、游戏研究者,特别是一些学院派,游戏玩家,我要把他们对这个东西的思考都调动,展示在一个界面上,那个界面就是落日间。在这里面我希望有一种去魅的语言能够很深入地去讨论这个东西,不管你是个创作者,还是一个研究者。首先它没有那种高傲的姿态吧,没有说玩家比什么高级,什么比什么更高级,能够推进对这个东西的思考,能够听到创作者的声音。
比如最近游戏和戏剧,我们和一些在做游戏剧场的人去讨论他们怎么看这个游戏,还有比如说线上戏剧,它和过去的一些有游戏剧场或者一些VR游戏,剧本杀游戏或者什么海盗多人游戏这种它有什么关系或它还能怎么做?我希望有一种这样的一个相互碰撞和激发,并且还能创作的一个过程。
我刚才说自己也在带学生,这其实也是我在NExT Studios这边在做的界面式的游戏研究创作方法,可能我会要求学生去找到自己的课题研究,做一点相关的翻译,然后再展开这种界面上的创作。比如有朋友在做历史游戏,我就说你得去找一下历史学家,他们会怎么去对这个东西有思考,做点翻译,在这基础上你再去做你的游戏,同时也看到过去这类游戏的局限性,然后再去看能不能推进这样的更多跨界的讨论等等。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模式,我后面会专门写文章聊这个。
Q22
好,最后一个问题,您能不能推荐几款游戏给我们?什么类型的都可以。
A22
讲真的这种推荐操作都挺难的。我上次刚和姜宇辉老师又聊了一期播客,回答了类似的问题,我推荐的是一个叫做Bitsy的网页端的一个游戏创作的工具,你能在半小时内做一个RPG的游戏,它粉丝做的教程我也翻译出来了,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试试。(Claire Morwood 给所有人的 Bitsy 游戏制作教程 A Bitsy Tutorial (2017))
-
访谈对象:落日间(叶梓涛)
访谈人员:李好,吴颖彬,周淑怡,叶子琦
时间:2022年11月17日
地点:线上 腾讯会议
-
落日间是一座有关「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迷宫
感谢支持落日间的朋友们
欢迎赞赏或在爱发电赞助落日间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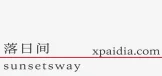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7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