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克拉科夫十一月末的日光像过期黄油般黏稠。我抚摸着作协徽章凸起的纹路,对着橱窗整理领结,玻璃倒映出某种诡异的场景:我的影子在阳光下拖长变形,仿佛有无数只手在撕扯脚踝。
这大概就是被寄予厚望的眩晕感,我安慰自己。毕竟,此刻我的包里装着《波兰文学》主编的推荐信。
作协总部设在圣十字教堂斜对面的灰色建筑里,青铜的门把手带着一股铁锈味。门卫用放大镜核对我证件时,镜片折射出沼泽般的绿光。
“你应该把袖扣换成银质的。”
直到晚宴开始前,我还在琢磨这句话。
三周前,我收到了镶着金边的通知书,要求我携带不少于三磅的原创手稿参加入会晚宴。我把自己反锁在阁楼,当第十二个墨带寿终正寝时,《雪与混凝土的十二夜》诞生了,这是一部讲述建筑工人在赫鲁晓夫楼里寻找诗意的实验小说。
晚宴上,二十四位会员代表围坐在长条石桌两侧,烛光将他们的影子投射在画着耶稣受难像的墙上,扭曲成蝙蝠形状。作协主席雅采克·格但斯基的胡须像两把倒悬的镰刀,“欢迎加入波兰文学的心脏,”他切开淋着黑醋栗酱的鞑靼牛排,“让我们开始品鉴。”
我的书稿被装进托盘里顺时针传递。
诗人安娜·诺瓦克用发簪戳起第三章:“这段描写水泥搅拌机的文字……‘灰色脑浆在铁颅中沸腾’,可否借我润色新作?”她说话时总是不经意露出两颗尖利的虎牙。还没等我回答,她手指划过的句子立刻渗出了猩红色的汁液。
戏剧家雅库布·斯塔赫直接撕下四十二页。“地下室独白正好填满我的新剧第三幕空缺,”他咀嚼着生牛肉含糊地说,“反正你在人物塑造方面欠缺火候。”
“这句‘像被剥去鳞片的鲱鱼在维斯瓦河底仰望星空’归我了。”文学评论家安德烈·沃伊切赫掏出一把镀金裁纸刀,将我最得意的句子从手稿里剜出来,像摘取牡蛎肉般滑进了西装内袋。“作为交换,我可以让你在读者来信栏发一百字感言。”
“借个隐喻”“分个倒装句”,他们的呼吸喷出校对红墨水的腥甜,瓜分台词的速度比集体农庄收割甜菜还快。我的角色们被拆解成零散的感叹词,主角的遗言变成了诗人联合会副主席的新书腰封。
晚宴过后,我抱着仅剩的扉页缩在门厅。雅采克递来白兰地。“这是入会必要的牺牲,”他揽着我的肩膀,袖口散发防腐剂与檀香木的气息,“你应该感到荣幸。”我注意到他领口别着枚暗红色领针,形状像极了凝固的血滴。
加入作协后的第一年,七封退稿信乘着乌鸦抵达。主编在便签上写道:“内容与诺瓦克女士获奖诗集相似度过高,建议多读读当代经典。”翻开那本烫金封面的《水泥与十四行诗》,我那个被剽窃的比喻正躺在铅字中央冲我狞笑。
斯塔赫的《混凝土奏鸣曲》在国立剧院首演时,我蜷缩在二楼包厢啃指甲,当男主角念出被我反复打磨四十二稿的台词“我们都是被预制板压扁的俄耳甫斯”,前排观众开始擦拭眼泪。掌声中剧作家转身朝我的方向举杯致意,水晶吊灯把他的牙齿映得雪亮。
两年后,我的名字终于出现在某期《新浪潮》杂志角落——在沃伊切赫的评论文章脚注里,作为"某些未成熟作者的典型错误范例"被引用。
当我颤抖着向文学伦理委员会控诉时,主席台后的七位元老正用银质牙签剔着什么东西。他们的影子在孔雀石吊灯下交错,仿佛某种有翼生物在啃噬光晕。最年长的卢卡什·谢尔基维奇突然打了个饱嗝,空气里顿时弥漫着墨水味。
“年轻人,”他的金丝眼镜滑到鹰钩鼻尖,“文学本就是集体创作。”
作为补偿,他们特许我在下期杂志刊登一首四行诗。
等到我的剧本《铅灰色黎明》被拆解成十二部获奖独幕剧时,我终于学会在句子里掺入玻璃碴——但评审团的消化系统显然进化得更快,他们甚至能分泌溶解隐喻的胃酸。
十年后的某个雪夜,我终于悟出那场仪式的真谛。当我将撕碎的新作扔进壁炉时,火舌突然吐出了《雪与混凝土的十二夜》的残页。焦黑纸片上,被掠夺的句子正像蛆虫般蠕动重生。
我立即拨通了殡仪馆电话,订购了一副柏木棺材,预约牙医将犬齿打磨成14K金,在跳蚤市场拍下了据说是某位特兰西瓦尼亚贵族用过的打字机。
如今,我的等身铜像矗立在作协中庭。当暮色染红维斯瓦河,我会站在灰色大厦顶层的落地窗前,数着楼下那些攥着申请书的身影。他们的影子被路灯拉长又缩短,像一行行被反复删改的蹩脚诗句。
I

OrioTysumi
534 人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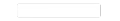
故事烩
9232 人关注




评论区
共 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