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初看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会感觉生涩难懂,大量陌生化的名词、片段化的叙事、完全未知的陌生世界等等因素都让刚接触的读者手足无措,甚至直接劝退,然后纳闷为啥威廉·吉布森写的书读起来是这种感觉?
那么今天就简单说说,威廉·吉布森为什么要这么写。
威廉·吉布森的赛博朋克小说,有着极具特色的叙述节奏和叙述结构。在叙述节奏上,正如矩阵空间里对于数据的处理和数据蔓生的描述一般,小说中总是充满了危机后的结构与规律,以及稳定后的危机四伏和无法控制的蔓生。事实上,成型与散漫在某种程度上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相辅相成的现象。威廉·吉布森也是利用了这一点,在叙述结构上充分加以利用,使得小说充满了重叠感:一方面,小说文本结构中有线性的叙述,也有非线性的叙述;另一方面,小说的结构也充满了隐喻象征,使得小说文本也和科幻世界的人体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威廉·吉布森的小说有着分散性的叙述线索,碎片式的情节在三部小说中比比皆是。它们之间的联系断断续续,有迹可循又纷繁复杂,仿若科幻世界里那复杂多变的情节一样,慢慢构建起小说的整体结构。
通常,威廉·吉布森擅长迟缓相间的叙述节奏,即一方面故意拖延交代事件的内部关系,另一方面又在内部关系的关键点暴露之后,就立即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
《神经漫游者》中在“冬寂”出现之前,读者感受到的只是凯斯、莫莉和阿米蒂奇之间不甚清晰的关系网络。等到“冬寂”出现之后,一切便真相大白,吉卜森也让特希尔-阿西普尔家族的秘密展现在读者面前,而剩下的就是主人公如何去应对这一切的危险了。主人公们的命运如同蔓生性的赛博空间,充满了太多的不确定性。
《零伯爵》以人物为主线将小说分成了几条线,譬如被身为生物医学专家的父亲在大脑中植入生物软件的安吉拉;寻找安吉拉的年轻狂妄电脑牛仔波比;受维瑞克指使的画廊女老板玛丽等等。吉卜森将这些充满不确定性的情节一一摆放出来,并在叙述中不断地以碎片式的变化来进行,使整部小说充满了悬疑,等到接近真相的时候,才告诉你安吉拉是这部小说的关键点。
《重启蒙娜丽莎》虽然延续了波比和安吉拉的故事,却在小说一开始就让一切都回到起点,曾在《神经漫游者》中出现的三简女士和莫莉(萨莉)再次登场,一切似乎又将暂时稳定的局势重新洗牌,开始新的裂变。等到蒙娜丽莎取代安吉拉的时候,一切豁然开朗,赛博空间则依旧充满神秘。
威廉·吉布森分散性的叙述结构和松弛相间的叙述节奏使得小说并不像传统小说那样有着万能叙述者的引导。对于读者来说,一切只有文中提供的线索,读者参与到这些线索的寻找中,有时也会产生错误的假定或过于匆忙的结论。
值得指出的是,威廉·吉布森不仅在整体结构上有着碎片式的组合,在每一个人物与事件的叙述上,也充满了困惑与分裂,这与他对人类记忆、肉身与科技的结合以及历史的构成等方面不确定性的叙述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中,他不断表明人类记忆既不是坚不可摧的,也不是可靠的,人类的记忆可以被电脑控制修改,就像《神经漫游者》中“冬寂”进入凯斯的记忆一样,将其中一些资料进行重组。因此,人类的记忆和对记忆的储存不再是确定无疑的事情,而是充满了疑惑和断裂的结合体而已。这种记忆的危险状况使得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怀疑,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和周边事件的叙述也充满了不确定性。
赛博朋克一直强调高科技对个人记忆的不断侵犯,威廉·吉布森更是不断在作品中暗示对过去的闪避。在赛博朋克中,过去是不可恢复的,即使它能渗透到现在或者将来,它仍然是不可能完整复原的。
威廉·吉布森的小说结尾没有将终极秘密公布于众,或者也可以说,他的小说根本不可能揭示终极秘密,人类对过去的记忆和在此基础上对未来的展望总是有着断裂的碎片。即使在小说末尾,暂时的危机过去了,读者还是对未来抱有怀疑和不确定的感觉,一切真的结束了吗?
《神经漫游者》中凯斯和莫莉没有任何理由地分手了;《零伯爵》中安吉拉和波比最终所处的田园地带总是给人不会长久的感觉;玛丽一直寻找的艺术性盒子,装满了毫无关联但引人回忆的东西,只可惜,这些和过去相关的东西,无法复原一个完整的过去;《重启蒙娜丽莎》也是以主人公进入无边无际的矩阵空间结尾,更加给人不确定的感觉。记忆对于威廉·吉布森笔下的人物来说,是始终围绕着自己挥之不去的,却又无法明晰的一切。
记忆的不确定性和威廉·吉布森对于人类肉身和科技之间的结合想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英澳双籍的社会学家布莱恩·特纳(Bryan Turner)认为人类的肉身有着“诡异、隐喻性和存在某些遥不可及的东西”,在威廉·吉布森的小说中,这种感觉可以从高科技对肉身的改造中表现出来。
人们凭借记忆和想象进行的叙述充满了各种可能性,譬如《神经漫游者》中,凯斯的叙述让人分不清过去与现在、事实与幻想,对于他的前任女友琳达的叙述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重启蒙娜丽莎》里更是强调了在电脑科技控制下人类的性状态,人类的本能受到干预,仅凭对各种故事和经历进行编辑,来满足个人的想象,其叙述也必然充满了各种随意性和突发性。
威廉·吉布森一直强调高科技下人类肉身与记忆所受到的压制,他的黑客牛仔和赛博空间的追逐者们一方面试图寻找自己往日的足迹,另一方面也无奈地接受无法找回过去的现实,徘徊在未来的迷茫中。
特希尔-阿西普尔家族利用克隆技术和基因操控保存其家族的神秘力量,作为克隆身份的三简女士,她的一切都控制在父辈血缘的迷宫当中,虽然背负着父辈的重托,却也无法确定自己的过去与未来。
威廉·吉布森对于人类记忆不确定性的强调也暗指了其对于历史的疑惑与质疑,由于人类记忆本身事实性受到质疑,历史便也成了一种备受压抑的构想。作为反映过去事件并记录和储存的历史,是建立在对个人记忆压迫和改变的基础上的,所谓官方的事实版本,其真实性仍是不确定的。在威廉·吉布森的笔下,所谓历史,就是由非真实的肉身对充斥着无生命残余的空间进行的虚构性再创造。
《零伯爵》里世界首富维瑞克派去的人用数字模式侵入生物芯片专家米歇尔的记忆时,“如同从噩梦中醒来”。这种神奇的感觉往往来自于对表面熟悉和正常的事物产生的恐惧与焦虑。米歇尔的女儿安吉拉,在感觉到自己身处不确定的环境或有潜在危险的环境时,会对自己经受过的创伤更加敏感,产生神奇的幻觉。她的记忆早在父亲对其大脑植入生物芯片的时刻,就有了特别的功能。她的记忆不再是个人的记忆,而是更多的具有神奇效果的赛博空间的轨迹,令人压抑、迷茫,又吸引着读者的模糊概念。
由此,赛博空间虽然是非物质性的感官空间,却并不因为其技术性而引人注意,反而是其展现出来的对记忆的侵蚀、对极具美学特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数据束游戏,构成了主人公对于历史的不确定性的判断,丧失了个人识别码。也正是基于个人和集体经验的神奇感,历史充满了个人心理暗示和拷问,威廉·吉布森颠覆性地夸大了传统现实主义叙述结构中避免的因素:即一切抑制的、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在赛博朋克中通过对个人记忆的改造,得到了极大地发挥。萦绕的空间、死亡的恐惧、疯狂的暗示、不祥的征兆等等或隐或现地穿梭于赛博空间当中,现在、过去、将来都交织在赛博朋克中,陷入无尽的矩阵空间。
作为赛博朋克这个科幻子类的创始人,威廉·吉布森对于同时代的其他科幻小说家影响很大。批评家拉里·麦克弗里(Larry McCaffery)曾指出,他的作品和早期革新的科幻小说家有许多契合之处:如“阿尔弗雷德·贝斯特(Alfred Bester)的早期小说、菲利普·迪克(Philip Dick)的中期小说以及塞缪尔·德兰尼(Samuel Delany)的《新星》(Nova,1968)。除此之外,吉卜森也从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和J.G.巴拉德(J.G.Ballard)那里汲取了碎片和异化影像快速涌入的特点。
同样他也从科幻小说领域之外的地方获得了灵感,如达希尔·哈米特(Dashiell Hammett)的强硬派写作,20世纪40年代的黑色电影(filmmoir),罗伯特·斯通(Robert Stone)的小说,摇滚音乐家路·瑞德(Lou Reed)作品中过于紧张和梦魇般的都市场景与节奏,以及托马斯·品钦(Thomas Pynchon)小说中繁杂的集科学、历史、流行文化、嬉皮术语和黑色幽默等等的大集合”。他所展现的赛博朋克主题理念、创作技巧和对传统科幻小说的更新都使得科幻小说作为一种文学类型,得到了又一次崭新的亮相。相比于其他的后现代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的地位更加具有开拓性,也为我们了解其他极具个性和特色的科幻小说家提供了前提和基础。
1 / 9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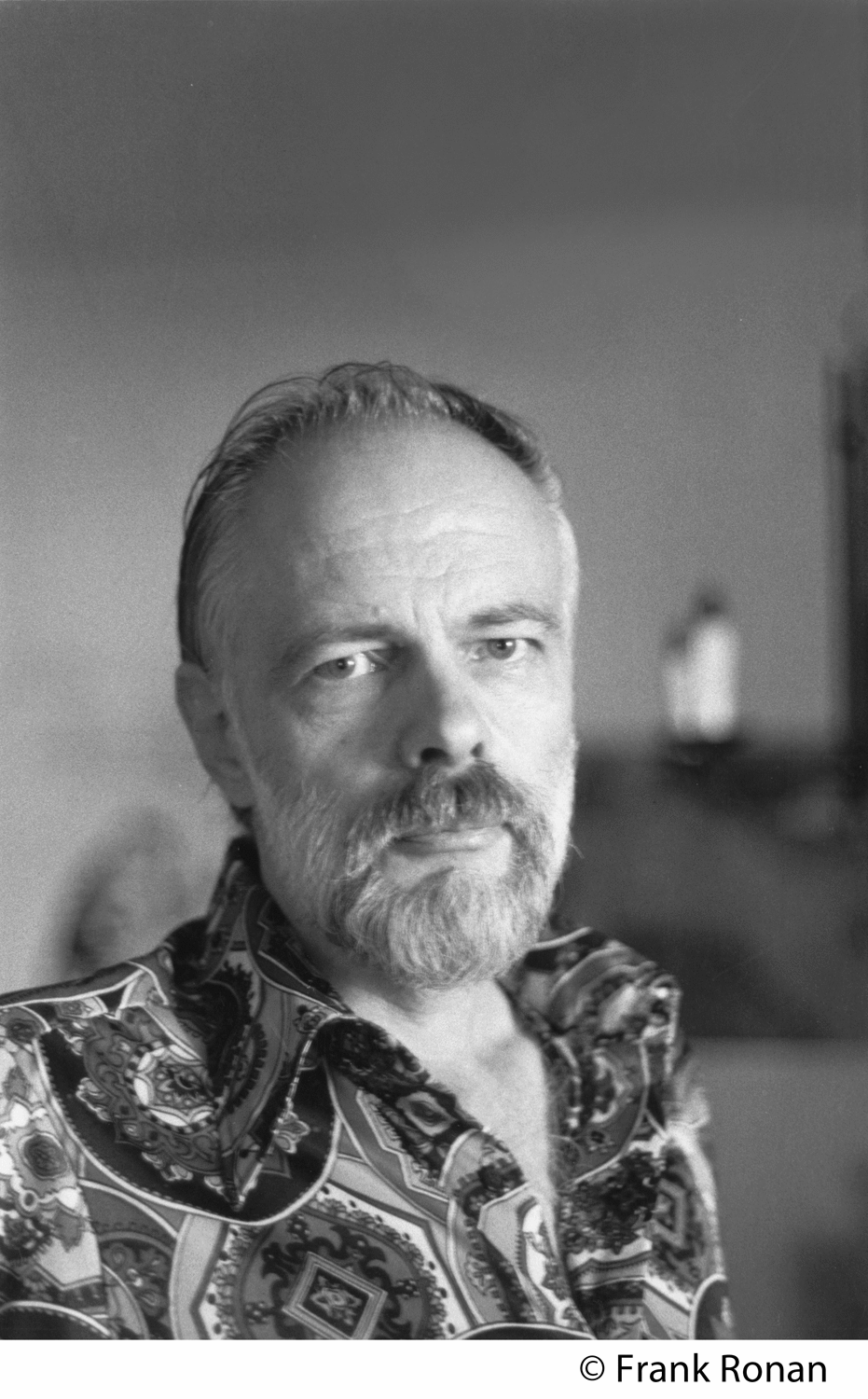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3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