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感谢果壳约稿、编辑biu,发布有较多改动、增补
Game Jam 是什么?
Game Jam 是什么?
如果将其描述为独立游戏开发社群所热衷的一项游戏开发挑战,那或许有些难以理解,毕竟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独立游戏都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但或许可以反过来,让我们用Game Jam 来进入、甚至理解独立游戏。
简单的来说,Game Jam 是限时的游戏开发挑战,通常由单人或数人组队,参与者被要求在短时间内(常常是48小时)开发一个可玩的游戏,交付后一般还会有展示、试玩、投票等环节。
从 2002 年开始,Game Jam 在社群和爱好者的推动下发展起来,如今已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今年 Global Game Jam 全球有 580 个站点,中国光是线上站点就有近 1000 位参与者,而 Ludum Dare 这个影响力最大的线上 Game Jam,至今已有 50 届,近来每届都有超过 1000 个游戏提交。
最早的 Game Jam,即第 0 届 Inide Game Jam 由 Chris Hecker 等人举办于 2002 年 3 月,14位开发者在4天之内创作了12个作品,并在实验性玩法工作坊上展示。目标是「鼓励游戏行业的实验与创新」。
如何在48 小时内制作一个作品
如何在48 小时内制作一个作品
在48小时内制作一个游戏?
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不可思议。 但或许我们可以打破两个迷思:
首先是门槛与技能,Game Jam 并非高级玩家的专属赛场。有些人看到「48 小时挑战」就会联想到黑客马拉松(Hackthon),认为那里就是大牛们炫技的地方,脑海里浮现这般画面:黑客对着电脑,倒计时滴答滴答,手指飞速敲击。
但恰恰相反,Game Jam 的很多参加者都是第一次来。
我第一次开始尝试游戏开发便是在 2016 年。那时在 Global Game Jam 上,作为一个什么都不会的策划,我和几位程序员和美术师,以及一位外国大哥一起,做了一个萨满在黑暗中寻找并鼓舞同类的游戏。
这其实是一个这样的活动:人们在一个周末,搬着自己的电脑过来,一块讨论,脑暴,各出其力,人们的目标是完成一个可以玩的小东西,并且和大伙分享,感受劳作的快感,而非竞争。
不少人会将其看作「开发大赛」,但其实 Game Jam 更恰当的形容方式是:
「一起玩」的派对,一起挑战自我,而不是「比谁更厉害」。
它不仅并非是只属于核心开发者享受开发乐趣和展现风采的场所,实际上,还可能是所有人接触游戏开发乃至深刻理解游戏最好的起点。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游戏论坛、视频平台、公司都在通过举办Game Jam 来吸引更多人,推动游戏文化,学生们也开始逐渐通过GameJam的参与锻炼自己并且成长,成为更多人进入游戏开发和设计的快车道。国外的游戏专业的学院教育也探索出了 one game weekly ,以短期制作挑战来教授游戏设计与开发的方式。
其次是关于工具。
相比十多年前,现在的游戏开发工具已经越来越「民主化」,且足够易用。彼时,限制于游戏引擎的不成熟与封闭,个人很难接触到合适的工具来进行创作。但在今天,我们可以很快地用上 Unity 或虚幻引擎等商业引擎(前者开发了《王者荣耀》,后者开发了《绝地求生》)。
而也有类似于 Godot Engine 这样更加轻量的开源引擎可以使用,也可以使用全程无需或只需少量代码的 Web引擎(Construct3,Bitsy,Twine2),在电脑浏览器上完成全部的开发与分享。甚至可以干脆在游戏内开发游戏(Roblox,Dreams Universe,Mario Maker,附带导航!一做就上手第一次的游戏程序设计等)。
限制与创造
限制与创造
Game Jam 氛围轻松,但却也有限制——往往设有题目,参赛者需要围绕这个主题创作。
题目是一场 Game Jam 的重要的启动因素。好的出题能够激发灵感,带来不同的阐释,而不同的Game Jam 场也有各自的风格:
Ludum Dare 给出的题目会先经过投票,最终定下的题目往往会比较具体且注重玩法,比如,「一个房间」(One Room)、「一个按钮」(One Button)、「生命就是货币」(Life is Currency)等。
国内的 CiGA Game Jam 则会给出具有多义性的图像,让参加者捕捉其中意涵。
比如以下这幅图:
CiGA Game Jam 出题人也很喜欢画家邱丹丹的作品,其耐人寻味的画作着实折磨了不少游戏开发者们,但如今回头看下来,反倒是蛮好的尝试,让两种艺术之间发生了共鸣。
题目这其实是一种自我设限,是一种能激发创造力的方式,在框架内或者命题限制下常常能比日常任意的情况中创造出更好的内容。
这点上让我想到古代诗词中的格律,以及法国文学组织OULIPO的实验写作方式。以及就像是即便是爵士乐的即兴,也会有 Fake Book 提供和弦的基底,限制划定的空间能更好地产生创造。
而这也与电子游戏作为一个技术媒体固有的「技术限制」的传统精神相吻合,毕竟电子游戏发轫之时,开发者们便是与16*16像素的像素画和动画,64K的卡带容量的斗智斗勇之中发展而来的。
而「限时」似乎也是创作者共通的一种实践,诸如编程马拉松 Hackathon,小说写作月National Novel Writing Month,每日涂鸦等 Sketch Daily等。
命题限制下,能更好地激发创造。另外,这也能让那些想着「做好游戏再带过去」的人打消念头,从而能够全然参与到「即兴」中来,而不把 Jam 当成比赛。
即兴的人情味
即兴的人情味
Game Jam 的 Jam 一词本身来自音乐的「即兴」,指的不同的音乐人在线下碰到一起的时候,即兴而无排练地进行演奏,应和,共同完成一段音乐的表演与发生。时间有限,形式不拘,题目现场揭露,如此设置达到了抛开束缚,迸发创意的效果。48 小时做出一款游戏,成为他们对自己的承诺与进入另一个状态的约定,极大缓解了创作焦虑,甚至常有意外之喜。
Jam 的这种状态,我们可以想象就如同《心灵奇旅》中主角让技艺与当下的灵感相融合,沉浸在「无我之境」的状态。
这恰恰非常重要,因为从这里,无论是参加者还是体验的玩家,都开始能意识到:电子游戏不再仅仅只能是一个充满着冰冷工业流水线,不再是服务器机房里的嗡嗡之声。游戏创作也可以是如站在塞纳河畔看着日落的塞尚,或是手指沾满颜料,聚精会神地捕捉那几分钟的稻草堆光影的梵高。
Game Jam 至少揭示出了一种可能大部分人对游戏从未有过的印象:游戏可以是一种创作,能成为一种灵感的迸发、当下的记录和艺术性表达。
如果你玩由个人制作的小游戏,你能可以看到其上布满着他们肮脏的指纹。你或许能在 Twitter 上看到他们的开发进展的 GIF 图,旁边还有他们宠物的照片。可以看到粗糙的边缘和小缺陷,但这并不会对游戏表达的想法有任何削弱。 —— Brendan Keogh
这种「人情味」的缺失在过去阻碍了我们尝试思考、理解、面对电子游戏。
这就像当我们看不到人工智能背后的无数「人工」标注的数据集,看不到事物背后的人,看不到那种作品和产品背后的诚恳时,我们就会恐惧、排斥,甚至觉得游戏是吞噬人心智的巨兽。
但如果我们能看到,电子游戏有大公司也有个人,有商业的手游,也有这种粗粝却可爱的想法,可以是精美严密的巨大黑箱,也可以是一种充满着个人印记,激情的与灵感的造物。那「游戏」的整体形象就会变得多元起来,我们就不再会一味的排斥,而是明白我们可以有所推崇,有所选择。
Game Jam 中蕴藏着正是这些游戏背后的「人情味」。
从业者的技艺与练习
从业者的技艺与练习
《蜡烛人》的开发者高鸣,或许也是国内Game Jam参与经验最丰富的的独立游戏人,在机核的电台《Game Jam远不只是你想的那样》中谈了他的经验与思考,他将 Jam 的48小时看作是游戏项目开发全程的微缩,是很好的演练。
这点我深有体会。
游戏开发期间的项目管理是一个坑,几乎所有开发者都掉进过:在限定时间内做一个项目,要怎么规划?先做核心中哪一部分来验证?如果时间来不及能舍弃哪些?如果做到一半发现方向并不成立,是否有勇气修改或推翻重来?何时找人测试、验证可玩性,并最终交付?
而对于游戏制作经验不足的新手来说,则在初期很容易过于庞大地构想项目(overscope),会错误规划游戏体量,构想过多的特性,从而陷入了「开发地狱」,斗志消磨殆尽。但若有 Game Jam 的经验,或许能帮他们修正并提高对游戏项目的判断力。
甚至在 Ludum Dare 这样一个带有论坛的线上 Jam 中,你可以同步在论坛上直播开发进度,在结束后可以从游戏中截取制作动图片段和玩家互动,并可以在持续数周的互评阶段持续运营,吸引更多人来投票、打分。
构思,招募合作者,到脑暴,开发制作,收尾,赶Deadline,宣发……这正是一个完整游戏的开发流程,你可以在Game Jam的几天内完整体验。
Game Jam 也赋予了经验老道的从业者「自我松绑」的机会。
擅于开发长期项目(《时空幻境》3.5年,《见证者》6年)的独立游戏设计师 Jonathan Blow 在《给游戏制作人的建议》演讲中分享了他的建议:将参加 Jam或开发小型项目作为一种工作放松和休息方式(Working Breaks)。
因为埋头苦干久了,或者陷入一些周边琐碎的与游戏无关事物的时候,你很容易忘记创造本身的快乐,而 GameJam 正是关于此的,在短短的48小时内抛下束缚,全然投入到创作技艺中去,重新找回这种热情。
Game Jam 还是一种创作方法。
爵士钢琴家比尔·埃文斯(Bill Evans)谈爵士即兴时说到,音乐在 20 世纪的发展中,即兴变得衰弱,只剩下了作曲与阐释。他强调,即兴恰恰是一种创作音乐的方式,而不是风格。
这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像是即兴而来的作品」也被看做最高的境界: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而王羲之的神品《快雪時晴帖》只是一封给友人的信。在国外也有类似的传统,将伟大作品的产生比作缪斯附体与降临的时刻,而非精心规划的结果。
大量成功的独立游戏原型,在 Game Jam 中诞生,并在之后发展成更成熟作品。比如,海外的 Evoland,Titan Souls,SUPERHOT;国人高鸣的《蜡烛人》《累趴侠》的原型也是在 Ludum Dare 中诞生,并斩获不错的成绩,这些积极反馈,都给了他验证以及将游戏做大的信心。
我在前段时间独自参加了第五十届 Ludum Dare ,做了从中国书法和吴冠中先生画意出发的《书》,拿到了创新小分第二的好成绩原本只是想作为一次实验的我也有了信心做更多接下来扩展。
让创作者成为自己
让创作者成为自己
事后在《落日间》的复盘及NExT Studios的播客中回顾时,希辰分享了自己的体验感想:即便过去已在像育碧这样的公司,做了大量 3A 大作的音频设计,但是更多的是作为一个「打工人」去配合,而不是一个完整游戏项目的参与者。
而在《剑入禅境》的开发中,他真正有了一种「要为整个游戏负责,参与开发设计直到完成一个完整的作品」的感觉。
不少同事提到,他们在 Game Jam 过程中体验到了别的工种。比如后台突然要去做客户端开发,设计师做起了美术等等。在Game Jam中,人人都可以成为创作者,他们迈出了自己的舒适圈,尝试着新的角色。
在这个自我磨合和探索的过程,也许就发现了隐藏着的作者性的自我。
这是工种之间的打通,我们不再是分管不同环节的螺丝钉,而是互相承担,共同促进,并体会着一个完整的游戏的诞生与完结,我们共享着整体设计的图景,成为项目的 owner。
我的一个朋友,在工作两年后参加了一次 GameJam 后毅然选择了离职,因为对比后,他猛然地意识到,当初冲着对游戏的热爱和对创造的初心,所选的这份工作让他远离了自己所要追寻的。(E28 不孤独的取经路,少年的戏游记 | 做事侠)
对从这点延伸到学习与技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思考:
或许真正学习「如何做游戏」的方式不是先成为美术专家再成为程序专家,或是参与过某个巨大的、完整且精美的大游戏中的某个工种。
而是不断地从粗糙的、糟糕透顶的小游戏,做出再算过得去的,最终或许很棒的作品。只可惜在今天大部分的互联网巨型项目中,很少人有这样的机会。
或许 GameJam-like 的实践是真正学习和练习游戏设计的方法,就像我们不能通过记诵词语来学习如何写作如何表达,就像永远做一枚螺丝钉并不能望见整个机械的运作。游戏技艺的最小的单位,也应是一个完整游戏的整体。
因为游戏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框架换上各种精致的美术和音乐素材,而是一种画面、音频、交互糅合且相互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完整体验。游戏技艺是构筑与实验不同媒介间的黏着、对抗、应和关系的炼金术,而非美术、程序、设计、音频能力的线性叠加。
让游戏成为它自己
让游戏成为它自己
「48小时也能做个游戏?」
面对这样的疑问,或许我们可以反问一句:
「为什么我们一提到游戏,都觉得应该是很长时间才能做出来的?」
这或许揭露出大部分人脑海中印象中的「游戏」,其实下意识地都是3A华丽大作或手机上能玩上数年的精致的商业产品。
但想到游戏就只想到商业产品与3A大作,这就好比当我们谈起文学,眼前只有托尔斯泰而没有李白,只有余华而没有顾城一样。
为什么不能有如诗一般的游戏?
在我看来,一个游戏设计的选择有自身的上限。有些游戏机制就适合在半小时内完结,再继续做只能是徒耗时间,很多独立游戏甚至像是一个小的交互点子,选取一个微型游戏 Microgames 的极端例子《Get up》:这个游戏就仅仅只有一个交互场景传达出起床的困难与「不可能性」。
我在 Game Jam 中做的《时间的形状 The Shape of Time》,是十多个不同的时间相关的哲学概念的一次设计实验,十分钟就能完结。而对于我在 NExT Studios 中做的 《写首诗吧》,你只需要一分钟就能完成一次游戏。
人们在 Game Jam 中迸发的想法和创作的游戏,毋宁说,是更自由的。
它无需被迫服从游戏平台两小时买断制游戏退款制度,或思考如何以更抓眼球的美术设计在弹窗中吸引点击。对于Game Jam 这样一种非功利性地创作来说,至少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只关注如何做符合游戏自身的「好的设计」,或大胆地尝试平常工作中难以尝试的想法,更加自由地探索游戏的潜能与实验。
Game Jam 给了一个机会,让我们能剥去通常一个游戏产品/商品附着的游戏消费,工业,创作预期,宣发要求等种种限制,在其中「你可以做任何尝试而不受指责,甚至也无需为之负责」,你没有想着要从玩家的口袋中拿钱,也没想着要面向哪些目标市场与用户。
我对用3A大作与商业产品代表绝大部分的游戏而感到不甘,我觉得围绕Game Jam的这些独立游戏,不仅应当与商业游戏等量齐观,甚至如上所述,这些难以被机构、媒体、利益所捕获的游戏,它们或许更接近游戏的本质。
在其中,游戏成为了它自己,
它最轻盈,也可能是最真诚的模样。
创造和解放
创造和解放
Game Jam 还不仅仅如此,在国外独立游戏托管网站 itch.io 上,任何人都可以发起自己的 Game Jam,基本上,每天都有数个 Game Jam 同时在进行。
相较于 48 小时的「常规款」,有的 Game Jam 加入了额外限制。比如,Train Jam 的参与者被要求在 GDC(游戏开发者大会)的前几天,从芝加哥乘坐火车前往旧金山,在旅程中完成游戏并最终展览。火车上没有互联网,这激发了强烈的社区意识和团队合作精神。而我在欧洲柏林的 A MAZE 独立游戏节上,也参加过 9 小时的极限 Mini Jam。
但不仅如此,Game Jam 甚至成为了独立游戏创作者的一种表态,有许许多多战斗檄文般的、独特的、充满了游戏精神的Game Jam活动,例如 em Reed 发起的一同创作宣言的「Manifesto Jam」。
我也写了一份《短游戏宣言》:
其中的第二条是这样写的:
「短游戏尽量缩短游戏时长,
因为我们尊重玩家的时间,
像尊重自己的一样。」
番外
番外
电子游戏和独立游戏一直是充满着先锋与反思创造的,今天的独立游戏和Game Jam 文化社区实际上沿袭了后控制论时代的嬉皮士传统,最Geek的那批人的。
乔布斯奉为圣经的《全球概览》的主编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是互联网创始之初的先锋.他在访问斯坦福大学的人工智能实验室的时候看到数百名计算机技术人员聚在玩着《Spacewar!》,他认为,不同于机器是一种对人的控制,和一切朝向效率的机器,电子游戏是控制时代的反制装置:
这款游戏代表了与已建立的权力原则的决裂。 它表现了即将到来的革命。 它不是要自上而下地控制, 不是要批量处理,不是要为了更高效地生产而向制造商发送数据, 不是要被动消费, 不是要最有效地利用机器。 这款游戏是所有这一切的对立面。
并非所有 Game Jam 都是好 Game Jam,每一场活动,每一个产品之间都有自身的复杂性,都是复杂的力的交织。我们能看到大公司通过 Game Jam 网罗人才,通过高额的奖金来改变其性质,平台通过较长期的 Game Jam 吸引免费的流量、引导新产品的孵化与上线发行。
但无可争议的是,看似只是简单小众的 Game Jam 活动中闪现出的是一种火焰般的可能性。我希望有更多人能够从这里开始,借此机会理解,接触,使用这样的媒介。
让游戏成其自身、也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
叶梓涛
2022/5
落日间是一座有关「何为游戏」与「游戏何为」的迷宫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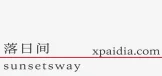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8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