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 未经作者授权 禁止转载
或许是我赛博冲浪过于频繁,且深受流行文化和阴谋论荼毒。当这件作品连同这处空间出现在眼前时,我的脑子里忽地蹦出一句话:
古罗马诸神万千,而我只信唯一的主——克苏鲁。
这当然是几类符号的并置,在我脑海中产生的与作者本意完全不同的含义。我想用几组词组,拆解一下这个念头产生的过程:重复的高耸砖砌单拱——古罗马建筑;顶部天窗采光——万神庙等宗教建筑;章鱼触手——克苏鲁神话……它们与我的专业教育经历和文化消费倾向有关,又或者还有更多调动我记忆的开关,只是我尚未识别。
回到作品和空间本身。这件作品是「北京艺术与科技双年展」的展品之一,为艺术家向京2019年创作的《降临》,艺术家希望「在肉身由于新技术介入濒临瓦解的今天……从去人类中心的视角里,肉身能够再次返回自然的整体。」
而这处空间所在的建筑,是本次展览的场地,建筑师朱锫2022年建成的798cube美术馆。这处由五道砖拱组成的小厅,建筑师称其为对798的旧工业建筑「红砖拱券元素进行延展。」
创作者的阐释和观看者的感受并不必然相连,个中关系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思考。总的来说,我并不想单独说建筑,也不想单独说展览,我更感兴趣的是《降临》/双年展和砖拱小厅/美术馆这两对关系:这件作品之于整场展览,恰如这处空间之于整座建筑。它们在各自的语境中都占据了一个特殊的位置,在比照中揭示出一种处于过渡中的认知与叙事。而这恰好与我关注的控制论,及其带来的新认知范式有关。
诺伯特·维纳的控制论,将生物体和机器通过电信号纳入了一个循环,之后在梅西会议上发展成不同的话语体系间可通约的模型。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信息时代的所有可感现实,都与控制论有关,但它却处于隐秘之中,不为多数人所知。上述的两对关系也恰好是这种状态的隐喻。
1 关于艺术,表象与过程
1 关于艺术,表象与过程
首先说说展览。
展览是首届北京科技与艺术双年展,主题为「合成生态」(Synthetic Ecology),意在技术极速发展的当下,探讨人与星球上其他存在的共生关系,它们可能是生物的/机械的/自然的/可感的/不可感的/有生命的/无生命的……因此展览作品的表达形式也打破了多数人对「艺术品」的固有印象,无论呈现媒介是VR影像、生物技术还是生态装置,其重点都不在于媒介审美本身,而是在于对人类感官范围之外的其它存在的呈现。
下面来看看几件展出的作品。
第一件,是美国艺术家特瑞可·哈波亚(Terike Haapajo) 的《群体》。这是放置在地面上的五段影像,长度2到5小时不等,呈现的是动物死亡前的红外影像,其中可以看到动物躯体颜色一点点由暖变冷。创作者从热力学的视角展现了死亡本身:温度趋于平衡,有序的生命归于沉寂,回到混乱无序的熵增状态。观看者能暂时从另一种视角审视死亡的过程,我看到的不是停止活动的肢体,也不是瞳孔里消失的光。而是温度——这一如若不借助红外摄影科学化的影像,只能通过触摸感受的「概念」。
《气候时钟》通过一个出现在不同场合的时钟提醒人们气候变暖的过程,跳动的倒计时数字同时展示了气候问题的紧迫性和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即「行动的时限与途径」。正如展览导言中提到的英国科学家詹姆斯·洛夫洛克 (James Lovelock) 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盖娅假说」 (Gaia hypothesis)中将地球视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一样。气候时钟这件作品,或者说「行动」的效果就在于,将被「第三自然」环绕的人类重新带入「第一自然」的情境之中,意识到自己与更大的生态系统的包含关系。
罗莎·史密特(Rasa Smite)与莱提斯·史密茨(Raitis Smits)的《大气森林》则是采用VR和影像媒介,将松树中的挥发性物质和树脂压力数据可视化,让化合物的挥发过程在人类视觉可感知的范围内显现,展示针叶林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联系。将不可见的气体运动及其生态系统,从数据、图表等一系列科学手段转化为感官经验,让观者直观的意识到自己身处的世界中正在发生的过程。
这些作品的呈现媒介是文字、视频、VR、装置……那么能否使用这些媒介反过来定义作品的类别属性?就像油画、雕塑一样?
显然不能,因为这些作品的目的不在于呈现某个凝固的结果和表象,它们不追求视觉符号的稳定性,外观的一致性,而是着重展现一种历时性的过程,呈现出那些无法被人类感官感知的存在。因此也就不能使用单一的媒介将其割裂或分类。
这些创作者们运用综合的媒介手段将观者「抛入」情境之中,让后者意识到自己正在经历某种存在的周期历程。因此观者对作品的审美并不是形体或色彩好看与否,而是要理解其传达/创造的情境,意识到自己作为个体所经历的某个过程或系统的变化,甚至意识到自己被包含于其中——这里不仅指此时此刻在展厅中体验作品,而是指远远超出这个展厅,甚至这座城市的更大的循环系统。
正如控制论艺术家罗伊·阿斯考特(Roy Ascott)在1993年所说:
以前,艺术过于关注有限的物体,一个已经成形且组织有序的结果,一个美学定局,一个决议或是结论,反映的是现成的现实。而现在,艺术则转向关注更为关键的出现和形成的过程。
这些作品用综合的表达映射进观者的感官,让不可见的过程浮现,让抽象的系统可感。观者对世界的认知,也由此在观看中被带入一种新的境地,就像那些欧洲中世纪的人第一次看到运用透视法画出的逼真画作时一样。
这种过程本身的浮现和对系统的意识,正是由控制论所造就:未来的目标持续地反馈输入到当下的现实,过程中的信息不断递归循环,路径和子路径在时间中显现,激发人们对过程和嵌套其中的多层系统的意识。
控制论从纯粹的技术面向反溯至哲学,深刻地改造了之后人类的认识论,而艺术也随着人们对现实的认知发生变化……
下面让我回到开篇提到的作品《降临》,它与创作者从前以身体为主要命题探讨个体、群体与世界之间的关系的创作不同。在创作者的叙事中,软质的章鱼装置表达了去人类中心视角下的肉体存在向自然整体的返回。
但这些表述和章鱼的形象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克苏鲁神话:人类面对不可名状、不可抗衡的巨大存在(古神)时,理性失效表现出的迷惘甚至疯狂;再加之与特德·姜原作翻拍的电影《降临》同名的标题。虽然作品从形象和材质上都能看到创作者走出舒适区的努力,但作为观者,我感受到的更多还是被流行文化符号吞没的创作者表达,以及单一媒介在类似主题中情境塑造能力的匮乏。
创作者在自觉中不自觉地遵循着呈现凝固表象的传统,着力于符号——意义的简单关系。它是这个展览中异质的存在,是一种具有巨大惯性的话语体系的历史残留。正如它所处的砖拱小厅一样。
2 关于建筑,结构与情境
2 关于建筑,结构与情境
其次,来说说建筑。
这次展览的场地798cube美术馆,是由旧建筑改造更新而成,创作者的叙事也围绕此展开。其中着重强调的是建筑设计从业者们再熟悉不过的话语:回应周遭环境和文脉,展现建筑空间与结构的契合之美……具体表述诸如「结构形式和材料的表现力」「两道混凝土墙上的缝隙是将798的道路网格‘竖立’起来所形成的意向」等等。
建筑师丰富的经验和娴熟的技法很好的完成了这种叙事。暂且不论项目背后的经济和社会考量,单就叙事本身来说,重点明显在于结构美学与文化符号。这是一套根植于建筑本体和其所处环境的叙事,是在专业领域内外的各方(业主、设计师、观众)之间相对可通约的话语。
通常来说,这种叙事保险可靠。只是,通过符号(空间形式、图案、建筑材料等)所传达的意义和「官方叙事」,在建筑师那里是创作的结果,而在观者这里则是理解的开始,它在体验上指向何处,无法控制。这可以理解为罗兰·巴特的「作者之死」。
上文中提到的展出《降临》的砖拱小厅,正是这种叙事中最为纠结之处。不论创作者的初心如何,「拱」这种视觉符号都容易唤起过多的历史记忆。文脉考量和形式借鉴哪个在前?结构美学和古典精神哪个优先?这很难判断,或许创作者最初的念头也是混杂而下意识的。
在这里,似乎看到了一位置身于历史之中的创作者,在不自觉中自觉地延续着一个悠久而庞大的话语体系:建筑要通过空间形式或视觉符号回应文脉;厚重的建筑材料要呈现出稳定的结构美学;砖拱可以打造有仪式感的空间……等等。
有趣的是,在回看整栋建筑时,似乎也看到了一位对新问题敏感的创作者,在自觉中不自觉地揭开新建筑的隐藏脉络:这里没有实体(建筑或材料),也没有符号。这里充满了变化与适应,中心是人的行为与事件的情境。
而容纳了这些的,就是美术馆中和展厅平行的露天院子。这里出现了两种可以改变空间的可移动构件。
第一种,是顶部可伸缩的帆布屋顶,安装在一组移动式钢梁上,由隔出院子的两道混凝土墙顶部的滑轨承载。
第二种,是院子东侧的翻转大门/墙体,既可以放下成为一道分隔院子和建筑内部的隔墙,也能翻转到水平角度,变成巨大的屋檐。
二者都借助了大型机械结构,回应了天气和院子中人的活动的变化,以产生不同的空间形式和情境。此处的关键词,看起来似乎是「可移动的建筑构件」,这不免让人联想到Archigram和新陈代谢派的那些天马行空的提案。
但实际上,几者有一个共同源头,那便是塞德里克·普莱斯(Cedric Price)和琼·林特伍德(Joan Littlewood)在1960年代的欢乐宫项目(Fun Palace)。这是一个使用了巨型结构和控制论技术手段,能根据使用者需求变化的自动化建筑。建筑中的程序可以将使用者的需求数据化后,通过计算机操纵机械设备改变墙体、楼梯、走廊、空调和灯光等空间参数,回应使用者的需求,实时变化。
而那个更切题的关键词也在其中浮现:「自组织建筑」(self-organization)。我在这里借用了控制论学家戈登·帕斯克(Gordon Pask)的控制论术语。「自组织」用来描述一个系统(有机体或机器)主动或被动地应对周遭环境变化的状态。而在帕斯克看来,整合了计算机和传感技术的建筑无疑也可能成为一个「自组织系统」,能够将使用者和空间整合为一个有机的共生体。这也恰好是他参与欢乐宫项目后的主要工作,为这座建筑带来了更为激进的技术面向。
虽然这座文化宫殿在离实现仅有一步之遥时终止了,但其中的诸多想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从Archigram到蓬皮杜中心,再到Diller Scofidio + Renfro & Rockwell Group在纽约建成的the Shed艺术中心,根据使用场景改变空间结构的理想一直在被践行,并且一步步从方案中的空头支票成为现实。虽然欢乐宫作为英国工人阶级文化宫的意识形态属性无法复制,但其仍是后世的大型可移动公共建筑极为重要的参照。
要强调的是,可移动的构件只是手段,适应人的行为、情境和天气才是目的。工程技术塑造的可变建筑构件在过程中产生的各种变化状态,带来了完全不同于结构美学或文化符号的空间美学。它不再囿于固定结果/形式的呈现,而着力展示不同的空间情境,变化的过程本身就是「审美」的对象。空间中被维护结构容纳的「无」回到了中心位置,人和事件成为了主角。这是技术手段发展后给建筑带来的新可能,它让曾经笨重的建筑面对快速变化的使用者和社会时,具备一定的灵活性。
而那个砖拱小厅,可以看作是某个庞大话语体系的历史残留,被创作者在自己的叙事中不自觉的沿用。但设计动作和实现成本更高的「情境院子」却没有占据主要的篇幅,且描述语言几乎是纯功能性的。
不过,院子的价值已经显现。我在参观时候,馆方正在调试翻转屋顶,我刚好经历了屋顶从竖直的墙体翻转为屋檐的过程。走出展览和商店,看到院子在视线中的比重随着慢慢翻起的墙体越来越大。为开幕场馆活动竖起的LED屏幕和混凝土墙体交织,灰与红冲入视网膜。一符熟悉又陌生的情境展现在我眼前。无言仿佛又说了很多。
3 关于控制论,隐秘的地基
3 关于控制论,隐秘的地基
《降临》和砖拱小厅的重叠,是一组绝妙的隐喻。虽然二者在空间位置和展览流线中都位于一个极为显要的位置,但在与控制论直接相关的整体语境之中(建筑和展览),却是一种旧体系与旧范式的残留物。
那些真正塑造了当下环境的隐秘脉络,却被深埋在地下。这既是隐喻,也是事实,因为地下展厅的某件作品,明确地指向了这条隐秘的控制论脉络的关键节点。
这件作品就是拉尔夫·贝克尔(Ralf Barcker)的《网络的自然历史》(the natural history of networks)。创作者将镓、铟和锡液态合金浸泡在氢氧化钠溶液中,组成一种软机器(Soft Machine)。然后以电能作为媒介,通过不同类型的电流刺激,让液态合金呈现甚至记忆不同的反应模式,创造出一种能适应外部环境的自组织系统(self-organization system)。
自组织、自适应等控制论术语在此出现并不奇怪,因为该作品的名字就直接取自戈登·帕斯克1960年的同名文章《网络的自然历史》,而作品本身则是对文中描述的电化学算法计算机的再现。
不同的是,帕斯克是将铂金电极插入硫酸亚铁溶液中。接入电源后,在电流通过量大的电极上,溶液中的铁聚集形成铁线,该条通路的电阻也因此降低。反复的电流刺激会强化这条线型结构,甚至产生分支结构。而那些电流较少的电极则不会如此。不同模式的电流刺激会形成不同的线型结构,电化学机器因此具备了一定程度的自组织(学习)行为。
下面我会花一点时间,尽量简略清晰地描述帕斯克的电化学计算机背后的深层想法。
《网络的自然历史》中的「网络」(network)并非是指如今的互联网或者抽象的连接,而是「任意一组相互连接的、可测量的活跃的物理实体」,具备自组织的适应性行为,可将其大约理解为我们周遭的世界。而电化学计算机就是帕斯克用实体模型的形式对「网络」的再现。
至于「自然历史」(natural history),帕斯克并非指某种生物或环境学科的概念,而是一种认知方式。帕斯克认为「我们都是不完美的观察者,发现着散落在我们周围现实世界中的系统」。如果将「网络」视为世界中的整体物理实存,那么观察者便是通过能量交换(熵)来识别包含在其中的系统(可以视为网络的子集),但是系统呈现出何种结构则完全取决于观察者自身的模式,所以不同的观察者也会识别出不同的系统。当一组共享某种模式的观察者共同认定一种系统时,就会形成某种共同的知识体系或学科。
而「自然历史」的方法,就是要意识到「网络」中不存在所谓的「本质真理」,一切系统和系统中的「本质真理」都是观察者自身模式在「网络」中的映射。因此「自然历史学家」就要通过对话(conversation)在互动中适应不断变化的系统边界,来认知这个「网络」/世界。
电化学计算机中的硫酸亚铁溶液和铂金电极构成了一种「网络」,而外界不同模式的电流输入,可以视为观察者与其进行的能量交换。「网络」在电流刺激下因此生成或保持不同的模式。
帕斯克与斯塔福德·比尔(Stafford Beer)曾为电化学计算机安装了一个电子耳,经过半天的训练后,溶液电极中生长出了能识别50赫兹和100赫兹两种频率声音的线程结构。
可以很明显的看到,帕斯克的电化学计算机并非某种工具,而是他认知理论的演示机器,它描绘出了一种基于反馈的自组织系统,具备模糊的初级智能。站在现在回看,这或许可以视为人工智能的另一条未充分发展的岔路。
回到拉尔夫·贝克尔的作品,它意味着什么呢?我想它能让生活在充斥着数字计算机系统世界的我们,看到另一种不同于现有范式的电化学计算机系统(或者称其为初级智能),体验其行为过程,意识到系统的浮现和过程的存在,来激发「对机器、人工和物质的重新想象。」
有趣的是,上面两部分中提到的控制论脉络:欢乐宫项目与罗伊·阿斯考特的思想源头(他也参与了欢乐宫项目),恰好都指向戈登·帕斯克。帕斯克从1950年代开始构建的一系列理论和发明的装置,是人机交互和人工智能的先锋实践,它们几乎奠定了关于过程和互动的艺术的旋律基调。
虽然这些的机器看似「复杂奇怪」,理论看似「晦涩难懂」,但帕斯克的最终愿景却非常简单:借助控制论式的对话和互动通向一个更好的世界,那里最重要的是对人(或其它存在)的价值既不傲慢也不贬损的肯定。
但由于种种原因,帕斯克的思想并未被充分发掘与研究。就像《维纳传》的副标题「信息时代的隐秘英雄」一样,帕斯克也可以被称为一名「隐秘的先知」。
拉尔夫·贝克尔这件延续他思想的作品,位于地下的漆黑展厅之中。它与顶层被天光照耀的砖拱小厅与《降临》,构成了这个控制论时代的绝佳隐喻:关于当下进程的源代码作为某种隐秘的脉络被「深埋」地下,它的轮廓由于无形而难以琢磨。
于是,人们依旧转向纪念碑和符号,追求表象与目的,而忘了追问过程为何。
延伸阅读:
参考:
1.未来就是现在:艺术,技术和意识,[英]罗伊·阿斯科特,2012
2.The Natrual History of Networks,Gordon Pask,1960
3.Gordon Pask and His Maverick Machines, Jon Bird & Ezequiel Di Paolo, 2008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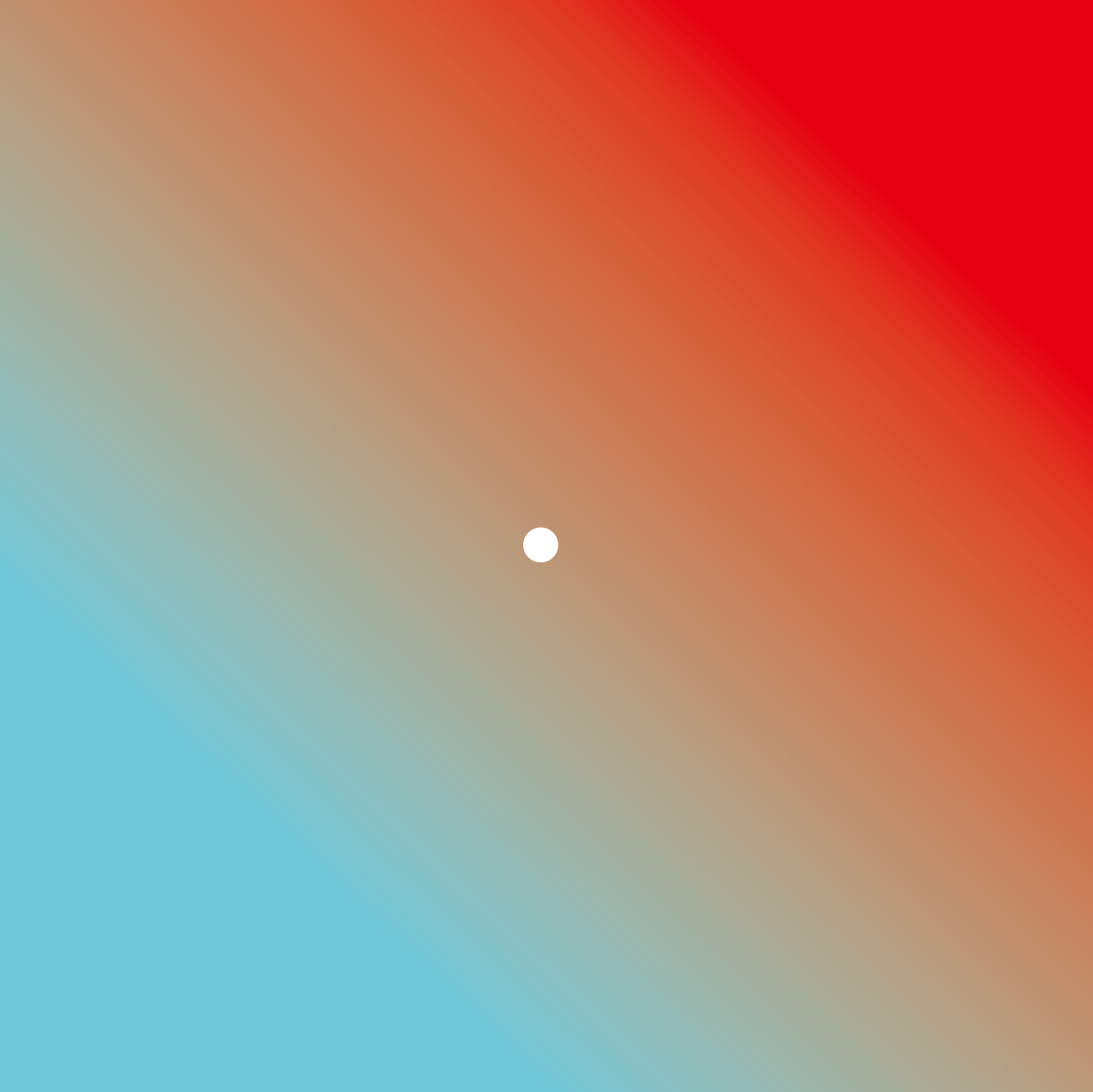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2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