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4. 维德昆 · 希尔德
4. 维德昆 · 希尔德
十二毫米胶卷嗡嗡地进入放映机。可汗挨着玛基耶克坐在幕布旁边的沙发上,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玛基耶克放在方形茶托上的方形咖啡杯。他拿起了一个用来搅拌方糖的勺子,小心翼翼地靠近那个杯子。这间叫做“电影院”的咖啡店全部由玻璃和白色构成。杰斯珀坐在一张被玻璃制的隔音墙环绕着的白色椅子上,调试着放映机。白色的幕布落在玻璃平面上,可汗和玛基耶克正坐着的沙发也是白色的,咖啡店中央的玻璃橱窗里放着一尊白虎的雕像。得小心别打碎任何东西——不然肯定得赔不少钱。
“让我猜猜,”那位探员把他的“阿斯特拉”牌香烟放在指尖揉捏,使它变得尽可能柔软,“这是你的设计?”
“是我一个学生的。这个地方就像电影院的屏幕,一块空白的白色幕布,而我们就被*投射*在上面,你明白吗?感觉如何?这块屏幕应该不会让你太舒服的,明白吧?”
“确实有点不舒服。”
“嗯,他是有点紧张,确实如此,但这个男孩有天赋。他需要一个有高能见度的项目,而只有这里能让他马上走到投影仪后面。所以让我们努力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吧,你懂的,”杰斯珀和那尊老虎雕像盯着可汗,老虎雕像的玻璃眼珠比这位室内设计师的还要明亮。
“嘿,老兄,我就在这样做!”
玛基耶克从他的夹克口袋里拿出了一支笔和一个笔记本。
“话说回来,”杰斯珀开始说,“我一位同事的亲戚是摄像机操作员,做纪录片的。去年秋天,他和我说了他的新项目,和盖斯勒有关。你知道康拉德·盖斯勒吗?”
“他干的都是些犯罪的勾当,对吗?”
“不止如此。约斯塔——这是这位摄像机操作员的名字——他告诉了我他在干这件事的时候有多么害怕,还问我应不应该干。他现在有孩子了,你懂的。事实上,这部纪录片是关于维德昆·希尔德的,而这就是我感兴趣的地方。”
“我的天呐!”
“我不想和维德昆·希尔德扯上任何关系!”
“等等,等等!我也不想,这部纪录片已经开始拍了,用的是阿尔达语,而不是瓦萨语或者其他语言。但我还是决定要盯着他一点,明白吧?然后,两周前,约斯塔来跟我说,他们马上就要有重大进展了。他们已经和维德昆·希尔德在喀琅施塔得[1]呆了六个月……”
“不可能!”
“……而且他们现在的策略是:给希尔德留下深刻印象。盖斯勒喜欢希尔德——盖斯勒是北陆人,皮肤白得像雪,博览群书,而且能说会道。这样一来希尔德就也会想给那些采访他的人留下印象,他会开始说话、开始吹牛。盖斯勒给他的印象是,那些天马行空的强奸犯已经有很多了,那么维德昆·希尔德又有什么不能做的?”
“嗯哼……”
“在开始的三个月里,维德昆只是暗示、挑起好奇心、抛出可疑的日期、谈论去海边。盖斯勒没有在意,只是继续和维德昆进行关于克服善恶观[2]的哲学讨论,我把这些内容都记录下来了。”杰斯珀拍了拍放在玻璃方块桌子上的文件夹,“然后有一天,希尔德受够了。”
他按了一下开关,投影仪的心脏里的一个小灯泡亮了起来。“我现在必须警告你,”他看向可汗,“我们中工作和调查沟渠和寻找失踪儿童无关的人,可能会把维德昆说的话往心里去。”
特雷兹往自己的黑咖啡里加进了第六勺白糖,然后顿了顿。在这下明显的停顿之后,他把已经像针一样尖的铅笔塞进了削笔刀里,装作很忙的样子,脸上露出了苦涩的笑容。
“老兄,你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说重点?调查沟渠和寻找失踪的儿童——那也是你的工作。”
“好吧,可汗,”杰斯珀叹了一口气,“调查沟渠和寻找失踪的儿童,那是我的工作。”
“敬沟渠和失踪儿童?”特雷兹突然开心地举起了自己加满砂糖的咖啡杯,等待着。
“干杯![3]”可汗叫道。
“干杯!”杰斯珀说道,然后从玻璃水杯里舀出了一片柠檬,咀嚼了起来,眉毛因为酸味而若有所思地皱了起来。
“那卷录像带呢,杰斯珀?”
“哦……”
一个超级人类、强奸犯、恋童癖以及类似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法西斯团体“郝姆达尔”的前成员,维德昆·希尔德出现在了白色的幕布上。他一只手被铐在椅子上,另一只手轻轻地放在自己的脸颊上,这个未来主义哲学家很清楚摄像机的存在。考虑到这一点,他把他北陆斗牛犬般的下巴抬到某个尊贵的角度,眼窝里投出的眼神上下扫视。他把头发以三十岁的方式小心翼翼地梳到一侧,翘着二郎腿。你能看出维德昆是一个虚荣的人。他拒绝穿着印有号码的囚衣变成历史,而是正穿着黑色的衬衫制服与康拉德·盖斯勒交谈。这只是他开出的众多条件之一。
“有些人诞生于死后[4],”他用古阿尔达语吹嘘道,古老的语言为他现代性的微妙情感注入了很多乡村风情。桌面上六位数字时钟表面,正在进行的是8月12日采访的第三个小时。
“你知道吗,维德昆,我写过一篇关于古阿尔达语的硕士论文。我可以帮你偷运一些文献出来。”
“哦,你真是太好了,康拉德,你知道我对于这所图书馆的选书是什么感受。”他们小声嘀咕着,仿佛在理解对方。
“阿尔达语是刻在我们族群骨子里的语言,”维德昆用一种宣告式的语气继续说道,“它的词汇是由几千年前在卡特拉平原定居的古代猛犸象猎人调整和发展而来的,它在关乎智慧的基本问题上具有某些语义上的优势,而这是大陆民族所缺乏的。阿尔达语是我们的本性,而现代的瓦萨语——一个大都市的杂种,被格拉德语所渗透,退化为了大陆性的。这种被稀释了的语言无法阐述真理。这个有缺陷的混合物中的所有句子最终都表达了同样的意思:国际污名。下一个世纪,我们族群将回归它最本源的语言,而这将是一个关于智慧的新时代的诞生!”
“这一点你已经谈过很多次了,我也读了你关于这个议题的笔记。它们都很有意思,但你不觉得你的历史角色正在破坏你教义中更细微的地方吗?”
“什么?”希尔德的眼睛突然亮了。他脸颊上的深沟拉长,嘴唇变厚,显得十分轻蔑。
康拉德假装没有注意到希尔德的情绪,继续说道:“虽然我理解你观察中的逻辑,但你不认为从一个被定罪的恋童癖口中所说的科学有效性很难被人们接受吗?”
"对于我们部落来说,交配的传统和现代社会色情宣传中所表现的浪漫主义或者其他什么我不理解的东西完全不同,你明白这一点,康拉德。等到他们无能的道德将大陆族群引向灭亡的那一天,你就会明白我和你说的这些话。”
“好吧,让我们从一个普通公民的视角来看......”
“一个普通公民会让他的女儿跟黑人和吉普赛人一起上学,让她从小就处在这口种族融合的大锅里。一个普通的公民会允许他的女儿在那里被强奸。你知道当你把四个女孩子送进这样一所学校之后,这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康拉德注意到了这位哲学家的低声咕哝,但他假装没听见。“普通公民是你未来的读者,普通公民将决定你的愿景能否被付诸实践。你探讨的是这个民族!而你真的觉得读者不会注意到吗?作者是个法西斯分子……”
“国族主义者。”
“……是个法西斯分子、一个有条不紊的强奸犯、一个在喀琅施塔得因至少四起谋杀案而被判无期徒刑的罪犯,而这本书则是历史哲学、人种改良学和强奸的混合物!”
“历史,历史,康拉德。你是个聪明人,但你受到的同性恋教育正在显现出来。你仍然认为历史是用硕士论文创造的,我不知道用什么……”
“好吧,它是用什么创造的?"经验丰富的采访者并没有丧失胆量,"通过强奸?”
维德昆抓起盖斯勒面前笔记本上的一张纸。一个穿藏青色制服的士兵在他这突然的动作后跳入画面,用橡胶警棍击打这个族群分子的手腕。希尔德疼得呲牙咧嘴,纸片飞到空中。世界著名的纪录片导演康拉德·盖斯勒,奥斯卡奖的三次被提名人,向士兵举手示意。士兵放下了警棍,但仍在男子身边保持警惕,按着他的手腕。
“给我一支笔。”维德昆愤怒地盯着盖斯勒。
被拘留者握着笔的手攥成了拳头,向士兵投以胜利的目光,“你!现在就把我的纸捡回来!”橡胶警棍已经被气势汹汹地举到半空,这时盖斯勒迅速撕下一张新的纸,放在希尔德面前的铁桌上。
“你现在明白了吗?这场远征,”维德昆精心梳理的头发凌乱不堪,一绺浅棕色的头发在他眼前晃动。希尔德用肘部压住纸,尝试用笔在上面写字,那支笔在他的手里显得尖锐而危险。他突然发怒:“请把我另一只手解开,我这样没法写字。”
在盖斯勒恳求的目光下,士兵从他的腰带上拿出了一串钥匙。现在,希尔德正面朝向观众:“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来到了这里,来到了这个世界的边缘,来到了这片土地上。他们坐着狗拉雪橇来到这里,穿越了苍茫的灰域。只有意志最坚定的生物在这趟英雄般的旅行中才能保持他们精神的完整性,而那些精神脆弱的大陆生物则被留在了那里,被留在了灰色的虚无之中。我们自律的祖先只是把那些失去理智的人从兽群中分离了出来。于是,只有纯洁的、坚定不移的哈康人、古德伦人以及其他初代人种从灰色的坑洞中爬了出来,踏上了卡特拉的土地。不到五十年,这些初代人种就把卡特拉大陆上的猛犸象狩猎殆尽,蓬勃发展。”维德昆·希尔德胜利般地伸展着他被解放的手,然后开始在纸上画小圆点。
“这是一条基本的人种改良法则,康拉德,基本的。环境越有挑战性,人类就越能进化,到草原之外,到这里,这片黑暗、飘雪的地方……人类本不应在这生活,仅仅是为了生存,就必须出现一种超越人类的倾向。”
盖斯勒满怀期待地耸耸肩,没有插话,只是理解地点点头。“这种超越人类的倾向不受道德的约束,这种超越人类的倾向是一种蓄意的欲望。对它来说一切皆有可能,没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在黑暗的夜晚,从一个冬天到另一个冬天,它通过血液被代代相传。甚至在你的身上,康拉德,也有这种超越人类的倾向。”
康拉德点点头。维德昆·希尔德的脸变成了不正常的红色,这种红色介于发烧和过敏性红疹之间。“我们所有人,包括你,都有义务增强自己体内的这个原初的实体。就像捕食者的下颚因吃肉而变得更强壮。义务……对你族群的义务。这样他们就也能拥有强壮的下颚、能够吞下很多肉的下颚。”
维德昆欣赏着这幅作品,脸上带着和他的面容不相符的骄傲笑容。镜头还没有明确展示纸上的东西,但盖斯勒凑近了那幅画。
“一个罕见的物种,中间的那个,真是一件稀奇的宝物。”
投影仪嗡嗡作响。杰斯珀从文件夹中取出维德昆那张纸覆盖着透明塑料薄膜的复印件,放在了桌子上。这张纸仔细地描绘了一个陌生的星座,一个由几十个点组成的优雅的星座。可汗恐惧地张大了嘴。联合警署探员特雷兹冷静地在他的笔记本上写下笔记。
“你无法想象,康拉德,我干她干得有多狠。你无法想象……”希尔德还在说话,杰斯珀就匆忙关掉了投影仪。
二十年前,六月。
海岸边松树林中的悬崖上昏暗而寒冷。炙热的太阳就挂在松树顶上,但只有几束光线能穿过交错的沙子和缠绕的树根,照射到树林的地面,仿佛海底的金斑。有一瞬间,树荫底下是绝对的寂静。在一百米开外,你就能听到石楠树叶在走近的男孩们的运动鞋下嘎吱作响,直到海风让松针沙沙作响。树的枝干轻轻摇晃,像是一根根暗橙色的柱子,两侧还有阳光映照出的金色条纹。树脂的香甜味在林间漂浮。洋甘菊的尘土味、一种甜中带苦的花香,萦绕在特雷兹的鼻孔中。一根火柴被划燃,偷来的“阿斯特拉”香烟厚厚的烟雾把所有气味一扫而空,轨迹在一束光中被清晰地勾勒出来。特雷兹放松下来,把风衣放在头顶,开始尝试在光线中吐烟圈。他父亲的外交别墅就在几公里外的小镇上。这座房子离热门的夏季海滩如此之近,以至于特雷兹在三周前在暑假开始时就成了受欢迎的男孩。就在能够清楚地听见其他人的脚步声从山后传来时,特雷兹在较大的烟圈中又吐了一个小烟圈。
“哦!我做到了……”他惊呼道,吹散了他的杰作。
“什么?”穿着短裤和水手衬衫的杰斯珀在爬上小丘后问道,“你做到了什么?”
“我让一个烟圈穿过了另一个。”
“你现在开始吸烟了?!”杰斯珀惊讶地问。
“要来一根吗?‘阿斯特拉’牌的,最带劲了。”
“给我,特雷兹,我要来一根。”原本正在画画的可汗走到了杰斯珀的身边,一个带皮质挂带的双目望远镜挂在他的脖子上。
“给。”特雷兹把烟盒扔向了可汗,他在笨手笨脚地接住时掉出来了几根,这已经让他筋疲力尽了,但他仍然努力不把它弄掉,并把它抬到自己眼镜下面。
“酷。”可汗对纸盒进行了专业的评估。蓝底的纸板上印着白色的星星。
“没劲。”杰斯珀从他嘴角说出这句话,然后迈开步子从特雷兹身边走过,到了另一座山顶去勘察土地。
“你的衬衫,那才是没劲。”特雷兹懒洋洋地站着,从火柴盒里拿出了一根火柴递给可汗。
杰斯珀眯起眼睛,像船长一样举起手,打量着眼前森林的地面。
“没劲,是吗?安妮可不这么想。你知道的,她昨天还因此*称赞*了我。就在昨天。”
“真的吗?”
杰斯珀转向可汗。这个男孩试探性地吸了一口烟。
“嘿,可汗,你还记得在更衣室里,安妮说这件衬衫好看吗?”
“是的,特雷兹,她确实这么说了。”
“菲尔森像个傻瓜一样跳了出来,抢先我一步跟安妮说她的衣服也很好看。他还说了一些关于她头发的话。真的太滑稽了。”
“永远不要错过展示自己礼貌的机会。”可汗笑着宣布,然后咳出了一些烟雾。
“咱们走吧。”
三个男孩穿过从树叶间投下的光斑,向坡顶走去。可汗用一种失败的方式丢掉了他的烟,然后开始甩着他望远镜的挂带绕圈。跑下斜坡后,男孩们跳过石楠树丛,只有杰斯珀担心他的白裤子,于是双手插在口袋里,像在晚上散步一样安步当车。随着他们接近悬崖上的老地方,从树林中传来的海浪声越来越响。
木质栏杆旁有警示坍塌危险的标识,其中一段斜坡已经摇摇欲坠。穿过人行道,从警示牌下钻进灌木丛中时,可汗对特雷兹解释道:“看,他们管它叫北海,但它其实是更广阔的一片大洋。理论上,它能穿过灰域,延伸到你们的伊格瑞希海,直抵格拉德。这使得北海的范围跨越极地,所以实际上它是一片大洋,这是一个分类学的问题。”
在一起的第三个星期,他们仨尽量保持着他们谈话的学术性,以便于在秋天返回时给大家留下知识分子的印象。杰斯珀跟在后面,小心翼翼地钻过灌木丛,接话道:“我们在卡特拉语中没有大洋这个词,一切都只是‘海’。”
一片巨大的水体在站在峭壁边缘的男孩们的面前展开。云在蓝天中被撕开,耀眼的白色阳光在水面上反射出一道道条纹,海浪慵懒而威严地冲刷着长长的沙带。夏洛茨扎尔。风停了一会儿,一阵热浪拍在男孩们的脸上。昆虫从正在开花的野生报春花的叶子里钻了出来。海岸在岩壁下朝着海洋蜿蜒前行,一直到半岛的顶端,哈弗桑拉里酒店就位于那里。沙滩上有像小点一样的人,旁边放着红白条纹的沙滩伞。特雷兹说过很多次他关于跳下这个柔软的岩石斜坡的理论——他会先从三米高的地方落到一个坡度缓和的小沙丘上,然后用脚跟滑下去。如果要采用这种方法,杰斯珀担心他的衣服,而可汗单纯只是胆小。即便是现在,特雷兹正坐在靠近边缘的地方,而杰斯珀正恳求可汗把双筒望远镜借给他。太阳光斑反射在像是昆虫弯曲的眼睛的望远镜上。在玻璃透镜黑暗、凉爽的中心,人们在海滩上的画面、来自北方的夏日游客带着他们的浴巾和沙滩伞的画面,被放大了。这个画面对可汗来说甚至更为清晰,因为他将透镜的参数调整为左:+7,右:+4。这个双筒望远镜是可汗用自己的钱从瓦萨的一家猎人商店里买的。
等杰斯珀扫视完海滩,就轮到特雷兹了。橡胶垫压进他的眼窝里,阳光在他的脸上晒出了更多雀斑。他承认道:“还没到时间,现在才十点钟。他们会来的。”
当可汗和特雷兹开始比较香烟的品牌时——他们说瓦萨产的垃圾都太温吞了,格拉德产的正牌货才够劲——可汗对一切都热切地点头。同时,杰斯珀将他的狙击镜对准了海滩,不愿放弃。小小的十字准心停留在了一顶白色的沙滩伞上,但没有找到它正在寻找的红色花朵。垂直参考线在年轻的家庭、倒塌的沙堡,以及棕色皮肤的日光浴者之间来回移动,在两个金色头发的女孩身上略有停留,然后又继续移动——那不是她们。杰斯珀调整了一下焦距。大约两百米之外,一种微弱但熟悉的感觉在他心中激荡,像是一个遥远的星座,一种物质性的交融。他挥手示意其他男孩,有什么事要发生了。可汗和特雷兹遮住阳光,朝海滩俯瞰去。
杰斯珀调整他泽乌牌镜片的焦距,淡粉色的面纱在他的眼中锐化成了一个胃的形状。呼吸造成的抖动使得望远镜对准的地方从女孩的肚脐移到了胸口,她胸部的曲线围成一个圆形,撑起了她的日光浴上装。白色的丝带穿过她的肩膀,纤维覆盖之下的胸部随呼吸上下起伏。双筒望远镜中央的轮子发出了两下咔哒声,视野随着女孩翻身趴下而扩大,定格在米黄色的沙滩布上。灰金色的头发和墨镜之下熟悉的圆脸蛋一闪而过。安妮-艾琳·郎德懒洋洋地用手肘撑起身子,把头埋进一本女性杂志中。在她小巧的后背上,一个精致得有些怪异的星座般的胎记沿她的脊柱而下,延伸至两侧像翅膀一样张开的肩胛骨上。
冰冷的恐怖透过窗户的阻挡渗入了这家叫做“电影院”的咖啡馆,里面的三个人正试图维持头脑中的表面张力,这是调查的第二十年。“谁知道这个?谁知道?这么久以来我从来没读到过任何一句关于它的记载。哪儿都没有!”
特雷兹把他的铅笔放在桌子上。
“这就是所谓的受控事实。它在个人描述中被刻意省略了,即使是在官方文件中——我脑海里有三十个那种文件夹,但里面没有一行文字提及它。他知道这一点,看看他!”
杰斯珀的脸色毫无改变,他已经经历过这一切了。“这就是约斯塔来找我的原因,那个公务员只是耸了耸肩。或许他在工作的时候听说了我认识这些女孩子。他们都很困惑,希尔德也没有再做任何解释。顺带一提,我不相信他的屁话。有些男孩去那儿是为了原则,但希尔德就只是喜欢胸大的古德伦人罢了。”
“这和档案不相符,从时间上根本不可能,”可汗振振有词,“他五个小时之前正在600公里以外,给他那个该死的强奸机器购买曲柄和垫片……我不了解,大概是某种密封塞。”
由于维德昆·希尔德在建造那台臭名昭著的强奸机器时发出的噪音,他的邻居终于报了警,而这就是他终结的开始。但印纳雅·可汗严肃地盯着这位联合警署探员的眼睛。
“特雷兹,你现在必须重新立案,继续调查。不管怎么样他肯定得知道,而且这是自从那封信以来唯一可信的线索。你必须这么做。”
“你无法想象现在事情究竟有多糟糕,这是翻旧账最坏的时候。军队不会再提供支持了,现在一切都处于半战时状态。没有人知道橙色王国[5]是否还存在。如果我再引发混乱,他们会解雇我的……”
“不,特雷兹,你还是必须做点什么。”杰斯珀有点烦躁,他对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没有兴趣。“你就是干这个的人,这是你的工作。去干活吧!”
“先等等、等等!我当然会继续。我在你们邀请我去同学聚会的时候就有预感了。你觉得我会相信你们就只是怀旧之类的吗?我的案子永远都在调查中,你懂的,这个文件夹不会合上。你只能祈祷当地人会乖乖配合,但他们讨厌这样,也几乎没有人会费心去核对那些签署的审讯文书。”
可汗狡猾地笑了。“审讯文书?所以说你还要去喀琅施塔得?”
“明天就走。”
“很高兴知道你还能保持冷静,特雷兹。”
杰斯珀也笑了,发红的脸颊和局促的语调让他显得有些不自在,“不过确实很冷静!那真是太好了。”
特雷兹赞同道:“确实是件好事。二十年了,也不应该抱有什么希望了。”
“但还是有希望的?”杰斯珀做出明智的样子,歪着他那和肩膀相比有些过大的脑袋。
“是的。很对,杰斯珀,你说得很对。”
“您好,买单!”这位室内设计师在过去的两年里都在远离活跃的商业活动,他对服务员打了个响指,然后用食指指向桌面。夜晚对他来说并不好过,但今天不同。今晚杰斯珀可以请自己吃点小零食,一点愚蠢的小零食。夜幕在这个方块建筑的窗外降临了,在黑暗中,一切皆有可能。有可能不知怎的就能在世界上某个隐秘的角落找到她们,可能是在沃斯托克湖[6]的永冻冰面下,或者是尔格沙漠[7]里——那也是雷蒙特·卡扎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地方,在格拉德大陆肺部的深处……你仍然可以找到他们,就像他们当时那样。渺小。然后借此让自己也变得渺小。在云层之上,蒙迪之躯[8]的脚下,你只需稍稍掀开雨滴的面纱,就能触摸到它们……“你们还没有放弃,这真是太勇敢了!其他人都忘记我们了,夜晚的天空上点缀着冰冷的星星,深蓝色的天穹在我们的头顶旋转,但我们知道,你们仍然在寻找我们。”
译注:
译注:
[1]喀琅施塔得(Kronstadt),现实中在俄罗斯存在同名港口城市,1921年在此发生过反对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的大规模水兵武装暴动。
[2]克服善恶(overcoming good and evil),是尼采在他的著作《善恶的彼岸(Beyond Good and Evil)》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主张挑战和超越传统道德中善恶的二元对立,接纳人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3]原文此处及下一行中的“干杯”原文中均为瑞典语,写作Skål。
[4]诞生于死后(born posthumously)出自尼采自传性作品《瞧,这个人(Ecce Homo)》,在引言中,尼采自称“一个在我父亲死后出生的孩子(I am a child born posthumously)”。
[5]橙色王国(Oranjenrijk),荷兰语,代指荷兰王室。
[6]沃斯托克湖(Lake Vostok),世界上最大的冰下湖,位于南极。
[7]尔格沙漠(Erg Desert),作品中虚构的大沙漠,位于伊尔玛大陆。
[8]蒙迪之躯(Corpus Mundi),作品中虚构的休眠盾形火山,是这个世界的最高峰。
[个人翻译,不做商业用途,如若侵权请联系删除]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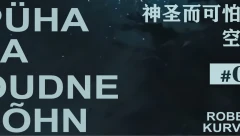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5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