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6. 无畏者弗朗蒂切克
6. 无畏者弗朗蒂切克
悬而未决的失踪案往往最令人悲伤。在成为一座水电站之前,佩雷门纳亚维拉还只是维拉河。歌剧明星纳德娅·哈尔南库尔在她名声最盛之时跳入其中。事情本可以就保持这样:在一个秋日的夜晚,在一场扣人心弦的演出之后,纳德娅突然消失了,她天籁般的女高音仍在歌剧院回荡。一名老人宣称自己曾看见她穿着晚礼服从桥上走过,他说的是真的吗?还是说那名她的狂热崇拜者——他坚称自己一年后在瑞瓦肖见到了她——说的是实话?在有妄想症的小说家所编织的低俗故事中或许能找到一些真相:在那篇小说中,纳德娅实际上是一名梅斯克共和国的间谍、虚无主义者、末日预言家。谁能确定呢?
但有一件事可以肯定,没有人想看见纳德娅穿着晚礼服的尸体出现在水库的淤泥中,也没有人想看见寄生在她眼眶里的河蚌、露出金牙的凝固笑容,或是水电站施工人员震惊的表情。
徒劳,是徒劳塑造了世界。历史是徒劳无益的故事,进步是徒劳无益的序列。未来主义者说:"发展!";反叛者说:"丧失!";道德家在后排喊道:"宿醉!"。"失败",愤怒的反叛者说,"时间是灰色的”。造物主的失败是这个时代的引子。卡拉斯·马佐夫一枪打爆了自己的头,阿巴达奈兹与多布雷夫在奥松涅群岛上服毒自杀。在棕榈树下,风拂过他们的骨头。谁会知道呢?来自世界各地的好人汇聚一堂,教师、作家、农民工挤在战壕里……年轻的士兵们抛弃了自己的部队。他们唱着的歌曲是多么动听!在他们看来,勇敢的孩子是历史的宠儿,他们挥舞着带银角皇冠的白旗。
然后他们输了。
政变被粉碎。无政府主义者被堆在格里特布鲁高原上的万人坑里。康米主义者在格拉德岛被击败,退守萨马拉,成为了官僚统治下的堕落工人国家。三十五年后,那对革命伉俪的失踪案终于有了结果,里切·勒庞八岁大的儿子尤金在一次周六傍晚的郊游时,在一个无名的奥松涅岛的海岸边发现了阿巴达奈兹与多布雷夫紧紧拥抱在一起的骸骨。尤金穿着短裤,拿着捕蝴蝶网,站在那困惑地看着这些来自过去、紧紧地贴在一起的骸骨。褪色而光滑。从哪里起是第一副骨架,另一幅骨架又到哪里结束?时间把它们像洗牌般混在了一起。之后,里切在那里建起了一家酒店,以及一个如今世界闻名的健康中心。
但最大的失败并非马佐夫的全球革命以流血和失败告终,也不是革命伉俪的尸骨如今被摆放在芳香疗法候诊室里。随着内部动乱被镇压,格拉德成为了世界强国,一个巨大的国家。它的城市欣欣向荣,发展的光芒就像轨道上的卫星网络一样闪亮。像齐姆斯克这样曾经拥有众多马佐夫支持者的国家,整个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人民则被贬称为"克吉克人"。时间久了,他们甚至都开始这样称呼自己了。
特雷兹·玛基耶克今年七岁。他的父亲是一名模范克吉克人、一名外交官,也是一名篡位的马屁精。他还没有带特雷兹去瓦萨上学。这座城市是一场生态意义上的灾难,是后大都市时期、前死城时期的人类居住区,正处于发展的倒数第二阶段。聚合材料在 齐姆斯克和南格拉德的边界蔓延开来。这个怪物吞噬了齐姆斯克的历史中心——弗迪德莱克的皇家古城和伦卡的松树林公园。夏天开始了,在昏暗的地窖里,一个名字被低声说出。孩子们在院子里喊着这个名字。树叶在宁静的街道上沙沙作响,只有那个名字的回声在格拉德民兵的耳边回荡:
“无畏者弗朗蒂切克……“
他是最勇敢的科伊科人、电影明星、革命家。就在不久前,春季的暴乱被残酷镇压,现在已经两个月没有他的消息了。据说他潜伏在遥远的针叶林里,在雅库特人的保护区里,并从土著祭司那里获得了特殊能力,奇妙的能力!他那草原雄鹰般的颧骨、渴望的目光、温和的微笑,仿佛针叶林中升起的太阳。只有在他严肃的眉毛因忧虑而皱起的罕见时刻,他才会露出这样的笑容……他勇敢的面庞成为了针织品工厂的禁止图案,但勇敢的女人们会将其将缝在从背心到内裤的白布上。不,勇敢者弗朗蒂切克在萨马拉!正在谈判。他要和人民共和国的军队一起来了!别天真了,弗朗蒂切克远在科拉,在冬季环线上,在依格努斯·尼尔森的小屋里,他们永远也找不到他!安静!勇敢的弗朗蒂切克不会躲起来的!就在昨天,有人看见他在排队买肉,他现在留着假胡子,穿着屠夫的围裙,他自称夫佐马·斯拉卡,倒过来读!
但几个月过去了,他还是音讯全无,秋天很快到来。工业粉尘像哀悼的面纱一样落在金色和红色的树叶上。十月,齐姆斯克开始流传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安静而胆怯。勇敢的弗朗蒂切克在垃圾箱后面被枪毙了。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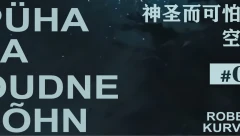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4 条评论热门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