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文系用户投稿,不代表机核网观点
5. ZA/UM
5. ZA/UM
安妮-艾琳·郎德摘下她的太阳镜,突如其来的亮光让她什么也看不见。一阵绯红而深蓝的漩涡在女孩的瞳孔里卷起,溅落在她的瞳孔上。她的烟熏眼妆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发亮。安妮小巧的头像小猫般灵巧地转开,而那道光线仿佛一只兔子,随着女孩的眼睛,从一本少女向的杂志蹦到了沙滩上,又从沙滩蹦上了遮阳伞。
“怎么了?”特雷兹问道。他的腿悬在悬崖边上,荡来荡去。
“我不知道,茉琳现在也在那儿。她正站在……”
“我从这儿也能看出来她正站着。”可汗不耐烦地打断道。
“她正站在那儿,而且不得不承认,那件有红色波点的泳衣在她身上看着也没那么糟。那件泳衣是两件式的,这好像是现在的潮流,而且,噢!她现在……该死的!”茉琳的笑容透过望远镜看起来有些诡异,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恶毒的喜悦。她抬起手,示威般地挥了几下。杰斯珀把那个诡谲的镜片藏在腹下,画面随之消失。
“趴下!所有人,都给我趴在地上!”
可汗半卧倒在带刺的玫瑰果灌木丛中,他能听见血液在耳朵里奔涌,手臂上的血管也阵阵搏动。特雷兹则直接迅速背朝下躺倒,仰面望着六月苍白的天空。
“快看,可汗,有只鹰!”
“什么他妈的鹰——噢!”玫瑰果灌木丛尖锐地提醒着可汗它的存在。
“别乱动,你会把灌木丛弄出响声的。”趴在中间的杰斯珀抱怨道,望远镜还被他握在手里。
“好吧,但如果她们都已经发现我们了,那就算我弄出声音也没什么关系了。嘿,快看看她们现在在干什么!”
“自己看。”杰斯珀把望远镜滑向可汗。
身穿松垮夏季衬衫的可汗手握望远镜,蠕动着爬出灌木丛,灌木丛随着他的动作沙沙作响。他扬起头,同时试着把自己藏在高高的草丛里。他急匆匆地把望远镜向下对准沙滩,先看向红花阳伞,然后停在旁边的沙滩巾上。出乎他的意料,他只看到了小玛吉坐在那儿朝前看着。汗水滴落在可汗的镜片上,担忧涌上他的心头。他有预感般地把目光移向底部的岩石。仅一百米开外的地方,一副用来看歌剧的小望远镜正透过他的镜片,直勾勾地盯着他。那是夏洛特,她是姐妹中的老大,身材瘦高,单手叉腰,一头乌黑的秀发随风飘扬。这位来自九年级、美丽而可怕的生物对于身为移民的可汗来说,就和议会的一个席位一样遥不可及。但现在她离得如此之近,即使不戴茉琳的歌剧望远镜,她的目光也能刺穿可汗那双可悲的眼睛,那双他现在想要用望远镜来遮住、而非放大的眼睛。
“天呐,她们带了一副小望远镜。”可汗在紧急会议上说。
“她们昨天就指着这里,我注意到了,本来应该告诉你们的……”
“什么,特雷兹?”杰斯珀突然变得怒不可遏,“所以她们知道,而你刚刚让我们径直走入了这个陷阱!”
“我忘记了,抱歉。我以为她们可能是想看看那只鹰。你知道的,它的窝就在这个崖边……”
“你该把那只鹰直接塞进你的屁股里!”可汗被这句话逗得大笑,而杰斯珀则继续说:“现在我们该做的就是站起来,向她们也挥挥手,这就算结束了。我不知道我们该怎么解释这场望远镜滑稽秀,我真的不知道。”
“我有个主意。”特雷兹坚定地站了起来,而可汗则扯住了他的裤腿。但不久之后,这三位在下面的沙滩上聚在一起的瘦高女孩们,就看见了一个瘦巴巴的金发男孩,随后一个稍微有些肥胖的伊尔玛男孩略显尴尬地站在了特雷兹旁边。
“你们好,小姐们!”特雷兹呼喊道。他高大挺拔的身影从四层楼高的岸上一跃而下,茉琳惊呼一声,捂住了自己的嘴巴。
第二天早晨,二十年后。
男人眼角疲惫的线条在颧骨上勾勒出弧度。他的眼睛下方有两个尖尖的突起,如同猛禽一般。两侧的脸颊因为等待和担忧而凹陷。联合警署办公室的百叶窗早已在他的眼前拉上,遮住了他恣意妄为的有色瞳孔;没有人可以透过这扇百叶窗看到后面发生的一切。这位联合警署探员的胡须刚修剪过,略微向前伸展,脖子苍白修长,因吸烟而苍老的皮肤上覆盖着白色的礼服衬衫,一条黑色的细领带从衬衫的领子上垂下。下了一整夜的雨已经停了,但天气仍然寒冷而有风。他用左手把大衣的领口拉紧,用右手拿着烟,抽了一口。
特雷兹正这样站在一艘边境巡逻小船的船头,他身边的另一位年轻瓦萨军官手里捧着热气腾腾的咖啡杯,问道:"喀琅施塔得有什么?”
“不好意思,我不能回答这个问题。”特雷兹机械地回答,仿佛在喃喃自语。他的眼睛盯着远处秋日的地平线。小船的引擎"咔哒"一声启动,一群海鸥从港口的芦苇丛中惊起,在冰冷的水面上发出尖锐的叫声。一阵燃油的气味飘来,某种化学物质在水里形成了彩虹。
“来点咖啡吗?”那位年轻人想要重新捡起话头。
“不了,谢谢。”
特雷兹感受到了落在脸上的水滴。清爽宜人。今早低垂的灰色天空中看不到太阳,只有飞艇的灯光盘旋在城市上空,而格拉德号大型巡洋舰钢铁的轮廓则悬挂在海湾中,仿佛一只幽灵。
亚恩斯班肯[1],这是他们对它的称呼,钢铁的幽灵。没人喜欢这儿的那些不详之船,就像见了鬼。他们在保持戒备,是的,但是是针对谁?谁又对谁宣战了?没人。而格拉德号,没法用它的钢铁庇护在这里赢得任何人心,甚至是特雷兹这个有着普通北方人长相,但说话和抽烟的方式都像格拉德男人的心。他会提起自己的祖国齐姆斯克、百年占领,以及“尤戈-格拉德大屠杀”,还有无畏者弗朗蒂切克,但却都谈不深入。
他当然想成为像无畏者弗朗蒂切克那样的人,现在仍然如此,每个克吉克人都想成为无畏者弗朗蒂切克。占领土地,崛起,再次升起西吉斯蒙德大帝[2]的旗帜;充满魄力,拥有隆隆行驶的三驾马车般的人生快乐。
发生什么了?
一只孤零零的边境巡逻艇正在横渡北海,海浪猛烈地摇晃着船身。不久,特雷兹就为了不在甲板上滑倒而不得不扔掉他的香烟。抽烟的环境这么糟,再继续站在外面发抖也没什么意义了,于是他走回舱内,坐在一张长椅上。他尽力不去看夏洛茨扎尔,那座坐落在蜿蜒海岸线上的城市。噢,他是多么渴望去那儿。有次他乘坐灰域磁力列车从4000公里外的格拉德回来,但没有告诉可汗或者杰斯珀,而是径直走进夏洛茨扎尔,就像个傻子一样坐在那,然后就回家了。穿越灰域又消耗了他一周的时间。他和杰斯珀那时还正因为在餐馆发生的那件事处于冷战中,而只和可汗出去闲逛也有些没意思——那是两年前他的冬至假期,那就是他的*旅行*。警署的精神科医生对他施以一年的旅行禁令。如此频繁地穿越灰域实在是太危险了。
玛基耶克嘴里咬着止血带,用金属和玻璃制成的注射器扎入手臂上清晰可见的静脉。
但他仍然想要看芦苇被风吹得弯倒,海水温柔而沉静地涌上海滩,那实在是太美了。遥远的海雾中显现出一座陡峭石壁的轮廓。还有那里的水,冰冷的水。雨滴。太美了。
特雷兹用青筋纵横的手深情地摩挲着放在膝盖上的黑色手提箱。
“哈德拉穆特卡赛![3]”小印纳雅·可汗呼喊着从山崖的边缘跳下。阳光洒落。他的腹部传来刺痛,仿佛还要坠落几百米,但下落的过程只用了一瞬。霎那间,他的脚就砸在了沙地上。他把鞋跟跺进沙子里,下滑的速度在几秒内减慢。小可汗能感受到树根戳着他的屁股,石头刮擦着他的后背,衬衫从裤子里翻了出来,眼镜也从脸上掉下。长着雀斑的特雷兹欢呼着冲了下来,女孩们也跑向他遍体鳞伤的躯体。
"你疯了!"安妮惊呼道。确实有理由欢呼。
但对小杰斯珀来说却不是这样。他现在正独自站在那儿,注视着悬崖、他的白裤子、水手服,然后又再次看向悬崖。
“算了。”他撅起嘴唇,收拾好可汗留下来的背包,选择走穿过森林的那条远路。他全速前进,步伐暂时还没变成某种不体面的小跑。男孩从松树遮蔽着的小径转上两座山丘之间的吊桥,然后下到另一边的木板路。前往沙滩的这段路程似乎会永远走不完。他已经想象到了那个愚蠢的可汗恐怕现在正在胡扯些什么。而他现在该如何不协调地加入对话呢?
仅半小时之后,杰斯珀到达了下方的海滩,无助地站在女孩们空无一物的沙滩毯旁。
“不好意思,您看见从那边跳下来的男孩子去哪儿了吗?”他指向背后的崖壁。女孩们让老人帮忙看东西。杰斯珀认为无论他们去了哪儿,都很快会回来。在炎热的太阳下沐浴了一会儿后,他在印着花朵的沙滩毯上坐下。天气越来越热了,在纠结他该不该脱掉自己的衬衫之后,他决定要有品位地躺在沙滩毯上,越*酷*越好。这个姿势的炫酷之处在于他双臂交叉枕在头下时所表现出的漠不关心。杰斯珀现在对云朵更感兴趣。他已经陷入沉思。他正在思考。
随后,他的鼻腔被一阵细微的、原子级别的香气所触动。山谷里的百合花、呼吸、人类的皮肤在他的眼前溶解。杰斯珀转过头,越过平坦的沙地,他看见了:一个由芳香、异物、少女气息组成的世界。那里有白色和其他素色的夏季连衣裙,上面系着过于整齐的领带、小腰带、毫无用处的小装饰、以及安妮精致的手镯;在那个编织篮子里放着的也是那种女生会喜欢的食物。杰斯珀不太记得都是些什么了,但他肯定量都不多。女孩子们不喜欢吃东西。杰斯珀知道这些。
在一种愚蠢的迷恋之中,他抬手拿起了从小包中露出来的小瓶子。这个香水瓶的外形像是一个石榴,金黄色的液体沿着莓色的玻璃流淌,杰斯珀看得出神。那个世界消失了,但他仍然拿着那个瓶子。出于他自己也不理解的理由,他偷偷地把里面的一条发带装进了自己水手服的胸前口袋。他重新躺下,透过玻璃瓶看着太阳。在很短暂的一瞬间里,他仿佛进入了石榴里的莓色世界,但突然,夏洛特的长腿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耸立在他面前。小玛吉越过特雷兹的肩膀直勾勾地盯着他的眼睛,问到:“安妮,他拿着你的瓶子干嘛?”
魔咒解除,杰斯珀头脑里火星四溅的突触开始建立起连接,他让自己一点惊讶也不表现出来。
“瑞瓦肖产,”他发音饱满地开口,随后像个老炮一样继续说,“格拉纳特三号,非常好的选择,香气浓郁、浑然天成,杜松子还带来了一种空灵的感觉……选的真好,我还能说什么呢。你怎么想,安妮?”
杰斯珀安染自得地坐了起来。可汗和特雷兹兴奋地看向女孩们的方向,尤其是安妮,她正面带微笑,舔着一支青柠味的冰淇淋。
“我的意见?好吧,”她说道,语气从刚开始的尖刻逐渐变得礼貌,“您的母亲是一位调香师,对吗?”
“最近倒更像进口而非生产了。但她确实有一些文件和那些玩意。你知道的,我去过瑞瓦肖香水厂,在那看到了格拉纳特是怎么被蒸馏出来的。”
“你还去过瑞瓦肖?!”甚至连夏洛特都被惊到了。她是学校里某种女神般的存在,高一个年级、穿着昂贵的衣服、身边跟着高中的男孩。而现在这位女神的双目也因为惊诧而睁大。杰斯珀的耳朵红得仿佛着了火。
“是的,去过一次,我妈的同事邀请她去旅游。”
之前一直脱颖而出的人,特雷兹,认为现在最大的危险已经过去,该让杰斯珀变回普通人了:“难怪你闻起来像朵花!”
这个男孩的每一句话都引得坐在特雷兹肩膀上的小玛吉哈哈大笑。他很幸运。特雷兹从不觉得自己是什么孩子王,但那次惊险的跳跃已经让他受人尊敬了三刻钟。而可汗则毫无用处。他能抓住特雷兹三分之一的话头,但却不知道该怎么接下去,于是只能嘟嘟囔囔。
安妮坐在脸红了的杰斯珀旁边。“我觉得杰斯珀闻起来不错,一点也不像是臭袜子或更衣室。”
“这也太糟糕了!”茉琳和善地说。
“其实这都是冯·菲尔森的错,”可汗第一次射门得分,“菲…菲尔森有很多运动袜,它们闻起来可不一般。”
特雷兹释然地叹了口气。冰淇淋摊前的队伍已经很长了。可汗和特雷兹都不是在紧急情况下能言善道的人,因此打算在杰斯珀来之前都先避开那个话题。幸好玛吉出来救场了,她要求要坐到特雷兹的肩膀上,而她的喋喋不休逗得大家大笑。
特雷兹觉得现在终于是处理那个问题的时机了。他把玛吉从自己的肩膀上举了下来,暗示性地盯着杰斯珀,故作自然地提到:“你带着那些东西吗?香烟?望远镜?”
安妮-艾琳没有被有关“香烟”的事情所吸引:“你们在那拿着望远镜干什么呢?我们昨天就一直看到有东西在闪光,就像一面小镜子。这真有趣!”
“啊,只是在观察鸟,你知道的,有一对海雕在这里筑了巢……”特雷兹几乎没法说下去了,因为茉琳冷笑着重复道:“观*鸟*呵。”
安妮在杰斯珀旁边咯咯地笑了起来,而夏洛塔,这位邪恶的女神,则说得更加尖锐:“确实,观鸟的确是最近绅士中流行的活动。”
杰斯珀的脸红得发亮。但在玛基耶克脸上雀斑的缝隙深处,无畏者弗朗蒂切克抬起了头。是时候了!他冲向特雷兹,毫不顾忌,冲向那最耀眼但也最不可能得到的奖品。第五代克吉克人的传统就是:要么全赢,要么全输。
“我的小鸽子[4],”特雷兹·玛基耶克带着富有魅力的微笑说道,“或许我们看见了十分罕见的鸟。”
通常情况下,“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对我们这些克吉克人来说意味着全输,但今天——二十年前炎热明媚的这一天,不是这样。夏、洛、塔!她丰润的肩膀向前移动,锁骨显露了出来。在她眉毛构成的弧形之下,原本冰冷的绿色眼睛随着笑容亮了起来,仿佛远星射出的光芒。这是因为特雷兹。
它在说:“有机会!”
特雷兹真是太开心了!一切都进展得那么顺利!影子逐渐拉长,时间流逝,白色的沙滩变成了黄色、随后是橙色,上面画着阴影构成的条纹。女孩们把沙滩毯搭在肩膀上,小玛吉打了个哈欠,盖着毯子睡着了。风逐渐减弱,四周静了下来。一个王国。轨道马车在远处运行,轨道嘎吱作响,远处某人院子里的音乐飘来。海滩变得空空荡荡,天空则形成了由蓝色向紫罗兰色过渡的渐变梯度。特雷兹和女孩们说了他父亲的外交官别墅、夏天的计划,以及明天的打算。更衣室立在沙滩上,阴影投下,像是钟表的指针。条状的云从平静的水面上升起,它们有着淡紫色的腹部,靠近地平线处则是青色、洋红和冷却后的橙色。茉琳试着戴上了可汗的眼镜,而可汗透过茉琳的大墨镜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女孩的轮廓若隐若现,仿佛上下颠倒的烛焰。
“带点苹果酒来!”安妮-艾琳在车门关上前喊道。四匹苍白的马从原位猛然冲出,车厢在黄昏的暮色中闪烁着黄色的光芒。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天使般翅膀的小玛吉睡在茉琳的大腿上。一支仙女的魔法棒从她的手里滑落,掉在了车厢里满是沙子的地上。
马车在转角处拐弯,从视野里消失,三位站在车站的男孩互相做了一个如释重负的表情。
温暖而酸臭的呼吸吹动了这位油地毡销售员嘴边的酒店白色亚麻床单。
油地毡销售员。油地毡销售员。油地毡销售员。他将左手放在自己的脖子上,把油地毡在脖子上缠了两圈,然后打了一个结。这个结错综复杂,而且打得非常好。八楼的阳台门还是坏的,凉爽的空气正在渗入哈弗桑拉里酒店的房间里。从阳台上向下能看见夜晚海滩上壮丽的景色。阳台芦苇编织的地板上放着一台带有反射箱的望远镜,它表面覆盖着保护色的涂装,现在从底座上拆了下来。侦查型号。望远镜的后面放着一台改装过的相机。这些东西被放在这个阳台上,而且只在这个阳台上,而非隔壁房间或者走廊上,因为那不是这位油地毡销售员行事的方式……所以只有在这里的这个阳台上,他才能听见恶魔紧张的喘息声。
二十年后,晚上。
维德昆·希尔德透过审讯室装着铁栏的窗户盯着一位痛苦的联合警署探员。真是卑鄙。希尔德穿着灰色囚服。反光条上写着“维德昆·希尔德”和他的囚号,附有字母缩写。探员脱下他的夹克,随意地扔在窗前。他动作不协调,衬衫腋下有汗渍,胸前别着一枚新印制的访客身份识别徽章。 风扇发出嗡嗡声。
“嘿!你——喝——醉——啦——!”维德昆越过他的肩膀,看着正在门口值守的警司,“酒味正在钻进我的脑袋……请把我放出去,我现在没心情。”
维德昆听着玛基耶克和狱警对话的片段,露出了诡秘的笑容。
“五分钟……十分钟……一名儿童的生命正遭受危险……”
警卫背后的门关上了,一把有着奇怪构造的钥匙在特雷兹手里一闪而过。
“玛——基——耶——克——,”维德昆读道,“你是克吉克人!你像是个格拉德人,某种二流的低级生命形式。”这次希尔德的手臂和腿都被铐起来了,弯曲着他手臂的巨大钢铁硌得他后背很不舒服。但除开这点,他不知怎么坐得仿佛一个高尚的人。
“你撒谎了。这张画是你从谁那儿拿到的?”特雷兹的双眼视线模糊,他愤怒地眨了眨眼。
“听着,你听说过那些优生学的研究吗,那里面称赞了克吉克人的谦逊。”
“你是从哪里得到这幅画的,贱猪?”
“有一个学者——你知道吗——提议将你们人种和黑人进行配种,来获得最佳的苦力。”
“闭嘴!”特雷兹突然拉下了问询室窗户上的铁制挡板,挡板哐地落下。门外立刻传来狱警紧张地把钥匙插入锁孔中的声音。
“蠢货!你是想去坐牢吗?在这里我们要遵守*宣言*办事,不是格拉德的那种无政府状态!”
在这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里,在房内钢铁的光辉中,特雷兹·玛基耶克站在一张桌子旁,打开了他的公文包。公文包的内胆里正好放得下一个铁盒子,盒子上用白色字母写着“ZA/UM”。
希尔德因为恐惧而瞪大了眼睛。门后传来砰砰声。
“你没有使用它的权限!你必须要有权限!给我看你的许可!”
“你在说什么?我听不清,有只贱猪一直在乱叫。”特雷兹用铁盒砸向希尔德的脸,血液泼在了灰色的囚服上。
希尔德哀嚎了起来,鼻子上露出了一小块白骨。这个男人气息微弱,门后传来压低的威胁声,但特雷兹的钻石钥匙在锁上叮当作响。
“我是国际联合警署格拉德米洛瓦分部的探员特雷兹·玛基耶克,我依法享有审讯的权利。如果你再乱动那扇门的话……”门上的敲击声停止了一瞬间,ZA/UM咔地打开。可以说,一切都发生得迅速而熟练。特雷兹从盒中的泡沫垫里拿出连着着输液针的发黄管子,用皮带将一个怪异的风箱形装置固定在他的手腕上,然后将橡胶管拉紧缠在维德昆·希尔德铁甲般的手臂上。他轻微晃动管子,随即旋在装置上,然后将针刺入维德昆的静脉。一滴希尔德红色的超人血液直直流入管中。
窗上铁制挡板的后面传来跑动的声音,沉重的靴子踩在监狱的地上。增援来了。装置的盖子在玛基耶克的手腕上咔地打开,里面出现了一排小药瓶。药瓶里盛着黄色的液体,像是在上唇下排着沾满烟渍的假牙的人,皮笑肉不笑地咧开嘴角。轻微的嘶嘶声之后,第一个药瓶咔地就位。盖子上方的风箱颤动了一会儿,玛基耶克手腕上的装置随后开始发出轻微的喘息声,仿佛一只宠物。黄色的仿佛尿液般的液体被泵入维德昆·希尔德的手腕。他睁开了眼睛,发出惊恐的喘息声。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阉猪?”特雷兹对着维德昆肿胀的脸,从牙缝里挤出这句话。
男人嘴里血和唾液的混合物溅在了玛基耶克的脸上,他恐惧地转动眼睛,哭喊道:“我撒谎了,你说的没错。我……我从没见过他们,我的狱友……”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
“我什么也不想,我是在告诉你,我有一位狱友,在几年前,他叫迪里克……”
“我不在乎你怎么想,我想要你知道的真相。”特雷兹眼球凸出,一把扯下维德昆手臂上的塞子,因麦斯卡林和麦角酸[5]而胀起的静脉明显收缩。
顿时,维德昆咬紧了牙关,紧得仿佛要把牙齿咬碎,“你不可能从我这里得到任何东西、现在没法从我这得到任何东西,”他语无伦次地说,“我是如此强大!”
门后传来破门锤的撞击声。
“我很喜欢你这样的想法。如果你能这样想就太完美了。”特雷兹喘着粗气,将另一根输液器接到设备上。这是给他自己的。他盯着自己的手腕,将针刺入静脉。
第一个药瓶空了。特雷兹和维德昆共享了第二瓶,他的嘴里开始蹦出亢奋的胡言乱语:“这是一台绞肉机。你根本想象不到现在我会用它把你干得多狠。”尿黄色的液体突破了维德昆的血脑屏障。一阵巨大的压力开始在他的脑袋里、在他的颅骨下积聚,仿佛吹起一个泡泡。
特雷兹用手紧紧按住男人的脸,开始尖叫起来。他的声音像是白噪音一样传进希尔德的脑袋,这是纯粹的嘶吼着的暴力。
“我会把你变成一个傻瓜,你感受到了吗?”
维德昆的头皮屈服于了这位探员双手施加的压力,像鲜花一样绽开,仿佛什么东西正从其中娩出。维德昆的手铐无助地发出哐哐声,他想要用手抓住这些正在从他的脑袋里喷涌而出的物质。他的几块脑组织还是从指尖滑落到了地上。他没法抓住,实在是太滑了,而且太多了。
“我能看见你的▢了,它在我面前大开门户。我要把你掰开。”特雷兹喘着粗气,看着维德昆·希尔德的一切在他面前打开。
这个人在特工的尖锐手指下颤抖,拼命想要说话,告诉他自己在寻找什么——用人类的语言说出来,但他的嘴不再听使唤了。而与此同时,在特雷兹像水中的老虎般在他脑海中跋涉时,维德昆只能看到从特雷兹的镜子中反射回来的一幅画面。在那个冷酷的表面上,维德昆逃离了脑海中毁灭性的屠杀,夏洛特·郎德深绿色的眼睛注视着他。在瞳孔的深处,特雷兹获得的机会闪闪发亮。这是如此的美丽而又无限哀伤,当特雷兹在审讯桌后筋疲力尽地倒下时,维德昆开始哭泣。
瓦萨城的海岸在他面前闪烁,夜晚的海浪拍在边境护卫船上,涌到他的脚边。遥远城市的上空有一圈黄色的光晕。那些白色和黄色的光,似乎融入了特里兹的手中,带来了无法言喻的喜悦。外面很冷,但他没穿外套。他的夹克被风吹开,维德昆·希尔德溅上来的血仍然在他的白衬衫上。这位联合警署探员的手被舒适地拷了起来,一名年轻的警官扶着他站在甲板上。
“你在那儿犯了什么淘气?”警官问道。
“如果我为你写了一首交响乐……”晶体管收音机里传出沙哑的音乐声。
“嘿,谢谢你能带我出来透气,今晚真美!”
“没事……”警官露出了无声的笑容。
“请问您能把这首歌的音量调大一些吗?”
“什么?”
“我保证我不会跳船的,帮我调大声一点吧!”
“我更担心你会掉下船,不过好吧。”警官走进了船舱又走回甲板。在海浪和引擎的噪音之上,厚重的节拍和男人的假声响起:“如果我为你写了一首交响乐,来证明你对我是多么重要……”特雷兹开始用脚打起了节奏,只有在使用“ZA/UM”之后他才能感受到这样的放松。他叹了口气,对警官说:“我刚刚解开了郎德家孩子们的失踪案。”
“什么?”
“你不知道吗?这是一件很有名的案子!”
“什么时候的事情?”
“噢,那是很久之前,你还没出生。但这不重要,我现在感觉好极了,我破了这个案子!”特雷兹笑了。那是充满黑暗的笑容,但又是真诚的,非常真诚,北海之上的夜空也对他回笑。
译注
译注
[1] 亚恩斯班肯,原文此处为瑞典语“Järnspöken”,义为“钢铁的幽灵”,常用于描述工业遗址等,此处为其音译。
[2] 西吉斯蒙德大帝 (Sigismund the Great),欧洲历史中有同名人物,为神圣罗马帝国的一任皇帝(1433至1437年在位)。
[3] 原文此处为“Haadramutkarsai”,似乎并无特定含义,只是某种呼喊时随意拼凑的音节,因此作音译。
[4] 此处原文为波兰语“Goląbeczko moja”。
[5] 麦斯卡林和麦角酸(mescaline and lysergic acid),两种致幻剂。
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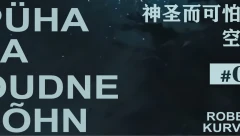





评论区
共 8 条评论热门最新